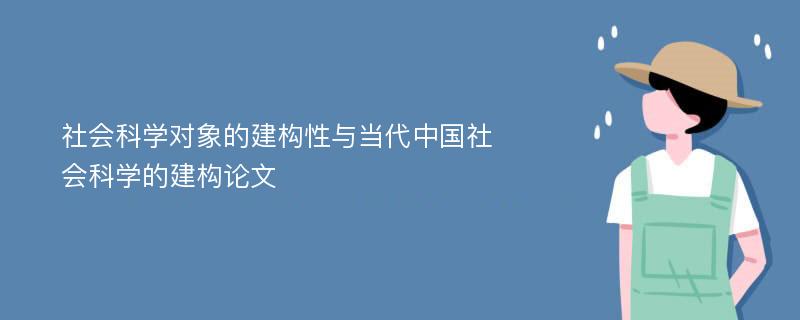
社会科学对象的建构性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
文/王南湜
社会科学是19世纪以来应社会现代化的需求而在西欧率先现代化的诸国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不同所带来的问题不同,适应于此,所发展起来的社会理论或社会科学也便有所不同。中国社会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也正呼唤着能够对这种变化进行深刻认识,并对这种巨变所带来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作为对这一呼唤的回应,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也正处于进行时。在这一进程中,有两种偏向可能会损害其健康发展:一种是基于对自然科学之客观有效性的误解,将社会科学亦看作是一种对客观的普遍规律的把握从而具有普遍适用的事物,而既未看到自然科学客观有效性之意谓,更忽视了社会科学因其所在之社会的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而具有的对象及方法的独特性;另一种则是过度强调社会科学之由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而将之理解为了一种不再具有科学的客观有效性的东西。前者可能导致的问题是,从一般性的原理出发所建构的理论无法真正切中中国社会的问题;后者的问题则在于可能导致社会科学成为一种相对主义的对于不同社会之表观特征的文学性描写,而无法提供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失去其科学应有且为社会所需之功能。克服这两种偏向之道并非另行提出某种与之全然不同的进路,而在于重新认识马克思建构作为社会科学之典范的《资本论》的方式方法,深入考察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近代科学的“科学性”之意谓,特别是这种“科学性”或社会科学对象的建构方式,进而揭示出科学性与民族性在社会科学理论建构中各自的位置,从而使之各自在其中发挥应有之作用,协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建构。
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之意谓
社会科学既然比肩于自然科学而被冠以“科学”之名,那么,循名责实,弄清其“科学”或“科学性”之意谓,便是我们当下考察的首要之事。毫无疑问,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是有显著差别从而是需要加以区分的,因而这一区分如果只是要揭示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之特质的话,无疑是十分合理的。但若是为了追赶某种最新潮流,一股脑地将社会科学从“科学”的领域中清除出去,使之成为一种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的东西,则是极其不合理的,且对于正处在社会科学建构之初的中国学术来说,更是极其有害的。
利用品管方法的目标值设定公式,对我院收治的规律透析的90例患者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发生率进行目标设定。设定患者动静脉内瘘穿刺渗血发生率为3.86,设定理由:拟定圈能力为60,按品管圈方法给出的公式计算出目标值=现况值-改善值=现况值-(现况值×圈能力)=9.65-(9.65×60)=3.86[4]。
为给社会科学之“科学性”正名,首先须给作为科学典范的自然科学之“科学性”正名。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以来广被推崇的科学典范,如果对比于古代“科学”,其“科学性”并不在于它是对于客观的自然规律照相式的纯粹描述,而是在于近代自然科学是指向改变世界的,是对于改变自然世界的规律之描述。
社会科学是仿照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牛顿力学而建构起来的,因而,其“科学性”也就不可避免地类同于自然科学之“科学性”,亦即并非对于社会世界超然的解释性描述,而是亦指向改变世界的活动。相应地,社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亦只能从马克思的立场上理解为实践中的客观有效性。如果说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起初还尚未明确地指向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而只是在后来才匹配于工业生产之发展从而起到改变世界之作用的话,那么,自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则可以说已经有了明确的指向对于现实社会生活中问题之解决的特征。这一点在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三大社会理论创始人那里有着特别突出的显现。此点诚如吉登斯所言,“马克思构思自己的著作,是旨在建立一个实现特定实践的平台,而不仅仅是对社会进行学术研究。涂尔干和韦伯也是如此,尽管它们并不是以一种可以完全比较的方式来进行的。他们俩著书立说,旨在预防他们所认为的现代人必须面临的最紧迫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且企图提出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212页)而这种不同,又是缘于他们各自所面临的问题的不同。
显而易见,三大社会理论创始人的社会科学理论建构方式,已充分表明了社会科学之真理性正在于其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中关联于不同问题及其目标的客观有效性。尽管这种客观有效性与自然科学之客观有效性有重要不同,但在与现实实践的关联这一点上却是根本一致的。这也就启示着我们,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必须关联于当代中国现实实践中的问题与目标。
社会科学对象的建构性
正是源于与自然科学目标之齐一性不同的社会科学这种目标的差异性,致使社会科学后来的发展显著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同一性,而呈现为多向性,其原因主要是源于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三位理论大师理论资源的学派差异性。
渐进成形回弹和冲压回弹不同,渐进成形回弹是工具头在加工一层等高线后,工具头卸载,加工区域的载荷消失,使得板料发生回弹。以后每一层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复合成形回弹是渐进成形和拉形载荷卸载后共同作用引起的回弹[7-9]。以实际加工轮廓和建模理论轮廓之间的夹角为回弹指标,进行回弹量的测量。回弹现象示意图如图7所示,选取加工深度、成形角度、拉形高度、层进给量、进刀方式等5组工艺参数进行试验,在不同工艺参数下测量回弹角的大小。
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对象都是建构而成的。自然科学的建构性在于其本质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或“订造”的技术,亦即自然科学的对象建构正是建基于技术的结构之上的。而技术作为人之改变世界的活动,其中的关键之处,乃在于工具的使用。如果科学的本质乃是技术,那么,凝结着技术的工具体系,便构成了科学理论之原型。换句话说,所谓科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正是对于现实实践中所建构的工具体系之符号化的再建构。同理,社会科学仿此也可以说是对于人所创造的社会世界之内在结构的符号化。在此,作为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或社会体系正类似于作为人与自然之本质性关系的工具体系。
对于社会理论之基本问题的解决,涂尔干抓住了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但却忽略了个体的能动活动,而韦伯正好相反,从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出发,却未能成功地达到客观性。两种片面性的存在,似乎昭示着有必要进行某种综合。
涂尔干、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差异之意蕴
3.想象诱导。对文章中比较抽象简略的内容,让学生结合经验加以发挥,或设身处地的进行具体描绘,或补充事实化虚为实。用这种方法,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充分展开想象,从而使沉睡在学生大脑皮层中的经验得以调动或“激活”。《狼和小羊》一文的结尾是“狼扑向小羊”,狼扑向小羊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可让学生展开想象去叙述一些惊险的情节。
主动探测辅助获取最新的恶意URL,则可定期遍历恶意放马服务器文件的变化,端口变更。对恶意URL可以持续周期性探测获取活性和可能的样本。
相对于自然科学之本质的技术性,社会科学理论之本质亦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改变社会世界的“社会技术”。若社会科学理论之本质也是一种“社会技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中介或手段,那么,社会科学理论所建构的对象的差异性又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某一特定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该社会总体上所存在需要解决之问题,另一是该社会中不同群体目标的差异所导致的对于所欲解决问题认定的差异。前面提到的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理论之差异,便既源于三位理论大师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亦源于三者所追求社会目标的不同。
马克思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优越性
限定了科学的领域之后,进一步的构造科学对象的工作便是具体地实现从主体行动的逻辑向客观结构的逻辑的转换。这一转换工作是在《资本论》第一卷“商品和货币”篇中进行的。在这里,就从抽象的人类劳动建构起了价值概念,而抽象的人类劳动又是包含在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之中的。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价值概念被奠定在了人类活动或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于价值形式发展的辩证分析而引导出或演绎出了“货币形式”这一“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从而由此构建起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结构。在此,货币作为有特殊形体的或具体的普遍之物,它对于各个特殊存在的商品之间的支配关系所构成的经济结构,不仅作为将矛盾“打包”封闭于其中而为科学对象的建构奠定了确定性的基础,同时还在于通过货币所构成的商品经济结构这一概念,马克思揭示出了这一结构对于人们的经济活动的整体支配作用,亦即在此范围内活动主体对于经济结构的从属性,即“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这样,对于人的经济活动的研究便不是直观地描述其经济活动,而是描述支配着经济活动的具有决定论性质的客观结构。这就在理论上实现了从主体行动到客观结构的转换,使得科学对象得以成立,并进而由之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下降规律这一整部《资本论》的核心命题。
马克思社会科学建构的出发点是“人是对象性活动”和对于将哲学指向“改变世界”的呼吁。进一步的问题则是如何从“人是对象性活动”这一主体行动或能动的逻辑转换到适合于科学所要求的概念的确定性的客观结构的逻辑。如果具体以《资本论》这一社会科学的典范为例来说明的话,那么,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建构对象的理论区域。这一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那就是,在这里马克思也是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亦即数学的精确性限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构造对象的方式。
妈妈60岁大寿时,我给她办了一个生日派对。派对上,我鼓足勇气,说我很钦佩她。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一会摇头一会点头。那天,她非常开心。
社会理论建构的方法论的核心问题,是以何种方式解决人的能动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客观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源于社会世界之不同于自然世界的存在方式:人类社会是由追求自我目的的人的能动活动所形成的,但人的活动所形成的社会一经形成便又具有不以人们的任意意志而转移的客观性。如何理解和处理人的能动活动或人的自由与社会结构的客观性的关系,便构成了任何社会理论所必需面对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对于社会理论之所以具有根本性,乃在于这一“二元对立的概念范畴,是社会学试图理解和把握以下两个过程之间微妙关系的产物:一方面是社会对个体的影响(结构),另一方面是个体的行动自由和对社会的形塑作用(能动)”(吉登斯等:《社会学基本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页)。
通过以上对三位社会理论大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简要描述,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的方法对比于涂尔干和韦伯,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在对于社会理论基本问题的解决上,涂尔干无疑实现了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但其代价却是无法容纳个体的能动活动,而韦伯顾及了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义,但却无法使之达到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至于吉登斯、布尔迪厄等人对于“两种社会学”的综合,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理论的深化,但并未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这是因为,如果只是从主体行动层面考虑能动与结构的二重性,这至多只是对于以往僵化的二元对立的软化,且在客观上并不能达到科学所要求的概念的确定性;而如果更多地强调活动的结构的制约作用,就仍然只是对于结构作用的软化,而在实质上远未解决问题。而马克思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优越性在于,他虽然在本体论层面上通过“人是对象性活动”这一命题合理地解决了人的能动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但却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本着改变世界的目标走向了科学的经验研究层面,并借助其辩证方法而成功地从主体活动的逻辑转换到客观结构的逻辑。这样,所谓“两种社会学”在马克思这里便成为了社会理论的两个层面,而两个层面之间又能够以一种辩证法关联起来,从而保持了本体论上的一元论。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马克思的启示
基于上述对马克思的解读,我们当能看到,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与涂尔干、韦伯并非并列地处于同一个理论层面上看,而是必须看到马克思在理论上跨越了主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两个层面,或者说,在马克思这里,主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不是并列的二元存在,而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两个层面。由此反观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理论,如果我们将韦伯的理想型方法主要地解读为一种历史社会学或历史解释学,而将涂尔干之社会事实理论解读为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兼有了历史解释学与实证性的科学两个层面,而且亦具有在两者之间相互过渡的辩证方法。准此,则似乎还可以进一步说,基于马克思的方法论框架,我们能够将韦伯的历史解释学与涂尔干的实证科学研究方法吸纳进来,充实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之中。在此观照下,吸纳并充实进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之中的历史解释学可作为对于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的再认识方法,以便为建构能够切中中国社会之特定结构提供一种有效的导引;而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概念,则可吸纳来作为建构具有科学所要求的确定性概念之方法指引,以之作为把握特定社会结构之表征。这样一来,在建构中国社会科学之方法论体系中,我们便可以马克思的方法为范型,从建构关于中国社会之理想型分析开始,然后过渡到对于现实社会事实或社会结构之实证分析。
如此,则建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之首要工作便是对于中国社会之再认识,亦即建构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理想型。此一工作之所以重要,便在于中国社会的极大独特性,而以往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却又往往简单地比附于西方社会而极大地忽略了这一点。
社会存在具有历史路径依赖性,中国社会发展之独一无二性,他国皆未有过的社会存在方式,无法简单归结为西方概念中任一种。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如古代之整体主义与现代之个体主义,皆有可能无法真正把握中国社会之特征。进而,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独特性以及其超大规模存在,其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对于世界格局产生重大改变。因而,中国道路之世界历史意义并非只是其范本作用,而是这一道路对于世界历史进程之改变。因此,在进行关于中国社会的科学研究之初,便必须首先对于中国社会之独特历史发展有一个清楚的再认识。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历史事实便是(广义)封建社会在唐宋时期解体,而后中国进入长达千年之久的“绝对主义”社会。这样一种长达千年之久的社会结构模式,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而,从这样一种社会模式进入近现代社会,便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一种与西方社会极为不同的现代社会结构,而且这一独特的社会结构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式也会持久地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只有在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这一独特性有充分认识的前提下,所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才可能真正切中中国社会。在这方面,韦伯曾经做过具有巨大影响的工作。但他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大多仍建立在一些不可靠的材料甚至臆测之上,因而必须予以批判性鉴别,并重新进行有关建构工作。在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再认识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并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之分析方法,便有可能建构起真正能够切中国社会的社会科学理论。
(作者系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摘自《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8期)
标签:涂尔干论文; 马克思论文; 客观有效性论文; 历史解释学论文; 建构性论文; 当代中国社会论文; 南开大学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