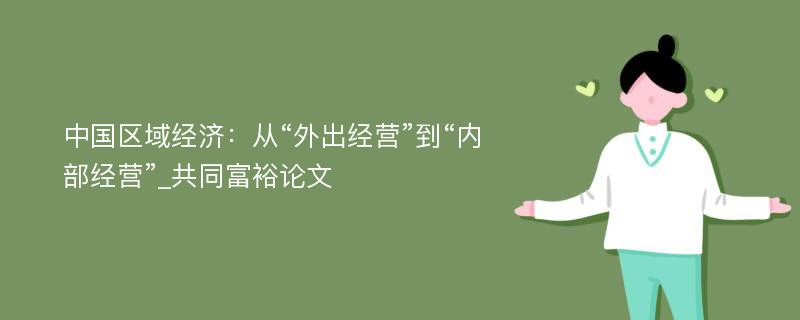
中国区域经济:从“局外运行”到“局内运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局内论文,区域经济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01)06-0090-05
一、何谓区域经济“局外运行”和“局内运行”
中国区域经济运行的关键,实质上在于如何处理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共同发展、共同富裕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第一个大局”的核心是: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并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就告诉我们,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必须率先发展,但是这种“率先发展”不仅不能损害内地的发展,而且还要带动内地更好发展。“第二个大局”的核心是:到某一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必须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更快发展。这就告诉我们,虽然在某一时期,内地更快地发展离不开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力支持,但是这种“更快发展”不仅不能损害沿海地区继续发展,而且还要有利于其继续发展。可见,无论是在“第一个大局”中还是在“第二个大局”中,邓小平强调的是不同区域共同发展、共同富裕问题。当然,这种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决不是平均主义式的。
基于上述理解,本文把符合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区域经济的动态过程,称之为“局内运行”;把违反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区域经济的动态过程,称之为“局外运行”。显而易见,中国区域经济应该保持“局内运行”状态,杜绝“局外运行”状态。
二、逻辑框架:“市场空间结构→市场空间结构机制→市场空间结构绩效”
市场经济制度下,市场、市场机制及其市场绩效之间,存在着非常严格的逻辑传递关系。有相应的市场,就有相应的市场机制;有相应的市场机制,就有相应的关于资源配置方面的市场绩效。反过来说,市场绩效、市场机制及其市场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逻辑传递关系。在现实活动中,市场、市场机制及其市场绩效,三者实际上是紧密相联不可须臾分开的整体,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理论思维中把它们看成是一种在时空中可以分开并且存在先后顺序的逻辑传递关系,即“市场→市场机制→市场绩效”。
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命题指出:(1)假如有足够的市场,(2)假如所有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能够按照竞争规则行事,和(3)假如存在竞争均衡状态,那么在此状态下的资源配置即为帕累托最优状态(阿罗,1951;德布勒,1959),亦即市场成功(莱迪亚德,1987)。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命题还指出:或者(1),假如没有足够的市场;或者(2),假如所有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不能够按照竞争规则行事;或者(3),假如不存在竞争均衡状态,那么在此情况下的资源配置就会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出现市场失灵(莱迪亚德,1987)。由此可见,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命题不仅内含着“市场→市场机制→市场绩效”这种逻辑传递关系,而且事实上也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市场不同,市场机制则不同;市场机制不同,市场绩效也不同。
经济学的发展史上,不少学者都研究过与市场成功相关的逻辑传递关系,斯密(Smith,1776)、奥曼(Aumann,1964)、文德(Vind,1964)、阿罗—哈恩(Arrow-Hahn,1971)、比利(Bewley,1973)、格罗德尔—希尔顿布兰德(Grodal-Hildenbrand,1974)、卡恩(Kahn,1974)、布朗—罗宾逊(Brown-Robinson,1975)等均在此方面有所建树。也有不少学者,诸如庇古(Pigou,1932)、西托夫斯基(Scitovsky,1954),科斯(Coase,1960)、弗利(Forey,1970)、斯塔雷特(Starrett,1972)、格林(Green,1977)以及克雷普斯(Kreps,1977)等,都曾研究过与市场失灵相关的逻辑传递关系。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所致,无论是研究前者的学者,还是研究后者的学者,他们都没有看到市场空间结构与市场成功或市场失灵之间的相关关系,甚至就连以区域经济为研究对象的所有理论,诸如其中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历史经验学派、现代化学派、激进学派以及乡村学派等,也没有看到市场空间结构与市场成功或市场失灵的内在逻辑关联。
市场空间结构是市场的客观存在方式。不理解市场空间结构,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市场、市场机制及其市场绩效。所谓市场空间结构,指的是市场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及其相互关系,亦即不同的区域市场的既定状态及其相互关系。由于市场空间结构是市场在空间分布上的一种客观存在方式,因而有什么样的市场空间结构,就有相应的市场空间结构机制;有相应的市场空间结构机制,就有相应的关于资源配置方面的市场空间结构绩效。尽管在区域经济运行中,市场空间结构、市场空间结构机制及其市场空间结构绩效,三者紧密相联不可分割,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理论上把它们看成是一种在时空中可以分开并且存在有先后顺序的逻辑传递关系,即“市场空间结构→市场空间结构机制→市场空间结构绩效”。从这一逻辑传递关系中,我们不难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市场空间结构不同,市场空间结构机制则不同;市场空间结构机制不同,市场空间结构绩效也不同。
其中,“市场空间结构”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类型被本文称之为市场空间二元结构,即发达的区域市场与落后的区域市场在空间分布上的同时并存状态及其相互关系;另一种类型被本文称之为市场空间一元结构,即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不同区域市场在空间分布上的同时并存状态及其相互关系。
市场空间结构的两种基本类型,决定了“市场空间结构机制”也有两种基本类型,即区域两极分化机制和区域共同富裕机制。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命题给出的思路,如果“市场空间结构”满足:(1)假如区域间存在足够的市场,(2)假如区域间能够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规则行事,和(3)假如区域间能够达到竞争均衡状态,那么这种“市场空间结构”必定内含区域共同富裕机制。反之,如果“市场空间结构”满足:或者(1),假如区域间没有足够的市场;或者(2),假如区域间都不能够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规则行事;或者(3),假如区域间不能够达到竞争均衡状态,那么这种“市场空间结构”必定内含区域两极分化机制。
“市场空间结构机制”两种基本类型,意味着“市场空间结构绩效”也具有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即区域两极分化绩效和区域共同富裕绩效。不言而喻,区域两极分化机制必然表现为区域两极分化绩效,区域共同富裕机制必然表现为区域共同富裕绩效。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说的区域共同富裕绩效,可以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区别为“温饱型共同富裕绩效”、“小康型共同富裕绩效”和“发达型共同富裕绩效”等三个不同层次,高一级区域共同富裕绩效的实现有赖于低一级区域间共同富裕绩效的实现,且每一级区域共同富裕绩效均存在富裕程度上的差别。例如,在“温饱型共同富裕绩效”中,有的区域温饱程度可能更大一些,有的区域则相对而言更小一些,如此等等。本文所理解的区域两极分化绩效,指有的区域处于温饱水平,有的区域处于小康水平,如此等等。
我们建立“市场空间结构→市场空间结构机制→市场空间结构绩效”这一逻辑框架的意义在于,我们如果能够证明现实的区域经济运行属于某种市场空间结构,那么就能够据此判断其是属于“局外运行”,还是属于“局内运行”,寻找到引起区域经济“局外运行”或“局内运行”的市场空间结构基础,为实现并保持区域经济“局内运行”提供理论说明。
三、逻辑框架运用之一: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与“局外运行”
经济学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可能性集表现出非凸性,那么竞争均衡就不存在,其资源配置就会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出现市场失灵(莱迪亚德,1976)。经济学还告诉我们,如果一家厂商或社会在它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以下进行生产,亦即它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凹向原点,其资源配置就可以被认为是低效率的(斯蒂格利茨,1993)。不妨令一国经济由A、B两区域构成,其中区域A市场发达,区域B市场落后。在这种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中,相比较而言,区域A的资源配置具有相对效率,其经济增长具有内在扩张机制。区域B的资源配置相对无效,其经济增长存在内在收缩机制。在区域市场动态运行过程中,对区域B而言,由于区域A资源配置方面的相对效率,无疑会抬高本区域各种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降低机会成本的理性决策会诱导区域B中数量愈来愈多、质量愈来愈高的投入要素不断流出,形成所谓“要素效益外溢”[1]。在此情况下,区域B所拥有或可支配的投入要素无论从量上看还是从质上讲,都会更加稀缺。更加稀缺的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收缩机制粘合在一起,区域B经济增长就会出现乘数式收缩。相反,对区域A而言,由于区域B资源配置方面的相对无效,无疑会降低本区域各种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并对区域B各种投入要素产生巨大的诱惑力,不仅本区域的各种投入要素不可能流出,反而还会大量吸纳区域B的各种投入要素,形成所谓“要素效益内注”。在此情况下,区域A可拥有或可支配的投入要素无论从量上看还是从质上讲,都会更加充裕。更加充裕的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扩张机制的联姻,区域A经济增长便会孕育出乘数式扩张[2]。在投入要素的上述流出流入过程中,尽管区域A中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区域B中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增,但由于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中,两区域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对比关系不可能发生实质性变化,故而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必然凹向原点。区域经济的整体运行偏离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出现了市场失灵,并表现为区域间经济增长的两极分化趋势。
生产可能性曲线的非凸性以及区域A经济增长乘数式扩张和区域B经济增长乘数式收缩,又从一个侧面说明区域A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A、B两区域的平均增长速度,区域A的“效率工资”便趋于下降(卡尔多,1970),由此就可获得一种为区域B根本不可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累积竞争优势(缪尔达尔,1957;卡尔多,1970),同时进一步遏制区域B,使其在经济增长中不断累积起愈益恶化其自身的各种因素。区域A累积的竞争优势包括:(1)累积起吸引新兴产业布局的优势。区域A凭借其足够的市场实力,能够累积起强大的科技力量、便捷的交通和通讯联系、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优越的协作条件、雄厚的资本和活跃的消费市场。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使得区域A对于新兴产业部门(例如电子电器、计算机、生物技术、高级材料等)的空间布局具有巨大磁力。(2)累积起资本分配的优势。区域A市场发达,经济繁荣,人才密集,必然成为政治权势的中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研究与开发经费、政府采购、国家投入、外埠资金以及公共工程项目的分配。(3)累积起服务部门成长的优势。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区域A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依次兴起与替代,势必带动一系列为之服务的产业部门,诸如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居民服务业、技术咨询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等的兴起与发展。(4)累积起市场成长优势。随着上述各方面优势的不断累积,区域A的产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产权市场、信息市场等也会得到空间发展,并形成相对完备的市场体系。与此相反,区域B尽管由于“扩散效应”的作用较之以往有着某种程度的进化,但也正是在这种进化过程中不断累积起方方面面的竞争劣势。比如累积起工业化进程的劣势。区域A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要求有充分的初级产品供给,并会通过技术转让、对外投资和产品统购等形式,刺激区域B增加初级产品生产,把区域B置于工业化进程的附属地位,甚至排斥在外,使得区域B工业化进程总是远远滞后于区域A。比如说累积起产业结构方面的劣势。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中,区域间的分工往往是垂直型分工[3]。在这种分工格局中,随着区域A产业部门的“外溢”,一些淘汰或即将淘汰的产业部门将会转移到区域B,构成区域B举足轻重的产业基础,致使区域B产业结构水平及其转换总是远远滞后于区域A。再比如区域B资本匮乏、人才奇缺、基础设施落后、观念陈旧、市场发育不良等等,归根到底都不过是累积竞争劣势的具体表现。
区域A不断累积起竞争优势和区域B同时不断累积起竞争劣势,又表明区域A实际上取得了一种市场垄断势力(Monopoly Power),可以通过索取高于边际成本价格占有尽可能多的市场利益[4]。市场垄断势力的出现,一方面意味着区域A的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规则,另一方面意味着区域B也不可能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规则行事。而且意味着,区域A可以通过操纵市场,稳定地占有巨额垄断利润,大大削弱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驱动力。区域间市场竞争的非规范性,造成的不仅是资源配置方面的低效率,而且还会成为进一步强化这种低效率的手段。
综上所述,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条件下,(1)区域间没有真正的市场,亦即区域间不可能形成足够的市场,(2)区域间不可能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规则行事,和(3)区域间不可能达到竞争均衡状态,因而这种市场空间结构存在着区域两极分化机制。在区域两极分化机制作用下,其市场空间结构绩效必然是区域两极分化,即“市场空间二元结构→区域两极分化机制→区域两极分化绩效”。也就是说,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条件下,区域经济必然“局外运行”。区域经济“局外运行”的市场基础是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任何不从根本上触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的一切努力,都不可能扭转区域经济“局外运行”的格局。
四、逻辑框架运用之二:市场空间一元结构与“局内运行”
在一国经济由A、B两区域构成的假定中,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意味着两区域的资源配置具有相同层次的效率,经济增长无论是从每一区域看还是从两区域构成的整体上讲,都具有内在的扩张机制。如果把区域经济增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加以表示的话,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所体现出来的制度重新安排,会通过提供更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尼科尔森,1988)改变该生产函数中的各种参数的输出功能,使区域经济增长能够突破既定的技术水平和投入要素规模的约束,产生出更大的经济增长总量。另一方面,从制度重新安排引起的投入要素流动的角度而言,投入要素在每一区域内部或区域间的自由流动,足以诱导这些投入要素在每一区域内部或区域间重新组合直至优化组合,同样具有突破既定技术水平和投入要素规模约束的功能。例如,假定区域A生产X[,A]产品(X代表产品品种及其产量,脚标A代表区域A。下同)具有比较劣势,生产Y[,A]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区域B生产X[,B]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生产Y[,B]产品具有比较劣势。在投入要素自由流动过程中,作为对比较利益牵引的理性反应,区域A原来用于生产X[,A]产品的投入要素,一部分会并入本区域Y[,A]产品的生产,另一部分会自动流出,与区域B产品X[,B]的生产进行优化组合。同理,区域B原来用于生产Y[,B]产品的投入要素,一部分会并入本区域X[,B]产品的生产,另一部分也会自动流出,与区域A产品Y[,A]的生产进行优化组合。结果,投入要素将聚集于两区域各自的比较优势产品部门,从而使得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大于两区域分别都生产两种产品时的经济增长总量。在这种投入要素的流出流入过程中,A、B两区域的要素边际报酬均递减,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必然表现出凸性[5]。
不仅如此,区域经济增长还在增长方式上具有内在的转换性。投入要素具有稀缺性,市场活动的利益主体具有价值上的无限占有性。市场空间一元结构中,各个区域市场的竞争实力处于相同层次的发育水平,为了摆脱投入要素稀缺性的约束,区域利益主体除了选择制度重新安排,促进投入要素优化组合外,对价值无限占有的追求过程,往往还体现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不断转换。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以工作日长度等等为既定条件的、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过程中,某一利益主体为了谋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设法让自己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为此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并以“超额剩余价值”的形式实现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超额剩余价值”占有形式的出现,表明这一利益主体占有的“剩余价值”在数量上多于其他利益主体,由此形成对其他利益主体强大的物质刺激力。在这种物质利益驱使下,其他利益主体也会或迟或早地采取相应的技术创新。一旦这些利益主体的技术创新完成,就会形成一个发端于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结束于所有的利益主体都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的社会整体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周期。“相对剩余价值”占有形式的实现,既是上一个技术创新周期的结束,同时又是下一个技术创新周期的开始。如此循环不已,推动社会整体技术水平不断由一个台阶迈向另一个更高的台阶,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发生质的飞跃。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逻辑,同样适合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分析。因此,在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条件下,区域利益主体面对要素稀缺性制约,发自于对价值无限占有的追求,会推动不同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不断转换,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
在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条件下,区域经济增长不仅具有内在转换性,而且在动态关系上还具有双赢性。具体而言,(1)资本形成在不同区域是双赢的。纳克斯、罗森斯坦-罗丹、刘易斯(阿加尔瓦拉,1973)、赫希曼(1958)[6]、斯特里顿(中译本1984)、罗斯托(1963)等都曾探讨过不同区域如何在资本形成上达到双赢的问题。由于他们的理论实际上局限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的框架内,因而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市场空间二元结构内含着区域两极分化机制,用缪尔达尔的话来讲存在着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和回程效应的综合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行平衡投资(例如纳克斯、罗森斯坦-罗丹、刘易斯)也罢,按照产业关联度(例如赫希曼)、立足于欲望合成代谢规律(例如斯特里顿)、依据主导产业部门(例如罗斯托)进行不平衡投资也好,资本形成将更有利于发达区域而不是落后区域。但是,在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条件下,区域间的有效投资需求处于相同的发展层次。区域间相同层次的实际收入水平会形成相同层次的需求弹性,进而具有相同层次的投资引诱及其在此基础上的双赢的资本形成。(2)生产要素的流动在不同区域是双赢的。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出流入的确取决于要素报酬的高低(或机会成本的大小),但是要素报酬的高低又以既定的区域分工类型为基础,区域分工类型又以市场空间结构的基本类型及其绩效为转移。在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条件下,区域间的分工不可能是垂直型分工,往往是水平型分工或混合型分工[3]。在水平型或混合型的区域分工格局中,才存在着有利于不同区域共同发展的比较利益,而不是李嘉图(1817)、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1997)笔下的那种更有利于发达区域的比较利益。此时,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出流入,才不致于仅仅是“孔雀东南飞”,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3)产业转移在不同区域是双赢的。现代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主导产业部门的成长过程(罗斯托,1963)。主导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通过回顾影响、旁侧影响和前瞻影响表现出来(胡代光、厉以宁,1986),而且还通过这三种影响的综合作用引导产业部门在不同区域间的转移来实现。在市场空间一元结构中,区域间主导产业部门的具体构成“趋异”,发展水平则“趋同”(这与郭万清的见解有所不同。参见郭万清,1992)。具有这种特征的主导产业部门的回顾影响、旁侧影响和前瞻影响的综合作用并非是封闭的,必然伴随着相应的产业部门在区域间相互流动,形成符合各区域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等要求的“主导部门综合体系”,构成区域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产业结构基础。
综上所述,在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条件下,(1)区域间具有真正的市场,亦即区域间存在足够的市场,(2)区域间存在着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竞争规则行事的市场基础,和(3)区域间能够达到竞争均衡状态,因而这种市场空间结构存在着区域共同富裕机制。在区域共同富裕机制作用下,其市场空间结构绩效必然是区域共同富裕,即“市场空间一元结构→区域共同富裕机制→区域共同富裕绩效”。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局内运行”的市场基础是市场空间一元结构。要想保持区域经济“局内运行”,必须构建并不断深化市场空间一元结构。
五、小结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区域经济运行虽然是依据邓小平“第一个大局”进行设计的,但由于市场化发展实际上是以构建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为导向的,因而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不断扩大[7],且越过了警戒线[8],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不仅没有起到带动内地更好发展的功能作用,相反还损害了内地自我发展能力,引发了不稳定因素增加,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疑惑[1],区域经济处于“局外运行”状态。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要想消除两极分化现象,促使所有区域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达到区域共同富裕目标,必然要通过市场创新,构建并不断深化市场空间一元结构,实现由“局外运行”向“局内运行”的历史性跨越。
收稿日期:2000-11-05
标签:共同富裕论文; 两极分化论文; 经济论文; 二元经济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二元关系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外运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市场机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