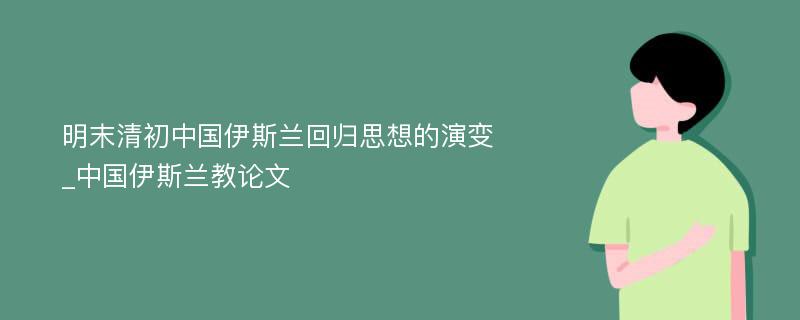
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回归思想在汉语中阐释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汉语论文,明末清初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斯兰教认为万物源于真主,而后复归于真主。“回归”说便是指复归真主之意,它是伊斯兰教创世观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环节,是伊斯兰教其他思想学说的基本依据。本文分析明末清初回族穆斯林学者对此学说的解释与翻译,探索该学说在中国发展变化的脉络。
一、“复帝者之命”的“来复”
“回归”思想在明朝后期变得清晰,其标志是山东济南清真大寺的《来复铭》,碑立于明朝嘉靖七年(1528年)碑铭全文一百多字,内容凝炼典雅,多用儒家、道家的术语来阐述伊斯兰教的思想。该文全文如下:
“无极太极,两仪五行;原于无声,始于无形。皇降衷彝,锡命吾人。与生俱生,与形俱形。仁人合道,理器相成。圣愚异禀,予赋维均。是故心为郛廓,性为形体。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存心与性,以事其天;慎修厥身,以俟此命;主敬穷理,以养此性;戒慎恐惧,以体此道;不愧屋漏,以事此心;斯与造物为徒矣!不尔,天故畀之,人故畀之!其将何以复帝者之命?!”
从以上碑文内容分析可知,此碑前半部分,主要讲宇宙与人的生命的形成、身心性命的产生,照应“来”即“皇降衷彝,锡命吾人”也就是说真主下降《古兰经》,为穆斯林安排了生活和法度。其中对宇宙生成的论述极其简单,对人的身心性命的产生论述很详细。后半部分主要讲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人的最终归宿,即修身以复命,照应“复”。由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该文的中心思想。“锡命吾人”和“事天俟命”确立了人与真主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便叫做“来复”,来指的是皇降,复指复帝命。这里的“来”与“复”已被赋予了伊斯兰教创世论和回归说的含义。深入了解“来复”的含义和用意,便能发现更为深刻的含义。用“来复”这一哲学术语为碑命名,使人直观地联想到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关“复”的观念,尤其是《周易》的《复》卦。如果我们结合穆斯林的日常宗教生活(如一日五次礼拜,七日一聚礼)来看,《复》卦简直就是一篇优美而简练的宗教劝诫,而且为这种生活赋予意义。《易·复》如下: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初九,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六四,中行独复。《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六五,敦复,无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上六,迷复,凶,有灾情。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
《复》卦讲述了各种状况下“复”的特征,总体来看,都是美好的,只有“迷复,凶”。“复”是构成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的、各家共同的观念[1],如《老子》中“吾以观复”、“反者道之用”等等。这里使用“来复”便把伊斯兰教与中国哲学联接起来,为伊斯兰教找到了广阔的中国哲学背景,使中国的哲学直接成为支持伊斯兰教的依据[2],隐约地显露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的范式和途径。
《来复铭》是中国穆斯林学者最早将伊斯兰教哲学与宋明理学交相融会的阐发教义的文献,其开创了明末清初伊、儒两种文化交融的局面。此后“来复”这一思想便被回族穆斯林学者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着,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有侧重于“真光论”,有侧重于“人主合一论”,有的侧重苏非密修等,但都是围绕着“回归”说展开的,并以此形成了伊斯兰教教义学说在中国的一大特点。
二、《敕赐礼拜寺碑记》的“回辉”
该碑现在北京牛街清真寺,立于明朝万历癸丑年(1613年)仲秋,此碑文对“回归”有其独特的表述。其最大的特点是将“回”、“辉”做了一种释义,体现“回归”这一哲学命题,该碑中这样写道“人知天之为天,不知天之所以为天,天之所以为天者何?主也,一也。人不知原始而生,愈不知反终而死。反终而死者名为何。回也,辉也。……叛此中者回回,则回矣暗淡甚尔;遵此中者亦回回,固回亦辉光朗焉。噫嘻!人寄生如寄蜉蝣之羽!与其暗而无光,孰若回光返照!掷室如掷燕雀之堂,与其绸缪待焚者,孰若绸缪久居者!”[3]此段的概念和论述可以图示如下:
天 主也:一也 原始
反终
人 回也:辉也 回矣暗淡
回辉光朗
从左表可以看出此处作者在天人关系的总体背景下理解“回回”,指出天是唯一的主宰,人从生命过程(原始而生,反终而死)来看是一个形式上的回归,并指出了不同内容的回归的意义。这里面反映了这样两方面的思想。一是“回”,二是“辉”,这里指出“回”是生命终结,是必然的,而辉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遵”与“叛”是能否发辉的直接原因,将“回回”分为“光朗的回回”和“暗淡的回回”,表明“辉”在这里成一个价值尺度。于是“回”与“辉”表达了人生归宿与人生价值取向。
三、王岱舆解释的“回回”与“升降”
王岱舆的主要贡献一是明确将回回民族族称与“回归”说联系起来,二是解释“降”与“升”的内涵。
王岱舆解释“回归”的主要内容见于《正教真诠·回回》、《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王岱舆是通过解释“回回”一词的含义来阐发“回归”学说的,“大哉回回,乃清真之镜子,天地即彼之模范也,万物之拥护,直为全镜之形;教道之磋磨,皆缘回镜之光。夫回光有二:曰身回、曰心回。”[4]这是第一次对“回回”二字做明确的哲学含义的解释,为“回回”在宗教教义中找到理论依据。他将“回回”分成两方面的内容,“回回”分为“身回”和“心回”两个方面,“还复”是指生命终结,肉体消失,“归去”,指受到末日审判。“心回”分为两方面,一是“正心之回”,二是“无心之回”。从而完整的表达了伊斯兰教的复归说。如下表:
回 身回 还复
归去
回 心回 正心之回
无心之回
在他的论述中由“正心之回”向“无心之回”的发展是一个认识层次逐渐提高的过程,带有由理性向直觉飞跃的含义,如文中所言,“忽然觉悟,利名若梦,身非己有,何况外物乎?复思本来,急寻归路,溶情欲而为天理,化万象而返虚无,兹正心之回也。”[5]这是一个层次,其特点为“有无道之回”,进一步发展将获得对真主的更深层次的体认,“欲更进一步,需得扯破真如幔子,钻碎太极圈子,拆毁众妙门子,始超三教之道也。”[6]这便是“回归”的最高境界,其特点是“显命源而得无极,体无极而认真主”[7]。
王岱舆对“回归”这一理论也进行了伦理本质上的探讨,在《清真大学》中通过人与主的关系来论证人在“来复”中的意义。王岱舆认为人承载作证真主的使命,人在作证真主的过程中寻求并获得“真我”。王岱舆将“我”分为“幻我”和“真我”两个层次,“幻我”是“人我分别之我”,“真我”是真主寄以大命的“我”,“真我”是来源于真主造人的初衷,是人生所要达到的目标。王岱舆指出“原夫真一、数一之机,总具于作证之我,作证之我,乃真主寄托之我,是为真我,除斯寄托之我,本无我也。”[8]“真我”与“幻我”来自于真主的造化,这一造化即是“降”,照应经文“真主始初造化人之妙明,至完全而端正,后复降之低中之至低”,“幻我”接近“真我”的过程便是“升”。在“升”的最高或最终阶段,体现了生命过程的实质,“方知无极先天乃初种之时,自上而下谓之降,是为原种,始无作证也;人极后天,乃浇灌之时,自下而上谓之升,本因结果也。树藏种中,果从树显,反本归元,果即是种,虽然不二,实有增益。”[9]这里指出了生命的过程是作证的过程,并提示了“升”是生命增益的过程,人作证真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是在信仰的旅途中由低向高的发展,人生最终获得的是“结果”和“增益”,即人在作证信仰的过程中,实现了向理想人生的发展。这便是王岱舆所论的“回归”的实质。
从明末的《来复铭》中提出“来复”,到王岱舆论证“降”和“升”,奠定了伊斯兰教“回归说”四个基本内容——“升、降、来、复”,其中“降”成为“来”的实质,“升”成为“复”的实质。若说“来复”侧重于“回归”的形式的话,“降升”则侧重于“回归”的本质,从阐释的先后顺序来说,“升降”则是“来复”的继承与发展。至此,“来复”、“升降”这两组对立统一的概念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回归”说的基本内容,以后的学者多是围绕这四个字阐发的。
四、马注对“回辉”说的继承与发挥
马注的主要贡献一是将“信仰”、“明德”统一于“真光论”,二是用“回辉”解释“回归”。他对“回辉”这一表述情有独钟,在著作中他多次引用“回辉”二字,使它成了“回回”或穆斯林的同义词。由于“辉”这一字有独特的含义,使“回辉”二字曲折地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他将信仰与“明德”、“真光论”统一起来。伊斯兰教中信仰一词称作“伊玛尼”,被马注译为“明德”,从《指南清真》、《正教真诠》可以发现解释的过程。
“真赐者,即所谓以妈纳也,此乃真主之动静,赐之于人者,所以遂其所赐,方认得真主确当,故谓之真赐。”[10]
“(问)何谓‘以妈纳’”?[11]
“(答)天命之明德”[12]。
“所谓明德者,不落声闻,不属造化,不系搀杂,无色相,无始终,回光不夜,慧烛长明,得则永存,失则永失,实由止一光明,传灯逐照,千烽万炬,从此发辉。”[13]
这里他将信仰概括为一个纯粹的精神本体,他从“真光论”角度解释“明德”和信仰,并将伊斯兰教的信仰与儒家《大学》“三纲”相联系。马注能将信仰、“真光”、明德这三者联系起来,“真光”是中介。对信仰和明德的关系在《清真大学》也可以看到,王岱舆将“作证之言”放到了与明德同等的地位,他这样论述:
“清真正教,入德之门,认主之要,首言‘我作证’一句”[14]。并这样解释“作证”,“《大学》正宗,‘作证之言’,特明主仆至大之理,真一、数一之殊。……主仆分明,真数一定,然后始知明德之源。知明德之源而后明明德,明德明而后真知,真知而后知己,知己而后心正,心正而后意诚,意诚而后舌定,舌定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15]
王岱舆虽将二者联系,但没有象马注那样用真光联系。以上分析便能发现马注在沟通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时有“真光论”的倾向。
五、刘智对“回归”的论述
刘智“回回”、“升降来复”的论述系统、完整。他对“回归”这一思想的论述主要在《天方性理》、《回回说》之中,从整个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中来定位“回归”说,肯定了这一思想的重要地位,指出了“回归”是一切学说和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也是论述最完整的。
《天方性理》论述宇宙和人的产生、发展、变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开始被称为“有”,终结被称为“真”,全部过程便是“升降来复”,是“真一”的自我显化。他这样论证:
“宇宙间千头万绪之理,至无尽也。然不过一真宰之自为升降来复而已。降于种,升于果,来于最下,复于最上。大世界之为降为升,即小世界之为来为复。而小世界之为来为复,妙于大世界之为降为升。则以大世界之由降而升也,其升尽于有形;小世界之自来而复也,其复尽于无形,无形较有形为于精也。”[16]
这里指出“升降来复”的本质及在大、小世界中的不同意义。这里升降来复被分成三方面,一、宗教哲学的整体观上的真宰的自为升降来复,二是大世界的升降,三是小世界的来复。由此看,刘智比前人论述较完整、全面。
如果说“升、降、来、复”是从宗教哲学的角度来论述人生,那么,刘智的《回回说》则是伦理角度来论证人生。他所论证的内容并没有超出以前的论证,而且很多是其父刘三杰《清真教说》部分内容的翻版。但是他的论证确实很独特,他以中国伦理和道德以及中国人的形象思维特征来说明“回”字,比如他解释颜回、方回等人名中之“回”字。他也概括出论证和解释“回回”的一般特征,“由数说观之,回字取象则统天括地,取义则反本归原。身心之关合,理象之包藏,一回字尽之,回之为义大矣!”[17]与此相似的解释有《回回原来》等。这种“取象”、“取义”的解释模式,正是中国传统哲学解释的一个基本的方法。
除了理论层面外,刘智对回归宗教实践也有独到的体验,他的《五更月偈》是一片通俗易懂的苏菲修行的歌诀,完整地描述了苏菲精神修炼到“天人浑化”的过程和境界。其中特别强调“自适其乐”的精神追求是伊斯兰教苏菲修行的最终目的,这种乐趣是“默然难言”、“独自乐”,此偈中云“五更中,月正残,清心显性道成全;升降合,循环完,更超名相真谛显;天人合一要浑化,三忘尽时本湛;玄中妙,妙中玄,难语难言默自然。五更末,月正落,复命归根上大罗;无色府,无相窝,无声无臭真寂寞;扯破纯一绵幔子,钻碎一真玉泉窠;无晨夕,无如何,依然最初独自乐”。这种“独自乐”的精神享受可看作是刘智对“回归”精神本质的一种概括,这是他以前的学者均未明确指出的。
六、“回归”思想演变特点的综述
以上便是这段时间对“回归”说的各种表述,很显然这些论述从来就没有统一过,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习惯而用自己喜欢的词汇来解释此命题。“回归”常常被表述成“复归”、“回回”、“回辉”、“归根复命”、“来复”、“升降”、“人主合一论”等。这里将“回归”思想的解释过程简单图示如下页:
时间 人名 书籍或碑刻主要概念主要含义
1518 陈思 《来复铭》来、复 “来”是人之受命而生;“复”是完成使命
1613 《敕赐礼拜寺碑记》 回、辉 “回”指回归真主;“辉”指建立信仰、完美人生
1640 王岱舆
《正教真诠》
回回、降升 “降”指真主赋予人类以形体和灵魂;“升”指完美人生,
复归真主
1683 马注 《清真指南》 “回辉” 指有信仰(或明德)的穆斯林
1700 刘智 《天方性理》
升降来复;
指“真一”的自我显化;
回回 大世界的升降,小世界的来复;
人与真主在精神上合一的过程
1.回归说的解释过程就是它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走向融合的过程
最初的《来复铭》单看名称和内容,简直就是一篇地道的中国哲学的文献,其表述是隐而不露,但他已经紧扣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基本术语,尤其是儒家的哲学概念,而且其中的论述有些直接取自儒家典籍《易经》、《诗经》、张载《正蒙》等。其后,更是明显的融合,如王岱舆将伊斯兰教的“作证”与儒家的“修齐治平”结合,如马注直接将伊斯兰的信仰与《大学》的“明德”等同。刘智则从哲学体系、内容及解释的方法上用中国的思想和思维特点出发来阐释,使解释“复归”的内容和形式均走向系统化、明确化。可见伊斯兰哲学的中国化是不断地从各个层面都在与中国哲学走向融合。
2.解释回归说与解释穆斯林群体相依
“回回”是伊斯兰教的载体,解释“回归”促使“回归”思想直指人心,直接与信仰的主体——回回民族相联系。由于“回归”说与回族族称之间的此种关系——这一关系主要是通过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解释赋予(或加深)的,解释此学说对于认识“回回”民族尤为重要,于是出现了“回回”与“回归”解释相混合的现象。这样解释是回族深化认识自我和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关系在“回回”的信仰与实践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即认识宗教与认识自身相结合。单就本文而言解释“回归”的过程就是穆斯林学者对宗教和人生的认识过程,同时也是回回民族逐渐自我群体认同及文化展示的过程。故今天的回族在一定程度上仍不可避免解释“回回”,故此解释丰富了回族的精神财富,解释过程所造成的心理机制已融化到回族的心理结构之中,也形成回回民族心理深层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决定了回回民族与伊斯兰教关系密切的一个心理因素。
3.解释的主观性的随意性
他们解释“回归”因各自的学识、经历或情感等因素而所侧重,依据伊斯兰教教义,对“回”字从“象”、“义”上的解释,如《易经》中的“来复”本来并没有“创世说”的背景,但在《来复铭》中“来复”则有了真主创世的思想。王岱舆解释“回回”并没有用历史学的方法,而是直接引申附会,这从历史的观点看是不足取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则是很深刻的。马注的解释主观色彩更浓,随意改写“回”字,表达他们的思想。刘智从“取象”、“取义”两方面综述“回回”的含义,这种带有象征主义的解释,为“回回”的解释提供了最完整的范式。“回”字在形状上表示了伦理、社会、自然环境中的对偶结构,如内与外、身与心、天与地等等。在意义上表示了不断地、往复地“反本归真”。“回”为这些对偶结构内部相互运动变化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描述,将这些辩证关系统一在“回归”这一过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