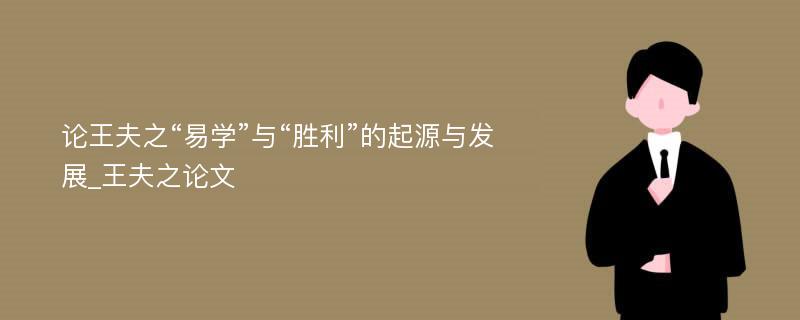
王夫之“因《易》以生礼”的源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王夫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王夫之看来,易与礼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讨论易与礼之间关系时,王夫之追溯了周王朝的政治基础,认为“周以礼立国,而道肇于《易》。”(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1页。)也就是说周礼的各种原则,是蕴含在《周易》中的,《易》是礼的源头。在历史上,将《易》与礼联系起来,并不是王夫之的创见,这是先秦时代就有的一种观点。当晋侯派韩宣子去鲁国行聘礼时,韩宣子观《易象》与《春秋》,就曾慨然称许:“周礼尽在鲁矣。”(注:《左传》昭公二年。)同样,在《易传》中,以礼释易的解释倾向也时有所见。王夫之在《易》与礼之间关系方面的创见,在于他对《易》为礼的源头作了新的论证,并认为以礼释易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易与礼之间有着一种普遍理与具体应用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在把古代学术分为六大类的同时,对各自的内涵及其关系作了区分,认为“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在此,刘歆提出了《易》在六经中居主导地位,且为五常之道的本原的观点。汉代学者陆贾在《新书》中认为,“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则明确地将《易》作为礼的内在根据,揭示无余。
王夫之在明清之际这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依据“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时代要求,对《易》作为礼的本原,作出了新的论证。首先,从时间上看,易、礼两者起源约略相同,“礼之兴也于中古,易之兴也亦于中古”(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1页。)。这种相同产生的时间,使得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共同地规划了与时代相适应的礼的精神。其次,由于“圣人之教,有常有变”(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4页。),礼乐与《易》分别体现了圣人之教的两种特性,即常与变的统一。因而,它们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但这两者又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从的。《易》是根本,礼则受《易》支配,是《易》所派生的文化形态。王夫之明确地称“《易》与礼相得益彰,而因《易》以生礼。故周以礼立国,而道肇于《易》”(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1页。)。其三,《易》之所以能包括礼的种种原则,在于“易兼常变,礼维贞常。”(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1页。)《易》作为“弥纶天地之道”的书,自然涵盖了礼的基本原则。在王夫之看来,礼是《易》中三才之道具体而微的人道原则的表现。尽管“时有常变,数有吉凶”,但是,圣人对于世事的常变两型,总能“于常治变,于变有常,夫乃与时偕行,以待忧患。而其大用,则莫若以礼。”(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1页。)凭借礼以待忧患,表明了《易》指导社会生活的功能与礼是相同的,但在范围上有宽窄的不同,但不出《易》的范围。《易》作为道的大全,是普遍的,是礼的一般的原则,礼的精神含蕴其中;礼则是具体的,《易》所揭示的吉凶,在人事方面的体现,与礼的节度相同。所以,王夫之认为“《易》全用而无择,礼慎用而有则。礼合天经地纬以备人事之吉凶,而于《易》则不敢泰然尽用之,于是而九卦之德著焉。”(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1页。)从礼方面看,违礼或应礼是人生举动吉凶的根源,但吉凶在《易》中除了来自人间的举止因素之外,更有自然的、非人为的各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它囊括了世间的一切吉凶及其根源,而礼的吉凶则纯为对人事仪则违顺的反映。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有九卦之德与礼的关系最为密切,它们反映了礼“以常待忧患”的方面,也体现了《易》之变与礼之常的统一。
在《周易外传》中,王夫之沿着《系辞下》的思路,深入地剖析了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九卦所反映的礼学精神,认为它们是“圣人以之实其情,酌其理,束其筋骸以强固,通其气以聪明”(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2页。)的工具,也是教导人们依礼而守正的卦。王夫之认为九卦之德的共同特点,就是再现了《易》中“反常以尽变,常立而变不出其范围”(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2页。)的礼学内容。
履卦涉乎忧危在于六三阴爻“失位以间乎阳”(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页。),使履卦在六十四卦中,再现的人道凶吉至为忧危。对此,履卦昭示的君子之德为“君子以涉于忧危而用为德基,犯难而不失其常,亦反求其本而己矣。”(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页。)在世事纷繁前面,反求其本是避免人生险阻的根本办法,这就是履卦之德。履作为“德之基”就体现在“初、二之刚实而无冀乎物情之应者以为之基”(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页。),也就是说履卦的初、二两爻皆阳,但却无求于外物,对外物无求的纯素本性,决定了外物也不可能宋惊扰自身,心怀坦荡,又不求外物,就可以在“行乎不得已而有履”(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页。)的情况下,“犯难而不失其常”,泰然处之。因为无求外物,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避免参与对人生有限资源的争夺,相反,在外物惊扰自身之际,却可以将自身的情况公之于众,“在心为‘素’,在道为‘坦’”(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页。),可以排除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造就的种种猜疑。用公开的“诚”,将一切因强求外物而召致忧患排除殆尽。在人际交往中,忧危险阻并非是一种不可预期的重大变故,其实,它就蕴含在平凡的言笑之中,蕴含在对他人不切实际的期望中,所谓“险阻生于言笑,德怨报以怀来。”(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页。)对这种日常生活中的险阻,要达到“履虎尾,不咥人”的有惊无险的平安,除了以宽容的胸怀、消弥招致外物反感的言笑之机外,是不可能有更好办法的。尤其是当人们一旦以谦退的态度对待外物时,我与他者的凶险关系将发生改变,一方面是客观情势将向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是“物之悍戾者亦恻怛而消其险。”(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页。)从自我对他者的关系改变的过程看,履虎尾而不咥人,并不源于猛虎的恩赐,而是“实自求之祥”(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页。),可能带来的一种结果。因而履卦作为德之基,主要体现在“初与二,无求者也”的身上,无求于他者,而反求自己,在反省中调适人与我的关系。
“是故谨于衣裳袺襘,慎于男女饮食而定其志,则取诸履。”(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2页。)履的礼学意义,是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庸言谨行中对礼的原则的践履。尤其是自《易传》中对忧患意识的阐发,将九卦之德作为消解忧患的手段以来,《易》的礼学原则,更为人们所注目。履卦的《象》传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对此两语,近代学者张洪之曾称,“象传两语,可括《仪礼》全书。礼云: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防患也。”(注:马振彪:《周易学说》,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上下之辨,之所以可以概括《仪礼》全书,在于它关乎个体各自的位与德,也是人们谨守各自的职分与修养德业的根据,礼正是通过尊卑上下原则来使社会中的众多个体各安其分的。司马光在对“辨上下”的阐释中,称“履者,人之所履也。民生有欲,喜进务得而不可厌者也,不以礼节之,则贪侈无穷。是故先王作,为礼以治之,使尊卑自等,长幼有伦,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觊觎之心,此先王制世御俗之方也。”(注:马振彪:《周易学说》,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如果说履卦的象辞所阐明是“辨上下”的尊卑原则,那么,是《序卦》所阐明的则是履卦对礼的践履原则。《序卦》称:“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这就明确地将履与礼对应起来,《荀子》称“礼者人之所履也”,也正强调了礼的践履原则。
履卦初九的“素履,往无咎”,为人们对礼的践履原则提供了解释的文本依据。宋代学者胡瑗在其《周易口义》中对《易》中的礼学原则的揭示,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他称“礼以质素为本。往则践而行之之谓。”清代学者李士珍则称:“素,无饰也。履道之始,无位之地,外不求应,内不失正,素位而行,无假缘饰。礼曰,甘受和,白受采。初之素,礼之本也。”(注:马振彪:《周易学说》,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王夫之在强调履卦所昭示的践履原则时,则着力批判了老庄的那种退婴式的逃跑主义,认为世间所谓以道消“履虎尾”之凶、或以数驭“虎”之凶的机变之士,其实他们“浮游于二气之间,而行不碾地”,“绝地而离乎人”(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页。),是不可能真正“履虎尾”的,“履虎尾”作为身处忧患的象征,与那些对人生漠不相关而自逃其难的退婴主义者、醉者是无缘的,因而他们也就难以体察到“履虎尾”这种人生忧患的艰辛。
谦卦之德,在王夫之的视野中,主要取《象传》的“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之意,即对多者进行节制,增益寡者,使其文彩焕燃,“执平施之柄,则取诸谦。”(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2页。)《系辞下》抽象的“德之柄”,在王夫之那里被还原成了人事法度的平施之柄。这种“平”符合谦的原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朱子所称:“人多见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谦则损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使是平也。”(注:[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五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769页。)这里的“平”就是自我贬损,也就是谦卦初六的《象》所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这种卑以自牧与《礼记》中的“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的精神是相通的。今人高亨对谦卦所概括的“地卑而山高,地中有山,是内高而外卑。谦者才高而不自许,德高而不自矜,功高而不自居,名高而不自誉,位高而不自傲,皆是内高外卑,是以卦名曰谦”,则全方位地揭示了谦谦君子在才、德、功、名、位等方面,对表现自我价值的节制。这种自我贬损正与“人道恶盈而好谦”(注:[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的社会期望相一致,也与庸人的社会尺度相一致。但是,这种“平”的方式主要取决于君子的德性,它是一种以牺牲自己的所得或抑制自己高出平均水准的德性来与世俗达到同一水平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这是有德性的人通过自愿让渡自己的所得而赢得社会整体的公平的方式,这种“平”虽与社会大多数人的期望相符,但却不宜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尤其是当有德者们将这种与自我德性相一致的裒多益寡方式推行到全社会范围时,就出现“削其多者以授寡者”(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页。)的平均主义式的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它就是对“多者”的侵害,人为地造就新的不公,必然导致因多而被剥夺者的怨愤。从自我方面来看,这种自我的贬损、抑制,若放在社会分配中,明知却故意地对他人的分配多于自己,这种方式就是个人对自己做了不公正的事。而这类事情只有那些谦虚知足的人才肯做,它是无法作为一条普遍规定而期望所有的社会成员遵奉的。
在王夫之看来,在行动上要做到符合礼的精神,但在财富的分配中又不放弃自己的所得,最理想的施平方案是增益社会的总体财富,而不是以剥夺一部人而补救另一部分人,所谓“平不平者,惟概施而无择,将不期平而自平。”(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页。)这种社会福利的整体改进方案,是以承认既存的多寡差异为前提,并指望通过消除绝对贫困而保证全社会福祉的增进,它实施的策略是“寡者益焉,多者裒焉,有余之所增与不足之所补,齐等而并厚,乐施之而不敢任酌量之权。”(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页。)将酌量之权悬置,让看得见的调节之手给一切人,无论是寡者还是多者都带来福音。这种平等是基于一切人所共有的生存条件的改善,使人们都得到基本生存保障的提高。但是,这种基本生存条件的平等,必须有社会财富的增加作其后盾的,否则,欲使全体社会成员生存的平均水准共同提高的愿望,只可能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画饼。在这里,王夫之事实上是将对多者的现状的承认,而且亦给予与少者相同的补助,看作是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办法。尽管他看到了这种“概施无择”可能会带来新的不平衡,即一方面是加剧了多者与寡者的鸿沟,另一方面是使寡者在享受福祉的同时出现新的心理不平衡。所以,他期望在“概施而无择”的公平原则实施过程中,“多者不能承受而所受者寡,寡者可以取盈而所受多,听其自取,而无所生其恩怨。”(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页。)但是,这种听其自取,且又希望多者在这种君子普降甘霖的“概施”中,能自觉做到“所受者寡”,则又回到了对多者的道德期望上来了,而这种发自内心的“裒益者”所实行的厌足之道,在生活中与大多数人对追求财富的本性相距甚远。相反,人们对于货贿之事,无不是孜孜以求的。所以,王夫之又清醒地看到,谦德作为“持物之长短而操其生死”的方式,是对待小人不得已的工具。尽管它是为了“调物情之险阻”,使公平作为一种理念使大多数人受惠,但它又无疑地带上了“以迎人之好,邀鬼之福”的阴谋之术的意味,德性便被贬作了“身涉于乱世之末流,不得已而以谦为亨”(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0页。)的处世策略。
对于谦卦的“裒多益寡”的解释,王夫之虽然在卦中的解释与《系辞下》的解释中,都涉及到了“调物情之险阻”的分配原则,但他前后解释的根据并不完全一致。在谦卦中,他对“裒多”解释为给“多者示裒”,是一种“有余之所增”的积极行为,这与《象传》的原意恰为相反。但在《系辞下》中,他又回到了《象传》的礼学思路上来,以礼的原则进行分配(注:孟子《尽心上》曾称“食之以时,用之行礼,财不可胜用也。”),对多者进行限制,所谓“裒多以为节,益其寡以为文”(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2页。),同样,《系辞》中对“谦,德之柄也”的解释,则要求“执平施之柄”(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2页。),这又明显地与谦卦中“乐施之而不敢任酌量之权”(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页。)的作法是相矛盾的,而这种矛盾体现了“圣人示平道焉以消其不平”方式上的差异。如果说在谦卦中,王夫之认识到“调物情之险阻”的忧患时,社会中只有两种类型的道德人格,即君子与小人,君子对于“有余之所增”的小人,与“不足之所补”的小人,一并予以财货上的增益,体现了君子对待小人的博大胸怀的话,那么,在《系辞》中,王夫之要求依礼对多者进行节制,给予处于社会弱势的寡者的关怀,使他们也能沾染礼乐文明的光辉“以为文”,则是一种以礼为德的解释思路,他依据礼的限制性原则,使得“圣人执平施之柄,裒多益寡”具有其合法性。即便依礼而执“平”也并非是完全平均,而仅是使“寡者”的生活略有比较得体的表现而已,它的前提依然是以等级的不同需要为依据的。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依礼的等级而分配、消费,对社会心理可以取到平衡作用。这就正如《荀子·荣辱》所称:“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个体所占有的资源多少,只要与社会各阶层的礼相符就可以做到心安理得的。
复卦所具有的礼学功能是“别嫌明微,克己而辨于其细”(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2页。)。由于复卦是阳一而阴五之卦,“阳一故微,阴五故危。”(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8页。)这是说复卦所显示的忧患,在于“一阳居内而为性,在性而具天则,而性为礼。五阴居外而为形,由形以交物状,而形为‘己’。”这样,一阳与众阴之间,构成了以少驭多,贵内而贱外的格局,但一阳与五阴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心存戒惧的交往,阴与阳之间,惟恐相犯。若从形性方面看,一阳代表的是内在的性,也即是礼,而五阴代表的外在的形,是个体的血肉之躯。由于形质的本我,与人的本性相对立,作为礼(即本性)的对立面,它往往要随外在条件而改变,因而,“克己”即规约六二爻以上的众阴,就是以礼来约形,克己以复礼,就是要返回到与天俱尘的本性上来。在王夫之看来,“人之初生,与天俱生,以天具人之理也。……凝其初生之理而为‘复礼,。”(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9页。)“复礼”从根源的意义上讲,表现为“复以为知”的道德自觉,而人作为天地之心,其道德自觉取决于“不息之诚,生于一念之复”(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0页。),这样,复卦既为外在规范意义上的“小而辨于物”的礼,提供别嫌疑、决是非的先验根据,又为人性的自我完善规划了“不远复”的反省路线。
贞常不变是礼的主要特性,但是,若一味地贞常也容易走向礼的反面,变作失礼。《礼记·礼器》中称:“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注:[元]陈皓:《礼记集学》,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202页。)《乐记》中强调“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在王夫之看来,这种依时而变礼的精神,是取法于恒卦的。恒卦显示的忧患正是“时”,“恒者,咎之徒也。非恒以致咎,其时咎也。”(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9页。)在这种凶咎之时,“体道者安其故常而不能调静躁之气”(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0页。)既有个体认识的原因,也有时代风雷激荡的原因。但人们若仅在形式上“安其故常”,以为自己的行为是在守礼,而不能在根源层面上“体天地贞常之道,敦圣人不息之诚”(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0页。),那么这种恒的形式恰恰不能保证礼的长存,因为历史的辩证法往往与个别的人愿望相反,守恒之道在于“非恒也而后可以恒,恒者且不恒矣。”(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1页。)一切恒常之物都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无论是情、势、位均是如此。所以,王夫之清醒地看到,“情不可救,势不可因,位不可怙。怙其位以保其固然,故恒四跃马关弓而禽终不获,恒初陆沈隐蔽而贞以孤危。”(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0页。)这种从恒四爻与初爻的恃有常位却一无所获中,可见“立不易之方”的礼固然重要,但若“恃之以终在”,以之为亘古不变的法则,则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样,礼取之于恒的,就不仅是“天尊地卑,雷出风入之规矩”,相反它主要汲取的是“巧者天地圣人之所以恒”(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1页。)的变的智慧,也即是《彖传》所明示的“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在凶咎之时,能以非恒而求其恒的态度处世,就能做到“涉于杂乱而酌情理以不拂于人心”。(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2页。)礼只有做到不拂于人心,才能体现出“管乎人情”、“负天地之情”(注:[元]陈皓:《礼记集学》,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333页。)的特征,只有这种本乎性情的礼,才具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注:[元]陈皓:《礼记集学》,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328页。)的功能。
损卦的礼学意蕴,在《系辞下》中被解释为“损,德之修也。”而修德是通过对自我的自由意志的抑制来实现的,即《象传》所云:“君子以惩忿窒欲。”王夫之认为,“柔以惩忿,刚以窒欲,三自反以待横逆”(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2页。)这种克己的态度就是损卦所含蕴的礼学精神。在王夫之看来,惩忿与窒欲都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就是个体情感存在忿的发动与欲的鼓动。君子用“损”的精神来指导自己立身处世,所需惩忿的忿是已处于爆发之际,“忿非爆发,不可得而惩也;用之于‘窒欲’,而欲非己滥,不可得而窒也。”(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页。)若没有忿已爆,欲已滥这种特定的条件,“若夫性情之本正者,固不得而迁,不可得而替也”(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页。)更不能对它不加区别地惩窒了。对于什么是不可惩窒的正常感情,王夫之主要列举了两种代表性的类型:一种是“大勇浩然,敢抗王侯”的“性主阴以用壮”的激情爆发,它们似忿但绝非普通的忿,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系统的反抗,它针对的对象是特定的暴政或异族的入侵;另一种是“好乐无荒,相思辗转”的对异性的正常渴慕。这两种性情发动的正当的形式,是不容惩窒的,它们是人所具有的“清明之嗜欲,强固之气质”(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页。),是人生有意义生活的必要条件。如果说惩忿窒欲是通过个体修德的方式来达到“损以远害”(注:[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的目的,那么,王夫之以为取之于《损》卦的“三自反以待横逆”的态度,则是调节人际关系的礼所固有的要求。孟子在考察“三自反以待横逆”时,先于王夫之作了具体的阐发。在《离娄下》中,孟子依据“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礼学对待原则,设想了“三自反以待横逆”的人生境遇。假若有人待我以蛮横或忤逆,一个君子的正确反应应该是反躬自问:“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注:[清]焦循:《孟子正义》上海书店198年版,第350页。)而不是勃然大怒,经过反躬自问,自认为自己的行为符合仁的精神、礼的要求时,就再想一想这种横逆是否导源于自我行为的不忠,“三自反”就是从仁、礼、忠三个方面来对人我关系所作的系统反思。若这三个方面均做得无所欠缺,我们就有理由确定“横逆”是凭空来自作为对象的妄人的无知,而不是作为主体的自我道德的缺陷。正是在这种“自反”过程中,人既抑制了非理性的暴怒,又表现出了优雅的礼乐教养。
在社会生活中,真正符合礼的精神的作法是既有讲求齐一的,也有容许异制的。《礼记·王制》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问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后易其宜。”(注:[元]陈皓:《礼记集学》,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114页。)这里强调因地制宜、依从民性是礼的重要出发点。《礼运》中称礼之不同,是圣王顺从民情的结果,“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注:[元]陈皓:《礼记集学》,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199页。)《礼器》中强调“礼之大经”为必举其定国之数,也就是“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同样强调的是因地制宜,并认为“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恰恰是一种非礼之举。这些强调礼在特定地域、特定时间、特定人群中表现出形式的多样性,王夫之认为是源自益卦的启示,益卦所表现出样性,王大之认为是源自益卦的启示。益卦所表现出的“因时制宜,如雷风之捷而条理不穷”(注:[元]陈皓:《礼记集学》,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201~202页。)的精神正是为礼所实行。益卦所体现的忧患在于“匮而不给之患。”(注: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2、100页。)王夫之比较了自然界(阴阳)以及圣人对待万物的态度,认为“阴阳与万物为功而不同忧;圣人与万物同忧而因以为功”,因而对于万物匮乏带来的忧患,阴阳是无须思虑,且也不能思虑的、不计较的。圣人则不然,在“博施忘己”的时候,就离不开万物。对于有限的财物,尽管可以“以义制我而不保己以贪其利”,但圣人在损己往益的过程中,必然只能“节宜五行而斟酌用之”,才可以使天财地产与阴阳的造作相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