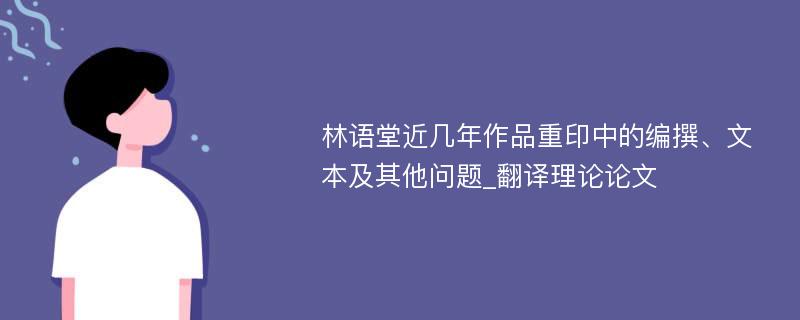
近年来林语堂作品重刊本中的编选、文本及其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刊本论文,及其它论文,文本论文,作品论文,林语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近年来各地重刊的不少林语堂作品编辑质量不高,出现问题较多。林为我国近代作家,没世不及二十年,但他的许多书却错记缪误严重,几予人以不堪卒读之感。事实上这一情况已经影响了正常的阅读与欣赏,从而构成了近代作家的书而亟需版本考订的奇特现象。对此本文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从林书重刊的编选、文本及其与阅读欣赏的关系等角度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与论述,并对其造成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林语堂对于今天的不少年轻人已快成了陌生的名字。这是不奇怪的。他的著作在大陆上已绝迹(应当说是禁绝)了三十年以上,超出一个世代。这中间的原因当然主要是政治上的。这点不言而喻。他的名字甚至是招祸的。正是为了这个,我在天津家中的一批林的中英文著作(约计十四五种)在文革初期曾被我的父母悄悄处理掉了,否则后来抄家抄了出来,就会是不小的麻烦。由于我深爱林的著作,至今引为憾事。八十年代后,情形有了改变。各地出版社纷纷刊印起他的书来。他的前期文集《剪拂集》、《大荒集》(上下线装两册)曾被全文影印发行。他的各式各类的选集、赏析本、评注本、删节本、翻译本,厚的薄的,单册的多卷的,也被众多的出版部门争先恐后地竞相推出,以其新的版面和装帧吸引着新一代的读者;另外评论和研究林的作品的文章也在不少期刊杂志尤其在学报上骤多起来,总之可谓极一时之盛,接近一个小热潮。这按说是件好事,大好事。对于我们一般读者来说,能够较容易地和不受限制地去尽情翻阅和欣赏这位我们心爱的作家的作品,自然也是一大快事。但是另一方面,这事也明显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这就是由于版本不佳、编校不精等也给林著的正常阅读增添了不少不应有的困难;个别选本甚至达到了粗制滥造、颠倒错乱的程度,令人难以容忍。近读林先生次女林太乙所著《林语堂传》,其中提到,他父亲的英文作品“有许多滥译的,都不堪一读”,又说,“那些滥译本,他看都没有看,要不然,不知会发多大的脾气。”(见该书188页)读后颇有同感。其实林著的重版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决不仅限于译本一端;事实上这事已从译本扩大到著作本身,但集中地讲,则首先还是一个版本问题。
说到版本,这在阅读上是件大事。所以历来读书都十分注重版本,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学者和专家固不必说,就是稍稍有点身份的人,读一部书时也常要强调某某书他是从什么什么本子读的。如果他是洋人,他在读到如莎士比亚或吉朋的著作时,每每会提出这些他是从W.G.Clark,J.Glavier,W.A.Wright编订的剑桥本和从四开的初版本读的;如果是我国的学者,那考究的程度就会更不得了。所以西方素有版本批评与版本比较之学,而在我国,由于历史的悠久与典籍的繁富,加之古书真伪的难辨、假托的严重以及脱文、衍文、错简、倒置等的复杂现象,书籍的校勘工作一向便是和版本学、目录学、辨伪和考据等学问密切结合着进行的。而且典籍的时间越古,版本上的问题也就会越多。现在回到林的著作。林属于近代作家,即使他的最前期作品,距今也不过六十余年,根本谈不上古,因而按说本不应发生多大的版本问题,更难言对林书有多大的辨伪工作!”①但是真正或完全“假”的“伪”的虽未必很多,“劣”的“次”的却绝不在少,而仅仅后者已经足以为害而有余了,面对它们你却毫无办法,它们不象盗本品那样,一经发觉,(至少从理论上)可以对之查处。下面笔者即准备就窜入林作的种种舛谬杂乱的成分,和就它们给正常的阅读与欣赏带来的危害及其造成的原因,谈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 双语作家与两种文本
林氏是一位古今中外都极罕见的双语作家,他的作品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有他自己的中英文两种文本。这个既是他个人写作上的一大特点,也往往给阅读和欣赏他的作品带来一定的麻烦,因而是读他的书的人(更不必说编他的书的人)所不可不知的。这里需要紧接着解释一句,所谓相当一部分“还有他自己的中英文两种文本”的话,这里仅指由林氏自己所著成或译出的文本;他人所译的林作当然不在其内,否则也就无所谓双语作家。为什么这一条我们这里要特别强调呢?这乃是因为,以笔者看来,这一情况对理解和欣赏林作有其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上面提到林是双语作家和他的一部分作品有他自己的中英文两种文本,那么他的另一部分则显然并无由他自己完成的那两种文本,而仅有其中之一,也即是说,他的另一部分作品在写成后并无由他本人亲自完成的译本。正因为这样,林书版本中各式各类的问题就全出来了。在林生前,未经林亲自准许的种种不够格、甚至文理不通、理解与表达都有问题的低劣译文已经为数不少,而当他故世之后,这种胡乱抢译的情况就更是有增无减。在前一段,林的书不刊于大陆,这种危害还仅限于港台,近十余年来,环境的宽松已使各类盗版劣译侵入到整个神州大地。不少书商和编辑完全不晓得林的书还有原作与译文这回事,于是把许多林作的译文也完全当成他的原作来对待,以致所编印的书在读者的心目中造成极混乱的印象(在这方面,亦即是著是译,许多读者自然比上述编辑更难于辨认)。其实由于昧于这一基本情况而在编选和阅读方面造成和出现的问题尚远不止此,这些下面还得细说,但问题的总根源却似乎主要还在这里——对双语作家和两种文本一事太欠明确。
二 两种文本在写作上孰先孰后
这在林语堂也是他作品上一个带有很大独特性的现象,故不容忽视。既为双语作家,他的作品的相当一部分又具有着其自备的中英文双套文本,那么一个很自然的结论便是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短篇散文之作)中有相当一部分会带有甚至就属于翻译性质,于是也就属于后出的。这样,在若干篇内容甚至标题都完全或基本相同的成对文章中,其中必有一些篇是先完成的——是为著,一些篇是后完成的——是为译。至于其中又哪些是前者,哪些是后者,这就得费点心思去弄清楚。但为什么要费心思去弄清楚呢?因为这事牵涉到行文、表达、语体、风格等许多方面,处处都与我们阅读和欣赏林文大有关系。至于这事(一次表达与再度表达)在语言学或翻译理论上的意义,那就更是有待专门学术深入发掘的重大研究课题。再说,这事给我们的观感也会很不相同。一部作品从原文去读和从译文去读,所得印象会一样吗?这不相同和不一样自然便影响着阅读效果和欣赏水平。所以同一作品的两种文本之孰先孰后,不论对林作的编者读者,都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也是编和读林氏之书与其他人的作品不大相同的地方。那么这些同一作品的两种文本是孰先孰后呢?
这里的情况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但概括地说,至少有以下三种情形:1、两种文本产生的先后绝对清楚无误的——属于这类的有,独幕剧《子见南子》(中文本在先,英文本Confucius Saw Nancy在后)、《中国文化之精神》(英文本The Spiritof Chinese Culture在先,中文本在后)、《啼笑皆非》(英文本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在先,中文本在后,又其中前十一章为作者自译,后五章为徐诚斌译)等等,2、两种文本的发表年限大致清楚,至少无大误者——属于这种情形的可列入林在The China Critic Weekly《中国评论周报》)上The Little Critic一栏中所曾发表,而后收入于商务的The Little Critic,1st & 2nd Series(《林语堂英文小品甲、乙集》)中的相当一部分(不是全部)文章;这些文章则稍后又以中文文本陆续刊出于《论语》、《人间世》与《宇宙风》等杂志,并不久收入林的《我的话(上、下集)》(亦即行素集》与《披荆集》)。以上的话也即是说,在林的这批散文作品(笔者始终认为这些乃是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中,一般情况是英文作品在前,中文文本居后;亦即是说,这些中文文本都不同程度的带有翻译的性质,但经过林的处理,这种翻译性质已被减至极小限度,几不为人察觉。而这一先后的根据是从这一事实来的,即The Little Critic中的英文文章发表于1930-1935年间,而《我的话》中的中文文章则发表于1932-1936年间,一般晚于前者二年左右;3、两种文本只是大致相符,并非全同,甚至在标题、细节乃至篇幅长短等都有较大差异,但写作时间也有先后之别——属于这种情形的是较少数。突出的例子为英文的The End of Life(见《吾国与吾民》)与《秋天的况味》(见《行素集》)的关系:从出版年限上看,显然《秋天的况味》在前(《行素集》出版于1934年)而The End of Life(《吾国与吾民》出版于1935年)在后。再如Confucius Singing in the Rain(见林的With Love and Lrony)与《思孔子》(见《行素集》)也是如此,前书的出版迟至1940年,当然比它的中文文本靠后得多。
三 两种文本在写作方式与风格上呈现较大差异性及其造成原因
林是一位在写作技巧、文字质量与风格上都十分成熟而又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家。除了最早期的文章外,他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老练纯净。奇怪的是,这一印象在翻阅近年来坊间的一些选本时每每消失,代之而来的则是一种在风格上驳杂不纯以及缺乏个性的感觉,仿佛面前的许多文章并非出自某一位作家之手,而是从性格很不相同的一大群作者那里胡乱拼凑起来的,因而也就缺乏着那种流贯于其间并将它们统摄到一起的文风个性上的一致性。这个也就减弱了这些作品为人喜爱的程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原因当然不止一个。林的英文作品被人抓去胡乱翻译肯定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在林的漫长的创作生涯中,由于不少作品成文的时间、地点与条件的不同,也容易形成风格上的某些差异。一件事物的形成总有它主客观方面的多重条件,写作作为一种精神活动虽说清高超脱一些,其实也不例外,它也是一定条件下的具体产物。环境条件一变,风格表达等也必随之而改变,林的散文也正是这样。那么引起这些变化的是什么呢?大而言之,是抗战,是二次大战,是作者的长期旅美等等。从小些说,是他在具体写作时对读者对象、发表场合、形式要求乃至中英文表达上文风习惯上的改变,这些,都会影响到他后来每篇作品的具体写作风格。但这样来讲,仍然难免抽象,现稍举一二实例来说明。首先,同样内容的一篇东西,写给本国读者和写给外国读者,在写作方式和文风上便会不同;其次,即使写给外国读者,发表在国人自办的外文刊物还是发表在外国人办的外国刊物,也会给写法与文风上带来差异。试以林三十年代前期为The Little Critic专栏所撰英文小品,同他以同一内容又发表在《论语》等刊物上的中文小品来作一比较,这一表达与文风上的差异便会看得明显。这即是,细观之下,两者的文风还是不完全一样的。在The Little Critic上所发表者,因毕竟要照顾西人的理解与口味,文章便多带西人风情(“林的幽默带牛油味”的话可能就是这么来的),而《论语》既以国内读者为对象,文章便自然纯乎本国风味,篇幅上也更为自由,有笔墨极简约的,因而也更符合汉语表达传统而不类西方文章。再比如,同一个林语堂,在他为国人桂中枢、陈石孚所办之China Critic撰文时,每文篇幅仅为英人Addison与Steele当年的长度,但到1941年他出With Love and Lrony时,除原来The Little Critic中一部分文章外,凡新加添的那些文章,都一概篇幅增大,以符合当代一般英美刊物的文章长度;另外短句与小段的更占优势,也是林文与西方新闻报章体更多靠拢的明显标志之一。这一切的发生本是很自然的,但如果对此缺乏认识和理解不当,也会出现本节一开头所提到的那种因所谓的风格驳杂不纯而败坏阅读胃口的情形。
但笔者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固多,编书的不善未尝不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我们的一些编辑对可能出现的这一情况是缺乏估计的,因而在其编选过程中也就始终不曾想到,他们完全有责任和有必要对上文我提到的那番意思,尽量利用前言、后话、注释、按语等各种形式为读者们多作些指点工作,以减少其阅读上的困惑和增进其欣赏的兴味。
四 作品语言上的分岐有待说明
这点与前一问题有密切联系,而造成的原因既和作者本人及其时代有一关,也与编他的书的人脱不开一定的干系,但在阅读与欣赏上却会同样起到不利作用,因而也不能不稍加说说。首先是时代的关系。时光易过,转眼之间,林的一些作品与今天的我们已大有隔世之感了。林的语言好当然好,对我们许多年轻的人怕已变得不够习惯。其次,语言上的这种分歧之感又显然和林在这方面的个人特点分不开;林在语言的使用上,除有从俗、从众和从时代的一面而外,也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特点,而与五四以来其他不少作家在语言与文字观上颇异其趣。这个就双倍扩大了他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老实说,如若不是出于对名作家老作家声望辈分上的尊重,我们今天的不少人简直会指斥他破坏了汉语的习惯(即过去人所谓的“不通”)!然而且慢,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如果英人至今尚未大举对Lamb的爱用古字与Carlyle的古怪表达以及对Aldous Huxley的成串雅语僻字等进行过什么声讨挞伐,那么我们对林也就未必不能更多容忍一些。我们似乎可以对当代的东西容忍极多,而对稍早的东西毫不容忍!其实,岂止可以容忍,我们早就应当抛掉我们一些陈旧的文字观,而好好向他学习,学习一下他的语言观与行文主张。他是有着他一整套行文用字的主张的。这些最简单地说来便是,行文虽然原则上应以口语为基础,但却又不能仅以口语为限;既然是文,便总会与口语有一定的差别。另外为了提高表达能力,书面语也就有必要从文言中酌收一部分可用的东西,这样在词汇上就有了文白或雅俗两套字眼,从而可在表现力上得到更大的增强与提高。那情形恰与近代英语相似。正因为近代英语拥有着从拉丁、法语来的和从盎格鲁-撒克逊来的两套词汇,所以才会在表现力上达到今天这样可羡的灵动与丰富。据此,他对所谓的纯口语的道路是并不赞同的(尽管他也常讲写文章应当尽量有什么说什么不可过于拿腔作调和不可把文字看得太值钱等等)。其实他的语言文字观说得更概括一些即是,言文一致,而以言为主;既要继承传统,又要符合当代与世界潮流,因而是一个极健康、合理而又全面的语言文字观。他的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点。他的语言写得既平易通俗,富于民族气味,而又极具文采,实际上是在饱读我国典籍的基础上写出的,因此读他的书虽未必一定需要处处出经入史,象读个别好掉书袋的人那样一句一个典故,但文学根基好的人肯定读起来更能欣赏。林是一位在语言的使用上极有长处和特色的作家,读他的书而忽略了他的语言,便是忽略了他最精华的部分,也就谈不上读懂林语堂。
这些,也都是编他的书的人非常需要为其读者费心指出的。但是请问我们指出了吗?
五 原作译作杂糅一处,纠缠不清
这当然也要大大影响到阅读者的兴味与积极性。谁也知道,原作与译作不完全是一回事,通常来讲,译作即便做得很不错时也难免会带一二分勉强。这也是事物本性所决定的。但原作则不同,由于它在表达时总会与某一语言的基本语性相吻合、协调和适应,这种表达通常都是较自然较贴切的,不唯意到而且词达,声音上也好听,甚至无需或不假任何雕饰也可取得某种天然的美,而这一切,和同样的效果,求之于一般的译作则不免是过高要求。这原因也很简单。任何表达上的任何优点,严格地讲,都是不大可能脱离其原来的形式而在另一种语言中获得同等程度的再现的。这正是为什么许多作品可以译得出来但却难以译得好的原因。林书的许多译作较之他的原作也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这是客观存在,不好完全改变。但关键还在于如何妥善处理。但问题是,目前不少林的选本的编辑者则对此处理得不够妥善。他们在编选的过程中,对于这个原作与译作的问题似乎从来不曾想过,于是只要遇有林记字样的便立即一古脑编进去,完全不问其为原作译作,其结果,在比如一本不过300页的林选中,译文部分竟高达200余页,而林自作的部分反不及1/3;或者更具体些说,节自《吾国与吾民》与《生活的艺术》中的章节却反而比选自《大荒集》与《我的话》的数量更大。这就未免出现了主次不分和以译压著的情况,而这样做的直接危害就是,由于林作中最精彩的部分受到不应有的压制,而使林书的受欢迎程度大为下降。当然我们这样来讲决非是否认上述两书(乃至更多的书)是林的作品,或者要说它们的质量如何低下。但毕竟这些书无论在写作对象、写作方式、书籍性质、篇幅以及写作目的等等方面,都与《大荒集》、《我的话》有了较大的距离,且又系出自他人的译文(有的甚至在译作上也不是高手),现在不加区别特别是不加说明地简单并置拼凑在一起,结果使一些人的不佳的译句也被误会为林自己的文笔,这种不负责任的选本所能带给读者的印象只会是大煞风景。要知道纯以完美精粹而论,那些来自上述大书中的章节当然是无论如何也抵不上那些短篇的——这些更是林文中的精粹。那些大书中的优点长处只是经过相当的篇幅之后才能渐渐看出一些,而不是立谈俄倾之间所能迅速察觉,而且在写作上既主要以西人为对象,方式与风格亦多如之,因而与那些精彩的短篇并置于一帧之内,其不利于阅读与欣赏是不难想见的。
写到这里,似乎有必要对上面个别提法作点补充或解释。不错《我的话》乃至《大荒集》中所收不少文章,如笔者在前二节中所提出的,从根源上说已属于二次性表达,亦即已带有译作的性质,但是这些通过林的一番神奇处理,已可完全当作林自己的写作来看——林自己就是这么看的,关于这点笔者拟另撰一文以论其详,这里即不多说。
六 自译和他译构成了另一对矛盾
此节系紧承上节而来。在林的选本中,不仅有着原作与译作的冲突(误将译作为原作,对读者与作者两不利),而且还有着自译与他译的矛盾,这也是编和读他的书的人不可不察的。自译和他译是很不相同的,这点不论在翻译的性质上还是在效果上都是如此。为了弄清其间的关系,先请看看几则译例。林在1935年曾将其英译的《浮生六记》首刊于当年的《天下》英文月刊1-4期,英译文开头有一篇他自撰的序言,事后他自译为中文。以下例子就是从那里摘出的。
1.Yun,I think,is one of the loveliest women in Chinese literature.She is not the most beautiful,for the author,her husband,does not make that claim,and yet who can deny that she is the loveliest?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一个最可爱的女人?
2.She is just one of those charming women one sometimes sees in the homes of one'sfriends,so happy with their husbands that one cannot fall in love with them.
她只是在我们朋友家中有时遇见有风韵的丽人,因与其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
3.I dare say there are a number of such women in every generation,except that in Yun I seem to feel the qualities of a cultivated and gentle wife combined to agreater degree of perfection than falls within our common experience.
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不过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中不可多得。
4.For whowould not like to go out secretly with her against her parents'wish totne Taihu Lake and see her elated at the sight of the wide expanse of water,or watch the moon wich her by 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Years?
你想谁不愿意和她夫妇,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观玩洋洋万顷的湖水,而叹天地之宽,或者同她到万年桥去赏月?
现在就让我们来简评一下。我们知道,翻译所以不容易做好,主要是因为翻译总是很难既极忠实又极漂亮。如果不一定都要求得那么忠实(即一忠到底,忠到每一个最微小的细节)而只是基本忠实和比较漂亮,那么有一多半的翻译还是会过得去的。不过以上所说,都是指的翻别人的东西;这时确实是事无巨细,那要求简直严格得不得了,叫你一丝一毫也含糊不得。但是翻译自己的作品呢(这个我们恐怕很少想过)?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时还会有人动不动就向你挥起忠信的大棒来吗?肯定是不会的。那时宽容就会取代了严格。宽容,还有灵活,这些幅度都会大大增加。译别人的最怕最忌的便是不忠;译自己的,还怕什么?即使不忠了,又有谁去追究?这就从最根本上保证了所译文章的质量,它的忠信度是可以免予追究的。这也就是自译与他译大不相同的一点。自译实际上是一种极特殊的翻译,性质与写作接近。
现在就来研究这些译例。请看,原文中的"one of the love liest women"到了译文里便成了“最可爱的女人?!如果这里不是自译,而是他译,请问别人让吗?"claim"译成“推崇”,也属偏话,这时编辑会令译者去自改。"so happy…that one cannot fall in lovewith them"译成“因与其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除了编辑是很年轻的外,当然谁也会认为是不错的翻译,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林的水平之高和汉语之美,但另方面却不等于说我们便也可以这么去仿效。如其我们也竟这么去做的话,姑不论你那效果为如何,编辑那一关你就会通不过,而且还会蒙受造作或卖弄之讥。不过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因为这是自译其文,因而才能享受到很高的灵活幅度,并因此效果也就更好一些,否则又曷克臻此?第三句的译文若与其原文相比,似显得更为精练;再者,译文极灵活而不拘泥,这效果的取得又与译文属于自译不无关系。最后第四句中原文的"with her",而中译作“和她夫妇”,也是只有自译才会有的。"wide expanse of water"译成“洋洋万顷湖水,而叹天地之宽”,确实极好,但也属于偏灵活的处理,通常人们不太会这么做。
以上简析说明,即使抛开水平或文才不提,同样一篇文章的翻译质量在自译和他译也会是不同的,即总是后者不及前者(他享受到的自由度你享受不到)。既然如此,如果一篇文字已由其原著者自译,他人则大可免去重译的麻烦,而且即使出于不了解抑或其它考虑而竟然再译了出来,这时林选的编辑人也最好拒收,以免在文字水平上降低林作的质量。但可惜有些翻译者和编辑人不曾想过这层道理,不是不经调查就干起这种重译的事体(以致提不出高质量的译文),就是不选作者的自译而反选他人的译文(以致编不出更理想的选集),结果都影响了阅读与欣赏。这一问题特别发生在With Love and lrony 的中译本一书,下面左列中的译文(他译),在右列中都已有林的自译(尽管有些添加变动),因而也就是编选人的问题了。请看:
《我喜欢同女子讲话》《女论语》
《家园之春》《记春园琐事》
《无折我树杞!》《冀园被偷记》
《予所欲》 《言志篇》
《遗老》《思满大人》
《阿芳》(名虽相同,但非林的文字) 《阿芳》
《中国有臭虫吗?》(情形同上) 《中国究有臭虫否?》
《忆狗肉将军》(情形同上) 《忆狗肉将军》
《与肖伯纳一席谈》(系林的自译,但改了林的标题)《水乎水乎,洋洋盈耳》
《我杀了一个人》(同上)《冬至之晨杀人记》
其实,不仅上书是如此,其它一些选本也多有类似情形,即放着林的自译不知去用,却反而用了质量远逊的他人翻译。
七 编选林书的人缺乏时间观念,前后混乱不清,读来令人摸不着头脑
这也是坊间不少林选的一大弊端。象林这样著作等身,写作生涯长逾半个多世纪的大作家来说,这种全无时间观念的选集是难以想象的;说真的,它们哪里够得上什么选集,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牟利而胡乱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罢了。这种恶劣选本惹人不满的另一原因还在于,它们把那本来不指也会有几分自明的一条写作发展路线也全给搅乱了。一个人的作品从幼至老是不会全无变化的,所以前人论文时,每有某人某人文风曾经三变几变的说法,比如说他如何是少而才藻艳发,及壮所作皆务为治,多凌厉语,老而渐入平淡,等等之类。而这个离开了一定的时间标记,又怎么能看得清?林的情形也不例外。他成名的确很早,但在写作上也自有他的一条发展轨迹,从中可以看出他曾如何迅速地迈出学徒期而逐步抵于成熟,以及嗣后如何名声更甚,而终于成为写作大师和文坛骁将的;而这个一路追踪而下,颇予人以其来有自与波澜壮阔之感。但现在徒因编辑上的不得力,使人竟看不出来,岂不十分可惜!
八 不少选集不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而只是从别人已编出的选本中作第二、三道手的翻印,结果以讹传讹,害已害人
这个,其本身既是一种弊病,一种亵渎编辑神圣职责的表现,也是造成上述种种问题的另一根源。这一道理比较明显,篇幅关系,兹不具述。
除此而外,由于多至数不清的原因而造成的问题障碍还有以下许多,诸如掐头去尾、任意删削、甚至高位截肢、中段腰斩、张冠李戴、错栽篇名、误记年月、胡拼乱凑、自我作古,点窜原文、目无作者,更易标题,以及书中外文书名、地名、人名绝大部分印错,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要之,大概人类所可能出现的几乎全部差错失误纰漏舛迕荒唐乖缪颠倒混乱,在这里或许都能找见。空说不能服人,现稍举一二例来说说。比如林有《论幽默》一文,分上、中、下三篇,为阐释林氏哲学之重要文字,素有名文之目,林本人也最以此为得意(见林太乙《林语堂传》),但当此篇入一选集时,中间的那篇却被从胸到腰给大块割掉,致使此文变成终身瘫痪!再如他的《作文六诀序》,也是一篇绝妙而美的文字,现在却被某编辑从其原处肢解下来,胡乱按到《有不为斋随笔》里去(不是《大荒集》中林亲自研题的《有不为斋随笔》,而是某编者自行编辑的一个选本!),而且还将该文最后几句瞎胡砍掉,使它成了有头无尾。关于乱改原文的也举一例。林在《论握手》一文中曾两次用过“避之若浼”一语。可能某编辑见之不习惯,经查字典,原来浼即污染之意,于是大笔一挥,也就两次均将此“浼”字改之为“污”!其结果,肯定将陷作者于不通。这真是活造孽。呜呼,林没世不及廿稔,其版本已混乱至于斯极,其书已变得几不可读,请问是谁之过?且将伊于胡底?
据史学家赵光贤先生讲,清朝人因不满明人重印古书时轻易改字,曾有过这样讽刺的话:“明人刻书而书亡”。另记得陈垣先生也讲过,“日读伪书而不知其伪,未为善读者也”。现谨以此二语,奉送给林作的编者与读者。
林书的版本问题,具如上述。至于这类版本,特别是那些腐本与盗本的编选翻印乃至出版发行方面的合法性与权益等,其本身既极复杂,也超出本论范围,这里只能暂付阙如了。
注释:
①不过完全的伪书还是有的。据林太乙《林语堂传》中讲,《林语堂短篇小说集》与《百科图解词典》就是他人假冒之作,见该书2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