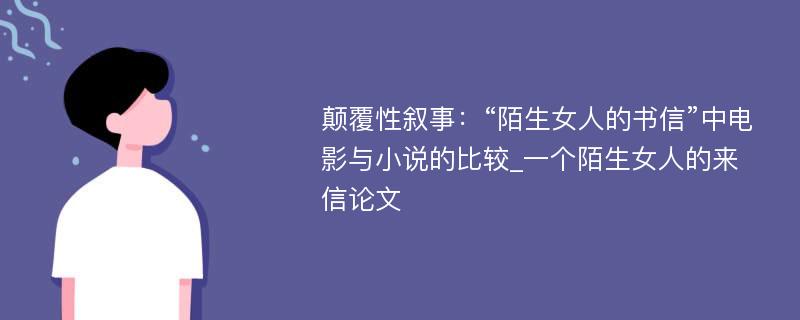
颠覆的叙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电影与小说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个陌生论文,来信论文,女人论文,电影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3月,改编自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同名小说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正式上映。该片由年轻导演徐静蕾执导,保利华亿公司出品。茨威格的这部小说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改编为电影了,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好莱坞就已经将它搬上银幕。这部由马克思·奥弗尔斯(Max Opuls)导演,琼·芳登(Joan Fontaine)主演的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中文或译作《巫山云》),大受好评。不过,这是典型的好莱坞式的改编,它使得故事与偷情、婚外恋和决斗有关,商业至上,首先满足的是人们的窥视癖,而茨威格的那种细腻心理,那种对灵魂猎捕的能力不得不屈居第二。
60年后,小说又被重新诠释,这一次它的背景被搬到了1930年代的中国北平。相比之下,徐静蕾的电影似乎更忠实于原著,她以全然的女性视角来体验和表达茨威格的笔触,在声画的世界里,集中于人物心灵的捕捉。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少女对一个成年男作家的近乎绝望的爱情。少女的绝望来自男子对这段爱情的全然不知,少女的生命在自己的爱情中成熟,又在这样的爱情中凋谢。她临死前给作家写了一封长信,倾吐自己的爱情和命运。故事从男子收到信件开始,以女子的信件自述为主要内容,然后又回到现实,以作家阅读结束而结尾。
该电影的结构与小说的结构几乎完全一致,但就在这样的貌似一致之中,叙事发生了一个重大的颠覆,其中的奥妙耐人寻味。我们可以从作品的两条线索来加以分析:一是女主人公,二是男主人公。这两条线索不仅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人物分析样本,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叙述视角,正是在对这两种视角的处理上,徐静蕾的电影表达了她不同于原著小说的理解。
一
由于电影和小说中最先出场的都是男主人公,我们还是从他开始讨论。小说中是这样叙述的:
著名小说家R到山上去休息了三天,今天一清早就回到维也纳。他在车站上买了一份报纸,刚刚瞥了一眼报上的日期,就记起今天是他的生日。他马上想到,已经四十一岁了。他对此并不感到高兴,也不感到难过。他漫不经心地悉悉窣窣翻了一会报纸,便叫了一辆小汽车回到住所。①
到家后,男仆把装了信件的盘子递给他,其中一封信引起了他的注意:
“你,和我素昧平生的你!”信的上头写了这句话作为称呼,作为标题。他的目光十分惊讶地停住了:这指的是他,还是一位臆想的主人公呢?突然,他的好奇心大发,开始念道……
典型的第三人称叙述,全知视角。此时,叙述者似乎试图将我们带入男主人公的世界,去了解他的行程,他的举动,甚至他的内心活动。尤其是那些心理描写,更让读者以为R就是故事的主角。事实上,这样的期待或许并没有错,因为,我们正是和R一道开始了对来信的好奇,开始阅读,并且在阅读结束之后,又和他一道从这封长信中抬起头来,去体会和感受:“他感觉到一次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一时间他的心里百感交集,他思念起那个看不见的女人,没有实体,充满激情,又如远方的音乐。”
尽管这一头一尾占据的篇幅是如此之小,但是它设定了一个前提:读者是和男主人公R一起观看和倾听这个女人的故事。我们被作者事先绑定在了R的角度上成为观者。
再来看徐静蕾的电影。尽管结构几乎完全一致,但是她采取了一些巧妙的方式,努力避免用男主人公的视角支配叙事过程。
电影是从信开始的。
第一个镜头是邮政所里盖戳的信件,分信,镜头跟拍邮递员骑动的自行车,转场到了一个大院门口,邮递员下车手拿信件进门往前走,挡黑镜头。叠到转动的人力车轮,跑动的车夫的脚。再切到座位上,特写:一双交叠的手,戴着皮手套,压在膝头的皮包上,悠闲地拍动。再切到人力车背后,镜头俯拍,慢慢摇起,看着他们在小巷中渐渐远去。车停在大院门口,乘客下车,迈腿进门。镜头从院内对着门口,逆光,只有人物的身影,我们看不到他的脸。
切到半空,落叶的树枝在黄昏中显得萧条。镜头从四合院的屋顶慢慢摇下来,俯拍,借着屋内的灯光,看到有人在帮刚才的乘客掸身上的灰尘。通过他们的对话,我们约略知道,这是一对主仆,但仍然看不到他们的面目。
进到屋内,主人坐下,镜头掠过他的背影,从肩头拍到他手中翻动的信件和报纸。仆人端来面条,告诉他,今天是他的生日。他一边感谢着,一边端碗吃面,展开桌上的信件。
画面淡出的同时,画外音响起:“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
黑场出片名字幕——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画外音:“我的儿子昨天死了,我和死神搏斗了三天三夜,在他身边足足坐了四十个小时……”
画面同时淡入,镜头从一个沙发靠背后面的黑暗角落摇起来,摇到已经坐在宽大沙发里的男主人公的背面。他在读信,吸烟。
画外音:“而我要和你谈谈,第一次把一切都告诉你,我要让你知道我整个的一生,一直都是属于你的,而你对我的一生一无所知……”
镜头还在摇,摇到他的侧面中景,我们听到他的叹息,但仍然看不清他是谁。
这一段影片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电影为什么开始于信,而不是像小说中那样开始于男主人公?第二,为什么电影要利用包括景别、角度、光线等各种办法遮掩男主人公的面目呢?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制造悬念,是叙事作品通常会采用的噱头,但深入分析,恐怕不尽如此。我们以为这是导演一个更深的谋划,她希望压制观众对男主人公的认同。以信开篇,并不断给信件以特写,带来的是对信件内容的期待;遮掩男主人公的面貌,使之符号化,抽象化,恰恰暗示男主人公并非故事的主角。
同样是第三人称叙事,我们从电影中获得的信息远比从小说中的相同段落获得的少。如果说小说作者强行使我们与男主人公建立了同盟关系的话,在电影中,导演则强行解除了这种关系。
在小说中,一头一尾,全知视角都向我们展示了男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但是在电影中,全片直到最后才有一个男主人公的主观镜头——他读完信,推开窗,略显惊恐地向外望去(客观镜头),镜头切到对面女孩曾经住过的房间(主观镜头)。其余的有关这个人的镜头,要么是便于叙事的客观镜头,要么成为女孩主观镜头的内容。
如此一来,徐静蕾颠倒了茨威格的叙事结构:男主人公从小说中的观者变成了电影中的被观者,不仅是女主角的观看对象,而且是观众的观看对象,观众与男主人公的联盟瓦解了。
二
我们再来讨论女主人公。
小说的主要内容开始于这么一句话:“突然,他的好奇心大发,开始念道……”(后接信件的全部内容)
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它没有用“信上写道”这样的说法,而是用的“他……念道”。如此一来,随后的那封“陌生女人的来信”便成了这个男主人公的转述,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呢?
从叙事角度上看,这种做法使得男主人公的观者地位再一次得到确认,他成了叙事者,并邀请读者参与他的“观赏”行为。借助一封信,女主人公无条件地成为了观赏的对象,换句话说,女主人公的存在是依赖于男主人公的,她只存在于男主人公的叙事之中。而如果从后现代叙事理论来看,“她”的存在甚至根本不重要。
小说叙事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在正文内容里得到了印证。
在正文中,也就是在那封信中,女主人公的人称变成了“我”,讲述了自己对男主人公那份绝望的爱情,从一个少女,到一个女人:
我的整个一生都要让你知道,我的整个一生都是属于你的,而对我的一生你却从来毫无所知……如果你手里拿到这封信,那么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已经死了的女人在这里向你诉说她的一生,诉说她那属于你的一生,从她开始懂事的时候起,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谈到第一次认识男主人公,谈到如何爱上他,那时她才十三岁,他已经是一个知名的作家了。这是孩子的纯真的爱:“这种爱情如此希望渺茫,曲意逢迎,卑躬屈节,低声下气,热情奔放,它与成年女人那种欲火中烧的,本能的挑逗性的爱情并不一样。”
童年就在这样的爱情中度过了。当“我”长大成人,终于委身于他时,他并不记得这样一个女孩。他始终处在“遗忘”中,一次次地忘记了委身于他的这个可怜的女人,直到她最后死去,给他寄来这封信,他依然只能在渺茫的记忆中找到一丝丝痕迹。
正如女主人公所说,她的一生属于这个男人,而男人对她一无所知。女主人公从感情上甚至从生命上附属于男主人公,而这些已经全都在叙事结构上暗示出来了。作为文体大师,茨威格将叙事结构与小说内容弥合得天衣无缝。
徐静蕾的电影则与茨威格进行了一次对话,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前已述及,电影开篇就故意“隐没”了男主人公,而信件的宣读者,即电影的旁白,直接就是女主人公的声音,电影的叙事者也就变成了女主人公。女主人公成为观者,她邀请观众参与到她的观赏行为当中,而观赏的对象则是男主人公。这样,从叙事上,电影已经表达了与小说全然不同的态度——女主人公不仅不属于男主人公,反而是她通过叙述“构建”了男主人公的形象。可以说,我们所看到的男主人公,是经过女主人公的感受过滤的。其中,三次细腻的感官刻画一步步织起了这张感受之网。
第一次是“听”。作家刚搬到小女孩家的院子里,小女孩并没有见到他——画外音:“一连三天,都只是听见你屋子里的音乐声和笑声,很多人的笑声。你好像只是一种声音,音乐一样温柔,笑声一样快乐。”
第二次是“闻”。小女孩帮助作家的仆人抱被子,第一次进到了作家的房间,在那个房间里,小女孩闻到了他的味道——画外音:“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你的房间,里面的一切都那么昏暗、懒散、舒适,像一个暧昧的邀请。我闻到你的味道,烟的味道,感到一股使人昏沉的幸福。那匆匆几分钟,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刻。”
镜头没有离开女孩的眼睛,通过她的眼睛向我们描述了作家的居所:宽大柔软的床,长长书架与高大窗户之间的狭窄走廊,整齐排列的厚重的书,书架后面的书桌、椅子、留声机,书架上的瓷制外国美人,一面大镜子,大镜子里对着自己凝视的女主人公……
第三次是“抚”。女孩长大成人,回到北平,遇到作家,作家邀请她到他家“坐坐”。跨入那个门槛,积满雪的长长的庭院(主观镜头),叠到特写:沙发的扶手,女子的手轻轻落下,指尖抚过;切到书架,女子的手翻过来,手背一路滑过那些童年曾经见到过的厚重的书;灯光下,湿漉漉的手心抚摩过那个瓷制的外国美人。她抚摩的是她的感情,她那来自童年的感情。
然后是炉火,温暖的缠绵……
女主人公如此俘获了观众,我们一步步与她重叠,一次次通过她的感受来理解她的心情,来审视男主人公。
至此,电影已经在叙事上完全颠覆了小说的叙事基点,把小说的观者(男主人公)变成了被观者,把被观者(女主人公)变成了观者。
不仅如此,在内容上,电影虽然一方面仍然强调“我的一生都是属于你的”,但在另一方面却出其不意地说:“我爱你,但与你无关。”这句近乎悖论的话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当女孩终于如愿以偿将要委身于他时,她抚摩的不是这个人,而是她的记忆,她的感情,这又说明什么呢?
女孩拥有着忠贞的爱情,而这爱情只是恰好碰到了这个作家而已。女孩掌控着一切,她的一生属于爱情,而作家只是一个对应的符号罢了,她为爱情而死,但这爱情只属于她自己。所以她说:“我爱你,但与你无关”。
三
美国女性主义者劳拉·穆尔维结合弗洛伊德和女性主义观点分析好莱坞电影的结构方式,她发现,在这些电影中,男性视觉快感占据了支配地位。她认为,好莱坞传统片所构成的观看方式给予影片以特有的结构方式,使被展示的女人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作为银幕故事中人物的色情对象和观众厅内观众的色情对象,从而使一种主动与被动的异性分工控制了叙事的结构,即把女人置于被观看的位置,男人做了看的承担者。②
这样的结构似乎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现代主义鼻祖波德莱尔就已经意识到了,他在一篇谈论画家的文章中说:“大体上,女人是为艺术家而存在的……远不止是相对于男人而言的女人。确切地说,她是神,是星……是一切造化铸就之典雅的闪亮的凝合,结晶成为单纯的存在;是生活的画面提供给它的沉思者的最热切的倾慕和好奇的对象。她是偶像,可能有些愚蠢,但却使人目眩神离而迷醉……”③波德莱尔的这一番论述应该是有感而发的,它正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某种特征。印象主义女画家玛丽·卡萨特1879年的作品《歌剧院》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在这幅画中,一个女人穿着黑礼服,坐在歌剧院的包厢中,她从观众席上朝画面的水平方向望去,而正当观画者追随着她的视线的时候,却发现画面的前景上有一双男人的眼睛牢牢地盯着她。作品并置了两种视线,女人的形象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空间,她专注于观剧的目光似乎也是作品的主要表现内容,但是,远处那双眼睛却揭示出真正的观者是那个男人和由此而引导的观众。正如卞之琳的诗,“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看歌剧的女人,成为了被观看的对象。
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几乎就是卡萨特画作的叙事版本。如前所述,尽管这篇小说的主体是女主人公的书信自述,但男主人公却处在宣读者(观者)的地位,并且,由于他的“邀请”,读者也站在他的角度上观看。这个可怜女人的一生则成为了穆尔维所说的“色情对象”。
这部小说的第一个电影改编版(1946年好莱坞的《巫山云》)甚至强化了这样的结构。片中,男主人公成了才华横溢的钢琴家,如此他的表现空间就更大了,也就更直接地确立了他的观者地位。该片的叙述视角非常符合穆尔维对好莱坞电影的分析。
但是,在徐静蕾导演的版本中,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仿佛是要和茨威格争论,徐静蕾保留了小说的叙述框架,但却“抹去”了男主人公观看的眼睛,强化了女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如此一来,观者和被观者变换了位置,男人成为被观者,而女人成为观赏行为的承担者,观众则被引导加入女主人公的视角中,带着一丝嘲弄,去品评姜文饰演的那个颇有些滑稽的男作家。
注释:
①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译林出版社,1997年。以下所引的这篇小说都是出此版本。
②参见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电影与新方法》第20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③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转引自罗岗、顾铮编《视觉文化读本》第34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标签: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论文; 茨威格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徐静蕾论文; 爱情论文; 剧情片论文; 美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