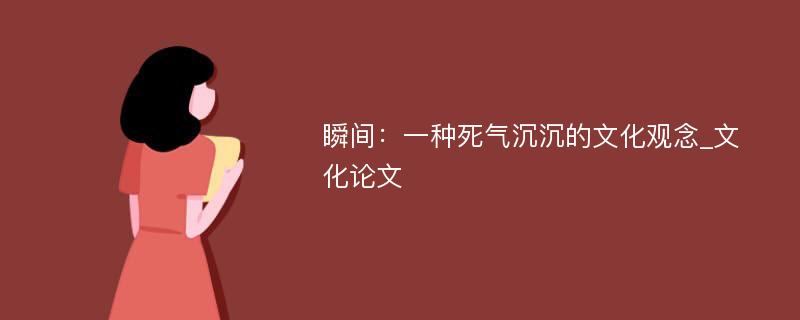
絜矩:一个已消亡的文化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文化论文,絜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起“絜矩之道”,今天的人们甚至学人,也都很少有人知道了;但它却是儒 家经典中关于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命题。《礼记·大学》篇首次提出这个概念,此后晦 而不彰;直到宋儒才将它再度重提,甚至张扬到君子之德、治天下之要道的高度;但其 后,特别是近代以后,它又再次湮灭不闻。今天研究这个命题,一方面,可以弄清儒家 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更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从思想发展的 历史说,我们也可以窥见一些范畴、概念或术语,被历史所筛选或淘汰的情景,对思想 史的认识或可有所启发。(注:关于“絜矩之道”,近代以来的学术界很少有人 研究。在最近几年来的学术研究中,个别讨论《礼记·大学》篇的文章,在介绍《大学 》内容时自然会有所涉及,如贾艳红的《<大学>主旨对后世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 学报》2002年第5期)一文,就对有关的内容有所介绍,但谈不上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 。对“絜矩之道”做过专题研究的是吴长庚先生,他先后就此发表了两篇文章:《试论儒家絜矩之道的理论意义》(《上饶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和《儒家絜矩之道的现代诠释》(《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吴长庚先生的这两篇 文章都偏重朱熹絜矩思想的考察,并侧重对“絜矩之道”现代意义的揭 示,但对它的思想史意义,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意义,则不涉及;而这一点,正是本 文的侧重点。尽管如此,吴长庚先生的文章,对本文的写作也还是很有启发。)
一 何谓絜矩
《礼记·大学》篇云:“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 ,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1](p1042)这段话是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之道思想内涵的阐扬。意思是说,大学之道强调平天下在于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是讲的一个上行下效的问题。国君尊敬老人,民众就会兴起孝道;国君尊敬长上,民众就会兴起悌道;国君同情、抚恤鳏寡孤独之人,民众就不会互相背弃。所以,国君对人民大众的行为有师范表率的作用。对于上级所做的令自己厌恶的事情,就不要用来对待下级;对于下级所做的令自己厌恶的事情,也不要用来对待上级;对于前辈所做的令自己厌恶的事情,不要用来对待后辈;对于后辈所做的令自己厌恶的事情,也不要用来对待前辈;对于身右的人所做的令自己厌恶的事情,不要用来对待身左的人;对于身左的人所做的令自己厌恶的事情,也不要用来对待身右的人。这就是君子应具备的基本品德,是谓“絜矩之道”。
《礼记·大学》篇所阐述的这个“絜矩之道”,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无疑具有重 要的意义,“絜矩之道”应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概念去对待。但是,在《礼记·大学》篇创造了这个范畴之后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除了注释家由于文字注释的原因对之进行释义训诂外,思想家们几乎没有人给予关注,使这个思想概念遭到不可思议的冷漠。自汉至唐,注释家的解释,目前可以看到的也只有郑玄和孔颖达二家之说。
郑玄注“絜矩之道”曰:“絜犹结也,絜也;矩,法也。君子有絜法之道,谓当执而行之,动作不失之。”“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于人耳,治国之要尽于此。”[2](卷六十)
孔颖达曰:“此经申明絜矩之义,上有不善之事加己,己恶之,则不可持此事 使己下者;为之下不善事己,己恶之则不可以此事己之君上也。前谓在己之前,后谓在 己之后,左右谓与己平敌,或在己右,或在己左,举一隅余可知也。”[3](卷一百五十 二)
这是注释家的语义上的解释,而非重在阐释其思想内涵,不是将“絜矩之道” 放在思想史的范畴中加以解说。从思想内涵上加以解说,真正对“絜矩之道”作为一个思想范畴给予重视并阐释其意义,则是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
根据宋卫湜所撰《礼记集说》中的记载,范祖禹是较早关注“絜矩之 道”的思想内涵的人。该书卷一百五十二载:“范氏曰:汉书云度长絜大,注 曰:絜,围束之也。《庄子》絜之百围,亦谓围而度之也。矩,所以为 方。絜矩,言度之以求其方也。既度其上,又度其下,既度其下,又度其上,于前于后,于左于右,莫不皆然,不使少有大小长短之差焉。是以物我各适其适,无往而不得其方也。天下者,国之积耳,以此推之,则自一国以至于万国,一理而已。”[3](卷一百五十二)
南宋时人蓝田吕氏释“絜矩之道”曰:“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 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盖所谓平者,合内外、通彼我而已。天下同 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虽广,出于一理,举斯心以加诸彼,推而放诸四海,而准 无往而非斯心也,犹五寸之矩足以尽天下之方,此絜矩之道也。上下也,左右 也,前后也,彼我之别也,通乎彼我,交见而无蔽,则民也,君也,将何间哉?此所以 为民父母而天下瞻仰之矣,故所以得国以得众也,所以得众以有德也。”[3](卷一百五 十二)
稍晚于朱熹的南宋学人毛居正说:“《大学》有絜,音结,当音襭。《庄子》絜之百围,谓周围而量之也;贾谊《过秦论》度长絜大,谓比量小大也;皆音襭,朱文公《大学章句》依此音。所谓絜矩之道者,矩正方之器也,
絜方方比量也,方方皆合乃为正,方己之于人,上下、左右、前后,皆揆量其情理,而无不合者,絜矩之道也。”[4](卷四)
在儒学思想史上,第一次全面发挥“絜矩之道”思想内涵的是朱熹。朱子曰: “盖人之所以为心者,虽曰未尝不同,然贵贱殊势,贤愚异禀,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实 蹈,有以倡之,则下之有是心者,亦无所感而兴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兴起矣。然上 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处之之道,则彼其所兴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 均之叹。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后有以处此,而遂其兴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为度也,曰:此庄子所谓絜之百围,贾子所谓度长絜大者也。前此诸儒,盖莫之省,而强训以挈,殊无意味。先友太史范公,乃独推此以言之,而后其理可得而通也。盖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恶者不异乎己,则不敢以己之所恶者施之于人。使吾之身一处乎此,则上下四方,物我之际,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则其广狭长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无有余不足之处,是则所谓絜矩者也。夫为天下国家而所以处心制事者,一出于此则天地之间将无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尽其心而无不均之叹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岂自外至而强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万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诚心正,故有以胜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为千万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间,则一膜之外,便为胡越,虽欲絜矩,亦将有所隔碍而不能通矣。”[5](卷二)
从《大学》篇提出“絜矩之道”,到后儒的释义和发挥,我们可以从中窥见“ 絜矩之道”的几层基本含义:
从简单的语义上说,“絜矩”即度量的意思。絜为“围而度之”;矩,所以为方;絜矩,言度之以求其方也。“矩正方之器也,絜方方比量也。”引申为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使上下四方,物我之际,各得其分,如矩之方,无大小长短之差,无多少不均之叹,至正至公。是则所谓絜矩。
“絜矩之道”即是恕道,强调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思维 方式。《大学》原文“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 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
絜矩之道”已说得很明白,后儒的阐释更有所强调。郑玄注曰“絜矩之 道,善持其所有以恕于人耳”;蓝田吕氏所谓“举斯心以加诸彼,推而放诸四海……犹 五寸之矩足以尽天下之方,此絜矩之道也”说得很是精辟;朱熹的论说更为推己及人找到了理论根据,认为“千万人之心即一人之心”,这样以己度人,实行恕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可以创造儒家和谐的社会局面。
“絜矩之道”的根本在于“均平”。从后儒的解释看,所谓“絜矩之 道”就是要达到均平的社会境界。范祖禹明确提出,絜矩就是要使上下前后左右“莫不皆然,不使少有大小长短之差焉”;朱熹更强调,有了“絜矩之道”,“使吾之身一处乎此,则上下四方,物我之际,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则其广狭长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无有余不足之处”,“天地之间将无一物不得其所”,“皆得以自尽其心而无不均之叹矣”。他认为,行“絜矩之道”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天下无不均之叹,人人各得其所,平均如一。从均平的角度去解释“絜矩之道”,是后儒对《大学》“絜矩之道”内涵的发挥或充实。
“絜矩之道”的终极关怀在于“治国平天下”。“平天下在治其国者……是以 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君子要行“絜矩之道”,是从治国平天下的角度提出的问题,强调通过“絜矩之道”去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范祖禹说“天下者,国之积耳,以此推之,则自一国以至于万国,一理而已”,君子行“絜矩之道”,一国治则天下平,“絜矩之道”的落脚点就在于万国或天下;朱熹所谓“夫为天下国家而所以处心制事者,一出于此则天地之间将无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尽其心而无不均之叹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平天下的目标与关怀也极为明确。最早看到这一点的是郑玄,他所谓“治国之要尽于此”,就直白地道出了“絜矩之道”的这一功能和作用。
“絜矩之道”是一种君子之道,强调君子、在上位者的表率作用,通过上行下 效实现平天下的终极目标。《大学》引文开宗明义,就是讲的这个君子对人民大众的师 范表率作用。“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正是有感于这种客观存在的师范表率作用,才提出了“絜矩之道”的问题。
以上是对“絜矩之道”思想内涵的简单抽象。为着更深入地认识其思想意义, 我们还需要对它做更广泛更细密的讨论,这就是本文后边将要展开的工作。
二 “絜矩”:均平概念的另一种表述
尽管“絜矩之道”如上所述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但它却不是一个独立的思想 文化概念。大量思想资料证明,它只是中国古代“均平”观念的另一种表述,而缺乏作 为一个思想文化概念的独立性品格。这一部分,我们就来讨论它和均平观念的思想关系 。
(一)以“平均”释“絜矩”
《礼记·大学》篇谈到的“絜矩之道”,从其原文看只是两层含义,一是强调 君子、在上位者的表率作用,二是阐述了一个“恕”的观念。此后千余年间,《大学》 的“絜矩之道”几乎成为绝响,无人问津,直到南宋朱熹的时代才被人重新提 起,并赋予了诸多含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文化中的“絜矩之道”,是朱熹所发明的一个概念。而朱熹的“絜矩之道”概念,则是一个均平概念的别称;并且在朱熹之后,对“絜矩之道”的理解,基本上都是沿袭了朱熹的说法。
前引朱熹的话中已讲明他对“絜矩之道”的基本理解:“使吾之身一处乎此, 则上下四方,物我之际,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则其广狭长 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无有余不足之处,是则所谓絜矩者也。”《朱子语类》中还载有他另外一处的解释:“平天下谓均平也……俗语所谓将心比心,如此则各得其平矣。”[6](p362~363)朱熹用均平或平均释“絜矩”的思想是很明确的。
和朱熹几乎同时代的邵氏也讲过类似的话:“矩所以为方也,上下四旁,长短广狭, 均齐若一,而后成方。所谓絜矩者,犹言斟量忖度,举斯加彼,使之均平也。”[3](卷一百五十二)这位不知名的邵氏也表明了“絜矩”就是平均的思想。
朱熹之后,解释“絜矩之道”者,几乎都将之与平均思想相联系,或直接以平 均释“絜矩”。解释最清晰者是元代的何异孙。他说:“问絜矩之道如 何,对曰:絜,度也;矩,所以为方者,今木匠曲尺是也,匠之造屋室器用也。上下四方,必使之均齐平正,所贵乎治天下国家者,与民同其好恶,使万物各得其所,相安于愿分之中,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以矩而度物,使上下、左右、前后均齐平正 也。”[7](卷二)
明代人吕柟更是将“絜矩”直接当作平均去解说。他说:“大学一部书极广大,而絜矩之道只在散财,则夫子所谓足食者,岂止仓廪充、府库实而已哉!盖欲使匹夫匹妇各得其所,无颠连饥寒者也。”[8](卷一)
“聂蕲问絜矩,先生曰,矩是个为方的器,大之而及四海,要之只在方寸,谓之絜矩,只是个无不均平意思。且如天下有样有权势的是一等,有样鳏寡孤独颠连无告者又是一等,天下之人便有这几等,怎么便得均平?故尧典称尧,则曰平章,百姓黎民于变时雍此,便是能絜矩的。象先因问天下亦大着,怎么便得均平如一?先生曰,此亦无大异术,亦只是把这些财散与百姓便能。得问百姓亦多着,怎么便能人人与他财也?先生曰,亦无大难事,亦只是要有个不要钱的官人便能得也。”[8](卷一)
吕柟讲“絜矩之道只在散财”,又讲“谓之絜矩,只是个无不均平意思”,均平如一,“只是把这些财散与百姓”,所有解释都在于说明“絜矩之道”即是经济、财富方面的平均而已。
中国古代的均平或平均,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概念,不光是具有今天人们所理解的财富 的绝对平均,甚至主要的基本的含义并非如此。古代平均或均平的基本含义是意味着公 平或公正的等级秩序的确定。只要人们都能尊奉礼所规定的社会秩序,使社会有条不紊 地进行运转,那就是一个平均或均平的社会状态,就是实现了“均平”。如:
《荀子·王霸》篇:“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 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若出若入,天下莫不 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9](卷七)
宋遗民无名氏《周礼集说》中说:“东莱曰:冡宰均邦国者,是使若贵、若贱、若小 、若大,各得其平尔。古之称宰相者,多以平为主。若商则谓之阿衡,阿衡平之之谓也 。天之所以立君命相者,不过欲平天下之所不平者尔,使四海之内,贵者贵,贱者贱, 耕者耕,织者织,士农工贾,鳏寡孤独,事事物物,咸适其宜,是宰相均平天下之道。 均之一字,是宰相之大纲。大抵天下本无事,须是识得简易道理,能行其所无事,方尽 得宰相均平之职,不是要作聪明之谓。”[10](卷二)
这两段引文对均平思想表述得十分明确。荀子认为只要人们各安其分,人们所从事的 职业符合“礼法之大分”,各尽其职乐其业,就是所谓“天下莫不均平”的状态了。说 得最明白的是那位无名氏,他认为只要是贵贱各得其分,百业各得其宜,人们都能够做 自己该做的事情,都能够在礼所规定的范围内找到自己的位置,贫富贵贱、士农工商、 鳏寡孤独都有所归,“咸适其宜”,就是人们所追求的平均之道,而不是不分贵贱、贫 富、强弱一律平等平均。这是研究古代平均思想应该注意的古今平均思想的一个差异。
公平公正各得其分的平均思想,在“絜矩”观念中也有体现。如清人陆陇其在 《四书讲义困勉录》中说:“矩字从平字生,盖平者,均平也,有一夫之不获非平也。 矩者所以为方也,方即平意。又曰絜矩字是借字,不是譬喻,作文亦不可言如。又曰,絜矩不但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须云以己之心度尽亿万人之心,盖度尽天下人之心,使各得分愿,才是所以为方。”[11](卷一)陆陇其所讲的均平和絜矩,就是要使天下人各得分愿,人人都得到自己所应该得到的东西。所应得到,就不是一种绝对平均的状态,而是一种公平合理的状态。古代平均的这一基本含义,也同样赋予了“絜矩”一词。
古代均平的另一种含义,是均衡或平衡。汉代元帝时翼奉上疏中的一段话,讲用人的 平衡问题,而他用的就是“平均”概念。他说:“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亲亲,必有异 姓以明贤贤,此圣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亲而易进,异姓疏而难通,故同姓一,异 姓五,乃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 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 。阴气之盛,不亦宜乎?”[12](卷七十五)在今人看来,翼奉讲的显然是一个用人应该 保持亲疏平衡、均衡的问题,但他却用了“平均”二字。
宋代司马光的一封奏议,对英宗时科举取士名额地域分配上的不均衡提出疑义,使用 的却也是均平概念。司马光的奏折中说:“在京及诸路举人得失多少之数,显然大叚不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虽微陋之处,必有贤才不可 诬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随其所长,各有所 取,近自族姻,远及夷狄,无小无大,不可遗也。今或数路之中全无一人及第,则所遗 多矣。……《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国家设贤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岂 可使京师诈妄之人独得取之。今来柳材所起请科场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 事理尤当,可使孤远者有望进达,侨寓者各思还本土矣。”[13](卷一百六十五)司马光 在奏议中还详细列举了各路州军取士名额的严重失衡状况,强调无论地之远近,无论京 师还是偏远之南省,名额均平分配,才有益于人才的选拔。司马光用的均平概念,显然 是均衡的意思。
从均衡、平衡角度理解的平均意义,在宋以后的“絜矩”概念中也可以窥见。 明人海瑞有《兴国县八议》,其中云:“一均赋役。古先圣人,九两定民业,九职厚民 生,而其取诸民也。又定为九赋之法,盖别内外、远近、多寡、轻重,使各相均称也。 ……县中又以失额不理所诉,其遍有轻重犹甚,奈之何民不穷而盗,盗而逃也哉?乃知 前日之言,皆不得其平,而鸣疾痛则呼父母,穷困则呼天,真情率心闲有过当之言,而 非全私己也。窃谓君子大心体天下之物,举凡天下之人,皆不当分为彼此,况在一省一 府,自笃近举远之道论之,情尤切也。今后当粮役之先,伏望批行司府查议,清查各县 之丁粮虚寔各县之人户富贫,将各县实征丁粮并原赋役,委官磨算,要见某县止当尽某县差粮,某县差粮当取某县津贴若干,又某县当津贴某县若干,上下四旁,均齐方正,君子有絜矩之道,而天下之情无不平矣。”[14](卷一百十九)海瑞的这段议论,一方面说明了古圣先王定赋役之法,别内外、远近、多寡、轻重而制定不同的赋役征收摊派标准,是出于均平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主张清查各县之丁粮虚实,均平各县差粮定额,其目的也在于使“上下四旁,均齐方正,君子有絜矩之道,而天下之情无不平矣”,都是出于贯彻均平原则的考虑,是要符合人们的平均心理。海瑞这里显然讲的是赋役征收摊牌的均衡问题,是平均赋役的问题,而使用的却是“
絜矩之道”的概念,足可见其所谓“絜矩之道”就是一个均平的理念,其本意就是以均平而达到社会的平衡。
南宋时代是中国古代平均思想比较发展的时期,“絜矩”概念的使用和流传也 因之而比较广泛。不少士人或官员之家,将自己的堂舍取名为“絜矩堂”,以表示自己贯彻大学之道的志向。南宋孝宗时人刘爚撰有《矩堂记》一篇:“予友祝君士表,取大学絜矩之义名其堂,而属予以记。……有志于仁者,当知穹壤之间,与吾并生,莫非同体。体同则性同,性同则情同,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齐而无偏吝,有方正而无颇邪。帅是以往,将亡一物不获者,此所谓絜矩之道也。然大学既言
絜矩,而继以义利者,岂异指哉?利则惟己是营,义则与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论说,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恶为当,然而私意横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尔。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蟊,正涂之榛莽欤。大学丁宁于绝简,孟子恳激于首章,圣贤深切为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则士之求仁,当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利义之分始,吾子以谓如何?祝君曰然,请以是为记。”[15](卷四)
朱熹的学生黄干也撰有一篇《袁州萍乡县西社仓絜矩堂记》,记云:“晦庵先 生初创社仓以惠其乡人,欲以闻于朝,颁之州县。江淛间好义者争效焉。袁州萍乡社仓九县西其一也。钟君唐杰为之记,有堂焉未名,胡君叔器谋于干,以絜矩名之。叔器归,以语唐杰。唐杰曰:可乎哉!以书来曰,子为我记之。干闻之师曰:
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处己接物,度之而无有余不足,方之谓也。富者连阡陌而余梁肉,贫者无置锥而厌糟糠,非方也。社仓之创,辍此之有余济彼之不足,
絜矩之方也。……质之圣贤之训,君子之道,孰有大于絜矩者乎!若夫横目自营,拔一毛不以利天下,充其小己自私之心,虽一家之内父子兄弟,尚有彼此之分,而况推之人物乎!故不能以絜矩为心者,拂天理逆人心,帝王之所必诛,圣贤之所必弃也。然则知社仓之为义而置者,絜矩者也。不知社仓之为义而不置者,不
絜矩者也。既不知之又欲坏之,是自不能絜矩而又恶人之
絜矩,贤不肖之分晓然矣。”[16](卷十九)
这两篇“絜矩堂记”,前者是祝君为表示自己的志向,将堂舍以“絜 矩”命名。这位祝君是位“有志于仁者”,他要“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齐而无偏吝, 有方正而无颇邪”,以均平之德来要求自己。其取名“絜矩”实为均平之志。后者是为义仓取名,选用了“絜矩”,而义仓之设,也是为了扶危救贫,实现社会贫富的相对均衡或均平。
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说,“絜矩”与“均平”这 两个概念有着相当大成分的同一性;或者说,“絜矩”即是“均平”的一个别 名。
(二)“絜矩”:平均天下的根本途径
“絜矩之道”最初出现在《大学》“平天下”章中并非偶然,从后来大量关于 “絜矩之道”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正是这个“絜矩之道”充当着儒家 “平天下”的手段或途径的重要功能。或者说,所谓“絜矩之道”,其终极目 标,就在于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首先,思想家们认为,如果人人都实行“絜矩之道”,就可以达到儒家平治天 下的政治理想。朱熹说:“老老所谓老吾老也,兴谓有所感发而兴起也,孤者幼而无父 之称。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所谓家齐而国治也。亦可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矣。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而天下平矣。”[3](卷一百五十二)
元人金履祥对此有更详细的解说:“夫老老长长恤孤之事行于上,而兴孝兴弟不倍之 心作于下,于此焉可以见人心之同然者矣。夫人之心本无以异于己,则己之心当推以处 乎人,使为人上者不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所欲而不与之聚,所恶而或以施之,则天下 之人将不得获其所处之分,而无以遂其所兴之志矣。是以君子于此有絜矩之道 焉。所谓絜矩者,图度取方之谓也。所谓絜矩之道者,即其在我,度其在人,必使物我之间,上下四旁,不相侵越,面面得其所取之方,人人得其所有之分,概而视之,累而观之,皆截然方正,无高低广狭长短不均之处,此之谓絜矩之道也。以絜矩之心,行絜矩之政,天下之大将无一人之不得其分,无一人之不获其所者,所以人人得亲其亲,长其长,恤其孤,而天下平矣。”[17]
“天下至广也,天下之人至众也,孰为经制之方,孰为统驭之略,传不一言焉,而惟 谆谆絜矩之义反复言之,何也?天下虽大,亿兆虽众,然皆一人之积耳。夫乾始 坤生体率性而为人,人情固不相远也。平天下者,惟以一人之心体天下人之心,以天下 人之心为一人之心,推而广之,概而处之,则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17]
从朱熹到金履祥都认为,行“絜矩之道”,一方面可以使天下均平,物我之间 ,不相侵越,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人人各得其分,这样就不会出现不满和纷争,达到 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另一方面,人人都可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一人之心体天下 人之心,以天下人之心为一人之心”,人人得以“亲其亲,长其长,恤其孤”,达到社 会的充分和谐,而这就正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理想,所追求的王道乐土。在思想家们看 来,“絜矩之道”的作用就是如此强大。所以,主张“絜矩之道”的思想家们,无例外地都把推行“絜矩之道”看做是平天下的惟一途径,目之为“平天下之要道”。
朱熹说:“絜矩二字之义,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以 此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以此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 皆然。则身之所处,上下四旁,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兴起 焉者,又岂有一夫之不获哉!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此平天下之要道也。”[3](卷一 百五十二)
明人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对“絜矩”为平天下之要道有最好的阐述:“平 天下之道,不外乎化之、处之二者而已。葢人君以一人之身而临天下之大,地非一方 不能处处而亲履之也,人非一人不能人人而亲谕之也,必欲治而平之,岂能一一周而遍 之哉!夫我有此本然之性,而人亦莫不有此本然之性;我尽我本然之性使之观感兴起, 而莫不尽其本然之性皆如我性之本然者焉,是则所谓化之也。夫我有此当然之理,而彼 亦莫不有此当然之理,我以当然之理推之以量度处置,使彼各得其当然之理,皆如我理 之当然者焉,是则所谓处之也。盖化之以吾身,处之各以其人之身,其人所有之理,即 吾所有之理是理也。具于心而为性,人人皆同,以吾之心感人之心,上行下效各欲以自 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彼此相方各得其分愿矣。必使物我之间,上下四旁,不相侵越 ,前后左右不相违背,面面得其所处之方,人人得其所有之分,概而视之,累而观之, 皆截然方正,无高低广狭长短不均之处。是则所谓絜矩也,以絜矩之心行絜矩之政,天下之大将无一人不得其分,无一事不得其理,无一地之不从其化,人人亲其亲,长其长,恤其孤,由家而国,国无不然;由国而天下,天下无不然。所谓王道平平,王道荡荡,王道正直,端有在于斯矣。”[18](卷一百五十九)
明人赵南星说:“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有絜矩之道,使远近大小平均如一,而 咸遂其兴起之愿也。……夫上下四旁人虽至众,而因心推己之中,即尽均调剂量之,法 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此之谓絜矩之道也。君子非此,何以平天下哉!”[19] (卷上)
清代《日讲四书解义》大学篇说:“曾子曰,人之制器,必度之以矩;而君子处物, 则度之以心。盖一人之心,无殊于千万人之心也。如上下四旁,位虽不一,其心则同。 ……盖以人比己,以己度人,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此乃谓之絜矩之道也。人君诚用此道以治天下,以一己之心度人之心,则天下无不各得其所,而无有余不足之憾矣。平天下之道,宁外此与!”[20](卷一)
为什么“絜矩之道”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平天下何以会非此不行?其根本的问题在于有个“均平”二字起着中介作用。
这要从“平天下”的基本含义说起。何谓平天下,传统的理解都把它作为治理天下, 达到天下太平;儒家倡导“平天下”之政治道德,就是要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参与 社会,改造社会。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很片面的,甚至没有触到其本质的含义。中国古 代的“平天下”,实际含义是“平均天下”或“均平天下”,它不光是要治理天下,还 有个如何治理和治理到什么状态的问题。在传统文献中,不少地方都是把“平天下”直 接表述为“平均天下”或“均平天下”。
《礼记·乐记》篇载:“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 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 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 ,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1](p656)
朱熹《诗经集传》原序中说:“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 无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 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 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 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21](《原序》)
明人邱浚《大学衍义补》中说:“是则《易》也,《书》也,《诗》也,《春秋》与 《礼》也,论《孟子》与《中庸》也,皆所以填实乎《大学》一书,今日在学校则读之 ,以为格物致知之资,他日有官守,则用之以为齐治平均之具。”[18](卷七十七)
这些文献中都把《大学》篇的修齐治平说明确地表述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特 别是明人邱浚更直接讲明他所说的“齐治平均之具”即是所谓《大学》之道。在这些文 献中,“平天下”就意味着“平均天下”。在另外一些文献中,“平均天下”则直接被 置换为“均平天下”,二者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如:
明人姚舜牧《重订诗经疑问》中说:“国均者,国所赖以均平者也。秉国之均,言其 所执持是均平天下之任,不可以不平者。”[22](卷五)
清人方苞在《礼记析疑》中说:“卜子在圣门,不过文学之科,曾子且罪以不能推崇 夫子之道。然观其对文侯,则春秋中国侨羊舌肸无此语言气象也。文侯自言,听古乐则惟恐卧,而正告以古乐和正以广,文武具备,可以修身及家,均平天下,受祉于上帝,施及于子孙。文侯自言,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而正告以是谓溺音,推其害至于父子,聚麀人纪,无存臣民,殉欲国维尽丧,故为人君者,不可不谨其好恶。”[ 23](卷二十)
《礼记·乐记》中魏文侯和子夏的对话,在方苞的引述中内容没有丝毫改变,只是“ 平均天下”变成了“均平天下”。可见,“平均天下”和“均平天下”完全是一个概念 ,它们都是对“平天下”思想具体的或者说强调性的说明。总之,儒家的平天下思想, 不仅仅表达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是对人们参与社会改造的激励,更是表达了他 们如何治理社会的政治理念,也蕴涵着对创造人间至公至正、均平合理的美好社会的期 待。“平天下”思想的灵魂在于“平均”或“均平”,而“絜矩之道”也要在 “均平”,“絜矩之道”即是“均平之道”,所以,如果真正实行“絜矩之道”的话,也就可以不折不扣地实现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了。这就是为什么思想家们把“絜矩之道”看做“平天下之要道”的原因所在。
(三)以“恕”释“絜矩”与均平思想之关系
从前边的大量引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絜矩之道”的思维方式即是推己及 人,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即中庸之道所讲的一个“恕”字。以“ 恕”释“絜矩之道”,是“絜矩”思想阐释中区别于直接以“均平”释之的一个显著特点。除了以上引文可以显示这一点之外,还有不少论说在解说“絜矩之道”时,即是直接使用一个“恕”字。特征引如下:
“问:‘终身行之,其恕乎?絜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絜矩正是恕。’[24](p1161)
“唯君子有絜矩之道,度诸己而安者然后动,故动不失其宜;度诸心而可者然 后语,故语必得其当;度其交之可求者然后求,故无悔吝之愆。是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 ,以人之心为己之心,故能与众同其利,而人亦与之也。若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徒知有 利不知有义,则其动也必危,其语也必惧,而人亦莫之与;不但不与之,且有起而击之 者矣。圣人举此,以为偏于利己者之戒。”[25](卷十)这段话集中表述、阐释的即是一 个“恕”字。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即大学絜矩之道。”[26](卷二十三)
“问齐治之言恕,何也?曰,不止齐治,其平天下之道,止是絜矩。絜矩即恕也。”[27](卷一)
“絜矩之道,无非以心絜心,内忠外恕之道也。”[28](卷三)
“究极絜矩之道,不过于恕而已。”[20](卷十)
“能持其所有以待于人,恕己接物,即絜矩之道也。”[29](卷七十三)
“圣贤无异学,千圣百王无异道,夫子、曾子与门人无异心,乃谓一贯之道,借尽己 推己之目以着明之,曾有丝毫见道者而肯作如是语乎?毋论夫子一生,只此忠恕。《论 语》二十篇,教人只此忠恕。即《大学》《中庸》《孟子》三书,亦只此忠恕也。《大 学》以明德新民为一贯,而务絜矩以该之;《中庸》以成己成物为一贯,而提忠恕,违道不远,以综统之。然且忠恕二字,要归在恕,以平天下育万物,非恕不为功。《大学》以藏恕喻人为絜矩,而《中庸》以求人先施为庸德,是以《论语》两一贯,一是曾子,一是子贡,曾子是忠恕,子贡只是恕,一言而终身行之。”[30](卷四)
以“恕”释“絜矩”确实符合《大学》平天下章的本义,但它和平均思想又有 什么关系呢?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再次回到古代平均观念的解释上来。中国古代的“ 平均”或“均平”,除了我们前边讲到的它有公平、公正和平衡、均衡的意义之外,合 理和谐也是其基本的含义,建设公平、公正、安乐祥和、秩序规范的和谐社会,正是平 天下的最终目标。
宋卫湜《礼记集说》中载:“又乐书曰:乐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主敬 主亲主顺之道,皆会归于和。父子兄弟和亲于闺门,乐之化行乎一家也;长幼和顺于族 长乡里,乐之化行乎乡遂也;君臣上下和敬于宗庙,乐之化行乎一国与天下也。古乐之 发,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已。”[3](卷一百)
同样是这一段话,清乾隆十三年钦定的《礼记义疏》记曰:“陈氏旸曰:父子兄弟和亲于闺门,乐之化行乎一家也;长幼和顺于族长乡里,乐之化行乎乡遂也; 君臣上下和敬于宗庙,乐之化行乎一国与天下也。古乐之发,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 而已。”[29](卷五十二)
这两段话都是在讲乐的社会功能和作用。乐之教化,可以使家族亲睦,乡里和顺,国 家天下祥和安乐。古代思想家把这种家族亲睦、乡里和顺、天下祥和的和谐状态,视之 为平均或均平。和谐是“恕”所追求的境界,也是平均的基本内涵。从这个角度讲,以 “恕”释“絜矩”,是不是又把“絜矩之道”纳入了含义广泛的“均平”思想的范畴呢?
其实,上边的例子中思想家们把和谐的状态归之为“均平”,而在关于“絜矩 之道”的资料中,也有直接把“絜矩”解为和谐的例子。明人项霦在《孝经 述注》中写道:“故礼备于家而治成于国矣。在家之严父严兄,即在国之尊君敬长也; 在国之抚百姓,即在家之爱妻子,恤其饥寒也;在国之御徒役,犹在家之有仆妾供使, 知其劳困也。然其敬爱之施,虽有亲疏先后之伦,而无彼我远近之间,故上下能相亲睦 ,以致天下和平,后世治家国者,不达絜矩之道,胶蔽亲疏,妄分彼我,昵爱于闺门以恩掩义,敛怨于士庶以暴胜恩,故常乱多治少,可胜叹哉!”[31]在这段关于 “絜矩之道”的论述中,“絜矩”指的就是“虽有亲疏先后之伦,而无彼我远近之间,故上下能相亲睦,以致天下和平”的状态,那么,“絜矩”自然就是“和谐”之义。这个实例更证明了我们把“絜矩”划入“均平”范畴的正当性。
三 “絜矩”概念消失的原因
“絜矩之道”这个源自《大学》、并被朱熹等南宋思想家重新发掘的思想文化 概念,自朱熹之后,在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曾广泛流行。它不仅出现在思想家们的 著作里,也出现在诗人的吟诵中:“民病何知渠即我,郡贫应念昔非今。圣门絜矩真良法,彼此秤停要尽心。”[32](卷五)“絜矩思为政,淳风个里寻。”[33](卷二十九)“藕花香里漾舟来,山榭登临万锦开。底事低徊看不足,吾因絜矩爱贤材。”[33](卷五十八)甚至,文人学士、乡绅大户人家,还以此为自己的堂舍取名,其影响可谓深远。但遗憾的是,历史进入近代,“絜矩之道”突然销声匿迹,几成绝响。特别在今天人们的意识中,似乎已根本不知“絜矩”为何物。这在思想发展史上,并不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尽管历史上的思想概念,到如今消失、淹没而不彰者也有不少,但像“絜矩之道”这样消失的例子也还是有些罕见。个中原委,着实值得探讨。
首先,从“絜矩之道”的基本含义上说,我们看到它缺乏独立性的品格。“
絜矩之道”的所有思想内涵,几乎都是其他思想文化概念所阐明了的,从而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概念的价值和意义。
《礼记·大学》篇最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谓“絜矩之道”就是两层含义 ,即提倡君子、国君对人民大众行为的师范表率作用和对待上下左右关系的忠恕之道; 南宋以后,经过朱熹等人的发明和阐发,又增加了一个突出的平均思想;“絜矩之道”在思想方法上,强调的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思想行为方式。这就是“絜矩之道”的全部思想内涵。而这些东西有什么独立的思想价值或意义呢?
我们先来说君子、国君对人民大众行为的师范表率作用问题。提到这一点,我们马上 就会想到孔夫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4](《颜渊》)的名言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先儒思想文献中早已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仅在《论语》 中就有非常丰富的论述: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4](《颜渊 》)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4](《子路》)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34](《子路》)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34](《泰伯》)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34](《 子路》)
在这些论述中,孔夫子已经把统治者行为的师范表率作用强调得十分清楚了,《礼记 ·大学》篇所谓“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的“絜矩之道”,对之又有什么新的发挥呢?
再说“絜矩之道”中的“恕”道。而这何尝不是被孔夫子讲得烂熟的一个概念 呢?孔子在对学生阐述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候,曾分别对曾参、子贡两次谈到“吾道一 以贯之”的话,而孔子思想的这个“一以贯之”的东西,按照曾参的解释,就是“忠恕 ”二字。[34](《里仁》)《论语》中关于“恕”的论述也很丰富: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4](《卫灵公》)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4](《雍也》)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34](《宪问》)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34](《卫灵公》)
既往不咎。[34](《八佾》)
这些都是关于“恕”的论述。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孔夫子答子贡的话,他认为一个人一 生可以奉为座右铭的东西,就是一个“恕”字;而“絜矩之道”中所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的处理上下前后左右关系的准则,相对于孔夫子的一个“恕”字,又增加了什么新的含义呢?
至于宋儒朱熹等人所附加给“絜矩之道”的平均思想,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 更是一个古老而深厚的思想观念。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均平文化” 。人们都知道孔夫子的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 ,安无倾。”[34](《季氏》)虽然孔夫子这里的“均”并非今天的绝对平均之义,但却 的确是一种平均思想。(注:关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一语的理解,笔者专门写有 《关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解说》一文,可供参阅。)除了孔子的均平思想之外,先 秦典籍中关于平均有许多论述:
《周易》谦卦的象辞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35](卷二 )唐代人史征《周易口诀义》中解释这句话说:“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者,裒, 聚也,寡,少也,谓人资财比多者行谦,即物益裒聚。故曰:裒多也,比寡少,行谦, 即物渐增益,故曰益寡也。称量事物,随其多少,均平而施给,故曰称物平施也。”[3 6](卷二)《周易》象辞中的这个“称物平施”就是一个明确的平均概念。
《周礼》中周官的设置,也很明确地体现着古老而鲜明的平均思想。《周礼》关于天 官冢宰职责说:“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37](p2)这 个“均邦国”就是要使天下邦国,无论上下、尊卑、贫富、远近都各得其平,各得其分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平均思想。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关于大司徒之职规定曰:“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 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37](p149)就是说, 大司徒的职责之一,是要按土地情况,运用征收赋税的合理法则,使天下赋税的征收均 平、合理,这也是明确地贯彻了一种均平思想。
可以说,中国古代就是以均平治天下的,在我们的先民那里,并不缺乏明确的均平思 想。而朱熹“上下四方,物我之际,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 则其广狭长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无有余不足之处”的所谓“絜矩之 道”,相对于“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以均齐天下之政”的传统思想来说,又增加 了什么新的思想要素呢?
最后,就连“絜矩之道”的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也消解在孔子“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恕”道论说中。如此这般,从思想史或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说,“
絜矩之道”还有什么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呢?它被遗忘是个极其正常的文化现 象。
就包含有以上所分析的三重思想内涵说,“絜矩之道”可以算上是一个内涵丰 富的思想概念。但它的三重内涵,都重复了其他已经发展成熟且影响更为深远的文化概 念,这样它就势必被他者所消解,失去作为一个独立文化概念的个性品格。“絜矩之道”最终无法逃脱被思想的历史所抛弃的命运,在所难免。
其次,从词性上说,所谓“絜矩”并不是一个实词性概念,而只是一个比喻性 的说法。按范祖禹的解释,絜,围束也,亦谓围而度之也。矩,所以为方;
絜矩,言度之以求其方也。元代的何异孙说,絜,度也;矩,所以为方 者,今木匠曲尺是也,匠之造屋室器用也。清人陆陇其在《四书讲义困勉录》中认为
絜矩不是譬喻,但却说是借字。(此三人的原话,都已见前引)总之,所谓“
絜矩”,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思想意义的概念,它的所谓思想意义的内涵,是后人附加上去的,是借用来说明问题的。“絜矩”不具备一个思想概念之基本要素,这大概也是它不能流传、缺乏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鉴于以上分析,“絜矩之道”的悲惨命运是一个很正常的文化现象。朱熹是中 国思想史上少数几位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四书集注》影响中国八百年之久 ,其思想不可能不被后人所重视。但他所极力推崇的“絜矩之道”却这样地被湮灭了,他对“絜矩之道”的解释、阐发和重新张扬,在近代落了个无人问津甚至被抛弃的悲惨下场,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结局。思想的历史就是这样,思想概念的生命力,永远属于那些新生的富有活力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