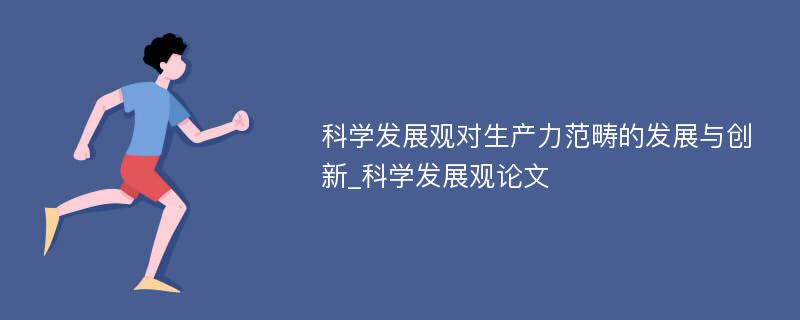
科学发展观对生产力范畴的发展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生产力论文,范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这是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对生产力范畴的经典表述,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实际状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生产力发展实践更是充分彰显了人们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量与豪情,自然界成了人们可以任意指使的玩物。但完全“被动”的自然界所表现出的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资源枯竭和人口爆炸等“报复行为”,又迫使人们反思自己的认识和行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在生产力范畴上的错误认知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完整准确地把握生产力范畴就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们反思和重建生产力范畴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在科学发展观看来,生产力是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能力,是既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作用,又关注自然的应有权利和地位,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生产力。科学发展观对生产力范畴的这一创新和发展,对于人们重新思考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被误读的社会生产力范畴:人类对生产力范畴的认知缺陷与不足
人类对生产力范畴的认识,是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展开而不断发展的,从古代人们单纯地顺应自然、利用天然自然到近代改造和征服自然,其中无不伴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活动的深入。
(一)利用天然自然:建立在依附自然基础上的古代生产力
在远古时代,由于人类刚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其自然属性远远超越社会属性,人类在一定意义上还未完全摆脱自然的附属物这一特征。由于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尚处于极端低下的地步,对于各种自然现象和外部世界的本质及发展规律无从把握,更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因而对自然界的一切感到既好奇又敬畏,自然在人们眼中是神圣而可怕的,顺应自然是人们的必然选择。由于缺乏直接加工食物的能力,为了更好地利用天然自然以维持生存,人类只能聚居在自然条件优越、天然食物丰富的区域,形成了利用天然自然直接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和仅能维持个体延续及繁衍的低水平物质需要的生活方式。这一时期人口的数量与平均寿命都很低,只能被动地依靠自然,人与自然处于原始的和谐状态。依靠自然界提供的天然食物等生活资料和天然生产资料是这一时期生产力的真实写照,这时的生产力简单来说就是人们顺应自然、适应自然和利用天然自然的能力。
进入农业社会后,人类的生产能力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人类对自然的依附程度仍然很高,人类的能动性淹没在受动性的海洋里,只能用人力、畜力和极为简陋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活动,经济结构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手工业为辅,劳动者被束缚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下,生产发展缓慢,甚至长期停滞不前。这使得社会财富极为有限,只能勉强维持社会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绝大多数人处于半饥半饱、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生存状态。
在农业社会,适应农牧业生产的客观要求,人口和土地成为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两大基本要素。当时,提高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的方式就是设法扩大国土面积和增加人口即劳动者数量,人口和土地就是当时生产力的根本标志。所以古代的统治者经常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企图侵占他国的土地,掳掠他国的人口。人口作为生产力中活的因素,是当时生产力中最重要的要素。在其他生产要素不能改变的前提下,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只能依赖劳动者数量的投入。“人海战术”成了提高生产力的主要手段。
虽然与远古时期相比,这时人类也开始尝试改造自然,但总体上,人类仍处在被动地适应自然和利用天然自然的阶段,以自然为中心和“靠天吃饭”仍是规律性的现象。纵然人类这时也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和改变着局部地区的自然环境,也产生了诸如地力下降,水土流失,河流淤塞、改道及决口等环境问题,但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作用尚处在自然生态系统自我更新的容许范围之内,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尚不构成威胁,人与自然尚处于原始的和谐状态。
(二)改造和征服自然:建立在科技发达基础上的近代生产力
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在这约500年的历史时期内,以劳动手段的突破性变革为内容,机器时代降临人类社会。后来,又经历了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蒸汽时代和生产工具更加发达、资源开发效率进一步提高的电气时代。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取得了巨大提升和长足进展,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发生了质的改变。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 与此相适应,人类的自我意识开始确立并逐渐膨胀,人的本质力量迅速凸现出来。生产力范畴的构成和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生产力不再被看作是人们顺应自然和利用天然自然的能力,而被看作是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们开始真正把自己从对自然的依附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开始确立并不断强化,人和自然被绝对对立起来,向大自然开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自然界由统治人类的神秘力量变成了人类可以任意改造与索取的对象,好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将永远在人类面前俯首称臣。
随着各种物质需要的不断满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产生并迅速强化了这样的观念:自然资源的供应能力具有无限性,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在数量上是不会枯竭的;自然环境具有无限的自我平衡能力,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这种观念更导致了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被当作人类追求的惟一目标,经济增长的总量即GDP(GNP)成了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唯一尺度。
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进程中,人们已经把各种自然规律抛诸脑后,完全忽视了生态环境支撑和承受能力的有限性,看不到各种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违背了生产力发展要以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为基础这一基本准则。无休止地向自然界进行掠夺式的、野蛮的开发和改造,远远超出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人类这种只关注自身利益的满足而忽视自然生态环境的存在及价值的做法,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环境的组成和结构,破坏和危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使得自然界开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人类“报复”。随之而来的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和人口爆炸,逐渐地从局部扩展到全球范围,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制约着人类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人类之所以在很长时期未觉察到盲目征服和改造自然的严重后果,是因为自然界的承受能力或自身代谢功能十分强大,对人类各种侵害自然行为的反应周期远远超出了单代人乃至几代人的生命周期。在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之初,自然界的报复并未大规模地出现,因而未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但是,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并不是无穷大,其代谢功能也是一定的,“忍耐”总是有限度的。一旦自然界对人类侵害行为的反应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就必然会做出人类无法消除的、大规模的报复性反应。
进入20世纪60年代,人们猛然发现,工业化时代的生产发展和物质繁荣乃是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平衡、过度消耗和占用资源、甚至严重透支后代的发展权益为代价的。工业文明虽然仅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它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是以前几千年农业文明不可比拟的。
总而言之,以前人类对生产力的认知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片面强调自然中心主义,以自然为中心,无限拔高自然的地位和作用,看不到人类这一主体的作用,把人类完全看成自然的附属物,生产力仅是人类顺应自然和利用天然自然的能力。要么走向人类中心主义,一切以人为中心,自然界完全成了人类可以任意驱使的奴仆。生产力被看作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这种认识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片面性所导致的环境问题也使人类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如果说古代人们对生产力的认知源于当时社会发展水平低下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近代以来人们把生产力片面夸大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忽视自然的反应的做法则完全是人类自我意识膨胀,缺乏全面和发展观点的结果。
二、重塑社会生产力范畴: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社会生产力系统
反思以前人们对生产力范畴的误读,科学发展观在扬弃传统观点的基础上,强调不能完全放任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忽视自然的权利,人类应抑制自身力量的片面扩张和强化,还自然以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更不能违背自然界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应该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来定位生产力范畴,使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一致起来。
在科学发展观看来,生产力应是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能力,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有机体系。而不仅仅是人单方面作用于自然、单方面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因此,科学发展观视野中完整的生产力系统应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互动关系之中。这种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对自然的关系。这层关系表现为改造与被改造关系。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主体,改造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前提,人只有通过改造自然以获取各种物质资料,才能保证人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自然对人的关系。这层关系表现为制约与被制约关系。人的活动不是没有限制的,自然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可以由人任意支配的存在物,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一定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当人们改造自然的活动触犯了自然界自身运动发展的固有规律时,自然界也会以它特有的天灾人祸的形式作用于人类,给人类实践活动的过失以“警告”和提示。恰如恩格斯早就告诫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 自然界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当人们强行去改变自然的运行规律时,它自然会做出一些特殊的、出人意料的过激反应。
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的人们仅仅把握了自然对人的制约作用这一方面,看不到人类对自然的能动改造作用;而近现代工业社会的人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只注重人们改造自然这一方面,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的开发、改造和征服,并把这种能力加以夸大,严重忽视了自然对人的制约作用。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生产力范畴不仅包括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还应包括人们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防止和根除自然界恶性蜕变、优化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能力。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后者同样是生产力,而且是更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更加具有现实价值的生产力。实际上,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人们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也要保护自然。在保护自然中体现着改造和利用自然,人类要在自然界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首先善待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然后才能更有效地改造自然界,超越这一关系,必然会受到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人们要想从自然界中持续获得更多更好的生产生活资料,必须严格按自然规律办事而不是完全以人的意志来办,在开发利用自然、谋求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尊重生态平衡规律,给予自然界以足够的更新和再生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长久的、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上要从“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转向“人是自然界的一员”,从“向自然界开战”和“征服自然”转向“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进而形成人与自然界双向互动的和谐关系。反对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单纯理解为向自然索取,把生产力的发展看成是对自然资源无限制改造的“单向”发展过程。必须树立以新的人与自然双向互动关系为基础的新生产力观,培养生态价值观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意识。
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里,人类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依赖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优化。马克思恩格斯曾把“人类整个进步”及“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更”,即他心目中所追求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要内容,理解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的和谐这两个方面。当人类社会面临生态失衡、资源枯竭和人口爆炸的严重挑战,陷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困惑的时候,我们迫切需要的正是“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新生产力范畴正是人类同自然和解的理想方式,它体现了对人类最长远利益的终极关怀。由此看来,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新生产力范畴是人类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代表了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从古代自然中心主义的生产力内涵,经过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产力观点的否定,到科学发展观视野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生产力范畴,人类对生产力范畴的认知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作为否定之否定阶段的新生产力范畴,它扬弃了古代和近代人们对生产力范畴的认知成果,又加进了时代的新内容,是生产力范畴方面的重大创新和发展,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理想目标的重要理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