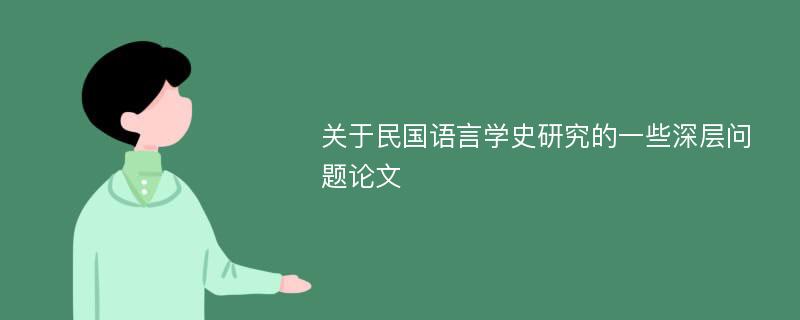
关于民国语言学史研究的一些深层问题
薄守生
摘 要: 民国语言学处于中国语言学大突破、大变革的紧要历史关头,它并未与此前的传统语言学撕裂。大变革时代的语言学较易“得风气之先”,民国语言学具有持久的影响力。《马氏文通》面世后沉寂了二十多年,最终确立了划时代的学术地位,其“比较”的思想在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言类型学”观念的形成离不开“比较”的思想。西方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并不彻底,而“中国结构主义”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语言学史的书写很难,主要因为“语言学思想”较难把握,兼顾“坚实”与“流畅”非常难。语言学学科呼唤“专业化”的民国语言学史研究。
关键词: 民国语言学史;语言学思想;马氏文通;中国结构主义
民国语言学史之于中国语言学史,在研究上有一定的特殊性。民国语言学史研究的突出表现是“家底不明”,目前还没有哪一位语言学研究者能够对民国语言学的发展细节、文献清单作出一个肯定的、明确的说明。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民国语言学史研究是一项填补学术空白的基础性的研究。由于中国语言学史学科现在还很不成熟,需要我们作出相关铺垫、补充说明的情况还有很多。中国语言学史的这种研究现状又与民国语言学史的学术空白交织、叠加在一起,使得研究民国语言学史尤为艰难。当前,民国语言学史研究须认真通读语言学原始文献,要重视“史论结合”,慢工出细活,长期坚持[1]。民国语言学史研究需要做到“专业化”[2]。在这里,笔者提出几个比较“散”的小论点,用以介绍“关于民国语言学史研究的一些深层问题”。这些“小论点”表面上似乎比较“散”,但它们在逻辑上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它们对勾勒民国语言学史的发展脉络有一定的帮助。
一、关键时期语言学思想在深层并未撕裂
民国语言学是中国传统语言学向中国现代语言学转变、过渡的关键时期,处于大突破、大变革、大发展的紧要历史关头,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处境很容易导致各种极端的观念和行为,甚至可以说:“传统”和“现代”的撕裂难以避免。在民国时期,“传统”的语言学思想和“现代”的语言学思想之间确实有过一定的紧张,但是,它们并未由此撕裂,甚至可以说它们在最后还进行了很好的融合。当今,我们语言学研究大繁荣,这种繁荣就是建立在语言学思想融合的基础之上的新突破、大发展。
文献[8]利用图论与矩阵理论证明了编队控制一致性的可实现性,为基于一致性理论的多智能体系统编队控制研究奠定了基础.Saber等[9]首次考虑时延情形,开展了连续时间多智能体系统编队控制一致性问题的研究.而后,Lin等[10]研究了通信拓扑切换情况下,时延多智能体系统的编队控制一致性问题.
语言学思想里的“新学”从来都能够与中国传统语言学成功结合,并创造出“中国特色的语言学”。以高本汉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为例,高本汉接受过较为系统的“西方语言学”的训练,但他也很好地继承与发展了我国清代学者的语言学成果,从而写出了包括《中国音韵学研究》在内的著名的语言学著作。高本汉原本不是中国人,但他也为“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赵元任的语言学思想原本有着深厚的欧美背景,但是,他的方言研究路径并未遵循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相关精神,他把方言、音韵结合起来,用国际音标记录方言,用中国传统的音韵学串联、对比不同的方言。所以,如果有人说高本汉、赵元任代表着完全意义上的“新学”,那并不符合语言学史的相关史实。纵然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纵然当时的中国缺乏最基本的“文化自信”“学术自信”,高本汉、赵元任等学者也从未以“生活在别处”的心态去展现“高高在上”的学术姿态,他们都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传统语言学。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顾颉刚发表《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一文,其中谈到:“中国到了现在的境界,说他专受了欧化的鼓动,可有些冤枉;现在事物的外观上面,确是触处可见欧式;至于内部的精神,多半是盲从的新思想,同牢不可破的旧思想。”[3]这不止新文化运动前后如此,整个民国语言学史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形。传统的训诂派人士公开宣称普通语言学新异而无用,普通语言学则批判传统训诂学僵死而顽固。即使开明的语言学家王力也要在1947年写出《新训诂学》,以“‘新’训诂学”来打破传统的训诂学,以“新‘训诂学’”来承接训诂学的传统。事实上,中国语言学除了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较大的那一段时期以外,中国语言学从未真正“西化”过①。当然,中国现代语言学并未固守“牢不可破的旧思想”,而是继承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许多“优良的旧传统”,中国现代语言学既不妄自菲薄,又从不忘本,在学科的发展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恰到好处”。
二、“得风气之先”却有持久的影响力
毋庸讳言,在思想激荡的民国时期,确实有一些语言学论著或者空洞浮泛或者僵化荒谬,毫无学术价值。例如,关于“大众语”讨论的许多文章就很空洞、口水化,当时对“汉字”进行“理论”阐述的许多论著也显得荒谬、机械化。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在当时也属正常。这就像我们所面临的今天的这个“出版时代”,每年都有数不清的“核心期刊论文”“权威出版社专著”,而真正有学术创新、学术价值并为时代所留下的论著只是沧海一粟,真正能够穿越历史、在历史上留下一席之地的论著少之又少。当然,民国语言学论著在“得风气之先”方面却是我们今天的语言学不能相比的,我们今天的学术背景已经不再是“凿破鸿蒙”的“鸿蒙”了,今天的“学术雾霾”与盘古开天时的“混沌一片”也完全不同。
转型、大变革、得风气之先,这些都是民国语言学的重要特点。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之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中国语言学的拓荒者”等语言学大师也多成长于民国时期。对于这些“得风气之先”的“语言学”,我们是否高估过它们?肖昊宸认为,“民国时期处在中国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过渡期中,许多新事物传入中国不久,各门学科还在形成中,研究者在研究中较易领风气之先,成为某个学科的开创者。‘百废待兴’,也就较易‘成名成家’。而以今天的眼光视之,民国时期的学科建设处在转型期中,学科发展并不成熟,学术成果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局限,而且这些成果中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其实并不多”[4]。民国语言学却不完全如此,民国时期“得风气之先”的语言学论著、语言学思想大多数至今都还有着持续的影响力。
第二天,翻开学生们的周记一看,意见还真不少。有的说我脾气大,有的说我粗心大意,有的说我有些懒,还有的说我经常不兑现承诺……我被学生敏锐的洞察力所震撼,很庆幸自己的做法,及时掌握了班级里学生的想法。
何北掏出一玩具手铐“啪”就把何东和自己铐一块儿了:“走什么走,上爷爷家去!不带这么不仗义的,平常尽看我笑话,八百年才穿越出这么点事儿,还想逃?就愉悦愉悦我们这一次,啊?”
三、《马氏文通》沉寂二十多年并非偶然
如果要问哪些语言学著作曾经“得风气之先”,那么,这应该是要包括《马氏文通》的。语言学界通常把《马氏文通》定为“1898年的语言学史”,其实,《马氏文通》最受人们关注(批评或推崇)应该是在它问世后的二十多年以后。考虑到“语言学史之不可绝对断代”,我们通常把《马氏文通》看成是民国语言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②。
在赵元任之前,《马氏文通》就已经开始把西方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应用到汉语研究中去,体现了一种“中国结构主义语言学”。陈保亚曾定义“中国结构主义”为:“中国语言学家在借鉴西方结构主义方法的前提下,在近代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通过对汉语的分析提出的一套方法原则。”[10]20年过去了,我们在今天说“中国结构主义”时依然会觉得这个名称有点儿怪异⑤。究其原因,可能就在于人们的感觉(意识)中对“结构主义还分中西吗”存在疑惑⑥。其实,西方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从来就很不彻底,中国语言学对西方理论虽有继承,更重要的却是改造西方理论实现理论的“中国化”。同时,人们对“中国××主义语言学”一直不够自信,并进而自嘲为中国语言学的理论意识不强。
《文通》出版后的十多年里,因其“文繁而征引旧籍多,今贤所束阁者,故不独喻之者寡,即寓目者亦已少矣”。可见《文通》曾一度受到冷落。语法学界真正对《文通》进行学术研究和评论,盖始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而且这些评论,除了指责它以文言文为研究对象外,主要是批评它机械模仿西方语法。这类批评,时断时续,绵延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正如邢庆兰师所说:“较《文通》晚出的一些文法书,不管是讲古文法的也好,讲国语文法的也好,每出一部,几乎都要把《文通》骂一顿。”……陈望道也说:“二三十年来,‘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对于《马氏文通》体系的千万忆恨缠结也就从这一部书的出版时候开始。”……朱德熙先生《汉语语法丛书·序》说:“《马氏文通》往往因其模仿拉丁文法而为人诟病。其实作为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能有如此的水平和规模,已经大大出人意表,我们实在不应苛求于马氏了。只要看《文通》问世二十余年以后出版的一批语法著作,无论就内容的充实程度论,还是就发掘的深度论,较之《文通》多有逊色,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出《文通》的价值了。”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前期《文通》研究和评论工作的小结。③
《马氏文通》的出版,本意是指导语言(文言文)教学,提高学习文言文的效率。对此,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后序》中[6]说:
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视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故其国无不学之人,而人各学有用之学。计吾国童年能读书者固少,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时为文而以其余年讲道明理以备他日之用者,盖万无一焉。
在当时,希望能够缩短文言文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的人为数众多,然而,人们为什么又要冷落“为了这个理想而奋斗”的《马氏文通》呢?一冷落就是二十多年。人们在不再冷落它的时候却又要批评它,批评的重点其实并非尽在“文言语法”,批评更多的是它“模仿”。人们又为什么要批评它“模仿”拉丁语法呢?因为《马氏文通》并不实用,对于提高文言文学习效率没有什么用处。
综观整个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本着实用主义的立场,语法学对中国人学习汉语确实没有太大的用处。如果没有中外语言的接触,没有语言的比较,如果没有汉语国际教育,语法学的诞生可能确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对此,我们从赵元任的学术历程、脉络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他那么一位哈佛博士回国后竟全无致力于提高国民语言学习效率的想法,而是主要去做那些于民众而言“高深”却无用的方言音韵研究,在国内期间他对汉语语法的相关研究基本上并无太大兴趣;后来,赵元任去美国从事汉语教学,他的语法学著述才逐渐多了起来。赵元任对汉语语法学的态度前后就有如此的转变,那主要在于“语言环境”的转变,在于有无“语言比较”的土壤和空气——汉语语法学对中国人学习汉语作用不大,而对外国人学习汉语应有一定的作用。“比较”乃是“模仿”的前提。在语言比较、语言接触的前提下,“得风气之先”的汉语语法学怎么可能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模仿”呢?在“模仿”的程度方面,《马氏文通》做的可能一点儿也不过分。
1932年,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国文考试命题,考试题目竟是“对对子”,此举在当时颇受争议。为什么用“对对子”作为考试题呢?后来,陈寅恪给出四个原因:(1)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2)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3)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4)可以测验思想条理。陈寅恪说,“在今日学术界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于对对子之一方法。此方法去吾辈理想中之完善方法固甚辽远,但尚是诚意不欺、实事求是之一种办法”[7]。以陈寅恪此举推断,《马氏文通》被冷落了何止二十多年,从1898年到1932年已有三十多年时间了④,三十多年后的汉语语法学也只不过是孙行者心中的“西方幻境”罢了。
然而,《马氏文通》的学术地位最终还是固定了下来,它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样的《马氏文通》确实“得风气之先”,我们能说它早已被历史湮没了吗?
四、从“语言比较”到“语言类型学”
陈承泽等人批评《马氏文通》是“模仿”的语法,要求人们追求“独立”的汉语语法,这种思想可能会在无意间助长汉语的“闭关锁国”倾向。1922年,胡适在《国语文法概论》中探讨了研究语法的方法:归纳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他还说:“我老实规劝那些高谈‘独立’文法的人,中国文法学今日第一需要是取消独立。但‘独立’的反面不是‘模仿’,是‘比较与参考’”[8]。“比较”的方法在胡适心目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也不局限于追求“比较的语法”,还包括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的各种比较方法。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不但如此,日本语里,朝鲜语里,安南语里,都保存有中国古音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西藏文自唐朝以来,音读虽变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变,更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中国古音里有许多奇怪的复辅音呢”。
在“全球化”趋势的今天,我们不宜再提“独立”的语法,“比较”已经在事实上无处不在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语言类型学”成为当今语言学中的“热门”研究方向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从人的“认同”与“局限”来说,哪里有比较哪里就有痛苦,哪里有比较哪里就有迷惘。今天的人们应该更能够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尊重这种“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既是“比较”的结果,又是“比较”的前提(没有“多样”,何来“比较”)。这样一来,我们对“比较”就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而不是盲目崇拜比较、事事都去比较。这样的认识高度是民国时期的大多数的学者达不到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达不到这种认识高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模仿”还是“独立”、“独立”还是“比较”的问题上,民国时期的学者观点激烈冲突的人多,以冷漠的态度故意忽视对方的人多,而能够平和、理性、宽容地秉持“多样性”的态度的人少。不同思想观念的人之间,彼此咒骂对方是禽兽、是妖孽,这种做派在中国很有历史传统,自先秦时代一直到民国时期自古尽然、绵延不绝。
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流布应该说是多元的,我们很难说是由哪一位语言学家一个人主导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其中,赵元任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无疑是有贡献的,他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和《国语入门》一直都被认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经典著作。然而,赵元任并没有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使用范围、有效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他大概更愿意把这种“主义”具体地应用到汉语中的一个个例子里边去。在对这些例子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赵元任曾有过一些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反思。
以上,我们从六个方面对民国语言学史研究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但是,民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工作远未完成。全面、深度、系统的民国语言学史研究,我们还需要若干年才能真正做好、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在更加全面、更加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总结出更多的关于民国语言学史的“史论”。比如说,日本《中国语音韵研究文献目录》(汲古书院,1987年)就收录了到1957年为止的汉语音韵学论著目录,其中就有属于民国语言学史的论著值得通读。同时,我们认为,研究语言学史应尽量少谈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我们实在不敢说中国语言学在未来一定会走向何方。尽量避免预测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并不代表我们不重视语言学史研究的“启示”。王力在回忆赵元任的学术生涯时,曾委婉地哀叹赵元任想回国却回不来的飘零之感,幸福从来都不是凭“锦衣玉食”代替“牛棚”那么简单。
五、中国语言学从来就不是片面化的“结构主义”
实践教学是高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实践课程可以从教学理念,资源建设,课程设计,组织实施和评估激励等方面进行。在具体的课程建设中,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
民国时期,“得风气之先”却又为历史所湮没的语言学思想,大概主要是“拼音文字”的设计。废除汉字、消灭汉字、发展拼音文字,这种思想在民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这种思想生长、壮大、开花却主要发生在民国时期。除此之外,当时“得风气之先”的语言学思想大多数都影响至今。
注 释:
王海棻曾在《〈马氏文通〉研究百年综说》一文[5]中说:
中国的语言学史专家们常常慨叹中国语言学缺乏学派意识,感叹中国语言学的理论意识不强,诚然,这是中国语言学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基本判断:一种语言学与一种语言相适应,那就是好的语言学。我们在讨论“××语言学”时,一定要留意这种“××语言”,决不可脱离了“××语言”而谈什么“××语言学”。有了这种意识之后,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对“学派意识”“理论意识”抱有偏见性的紧迫感。事实上,“一种语言学”拥有自己的“学派”、自己的“理论”,除了关于“这种语言学”的“语言学史”更容易书写以外,“这种语言学”不见得就比“其他语言学”更有优势。我们也不能仅仅为了追求书写“语言学史”的方便、易写,就去对“语言学”作出太多的不同的评价。
由输电塔的前12阶模态分析可以看出:整个钢管塔在中横担以下部位变形较小,中横担以上部位变形较大,地线横担及上横担较易发生扭转变形,地线横担的变形尤为严重.因此,在钢管塔抗震分析时,中横担以上的部位应重点研究.
六、史重要、史艰难、史严谨
中国语言学史很重要,中国语言学史很难写。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为什么难度那么大呢?对此,陈保亚说,“由于中国语言学把方法隐藏在材料背后的这种特殊传统,梳理中国语言学方法的线索就显得非常困难。这就需要我们有面向材料的评价标准,根据这样的标准,我们能够判定隐藏在材料背后的方法的得失”[10]。其实,不独独是“方法隐藏”的问题,关于中国语言的某些材料本身就很繁难。
全民学习共享平台呈现了全新的教学服务平台,给课程教学带来开阔的视野,提供强大的课程服务和学生管理能力,给教学传播带来新的契机。教研组可以申请、创建微信雨课堂教室,分享具体课程内容资源。教学团队可以自主制作视频和实验模板,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所体验,而且雨课堂可以不用下载APP,占用空间很小,触手可及,用完就能退出。在内容设置安排上,要以直观且清晰的关键词来设计大数据信息,在线学员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和兴趣点到达不同的页面空间,开展学习活动。
罗宾斯在《简明语言学史》中曾坦承语言学史的书写对他本人来说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当我试图编写一本范围如此大的书的时候,立刻就意识到会遇到很多困难。首先,写这本书的作者应该对语言学的所有领域都同样地熟悉,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其次,各个时期的原始资料的范围、性质和保存的状况都大不相同。比如,我们对某些早期语言学先驱的了解,还有欠缺,这很可惜。但是,在有关当前发展趋势的近代历史方面,困难的性质又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选出可能具有深远意义的材料。除此之外,主要文献在是否保存下来、是否能获得以及版本质量的好坏等方面,也有很大差别”[11]。罗宾斯的这些感受不无道理,书写一部自己比较满意的语言学史著作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正是这个原因,越是“专业化”从事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学者越是低调、老实却又自信,而那些只是“临时客串”做语言学史研究、没有长期的“专业化”的研究计划的人却会显得很狂妄、轻浮但又没底,从事中国语言学史研究要求“心里有底”很重要。以“我是打酱油的”的态度去研究语言学史很不合适,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必须走“专业化”的研究道路。
通常,人们会以罗宾斯的《简明语言学史》为例,感慨西方语言学史的流畅、行云流水,读起来让人感觉舒服、轻松。可是,姚小平曾实事求是地批评过《简明语言学史》:“罗宾斯长于说理,他以轻松畅达的笔触,把一部西方语言学发展史通俗明白地勾画了出来。他的缺点之一是对史料的把握不够严谨准确,有人批评说,他的这本书史实方面的错误太多,不能列为可信赖的参考书(Koerner,1987b:5)。”[12]罗宾斯的《简明语言学史》一书中的“史实”错误究竟有多少,笔者未能一一考索、核实,但是,过多的史实错误确实是语言学史研究的致命缺陷,因为语言学史著作只有建立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之上才有意义。语言学史著作毕竟不是诗歌散文,称赞它“流畅”是有前提的,“史实”才是它的坚实基础。此前,我们已经反思过以往的中国语言学史著作总是磕磕绊绊、细小琐碎、很不流畅的问题[13],并希望能够从语言学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突破,但我们至今也还不敢说我们的研究已经完全成熟。由是看来,民国语言学史的研究难度确实很大。
在“语言比较”的问题上,“预流”也好“腐旧”也罢,它还始终摆脱不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比较”是为了什么?时代发展到如今这开明盛世,我们今天都还在批评“为了比较而比较”,言外之意,“比较”是有“目的”的。回想民国时期的语言学家,他们提倡“比较”大概主要是为了发现“汉语的特点”,而不是为了提高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效率。这又打了庸俗的实用主义语言学一个大巴掌。
我们在以上六个方面提出来的些许“小论点”,也是我们继续深化民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小驿站。我们乐观地相信,从此出发,等待民国语言学史研究完全成熟后,一部比较完善的《民国语言学史》专著必将能够促进中国语言学的极大发展,必将能够推进“民国史”研究的全面提升。
赵元任曾举例说,“动词的动作方向虽然模棱两可,但通常可以从上下文或说话的场合判别,而不至于引起误会。例如:‘你就写他偷车的事情。’这一句话要是没有上下文,就好像是他偷了车的意思。但是因为听的人老早知道说的人在说什么,就清楚的了解,其实是他的车丢了的意思。正因为说的人知道听的人晓得这件事,所以就用不着说的那么明确了。只有对语言学者来说,这些句子才成问题,因为他们所研究的,多半是脱离上下文单独孤立的句子。其实大体上说,中国话含混的地方不见得比其他语言多,也不见得少”[9]。赵元任的这种重视“语境”的思想,既可以看作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反思,即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应用范围仅仅局限于语音、词汇、语法等层面是不够的;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新拓展,把“语境”也纳入到了“大结构”之中。无论哪种理解,都是反对机械地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我们不能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看成是“包打天下”的灵丹妙药。
①中国语言学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也不是真正的“西化”,详见下文。“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主要是一种“随风潜入夜”的较为隐蔽的影响,而非“暴风骤雨”、大起大落的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中国语言学影响的“高潮”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但是,这个“高潮”的标志并不明显。
田志芳立即慌了,她发现杨连长也在,他是和刀营长骑马提前来的,但他胸前没挂红花。她扭过头问向阳花:“谁?谁结婚?”向阳花笑嘻嘻地说:“别急,妹子,你今天仔细找找,这里还有比杨连长更好的不?”
②这并非因为《马氏文通》“在民国时期受到重视”才把它划归民国语言学史,《马氏文通》“得风气之先”与它“沉寂了二十多年”二者之间并不矛盾。
③这段话中的“十多年里”“二三十年来”“二十余年以后”等表述不一定非常准确,但这些表述在大体上还算是正确。另外,还有两点值得提及:一是《马氏文通》出版不久以后对日本的汉学家有一定的学术影响。二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氏文通》也并非只是被批判的对象,比如说,赵元任就曾积极地吸收过其中的语言学思想。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大学生群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探索“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创新内容与形式,适应网络化的发展。紧跟技术进步与话语情境的变化,将工作延伸到虚拟世界,充分发挥网络信息技术的优势。积极促进融合发展,用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协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④我们说《马氏文通》在早期曾受“冷落”,并不是说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及、涉及《马氏文通》,其“受到冷落”大约接近“学术影响小”之义。比如说,杨树达至迟从1921年开始就已经从事“马氏文通刊误”等相关研究了。
脑卒中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这种疾病会导致患者出现残疾,有研究认为大约存在有3/4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情况[1-2]。所以对于脑卒中患者进行介入系统规范的作业治疗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治疗方法,现如今国内开展作业治疗普遍局限于对于患者的肢体功能的恢复,并没有针对患者所处的环境和患者个人能力因素等进行干预,而且也不具备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和相关的指导[3]。本研究基于此分析将ICF理念和患者结为一体,从患者的个人因素等角度出发,为患者设计针对性的作业治疗方案,以便于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进行改善,现将主要研究情况报告如下。
⑤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使用“中国结构主义”这种“怪异”的称呼。其实,称述一种“主义”和说明一种“怪异”可以并立共存。
⑥当然,我们知道“American Structuralism(美国结构主义)”是索绪尔之后的重要的语言学流派,有些学者说它是20世纪的“三大结构主义”之一。但是,以“国别”命名的“结构主义”,除美国外,大概还没有其他的“某国结构主义”取得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参考文献:
[1]薄守生.推进中国语言学史研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9-19.
[2]薄守生.做“专业化”的中国语言学史研究[J].汉字文化,2017(6):45-46.
[3]顾颉刚.顾颉刚卷[M]//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738.
[4]肖昊宸.高估民国学术有失科学理性[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3-28.
[5]王海棻.《马氏文通》研究百年综说[J].中国语文,1998(5):335-345.
[6]吕叔湘,王海棻.马氏文通读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后序2.
[7]陈寅恪.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J].青鹤,1932(3).
[8]姜义华.语言文字研究[M]//胡适学术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34.
[9]赵元任.赵元任卷[M]//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84.
[10]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8,自序1.
[11]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M].许德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
[12]姚小平.西方的语言学史学研究[J].外语教学,1995(2):1-8.
[13]薄守生,赖慧玲.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30-331.
Some Deep Problems on History of Linguist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O Shousheng
Abstract: Linguist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at the 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 of the great breakthrough and great change,but it did not deviate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Linguistics.Linguistics in the era of great change was easy to“get ahead of the fashion ethos”,and Linguist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lasting impact.Having been silent after its publication for more than 20 years,Mashiwentong(马氏文通)got the final establishment of the epoch-making academic status,especially with its thought of“comparison”having a profound impact in our country.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linguistic typology”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thought of“Comparative Method”.The impact of western“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on Chinese Linguistics is not thoroughgoing,but“Chinese Structuralism”sti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up to now.It is difficult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mainly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grasp the Linguistics Thoughts,and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s how to reach balance between“solid philology bas”and“fluency in writing”.Linguistics discipline calls for the“specialization research”on Linguist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History of Linguist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Linguistics Thoughts;Mashiwentong(马氏文通);Chinese Structuralism
作者简介: 薄守生,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南 郑州450001)
DOI: 10.19503/j.cnki.1000-2529.2019.01.014
(责任编校:文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