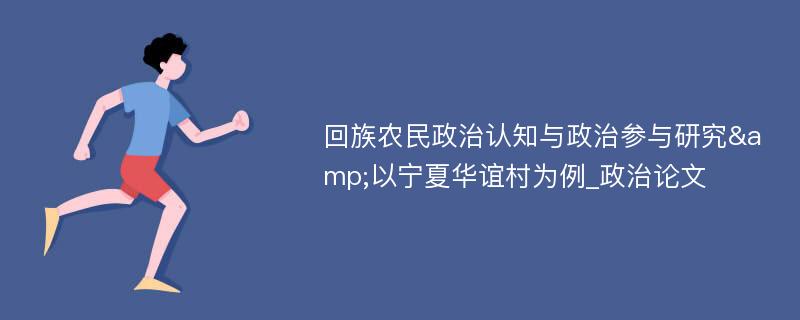
回汉农民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研究——以宁夏华一村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宁夏论文,为例论文,认知论文,一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7)06-0041-05
公民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状况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我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农业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农民的政治认知与参与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有较大比重,加上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状况,较全国其他地区表现出不同特点。基于此,我们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华一村为例,对回汉农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状况进行了调查,以期个案反映西北地区政治文明的状况。
一、调查地点及研究方法
华一村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西南方,处于灵武市和利通区的中间位置,面积约为80平方公里,靠近黄河,水资源比较丰富。全村人口有804户,4823人。其中男性2713人,女性2110人。村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水稻、小麦和玉米,也有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种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还有部分农民从事商业、运输业和养殖业等。该村为回、汉混居村,全村共由13个生产队组成,其中10个生产队以回族为主,3个生产队以汉族为主。
本研究主要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判断抽样的方法获取样本。先从13个队中抽出5个队,由于10队居住的回族比较多,故直接抽取。然后再从其他12个队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抽签的方法)抽取4个队。再从抽取的队中,采用非概率抽样法中的判断抽样法,每队抽16户,共计抽取80户,作为调查样本。在所抽取的每一户中,抽取生日接近7月1日的人来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80份,回收有效问卷80份。尽管调查的样本不能够完全推论总体,但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该地区居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状况,也反映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现状。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政治认知:农民政治意识的反映
政治认知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其基础首先是政治认识的形成,也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学习、观察等多种途径所获得的政治认识和感性认识,在政治认识基础上对各种政治事物、现象产生喜、恶、恐惧、焦虑等情感反映,这种情感反映叫政治态度,人们基于一定的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对现实政治事物、现象产生的自主性判断,称为政治评价。在政治评价不断发生的同时,人们对政治事物与现象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就是政治价值。政治认识——政治态度——政治评价——政治价值的不断继替和循环,就构成了政治认知的不同水平和不同阶段。
1.农民政治认识水平普遍比较高,对常识性的政治符号认识明确,对重要的政治人物、政权机构的认识由于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差异。政治认识是政治认知的基础,也是政治社会化的初始阶段。农民的政治认识主要体现在对政治符号、政治人物、政权机关等一些政治知识的认识上。调查表明,农民对政治符号的认识比较清楚,有86.3%的被访对象认为,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有68.8%的人认为,我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但是,对政治人物的认识表现出很大差异性,有62.2%的人不知道全国人大委员长是谁,选错答案者占8.8%;而不知道国务院总理是谁的仅有7.6%,选错答案者占1.3%,这与政治人物的媒体曝光率有直接关系。当前,广大农民认识政治人物的最主要途径是通过电视传媒,所以,曝光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对政治人物的认识。在被问及“中国最高国家权利机关”的回答中,选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仅有46.3%,选择“说不清楚”的多达13.8%,认为是“党中央”的占31.3%。可见,对国家政权机关的认识出现了定位的模糊性,这与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有关系。数据表明,说不清楚我国最高国家权利机关的人员中,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的人员占63.6%,小学文化程度占36.4%。回答正确的人员中,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累计占83.8%。
2.农民政治态度比较模糊,回汉民族农民在政治活动参与方面呈现出明显差异。农民的政治态度来自于人们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直接感受,是个体对政治的感情的主观反映,主要体现在个体对自身与政治活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及政治活动参与等方面。调查表明,问及“政治是领导的事还是大家的事”的回答中,仅52.5%的人认为政治是大家的事情,多达23.8%的农民认为政治是领导的事情。而53.8%的农民认为政治是好事,另有46.3%的人选择“说不清楚”。调查表明,75%的人没有参加过人大代表的选举,57.1%的人没有参加过村委会选举。值得关注的是,在个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认识上,回汉两族群农民大多数认为自身和政治之间是有关系的,而且回族(88%)和汉族(92.6%)差异性不大,但是在选举活动的参与上,却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如表1所示)。
表1:回、汉族农民选举活动参加情况(单位:人)
问题表述 汉族回族总数
50 (62.5%)
22 (27.5%)
政治是和自己有关系 72(90%)
%within民族成分 92.6%%within民族成分 88%
15 (19.7%)4 (5.3%)
参加人大代表选举
19(25%)
%within民族成分 29.4%%within民族成分 16.7%
24 (31.2%)9 (11.7%)
参加村委会选举33(42.9%)
%within民族成分 47.1%%within民族成分 36%
这表明,回汉农民虽然政治认识、态度具有趋同的一面,但在政治实践参与过程中,回族农民参与度较低。
3.农民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状况不满意比例较大,对政治机构工作效能的评价呈现出机构级别越高评价越好的特点。农民政治评价是农民基于一定的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对现实政治事物、现象产生的基于理性基础上的自主性判断。调查主要从农民对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的办事效能、农民对政策执行的评价上入手。在对中央、乡镇、村委会三级机构工作人员是否为民办事的调查中,农民普遍对级别越高与农民现实生活产生直接联系越少的机构工作人员的评价越高,认为中央和乡镇领导干部为民办事的分别占97.5%和78.8%,仅有44.3%被访对象认为村委会领导干部是为民办事的(见表2)。究其原因,一方面政治机构级别越低,与农民社会生活联系越紧密,互动频率也就高,双方必然会因为大小事情产生摩擦的机会就越多,容易使农民产生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在宏观方面的政策制定,而乡镇、村委则主要是微观具体政策的落实。制定和落实之间存在差距或者政策在基层落实乏力的情况,也影响着农民的评价。农民对村民自治制度在本地实施状况的认识和评价也是反映农民政治评价的主要变量。仅有2.5%的被访对象认为所在地村民自治制度实施“非常好”,认为实施状况“好”的占21.25%,“不清楚”的比例最高,占58.75%,认为“不好”的占16.25%。
表2:对中央、乡镇、村委三级为民办事的评价(单位:人)
为民办事 不为民办事 说不清
村委会领导干部是否为人民办事
36 44.3%19 24.1%25 31.6%
乡镇领导干部是否为人民办事63 78.8% 9 11.3% 8 10%
中央领导干部是否为人民办事78 97.5% 0 2 2.5%
可见,农民对当地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并不是很满意。这种不满意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调节和合理的引导,持续蔓延将严重制约农村地区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有可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政治认知动态循环往复的性质虽然表现出了形成过程的递进性,但从政治认识、政治态度、政治评价到政治价值的最终形成,都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交错并存、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政治价值是贯穿自始至终的核心。经过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理念教育和历史事实的影响,可以看出,被调查地区的回汉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信心,牢固树立了社会主义信念,对国家的一些根本性制度认同度很高。
(二)政治参与:农民政治意识的实践
政治参与是公民自愿地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参与社会政治的过程,表达各自的政治态度,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它不仅是公民享有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也是现代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农民的政治参与是广大农民在政治认知基础上的一种行动,是农民政治意识的实践过程。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表现为村委会的选举、人大代表的选举、党支部的选举以及村庄运行中表现出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等。这些方面构成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衡量指标。
1.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不高,与其他地区相比差距较大。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步伐的加快、村民自治制度的全面实施,农民在制度框架内实现政治参与的途径日益规范化、常规化、程序化,农民政治参与热情普遍提高。根据郭正林2002年对广东省26个乡村的调查表明,仅仅有23.8%的农民没有参加过村委会选举,64%的农民没有参加过人大代表选举[1]。但是本研究调查表明,农民没有参加过村委会选举的高达57.1%,没有参加过人大代表选举的高达75%。如表3所示。
表3:农民对选举活动的参与情况(单位:人)
各项参与
参加过没有参加过总计
人大代表选举的
19 57
76 100%
参与25%75%
33 44
村委会选举的参与
42.9% 57.1%
2.被动性参与仍然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流,自主意愿性参与逐渐成为选择趋向。政治参与是公民自愿地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参与社会政治的过程。农民政治参与中自主意愿的不断增强,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调查表明,当地农民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活动的原因中,“上面安排”的选择高达40.9%,选择“别人都去了我也就去了”随大流的占31.8%,真正当作“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仅占27.3%。可见,当地农民参加选举活动主要还是以被动性参与为主,自主自觉性的参与还是少数。而村委会选举中,有55.6%的人表示参加选举主要是想选出好的干部,上面安排的比例仅有16.7%。可以看出随着政治认知的提高,农民政治参与开始由被动趋向自主自愿性。
3.农民对选举对象考量标准的多元化彰显出农民理性化政治参与的趋势。农民理性化的政治参与,是农民自身政治认知不断深入的表现,也是农民政治参与理念趋向成熟的标志。在村委会选举中仍然有55.6%的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参选人中间作出自主选择,从侧面反映出在可能的范围内,农民还是希望能够自主性地参与政治活动的。调查中20个人先后101次对选择的标准表达了看法:人品、工作能力、文化程度、威信成了主要考量因子。人品好是出于农村乡土道德遵守的考虑,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是对选举对象领导农村事务能力的一种期望,威信高低则是传统农村社会关系在选举中的体现。而“原来就是村干部”这一因素的考虑非常少,不会因为“原来是村官,现在就选你当村官”。农民们开始抛弃传统观念的影响,按照自己的意愿,以理性化为标准参与政治(如表4所示)。
表4:自主意愿选举村干部的农民对选举对象因素的考量(单位:人次)
选举原因 频次百分比(%)
工作能力强 27
26.7%
文化程度高 15
14.9%
原来就是村干部 21.9%
人品好32
31.8%
威信高22
21.8%
会赚钱 32.9%
其他 0
总计 101
100%
4.民族传统文化差异对农民政治参与状况有较大影响。由于历史、地理、信仰等原因,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内涵,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内涵的准则、规范、行为、模式表层下,都有一套价值系统。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的总体以及个人从其总体中得到的文化信息,常常是这一民族中较为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以个人为代表,而是以一个族群或地区社团为代表。这种特定的模式客观地构成了民族文化差异性。而民族政治发展与民族文化相互关联,民族文化差异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政治参与有很大影响。前文表1数据反映出,回族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人只占该民族调查对象16.7%,参加村委会选举的人中,回族只占该民族调查对象的11.7%,与汉族相比较,回族农民政治活动参与率比较低。回族农民政治参与的消极状态,与回族人的历史遭遇及其持续影响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前,历代统治者对回族采取了民族沙文主义政策,尤其是经过清王朝的镇压和屠杀,回族人对政治有很大的排斥性。另外,回族农民政治参与率低还与文化适应有关,即回族文化传统与当前政府意识形态存在一定差异,需循序渐进地引导之。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汉农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的调查,我们可以发现:
1.农民政治认识水平普遍比较高,对常识性的政治符号认识明确,对重要的政治人物、政权机构的认识由于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差异,但农民政治态度比较模糊,回汉民族农民在政治活动参与方面呈现出明显差异。同时农民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状况不满意比例较大,对政治机构工作效能的评价呈现出机构级别越高,评价越好的特点。
2.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不高,与其他地区相比差距较大。被动性参与仍然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流,但自主意愿性参与逐渐成为选择趋向。农民对选举对象考量标准的多元化彰显出农民理性化政治参与的趋势。
3.民族文化差异对农民政治参与状况有较大影响,需积极引导之。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在充分了解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性基础上,不断深化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认知水平,对农民政治参与应该合理、正确地引导。实现有序地政治参与,不仅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更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