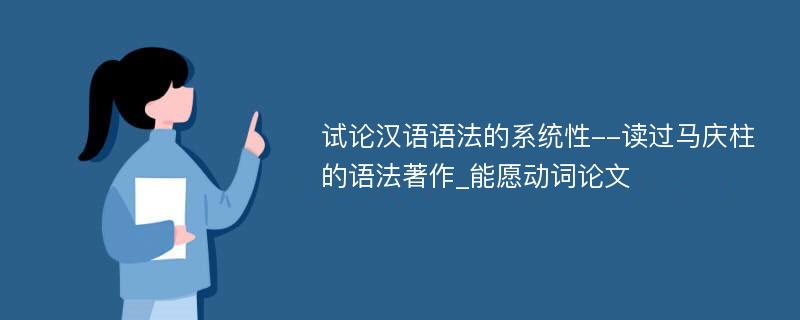
努力发掘汉语语法的系统性——马庆株语法论著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法论文,汉语论文,论著论文,读后论文,努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365(2001)02-0010-07
迄今为止,马庆株出版了两本个人语法论文集——《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1992)和《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1998)。对收在这两本集子中的论文,学术界已有评论,(注:见雷涛(1993)、邵敬敏(1994)、项开喜(1994)、邢欣(1995)、陈昌来(1995)、尹世超(1995)、张国宪(1999)、史金生(2000)。)而对这些语法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等深层次方面的问题,却未见有研究的文字。作为新时期汉语语法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注:见华萍《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的研究》,载《80年代与90年代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邵敬敏《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载《世界汉语教学》1998年第4期。)马庆株的研究成果已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他的研究思路、方法进行探讨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对汉语语法研究的认识和理解。本文拟从语法研究的目标、语法研究的方法论、语法研究的具体方法三个方面对马庆株以上两本论文集的论文进行挖掘。
一、语法研究的目标
各种语法学流派大体上都有自己的研究目标。就近代的传统语法来说,其研究目标是搜集语法事实并从中概括出语法规律。美国结构主义语法的研究目标不仅要描写语法事实,而且要研制一套提取语言结构的操作程序。生成语法的研究目标是描写人的大脑中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确定存在于人类语言中“普遍语法”的范围及其与各种语言的个别语法的关系。功能语法的研究目标是根据语言的外部因素,如交际、认知等对语法事实进行“所以然”的解释。
尽管汉语语法理论的源头来自西方,但在“经世致用”的文化背景之下,自诞生起就以发掘汉语事实、概括语法规律为主要研究目标。由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以及兴趣方面的差异,因而使不同的研究者又有自己的特点。马庆株语法研究的理论背景主要来自结构主义,这种学术背景使得他以发掘汉语语法的系统性为自己的研究目标。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揭示语法事实之间的联系
系统思想是20世纪自然科学的精华,索绪尔把它用于语言分析,认为在语言中重要的不是声音或意义本身,而是声音或意义之间的差别,即关系,语言系统内部的关系包括横向的组合关系和纵向的聚合关系。因此,揭示语法事实之间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就是发掘语法的系统性的一面,马庆株的语法研究大都集中在这方面。
《现代汉语的双宾构造》是描写动词带两个宾语这种结构格式的论文。语法结构一般由两个成分按照一定的语法关系组合而成,研究结构就要研究构成的两个成分本身的性质以及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此外还要研究结构体在更大环境中出现时表现的能力。这篇论文研究汉语的双宾结构时首先根据双宾结构中述语动词与宾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把宾语分为客体宾语、予夺宾语、表称宾语等15类,之后又根据双宾结构中宾语的语义差别把双宾结构分为包含虚指宾语的和只包含实指宾语的两大类,然后又根据语法差别把只包含实指宾语的一类分为包含准宾语的和只包含真宾语的两类,最后再各把包含准宾语的和只包含真宾语的两类按照述语动词和宾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分为若干小类。在此基础上,马庆株细致地刻画了每一类双宾构造中动词的语义特点,两个宾语的语法、语义特点,以及这两个宾语与动词之间的语义联系,并且又根据动词的语义特点进一步把双宾构造分为更小的类,描写各个小类的语法表现。
收在这两个集子中的研究语法事实的论文大都是从组合和聚合两个度向深入地分析语法现象之间在语义、语法上的联系的,因而从某个侧面揭示了汉语语法的系统性。
2.归纳词的语义小类
同一类的词,其语义上可能会有差别,语义上的这种差别会对其排列组合的顺序及所在的句法结构的语法形式产生影响,因而,在语法研究中给词归纳出语义小类可以对句法结构形式的差别作出解释。这两本集子中的不少论文都采取了这样的思路。
《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同是动词带时量宾语的句法格式“V+(了)+T+了”,但表示的语法意义却并不相同,有的表示动作完成以后经历的时间(如“死了三天了”),有的表示动作行为持续的时间(如“等了三天了”),有的既可以表示动作完成以后经历的时间,还可以表示动作行为持续的时间(如“看了三天了”),有的还可以表示动作行为所造成的状态持续的时间(如“[灯在门口]挂了三天了”)。马庆株研究发现,“V+(了)+T+了”所表示的语法意义的差别,是由格式中的动词的语义小类不同所造成的。根据动词构成的“V+(了)+T+了”有无歧义,并且借助替换、变换等手段把动词作了如下的分类:首先把动词分为持续动词与非持续动词,持续动词再分为强持续动词和弱持续动词,弱持续动词再分为状态动词非状态动词。
《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一文是马庆株对动词进行语义特征分类的另一重要成果。藏语动词存在自主与非自主的区别,这两类动词有不同的形态变化。马庆株发现,汉语动词也存在自主与非自主的区别,研究发现,汉语自主动词与非自主动词在句法形式上存在着二十多种对立,因此,这两个语义小类的建立有着坚实的语法形式的基础。而非自主动词又可根据语法形式的差别分为变化动词和属性动词,这样又得到一个动词的语义分类系统。在其他很多论文中,马庆株很注意词的语义小类的划分。
语法结构的实质是一系列的句法位置,而句法位置的基础就是词的语法语义小类,因此,研究句法结构不能不精确地归纳词的语法语义小类。每个词类都可以根据语法或语义标准划分为更小的次类,词类是一个系统,词的次类也是系统,大的系统之下包含着更小的系统,系统是有层级的。层级性是系统的重要性质之一,因此,归纳词的语义小类就是揭示词类内部的系统性,也就是在揭示语法在聚合方面的系统性。
3.提炼语法模型
语法模型是语法单位排列组合的结构格式,也是形式与意义、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复合体。因此,语法模型也是小的语法系统,如果在语法研究中提炼出语法模型,也就是发掘出了一个小的语法系统。马庆株在语法研究中很注意提炼精确的语法模型。
能愿动词可以连用,这包括连续连用和间隔连用,前者如“应该会肯(帮忙)”,后者如“(不)该(不)会”。能愿动词连用的规则是什么,马庆株在《能愿动词的连用》一文中首先把能愿动词从语义上分为可能动词A类、必要动词、可能动词B类、愿望动词、估价动词和许可动词六类,之后用数学的方法推导出了如下的能愿动词排列组合的模型:
可能动词A类>必要动词>可能动词B类>愿望动词>估价动词>许可动词
能愿动词连用时,不管出现几项,也不管这几项是哪一类能愿动词,都不会打乱上述模型中各项排列组合的次序,因此,这个语法模型有很强的预测性。
此外,马庆株还在《顺序对体词语法功能的影响》一文中提炼出了时间词、指人名词排列组合的语法模型,在《多重定名结构中形容词的类别》一文中提炼出了形容词、区别词排列组合的语法模型。
二、语法研究的方法论
语法研究受语言学方法论的指导,笔者认为语言学方法论的含义应该指对语言的看法,具体说来包含以下内容:语言是什么、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如何、语言由哪些部分构成、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语言与外部因素的关系如何、某种具体的语言与世界语言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位与变体的关系、语言结构具有层次性等等。
作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语法学还有它独特的方法论。本文只研究马庆株的语法论著,所以只讨论体现在马庆株语法研究中的语法学方法论。据我们研究,体现在马庆株这两本论文集中最重要的语法学方法论原则有以下几条。
1.利用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之间的依存关系
组合关系是呈线型排列的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它不是靠某几个语言符号建立起来的,而是靠具有相同特点的某几类语言符号建立起来的。因此,抽象地来看,一个语言符号的链条,实际上是由若干语法位置构成的序列,而这些语法位置可用具有不同的语法特点的语言符号去填充。聚合关系是具有相同特点的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语言符号的相同特点表现在语音、语义、语法各个方面。从语法方面来看,具有相同聚合关系的语言符号就是能在相同的组合位置上出现的一组语言符号,即具有同样分布的一组语言符号。由此可见,组合关系要靠具有同样聚合关系的语言符号按照一定的顺序来建立,而聚合关系的建立又离不开特定的组合位置,两种关系互相依赖,密切相关。所以,利用聚合方面的特点去说明组合方面的性质,或发现了组合方面的问题后到聚合方面寻求解释,都具有方法论的基础,马庆株的语法研究大都体现了这一方法论原则。
同一个名词前出现几个形容词(包括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区别词)时它们的语序如何?马庆株在《多重定名结构中形容词的类别和次序》中研究发现,形容词在名词前的排列顺序与性质形容词、区别词的语义特征有关,于是他按语义特征把性质形容词分为以下六类:(1)大小[,1]、(2)质量、(3)嗅味、(4)大小[,2]、(5)颜色、(6)形状,按语义特征把区别词分成以下四类:(1)数量/指大、(2)来源、(3)特种、(4)关系。无论性质形容词还是区别词连用都严格遵守以上的顺序,而状态形容词与性质形容词、区别词连用时则一定是状态形容词在前。像这样根据聚合方面的语义特点来解释组合方面的语法功能的论文还有《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顺序义对体词语法功能的影响》。
而《指称义动词和陈述义名词》则是利用组合位置来确定同一聚合类的特点。某些动词除了有陈述性外还有指称性,某些名词除了有指称性外还有陈述性,马庆株首先根据名词、动词与方位词组合后表义的差别分出具有陈述义的名词和具有指称义的动词两个小类,然后又进一步用与数量词的组合证明两个小类(具有陈述义的名词可与动量词组合,具有指称义的动词可与名量词组合),之后又借助体宾动词的宾语、准谓宾动词的宾语的位置来确定动词的指称性。利用组合来证明聚合,借助聚合来解释组合,这可充分揭示出语法的系统性,《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也是这种类型的论文。
2.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相互参证
语法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即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是如何对应的。传统语法由于研究语法意义因而能触及语言的较高层面,但由于常常混淆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使得语法研究不能成为精密的科学。结构主义语法区分了语言形式和意义,追求方法的严密,使语法研究成为一门精密的科学,但由于回避意义而不能在语言的较高层面上作业,终于被后起的生成语法取代。无论当代的生成语法,还是功能语法,也都是在努力地解决语法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处理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关系上,中国学者提出了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相互参证的原则,具体说就是,研究语法形式的时候要找到语法意义上的根据,而研究语法意义的时候要有语法形式上的表现。(注:见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年。陆俭明《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语法研究有从意义到形式,即“从内到外”的路子和从形式到意义,即“从外到内”的路子,不管从形式出发还是从意义出发,都要到另一个层面上寻找根据,语法学史证明,这条方法论原则是经得起考验的。马庆株的语法研究大都贯彻了这一方法论原则。
《能愿动词的连用》和《多重定名结构中形容词的类别和次序》两篇论文的研究路子是从外到内。词的排列顺序是语法形式问题,其中的规律如何?马庆株到语法意义上寻找根据,具体说就是到能愿动词和形容词的意义的差别上寻找根据,把能愿动词和形容词划分为更小的意义类别之后,就可用词的意义小类来说明词的排列顺序。《动词后面时量成分与名词的先后次序》也是从形式入手寻找意义根据的论文。动词V后面可以出现时量成分T和名词性成分N,二者在动词之后共现时可以形成以下两种格式:V+T+N(A式,如“去了三趟北京”)和V+N+T(B式,如“去了北京三趟”)。但有时T和N在动词后共现时只能形成A式(如“做一小时练习题”)或B式(如“到中国三年了”)。T和N排列先后的规律是什么?这与V的语义性质、T的语义性质以及V和N之间的关系都有关。能带时量成分的V可首先分为非持续动词和持续动词,持续动词又可分为强持续动词和弱持续动词,弱持续动词还可再分为不能表示状态的动词和可表示状态的动词,T可分为确定的时量成分和不确定的时量成分。从与T和N排序有关的V和N之间的关系来说,N可以是处所、予夺的对象、指人的使动对象、主体、客体、结果、工具等。根据T和V之间的语义关系,T和N、V之间的语义关系、T和V-N的语义关系,就可推断T和N的共现次序。
《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名词性宾语的类别》、《现代汉语的双宾构造》、《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顺序义对体词语法功能的影响》等论文则走的是从内到外的研究路子。例如,《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是根据数词、量词的语义特征来推导数量结构的语法性质的一篇论文,刻划数词、量词的语义特征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于是马庆株详尽地列举了基数、序数,特别是序数的各种形式,分别从基数词和序数词中提取出[-次第]和[+次序]的语义特征,然后分析量词之间的各种语义关系,根据量词与数词组合后表达意义的差别把量词分成序量词和基量词,从而从基量词中提取出[+次第]的语义特征,之后又从语义上把量词分出个体量词和范围量词。在充分地分析数词和量词的语义特征的基础上,马庆株推导出了数量结构连用时形成加合关系、偏正关系、主谓关系、联合关系的规律,以及“序数+名量词”数量结构指代整个数量名结构的规律。
以上论文大都采用从内到外或从外到内的一种语法分析的思路,而《含程度补语的述补结构》、《指称义动词和陈述义名词》则是交错使用这两条研究思路。
3.区分不同性质的语言成分和语法研究的不同层面
语言中存在着不同功能和不同结构的语言成分,比如语素(构词语素和变词语素)、词(实词和虚词、单纯词和合成词)、词组和句子(不同结构或功能的词组和句子),在语法研究中应该对这些不同性质的语言成分自觉地加以区别,否则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以《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为例,为了确定现代汉语词缀的范围,他首先把词缀同多音节单纯词中的音节、同虚词、同实义词根、同实义不成词语素、同构形语素等加以区别,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词缀的性质。“篱笆”从字形上看很像单纯词,这样“笆”就成了单纯词中的一个音节而不可能是词缀了,但是“篱”还可构成“樊篱”,这说明“笆”也是一个语素,由于是后附的,宜看作词缀。表示序数的“第、初”一般都看成词缀,但它们都只和成词语素组合,“第”还可与词组组合,不宜看作词缀,而应看作助词。“白皑皑”与“绿油油”不同,“皑皑”可以作定语和谓语,如“皑皑白雪、白雪皑皑”,而“油油”只能附在形容词之后,因而“皑皑”是实词,“油油”是后缀。在《与“(一)点儿”、“差(一)点儿”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中,他则根据句法功能的差别把“差(一)点儿”分解为性质不同的动词性成分、形容词性成分、副词性成分。
语法结构包括词法结构和句法结构,与语义一起构成结构体,然后与表达(语用)构成对立。传统语法不能自觉地区分结构层面和语义层面,结构主义语法只研究结构层面而回避语义层面。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韩礼德区分了这三个层面,中国学者在80年代中期提出区分这三个不同的层面。(注:见胡明扬《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和展望》,载《80年代与90年代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语法研究中区分这三个不同的层面对语法研究的科学化、精密化、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庆株在语法研究中很注意区分这三个层面,并且努力沟通这三个层面之间的联系。上文谈到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相互参证属于沟通结构和语义两个层面的研究,此不赘述,下文只讨论马庆株关于语法层面和表达(语用)层面互相沟通的研究。
《顺序义对体词语法功能的影响》研究了语用因素对语法的影响,指出指人名词自相组合一般只有一种语序,而衔位名词与专有名词的组合则有两种语序,如“蔡元培校长(A)~校长蔡元培(B)、里根总统(A)~总统里根(B)”等,其规律决定于功能层面:背称时两种语序很自由,而面称时只用A式,自称时只用B式,信函、电报、命令等的上款只用A式,下款只用B式。这就是说,A式是尊称,B式是谦称。
名词具有指称义,动词具有陈述义,但也有的名词有陈述义,有的动词有指称义。《指称义动词和陈述义名词》一文利用语法位置来确定名词是否具有陈述义,动词是否具有指称义。由于陈述义和指称义都是语用意义,因此,这篇文章是借助语法因素来确定语用意义的有无和程度的大小。
除以上三条以外,马庆株在语法研究中还有其他的方法论原则起作用,比如在语言共性之下审视汉语的个性在《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中就有充分的体现。
三、语法研究的方法
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中采取的具体手段、措施。从逻辑上说,所有的科学研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不外乎归纳和演绎两种,但是,每个学科都还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据我们研究,马庆株在语法研究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结构主义的方法:替换、扩展、变换
结构主义语法致力于语法形式的研究,发展出一套分析语法形式的方法,包括替换、扩展、变换等。
替换,是用某个词语代替组合序列中某个位置上的词语。使用替换方法的目的是归类,替换者和被替换者必定具有相同的特点,属于同类词语,否则两者之间不可替换。《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就使用替换方法来给动词划分语义小类。同是动词带时量宾语的句法格式“V+(了)+T+了”,但时量宾语表示的语法意义却并不相同,马庆株认为时量宾语语法意义的差别是由格式中动词的语义小类不同造成的,于是他用替换的方法划分了动词的语义小类。首先以“着”为分布环境,能在此出现的动词归为一类,是持续动词,不能在此出现的归为另一类,是非持续动词。持续动词之间的差别表现在多方面,其中之一是能在“完”前出现,不能在“完”前出现的动词是强持续动词,能在“完”前出现的动词是弱持续动词。弱持续动词内部仍有差别,其中之一是构成的“动+着+名”格式是否可以表示动作的持续和状态的持续,有的动词构成的这个格式只表示动作的持续,有的动词构成的这个格式既可以表示动作的持续,又可以表示状态的持续。前一类动词是持续动词,后一类动词既是持续动词又是状态动词。
扩展,是在由两个直接成分构成的组合序列中增加一个词,以此把两个直接成分分开。组合序列能否扩展,用什么词语扩展,可以反映出组合序列的语法性质。《述宾结构歧义初探》一文,在分析层次不同的述宾结构时指出,“刷白墙”有歧义,一是表示“刷白的墙”,一是表示“把墙刷白”。表示前一个意义时“刷白墙”可扩展为“刷着/了/过白墙”,表示后一个意义时“刷白墙”可扩展为“刷了/过一面白墙”。借助扩展,就为意义的差别找到了形式根据。
变换,是通过移位、添加、删除等手段把一个组合序列变成另一个组合序列。组合序列能否变换,如何变换,都可反映一个序列的语法性质。能愿动词和后面动词之间是什么关系?《能愿动词的意义与能愿结构的性质》一文借助变换作出了判断。述宾结构如“唱歌”可以变换为主谓式“歌唱了”,和肯定否定相结合的重叠形式“唱不唱歌”,状中结构(如“慢走”)和述补结构(如“吃饱”)变换成的主谓式和肯定否定相重叠的形式要么不成立,要么改变了原意。能愿结构则有与述宾结构相同的两种变换格式,如“应该去”可以变换成“去应该”和“应该不应该去”。显然,能愿结构与述宾结构的语法形式平行,应该属于述宾结构。
2.语义特征分析的方法
语义特征是能在某个组合位置上出现的一组词所共同具有的语义因素,通过分析在某个组合位置上出现的一组词的语义特征,可以有效地说明组合序列的语义或语法性质。乔姆斯基在其《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65)中使用了语义特征分析,中国学者朱德熙在其《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1979)首先在汉语中使用了语义特征分析,马庆株的《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1981)也是较早地使用语义特征分析的论文。这篇文章把“看了三天了”这种格式产生歧义的原因归结为动词的语义特征的不同,借助替换、变换以及歧义辨析等手段把能在这种格式中出现的动词分为以下具有不同语义特征的四类:(1)[+完成][-持续]动词,如“死、来”等。(2)[-完成][+持续]动词,如“等、睡”等。(3)[+完成][+持续][-状态]动词,如“看、说”等。(4)[+完成][+持续][+状态]动词,如“挂、写”等。而像《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则是专门论述自主与非自主这对语义特征的句法表现的论文。语义特征是马庆株主要的句法分析方法之一。
3.亲属语言比较的方法
这种方法一般只用于历史比较语言学,马庆株在《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中把它用于句法研究。汉语的亲属语言藏语区分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自主动词在语法形式上有三种表现:多数有命令式、有特殊的后加成分、可以构成祈使句。在这三种语法表现中,可以构成祈使句是最整齐划一的标准。既然藏语用句法标准区分自主动词与非自主动词,汉语的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也应该根据这个标准来划分。于是马庆株为这两类动词找出了两大类八种句法区别,区分开自主动词与非自主动词。这种方法在鉴别能愿结构的语法性质、讨论拟声词的构成以及指称义动词和陈述义名词时都曾使用过。
4.数学推导的方法
马庆株在研究同类词的连用时还使用了数学推导的方法。如果词项A、B、C、D、E、F、G等的排列顺序是A>B>C>D>E>F>G,那么,就可以得到以下的词序:A>C、A>D、A>E、A>F、A>G、B>C等等。语言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很有成效的,马庆株概括出的能愿动词连用的顺序、形容词连用的顺序都经得起汉语事实的检验。
语法研究的目标取决于语言观,它是在语言观的指导下确定的,只有把语言看作符号系统才能把研究语法的系统性作为语法研究的目标。语法研究的方法论也受语言观的支配,只有明确了语言是什么、有哪几部分组成、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理论问题后,才能确定语法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而语言研究的具体方法则是在语法研究的方法论指导之下所采取的具体步骤、手段,是为语法研究的目标服务的。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对马庆株的语法研究进行了探讨,无论是语法研究的目标,还是语法研究的方法论,还是语法研究的具体方法,都是就马庆株整体的语法研究而言的,而不是就某一篇论文而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