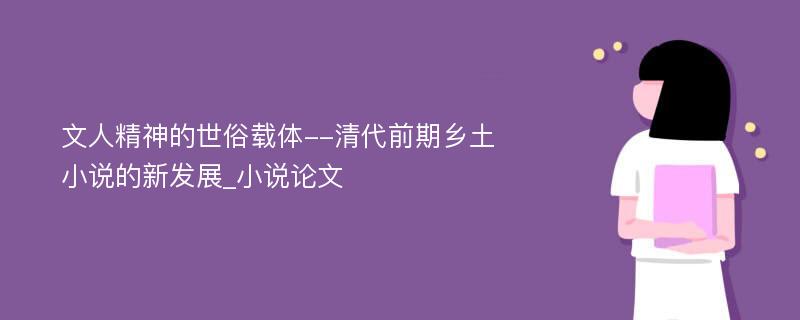
文人精神的世俗载体——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白话论文,短篇小说论文,文人论文,载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不太赞成用“拟话本”来指称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主要还不是因为在文体上所谓“话本”与“拟话本”有时难以辨析,而是因为它预设了一个标准,即以传统的话本小说作为白话短篇小说的正宗。当小说创作已远离书场,成为纯粹的书面文学时,这一标准更显得专横无理。诸多小说史著对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轻视和抹杀就是一例(注:以诸选本为例, 吴晓铃等编《话本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共选作品38篇,其中清初只有3篇;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古代白话小说选》(同社出版)50篇作品中,清初只也占3篇; 何满子编《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20篇中,清初为2篇,平均不足十分之一。 而且各本序言都强调了脱离生活、充斥说教,是清初拟话本走上末路的表现和原因。)。近年出版的一些论著如陈大康的《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欧阳代发的《话本小说史》等,始对清初短篇白话小说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在相关作品的认识方面,多有创见。只有囿于话本和拟话本的观念,一些有价值的看法仍稍嫌彰而不显。不言而喻,如果不是仅仅从“拟”话本的角度,而且也从这些小说自身的创作特点出发,我们应该可以对它们作出更恰当的分析和评价。
编纂与传播:世俗文化对文人精神的裹挟
世俗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文化集合。在形成背景、表现形态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与文人精神都有所不同。大体上,世俗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而文人精神则更多地带有个性特点,至少在外观上是如此。同时,世俗文化往往以现实物质利益为目标,具有很突出的功利性和享乐性;而文人精神则更偏向于文化本体和道德理想的探求。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世俗文化和文人精神及其关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明中后期,世俗文化在商品经济和心学思潮的双重推动下,曾表现出波澜壮阔的态势。清初,在经历巨大的社会变动之时、之后,世俗文化承其余绪,既有发展,又有所沉淀和收敛。比较明显的事实是,不少文学作品仍极力褒扬人情却又不再肆意煽情。与之相应的,文人精神也义帜重张。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明末士风的批判堪称这一倾向的代表。不过,这种批判并不是对明末单纯的反动,他们同时倡导的“工商皆本”思想,就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依托的。所以,在世俗文化和文人精神两个层次,实际上都出现了一种双向交流和互为牵制的局面。而要透视清初社会思潮的这一脉动过程,当时涌现的大批短篇白话小说,可以说是最生动的例证。
白话小说原本是世俗文化的产物,它凭借商业化的渠道,广为传播,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文化效益,文人精神被裹挟进来实属必然。从文人的角度说,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应当借助小说的影响传播“精神文明”。特别是明清易代,冲击了许多文人的梦想,对社会的责任不再表现为用世热情,而较多地转向对人的道德品质进行深入的考量。所以,很多小说家执着地强调小说的劝惩作用。例如《鸳鸯针》、《照世杯》等书前序文都宣示了这一点。重要的是,当小说的劝惩作用不但作为旗子、也作为幌子为全社会所认同,文人参与小说创作的心理障碍就不复存在了。
不过,源于书场的白话短篇小说,作为作者——接受者双向交流的产物,来自接受者一方的影响历经数百年的积累,已形成了一种编创——接受定势。换言之,文人作家在创作之初就面临了如何对待前此小说创作经验的问题。而小说的吸引力并不全在于它的说教功能,文人精神也不是单一的。如果文人精神可以划分不同层次,那么被裹挟进来的恰是最易与世俗文化结合的那部分,如寒儒意识、社会批判意识、情欲意识等。随着文化普及程度的日益提高,注定了有一大批文人只能屈身于世俗社会。他们的才华无法在主流文化中得以施展,只好转向“文备众体”的小说,借以抒愤自娱、驰骋情思。《豆棚闲话》天空啸鹤《叙》即称小说作者“卖不去一肚诗云子曰,无妨别显神通”。余怀在《一家言全集序》中则提到:“世之腐儒,犹谓李子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对于这种批评,杜浚《十二楼序》引李渔的回答是:“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终不敢以稗官为末技。”这既是对小说文体的自觉肯定,同时也是对自身文化角色的清醒认识。
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编纂出版有几种情形。一是翻印明代和当代作品。除了《今古奇观》这样著名的选本,还有不少改头换面之作。如明代《欢喜冤家》,清初改名为《贪欢报》、《欢喜奇观》及删节本《艳镜》等出版;陈树基编《西湖拾遗》,实际上是明末《西湖二集》和清初《西湖佳话》的汇编;还有《八段锦》,也是辑录明《古今小说》和清初《一片情》等而成。《四巧说》则是选编了《八洞天》和《照世杯》中的四篇作品。翻印之作文字略有增删,情节则多一仍其旧。
与上述情形相关的是抄改。所不同的是它不是完全照搬,而是有较多的改动。如《西湖佳话》卷15《雷峰怪迹》选自《警世通言》卷28《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但有所改动。《二刻醒世恒言》则抄改了《西湖二集》、《石点头》的某些作品。直到清中叶的《娱目醒心编》,还抄改了《古今小说》、《石点头》等中的作品。
再一种情形也是主要的情形乃是清人的独创。根据有关书目加以统计,现存清初白话短篇小说集约有三十余部(注:清初白话短篇小说集的实际数量不易统计。是否有亡佚失传者姑且不论,另有若干作品创作在明清之际,具体时间则不详。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所列顺治到乾隆主要作品为31种,本文取例仿此,上下限略宽,要以说明事理为主。)。这些小说集单部的分量都不如明代的小说集大,但总和却超过了宋元以来同类作品,无论如何是一个不应忽视的作品群。
清人的独立创作是在明末文人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从创作思想还是从小说体例看都是如此。例如明末《西湖二集》各篇俱以“西湖”为背景,《欢喜冤家》“演说二十四回以纪一年节序”,初步显示了短篇小说编撰的统一构思。而清代作家这方面的创作意图更明确。李渔的《十二楼》,篇篇俱以“楼”为中心,就表明它不是随意创作的简单汇编;《连城璧》辰集和巳集是两个独立的短篇,但在辰集结尾处,作者说:“这一回是处常的了,还有一回处变的,就在下面,另有一般分解。”在巳集开篇则说:“前面那一回讲的是命了,这一回却说个相字。”表明了作者创作的连贯性。《豆棚闲话》围绕“豆棚”叙述故事、展开情节,也极为别致;更值得注意的是《生绡剪》,这部小说集的作者署名有15人,显然是多位作者的合集。而这一合集不同于以前那种由一位作家不分时代先后的搜罗编辑,它很可能是若干作家为了同一目的的有计划创作。这种情形实际上在明末也已初见端倪。峥霄馆刊《皇明十六家小品》上有一则“征文启事”称“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异闻”。如果说这还可能只是征集小说素材的话,那么,《生绡剪》组织形式上就更进了一步。就征稿而言,这也并非特例。清初刊《资治新书》初集卷首载李渔《征文小启》云:“名稿远赐,乞邮致金陵翼圣堂书坊。稿送荒斋,必不沉搁”可为旁证。
大量的翻印和抄改曾被认为是话本小说衰落的表现。其实,从小说的传播来说,上述现象是很自然的。值得注意的倒是,清初新产生的白话短篇小说在后世很少有这样的幸运。按照国外一项文学社会学的调查,新出版的书20年后99%会被淘汰(注:参见张英进编《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8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 )对古代小说的流传很难作出这样的精确统计,据版本著录较多的大塚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清代白话短篇小说集几乎只有极少初期版本,许多只有一种甚至孤本抄本,与著名长篇章回小说的不断翻刻印行形成鲜明对比,甚至也比不上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版本之多。烟水散人的《珍珠舶》就只有一种抄本传世,而他的才子佳人小说《合浦珠》则中外公私皆有收藏;《云仙笑》也只有一种完整刻本传世,如此书作者天花主人即天花藏主人,其《玉娇梨》版本竟不下三十余种。一般来说,文学史总是偏爱开创者。一个清代诗人尽管可能写出比唐人更精美的诗,也难以使其获得唐诗那样的广泛流传。清初白话短篇小说传播有限,也与其后出且多效颦之作有关吧?事实上,在清初白话短篇小说集中,版本稍多的正是那些有所创新的作品,李渔曾为其作品盗版之多而苦恼(注:李渔多次提到他的作品被人翻版,以致发出“似此东荡西除,南征北讨,何时是寝弋宴甲时”的感叹(《与赵声伯文学》,《笠翁一家言全集》卷3)。);《豆棚闲话》、《西湖佳话》的版本不在少数, 也因为它们较有新意或适应了某种特殊的阅读需要。
从作者的角度看,清初小说家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当代性质,因此,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时代特征较之早期话本小说更鲜明。后者的创作与流传往往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则不然,它们一般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创作出来的,如《豆棚闲话》,据书中的评语用是“不数日而成”。在取材上,也尽量贴近现实。据统计,“三言”中的明代故事仅占23%左右(注:参见缪咏禾《冯梦龙与三言》,2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其他多为前朝旧事。而清初短篇白话小说则不然,如《醉醒石》除第六回所写“李微化虎”取自唐代外,其余14篇都写的是明代故事。《连城璧》18篇全为明代故事,都较接近当代。有的小说还带有一定的时效性,如《清夜钟》今存10篇均取材于明代,第一回、第四回写明末时事,距事件发生的时间极短;《云仙笑》中则有以天启、崇祯为背景的;《生绡剪》故事也较集中于明末,且有以清初为背景的。稍后的石成金《雨花香》、《通天乐》,更在书名上以“新刻近事”相标榜。贴近时代的选材,决定了它们的“当下性”,大约也是这些小说在时过境迁后就流传不广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清初小说家松懈了以往小说家自命的历史责任感。他们不再简单地把小说当成“野史”,而更多地将其视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展示自己社会认识的工具。李渔的不少小说在开篇即以第一人称“予”、“我”、“觉世稗官”等出面引述自己的诗作、介绍自己的经历、发表自己的见解。大约因为同样的原因,在早期话本小说创作中,征引前人诗词的惯例(注:参见拙作《三言署名诗词述考》,载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1号,1996年。),在清初白话短篇小说中明显减少。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石成金《雨花香》、《通天乐》在诸篇小说后,还附录他的《惺斋十乐》、《莫愁诗》、《武略私议》、《恤农现德》等诗文。文人精神与世俗文学相伴而行、相映成趣。
所以,在创作中,这些小说家更注重独创性。早期话本小说往往历经本事记录、艺人敷演、文人加工三个阶段,或者说其中通常包含三种文学成分。而清初短篇白话小说虽然仍有一些作品与以前的话本小说一样,有可考的本事出处,如《醒梦骈言》十二回俱依《聊斋志异》改编;但更多的作品一无依傍,完全出于作者的独立构思。李渔在《连城璧》酉集头回故事后就特别声明:“这一个是区区目击的,乃崇祯九年之事。”《十二楼·合影楼》结尾处说:“这段逸事出在《胡氏笔谈》,但系抄本,不曾刊板行世,所以见者甚少。”所谓《胡氏笔谈》不过是为自己“胡编乱造”张本罢了。《生绡剪》第四回结尾说:“这一篇事,载在《吴太虚家抄》。”大概也反映了同样的狡黠。从小说发展的角度看,独立构思、自行创作无疑的是一个进步。
事实上,清初的小说家是很善于编故事的。他们可能缺乏早期话本作者那样的世俗生活经验,因而无法在展示原生态的生活场景方面,表现出充分的素材积累。但他们有广博的知识,有丰富的技巧,加之他们的创作理念又往往不为“真”所左右。因此,他们敢于突破现实生活的束缚,大胆的构造自己的艺术世界。尽管其间可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却在作者的精心编织下,形成了独立自足的形象体系。《八洞天》作者序就明确地以女娲补天标榜,宣称他所创造的是“克如人愿”的“别一洞天”。同一作者的《五色石》也表现了同样的机趣,例如其中的《二桥春》将“二桥”置于优美景色中,既是烘托人物的自然环境,又隐喻两位佳人,还关合情节的发展,虽不尽合理,但构思缜密,用心精巧,足当补之。李渔小说更是匠心独运,构思出一个个精致圆满的艺术天地。
对于小说创作本身,文人作家也在无奈中获得了一种满足。小说取名《生绡剪》、《珍珠舶》、《连城璧》等,就都带有孤芳自赏性质。《珍珠舶》作者自序称:“若夫余之所传,实堪警世。”这种自豪其实也是文人精神的一种反映。因而,文人的文化优越感和自负感取代书会才人天真的卖弄,在小说中每每有所体现。他们经常嘲讽不学无术之人。如《鸳鸯针》卷3《真文章从来波折
假面目占尽风骚》极力讽刺胸无点墨的假名士;《五色石》卷6 《选琴瑟》中有一篇文字“诮那定别字、念别字的可笑处”;《八洞天》中《正交情》也有类似态度。《人中画》中的《风流配》则与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同一机杼,篇中用诗极多,实不能免借小说显扬才情之讥。
与此相对应,小说的知识含量与精确性有所提高,早期话本那种叙述的随机性、即时性被书面化写作的严谨和深思熟虑所取代。有的作品涉及历史,往往很注意细节的真实,如《十二楼·鹤归楼》第三回开头提到“宋朝纳币之例,起于□□年间”,看样子就是作者故意留下空缺,以待查考的。这样的谨慎态度大概只有文人作家才有。而对他们熟知的历史则会不厌其烦的加以介绍,如《清夜钟》第一回中就有高密度的历史材料。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一定是作者的炫耀博学多识,而只是文人秉性的流露。不过,要借助世俗文化的载体来表现文人的才学,总归是一件难堪的事。所以,有时对小说文体的认同,也就标志着一位小说家所达到的水平。例如当李渔不只是把小说与经史著述相提并论,而是充分肯定了前者的独特价值,他的创作就少了那种文人的忸怩作态。
在小说类型上,也有一些变化。早期话本小说题材广泛,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无奇不有。其中凶杀、奸情等极具刺激性的内容和发迹变泰之类离奇故事,尤为当时的小说家津津乐道。而文人作家更关注的是常态生活中的世道人心。例如爱情题材虽然一如既往地受欢迎,但着力表现的也不是人物的感情冲动,而是这种冲动的文化心理内涵,与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思想旨趣基本一致。
无庸讳言,世俗文化对文人精神的裹挟,有时就是文人向世俗的屈从。尤其是当商业化已经顽强左右小说创作时,趋俗媚俗差不多成了小说的普遍特点,区别只在多少而已。表面看,则似乎又有雅与俗的二水分流。高雅者或以风流自赏,或以劝世自命,这是大多数;低俗者则沉迷世俗趣味,这在色情小说中最为突出,如《载花船》、《弁而钗》等。像《一片情》等书名就表明了迎合时尚的目的,与《清夜钟》、《鸳鸯针》等的取意俨然分庭抗礼。这说明,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不是单一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小说家还致力调和二者的关系,如《云仙笑》中的《厚德报》结尾处,作者声称:“我这些说话,不但是劝世良言,直又是新翻刻的一部致富奇书。”作者靡然从俗,又欲以俗化俗,可谓用心良苦。
抒愤与开拓:文人作家对世俗文化的矫正
一旦文人精神被裹挟进来,势必成为世俗文化发展变化的催化剂。文人作家与书会才人的区别主要不在于他们的文化修养,而在于他们认识社会与人生的角度及表现方式、在于他们的文化关怀与使命感。从这一角度说,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在显示出对世俗文化矫正的勇气和实力时,才具有真正的特点和价值。
劝惩与娱乐是白话小说发展中形成的两大基本功能。如果还要细分的话,宋元时期更偏于娱乐性,而明中后期则突出了劝惩意义。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继承这一传统,但有所变化。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看,劝惩与娱乐主要是群体意志与需求的反映,而文人投身小说创作还必然使作家的个性意识随时表现出来。就劝惩而言,明中后期白话短篇小说并不限于道德层面,一般的人生经验也足以喻世警世醒世,如《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等的劝人忍辱戒忿。而清代白话短篇小说有不少作品强化了道德层面的意义。如《警寤钟》分述仁厚、忠义、孝悌、节烈四事;《八洞天》各篇命义都取自儒家经典,其故事也多用传统道德规范来观照现实人生,以致屡作有悖常情的描写,如男性义仆溢乳育主、善良太监生出胡须等等。诸如此类,是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经常为人诟病的地方。但是,清初白话短篇小说也并不像许多论者所批评的那样,只是一味的教训,其中也往往因作者态度不同而有所区别。如《五色石》中不但正面人物事事如意,皆大欢喜;其中恶妻逆子之类,也多悔过自新,得以善终,体现出作者宽厚仁慈的情怀,并不为极端的社会理念所左右。另一方面,传统的“发愤著述说”在明代经李贽等人引入小说理论后,得到了文人小说家的广泛认同,明末周清源作《西湖二集》即以此张本。明清易代,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种创作意识更为强烈,不少清初小说家遂将道德劝惩承诺升华为一种义愤。因此,他们笔下的道德内涵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如《清夜钟》成书于明清易代之际,作者自称:“余偶有撰著,盖借谐谈说法,将以明忠孝之铎,唤省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他所关心的道德问题不同于早期话本中的日常道德问题,而具有伦理纲常的重大性质,是剧烈的社会冲突的反映。如第一回《贞臣慷慨杀身 烈妇从容就义》正面讴歌甲申之变前后的忠臣烈妇,谴责那些误国背君、丧心丧节的达官贵人,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其他几回也多如此。类似的作品在当时并不鲜见,《醉醒石》第二、五回都表彰了忠臣临难、视死如归的品节;《十二楼》中《奉先楼》据作者称,他所写“这场义举,是鼎革以来第一件可传之事”。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八洞天》中《劝匪躬》则描写了文字狱的严酷,表现了民族反抗情绪。如此书作者确为明末清初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文人徐述夔,这种现实针对性尤堪瞩目。
同样,娱乐之于清初文人小说家,也不只是一种社会功能的体现。对他们来说,娱乐还离不开自我的遣兴逞才。说到底,他们从事小说创作是在失去了诗文的经典写作和淡化了史的意识后的一种良心游戏。而对市民生活的陌生,也使他们更多地依托内心深处的创作冲动,在精神领域展开幻想的翅膀,作轻松自在的游历和探险。李渔小说虚化现实,消弥冲突,致力创造一种欢畅风趣的轻喜剧气氛,就是这种新的娱乐风格的典型体现。
如果从新的角度来审视文人作家在白话短篇小说内容方面的拓展和开掘,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散发出的新的思想意识。概括地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社会问题描写的广度和深度有所提高,思考的自觉性也有所加强。如“三言”中很少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仅有的若干篇也未见深刻。而清初白话短篇小说中就有不少是正面表现知识分子的,尤专注于科举制度与士人品德。如《鸳鸯针》集中表现科举制度下不同儒生的形象,就是一种拓展。其中卷1《打关节生死结冤家
做人情始终全佛法》揭露科场弊端,令人扼腕;《人中画·自作孽》描写老秀才科举道路上的坎坷,充满辛酸与不平;《云仙笑》中的《拙书生礼斗登高第》意在批评有才无德的学子,赞扬诚朴的书生;《醉醒石》、《清夜钟》中也各有数篇写到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描写这些知识分子的作品中,不仅有对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生动展示,还有对他们内心世界的冷静解剖。如前举《鸳鸯针》卷1对徐鹏子等待发榜、 看榜及看榜之后的复杂心理的刻画,异常细致深刻。有的作品还有更深的思想意义,如《照世杯》中的《七松园弄假成真》就触及了文人的生存方式问题,它描写一痴情书生怀着才子佳人的梦想外出寻访意中人,却受到“众美人”的羞辱。这不啻为当时同样陶醉于这种“飞花艳想”的小说家的清凉剂。不过,此篇作品的后半部,又让这个失意的才子在风尘中找到了知己,提前做起了“青楼梦”,缺少吴敬梓描写“呆名士妓馆献诗”的那种彻底的冷峻。同书的《百和坊将无作有》写假名士招摇撞骗,反被更狡猾的骗子所骗,也直接触及士林丑类的肮脏灵魂。这些小说从总体上构成了《儒林外史》产生的背景,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事实。
除了题材的开拓外,对题材的开掘也引人注目。 如《珍珠舶》卷1所写蒋云诱奸商人赵相之母及妻终得报应事,颇有与“三言”名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相通处,而其中对赵母矛盾心理的表现,又令人想到《石点头》中《瞿凤奴情愆死盖》对孀妇方氏的描写,曲尽人情,十分深刻。即使在所谓色情小说里,有时也有对人性的精微剖析,如《一片情》对婚姻问题从人性的立场所作的描写就较有新意,作者认为“男情女欲”都是人之常情,因而赞成错配老夫或枯守空房的少艾、所嫁非人的丽人以及寡妇等都有追求性爱的权利;其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描写,颇堪圈点。
其次,反传统的逆向思维。李渔自称:“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闲情偶寄》卷4), 力求“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与陈学山书》,《一家言》卷3)。所以,在小说的命题立意上, 他刻意追求新奇,喜作翻案文章。如《连城璧》卯集写清官自恃清廉而固执断案,险些酿成不白之冤,表明清官之误,甚于贪官;辰集认为才子配佳人是“理之变”,美妻配丑夫才是“理之常”。作品的构思即从这种出人意表的观点展开。此书外编卷5又公然肯定同性恋, 把它视为三纲的异常方式,也算五伦中夫妇一伦。明末以来,南风颇盛,小说中也多有以此为题材的,如《弁而钗》4篇都是写这种变态之情的。李渔和而不同, 曲为之说,显示出他的机巧。
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力图“解豁三千年之惑”,更是充满了翻案文章。作者对一些历史故事作了新的解释,在翻案中显示了对社会现实的独到认识。如第一则把介之推不愿出仕说成是被妒妻所纠缠;第二则“唐突西施”,把人人艳说的范蠡西施爱情故事,写成了丑陋的阴谋。这种逆向思维并非凭空产生的。元散曲中已有不少对神圣事物的嘲谑;明清之际,思想解放,标新立异,更蔚然成风。李贽所谓“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正可视作艾衲居士创作的先声;而贾凫西的《历代略史鼓词》与《豆棚闲话》则有异曲同工之妙;独逸窝退士编《笑笑录》引清初滑稽者诗曰:“天开文运举贤良,一陈夷齐下首阳。”“岂是一朝顿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也堪称《豆棚闲话》中《首阳山叔齐变节》的同调。
再次,作家思想情趣的表现。李渔的小说在这方面同样比较典型。他是一位喜剧感很强的作家,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有充分地体现。同时,他的小说形象还浸淫着他的自我意识。《十二楼·闻过楼》就是一篇极为特殊的作品,其中明显地寄寓了李渔的人格理想,情节的淡化以及明显的编造痕迹,使这篇小说更像一篇言志抒怀的散文(注:参见沈新林《论李渔小说中的自我形象》,载《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4期。 黄强《李渔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中对沈作提出异议,但也肯定《三与楼》、《闻过楼》是李渔的自寓之作。)。
《西湖佳话》的编撰也体现出文人墨客的雅趣。据郑振铎介绍,此书刻本中有彩色套印西湖全图及十景图的,极工致。书前东谷老人序亦称:“今而后有慕西子湖而不得亲睹者庶几披图一览,即可当卧游云尔。”表明此书之作,近乎游览指南。因此,它突出的是“佳话”,主要是与西湖名人名胜有关的风流韵事,而很少话本小说常见的凶杀奸情之类。所以,它可以在“三言”中选取《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却不选另一篇也很著名的“西湖小说”《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注:据《七修类稿》卷40载“沈鸟儿”已成杭州俗语,可知此作也当为人熟悉。)。其编撰与明代田汝成编《西湖游览志》及《志余》实俱同样的情怀。此书还极少生硬的道德说教,行文也往往在平淡中见高雅,如《梅屿恨迹》的开头结尾,为主人公小青之恨作解释,聊聊数语,淡入淡出,极有韵致。
另外,清初白话短篇小说中的一些议论情理兼备,有时还带有明末小品文的风格,显示了文人的审美趣味,也为小说增色生辉不少。如李渔《十二楼·夏宜楼》中关于荷花的一段描写评论,妙语连珠,独具匠心,与其小品文《芙蕖》无论在思想意绪上、还是在遣词造句上,都如出一辙。《豆棚闲话》第六、九则等处对豆棚景致的描写,亦声色并作,清润可喜,韵味无穷,不及细摘。
在思想风格上,与早期话本的驳杂乃至浑沌不同,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在明晰清澈中又有流于单纯的一面,立意也更加显豁,概念化成为不少作品的特点。——我说“特点”而不像习惯上说的“弊病”,是因为这种概念化不一定就是思想的简单化,而可能与某种艺术追求联系在一起。如李渔《十二楼·合影楼》道学管、风流屠和不夷不惠的路子由,恰好构成了体现作者用意的戏剧冲突。这种概念化、象征性的人物在早期话本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它与文人作家追求主题的明快是一致的。这甚至在人物的命名上也可以看出,如《十二笑》中的崔命儿即“催命儿”,巫晨新即“无诚心”,墨震金即“没正经”等。类似的命名明代小说已偶尔有之,至李渔等人的作品以及《红楼梦》等中则时常可见,表明这也是文人小说的一个惯例。
另一方面,白话短篇小说变得更富于隐喻性,即使简单的情节也有丰富的题外之旨。《连城璧》之《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描写谭、刘二人的爱情,因情生戏,借戏传情。这种变幻莫测的戏梦人生,首先通过戏曲手法与小说手法的揉合得到生动表现;在此基础上,人物的人生经历又与作者刻意设定的戏剧情境相吻合,造成一种特有的艺术世界;而更深层的暗示则是人生哲学中的真假虚实问题。如此深刻的寓意也是以前的话本小说所少见的。
圆熟与超越:小说文体的新变及局限
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在文体上有不少创新,也有一定的局限。这种新变及局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白话短篇小说作为世俗文化的产物与文人精神载体之间的磨合、游移造成的。
就总体而言,清初短篇白话小说是话本体制发展到圆熟阶段的产物。因此,在小说的形式结构上,表现得游刃有余。与此相对应的、也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清初短篇白话小说对传统话本体制的超越,这种超越使之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从而更充分地发挥了短篇小说的特长。
小说文体的明显变化是体制的灵活,表现之一则是短篇小说的章回化。如《载花船》4回叙一故事,《十二楼》、 《照世杯》等都对短篇小说进行了分回标目。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反映了白话短篇小说向中篇小说的过渡。其实,所谓短篇与中篇,本来很难划一条鸿沟。《珍珠舶》每篇分3回, 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话本大系》校点者即断为中篇,而类似的作品甚至更长的,却又多有称为短篇的。实际上,若以篇幅论,清初许多小说即使在一集中也并无一定之规。《连城璧》丑集颇短而午集甚长;《十二楼》中长者如《拂云楼》分6回, 短者如《夺锦楼》仅1回。这些长短不一的篇什, 在作者的创作态度和方法上自无区别。相比之下,以才子佳人小说为代表的中篇小说则多在10至20回之间。当时,题署“天花(藏)主人”和“烟水散人”的中、短篇小说各有若干,作者俱是因事命篇,随物赋形的,绝无拉长截短之意;若以情节段落论,也有耐人寻味之处。标准的章回应是一个独立的情节单元,清初短篇白话小说中这样的章回自然不少,但也并不都如此,《照世杯》每篇正文有若干俪句标题,内容却长短不一,只是貌似章回而已。《四巧说》之《赛他山》据其《七松园弄假成真》改编,整饬标题,分为6“段”。是书其他3篇出自《八洞天》,《八洞天》原无章回,至此也被分别标出6“段”。而各段题目又只见于书前总目,篇中并未划分。 可见,这种分段只是为了便于阅读。从小说史的发展来看,短篇小说的分回在早期话本中就已存在,《醉翁谈录》中提到小说可分数千回自然是夸张之词,但《碾玉观音》等作品也确有分回的痕迹(注:《碾玉观音》分上下两回,《张生彩鸾灯传》、《李秀卿义结贞女》等作品中也有“且听下回分解”之类套语,可见短篇小说分回渊源有自。)。不过,早期话本小说中的分回主要是建立在说书者分回讲述基础上的,而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章回化则是与它的书面化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李渔在分回处常有“看官们看到此处,也要略停慧眼,稍掬愁眉,替他存想存想”、“暂抑谈锋,以停倦目”之类话,显然是为了方便阅读而设置段落。当然,这样做也是为获得一种更好的阅读效果,李渔在《十二楼·夏宜楼》中就曾说过:“做小说者偏要故意迟迟,分一回另说。……比一口气做成的,又好看多少。”值得注意的是,短篇小说一旦章回化,又会产生其独立的文体意义。
众所周知,话本的体制大体可分为入话及头回和正话两部分,它们相互映衬,连成一体。一旦分出章回,就容易失去照应。而且以一头回对若干回正话,比例上也更形悬殊。所以,许多小说干脆取消了头回,如《人中画》每篇分2至4回不等,一篇之前无头回,而各回之前却有篇首诗词,这相当于有几个“准篇首”。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娱目醒心编》多分2回,头回与正话各占1回,如卷9《赔遗金暗中获隽
拒美色眼下登科》头回正话,各叙一事,俱见标题。实际上头回即篇中第一回具有了与正话即第二回同等的地位;而第二回又自有回前诗,相当于入话。换言之,只此一回,亦符合话本惯例。这种畸轻畸重就是固守原有体制造成的。其实,头回之有无,也正如其他外部特征一样,并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体制活性化。事实上,现存宋元话本在体制的完整性上,恐怕还比不上明末的一些“拟话本”如“二拍”之类,但没有人会怀疑前者比后者更接近说书艺术的本来面目。因为,也许正是那种不完整性为说书人提供了即兴发挥、施展自己雄辩口才的机会。而过于完整的体制与描写则是书面化初起阶段的表征,一旦发展到圆熟时,就孕育出新的变化。李渔在《连城璧》之《谭楚玉》即声称:“别回小说,都要在本事之前另说一桩小事,做个引子;独有这回不同,不须为主邀宾,只消借母形子,就从粪土之中,说到灵芝上去,也觉得文法一新。”正可见出这种求新意识。同样,如《西湖佳话》、《雨花香》等开篇就进入正话,也是在圆熟中超越出来的。
在叙述上,清初白话短篇小说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首先,叙述者的身份和地位有所不同。早期话本的叙述者是以“说话人”的面目出现的,其叙述风格是讲述式的,与听众保持着一种平等的交流。而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叙述者通常带有“著作者”的口吻,叙述风格是记述式的,因而较少讲述时的临场特点。虽然平等的交流依然是理想的叙述语调,但文人的自说自话、高谈阔论乃至居高临下的宣讲却不时流露出来。最典型的是议论的大量增加。这一点在“二拍”、《西湖二集》等明末文人白话短篇小说中已有体现,而清初白话短篇小说更为普遍和突出。他们甚至以此自豪。《肉蒲团》第五回回末评云:“从来小说家,止有叙事,并无议论。即有议论,旁在本事未叙之先,敷衍一段做个冒头。一到入题之后,即忙忙说去,犹恐散乱难收,岂能于交锋对垒之时,作挥麈谈玄之事。”这其实就反映了当时小说家的态度与实践。其议论之多,随处可见,而且与明人议论主要用于揭示主题、突出劝惩不尽相同,清初小说家多喜欢借议论阐发自己的思想情趣。如《十二楼·夺锦楼》在一番通达的议论后,李渔说:“这番议论,无人敢道,须让我辈胆大者言之。”正表明他的议论不同于早期话本中的议论多以“公论”出之。同书《萃雅楼》开篇关于“雅俗”的大段议论,也表现了李渔的清谈兴致。这种夹叙夹议使得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文人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次,是叙述方式的变化。早期话本的作者虽然有“书会才人”一说,但基本上被重叠在叙述者即“说话人”中,因此叙述层次只包括“叙述者——人物”两方面,至多有时在引用诗词评论时,加上完全外在的“前人”、“当时有人”之类。而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却不这么简单。一方面,在有的小说中,“隐含作家”从叙述者中凸现出来(注:关于“隐含作家”,参见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中译本)第六章的论述。)。 如李渔小说中李渔本人就经常以第一人称“我”出现在作品中。另一方面,则是叙述者有时又从“隐含作家”分离出去。如《豆棚闲话》的叙述层次就更为复杂。以其中第一则《介子推火封妒妇》为例,一开始有一个“主叙述者”(“我”即艾衲)介绍叙述背景,接下来就是“次叙述者”(“老成人”)与“听众”(“后生”)的对谈;在对谈中,“次叙述者”又引出了“第三层叙述者”即作品中山东蒙师和山西驴夫。故事由此得以逐步展开。叙述者的多层次及虚拟听众的进入作品叙述层面,瓦解了“主叙述者”体现的权力话语,丰富了作品的叙述语调。如同书第七则开篇就对第六则正面叙述的故事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而第十二则陈斋长的长篇大论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作者思想的表露,其实,就在篇尾,作者又通过“听众”将其斥为“迂腐”,令读者莫衷一是。这种复杂内涵是以前话本单一叙述所不可能具备的。
在叙述具体情节时,早期话本由于说书的特性,常用正叙法,依次介绍故事的原委。而清初白话短篇小说不再拘泥于自然时间的先后,《十二楼·夏宜楼》中先叙瞿吉人对詹小姐及其周围的事十分清楚,然后才叙述他购买千里镜事,就是标准的倒叙。这样的倒叙在早期话本中是难得一见的。对于素材的剪裁,清初白话短篇小说也相当灵活。一般说来,早期话本,情节集中,细节丰满。“三言”中涉及苏轼的几篇小说皆是如此。而《西湖佳话》中《六桥才迹》也是以苏轼为主人公的,但它更像一篇传记,没有通常小说中必备的生动细节和情节高潮。不过,说它是个缺点,也不如说它是文人小说的一个特点,至少对这部“佳话”体小说来说是如此。
在叙述语言方面,通常所谓“韵散结合”也有所变化。早期话本中韵文极多,功能也各有不同。除了人物诗词外,还可以用于评论、点题、抒情、写景、状物、图貌等。清初白话短篇小说中的韵文明显减少(注:参见陈大康《论元明中篇传奇小说》,载《文学遗产》1998 年第3期。),尤其是套语更为稀少。同时,韵文的功能也大大弱化了,主要集中在评论方面。如《醉醒石》某些篇目用诗并不少,但功能几乎都是为了点明思想、评论人事的。
至于语言风格,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固然也继承了以往白话小说的成就,保持和发展了通俗活泼的一面,但更突出的则是它的知识化、书面化、艺术化。语言知识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文人小说家习用成语、典故和具有文人特点的比喻,这一点甚至在小说的题目上也可以看出。当时,例如《八洞天》各篇在通常的对句标题外,又另立三字标题,卷1 《补南陔》、卷4《续在原》都取意于《诗经》,卷8《劝匪躬》之“匪躬”则语出《易·蹇》;《五色石》诸题亦多类此,殊非一般读者所能明了。在具体行文中,更是成语典故层出不穷。这样的语言,文人阅读,自可会心;俗众翻看,就多有不便了。
与此相关,清初白话短篇小说更适合阅读而不适合演说。也就是说,白话短篇小说已从言语艺术蜕变为地地道道的语言艺术。例如长句式的运用时常可见,《五色石》卷6 《选琴瑟》开头有这样一句“如今待在下说个不打诳语的媒人,不怕面试的妻子,自己不能择婿、有人代他择婿的妇翁,始初被人冒名、终能自显其名的女婿,与众官听”,长达30余字,口头讲说,是不易听清的。同书《虎豹变》中又有《哀角文》、《戒掷骰文》两篇长赋,显然也更适于阅读。
小说语言从本质上说都是艺术语言,而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在语言的艺术化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特点。一般来说,叙述语言更加雅致纯正,有时甚至接近文言的风格,与早期话本那种扣紧生活本真的火爆热烈殊不相类。人物语言也往往因作者观念与修养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特点。如《十二楼·夺锦楼》中小江夫妇吵架,你一言我一语,完全以对句出之。这种语言很像戏剧的宾白,与李渔小说是“无声戏”的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又表明小说语言的发展其实是个性化的一个表现。事实上,早期话本的语言个性化的特点是不明显的,它主要体现的是说书人的共性。类似李渔小说语言的那种幽默风格是不易在早期话本中看到的。
从接受的角度看,清初白话短篇小说更适合于品味、体会,而不是简单的“看官听说”。至少,对那些知识含量较高的作品来说,浮面的故事并不总是精彩纷呈、引人入胜的。代之而起的巧比妙喻、意象思维,却可能代表了作者和作品的个性。然而,也正在这当中潜伏着它的始料未及的危机。
赘语:清初短篇白话小说的历史命运
最难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白话短篇小说没有直接发展为现代短篇小说?甚至连时间上的联系也似乎不存在。本来,这样的契机并非不存在。例如《豆棚闲话》与鲁迅的《故事新编》无论是古史传说的取材与翻案、还是油滑而又不失严肃的表现方式,都存在某种精神联系(注: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较早地指出了这一点,可资参考。)。然而,乾隆末期出现的《娱目醒心编》,似乎就为同类小说画上了句号。
很多研究者把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迷失归咎于它的说教性。其实,就具体作品而言,有说教内容的未必低劣;一无教训的也不一定高明。何况说教并不是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唯一的内容,还有不少小说不仅有意淡化了说教,而且在开拓题材内涵上作了可贵的努力。联系整个白话小说发展来看,长篇小说在《儒林外史》、《红楼梦》后,也呈衰落之势。换言之,小说的颓势是全局性的,不独白话短篇小说为然。所以,孙楷第在《李笠翁与〈十二楼〉》中就曾结合清代士人志趣的专注于朴学来说明小说的式微。
另一个常被提及的原因是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拟话本”性质。从清初白话短篇小说作者的文体自觉意识来看,他们确实没有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如果有全新的话——白话短篇小说文体。就这一点而言,说他们在模拟传统话本,当然是实情。但是,只要话本文体没有发展到穷途末路,在文体意义上的“拟”就不构成其衰落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原因。事实上,清初说书艺术还是很有市场的。如果从相反的角度看,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拟话本”,“拟”得还不如明代一些同类小说多,恐怕也说得通。所以,如果我们坚持要用“拟话本”的概念,从小说发展方面来说,至少应明确两点。首先,话本的可拟性,即它在内容选材、叙述方式等方面客观存在的可以模仿、效法的地方。提出这一点,是因为通常所说的话本直接关联着说书艺术,而后者具有许多不可拟因素,如它的表演性等;其次,“拟话本”作者模拟行为的动机、方式、程度和效果,这些具体而微的差别也往往被研究者忽视。而事实上,这当中可能正包含着一个小说家的个性。勿庸讳言,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在体制上确实存在着先天不足。在实际创作中,类似李渔、艾衲居士等人富有创意的作品并不多见。其间尚有《雨花香》、《通天乐》这样的作品,满足于题旨故事的陈述,几乎失去了对文体的关注,类似于白话笔记。稍后的《娱目醒心编》则代表了固守话本体制、毫无革新意识的创作倾向,是从清初白话短篇小说已经取得的成就上的倒退;再往后的《跻春台》尽管命题行文皆不累赘,内容也富于生活气息,但在文体形式上仍无实质性突破。白话短篇小说终于淡出文坛,实非偶然。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由于话本小说原属市民文学,创作者和接受者都以普通市民为主。而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作者基本上是文人作家,但文人又不大可能成为它们的主要接受者,他们也许更愿意欣赏当时一度中兴了的文言小说如《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清乾隆间曾衍东写过一部文言小说集《小豆棚》,在自序中,他反复强调一个“闲”字。光绪时项震新则在此书的《叙》中径称其为《小豆棚闲话》,说《豆棚闲话》“自出机杼,成一家言”,而《小豆棚》“其义类颇相似”,且在其上。这足以证明文人的审美情趣仍顽强地左右着他们对小说评判的价值标准,即使是《豆棚闲话》这样文人精神极为鲜明的优秀作品,也在这一标准下相形见绌。
因此,文人精神虽然被裹挟进了小说,却不足以改变它的世俗性质。如前所述,文人精神的一个核心因素是个性化的思维。而在清初白话短篇小说中,那种如同吴敬梓、曹雪芹所具有并且成功地加以表现了的个人化的挫折、失意、忧伤、忏悔等情感,还没有从群体的喜怒哀乐中凸现出来。传统话本早已形成的故事性叙事定势,也使文人小说家还不习惯借此短小篇幅思考重大的人生哲学问题,因而文人的强项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究其实质,这些小说家本身也是边缘化人物,他们未能跻身上层,又不甘于下层,游移两途却不能左右逢源。应当说,小说文本的意义在他们手中尽管有所强化,但就总体而言,世俗文化所关心的道德改良并没有提高到精英文化所强调的、类似《儒林外史》、《红楼梦》中那样的终极关怀的高度。偶尔流露的忧世伤时也总是被道德说教模式所含摄,丰富的人文信息在小说中往往成了一种叙事过程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和卖弄,而文人创作心理上的缺陷却在小说中扩大了,例如有意无意地回避矛盾等;与此相对的是,通俗小说本来具有的情感浓度与原生态的勃勃生机却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害,表层的娱乐性弱化更加剧了它与大众的疏离。所以,清初白话短篇小说从一开始就面临了一个矛盾,即文人精神与世俗载体的矛盾。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无法深入市民社会,也无法深入文人群体本身。这大概就是它应运而生又无疾而终的宿命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