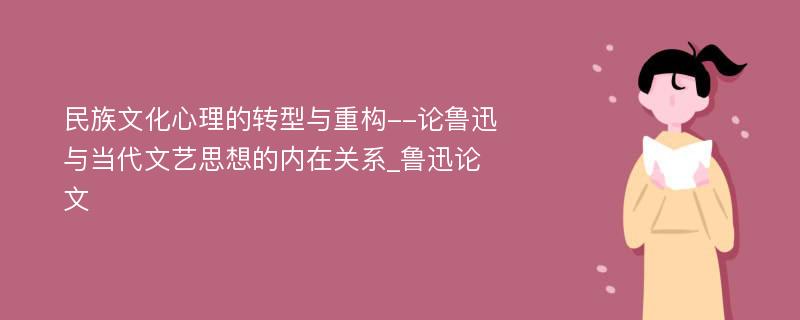
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与重塑——论鲁迅与当代文艺思潮的内在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思潮论文,民族文化论文,文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曾经借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的话说:“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1〕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 鲁迅虽然早已离世,但是,作为民族的一代文化伟人,他的思想,他的学说,他的精神给后世的影响则愈来愈大。尽管从时间的关联上来说,鲁迅与当代文艺思潮没有任何的联系,然而,从思想、精神、意识观念的关联上来说,鲁迅与当代文艺思潮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纵观鲁迅对当代文艺思潮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联系的焦点,这就是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与重塑的层面上,鲁迅与当代文艺思潮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1
面对近代中国社会遭受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外来入侵的双重压迫境况,鲁迅在执着于现实和历史的严峻思考中,首先发现了“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2〕的事实, 并在小说《狂人日记》里,以“吃人”的形象论断,指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历史特征。鲁迅由此而作出了他的选择:以“立人”为理想目标,追求以人的解放,尤其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为核心的社会解放与民族解放,不遗余力地关心人的命运和生存境况,寻找人的异化根源和整个民族与人类的出路。因此,居于鲁迅意识之中的,不是外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动,而是人是主体性的确立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鲁迅的这种思想意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艺思想,使他的全部的文学创作活动,都总是围绕着“立人”——对人的发现、追求人的解放这个主题思路而展开,即鲁迅自己反复强调的:“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3〕
通过文学的方式来发现人,追求人的解放,鲁迅发现了文学的独特作用。他指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4〕在鲁迅看来,文学作为发现人,塑造人的灵魂的重要手段,在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使命中,担负着独特而崇高的任务。它能够以生动的形象、激越的情感、深邃的哲理去面对落后僵化的民族文化心理,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使昏睡的人们觉醒和觉悟起来,成为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依据这样的思路,鲁迅在文学创作中,着重的不是表现包括农民在内的下层人民所受的政治经济的压迫与剥削,而是精神的毒害;不是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而是精神上的痛苦与病态。鲁迅选择了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那些受迫害最深的一组人物——那就是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来进行描绘,着重反映出他们的精神疾苦和心理异化现象,揭露病态的社会和病态的人生。譬如,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只仅仅用一些简单的交待来说明下层贫民物质生活的贫困,而重点是展示他们精神上被奴役的过程。像小说《药》,就仅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华老栓一家生活的拮据,而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精神上的愚昧;《故乡》里,最震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困,而是在一声“老爷”的称呼中所显示出来的精神麻木。对于妇女形象的刻画,鲁迅也是沿着这个主题思路来进行展示的。由于在“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中,妇女作为“悲惨的弱者”,精神上受迫害也最为严重。《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她的不幸不仅在寡妇丧子,更重要的是她精神上感到的孤独和空虚;《祝福》的深刻性也是如此,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精神上的恐惧;《离婚》里的爱姑,虽然如此坚强泼辣,但鲁迅却冷静地透视爱姑的灵魂,发现她灵魂深处的弱点,说明她精神上被奴役的程度,丝毫不比其他的人低。即便是在读书人——知识分子身上,鲁迅也同样是着重揭示他们精神的痛苦和自身的精神危机: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始终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苍蝇一样“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磨消沉中无辜销磨着生命”(《在酒楼上》),甚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成了真正的“孤独者”、“失败者”(《孤独者》)。就连在“五四”高潮时期曾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最后也因失去理想目标,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结果爱情也失去了附丽,只能怀着悲哀的心情回到旧家庭(《伤逝》)。由此可见,鲁迅有关人的发现,追求人的解放的文艺思想,正是“五四”文学所倡导的“人的文学”的集中体现,同时也代表“五四”文学的最高成就。
鲁迅的这种文艺思想,无疑对当代文艺思潮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里,所指的当代文艺思潮主要是指新时期(1976年以后)以来的文艺思潮。不难发现,自“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文学的最初阶段,也是通过对“人”发现,即开始向着普通人的血泪真情,向着整个民族的生存境况的出发点回归,而开始自身发展的历程的。新时期文学的早期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方之的《内奸》等,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可以说是不约而同地把对人的发现,以苦难唤醒人民,控诉极左路线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作为创作的重心。《班主任》通过对两个被迫害的孩子,尤其是对谢惠敏式的精神麻木,思想和灵魂都僵化的典型刻画,把笔触直接伸进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处,发现了极左路线对人的精神摧残。《伤痕》则选择中国人最讲究的血缘关系,在“文革”中被政治的极左思潮无情地扭曲的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心灵深处的创伤。《内奸》通过对视为“内奸”的田玉堂那种爱国精神的剖析,写出他决不卖友求荣的性格特征,写他谐谑中的不失正直,讲良心、讲义气人格精神,也是将文学创作的视点对准了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现人的存在价值,探求民族精神的实际内涵。
有趣的是,新时期文学在起步阶段,通过对人的发现,探索人被奴役的精神根源、心理根源和社会根源,也是选择了农民、妇女、知识分子这三个重要的形象来进行典型刻画。高晓声笔下的农民形象——李顺大和陈奂生,几乎可以说是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式的人物再现。 李顺大的天性似乎就是逆来顺受,连他自己发出的自责,也充满受传统观念制约的因素,在性格上,心理上表现出愚昧麻木的精神特征。他四十年建不起房子,其实是他四十年一直未能摆脱精神上魔魇的结果。陈奂生似乎更是“阿Q”的翻版。他沉默得近乎木然,感情内向, 而分到粮食后的热泪潸然,上城“卖油绳”的怡然自足,对沙发枕巾的忿然报复,住招待所交钱后的“优胜”心理,想到县委书记的青睐后的自高自大,都活生生地表现了一个“站惯了而不敢落座”的“奴隶”形象,一个以“暂时做稳了”的“奴隶”为最高心愿的农民典型。从这种对农民性格形象的描绘当中,可以看到,新时期文学是以鲁迅当年对中国农民的认识与表现为起点,而开始对人的发现,探索人的精神疾苦的思想进程的。在对中国妇女形象的描绘上,新时期文学对中国妇女身上因袭的重担与悲惨的命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张弦笔下的女性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是喜剧人物,即使在最幸运的人身上,也未能“挣脱”命运的“红丝线”,未能减轻所特有的传统枷锁的沉重感。张洁的女性系列小说,侧重表现知识女性更高层次的精神饥渴,暗示出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上即便是可以与男人一样平等,而未必在精神人格上获得独立与真正的平等,并向人们揭示,民族心理的惰性还会深深地压迫每一个敏感而自尊的女性。此外,作为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另一重要方面,新时期文学对于人的发现,探索人的精神疾苦,还表现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文化心理气质的重新发现和深入挖掘上。不论是被称为“归来的一代”(代表人物有王蒙、张贤亮、李国文、从维熙等),还是被称为“思考的一代”(代表人物是知青作家等),以及后来出现的“新生代作家”(如洪峰、苏童、余华、陈染等),都是以深入自我的方式,来解剖人的灵魂,并显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传统的人格理想作为最后的精神屏障,挖掘蛰伏在他们深层心理中“兼济”与“独善”、“不屈”与“不移”的儒家文化性格。
当代文艺思潮在新时期的种种表现,与鲁迅当年所倡导的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决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鲁迅文艺思想在新时期的逻辑再现,是在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上产生影响的结果。如果说鲁迅在他从事文学活动之际,就以反思整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方式,探索如何强化民族灵魂、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的方式,来展现他的文学创作业绩,那么,在新时期一旦封闭的大门被打开,中西文化的再度冲撞,民族灵魂处在裂变的阵痛之中,伴随着人的重新发现,人的解放的时代思潮的出现,一个深入挖掘和改造、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的文学新潮,就不可避免地汹涌而来。所以,鲁迅当年的认识,在新时期的逻辑再现,正是与当代文艺思潮保持内在关联的一个重要表现。
2
通过对人的发现,揭示异化现实对人的精神摧残现象,鲁迅又在探视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层面上,展现了民族灵魂内部搏斗的状况,并用文学的形式展现了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以“幻灯片事件”为引子,鲁迅从国人的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中,发现了千百年来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结构制约机制。他曾愤慨地说:“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能治疗的么?”〔5〕并发现:“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6〕于是, 执意刻画出一个现代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集中地“暴露国民的弱点”,就成为鲁迅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心。在《阿Q正传》中,鲁迅就通过阿Q矛盾性格心理的刻画,展现出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特征,深刻地揭示出阿Q精神胜利法与支配着整个社会的传统思想、文化心理结构的联系,以及与农民小生产者的落后、闭塞、保守、软弱的历史地位的联系。同时,阿Q 的精神胜利法又是古老中国不能适应近代社会急剧变动的产物,是一种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安于并掩饰民族落后与被奴役命运的民族精神病态,即“国民性弱点”。鲁迅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现状的深刻研究中,发现了阿Q精神胜利法, 正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并通过这种对国民灵魂的剖析,展现了中华民族进行自我批判——这正是民族的伟大觉醒的标志——的历程,力图通过这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寻找民族振兴的希望。
无疑,鲁迅文艺思想的生成及其发展是紧紧地抓住了“人”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尤其是抓住“人的发现”、“人的觉醒”这个精神发展的线索来展开的,并显示了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揭露、批判和改造,对封建意识残害下的民族灵魂及其近代畸形形态进行深入的挖掘的思想倾向。正是在这样一层的深刻涵义中,当代文艺思潮的发展,就紧扣鲁迅当年所确定的方向而行进,使整个当代文学显示出深刻的思想力度。
在重新回归到“人”的主题之后,当代文艺思潮也把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新认识与自觉改造及建构,作为一项神圣的使命。新时期文学创作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对民族心态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透视和扫描。例如,贾平凹的《浮躁》和张炜的《古船》,就对民族的文化心理痼疾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形象地告诉人们:长期的传统文化观念熏陶与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机制仍带有严重的宗法血缘关系色彩的人身依附因素,代表着家族利益的部分基层政权,还在阻碍着现代化进程。作者发现,如果不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去挖掘,所谓的改革也只能是在旧的传统结构中改革,至多不过是代表某一特定的群体、特定的阶层的“英雄”奋斗(如《浮躁》中金狗的行动),甚至将出现由除暴安良向杀人越货的亡命之徒蜕变的游侠式抗争(如《浮躁》中雷大空形象塑造)。又如郑义的《老井》,通过孙旺泉、赵巧英和段喜凤的爱情纠葛及老井村前仆后继的打井找水斗争,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弱点进行了深度的刻画。新时期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发现,造成民族文化心理弱点的机制,在于传统的“人伦”为核心的文化观念,总是以牺牲独立的个体为代价,忽视人应有的权利、地位、价值和尊严。这样,人的自由和自觉的创造本质就被抹杀,大多数人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从而被异化为非人。所以,新时期作家将笔触深入到民族灵魂的内部时,就必然会像鲁迅当年一样,对民族文化心理弱点,予以高度的关注和深刻的表现。这种现象告诉人们,当代文艺思潮倡导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与重塑,是不可能脱离对民族文化心理弱点的当代形态进行深入发掘的。偏离鲁迅当年探索的轨道,必然会影响文学表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思想广度与深度。
通过文学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其它方面如哲学、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方式来展现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因素,这是因为文学以其生动的形象、真实的情感,保存了以集体无意识和积淀的方式遗留下来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相对稳定的因素,更能够以对应民族文化心理的内部构造与功能的形式,穿透人的心灵深处——心理结构的潜意识和无意识层,来进行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与重塑。别林斯基说:“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7〕。这也就是说,文学总是要表现一个民族的意识、 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的,即表现民族性。鲁迅以文学的方式来展现民族灵魂的内部搏斗,来改造国民性,是遵循了文学的这一特性的。所以,通过文学的方式发现人,追求人的解放,改造国民性,鲁迅就能够深层次地发现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些本质特征。他指出:“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极不容易”〔8〕。这种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带来了许多负面的效应。鲁迅说:“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又说,这使“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9〕在鲁迅看来, 这种情况造成了国民心理性格上两方面特点:一是无热情、麻木,“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10〕;二是无悟性,甚至阿谀奉承和无端发泄,如“在弱者身上发泄”。国民的这种心理性格结构,正是在传统文化观念负面影响下形成的奴性心理,前者是奴隶心理,后者是奴才心理。鲁迅在文学创作中,通过形象的描绘,表达了他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激烈否定的情绪和思想倾向。
当代文艺思潮在沿着鲁迅开辟的改造国民性的方向进行中,通过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展示,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局面,即一方面是直接地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和方法,侧重于对民族文化心理弱点的揭露的批判,由此来达到改造与重塑的目的。如高晓声对农民形象的刻画,李顺大的奴从思想,陈奂生的阿Q式的“自我解脱”, 都是以否定的方式来透视民族灵魂的内部斗争的;另一方面则是在这个基础上,多层次,多方位地表现民族文化心理的当代形态的丰富性。如新时期文学从“意识流”小说,朦胧诗,一直到寻根文学(如莫言的《红高梁》、韩少功的《爸、爸、爸》)和探索文学(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以及后来的“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就试图从人的情绪感受的某种非逻辑性、非理性的部分入手,展示人类精神的全面性、丰富性,并在不同的程度上,展示民族灵魂内部搏斗的轨迹,触及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深层中的弱点。此外,还有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中展示对民族灵魂搏斗的描绘。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路遥的《人生》等都分别从这个角度,表现了这个鲜明的主题。《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形象及其内在精神的演变,就在触及到人的存在意义、人的自我价值和潜能的根本性问题中,展现了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族灵魂内部搏斗的轨迹和改造、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的主题思路。《人生》中的高加林,以于连式的个人奋斗,试图摆脱土地(传统的象征)的束缚,尽管暂时以失败而告终,但却表现了向着传统的农民灵魂表示怀疑的思想倾向。所以,当代文艺思潮以展示民族灵魂内部激烈搏斗的方式,汇入鲁迅开辟的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的思想洪流中,就在继承鲁迅精神、发扬鲁迅精神,以及开拓不断地超越鲁迅的传统当中,获得自身发展的广阔空间,并在所描绘的民族灵魂的内部搏斗中,更深层次地引发了对于人的价值、尊严、权利和存在意义、命运境况进行多层次、多方位思考与探寻的创作主潮。
3
鲁迅文艺思想的生成,无疑是对传统文学的文化形态的超越,构成了文学完成民族文化心理改造与重塑的巨大工程的“心”的历程,也构成了向新型文学观念、形态、体式、语言和话语方式转变的新的起点,真正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从而也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光辉历程与独特的精神文化风貌。深究鲁迅文艺思想的本质特征,不难发现,鲁迅对于文学及文学所表现的社会现象的把握,总是在清醒地审视民族灵魂的思想层面上,将其上升到文化层次、文化审美层次来进行观照和表现,从中探讨蕴聚在文学内部结构中的深刻、稳定和恒久的,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形态而表现出来的人类文化精神和文化审美价值,探讨文学与人类精神活动、人的主体创造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突出文学对于人的关怀的终极价值与意义。
鲁迅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沿着发现人,追求人的解放,探视民族灵魂内部搏斗的主题思路,善于在“显示出灵魂的深”的境界中,来进行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与重塑。在写出一个现代的“沉默的国民魂灵”的《阿Q正传》中,通过对阿Q矛盾性格的刻画,就成功地显示出蛰伏在阿Q灵魂深处的那种民族的劣根性。小说描写阿Q在临刑前所看见的那“咬他的灵魂”的“狼眼睛”,以及他最后喊“救命”的细节,实际上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警告和文化提示:没有一场真正消灭“咬嚼”民族“灵魂”的精神上的野狼式的思想革命,整个民族就难以摆脱“永劫轮回”式的“大团圆”命运的束缚。鲁迅十分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中间发现人”的文学命题,指出“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11〕。在人中间发现人,在审视灵魂中显示灵魂的深刻,鲁迅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进行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与重塑,也就获得了双重涵义:一是构筑了一整套重铸民族灵魂、改造国民性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二是通过文学的形式成功地传达出了现代人那种刻骨铭心的人生孤独感、寂寞感和深刻的忧患意识,从而获得了一种清醒的理性自觉精神和文化自觉意识,也使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获得了一种参与世界文化对话、交流的话语权利和方式。这样,鲁迅的创作可以说既是对整个中国社会发出的深刻呼吁,对改变民族生存境况的强烈呐喊,又是赋予文学以生命意义、生命形式的一种文化形态的精神载体,并在汇入世界文化交流、世界文学对话当中,显示出文化意识的自觉对文学发展的深刻意义。
当代文艺思潮在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几个环节之后,自“寻根文学”后,开始超越政治和伦理的层次,更深入地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与背景中来对现实历史作总体的文化审美观照与把握,并在文化反省与批判当中,逐渐地使文学向自身回归,显示出当代文学向成熟、深化方向发展的轨迹。
以“寻根文学”为起点的当代文艺思潮的发展,或多或少地都触及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与症结,体现了一种自觉地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深处开掘的创作总体趋向。特别是中西文化冲突在新时期重新得以冲撞、交汇,这使许多当代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把文学引向了文化审美的深层领域。当代文艺思潮虽然出现了许多派别,如“寻根派”、“现代派”、“先锋派”等等,但深究他们文学创作的内核,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了走向文化深层结构,发掘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为代表的人类精神奥秘和心灵奥秘创作趋向。不论是“寻根派”的深沉,还是“现代派”的颓唐、“先锋派”的调侃,所展示的仍然是由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民族灵魂搏斗。阿城的作品表面上是那样的平静,王一生(《棋王》)对正式棋赛和名次不屑一顾,颇有老庄哲学的超然之志,但深藏其中的不正是现代人由文化冲突而引发的孤寂心态吗?徐星、刘索拉的作品虽然是那样的颓唐,李鸣(《你别无选择》)的沉睡不醒及对贾教授的轻蔑,说到底是对所谓神圣的伦理规范的轻蔑与嘲讽。这些创作都在超越“伤痕文学”以来,甚至更远的文学依附政治伦理的传统中,显示出在文化审美意义上的对生命本质与永恒价值探讨的创作努力,并与鲁迅的创作保持着内在的一致:在灵魂中深藏着由文化冲突而引发的人生忧患意识。
当代文艺思潮从“寻根文学”开始超越政治伦理层面,走向文化层次、文化审美层次,仍是与鲁迅精神保持内在关联的结果。鲁迅当年选择文化观照为突破口,由此深入到对国民文化心理进行改造与重塑的文学创作之中,正是他清楚地看到文学需要在文化这个更深更广的综合层次的高度,来体现对现实历史的深刻和整体性把握的规律特征。正如卡西尔所强调符号动物——人创造了文化,而文化是属于人的文化,是人的外化,它紧紧围绕着人并由人的“圆周”把它们如“扇面”似地整合为一体那样,鲁迅将文学引向文化层次,文化审美层次,从而使文学创作无论是在意识观念上,还是在艺术形式、技巧和话语方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并使文学的立足点升高,使人们通过文学对于现实历史的描绘,看到茫茫大千世界中人的灵魂奥秘,标明了文学的独特价值和作用,创造了中国文学的新的形态。当代文艺思潮走向文化层次、文化审美层次,也基本上是与鲁迅的方向保持一致。“寻根文学”以后的当代文学创作,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区域文化风俗的图景,提供了多少类似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精神图景,而在于在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和时代的需求中,力求在中西文化再一次碰撞、交汇的历史机遇面前,重铸民族灵魂,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期待在置身世界潮流中记录自己民族的苦难、惊醒、衍变与强大的心灵轨迹,反映整个民族生存的境况,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共鸣。
鲁迅在走向文化层次、文化审美层次中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使人们看到了文学探索民族灵魂、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的远大前景。当代文艺思潮沿着鲁迅开辟的方向,在走向文化层次、文化审美层次中,使当代文学创作在重铸民族灵魂、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朝深化方向发展,朝与世界文化、世界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方向发展,这样也就大大地促使了文学主潮在90年代,以至在迎接下一个世纪到来中得以深化和博大。可以预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21世纪必将是整个中华民族崛起的世纪,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舞台发挥更大作用的世纪。文学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和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精神最敏感的表现区域,必将最先传导出整个民族崛起和强大的信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当年在文化冲突中所确立的发现人,追求人的解放,重铸民族灵魂,改造与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主题,所张扬的文化反省与批判精神,仍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当代文艺思潮和文学创作主潮沿着鲁迅开辟的方向行进,也必将会在充分地吸取人类文明的精华中,闪烁更加耀眼的光芒,真正地成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更深层次地探求人的解放,特别是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的启明星。
1995.8.30.于西子湖畔
注释:
〔1〕《华盖集·战士和苍蝇》。
〔2〕《坟·灯下漫笔》。
〔3〕《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4〕〔6〕《呐喊·自序》。
〔5〕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7页。
〔7〕《别林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8〕《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9〕〔10〕《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11〕《集外集·〈穷人〉小引》。
标签:鲁迅论文; 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艺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艺术论文; 浮躁论文; 灵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