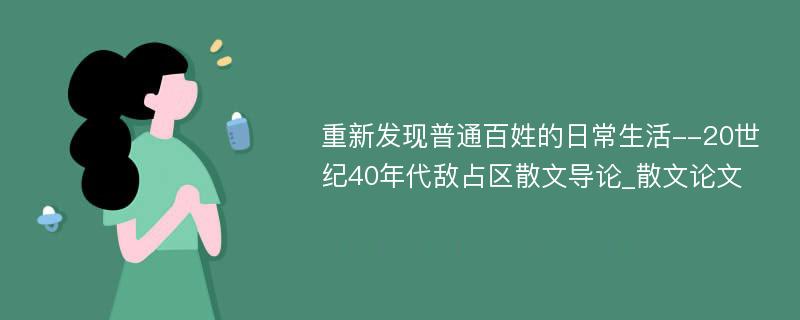
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40年代沦陷区散文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沦陷区论文,日常生活论文,概论论文,普通人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讲述了沦陷区散文发展的基本脉络,描述了沦陷区散文的面貌,分析了沦陷区散文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和成因,指出了沦陷区散文对历史的承继和在现实中图生存求发展的处境,并对散文文体的研究进行了一点尝试。
关键词 散文 沦陷区 沉潜 散文家的散文 诗人的散文
1
学术界有沦陷区文学曾经历过“沉寂调整期、复苏建设期、中兴期、衰落期”几个阶段之说〔1〕。进一步考察则发现, 在沦陷区文学的调整、复苏以至中兴中,散文创作几乎是起了“先锋”的作用,这个现象颇值得注意。
首先沦陷的东北地区,在其保持民族文学(文化)血脉的最初努力中,曾有过“杂文”的短暂兴起。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沦陷初期,日伪文化统治尚未严密,‘五四’、左联新文学的余波还在东北文坛激荡,国土沦丧的现实又使作家郁积的悲愤日益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充满批判、战斗激情,长于议论的杂文被许多东北作家启用,其中不乏笔锋犀利之作”〔2〕。1931 年底《哈尔滨公报》发表的《老裴语》系列杂文(作者裴馨园)即其中的代表作。以后随着日伪文化专制统治的不断强化,杂文锋芒虽有所收敛,但作者仍委婉而又明确地表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同时,也表露了在“言与不言”间选择的艰难与困惑(季疯:《言与不言》)。这意味着,沦陷区散文创作(以及整个沦陷区文学)在经历了最初的激昂以后,将进入一个生命与话语的“沉潜”时期。
复苏的最初“消息”是由有着更深厚的文学传统的北平文坛首先传出的。1938年上半年创刊于五四之后的北平《晨报副刊》率先复刊,与《新民报》副刊《天地明朗》、《沙漠画报》等一起同时推出了最初一批散文小品,尽管多半是水准以下的不成熟的作品,却毕竟开了个头。于是,这一年的年底,终于有了大型文艺刊物《朔风》的创刊。编者开宗明义宣称本刊“以小品文为主”,因此,评论者普遍认为,《朔风》是战前(三十年代)《人间世》或《宇宙风》的继续〔3〕; 但编者却郑重声明“不提倡幽默”〔4〕,因为无论客观时代条件, 还是作家主观心态,均无从(不能)幽默,就只能趋向“严肃”,主编者却又特意点明这“过分的严肃,也可以说是含有一种不得已的苦衷”〔5〕。 而评论家则注意到,“这个小刊物的执笔人都是沉寂中的作者”,其中坚力量除周作人、沈启无、毕树棠、傅芸子等三十年代的老作家外,也还有麦静、南星等青年作者。这样一批“沉寂中的作者”,以“严肃”的心境与态度,以“水平比较严整”的创作实绩,显示了一种散文创作的新的风貌与趋向,评论者当时即指出,《朔风》不但“填上了空白的一页,把过去的光荣的历史衔接起来”,而且“也开拓了未来的道路”〔6〕,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了其后数年华北散文创作的格局。
于是又有了1939年的收获。4月初春时节, 辅仁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师生自动募捐,出版了“纯文艺集刊”《文苑》(后得到校方资助,作为校刊出版,改名《辅仁文苑》);编者在《编辑后记》里宣称:“我们不曾抱有办杂志,甚或以这为营利的妄念,事实上,就不愿它成为一件公开推销的庸俗刊物。仅只是珍贵的友情结成的纯晶,是爱好文学同人们写作实习相互批评的园地,除了本身纪念的意义外,更没有什么副作用”。怀抱着纯正的文学(文化)理想主义,标榜超商业(物质)的纯精神性,这正是“校园文学(文化)”的特征。同一年,燕京大学先后出版了《篱树》半月刊、《枫岛》文艺周刊、《燕京文学》半月刊,北京大学文学院则创办了诗文专刊《诗与散文》,10月,汇文中学的师生也创办了《覆瓿》文艺月刊。吴兴华、南星(林栖)、林榕、张秀亚(亚蓝)、毕基初、李道静(麦静)、秦佩珩等一大批青年诗人、散文家在他们自己开垦的文艺沃土中脱颖而出,这是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北京校园出现何其芳、卡之琳、李广田等“京派”青年作家群之后,又一次校园创作群体的勃起,与稍后出现于大后方的西南联大诗人群(穆旦、郑敏、袁可嘉等)遥相呼应,此后校园文学曾有过长时期的停滞,直到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才重又复兴。1939年的北方文坛正因为有了这生机勃勃的“开端”,才于这一年下半年推出了被史家们称为“华北沦陷区文坛最重要的刊物”《中国文艺》〔7〕, 它一开始即以“高级的纯文艺杂志”为号召,内容相当庞杂,甚至包括了艺术、绘画、电影等在内,但编者却特别着意于随笔小品的倡导,曾在2 卷2期中专门刊发“散文专号”,组织了“国内随笔”、“国外随笔”、“书简”、“散记小品”四个特辑,近三十篇文章,表现了相当的胆识与眼光,一时蔚为大观。《中国文艺》还经常发表散文译作,这在相对冷寂的沦陷区翻译界中是颇引人注目的,对推动散文创作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文艺》的作者队伍广泛而具实力,有“华北文艺人的宝库”之称〔8〕,不仅有周作人、沈启无、张我军、澜沧子、 芸苏、纪果庵、俞平伯、傅芸子等中年作者(他们大都为“既成作家”)为其基本队伍,前述“新进”青年作者(及柳雨生、侯北子、狂梦、雷妍、闻青等人)也因在《中国文艺》上发表作品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可以说《中国文艺》包容了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散文作家。上述两大作家群分别受到了周作人与何其芳的影响,着力于“随笔”与“诗化散文”(当时称为“田园风味”的散文〔8〕)两种不同的散文体式的创作试验,但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沉潜于人生与艺术上又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当时就有人把这两类散文都通称为“个人为中心”的散文〔9〕。 以《中国文艺》为中心的上述散文作家这一创作倾向也曾引起过不满与反拨的努力。1940年报刊上先后发表了丁谛的《重振散文》(载上海《新文艺》月刊1卷1期)、萧人的《由〈重振杂文〉说起》(载《辅仁文苑》第5辑)、林慧文的《现代散文的道路》(载《中国文艺》3卷4 期),不约而同地批评“个人为中心”的随笔,田园风味小品的个人主义与唯美主义“范围未免太狭隘”〔10〕,脱离了“时代”与“大众”,并呼吁时代感与现实感更强的“杂文”与“通讯”(报告文学)的“重振”与“随笔”、“小品”题材的扩大〔11〕。1941年《吾友》杂志增辟“杂文”版面,杂文家吴楼因此而预言:“我们将又看见这样的战士——他举起了投枪”〔12〕。但实践的结果,却使他的这一预见落空。批评家在总结这一年的杂文创作时,尖锐地指出,《吾友》上的杂文最后都成为“社会的随感”,“正失掉它战士的态度”了。吴楼本人的杂文,虽竭力保持杂文的“批判”性,但也只能指向文坛与社会上的某些不良倾向,很难说有多少“战斗锋芒”。正像批评家所说,“杂文的不易发展,乃是这时代中必然的结果,因为‘战士’是最难做的,‘但他举起了投枪’就更难了”〔13〕。“通讯”(报告文学)的命运也是如此,人们所期待的及时反映时代大问题的“报告”亦未出现,所能产生的仍然是反映社会、人生一角的“社会通讯”。而另一方面,“以个人为中心”的随笔小品至少在1940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发展。批评家仍作出这样的估价:“事变后北方文艺界的主潮是散文,散文随笔的成功是在其它体式之上的”〔14〕,而且影响所及,当时的小说创作也出现了“散文化”,“随笔化”的倾向〔15〕。这种情况到了1941年才开始发生变化:批评家楚天阔在年底所写的《一年来的北方文艺界》,第一次宣布,在考察本年度的文艺实绩时,“首先注意到的是小说创作”〔16〕(同一位作者在1939年所写的年度总结文章里曾明确指出:“小说今年也有人写。论到牠的成就远不如散文”〔17〕;1940 年的回忆中则说:“这一年北方的小说,真叫人羞愧万分”〔18〕),1942年小说创作更进入了“求普遍发展”的“兴盛”时期〔19〕,到了1943年,批评家发现“散文的成绩,今年最为贫乏”〔20〕:北平以随笔、小品为中心的散文创作就这样完成了一个“由盛到衰”的历史过程,它同时也尽到了(完成了)自己的“开路先锋”的历史责任。
当“重振杂文”的呼唤在北方沦陷区终不免成为一个“善良的愿望”时,从1942年下半年起,以文学刊物的相继问世为标志,上海沦陷区文学开始出现复苏的势头,散文的创作首先勃起。《古今》、《文史》、《风雨谈》、《人间》、《天地》、《文艺》、《苦竹》等一批以发表散文为主的刊物,先后在上海、南京问世,推出了文载道、纪果庵、张爱玲、苏青、胡兰成、陈烟帆、谭正璧、周楞枷等一批散文家,研究者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散文创作为主的作家群体”〔21〕。创办于孤岛时期的《万象》从1943年7月由柯灵主编后,成为上海沦陷区文学的主要阵地之一。柯灵、芦焚、唐弢等《万象》散文作家成为上海沦陷区散文创作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与《万象》有着同样影响的另一个以文艺为主的大型综合性月刊《杂志》(1942年8 月复刊)也以相当的篇幅发表散文作品,并特别提倡“杂文”与“报告文学”的创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时有关于“杂文”、“报告文学”的自觉提倡,如前所述,有些杂志还专门提供发表阵地,但这一时期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散文体式,仍然是回忆童年往事、描摹风土人物、絮谈人生体验、抄录古书、以史遣愁的随笔,另一些作者也仍然执著于“诗化散文小品”的创作实验。这就是说,随笔、小品等个人性散文在北方文坛日趋沉寂时,又在上海沦陷区文坛上复兴,并且由于其中大多数作者有着较深的学养,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所创作的散文更有一种重实感,在生命体验的深沉、文字韵味的淳厚,以至超越的哲思上,都把随笔、小品的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所说的沦陷区散文的“沉潜”特征,直到这时,才得到了较为成熟的体现。
一位批评家当时对“散文随笔的成功是在其它体式之上”这一现象,作了如下解释:
第一,事变后留在北京的较有地位的文人,而又肯答应在新刊
物上发表文章的有周作人氏。‘知堂’一个名字已经成为北方文艺
界的偶象。凡是刊物出版能得到他的文章的,都必要放在第一篇。
他所写的不过是读书的随笔,因此也就提高了这种随笔散文的地位。
第二,散文随笔的范围较广,所写的内容是‘宇宙之大,苍蝇
之微’无所不包。同时以个人生活为主。不敢于牵涉到另外的事情,
写的是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用不着担心意外的麻烦。所以散文的产
量非常多,尤其是限于以个人为中心的作品〔22〕。
所谈的第一个原因显然是一个“传统的承继”问题。纵观这一时期的随笔、小品,古典传统的影响已渗透于作者的体验方式与笔墨趣味之中,周作人所倡导的“文抄公体”的随笔,更是明显地受到了中国传统笔记的启示。而四十年代的散文家们的得天独厚之处,还在于,他们同时又受到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滋养。除了批评家已经指出的周作人之外,也还有何其芳的影响。英国风随笔仍然保持着它的影响力,这一时期也有过专门的介绍。而这一时期散文的“个人性”特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作家们从自己的艺术个性出发,以“我”为主地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艺术营养,达到外在影响与作家个人内在精神的统一:这在周作人、张爱玲这样的成熟作家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从一个重要方面显示了这一时期散文艺术所达到的历史水平。
促进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相对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学期刊、文学市场对推动散文创作发展的作用。沦陷区散文的每一次重要勃起都是与文学期刊的创办、文学市场的开拓联系在一起的,每一时期的散文创作都是以某一文学期刊为中心,在争取老作家的支持,发现、培养新作者,推行某一散文体式,倡导某种创作风格……这些方面,文学期刊实际上起了“组织者”的作用——北平地区的《朔风》、《中国文艺》、《辅仁文苑》,上海地区的《古今》、《风雨谈》、《万象》、《杂志》等,对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组织、推动作用,都是十分明显的。而在文学期刊积极组织散文创作的背后,则有文学市场需求的推动。经过战乱的中国市民(他们是这一时期文学期刊的主要读者)都有一种“趋轻”的心理欲求与阅读期待,但他们又不能完全脱离现实,仍然保留着某种人间关怀,集知识性、趣味性与人生体味于一炉的随笔正是适应这样的阅读心态而风行一时。而诗化散文小品则因为适应集国难、家愁与青春苦闷于一身的青年知识者(他们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渲泄心理与煽情需要,而备受青睐。
但四十年代沦陷区散文的发展更深层的动因,却来自这一时期对“个人生活”和个体生命存在的特殊关怀。这自然有因政治不自由,写“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用不着担心意外的麻烦”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却是战争毁灭了一切,不仅危及到国家、民族的生存,而且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因此,在四十年代,不仅有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有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与思考。在沦陷区,当文学中的民族意识受到了政治的压抑,个体生命意识就被推于文学图景的前景位置,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凸现。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序》里,曾将文学分为“民族的集团的文学”与“个人的文学”,而称小品文为“个人的文学之尖端”〔23〕。说明了四十年代沦陷文学的个体关怀在小品文的文学体式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艺术表现。这种情况,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散文,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并非不重要的区别:同是“个人的文学”,但五四时期散文中的“个人性”是以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为其背景与动因的,主要表现为一种个体意识的觉醒;而40年代沦陷区的散文则是战争背景下对于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怀与探寻,并由此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价值。
2
张爱玲在她的《烬余录》里对于战争中人的生命体验,有过真切的描述。并指出,在沦陷后的“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张爱玲这里所说的“重新发现”,颇耐寻味。战争使人经受着生命的大破坏,大毁灭,大劫难,刹那间失去了一切又在一瞬中重新获得,直逼死亡又陡然获生,“劫后余生”的人仿佛初生的婴儿,过去的“一切”都成为一种遥远的、古老的记忆世界,变得陌生而新鲜。于是,用一种新的眼光、新的感觉(体验),去“重新发现”。
如张爱玲所说,人首先发现的是“吃”(饮食男女)这一人的“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日常生活”这一最稳定的、更持久永恒的人的生存基础。这确实是战乱中人的真实而独特的生命体验。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写身边琐事的散文,借用文载道对明代小品的评价,所记虽“生活中的一枝一节,而琐琐写来,都涉笔成趣”〔24〕。过去人们常常笼统地将之视为生活空虚的表现,恐怕是一种隔膜之论,至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表现了这种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重新发现与肯定的。
这一时期随笔中有大量的回忆过去之作,恐怕也不能简单地以“怀旧”一语概括之。文载道在他的《关于风土人情》中解释说:“人们在‘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之后,所留下来的,却是经过千锤百炼之余的一种生的执著——由此而出发的对于过去的彻骨的眷念,如陆士衡所谓‘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者”。张爱玲则更进一步指出:“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25〕。也就是说,追怀过去,不是“死之迷恋”,而正是“生的执著”,并非为了否定现在,恰恰是为了借助于“古老的记忆”,来“证实”现在的“存在”。
人们还会注意到,这一时期的“回忆”之作里,最大量的是关于乡间生活与童年的回忆,二者又是共生的。乍一看似乎是三十年代散文中常见的城、乡对照主题重现,也确有作品表示了类似的“批判城市,憧憬乡村”的情愫,但同时发出的却是对这憧憬的现实否定:“乡村今日,早已无复此种趣味,有的只是流亡与灾祲,死灭与凌辱,即使是生在乡村,想也不会再有什么顾恋矣”〔26〕。因此,此刻的回顾,具有“人穷则反本”的性质,是处于“围困”中的现实的人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本源及归宿初始性(本真状态)的一种追寻。这种“皈依”的生命欲求在某处意义上正是一种宗教性的情怀,这也正是周作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无生老母的信息》中传出的信息:怀着深深的同情与理解,重新审视明清两代广泛流传于北方民间的宗教红阳教。周作人对据说是红阳教教主的“无生老母”“赴命归根早还源”的呼唤也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他说:“大概人类根本的信仰是母神崇拜”,人“非意识的也常以早离母怀为遗恨,隐约有回去的愿望随时表现”,“不但有些宗教的根源都从此发生,就是文学哲学上的秘密宗教思想,以神或一或美为根,人从这里分出来,却又靳求回去,也可以说即是归乡或云还元”。这战乱中的宗教情结的表现是自然的。
除几乎无处不在的对儿童生活的回忆之外,这一时期还有更直接、真切地对“童心”的关注。人们往往以“儿童状态”与以后的“成长”相对照:胡兰成赞赏于儿童生命形态的“认真”、“完全”与“无限”,却为“大了起来以后”,“做了许多事,有了许多东西,反而感到了人生的有限”而感慨不已〔27〕。柯灵(司徒琴)更注于儿童“成长起来,苦难也跟着成长”,但终有一天,他们跟“自己所属的社会为敌”,“像被放逐的逆子,永不回头”,在作家看来,“这是命运——它们从毁灭中描画着一种时代的风貌”〔28〕。而另一些作家,如钱公侠既为孩子身上的“野蛮”气而费神,却又掩饰不住欣赏之情〔29〕;张叶舟则怀着成年的忏悔意识,从孩子无私的天性的爱中获得了“生命的妙秘”的启示〔30〕。这些似乎都是五四时期“小儿崇拜”的呼应,却又间隔着近二十年历史的风风雨雨,自有更为复杂的意义。
沦陷区的散文家们似乎都热心于抄录古书,这引起了毁誉不一的种种评论。其实这也是对“历史生命”的一种关注和“重新发现”。历经沧桑之变的人是不可能没有历史感的。作家纪果庵说得好,“生于乱世,总好以史遣愁”,这本也是历代知识分子的传统。〔31〕但纪果庵又说到“‘盖棺论定’之不可靠”〔32〕因此,“抄古书”,本质上又是一种“重读”,即从离乱中的生命体验出发,用一种“新的眼光”去重新解读(发现)历史,是“现实生命”与“历史生命”的一次“对话”。于是,就有了《重读〈论语〉》、《读〈浮生六记〉》这类的题目,而且有了如下的表白:要“从一道同风的盲从之中,从巨贾屠伯的手里,使几个古人几部古书,揭去乌烟瘴气的笼罩涂抹,复返于原来血肉的真相,成为太阳底下的平淡事物”〔33〕。因此,被历代权势者和文人捧为“圣经”的《论语》,在四十年代沦陷区作家文载道的笔下,“不过是摄取孔门弟子在茶余饭后,在晓风残月的一些苦乐得失的生活状态罢了”〔34〕。作者自称这是一种更为“平淡一点自然一点的眼光”〔35〕,这与前述对于人的日常生活平凡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重新发现,内在精神与心理动因都是相通的。
同样被“重新发现”的还有“大自然”。在北方文坛颇有影响的青年散文家南星曾写过一篇题为《来客》的散文,把叩头虫、白蛉、钱串子、蜘蛛、蠹鱼等小生物都亲昵地称为夜间来访的客人;无意中打死几只白蛉,白蛉就此绝迹,他后悔不已,“总觉得对那几个死者有些歉意,因为它们是我的最小的客人”。他以极其细致、亲切的笔调描述着与那只态度“文雅而庄重”的“我的蜘蛛”的友谊:“只见它对我像是遇到旧相识,我们各自没有惊慌,并以友谊的眼光互相睇视。有时它走到我的书上来,停一停然后回到墙上。我至今没有发现它的网或住处,但总觉得它不是一个远客”〔36〕。这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对一切生物的博爱与同情,对自然生命的亲切与和谐感,其实正是作家前述对于人的自然生命的亲合感的泛化,显示出一种积极肯定的“生命意识”,将其置于“生命毁灭”的战争背景下,就有一种特别动人的力量。
于是,我们在沦陷区风行一时的随笔里,发现了外在文字与内在生命的“沉潜”:沉潜于身边日常生活的体味,童年、乡村的记忆,历史与自然生命的沉思之中。文载道曾写过一篇随笔,描述“夜读”的境界,说“夜读”是“真正的超越一切的在寻求书中的乐趣”;“澄明而清彻”的灯光,“在夜读中添了意外亲切的低徊”;“夜读的另一种胜处,即在午夜中可以听到各种声响。有天籁的,如风雨,有人工的,如车马。此时如摈除哀乐,起视中庭,即感到大自然的离奇倘恍,真有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之慨,‘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上有许多事情,往往在静观中,在无意中,会得到人生的哲理的启示”〔37〕。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时期的随笔都是“夜读”的产物;而“夜读”的境界更与随笔作者的心境与文章的境界暗合。文载道文章中所说的“澄明而清彻”的状态,“亲切的低徊”的趣味,“超越”中的“乐趣”,以及“万物静观皆自得”中的哲思,其实都可以用来揭示前述生命与文学的“沉潜”的丰富内涵的一个侧面。沦陷区随笔的“沉潜”状态,借用纪果庵对“夜读”境界的描述,这是“于苍凉中得潇洒之味”〔38〕;周作人在《〈文载道文抄〉序》则将其概括为“惆怅”中“别是一样淡淡的喜悦”,“寂寞的不寂寞之感”,并称之为“忧患时的闲适”〔39〕,都是提醒我们注意沦陷区随笔内在蕴味的多层次性和驳杂性。
3
沦陷区散文还有另一种生命形态的显示,展现出另一番风貌。
北方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散文家林榕在他的一篇散文里曾引用高尔基的话,区别两种“沉默”(“无语的寂寞”),据说“只有对于一切都已经说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人,沉默才是可怕的,痛苦的;对于还没有开始自己的说话的人呢——对于他们,沉默是简单的,轻松的”〔40〕。这话说得很有意思,用来描述沦陷区散文创作中的两种话语也很确切:如果说,我们在上文作了详尽分析的“随笔”体的散文,都是饱经沧桑,看够了一切,说尽了一切,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中老年的话语;那么,我们将要讨论的,则是初涉人世,“还没有开始自己的说话”的年轻人(以及虽也有一定阅历,却仍然保持青年心态的少数中年以至老年人)的话语。
当然,这不仅是年龄的区别而已。在前文中一再提及的,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随笔作者之一的纪果庵,曾有过这样的自我体认:“我乃农家子,不是航海者”〔41〕。这里说的是所担任的“社会(人生)角色”:所谓“农家子”其实是表示对于生命之源(根基)的固守与坚持。而“航海者”则是永远在茫茫大海中漫游的生命的“飘泊者”。“飘泊”与“固守”表现着人的“追寻”与“皈依”的两种生命欲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人生旅途中的两个阶段:生命的起始与生命的安顿。因此,当前述沦陷区的随笔作者,以固守、皈依者的姿态,叙说着他们的“家园”情绪,沉醉于身边日常生活中的凡俗世界时,另一些年青的作者,却以飘泊者的身姿,遥望“远方”,沉迷于“梦”的世界。
“远方的梦”,这正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作者苦闷的心理情绪,并构成了他们散文中的基本意象。前述随笔家们将遥远的记忆“身边”化的叙述策略相反,这些年青的散文家使用的是“远景叙述”。林榕在他的《远人集》(这一时期所有的年青人的散文都可以以此命名)中的一篇散文里曾有过如下的解释与说明:“每逢听到刺耳的,喧嚣的,都市的吵嚷,我就想逃避开。明知摆脱自己的环境,去一个孤岛上过日子是不可能的事情,只好从各方面减轻就是了。减轻的唯一方法是从接近移向遥远”,据说“传自远处的音乐,比在耳畔的幽美。”〔42〕。这里所传递出的信息,是颇为重要的。它告诉我们,这些年青的作者都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也即现实社会的异已者,二者之间存在着不能相容的对立的紧张——而前述固守者们尽管也有不满与不和谐,但它们又确实在现实环境中发现了某种和谐,至少是找到了或一立足之地;因此,对于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自己位置的年青人,“远方的梦”即是一种逃避,一个在想象与虚构中与现实拉开了距离的精神避难所。应该说,这类远方的梦境是每个时代的每个年青人都曾幻想过与追求过的;而命运似乎对这批四十年代处于异国统治下的青年要格外严酷,使得他们甚至不能享受哪怕是刹那的幻觉快感,他们几乎是在虚构“远方梦境”的同时,就对其产生了怀疑。在一篇《〈秋愁〉序》里,作者如此描述这个时代的年青人所感到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他们“敏锐地感到他自己所住的世界,是一个他不希望住的世界,他才要飞向那遥远的地方”,但“横在面前的(只)是模糊的远山,却没有走入远山的路”,终于在梦中见到了“那青青远山”,“但进入远山,才发现山色并不青,也没有鲜艳的春花”,“他所不了解的生物,仍都在山里生活,他和他们依旧互不相知,灵魂与灵魂,隔离得非常辽远”,原来“远山也不是可以躲避秋愁的地方”。“他最后乃梦见所有的生物皆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有弹性的薄薄的网”——连那“远山”也笼罩在内。涂抹了如此浓重的怀疑的色彩,这一代青年的“远方的梦”就显得特别不稳定,仿佛仅仅是生命旅程中短暂的“一站”,有不少人很快就超越了它,投入更广阔的社会人生,一如他们的先行者何其芳那样,从《画梦录》走向《还乡杂记》,在“群体”的“伟大灵魂”里安置下个人渺小的灵魂,从而开始另一个精神历程。而另一些人却依旧离不开这“远方的梦”——但这已是明知其虚谎而故意安排的梦境,一位作者自称是“失意的在梦里打着圈子”〔43〕,这多少带有自欺色彩的绝望挣扎的苦况,距离所谓“青春情怀”已相当遥远——这精神上的“未老先衰”是格外给人以沉重之感的。
这样,在沦陷区寂寞的文苑上,终于收获了具有不同生命内容,显示着不同生命体验的散文。——而两者的区别又不止于此,它们同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散文体式,而生命内容与文体形式间又显然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纪果庵曾“基于作文积习,把人性析为散文的与传奇的二类”。据他的解释,“传奇亦即小说,盖即使写实,也有若干传奇的手法与意象在内,故以此名名之”。在纪果庵看来,“传奇是诗的,想象的,奔放的;而且是结构的,组织的,有整个的轮廓的结晶体”,而散文,则是“随便的,坦荡的,无所容心的,没有组织的”〔44〕。周作人也曾与废名讨论过所谓“戏剧化的小说”与“随笔化的小说”的区别。周作人说:“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化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其有结构有波澜的,仿佛是依照着美国版的小说作法而做出来的东西,反有点不耐烦看,似乎是安排下好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看了欢喜得出神”〔45〕。不用说,这些关于文体的议论,尽管多为随意而谈,但却是自出心裁,发人深思的。这里所提及的“诗”(小说、戏剧)与“散文”的区别,以及这种文体区别与人性(人的生命形态)的联系,都很有意思。就我们所讨论的课题而言,能不能说,前述着眼于凡俗生活的随笔,是“散文”的,即所谓“散文家的散文”,而精心构制“远方的梦”的小品,更是“诗”的,是“诗人的散文”呢?以“散文家的散文(随笔)”来说,借用胡兰成的说法,它是更接近“词”的,它将“人的感情”润泽日常生活”〔46〕,从而显示出一种独特的价值。那么,这类“散文家的散文”是不是也有高下之分呢?有的。这就是看是否能以“人的感情”去“润泽日常生活”,或者说,在“日常生活”的描述中,内在的生命质量如何,是否充溢着生命的元气,包蕴着对生命存在的开掘与思考。否则,日常生活的描述就会变成琐事的无谓咀嚼和孤芳自赏,显示出生命的苍白、平庸以至无聊。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陷阱。“诗人的散文”也自有“规范”:如纪果庵所说,它是想象的,有意组织、结构的。对这一时期的诗人散文家最有影响的何其芳早就说过,他是“惊讶,玩味,而且沉迷于文字的彩色图案,典故的组织,含意的幽深与丰富”〔47〕的。批评家们在介绍何其芳散文的“特质”时,首先强调的是“不注重内容,只注重表现”,这至少是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何其芳散文观”〔48〕。人们在谈论何其芳对这一时期的“诗人的散文”的影响时,同样强调的是“遣词运句的惨淡经营”,“优美的形式”,“深邃缥渺,幽远,恢诡,迷离境界”的营造这些方面〔49〕,这恐怕都不是偶然的。曾有人批评何其芳《画梦录》及其影响下的散文过于雕琢、精致、艳冶,提倡“自然,简单”,“安祥、坦白”的散文〔50〕。这其实也是用“散文家的散文”去要求“诗人的散文”的隔膜之论。林榕在《简朴与绮丽》一文里对此提出了异议,他指出,“由简朴到绮丽”,这“正是散文向上的发展”;他认为,“《画梦录》的产生也正是散文可走的道路,不能以其表面的美丽的彩色而轻视它”〔51〕。因此,对于“诗人的散文”,危险(陷阱)不在内在生命的贫困,更在于想象力的缺乏,语言文字能力的不足,形式追求的不力,所谓“每篇必须有‘梦’,一个绮丽的‘梦’,又画在一把‘团扇上’”的泛滥成灾,首先反映的是艺术创造力的匮乏,或者如一位批评者所说,“在素养上患着贫瘠症”〔52〕。何其芳的模仿者到最后难以为继,也陷入了“散文的堕落”,“有其志而无其才”,或者缺乏形式上的精雕细琢所必须的余裕心境,这都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这样,无论是“散文家的散文”,还是“诗人的散文”,由于自身存在的“陷阱”,最后都出现了“危机”,其主要表现正是生命力与艺术力的不足。沦陷区的散文终不免“由盛而衰”,并在总体成就上受到限制,这恐怕是更为内在的原因。
注释:
〔1〕〔21〕黄万华:《沦陷区文学鸟瞰》,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1期。
〔2〕黄万华、申殿和:《多个方向上探索的散文艺术》, 收《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6〕上官蓉:《北方文坛的今昔》,载《文化年刊》1994年第2卷。
〔4〕〔5〕陆离:《朔风室札记》,《朔风》第1卷第2期。
〔7〕〔8〕参看封世辉:《华北沦陷区文艺期刊钩沉》,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1期。
〔9〕〔10〕〔14〕〔18〕〔22〕楚天阔:《一九四○年的北方文艺界》,载《中国公论》第4卷第4期。
〔11〕林慧文:《现代散文的道路》,载《中国文艺》,1940 年3卷4期。
〔12〕吴楼:《我们的毒舌》,载《吾友》第1卷第43期。
〔13〕〔16〕楚天阔:《一年来的北方文艺界》,载《中国公论》第6卷第4期。
〔15〕上官蓉:《目前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文艺》6 卷6期。
〔17〕楚天阔:《一九三九年北方文艺界论略》,载《中国公论》第2卷第4期。
〔19〕楚天阔:《一年来的北方文艺界》,载《中国公论》第8 卷第4期。
〔20〕楚天阔:《三十二年的北方文艺界》, 载《中国公论》第10卷第4期。
〔23〕周作人:《苦雨斋序跋文·〈近代散文抄〉序》。
〔24〕文载道:《关于风土人情》。
〔25〕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26〕纪果庵:《小城之恋》。
〔27〕胡兰成:《新秋试笔·三》。
〔28〕柯灵:《遗事》。
〔29〕钱公侠:《“野蛮”》。
〔30〕张叶舟:《宇宙之爱》。
〔31〕〔32〕纪果庵:《亡国之君》。
〔33〕〔34〕〔35〕文载道:《重读〈论语〉》。
〔36〕南星:《来客》。
〔37〕〔38〕纪果庵:《夜读》。
〔39〕周作人:《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
〔40〕林榕:《寄居草·井》
〔41〕纪果庵:《知己篇》。
〔42〕林榕:《寄居草·音》。
〔43〕狂梦:《童年彩色版·甜蜜的家》。
〔45〕周作人:《明治文学之追忆》,收《立春以前》。
〔46〕胡兰成:《读了〈红楼梦〉》。
〔47〕何其芳:《梦中道路》。
〔48〕上官蓉:《散文闲谈——一年来的华北散文》,载《中国文艺》7卷5期。
〔49〕丁谛:《重振散文》,载《新文艺》(上海)日刊1卷1期。
〔50〕参看欧阳方明:《何其芳的散文之路》(《艺文》1卷3期),欧阳竟《谈何其芳的散文》(《燕京文世》1卷1期)。
〔51〕林榕:《简朴与绮丽——现代散文谈之二》,载《风雨谈*5期。
〔52〕曹原:《远人集》,原载《风雨谈》第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