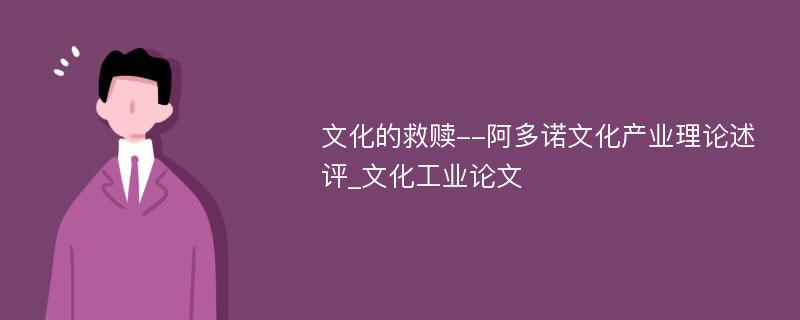
文化的救赎——评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多尔论文,理论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0)09-0005-07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中间,阿多尔诺的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他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上面。爵士乐、侦探小说、心理电影、电视节目、电台广播、生活杂志、商业广告等文化现象,都成为了他集中分析批判的对象。由于他受过古典音乐教育的特殊背景,使得他对以爵士乐为代表的音乐拜物教展开了深刻的剖析(这也构成了他开创的音乐社会学的主干部分),也使得他的“文化工业理论”似乎具有一种音乐社会学的色彩。尽管他坚守“精英文化”的思想立场总是遭人诟病,但他所阐发的“文化工业理论”确实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现代极权主义的无情批判。他将其“否定的辩证法”贯穿到底,力求用一种“崩溃的逻辑”去反思和暴露“文化工业”的心理操纵模式。也可以说,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是对现代社会病症的诊断。他从文化问题切入,直接秉承了马克斯·韦伯以来的德国“文化危机思潮”的理论传统,即把现代社会的种种矛盾问题归因于“文化危机”。成也文化败也文化,现代工业社会的乱象可以说与现代文化有着莫大的关系。西方工业社会为何会变得如此的整齐划一?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为何会完全丧失了革命性?在阿多尔诺看来,这些都是因为“文化工业”有效地培养了大众的“顺从性”或“一致性”,导致了人们往往逃避现实而且无所思索。欲探讨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就必须揭示“文化工业”所固有的欺骗性和操纵性,让艺术本来具有的拯救作用发挥出来,让否定的思想照亮现实的矛盾。当然在今天看来,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有些完全忽视消费者的主动性和选择性,甚至将消费者看作是像儿童一样的幼稚可欺。鉴于今天流行文化的巨大变化和崭新格局,我们确实需要对他的“文化工业理论”做出应有的分析和评价。
一、极权主义与“文化工业”
阿多尔诺为何会有文化救赎的想法?或者说,他为何将理论批判的焦点指向了“文化工业”?从现实的经验层面来看,他找到了现代极权主义与文化操纵之间的联系;从法兰克福学派坚持的总体性逻辑来看,他始终相信文化在社会历史演变中具有一种综合性的或者说整合性的功能;再从他骨子里的精英主义取向来看,他无法接受作为一种娱乐工业体系的“大众文化”。总之,按照他的思想逻辑,在商品拜物教的主宰之下,在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原则的支配之下,“大众文化”完全变成了没有思想、没有超越的消费娱乐产品,与此同时也就变成了“新的控制形式”。“大众文化”满足于平庸和消遣,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现状。从理论上分析批判“大众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不仅可以解释革命为什么一直没有在发达工业国家出现,可以解释工人阶级为什么被“收编”而一直保持沉默,同时还可以找到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社会变革的某种可能性。
阿多尔诺贬斥作为流行文化集大成的“文化工业”,主要是因为“文化工业”磨平了文化本来具有的批判锋芒,促成工人阶级和社会大众的非政治化,有效地维护了现代极权主义的社会统治。他的这番认知直接源于他的现实生活体验,首先是德国纳粹政权的意识形态传播模式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其次是他在美国看到了十分成熟的以电影工业为代表的流行文化体系。他发现,纳粹德国与民主美国在凭借电影、电视、广播、杂志等文化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操纵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德国纳粹的宣传机器和美国的流行文化有着相同的地方,这就是建立了一种以“文化工业体系”为基础和导向的“新型控制形式”。这种控制形式在德国是赤裸裸的政治宣传,在美国则是非常商业化的娱乐消遣。后者的控制形式表面上看很民主很自由很包容,但其实质还是强制性的和欺骗性的。依赖于现代技术手段,“文化工业”的控制形式具有遍布一切领域的特征,其总体的效果是反启蒙的。也就是说,“文化工业”成为了一种束缚自由意识的普遍手段,有效阻止了独立个体的判断和冲动①。在阿多尔诺看来,“文化工业体系之所以出自自由主义的工业化国家,显然是因为这些国家成功地制造出了特有的文化媒介,特别是电影、广播、爵士乐和杂志。当然,它们的发展源于资本的普遍规律”②。也可以这样说,尤其是以广播电影电视为核心的文化工业造就了现代极权主义的统治。他的这一判断令人遗憾地抹去了纳粹政治文化和美国大众文化之间的根本区别,毕竟这两种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因为他将德国的纳粹暴政与美国的商业操纵视为现代极权主义的两个样本,反犹太主义的大屠杀和纽约城里的广告霓虹灯似乎都在诉说着因为启蒙而招致的灾难。
本该是文明昌盛的20世纪为何会发生如此野蛮的行径?德国纳粹及其法西斯主义得以兴起的原因何在?现代社会的管理化趋势为何会不断地增强?人类未来的命运究竟是福还是祸?如果说这些都是启蒙理性走向失败的证据,那么以人类解放为旨趣的启蒙理性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结局呢?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特别急于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发现仅仅采用经济政治维度的解释是不够的,于是另辟蹊径从心理意识和文化观念上面寻找原因,就成为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其“批判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显然是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概念进行了综合。他们采用集合起来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方法分析了“独裁人格”、“启蒙精神”、“工具理性”、“实证主义”等思想意识,尤其对作为一种大众欺骗形式的“文化工业”做出了批判性的论述。“文化工业”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阿多尔诺与霍克海默尔于1947年合作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该书主要探讨了启蒙理性为何走向极权主义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启蒙理想始终追求建立起一个包罗万象的原则体系,而这个体系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一样,所以从根本上讲“启蒙就是极权主义的”③。这种极权主义的控制形式,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的社会运行之中,而且还渗透在文化的生产和消费领域。该书有一章题为“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明确将新兴的“文化工业”视为权威的驯服手段,因为“文化工业”不仅辅助纳粹政权将政治审美化从而达到有效鼓动德国大众的目标(其中体现为宣传性的大众文化),而且也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起到了“社会水泥”的作用(其中体现为商业性的大众文化)。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纳粹就充分运用大众传媒将其暴政统治用文化强国战略包装起来,促使大众将无条件地服从看作是一种义务。纳粹推行的文化政治,其“煽动的艺术”和仪式化的力量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大众在变得没有思想的同时,也愈发变成了野蛮的动物。阿多尔诺在这本书中对于“文化工业”的讨伐是满怀愤怒的,因而也是失之偏颇的。个中原因主要还在于他自始至终对于“文化工业”,及其社会效应所持的否定判断。如果套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在阿多尔诺的心目中,将人的灵魂完全物化的“文化工业”显然就是“人民的鸦片”。
对于阿多尔诺来说,“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是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发展演变而来的,或者说就是现代“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形态。他之所以改称“文化工业”而不是“大众文化”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是为了避免概念上的误解,因为“大众文化”这个概念本身还有从民众自发产生和为民众服务的意思;其次是为了强调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文化形态及其功能的深刻变化,即一种生产流水线式的娱乐工业体系的建立。事实上,“大众文化”这个概念一直都很模糊,因为其中的“大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本身就很模糊。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大众文化”是指大量生产和大量传播的文化。与“小众文化”相比较,它的受众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显然,它是现代工业文明及其生产方式的产物。按照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的分析,“大众”(Masses)的含义从开始的“多数人”和“集合体”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些意思:即众多的人数、大量的生产、流行的模式、低等的品位、平庸的思想和广泛的传播等④。阿多尔诺其实也看到早在“文化工业”形成规模以前,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许多娱乐性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包含的所有要素都存在了,这就是以娱乐消遣和商业交易为目标的文化生产活动。例如英国作家笛福(Defoe)的小说就是有意识地为中产阶级的阅读市场进行创作的。只是今天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提高,对于大众的影响明显地增强。“大众文化”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还表现在性质上。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洛文塔尔(L Lowenthal)曾经对此现象做过研究:他认为“大众文化”的概念及其争论可以追溯到16和17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两位思想家作家帕斯卡(Pascal)和蒙田(Montaigne)已经就市场经济与文化消费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都看到在教会和封建统治力量逐渐崩塌以后,人们的精神寄托和社会安全感有待充实,大众需要文化的娱乐和消遣。然而,帕斯卡坚决反对用肤浅粗俗的“大众文化”来填补心灵的空白;蒙田则要为娱乐化的艺术生产进行辩护⑤。在有些人看来,“大众文化”代表着民主与进步;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大众文化”代表着低俗平庸的东西。这种评价格局自20世纪以来愈发地分明和对立,于是就出现了关于“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和“低级文化”(low culture)的划界和争论。显然,阿多尔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大体上站在了追捧前者、贬斥后者的立场上面。这也正是其“批判理论”一贯坚持的价值立场。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步伐愈发地加快,其娱乐化的印记也愈发地鲜明。占据时代文化潮头的总是那些大量生产复制出来的“大众文化”,它们不断地挤压着“精英文化”的生存空间。其中,以“美国化”(Americanisation)为代表的消费娱乐文化,如好莱坞的电影、百老汇的歌舞、流行的音乐、侦探小说、电视肥皂剧、广播节目、商业广告等,更是突出了文化的流水线生产及其商品属性。最让阿多尔诺不能接受的就是这种“美国化”的文化了,他“发明”和使用了一大堆贬义词来概括这种强势的“大众文化”:比如说“商业化”、“标准化”、“固定化”、“强制化”、“保守化”、“虚假化”、“顺从化”等。他发现,这种“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产品数量(如电影电视小说)已经增长到这样的惊人程度,即没有一个人可以躲开它们而不受影响,就是那些远离城市住在乡村的农民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也无法逃脱⑥。电影院里放映的几乎都是好莱坞的类型化电影,电视节目里充斥着时尚化的肥皂剧,书店里摆放着畅销的言情小说和侦探小说,广播节目里的歌曲大多是流行的爵士乐摇滚乐。你不看都不行,因为你不看就意味着你跟不上潮流,你就会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人。现代极权主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们的统治形式不再是赤裸裸的暴力控制和血腥镇压,而是变成了温文尔雅的心理疏导和意识形态操纵。当娱乐逐渐变成了人生的一种理想,大众的政治想象力也就随之消退。
我们应该看到,当阿多尔诺在贬斥“文化工业”的时候,他的思想中间似乎有一些反对文化民主化的倾向,因为“文化工业”总是与大众化和通俗化相关联的,而且文化民主和文化平等的结果往往与维护现存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不过,他反对文化“大众性”的理由在于这种“大众文化”并不是由大众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制片人、出版商、公司以及拥有话语权的集团所决定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建者霍克海默尔对此有过论述:“大众性不再与艺术生产的具体内容和真理性有任何联系。在民主国家里,最终的决定不再由受过教育的人负责定夺,而是由娱乐工业负责定夺……在专制主义国家里,最终的决定则由直接或间接从事宣传工作的管理者定夺,然而宣传本质上是与真理无关的……有朝一日,我们总会发现,即便是在法西斯国家里,大众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也暗暗地确信真理,不相信谎言,这就如同精神病人只有病愈后才使人们知道,什么也没逃过他们的眼睛。”⑦他们的批判逻辑十分清晰,“大众文化”纳入“文化工业”的娱乐体系之后就不再是“大众”的文化,而是成为了现代极权主义隐蔽的控制手段。由于享受着“大众文化”的“大众”还蒙在鼓里,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揭示真相,“文化工业不断地给消费者一些许诺而不断地在欺骗消费者……文化工业不是升华而是压抑”⑧。现代人不是卑贱而是被巨大的机器奴役了,尤其是被无孔不入的“文化工业”操纵了。因此他们关于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往往是总体的和综合的)大多围绕着“文化工业”的种种操纵模式而展开。
二、“文化工业”的操纵模式
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对“文化工业”的特征及其操纵性有一个十分尖刻的判断。他提出,作为现代娱乐生产消费体系的“文化工业”无非是为大众提供一些无脑子的消遣快乐,而“快乐始终意味着无所思索,忘却痛苦,即使是正处在痛苦之中。从根本上讲,它是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快乐确实是一种逃避,但并非如人们所说的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而是对最后一点反抗现实的思想的逃避。快乐许诺给人们的自由,就是逃避否定的思想”⑨。在阿多尔诺及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追求思想性超越性是文化的一种天职。如果文化里面没有思想没有超越,文化就不成其为文化,这就是“文化工业”的症结所在。为什么说“文化工业”的总体效果是反启蒙的,因为它不是在启蒙而是在蒙骗。它生产出许许多多无脑子的消遣文化,比如类似于婴儿食品的文摘式读物,为了适应商业社会快速成功需求的快速阅读和傻瓜手册(人们奉行的是快鱼吃慢鱼的生存法则),还有许许多多专门针对成人和女性群体的图文出版物。最让阿多尔诺这位古典音乐的坚定信奉者不能容忍的是,在消费生活观念的引导下,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被改编成为聊天吃饭睡觉的背景声音,即使是在音乐会的欣赏过程中听众也不能集中听力而是心不在焉,甚至可以说“消费者实际上崇拜的是他为购买托斯卡尼尼音乐会票所付出的金钱”⑩。那些音乐发烧友关心的不是听到了什么或者怎样去听,而是能否用最好的音响设备听到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的声音。他们真正喜欢的是高保真的音响,而不是什么古典音乐(11)。音响发烧友和无线电爱好者是受拜物教主义左右的最为典型的人群。事实上,“文化工业”所进行的有组织的娱乐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有组织的施暴过程。它采用一些心理控制手段来制造出自动式的反应,并由此而削弱消费者个人的抵抗力量。从表面上看,“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很有个性,消费者也自以为享受这样的产品会让自己显得很有个性,其实这种个性不过是一些伪个性而已。“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力量恰恰体现在它用十分隐蔽的手段来达到意识的一致性和认同性,从而实现其全面的控制。在今天,任何人如果不能用时尚的方式来说话、打扮和生活,其生存就会遇到威胁。他要么被当作是傻瓜,要么被看作是偏激的知识分子。总之,他必须接受和赞同流行的“大众文化”,不然他就得不到现代生活的护照。在这种“大众文化”的生产体系中,是没有人可以与它分离开来的。
尽管阿多尔诺声称要将“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区别开来,但他在贬斥“文化工业”的时候还是经常将“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或者“流行文化”混淆起来。那么他所讲的“文化工业”究竟指什么呢?为什么说“文化工业”就不是“真正的”和“优良的”文化而只是“虚假的”和“劣质的”文化呢?根据阿多尔诺的有关论述,他关于划分“文化工业”的标准大体有两层意思:首先,“文化工业”要突出其商业化的倾向,主要指商品生产及其交换价值已经成为了文化生产的基本形式和普遍法则,这种商品化和功利化的文化与原来的超脱性文化的创作理想相去甚远;其次,“文化工业”要突出其工业化的特征,明确代表了一些特殊的生产部门,比如电影制片厂、录音工厂、唱片公司、印刷工厂、广播电台、电视娱乐台、戏剧音乐演出机构等。就其生产的动机和模式而言,“文化工业”以追求商业利润和同质化产品为目标,因而消除了文化固有的批判功能。事实上,在阿多尔诺的理论分析批判之中,“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通俗文化”、“娱乐文化”、“同质文化”等概念是可以通用的。因为它们都将艺术彻底地纳入到商业活动之中,将艺术和消遣调和起来以便为娱乐的大规模生产服务。其实,这种娱乐不过是劳动的延伸,“人们追求它只是为了从机械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能够恢复精力而再次投入到劳动之中”(12)。应该说是取乐代替了娱乐,而取乐使得所有需要思考的逻辑联系都被切断了。“文化工业”向消费者承诺的是可以由此逃出日常生活的苦役,其实就是通过取乐来帮助人们忘却屈从的现实,并且变得更加服服帖帖了。这些结果都是借助其基本的操纵模式,即“标准化”、“被动化”和“顺从化”的意识控制来实现的。由于他对古典音乐的执著和热爱,由于他对音乐固有的情感刺激作用的关注,他将“文化工业”的分析批判集中在了流行音乐,尤其是在爵士乐上面(他留下来的23卷全集,其中有12卷的内容属于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拒绝从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到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音乐作品,主要不是因为这些作品多么地通俗流行,或者多么地刺激情感,而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操纵性,往往会导致听众听力的退化和理解力的削弱。在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中间,有关流行音乐和爵士乐的分析批判确实是他最为出彩的地方,但与此同时也是他最遭批评者诟病的地方,这是因为他对爵士乐的评价过于片面而带有十分明显的个人好恶。
爵士乐(Jazz Music)是20世纪以来最为流行和最具影响力的一种音乐形式,并且形成了一个“爵士乐的时代”。爵士乐是一种典型的都市流行文化,它往往反映和表达了都市人群的声音和感受。它的新颖之处不仅在于乐器上面的创新和由此产生的独特声效,而且还在于它的即兴演奏方式。与传统的古典音乐相比,“爵士乐总能给人们带来不假思索、信手拈来般的乐趣,完全无视思维的控制……”(13)。喜欢者认为,爵士乐对西方世界的主要贡献就是对于欲望的肯定,因为它是一面象征着纵欲狂欢的旗帜。爵士乐“就是魔力,是相聚,是交融,是占有和满足——是爽快的情欲”(14)。然而像阿多尔诺这样的不喜欢者则是带着轻蔑的态度来评价爵士乐的,在他看来我们从爵士乐中听到的是一种明显的“无助感”,这种“无助感”源于普通人对社会权力的恐惧以及对于权力的服从和适应。在爵士乐的演奏和欣赏中往往表达出这样的意思:我什么都不是,无论强权对我做些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按照精神分析学观点,爵士乐可以说是一种“阉割式的”或者“手淫式的”音乐,因为在这种音乐中间有一种受虐狂式地对于社会力量的顺从。在“论爵士乐”(On Jazz)和“论音乐中的拜物教特征和听力的退化”(On the Fetish Character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of Listening)等文章里面,阿多尔诺围绕爵士乐和电子音乐等现代流行音乐探讨了“文化工业”的一些基本特征。依照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他直接将爵士乐等流行音乐视为“文化工业”的时代标本。爵士乐就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商品,它完全遵从商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等规则。对于爵士乐的听众而言,听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与看比基尼的表演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听众也是按照足球和汽车的概念即消费品的概念来欣赏音乐的。爵士乐作为流行音乐的一种普遍效果,或者准确地说是它的社会角色,可以定义为一种同一化的模式。从表面上看爵士乐是无规则性的和随意性的,其实背后受到一致性的支配。这种同一化和标准化的模式直接导致听众只能是被动地听。在爵士乐的创作和欣赏中间,其音乐的意识和理解几乎都丧失了,因此“与音乐拜物教相对应的便是听力的一种退化”(15)。这种听力的退化具体表现为消费者要么是漫不经心地要么是情绪失控地享受音乐,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地服帖和屈从了。这样,以爵士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还起到了“社会水泥”的作用。
在现代的商业社会中,人们只要有一点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工业”所提供的娱乐产品。这些产品在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将消费者模式化了。阿多尔诺还找到电影作为这种操纵模式的样本,因为是电影制造商的意识在制造和培育消费者的意识,是电影在强迫它的受害者直接把它当作现实本身。消费者总是那些工人、农民、雇员和地位偏下的中产阶级,他们需要的是米老鼠和唐老鸭而不是什么悲剧性的正剧,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成功神话的迷惑而始终固守着奴役他们的那些意识形态(16)。好莱坞的那些电影制片商往往将电影故事设定在11岁的孩子都能够理解的水平上面,于是他们也将作为消费者的成年人降低到了11岁孩子的水平。在各种电影类型的生产之中,我们更能看到普遍存在的娱乐化、低幼化和平庸化的现象,这些都对消费者产生了难以逆转的影响。电影的娱乐性很强,因此它的许诺很多欺骗也很多。它许诺的自由,其实只是丧失了思想和否定的自由,因为它所提供的各种幻象都是以匿名的市场为基础的。总之,“文化工业”通过重复性、同一性和强制性等操纵模式制造出自动式的反应,因而逐渐削弱了个体抵抗的力量。
阿多尔诺对于“文化工业”操纵模式的分析,显然是很偏激的,因为他没有看到消费者身上的自主性和选择性,事实上消费者并不完全像小孩子一样被流行文化所操纵。他只是一味地假定法西斯主义的大众文化与美国的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一致性,那就是对于人们思想的窒息,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些都体现在他对于电影工业和流行音乐的分析上面。面对“文化工业”对于人们思想的窒息,他寄希望于那些具有一定批判潜力的先锋派音乐和艺术电影。在他的心目中,文化的救赎只能依赖于那些反叛的艺术。因为反叛的艺术重在思想而不是娱乐,重在否定而不是肯定,重在抵抗而不是接受;因为反叛的艺术具有超越的精神,可以将自由的光芒照射到人类和事物身上。
三、艺术的拯救力量
如何才能突破“文化工业”对于现实的操纵?如何才能揭示虚假的意识形态?在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中间,这些问题与文化的救赎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商业化的艺术只能用非商业化的艺术来对抗,对于顺从的艺术只能用否定的艺术来改变,对于麻木的大众意识只能用清醒的精英意识来唤起。真正的艺术往往具有一种拯救社会的功能,因为艺术饱含了乌托邦的希望。面对现实的矛盾和苦难,艺术必定是乌托邦的。阿多尔诺在其《美学理论》一书中,再三强调艺术借助其自主性和幻想性能够超越异化现实,能够对我们的感觉和意识起到破坏性的作用。因为否定性的活动,艺术本身就完全是实践的。反叛的艺术本身就是一篇篇的现实控诉状,其实践性正是体现在它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上面。“艺术的影响正是在于它有精神的参与,这种精神被凝结在艺术作品之中,并且通过一种地下的和隐蔽的形式给社会带来变化”(17)。艺术自身的“拯救绝望”的作用当然是中介性的,即它总是给人指出一种希望所在。艺术的反叛性和革命性,并不在于它喊出了多少革命的口号,也不在于它是专为无产阶级而写,而是在于它是不是表现了普遍的奴役状态,是不是突破和揭示了被蒙蔽起来的社会现实。大众为何不好理解那些抵抗的音乐和戏剧,当然不是因为大众有什么智力上的缺陷,而是因为大众已经成为了虚假意识的牺牲品。大众已经不习惯于这些暴露式和抵抗式的艺术作品,愿意接受的还是那些轻松愉快的消遣作品。阿多尔诺的思考就是指向我们怎样才能突破“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种种意识屏障,怎样才能让大众从接受现实走向超越现实。他之所以推崇以勋伯格(Schoenberg)为代表的现代新音乐(十二音体系)和以贝克特(Beckett)为代表的荒诞派戏剧,正是因为他们的音乐和戏剧都具有超越异化现实和指向反思的特征,在其爆炸性和破坏性的绝望中带有真正自由的气息。他们的否定艺术与现代社会处于一种对立关系之中,因而体现了其批判的和抵抗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特征有时就像谜一样地让人听不懂看不懂,原因在于它们往往是超前的和异在的,其乌托邦的指向如同密码一般存在于艺术的形式之中。
坚持音乐与社会的关联性,信奉音乐的拯救力量,是阿多尔诺一贯的思想立场。“阿多尔诺强调如果与文献记录相比较,‘艺术的形式’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人类的历史。”(18)他特别集中地探讨了现代主义音乐的拯救作用,并且将勋伯格的“新音乐”视为现实矛盾和社会异化的展示,因为正是不协和音的冲突照亮了黑暗的世界。这种“新音乐”的声音自然没有给听众提供安慰和消遣,而是让听众感到震惊和不适。在音乐中,我们似乎听到的是城市人互不相识而产生的孤独感和恐惧感。勋伯格用不协和音表达出来的恐惧感,不是因为他丧失了理解力,而是因为他非常真实地把握了这些恐惧。音乐的力量不是简单地去描述现代社会生活的异化状况,而是要去铭刻社会给人带来的孤独和痛苦。在哭泣的现代主义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乌托邦的力量,它既是一种抵抗同时也是一种渴望。“指向他物”似乎就是音乐的本来之意,即音乐自身内含了一种超脱的乌托邦力量。当然,除了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之外,阿多尔诺还将卡夫卡的超现实主义小说、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和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等列入到他的先锋艺术名单之中。在“文化工业”充斥现代社会生活的情形下,以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为特征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不失为一种唤醒的意识。这种意识能够起到拯救绝望的作用,因为它能够给主体带来战栗,从而使主体跳出物化的陷阱。
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理论”贯穿了一种美学胜过政治的思想逻辑,并且将文化的救赎作为人类走向自由的坦途。尽管同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一样,他也没有直接打出“文化主义”的旗号,但是其“否定的辩证法”显然是文化主义的。他的文化逻辑在于突出社会革命的主观条件,即主体意识的能动作用。他坚决反对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始终强调唯物主义不等于是唯心主义的反义词,也不等于是对非物质性存在的简单否定。他的“文化主义”突出了社会的总体性,将文化看作是实现社会总体的中介力量。在他这里文化决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派生物,决不仅仅是阶级利益的反映,也不只是精神的幻想活动。文化既表现了社会的矛盾,同时又潜藏着否定的力量。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之所以要批判和贬斥那些以消遣娱乐为取向的流行艺术,正是因为流行艺术往往没有思想没有超越,而现代主义艺术不仅有思想有否定,而且还包含有乌托邦的因素,其艺术的指向是社会的变革和自由的未来。按照他的思想逻辑,“文化工业理论”是一种理论的批判,“这种理论上的义无反顾本身已经包含着一种实践的因素,我甚至还敢于如此极端地说,实践在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悄无声息地进入理论之中,也就是说,实践本身已经属于对正确行为的可能性重新进行周密思考的范围”(19)。于是,文化的救赎也就顺理成章。人的问题总是与思想或者精神联系起来的。当人的思想有所否定、人的精神有所超越的时候,人的现实及其社会实践就会发生变化,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文化的中介作用。
今天的“文化工业”(更流行的说法是“文化产业”)相比阿多尔诺的时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化问题的讨论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性,这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的“文化转向”中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明。在商业化逻辑已经实现全球化的情形之下,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尽管显得有些过时和片面,尤其是他对于“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所持的精英主义立场屡遭批评,但是他对于“文化工业”的操纵模式的理论分析依旧有其现实的意义。如果撇开他过于低估流行文化消费者的辨别力和抵抗力的盲视部分,他所进行的哲学式的文化批判不失为一种独立的声音。在任何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需要一种独立的声音,都需要一种文化上的自觉意识。
注释:
①⑥⑩(11)(15)T.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M].London:Routledge,1991,p.106,p.160,p.38,p.54,p.46.
②③⑧⑨(12)(16)M.Horkheimer and T.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Philosophical Fragments [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04,p.4,p.111 ,p.116,p.109,p.106.
④R.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M].Glasgow:Fontana,1976,p.231.
⑤Leo Lowenthal.Literature and Mass Culture,Communication in Society,Volume 1 [M].New Jersey.Transaction,Inc.1984,p.4.
⑦霍克海默尔:《霍克海默尔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27-228页。
(13)(14)吕西安·马尔松:《爵士乐简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7页。
(17)T.W.Adorno.Aesthetic theory [M].London:Routledge,1984,p.343.
(18)Robert W.Witkin.Adorno on Music [M].London:Routledge,1998,p.132.
(19)阿多尔诺:《道德哲学的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