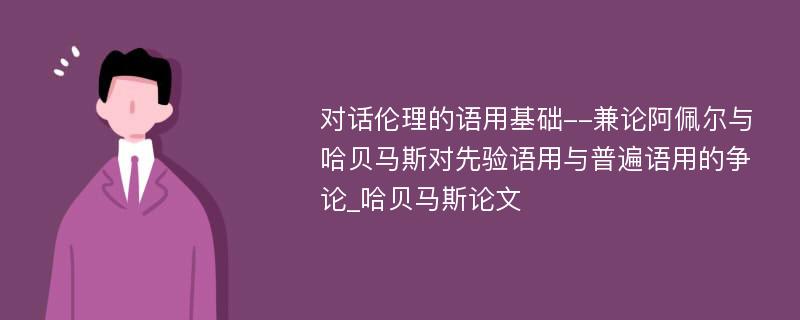
对话伦理学的语用学基础——兼论阿佩尔与哈贝马斯的先验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伦理学论文,之争论文,佩尔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共同创立的对话伦理学,可谓当代德语圈内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或许是因为阿佩尔的艰涩和哈贝马斯的广博,国内学界对对话伦理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于观点的介绍,并且主要限于哈贝马斯的相关观点,而对阿佩尔的对话伦理学思想、他与哈贝马斯之间的同异以及对话伦理学的来龙去脉等重要问题,都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无意于也不可能全面探讨这些问题,而只是着眼于其中的一个小问题,即对话伦理学如何在道德怀疑论盛行的年代开创出一种新的规范伦理学说。基于对阿佩尔和哈贝马斯早期对话伦理学著述的细致研读,笔者将着重指出有关“言谈的双重结构”的语用学发现在对话伦理学奠基中的重要意义,以及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在语用学进路上的差异与他们日后的分歧之间的关联。本文包含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奥斯汀等人的言谈行动理论和哈贝马斯的“言谈的双重结构”的概念;第二、三部分分别结合阿佩尔和哈贝马斯早期论述对话伦理学的文章(主要是阿佩尔的《交往共同体的先天性和伦理学的基础》和哈贝马斯的《真理理论》),说明“言谈的双重结构”这一语用学发现在对话伦理学奠基中的重要意义;第四部分则从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后来产生分歧并渐行渐远的事实出发,反观其早期的论述,指出他们的分歧源于先验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的不同进路。
一、“言谈的双重结构”
自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以来,伦理学就丧失了其在哲学中的地盘,此后唯一有关伦理学的讨论就是元伦理学,而这期间的元伦理学也无非是表明驱逐伦理学有理,各种不同的元伦理学都众口一词地表明道德只是某些不具普遍意义的价值诉求的表达。在此背景下,对话伦理学要建构一种新的规范伦理,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在元伦理的层面上应对怀疑论者的质疑。这一点在阿佩尔和哈贝马斯早期关于对话伦理学的文章中都有直接的体现:阿佩尔的《交往共同体的先天性和伦理学的基础》一文就是从科技时代建构一种普遍伦理的迫切性和似乎不可能性的悖论出发展开论述的,此文堪称对话伦理学的开山之作;哈贝马斯1972年的《真理理论》一文中则主要针对怀疑有关规范的陈述有类似于描述性陈述的真值的怀疑论主张,甚至到1983年哈贝马斯撰文考察对话伦理学的讨论(即《对话伦理学——论证工作记要》[Diskursethik - Notizen zu einem Begründungsprogramm]一文)时,也还是围绕着与道德怀疑论的对抗展开的。语言分析哲学可以“摧毁”伦理学,也可以“重建”伦理学。在研读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这些文章中,笔者发现在对话伦理学的奠基过程中,有关“言谈的双重结构”的语用学发现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故下面先介绍这一概念。
语用学的提法最早源于莫里斯有关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符号学三分法:句法学聚焦于句子的语法结构,语义学关注语词的意义问题,语用学则以语言的运用问题为研究对象。语言的运用涉及言说者对语词的理解、言说的意图、听者的理解、语境、说者与听者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它不局限于客观的语言体系(甚至可能否定这样的语言体系,如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而为语言学开拓了更宽的视域,触及言说者的背景世界,包括文化背景和交往关系等。这似乎提示了语用学与伦理学之间的某种关联。
言谈行动理论可谓奥斯汀和塞尔对语用学的一大贡献,他们将言谈(speech)理解为一种行动(act),奥斯汀在其名著《如何以言行事》中最早提出了“以言表意”(Locutionary act)或“述谓句”和“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或“施为句”的区分。(Austin,pp.5ff.)前者即用语言表达某些意思,这可以说是言谈的主要功能。但除此之外奥斯汀还注意到另一种类型的言谈,比如当我说“请给我一杯水”或“把枪放下!”时,我是在做一件事情——表达一个请求或作出一个命令。奥斯汀称之为“以言行事”,称这类言谈中的句子为“施为句”。奥斯汀的学生塞尔继承了这一区分,并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其中也涉及一些方向性的问题。(cf.Searl)
这一区分给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带来了启发,他们由此看到言谈和行动之间的关联。但他们所理解的言谈和行动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奥斯汀和塞尔所理解的更加明确,更加紧密。因为在奥斯汀和塞尔那里,虽然言谈被理解为行动,但当他们将“以言表意”和“以言行事”分配给不同的言谈行动时,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言谈和行动。而哈贝马斯则明确指出,各种不同的言谈——不管是奥斯汀和塞尔意义上“表意的”还是“施为的”言谈行动——都既有“表意的”方面又有“施为的”方面。“请给我一杯水”即我请求你给我一杯水,“把枪放下!”即我命令你放下枪,这是施为的方面;同时,其中的“给”、“水”、“放下”、“枪”等语词则包含了请求和命令的具体内容,是表意的方面。表意的“述谓句”,比如“这是一张圆桌子”,也同时体现为一种行动,即作出断言或传递信息等:当我说“这是一张圆桌子”时,就是表明,我认为或我告诉你这是一张圆桌子。
上述思想在哈贝马斯1976年的《何谓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有清楚的论述,哈贝马斯称之为“言谈的双重结构”。(cf.Habermas,1984b,pp.404ff.)这一提法很快得到阿佩尔的响应和高度评价,阿佩尔认为这一从言谈行动理论发展出来的有关人类言谈的“施为和内容的双重结构”的思想,包含了对语言的“交往功能和自我反思功能”的深刻洞见,在语言哲学中实现了一个“范式的转变”,其影响在语言分析哲学中甚至还没有得到正确的估量。(cf.Apel,1998,S.200)结合阿佩尔和哈贝马斯此前论述对话伦理学的文章,不难发现其中已经包含了“言谈的双重结构”的思想,以及这一思想之于对话伦理学的奠基意义。
二、“交往共同体的先天性和伦理学的基础”
本小节标题即此处将要讨论的阿佩尔文章的标题,该标题直接表明了阿佩尔关于伦理学奠基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建构一种普遍的伦理学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不可能的,其可能性就在“交往共同体的先天性”之中。
阿佩尔所谓“交往共同体的先天性”表明,任何以语言为媒介的人类活动必然要预设一个“能够进行主体间沟通并达成共识”的论辩共同体或交往共同体。先天性概念旨在强调交往共同体是人类活动必然要预设的前提。阿佩尔在驳斥道德怀疑论时得出了这一结论。道德怀疑论否定普遍伦理之可能性,其另一面就是只肯定科学的客观性,这源于分析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事实具有客观性,价值不具有客观性,因此,唯有有关事实的科学是客观的或普遍有效的,而涉及价值的伦理学不具有客观性。阿佩尔当然肯定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他也承认伦理学并非价值中立的学科,但他一方面从伦理学入手,质疑是否关涉价值的学科就不具有普遍性:他用一种包含规范目标的“规范释义学”对抗伽达默尔的具有相对主义危险的释义学,以提示一种普遍伦理的可能性(cf.Apel,1976, S.386ff.);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他对科学进行质疑,指出“无涉于价值的科学的客观性本身还要以道德规范的主体间有效性为前提”(ibid,S.395),以此消除科学与伦理在普遍有效性问题上的对立。
这一工作大致经过两个步骤完成:第一步表明任何科学活动都要预设一个论辩共同体。在阿佩尔看来,科学的“客观性”只有在“一个能够进行主体间沟通并形成共识的思想家共同体”中才能得到检验,“即便实际上孤独的思想家个体,也只有当他能够在‘灵魂与他自身’所作的批判性的‘会话’(柏拉图)中把一个潜在的论辩共同体的对话内在化时,才能阐明和检验他的论辩”。(ibid, S.399)这也就是说,科学活动乍一看只是科学家作为思想主体与客观世界的认知关系,实际上它同时也是科学家作为论辩者与其他科学家或其他认知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科学家提出一种科学理论总是在事实上或虚拟地与其他人展开论辩性的对话,科学家单个的或小群体的活动同时总是预设了一个无限的交往共同体。
第二步则是指出作为检验“客观性”之最高机构的论辩共同体必须遵循某些主体间有效的道德规范。阿佩尔以列举的方式提到不能说谎、解释或辩护的义务等等,他说:“比如说谎显然会使论辩者之间的对话不可能。同样,拒绝对论据作批判性理解、解释或辩护也是如此。简言之,在对话共同体中要预设所有成员相互承认彼此是平等的对话伙伴。”(ibid,S.400)既然科学活动必须预设一个作为检验其“客观性”之最高机构的交往共同体,而这种交往共同体只有遵循这些规范才有可能,那么这些规范就是科学活动必须预设的前提,是保证科学“客观性”的前提。
而鉴于“一切语言表达以及一切有意义的行为和身体表情(只要它们能够被语言化)包括‘要求’都能够被理解为潜在的论据”(ibid),这种交往或论辩共同体就不仅仅是科学活动的前提,同时也是所有人类活动必须预设的前提。同理,既然这种论辩共同体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前提,其所必须预设的规范也就成为人们必须预设的伦理规范。
至此,阿佩尔驳斥道德怀疑论尤其是相对主义并确立一种普遍规范伦理的思路已经大致清楚,而其关键之处在于作为科学活动乃至所有有意义的人类行为之背景的“交往共同体”的彰显。人们一般强调引入交往共同体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用交往共同体的共识取代单个主体的意识作为检验思想有效性的标准,以对话取代独白,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这些无疑都是对话伦理学的重要贡献,但它们是就该概念的理论后果而言的。笔者认为,要理解阿佩尔的对话伦理学,更有必要对照交往共同体的先天性的思想与言谈的双重结构概念。我们可以说,“交往共同体的先天性”已经包含了有关言谈双重结构的发现。首先,就内容而言,它揭示了各种具体的人类行为的交往方面,这其实就是双重结构所强调的施为方面。阿佩尔在其文中完成了对“无涉于价值的科学的客观性本身要以道德规范的主体间有效性为前提”的论述之后,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在‘言谈行动’理论的意义上区分人类言谈的施为部分和内容部分”,将有助于澄清前面的思想,因为这种区分足以表明,“在论辩者的对话中不仅作出了关于事态的价值中立的陈述,而且至少隐含地将这些陈述与交往行动相联系——即与那些向交往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提出道德要求的行动相联系。因此,任何事实陈述,作为必须在逻辑上加以辩护的陈述,在语用学的深层结构中都是以一种施为式的补充为前提的”。(ibid,S.401)
另外,在阿佩尔这里,尤其要强调这一发现所包含的方法论意义。科学活动乃至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必须预设“一个能够进行主体间沟通并达成共识的思想家共同体”,这不是智商超常的阿佩尔的偶然发现,而是任何有正常理性能力的人通过反思所能达到的认识。这里所说的反思是指一种自我审视,一种对自己行为的反观。通过这种反思,一个人得以在当下言行的主客关系之外看到作为其前提的主体间关系。我们只有基于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阿佩尔有关终极奠基的思想。
所谓“终极奠基”,就是要为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学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阿佩尔很清楚,他无法在形式逻辑推理的意义上获得一个最终的基点,但他认为内容和施为两方面的区分为此开启了一种可能。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处在不同的维度上,但它们又属于同一个言谈行动,这样彼此之间势必会形成一定的钳制:如果内容方面宣称的东西与施为方面预设的东西相互矛盾,那么所宣称的命题就不成立。这就是阿佩尔所说的“施为的自相矛盾”。在他看来,一个命题如果否定它就会陷入“施为的自相矛盾”,那么这个命题就是普遍有效的。阿佩尔非常强调这一发现,认为这对可错性原则的应用做了有效的限制。(cf.Apel,1998,S.203)落实到对话伦理学的奠基上,是否陷入施为的自相矛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前面列举的不能说谎、相互承认彼此的平等等规范都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检验,因此就是可以获得终极奠基的普遍有效的基本道德规范。
有关终极奠基的思想和“施为的自相矛盾”的概念,有不少需要解释和值得争论的地方,在这里仅讨论一个相关的问题:将不说谎或承认彼此的平等确立为普遍有效的规范是否太过理想?因为现实生活中似乎有太多不得不说谎的时候,生活中似乎没有真正的平等。阿佩尔当然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在阐述了交往共同体的预设之后,马上表明这种预设中的作为检验“客观性”标准的共同体是一种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对照理想与现实,他将终极奠基获得的基本规范理解为一种康德意义上的指导性理念,并由此阐发出一套对话的责任伦理学。(ibid,1976,S.429 ff.)需要指出的是,阿佩尔强调这种理想的共同体虽然是反事实的,但也是在任何现实的交往共同体中必须预设的,它与现实的交往共同体处于一种辩证的关系之中。因此,在阿佩尔这里,基本的道德规范即便在现实的生活中不能直接应用,也始终有其指导性意义。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论及。
由于阿佩尔在论述对话伦理学的早期论文中使用的理想交往共同体的术语经常被人们误解为某种乌托邦的社会构想,为了避免这种误解,他后来有意避免使用这一术语,而是用理想的对话等术语替代。但此处是介绍和分析其早期文章,故还是沿用当初的术语。
三、规范正当性与理想言谈情境
哈贝马斯对怀疑论者的挑战在于,他明确提出有关规范的陈述有类似于描述性陈述的真值。在《真理理论》一文中,他从一般的真理(主要是描述性陈述的真理)问题入手,驳斥了符合论的真理观,提出真理的共识理论。实现这种真理观的转换的关键在于有效性要求概念的提出。简而言之,有效性要求即言说者在言谈行为中针对其言谈对象或潜在的交往共同体提出或预设的言谈内容或前提的有效性。所谓四个有效性要求,即可理解、真理性、真诚性和正当性要求,分别就有言谈的语言媒介、内容、言说者的意向和言谈行为的规范前提而言。将真理理解为有效性要求,其鲜明之处在于还原命题背后的交往关系。哈贝马斯指出,陈述总是某个人提出来的陈述,其真假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其与对象之间是否相符合(更何况“符合”的说法也经不起推敲,因为符合总涉及两样东西,但在这里是经验与事实的符合还是陈述与经验的符合、它们之间又如何符合,这些都是很成问题的)。实际上,即便是诸如地球到月球距离多少之类的陈述,对其真理性的辩护最终也只能通过论证,而非简单地付诸感觉经验。因此,陈述的真假归根到底依赖于提出者能否提供充分的依据或理由向其受众证明其为真,即依赖于提出者和接收者(读者和听者)能否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亦即提出者的有效性要求能否得到兑现。(cf.Habermas,1984a,S.149ff.)正是通过这种真理观的转变,哈贝马斯成功地开启了谈论规范性陈述之真假的可能:与描述性陈述一样,规范性陈述若能在言谈者和接收者之间达成共识,也就能被认为是真的。哈贝马斯称规范性陈述的真值为正当性,以区别于描述性陈述的真理性。
这显然已经是在运用“言谈的双重结构”的语用学发现,而哈贝马斯当时也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发现对于揭示言谈的反思功能的重要意义。在上述文章中,哈贝马斯驳斥了真理冗余论。所谓真理冗余论认为,说一个陈述p是真的(It is true,that p.)跟直接作出p这个陈述,两者没有区别,因为作出一个陈述p就意味着作出者认为p是真的。哈贝马斯肯定真理冗余论有关作出一个陈述p就意味着作出者认为p是真的发现的重要意义,但强调两种情况(一种是元语言的断定,另一种是自然语言的陈述)的层面区别以及元语言的断定所包含的反思关系:“在这个层面的句子和直接作出p的断言之间并不存在演绎的关系,而是一种反思的关系,一种辩护关系一旦被明确认定,这种反思关系就会发生。在简单作出的断言中隐含地包含的有效性要求,在元语言的断定中被明确提出,并且要么得到确认要么被否定。”(Habermas,1984a,S.130)
但真理的共识论显然还需要进一步展开。什么样的共识才能作为真理或正当的标准?你我两人之间的共识显然不行,人数较多的一群人的共识也没有本质的不同,甚至假定的现实的一代人的共识有朝一日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哈贝马斯认为应该是所有有理性能力的人(在规范的问题上,他也说“所有相关者”)通过无强制的对话达成共识。这种共识在概念上必然包含一系列的前提,哈贝马斯顺着这个思路在《真理理论》中阐发了“对话的逻辑”,并在其中提出理想言谈情境的预设。他认为,理想言谈情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所有潜在的对话参与者必须享有同等的使用交往言谈行动的机会,以便他们任何时候都能够展开对话,并通过演说和答辩、提问和回答持续对话。
2.所有对话参与者必须享有同等的作出阐述、主张、建议、解释和辩护的机会,享有同等的质疑、论证和反驳有效性要求的机会,以免任何观点在讨论和批判中遭到压制。
3.言谈者作为行动者参与对话必须享有同等的使用表达性言谈行动的机会,即表达他们的看法、感受和愿望。因为只有个人言论的游戏空间的相互契合以及行动关联中的相互接近,才能保证行动者作为对话参与者面对自身采取真诚的态度,袒露自己的内心。
4.言谈者作为行动者参与对话必须享有同等的使用指导性言谈行为的机会,即命令、驳斥、允许、禁止、允诺、收回允诺、辩解和要求辩解等等。因为,只有行为期待的完全相互性才能排除特权,即某种片面要求的行为和评价规范,才能保证进行和继续演讲的形式的机会平等能够切实地用于搁置现实强制,从而进入一个独立于经验和行动的对话交往领域。(ibid,S.177-178)
既然衡量规范正当性的尺度在于对话达成的共识,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共识必须满足以上的规范前提,那么在哈贝马斯看来,就必须谋求这些前提的实现;这种要求被视为基本的规范。
四、先验语用学与普遍语用学之争
阿佩尔的再传弟子维尔纳(M.Werner)曾经说,对话伦理学之所以称为对话伦理学,在于其将伦理学的问题与对话的实践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话伦理学试图通过对对话实践的反思完成其基本道德原则的奠基,它将对话者“总是已经”承认的道德原则视为规范伦理的基本原则或最高原则。(cf.Werner,S.140)其二是,“对话伦理学的道德原则从内容上要求论辩性的对话。这也就是说,只有其所有相关者作为无强制的论辩性对话的参与者能够一致同意的行为方式才是道德上正当的”。(ibid)
这一概括尽管用的主要是阿佩尔的术语,却也是对对话伦理学基本主张的精辟概括。它表明了对话伦理学两个方面的基本主张:一是将对话的规范条件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二是提出无强制的对话作为确定具体规范的程序性原则。但结合上文对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方面在他们那里的主次地位并不相同:阿佩尔强调普遍主义,强调基本道德规范的义务性,其立足点在第一方面,连带着确立了第二方面;而哈贝马斯则走的是一条认知主义的道路,其侧重点在第二方面,似乎连带着承认了第一方面。这一元伦理层面上的普遍主义和认知主义的殊途在一定程度上也注定了他们在同归之后又分道扬镳的可能性。不过,他们日后的分歧还必须追溯到更为深层的原因,即他们在语用学上的先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进路的分歧(他们也因此分别称各自的对话伦理学为“先验语用学路向”和“普遍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而这一点,如果结合他们后来出现分歧甚至渐行渐远的事实,那么在早期的文章——包括上文提及的他们各自的对话伦理学的开山之作以及哈贝马斯稍后的文章——中已经初见端倪。
此端倪即他们在不同的语用学进路下,对理想交往共同体或理想言谈情境的目的论意义的不同理解: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强调先验反思,以此直接确定理想交往共同体(注意不能将“理想交往共同体”理解为某种关于社会状态的乌托邦预设)的目的论意义;而哈贝马斯一开始似乎也在反思中直接预设了理想言谈情境的目的论内涵,但随着其普遍语用学的形式重构的方法的日益明朗,他在这个问题上不像阿佩尔那样有明确的肯定立场。
阿佩尔称自己的方法为先验反思的方法,这首先在于他不是分析实际的交往行动的实际的前提,而是分析交往行动之为交往行动的“可能性条件”,这类似于康德先验哲学追问经验的“可能性条件”;而这同时也意谓着此可能性条件必定包含一种超越现实的规范内涵。阿佩尔强调这种超越现实或反事实的规范性条件作为交往的“可能性条件”,是所有论辩者必须预设或总是已经预设的,因此他说:“(因为)任何一个论辩者总是已经同时假定了两样东西:一是某个现实的交往共同体,论辩者本身已经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而成为其中的一员了;二是某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它原则上能够充分地理解论辩者论据的意义并明确地判断这些论据的真理性。但是情境的奇特和辩证性在于,论辩者在某种意义上把理想共同体先行假定在现实的共同体中了,也即把理想共同体先行假定为现实社会的现实可能性了;尽管论辩者知道,(在大多数情形中)包括他本人所在的共同体在内的现实共同体根本不能与理想共同体同日而语。可是,根据其先验结构,论辩者除了正视这一既绝望又充满希望的情景之外,别无选择。”(Apel,1976,S.429)
尽管我们可以像哈贝马斯以及其他一些学者那样对阿佩尔的“先验反思”进行质疑,但阿佩尔的目的很清楚,他要以此确定理想交往共同体的目的论意义,并进而表明其所包含的规范前提的义务性。就此而言,阿佩尔的论述逻辑上较为严密。相比之下,哈贝马斯一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则存在有待澄清的地方。结合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真理理论》中的基本思路是:确立真理的共识论,为规范正当性铺平认知的道路,继而阐述作为真理性和正当性标准的共识的规范前提(理想言谈情境),并将其确立为对话伦理学的道德原则。但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是否必须寻找共识?或者说,为何必须寻找共识?如果不能对此给出肯定的答案,则理想言谈情境不具有目的论意义,其所预设的规范也不能被视为普遍的道德规范。哈贝马斯在文章中并没有对此明确展开论述:当他直接把理想言谈情境的前提当作道德规范的时候,他似乎直接认定要寻找共识是理所当然的。但他在文中关于行动(Handeln)与对话(Diskurs)的区分,恰恰为质疑这种理所当然的预设埋下了伏笔。
他是在阐述有效性要求的概念时引出这对概念区分的:“行动”“直接预设并承认了”所说的话(或表达的主张)所包含的有效性要求,我们所做的是进行信息的交流;而“对话”是指以论辩为特征的交往形式,在对话中我们并没有直接承认所说的话或提出的主张所包含的某种有效性要求,而是对之进行质疑或辩护。对话不是交流信息,而是论辩;对话摆脱了行动的关联,搁置了行动的压力,其目的在于达成沟通。(Habermas,1984a,S.130)这也是哈贝马斯一直强调的区分;后来虽然在表述上有所调整,比如将对话与共识言谈行动(konsensuelle Sprechhandlung)相对照,前者可进一步区分为理论对话和实践对话,相应地后者包括信息交流与行动,但这种调整是为了将区分表述得更完整和精准。
为彰显对话伦理学之对话的特定含义,这样的概念区分自然是必要的,但哈贝马斯所做的不仅仅是概念的区分,他还在对应现实的人类行动时将它们理解为两类不同的交往行为,这里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这种做法是否合理?生活世界中是否有这样泾渭分明的共识言谈行动和对话?不要说共识言谈行动和对话这两种不同的交往行动往往彼此包含,甚至交往行为与策略行为也往往相互纠缠。这也是阿佩尔后来质问哈贝马斯的问题(阿佩尔很快就敏锐地意识到了他与哈贝马斯之间的分歧以及这种分歧可能引发的后果,故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发表之后,他先后接连发表了《回到生活世界之伦理的“批判理论”的规范奠基?——以先验语用学为导向和哈贝马斯一起反对哈贝马斯的一次思想尝试》和《用先验语用学的眼光看明显的策略性语言使用——与哈贝马斯一起反对哈贝马斯的第二次思想尝试》等文章,对此处涉及的问题与哈贝马斯展开争辩)。其次,这样的区分也为从此到彼的过渡带来了理论上的困难。在1976年发表的《何谓普遍语用学?》一文中,哈贝马斯提到,一般的共识言谈行动的前提若受到质疑,即至少有一个有效性要求不能兑现,则交往行动可能无法继续,要么转变为策略行为,要么中断,或者进入另一个层面的交往行为,即对话。(cf.ibid,1984b,S.355-356)但我们可以问:这些不同的出路(转变为策略行为、中断或进入对话)是否有优劣之分?哪种出路更加合理或最合理?也许人们(包括哈贝马斯本人)都会认为转入另一层面的交往行动即对话最为合理,但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过渡?过渡的动力从何而来?这些问题迫使哈贝马斯直面前述理所当然之预设的合理性问题。
《何谓普遍语用学?》并未直接论述对话伦理学,但也正是此文确立的普遍语用学的思想注定了哈贝马斯与阿佩尔之间在对话伦理学上渐行渐远的结果。哈贝马斯将普遍语用学的任务界定为辨别和重构交往行为的普遍前提,而他解释说此处“交往行动”限定于共识言谈行动而非对话(ibid, S.356),尽管“交往行动”在概念上包括对话。其结论是:一个人一旦进入与他人的沟通过程之中,他就会提出四个有效性要求,即语言的可理解性、内容的真实性、真诚性和规范的正当性;只有这些有效性要求得到兑现或能够兑现,交往才能顺利进行。这看似与阿佩尔的观点并不相左,但结合他对这些有效性要求的具体论述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异,下面以规范正当性的要求为例加以说明。
在《何谓普遍语用学?》中,哈贝马斯这样表述有关规范正当性的有效性要求:“言说者必须基于现有的规范和价值选择正确的言论,使得自己的言论能够被听者接受,这样,听者和说者彼此才能就涉及业已获得承认的规范背景的言论达成一致。”(ibid,S.355)这可以说充分体现了他在文中强调的“形式重构”的方法。而鉴于其普遍语用学对象限定于共识言谈行动而不涉及对话,我们大概也可以理解他将规范正当性落实到“现有的规范和价值”与“业已获得承认的规范背景”。但是对照一下阿佩尔有关理想交往共同体与现实交往共同体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别:在哈贝马斯这里我们看不到从共识言谈行动内部生发的向对话过渡的动力。若从此文回到《真理理论》,不难看到形式重构得出的交往行为的普遍前提与根据“对话的逻辑”得出的理想言谈情境之间存在的差距,这一差距更加凸显了前面提出的是否或为何必须寻找共识的问题。哈贝马斯在后一篇文章中也提到阿佩尔,他认为他所界定的普遍语用学也是阿佩尔在做的工作,只是他不赞同先验语用学的提法。(cf.Habermas,1984b,S.379ff.)从他给出的反对理由看,多少有点抵触先验概念的味道,因此为康德专家和阿佩尔拥护者所诟病。但他的普遍语用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在《真理理论》中建构的对话伦理学的根基,这使得他最终与坚持“终极奠基”的阿佩尔产生了分歧并渐行渐远。
哈贝马斯虽然是“多变”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他至少是忠实的。他最终将这个有关动力的问题交给了生活世界,交给了历史。但思想并没有结束,阿佩尔和哈贝马斯这两位对话伦理学的创始人的分歧最终成为了指导性理念与生活世界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