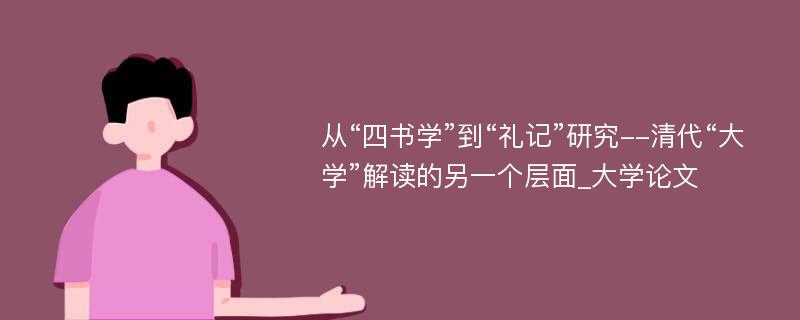
从《四书》之学到《礼记》之学——清代《大学》诠释的另一种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记论文,清代论文,之学论文,大学论文,四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是宋以后最重要的儒家文献之一,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核心的价值观。《大学》本为《礼记》的一篇,后来朱熹分经、传,补格物致知章,将其纳入《四书》体系。元仁宗延佑科举后,朱熹《四书》说解悬为功令,家弦戶诵,习见无奇。至清乾嘉时期,尊经崇汉,主张回归原典的汉学与考据学已开始占据学术界主导地位。四书学的研究出现经学化趋势,注重音韵训诂与名物度数的考证。这时的汉学家对朱子确认《大学》作者、改动《大学》文本,从《礼记》中将其抽出成为《四书》一部分的做法,不能没有微辞。然而,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持,势必要维护朱熹义理诠解的惟一性。若重汉学,恢复经典原貌,必将《大学》回归《礼记》研究,使之成为礼学研究的一部分。这使得以考证见长的经学家,通论《大学》义理的专著几付阙如。正如晚清郭嵩焘感叹的那样,“雍、乾之交,朴学日昌,博闻强力,实事求是,后凡言性理者屏不得与于学,于是风气又一变矣,乃至并《大学》、《中庸》之书蔑视之,以为《礼记》、《学记》之支言绪论。”①《大学》研究出现了由《四书》之学向《礼记》之学转变的新取向,开始重视古本和汉、唐注疏,成为经学研究的一部分。
在传统观念中,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是一个缺少思想活力的时代,考证为当时学术之全部。但是,新近的研究表明,乾嘉时期有着丰富的经世思想。同时,有不同于宋、明义理学话语系统的重实际、重实效的“新义理学”存在。②我们看到,清儒对《大学》性质的认识,以及“明明德”、“格物致知”等范畴另作新解的考证,也成为明清儒学思想转型的一大见证。本文试图考察形成清代《大学》诠释的另一种向度的历史过程,疏理以经学闻名的清代学者,在经学隆盛时期的十八世纪有关《大学》的态度与认识,以期了解汉学家所理解的《大学》思想“新义理”所在,昭示清代思想史的另一面。
一、从《四书》之学到《礼记》之学
清初的阎若璩(1636-1704)为后来乾嘉学者所认同,主要在于他长于考据。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确证了梅颐所献《古文尚书》为伪书;《四书释地》校正了不少古地名的附会和讹误。阎若璩与清初钱塘冯景(1681-1762)相交甚密。阎若璩力攻伪《古文尚书》,冯景与其桴鼓相应,互质疑难。不过,对经典真伪的考辨,最终会触及经典的合法性问题。在写给冯景的信中,阎若璩表达了他对《大学》文本的怀疑。朱熹分《大学》为经与传,认为传文成于曾氏门人之手,阎若璩认为没有根据。阎若璩统计了《礼记》中“曾子”出现的次数,认为“曾子”为记礼者的通称,朱子以“诚意章”有“曾子曰”三字认定《大学》为曾子所作,并无多少证据。冯景认为阎若璩的论述看似“既辨既博,亦经亦史”,却也是不可理喻,“愚以为即通十传,并无‘曾子曰’字,亦决其为曾子之传,匪异人任矣,称子诸证不必论也”,“吾决其为曾子传之,而子思述之,以尊其统,犹恐后之为僭为伪者阑入于其中,奈何先生为无端之疑,而启天下后世不尊不信之渐哉?”③从维护道统的角度,冯景担心阎若璩会开后世不尊信经典的风气。
冯景的担心不为多余。明清鼎革之际,对理学末流的批判往往与《大学》相关联。较早的陈确(1604-1677),就明言《大学》是伪书,④姚际恒(1647-1715)也有相近的论述,认为《大学》为禅学文献。⑤后来以辨伪闻名的崔述(1740-1816),同样认为《大学》非曾子所作。⑥对经典的“不尊不信”,最终会造成对意识形态的冲击。这样的局面,是官方所不愿意看到的。清开国至康熙朝,提倡程朱理学。康熙本人尊崇宋学,启用理学名臣,纂修《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目的在培养士风,敦励名节。官方对程、朱之学的认同,使得清初对《大学》可以争论的多样化局面不复存在,但是,这些学者对《大学》经典性的消解、对朱熹《大学》解释的批判,无疑成为官方《钦定礼记义疏》重新处理《大学》的存在方式以及汉学家不重《大学》理学思想阐释的知识与思想背景。雍、乾之际,朴学开始兴盛,认同考据学方法的经学家开始致力于《大学》作者、名物、改本的考证,但这只说明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对《大学》的关注角度开始有了变化,并不代表他们对程朱理学地位的否定,反而却有足够的推崇。
江永(1681-1762)作为皖派朴学的开山者,生平致力于经学、音韵学,于理学服膺朱熹之学,深究力行。江永认为《大学》的作者应是曾子门人,怀疑是子思所作。又考证《大学》传文中“盤”的功用,是作为盥洗之用,而不是沐浴之盤。不过,江永未将《大学》放入《礼记》中研究,仍将其单列论述,没有深究义理,表明了他对理学的态度,又不太注重以宋学为中心的义理阐释。⑦戴震(1723-1777)以考证闻名,后来对程、朱义理之学多有訾议,年少时就向私塾先生质疑朱熹断定《大学》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的可信性,⑧但是却认为朱子《大学》格物致知章该补,“自程子发明格物致知之说,始知《大学》有阙文,凡后儒谓格物致知不必补,皆不深究圣贤为学之要,而好为异端,其亦谬妄也矣。”⑨明代曾出现众多《大学》改本,对此戴震说:“夫古人之书,不必无残阙。知其有阙,而未言者,则书虽阙,而理可得而全。苟穿凿附会,强谓之全书,害于理转大。读古人书,费心通乎道。寻章摘句之儒,徒滋异说,以误后学,非吾所闻也。”⑩戴震对程、朱《大学》之说,是有不少辩护的。(11)
清至乾隆皇帝,崇尚经术,讲求实用,视“穷究性理”为空疏。官方开始改变《大学》的存在形式。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礼记义疏》将《大学》回归《礼记》,用古本原文,并将朱熹《章句》与郑玄注、孔颖达疏并录,“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为妄削古经,今仍录全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戶之争。盖言各有当,义各有取,不拘守于一端,而后见衡鉴之至精也。”(12)此一分类的转变,正萌蘖着乾隆以降《大学》认识以及研究方法之转向。(13)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馆,纪昀为总纂,四库馆顿时成为考证学的大本营。四库馆臣以为,向来解《大学》者,是朱熹《四书》理论体系之中的《大学》诠释,而不是《礼记》之中的《大学》,“案训释《大学》、《中庸》者,《千顷堂书目》仍入‘礼类’。今并移入《四书》,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14)清儒将《大学》分为《四书》之《大学》和《礼记》之《大学》。朱子《四书》说解,依旧成为士人科举的必读书,也为尊程、朱的宋学家所推崇;而对重汉学的乾嘉学者而言,不少学者将《大学》放入《礼记》研究。
二、礼学下的《大学》诠解
乾隆后期至道光初年,考据学最为兴盛。同时,知识界谈礼思想蔚起,“以礼代理”思想流衍。不少学者开始转化理学家论道德偏重内在心性体悟之途,而是直接切入实际人伦日用之践履。(15)此时期,经学家对《大学》的认识,是将《大学》变成考证之学,关注《大学》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同时,在义理阐释上也有所突破,主要是对“格物致知”等概念作出新的阐释。这两种向度,多是在礼学视野下来认识《大学》,与宋明儒四书学下的《大学》诠解取向不同。
杭世骏(1696-1773),乾隆元年(1736)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纂修《三礼义疏》。晚年,主讲扬州、粤东书院,以实学课士。在《续礼记集说》中,杭世骏录《大学》古本,有《大学》集说,总以郑玄、孔颖达之说为依据,又引宋王应麟、清姚际恒的说解,不言宋、明理学中解《大学》者。我们看到,王应麟的《大学》说解,黜虚崇实;姚际恒质疑《大学》的作者与性质,对理学末流的《大学》说十分不满。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将《大学》回归《礼记》,注疏以郑注、孔疏为主,兼采王、姚二人之说,用集说的形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16)徐养原(1758-1825)(17)与李惇(1734-1784)(18)均主张不废《大学》古本旧注。徐养原承认程、朱理学的地位,强调也要重视郑玄旧注,“程、朱为理学正宗,则《或问》所载二程之说一十六条,乃格物之正义,其余曲说,固可一扫而空之矣。惟郑氏旧注,立学校者已向千载,虽精研未若闽、洛,而诂训具有师承,或尚可以备一解乎?”(19)李惇(1734-1784)说道,数百年来遵从朱子《四书》之《大学》,未有异议,“但《戴记》中犹当载其原文,使学者知二书本来面目,并知程、朱改订之苦心,今惟注疏本,尚载原文而不能家有书,坊刻读本止存其目,学者有老死而不见原文者,窃谓急宜补刊,庶得先河后海之义。”(20)杭世骏、徐养原、李惇均是主张将《大学》回归《礼记》,用《大学》古本。
惠士奇(1671-1741)有专著阐明《大学》义理。后学周漪塘见到惠氏《大学说》,以为应将《大学说》附于惠士奇经学著述《礼说》后一并印行,这代表了乾嘉时期将对《大学》回归《礼记》的主流看法。段玉裁(1735-1815)从解经的角度认识到惠士奇《大学说》与理学家《大学》诠解的不同,认为此书可以单行付梓。段玉裁说:“愚窃观此说,论‘亲民’不读‘新民’,‘格物’不外本末终始先后,即絜矩之,不外上下前后左右,不当别补格致章,确不可易”,以为其言“针砭末俗,有功世道人心不小,不徒稽古数典已也”。(21)惠士奇的《大学说》,认为《大学》之本不在“明明德”,而在“新民”,宋儒破“亲”为“新”,使亲民之道不在。而《大学》之说,乃是成己成物之说,“格”之言度也,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不须偏格物理,而《大学》以格物始,以絜矩终,而格即絜,矩即物,格物就是推心之恕。段玉裁自己解“明明德”,遍引小学、经传之书的“明明”句,考证“明明”,即为“察”之义,明明德,即是《左传》、《论语》中所说的崇德。(22)这与程、朱义理上解明为虚的取向迥异。可以说,他们均是在礼学视野下审视《大学》的思想。惠栋(1697-1758)传承其家学,却也不再像其父惠士奇那样对《大学》有如此之兴趣专论《大学》。不过,在谈及《九经》古义《礼记》中《大学篇》,惠栋解“大学致知在格物”引“《文选注仓·颉篇》云格,量度之也”(23),解格物为量度事物,与其父是为同解。只是惠栋已将《大学》变为礼学的一部分。
另外,金榜(1735-1801)、孔广森(1753-1786)一为考证大学制度,一为考证大学古义,“周立三代之学,夏氏之东序,在东郊;殷之瞽宗,有虞氏之上庠,在西郊,皆大学之教。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24),金榜所关注的已不在《大学》义理。孔广森引《礼记》之《哀公问篇》解“格物”,落实到五常、五伦之上,而将格物致知之学变成道德范畴,“《大学》致知在格物,即致知止之知也。格,至也;物,射者画地所立处也。《哀公问篇》曰:‘孝子不过乎物,仁人不过乎物’,言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朋友止信,皆有定则。如射之有物,不可以过。至乎物,则不过矣。不过乎物,则得所止矣。上文皆曰‘欲’,曰‘先’,此变言在‘明’,非于致知之外,别有格物之功也,朱子格致补传前人已有疑之者。”(25)汪中(1744-1794)以为《大学》和《礼记》中其他篇章价值相同,并无特殊之处。“其文平正无疵,与《坊记》、《表记》、《缁衣》伯仲,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于孔氏为支流余裔,师师相传。”通过分析先秦古书写作形式的通例,汪中驳斥朱熹分经、传,补格物致知之传,肯定《大学》作者的做法不可靠。孔子平日教人,经常结合具体的人,作出具体的教导,而宋儒“标《大学》以为纲,而驱天下从之,此宋以后门户之争,孔氏不然也。”(26)汪中解《大学》回归原儒,完全消解了《大学》的经典性,连有“理学干城”之称的方东树(1772-1815)也不得不承认汪中“拔本塞源,直倾巢穴之师也。较诸儒之争古本补传者,更为猛矣。”(27)凌廷堪(1757-1809)更是以习礼、明礼意、复性于礼,重解《大学》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28)凌廷堪引《礼器》之语,说明礼的性质与重要性,“君子曰:‘无节于内者,观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礼,弗之得矣;作事不以礼,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礼,弗之信矣。故曰礼也者,物之致也。”而《大学》格物即为礼,“此即《大学》格物之正义也。格物亦指礼而言。‘礼也者,物之致也’,《记》文亦明言之。然则《大学》之格物,皆礼之器数仪节可知也。后儒置《礼器》不问,而侈言格物,则与禅家之参悟木石何异?”(29)凌廷堪以“礼”代“理”解《大学》,完全将其变成礼学的一部分。
三、《大学》诠解中的新义理
惠士奇、汪中、凌廷堪等对《大学》的有关认识,已不同于宋、明学者。惠士奇对《大学》重新诠解,昭示着《大学》说已不再囿于理学,不论形上本体,而是在经验界中考察人性、物性、理性,重人伦是用,集中在道德修为的践履上彰显“絜矩”之道。其解格物,扣紧人情之上,又为后来的焦循、阮元所继承,形成了正视人之情欲的新义理传统。以人事解格物,在程瑶田、钱大昕、焦循等经史大家身上,亦有充分体现。
程瑶田(1725-1814)曾师事江永,与当时著名学者戴震、钱大昕、阮元、金榜、段玉裁等均有交谊,颇受推重。程瑶田以为“诚意为明明德之要,而必先之以致知,知非空致,在于格物”,何为“格物”,“物者,身心家国天下也。丽于身者有五事,接于身者有五伦,皆物之宜格焉者也”,“格者,举其物而欲贯通乎其理,致知者能贯通乎物之理矣”(30),诚意,就是要不违乎物之理,而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不外乎顺物之情,尽物之性。明明德之事,即崇德,崇德一大端,是问学之事。不可离物慎独。
乾嘉时期,首重经学力倡治史的钱大昕(1728-1804)同样信奉《大学》古本,“盖《大学》一篇无可补亦无可移,先儒之说与经文有不安者,信先儒,不如信经之愈也。余姚王氏、安溪李氏皆尊古本者也,安溪笃信朱学,非余姚比而于此篇亦不能强同,尊经崇古之心所由高人一等矣。”钱大昕对《大学》的认识也比较平实,“然予读《大学》书,与忠恕一以贯之旨,何其若合符节。”“身正而天下归之,古人治天下国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絜矩之道,即修身之道,由身推之而至于家,由家推之而至于国,由国推之而至于天下,言道一以贯之而已矣,忠恕而已矣。”(31)“新民之本在于明明德,而明德之极即是至善,仁、敬、孝、慈、信,皆修身之事也,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已备矣”。(32)程瑶田与钱大昕此论,已不论心、性、理、知等概念,均以孔、孟之语证之絜矩、忠恕之道,强调自身修养与道德习行的重要性,不再仅是追求内在修养,而是通过推己及人的方式,实现《大学》“三纲领”与“八条目”,这就跳出了理学讲心性的范畴,实现了向原儒义理的回归与超越。
焦循(1763-1820)为清扬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论《大学》有云:“格物者何,絜矩也,格之言来也,物者,对乎己之称也……絜矩者,恕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足以格人之所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足以格人之所好。为民父母,不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33)“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于己之有夫妇也,因而知人亦欲有夫妇,于己之有饮食也,因而知人亦欲有饮食。”“平天下,所以在絜矩之道也。”(34)“‘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故格物不外乎欲,己与人同此性,即同此欲,舍欲则不可以感通乎人,惟本乎欲以为感通之具,而欲乃可窒。”(35)焦循同样以“絜矩”之道立论,承认“欲”存在的必要性,只要能推己及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能格人之所好恶,推己之欲。治人者以此用于家、国,则天下平而治。
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的阮元(1764-1849),并未公开表露反对程、朱理学的意见,但于朱熹的“格物”说也有不满。他说:“《大学集注》‘格’亦训‘至’,‘物’亦训‘事’,惟云‘穷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穷’字、‘事’外增‘理’字,加一转折,变为‘空理’二字,遂与实践迥别。”阮元注重的是在实践与经世层面阐发理学,“物者,事也。格者,至也。事者,家国天下之事,即止于五伦之至善,明德、新民,皆事也。格有至义,即有止意,履而至,止于其地,圣贤实践之道也。……格物者,至止于事物之谓也。凡家国天下五伦之事,无不当以身亲至其处而履之,以止于至善也。格物与止至善、知止、止于仁敬等事皆是一义,非有二解也。必变其文曰格物者,以格字兼包至止,以物字兼包诸事,圣贤之道,无非实践。”(36)为阮元称道的洪震煊(1770-1815),也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大学》第一义在先学习,招致所知以待物来而知其至耳”,“学习当居致知之先,格物实在致知之后,善恶之来,惟致知者能知之也”,“格物为身外之事,非有关于学问也,惟物之未来,我则学习招致所知,有以待之物;既来,我则知其善恶成败所至,而有以处之”(37)阮元、洪震煊以实学解《大学》,强调认知上要博学,价值取向上要践履五伦,这无疑是想将宋、明儒形而上学的思辨转变到普通百姓的日常体验上来。
乾嘉时期的汉学界,将《大学》回归《礼记》,并倾向于越过宋学对《大学》的诠解,实现了《大学》从《四书》之学到《礼记》之学的转变。回归《礼记》,即要重视《大学》古本,将《大学》视为礼学的一部分。认为格致传不用补,朱子改经之法不宜行,势必会在义理上,与程、朱理学的说解有所不同。一方面,汉学家强调汉、唐《大学》注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普遍重视“絜矩”之道,强调经验世界的伦理秩序,在《大学》的“三纲领”中,解“明明德”为崇德。在“八条目”中,不论心、意,将格物与修身相连。修身,在于五伦、五常的道德范畴的实践,通过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絜矩之道,实现家、国、天下同治,这与宋、明理学的《大学》说明显不同,见证了清中叶儒学思想的转型。
值得说明的是,时人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对藏琳、毛奇龄、李塨、戴震、阮元等汉学家的有关《大学》诠解,追根溯源,一一辩驳,坚守程、朱理学的立场,“此之宗旨,盖欲绌宋学,兴汉学,破宋儒穷理之学,变《大学》之教为考证之学,非复唐、虞、周、孔以礼垂教,经世之本,并非郑、贾抱守遗经之意”,“以注疏名物制度破宋儒格物穷理之学,此论出之最后,最巧,最近实,几于最后转法华”(38)。方东树强烈的门户之见,影响了他对学术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不过,从理学家的角度而言,宋学说汉学“变《大学》为考证之学”,虽失之偏颇,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毕竟,经典的意义在于阐释。乾嘉学者众多对《大学》文字的考证,的确解决了不少训诂上的问题,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但是缺少对《四书》义理的整体把握。到后来的陈澧(1810-1882)(39)、朱一新(1846-1894)(40)调和汉宋之说,在承认朱熹义理的同时,也庚续了乾嘉诸儒的《大学》诠释思想,对待《大学》已是汉宋兼采。
注释:
①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自序》,《郭嵩焘诗文集》卷三,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4页。
②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等著述,对此一时期的经世思潮有所说明。参见周积明、雷平在《清代经世思潮研究述评》中的论述,《汉学研究通迅》(台湾),2006年第25卷第1期。乾嘉新义理学,指乾嘉时期主流社会文化思潮。其主要内容包括:力主达情遂欲,反对存理灭欲;力主理气合一,反对理在气先;注重实证、试验、实测以及行为效应的社会功用,摒弃“言心言气言理”的形上性理之学。由于如上范畴皆与宋、明“义理”学对立,故称为“新义理学”,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内含有“近代指向”的重要思想范型。参见林庆彰、张寿安编《乾嘉学者的义理学》,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3年版。
③冯景:《解舂集·大学问答》,阮元、王先谦编:《清经解》卷206(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86页。
④陈确认为《大学》首章非圣经,其传十章非贤传,“言知不言行”,是禅学无疑,“弗如黜之”,参见氏著:《大学辨》,载《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⑤姚际恒著《九经通论》,中有《礼记通论》,今多亡佚,有关《大学》部分,幸为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所引。
⑥崔述:《〈大学〉非曾子所作》,《崔东壁遗书·洙泗考信余录》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374页。
⑦江永:《群经补义·大学篇》,《清经解》卷259(第二册),第270页。
⑧参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5“戴震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页。查文献目录,戴震有《大学补注》,可惜未传,现可见者为《中庸补注》一书。
⑨《经考》附录卷四《二程子更定〈大学〉》条,《安徽丛书》(册六)《戴震全集》丛书编印处,1932年刻本。
⑩《经考》附录卷四《变乱〈大学〉》条,同上。
(11)戴震《经考》、《经考附录》,博引众说,间加按语,经余英时先生考证,二书为戴震早年著述,是入都前的作品,下限大约在丁丑(1757年),上限在至少己巳、庚午(1709-1750年)已成卷帙。大抵戴震学术,有几变,在后期,对程、朱义理批判较多。参见余英时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8页。
(12)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2页。
(13)雍正间治礼记学者姜兆锡(1666-1745),认为《中庸》之性命道教、《大学》之纲领条目,皆源于三礼。换言之,《大学》必须回归到《礼记》一书,和三礼并论,这和宋明《四书》概念已完全相反。与乾嘉以后学术思想之走向并观,姜氏此语,暗指着康雍间的学风变化,确是有迹可寻。参见张寿安《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14)《四库全书总目》,第176页。
(15)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16)参见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大学篇》的论述,今有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17)徐养原,字新田,又字饴庵,浙江德清人。初,阮元抚浙,筑精舍西湖上,选高材生数十人讲肄其中,养原及弟养灏与焉。又集诸儒校勘《十三经注疏》,养原任《尚书》、《仪礼》。著有《明堂说褅郊辨》、《井田议》、《饮食考》、《周官五礼表》、《五官表》、《考工杂记》、《尚书考》等。
(18)李惇,高邮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深于经传,曾与王念孙、贾田祖同力于学。又与任大椿、刘台拱、汪中、程瑶田等有交谊。晚好历算,得宣城梅氏丛书,尽通其术。著有《群经释小》、《古文尚书说》、《左氏通释》等。
(19)徐养原:《格物说》,《清经解》(第七册)卷1388严杰补编《经义丛钞》,第849页。
(20)李惇:《群经识小·大学中庸》,《清经解》(第四册)卷722,第866页。
(21)惠士奇:《大学说附录》,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00页。
(22)段玉裁:《经韵楼集·在明明德说》,《清经解》(第四册)卷662,第529页。
(23)惠栋:《九经古义·礼记下》,《清经解》(第二册)卷370,第772页。
(24)金榜:《礼笺·大学》,《清经解》(第三册)卷556,第838页。
(25)孔广森:《礼学厄言》卷五《致知在格物》,《清经解》(第四册)卷696,第783页。《礼记·哀公问篇》原文为“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
(26)汪中著,王清信、叶纯芳点校:《大学平义》,《汪中集》卷一,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发行,2000年版,第66—67页。
(27)方东树:《汉学商兑》,钱钟书、朱维铮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28)凌廷堪的礼学思想,以及对乾嘉学者的影响,参见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一书,此处所引,见该书第182页。
(29)凌廷堪:《慎独格物说》,《校礼堂文集》卷十六,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19页。
(30)程瑶田:《论学小记上·诚意义述》,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42页。
(3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大学论》上,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64页。
(3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读大学》,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00页。
(33)焦循:《雕菰集》卷九《格物解一》,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92页。
(34)焦循:《雕菰集》卷九《格物解二》,第193页。
(35)焦循:《雕菰集》卷九《格物解三》,第193页。
(36)阮元:《大学格物说》,《古揅经室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6页。
(37)洪震煊:《格物说》,《清经解》(第四册)卷1388严杰补编《经义丛钞》,第849页。
(38)方东树:《汉学商兑》,第294—295页。
(39)陈澧以格物,是亲历其事,兼读书言之,“《大学》后世所谓理学,古人则入礼记”,“格物致知,犹言实事求是”。“朱子之补《大学》,不必补也,然所被之说,则无可议也。”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第174页、第176页。
(40)朱一新批评解《大学》者,先入为主,以己意得解,又批评汉学家解《大学》看似用注经解字之法,实也是阐明自己之观点,他说:“穷理之功,在明善以复其初,而吾心自以为明,未必合于人心之同然,不得谓之明也。故当博文以求圣贤之旨趣,随事随物,义理见焉。若析义未精,而先立一定见,则往往误于意见而不自知矣”,“格物本无的解,程、朱亦不免添字释经。然其言则极纯无弊”。朱一新著,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6—148页。
标签:大学论文; 礼记论文; 四书论文; 读书论文; 理学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朱熹论文; 中庸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