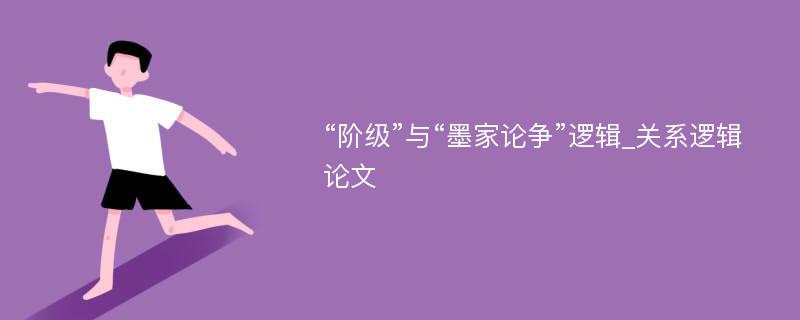
“类”与《墨辩》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墨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2359(1999)06—0021—02
“类”在中国思想史中渐进稳定的有两层含义:一是“事物之类”,二是“认识之类”。前者是物性本身之异同,后者是对物性认识的异同及认知的方法、原则之异同。墨家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以“事物之类”为基石,对“认识之类”进行辩说。《墨辩》谈“类”是从认知之理则角度上展开的。
一、类与举“名”
“名”作为中国古代逻辑中的基本范畴,指思维之基本单元、概念,亦指语言之基本构成要素:名词,与“实”相对。墨子深入考察了概念之名与实的关系,批评“攻伐并兼”的诸候“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非攻》)。后期墨家将概念之“名”与言辞之“名”进行统一研究,认为“声出口,俱有名”(《经上》),名的作用在于“举实”(《小取》)。有了名便可以“言犹名致”(《经上》),“知其所不知”(《经下》),从而“摹略万物之然”(《小取》)。名要摹略万物,则须对万物先进行异同别类,即“以类取”,取此择彼,使其有相同物性之物“类聚”,并“告以义名”(《经说上》)。这是由物到名的思维取向,继之墨家又对名进行分类细究:
名:达,类,私(《经上》)
“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藏”,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经说上》)
“达”,通也。通所有物之名则是反映最普遍共相的哲学范畴。故对所有物之实予以“达名”命之。“类”,同也,似也。相同、相似之物亦以名示之。因此“类名”则是同类之名,是外延为多的普通概念。“私”,所固有也,亦可用名举之。所以,“私名”便是反映个体之物的单独概念。
显然,墨家对名的分类很得体要,由形而上向形而下延伸,这不仅穷其物类,而且名类分明,从而构成了立辞、辩说的逻辑基础。
二、类与立辞
辞,最早出现于《周易》:“辩吉凶者存于辞”,“系辞焉以断其吉凶。”(《系辞上》)可知辞是对思维对物象的断定。孔子认为:“辞达而已矣。”(《论语·季氏》)辞为思想的语言表达。因此,辞便有双重含义:一是思维运作的基本形式:判断;二是思维表达的基本形式:命题。两者虽均属逻辑学所研究的对象,但在《墨辩》之前,尚未作为逻辑的专门术语研究之。
墨家立辞是出自辩说之需要。《小取》云:“以辞抒意”,可理解为辞是展示意见,想法的一种辩说形式。《大取》又云:“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这里所谓的辞,亦是立辞,论证。立辞之法则是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故”是成辞之因,理是成辞之法。而同因、同理立辞则必同类。同类便可相比、相通,通而行之,思维便可流而转廻,论证便可密无隙。故,“辞”在《墨辩》中作为一专门的逻辑术语、思维的基本形式进行探讨。
《大取》所确定辞的逻辑含义是以“察次比类”为根据的。《墨辩》对“比”有严格规定:“仳(比),有以相樱,有不相樱也。”(《经上》)“异类不比”(《经下》)。樱,容也。同类事物尽管有差别,但有相樱之处,故可比。比,便是比较同类事物的相樱(同)与不相樱(异)之处。异类,例如:木与夜,智与粟,无相樱之处故不可比。由此可看出,墨辩的立辞是以物类为基础,表现出其朴素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立场。《墨辩》作为“辩说”之经典,既有理性之演绎,又有感性之归纳。前者以它的立辞之据:“类”、“故”、“理”为代表,后者以它的列举十三类辞例为明证,细究这十三类辞例的论证,皆可看出其“类取、类予”的思想,皆用类比的方法,修辞也皆采取“其类在……”的形式。例如,《语经》云:
故浸淫之辞,其类在鼓粟。
或寿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类在誉名。
……
《墨辩》还深入到辞的内部结构,对主、谓词之间的联系、量的关系、辞所断定的或然性、必然性、时间性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与科学的分类,共列出尽、或、假,正、宜、必、且然、已然、方然九类判断。释墨诸书对此均有评述,本文不再赘述。
《墨辩》是在百家争辩中对“狂举”、“淫辞”的辩驳中日臻成熟的。面对庄周将一切物类的同异差别都抹煞掉的“齐物论”,公孙龙是将所有物种的差别绝对化的,“白马论”墨家立足客观事物的同类与异类,对这些“无类逻辑”进行批判,使“类”概念在“举名”与“立辞”中达到了事物之类与认识之类的初步统一,确立了其逻辑起点与逻辑中介的地位。
三、类与辩说
春秋时期,邓析“操两可之说”教民兴辩,开创了先秦二百多年的辩说局面,使“辩说”具有推理、论证、反驳三义。由于受到“无类”之影响,庄周对辩持有消极的“辩无胜”的态度。墨子却提倡:“能辩者说辩,能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由此看来,墨子将言辞之辩、认识之辩与事物之理合三为一,从而奠定了辩说的客观基础。后期墨家进一步将辩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活动加以系统的考察与分析,指出辩的理则是:“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小取》)辩的任务是:“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小取》)
“以类取”,类在此有三种含义:一是类似;二是类同;三是“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经下》),即同法则同类。例如,由矩成方,不问其木其石都属方类;由规为圆,不问其虚其实都属圆类。“以类取”,首先指“举相似”,举出类中已知个体,推出类中未知个体,其根据为同类相似。其次指“归类”,即从类中抽取个例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类之共相,其根据是同类一理。“以类予”便是以类取得到的共相为前提推予到类中其它事物中去,其根据是同类同法。“举相似”是个体到个体的横向的转移,“归类”是纵向的归纳上升,“类予”是纵向的演绎深入,这三种辩说方式均据类之关系而进行。
“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是墨家在辩说中倡导遵照的道德要求。同类之物自己认可则不能反对他人认可,自己反对则不能要求他人认可,类的同异仍是其客观根据。
辩有六项任务,其中“明是非”、“明同异”、“察名实”,属认识范畴,其逻辑递进关系为:先摹略万物之然,明了类同与类异,再察名实是否相怨,从而达到辩明否为是正名或狂举的目的。“审治乱”、“处利害”,则属实践范畴,以“是”或“非”来审国家的“治”或“乱”,由“治”或“乱”来处民众的“利”或“害”。“决嫌疑”则属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范畴,以论求群言之比,以实践中的“利”与“害”来裁定思想中的惑和疑。在这里,不仅十分清晰地看出墨家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路线,亦可看出他们将“明是非”、“决嫌疑”作为辩说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目的,使《墨辩》终于从实践的论辩之需前进到认识中的求真之学。基于此,与别墨各家相比,唯有《墨辩》才能称之为“逻辑”。
对于辩说的具体形式,《墨辩》列出八种。直接表现推理的是:“或”、“假”、“群”、“侔”、“推”;直接表现论证的是“效”,直接表示反驳的是“止”。这就是辩说三义之例证。当然,三义相蕴,推理、论证,反驳相涵,无须细究其差别。但需审明的是,这些具体的形式均以沉淀其中的类之关系为它们自在的根据。
从上述的考察中,不难看出,《墨辩》逻辑中名、辞、辩的各种分类与界说,各种立辞的形式,各种辩说的方式均是类同、类异关系的展开与外化,类与名自在地一致与统一,类与辞是自为的一致与统一,类与辩是自在自为的一致与统一。因此,类可谓之《墨辩》逻辑的起点、终点与主线。
收稿日期:1999-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