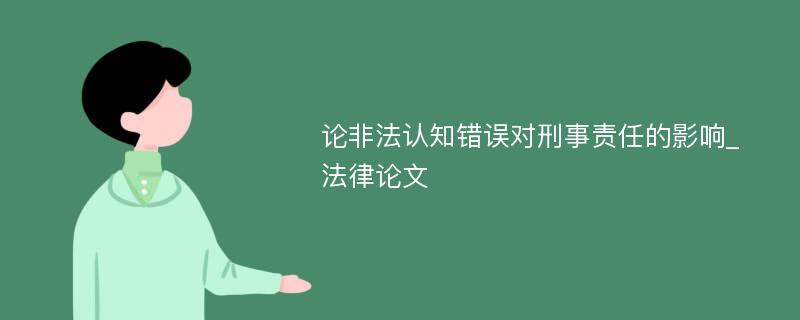
论违法性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事责任论文,错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欠缺刑事违法性意识,可否成为犯罪构成阻却事由,或者成为减轻刑事责任的理由呢?若对任何仅具备刑事违法的外观而缺乏违法性意识的行为都不加区别地追究刑事责任,是否符合刑事立法公正;谦抑的价值要求?反之,若容许欠缺刑事违法性认识可以导致刑事责任的减轻或免除,是否会降低刑法的权威性、阻碍刑法目的的实现呢?
上述问题值得任何一个反对机械的客观主义归罪原则的刑法学者深思,特别是在法令滋彰的现代社会,在与传统的道德原则并无实质联系的“法定犯”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在许多仍有其深厚土壤的旧的习俗和观念与体现时代要求的刑法禁止性规定剧烈冲突的严峻现实中,这种关注就更显示出其迫切性和必要性。
一、国外刑法理论中的违法性认识错误问题
国外的刑法学家们在论述中,大都认为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为法律所禁止,就应认定其具有“违法性意识”,而并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违反刑法法规。因此国外的刑法论著一般都对刑事违法性认识错误和普通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加区分,而统称为法律错误或违法性认识错误、禁止错误。
关于违法性意识与刑事责任的关系问题,国外学术界的观点大致有三种:
(一)消极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的承担不以行为人具有违法性意识为要素,因此对法律认识错误不能成为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的理由。消极说的依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1.一些学者试图依据罗马法中“不知法有害”、“不知法不赫”的传统原则说明法律作为客观的行为规范,明白易晓,为每一个具备生活常识的人所了解,因此不知法律或法律认识错误不能成为减免刑责的理由。但正如台湾学者林瑞富所指出的:“此说如适用于古代社会,其时道德与法律并无显著之区别,人民对简单之行为规范,咸知共守,固可自圆其说。至于现代社会,法令纷繁,虽司法之士,亦未必尽知,焉能期待人尽皆通晓,且法律为抽象之规定,常需间接推理,始能体会,是以法律之认识较之事实之认识,更为不易。则传统主张法律错误,不能阻却责任之理由,未能说明矣。”〔1〕
2.认为法律为他律性规范,其适用并不以行为人知悉为必要。若把违法性意识作为责任承担的要件,就会大大降低刑法的权威性。德国学者洛克思(Lucas )甚至耸人听闻地说:如果把违法性意识作为处罚国民的一般条件,就等于国家为轻率者、梦想家、狂狺者和愚蠢者提供了违反法律的通行证,就等于国家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权。〔2 〕该说所作的理论假设是:若允许法律认识错误可成为阻却刑事责任的理由,会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考虑到容易发生认识错误的犯罪并不包括那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类型,而且这种情况又不具有普发性。因此上述理由并无太强的说服力。
3.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不易证明,承认违法性意识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要件,就会给刑事司法带来困难。英国法学家奥斯汀(Austin)认为刑法对于法律错误不允许作为阻却责任事由与了解法律之难易无关,而是为了避免举证的困难。因为行为人认识法律与否及其精神状态,并非他人可以察知,若认为法律认识错误可阻却责任,法院将以何种标准判断行为人是否知法,颇成问题。坚持客观主义归责原则的美国学者林德格恩(Lindgren)也指出:若依据被告人的主观责任状况确定其刑事责任,我们能够确信他的陈述是真实的吗?如果对被告人主观心态的判断仍要由法官确定标准,能保证这一标准符合被告人的实际情况吗?〔3 〕该说无法回答的是:在对事实认知错误的案件中,同样存在难以证明的问题,为何人们一致认为事实错误要以阻却责任呢?
4.认为对法律认知错误对行为人主观上的可责难并无影响。法律规范社会生活,并非仅凭形式的力量予以维持,而是以其实质内容能否适合社会利益,为大众信守奉行,充分反映民族的风俗习惯与道德观念,凡是情势稳定国家的法律,都有其浓厚的社会观念基础,行为人做出违反刑法的行为即使意识不到其行为的违法性,也必能认识到其违反社会公益性,若犹顾为之,即已具备犯罪之心素,所以不能因不知法而减免刑责。〔4〕
5.刑事实证学派站在社会防卫的立场上,认为对行为人进行刑事追究系以其人身危险性为前提,而不以行为人具有违法性意识为必要性。但并非所有欠缺违法性意识的人都具有人身危险性。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中提及。
(二)积极说。积极说目前是德国的通说,在其他国家,也拥有众多的支持者。该说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可成为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的理由。坚持此说的学者的具体见解又各有不同,在此仅简介以下几种观点:
1.严格故意说。该说为德国的宾丁、贝林格,日本的小野清一郎、大冢仁等人所主张。严格故意说认为成立犯罪故意不仅要具备对犯罪事实的认识,还必须具备违法性意识。该说以道义责任为依据,认为具备了违法性意识,行为人就会产生抑制动机,避免实施违法行为,若行为人突破了该抑制动机而实施了违法行为,就具备了受责难的依据。但若行为人不具有违法性意识,就缺乏对其给予故意这种重的责任非难的依据。因此该说认为:欠缺违法性意识系不可避免的,可以阻却责任。若这种欠缺因过失引起,而该罪在刑法上又存在追究过失犯的规定时,应按过失罪处理。
2.限制故意说。该说为日本学者团藤重光、板仓宏和德国的麦耶等人所主张,认为不是违法性认识而是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是犯罪故意成立的条件。只要行为时存在违法认识的可能性,则阻却故意。该说把法律过失视同故意,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
3.责任说。该说为日本的西原春夫、木村龟二、平野龙一等人所主张,认为违法性意识的有无与故意的成立无关,而与期待可能性有关。在欠缺违法性意识系不可避免时,就不存在期待行为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此时应阻却责任。因过失而欠缺违法性意识的,可减轻责任。责任说目前在德、日刑法学界已有众多的追随者,并且德国法院也采此说。〔5〕
(三)自然犯、法定犯区别说。该说为日本著名刑法学家牧野英一所提倡。牧野认为自然犯的规定根植于大众所奉行的道德原则之中,因此犯此种罪的反社会性在行为本身中已经蕴含,无须再有违法性意识。而法定犯与社会成员咸知共守的道义观念并无实质联系,仅是出于某种政策的考虑才规定为犯罪的,因此构成此类犯罪应具有违法性意识。由于自然犯与法定犯并无明确的区分标准,牧野的这种观点也并非不存在任何问题,但他在讨论违法性认识问题时不采取一概而论的做法,而是在对犯罪类型做性质区分的基础上分别下结论。这种做法确有其可取之处。
二、我国刑法界对违法性认识错误问题的探讨
关于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内容,我国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为道德规范所禁止,就视为具有违法性认识。第二种观点认为只有认识到行为触犯法律,才算具有违法性认识。第三种观点认为只要认识到其行为为法律所不容许,就算具有违法性认识。〔6〕这种观点为很多学者所接受。
关于违法性认识错误能否成为减免刑事责任的理由,我国刑法学者也是各抒己见,依观点和见解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学说:
(一)否定说。该说认为犯罪故意的成立与违法性认识的有无无关,违法性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无丝毫影响。捍卫此说的理由有犯罪故意的成立只须有对事实的认识,否定无须有对违法性的认识;刑法的效力不以行为人知法为必要;承认缺乏违法性认识可减免刑事责任,就会为犯罪分子逃避惩罚提供借口;违法性认识是每一个有责任能力的人所应该具备的,所以没必要再把违法性意识列为故意的认识内容等等,其中比较有中国特色的论据有以下几点:
1.只要行为人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认识,就足以显示出其主观恶性,因此犯罪的成立不以行为人具有违法性意识为必要。有些学者把我国原刑法中没有违法性认识的规定作为立论的依据,指出刑法第11条仅规定了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便成立犯罪故意,可见故意的成立并不以具有违法性意识为要件。
2.认为我国目前有相当数量的法盲存在,在当前条件下,要求人们都明知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违法犯罪,从而将法盲排除在故意犯罪之外,是不现实的,是脱离我国实际的。〔7 〕“这种做法会鼓励人们不学法,不懂法,因为不懂法的人不承担刑事责任,懂法的人则会承担刑事责任,这显然不公平。”〔8〕
(二)肯定说。此说认为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是个人决定其作为或不作为的依据。知法而犯法的,表明行为人“对法有敌意”,国家便拥有对其进行处罚的依据。因此“不知者不为罪”不仅有其浓厚的观念基础,而且有其法理依据。在我国刑法界,最彻底和最毫无保留地坚持肯定说的是冯军博士,他强烈地抨击以社会危害性作为刑事归责的主观基础的观点,认为“在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认识脱节的情况下,只应该要求人们依据其行为违法与否的认识来决定其行为。在刑法的领域里,刑罚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公民唯一的行为依据。”〔9 〕对持否定说的学者提出的我国目前存在相当数量的法盲,采肯定说不符合我国国情的理由,冯军认为“法盲中的大多数在良心的看守下成为守法者。就是那些犯了法的法盲也有种种情形……对于法盲中那些由于教育环境的恶劣、物质生活的贫困等没能知法,不幸误犯了法律者,有什么理由不把他们排除在故意犯罪之外?”〔10〕针对持否定说者提出的采违法性意识必要说会鼓励人们不学法、不懂法,惩罚知法者而放纵法盲不公平的理由,冯军认为“至于说要求有违法性认识,就会鼓励人们不学法,甚至会产生不公平,也是片面的看法。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人们学法、知法、守法是为了保护自己……法本身的功能就是鼓励人们学法。为了保护自己,使自己不负刑事责任而不学法,只有哪些卑劣的人才做得出来,倘若真有这样的人,不妨宽容他一次,待他下次再犯时,就完全有理由重重处罚他。知法犯法者应比不知而误犯者负担更重的责任,理所当然,有什么不公平的呢?要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许有行为人自身的原因)没能知法的人,都承担刑事责任甚至是故意犯的刑事责任,实是过于苛酷了”。〔11〕
(三)基本否定说。此说认为“认识行为的违法性一般来说并不是犯罪故意的内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绝对化,不能排除个别例外的情况。如果原来并非所禁止的行为,一旦用特别法规规定为犯罪,在这个法律实施的初期,行为人确实不知有这种法律,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的,那就不应认为具有犯罪故意”。〔12〕既然承认在“个别例外的情况”下,确实不知法可阻却责任,为何违法性意识“一般来说并不是犯罪故意的内容”呢?例外情况下承认不知法可阻却故意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一般情况下违法性意识不被认定为故意内容的依据又是什么?有关的论著并未给出明确的说明。
(四)折衷说。此说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可否阻却或减轻刑事责任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人借鉴国外刑法理论中的责任说,认为违法展开性认识错误系不可避免时可阻责任,在存在违法认识的可能性时,只可减轻责任。也有人认为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缺乏认识并不影响成立犯罪故意,但只要这种缺乏是由于行为人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缺乏认识造成的,可以排除主观故意。〔13〕
三、外国对违法性认识错误问题的规定及对我国刑法应增设违法性认识错误规定的建议
最近几十年来,大陆法系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都放弃了对“法律错误不免刑责”传统原则的绝对遵从,而承认了违法性论证错误可以成为减免刑事责任的理由。1994年3月1日生效的法国新刑法典第122—3条增设了“能证明自己系由于无力避免的对法律的误解,认为可以合法完成其行为的人,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从而抛弃了法国刑事立法和判例长期奉行的“任何人不得被认为不知道法律”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再如1975年德国新刑法典增加了“行为人在行为时对其行为的违法性缺乏认识,而且这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得减轻处罚”的规定。
在英美普通法中,“不知法律不可恕”(ignorance of the law is no excuse),但当政府未能将制定的法律公布于众时或行为人违反法律是因为信赖官方对法律做出的后来被认为是错误的声明时,法院可以接受为可得宽恕的辩护理由(excuse)。〔14〕近年来,美国也确实有一些判例和制定法抛弃了“事实错误阻却责任,法律错误不阻却责任”的原则。
我国刑法中应否增设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规定呢?如果应该,哪种学说宜采纳?笔者认为:
首先,那种不加区别地坚持违法性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无丝毫影响的观点不可取。近现代刑法理论在摒弃了机械严苛的结果责任观后,一直强调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应成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不论是教育刑论者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矫正的强调,还是我国“双重预防论”中将犯罪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主张,都认为刑事责任的追究应服务于消除犯罪人的反社会性这一目的。当行为中体现不出行为人的反社会性时,刑罚的施加就是没有依据的。刑法旧派的报应刑论把犯罪看作是行为人违反了他与其他社会成员达成的契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是惩罚他自由地做出了这种错误选择,仍然是把行为人道义上的可责难性看作刑事责任的条件。在现代社会,是否任何缺乏违法性意识而在客观上触犯刑法的行为都具有道义上的可责难性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正如牧野英一所指出的那样,许多“法定犯”与传统的道德观念并无实际联系,普通人若不知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很容易以其为正当行为。其次,有些行为是否正当,应否为法律所禁止,连专家也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如安乐死行为,当行为人因不了解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善良地实施了这类行为时,对其做出有罪认定并科以刑罚不是太残酷了吗?再次,有些行为,如正当防卫、自救行为,实施到什么程度算正当,法律并未给出明确的标准,普通的人在紧急状态下,又如何总是能够正确地判断法律容许的行为限度?据笔者了解,对此类问题有些地方法院根据审判经验,制定有审判工作所依据的内部标准,有些法院则直接依据某种学理解释作为标准。这些标准都不具有公开性的特点,但却是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的依据。当行为人的善意行为违背了上述内部标准时,对其进行责难的依据是什么?且不说这些标准本身正确与否是不是值得探讨。可见,对某些缺乏违法性意识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并不符合刑事责任的基础理论。
那种认为只要缺乏违法性意识便一概可阻却或减轻刑事责任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特别是认为刑事领域刑法的禁止性规定是行为的唯一依据的观点就更应予以摒弃。法学界确有一些人对法律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就是把法律看作是国家对个人的承诺,〔15〕是国家根据不同行为危害性的不同而向行为人开列的一份要求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价目表,并认为只有这种承诺为行为人所明知,国家才能按事先规定的价格向其索酬,否则就不符合公正的要求。这完全是把私法中的原则硬套到公法中来。更何况,这种明码标价的价目表,其实也是不存在的,法律总是概括的、抽象的、滞后的,有时是具有不合目的性的。对好多行为将得到法律何种性质的评价,即使专家也未必能够给出准确而肯定的回答,又如何能够想象普通人能够有这种明确的认识呢?确实,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违法性甚至是刑事违法性有清楚的认识;有些情况下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违法性仅有概括的认识;还有很多情况下,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其意识中并无法律的存在,在总是把法误解为刑的人的心目中,法距离自己是遥远的,他们并不象某些专家们所想象的那样,总是习惯于对自己的行为做法律上的评价。对同一行为性质的评价,普通人平时想当然的看法与经过长时间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也不总是一致的。正因为行为人的反规范意识常常具有模糊性的特点,所以,按行为人违法性意识的性质确定其法律责任的想法,即使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中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而且,追究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而不是因为行为人故意地违反了他与国家之间所达成的契约,因此刑法要惩罚他的这种错误选择。某些学者天真地认为刑事责任的追究若不以行为人的违法性意识为必要,就会使人们在行为时无所适从,而采违法性意识必要说,就会大大促进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难道除了法律以外,人们就再无其他行为规范了吗?让那些明知其行为有害于他人或社会而犹为之的人逍遥法外,难道就有助于刑法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笔者认为,为恶的人没有同社会讨价还价的权利,只要行为人故意做出了明知是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国家就有权力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而不论其对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有何种认识。
认为社会危害性认识是成立犯罪故意的必备要件的观点,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适用。认识到犯罪的功能具有相对性的人,就会承认对有些犯罪类型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是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的。还有,“利他型犯罪”的犯罪人总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是有益于社会的,如某些基于一定的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而犯罪的人便具有这种认识。笔者认为,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认识,不是应从其反规范意识(这里所说的规范不仅指法律规范,也包括道德规范)中寻找。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为人们普遍遵行的行为规范所不容,而仍然实施该行为,即使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也仍然可以以为其具有蔑视社会规范的主观恶性,从而就具有了可罚性的主观基础。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
(一)行为人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对行为的违法性有认识的,不阻却刑事责任。
(二)行为人欠缺违法性意识,但认识到其行为违反道德规范的,仍不能阻却刑事责任。有些学者认为法律和道德毕竟是不同性质的规范,既然法律不干涉仅违反道德的行为,也同样应免除仅具有违反道德认识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其实,违反道德的行为和刑事违法行为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过去许多被认为“应提交道德法庭审判”的行为,现在不是已按犯罪处理了吗(这种改变甚至常常是在刑事立法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由于我国刑事立法过于粗陋简约,在审判实践中对许多行为确定是否构成犯罪时,往往也是根据其违反道德的严重程度的。
(三)行为人并未认识到其行为为法律和道德所禁止,而认为其具有正当性的,若这种错误不是因为过失所致,应阻却刑事责任。若行为人对行为性质的错误判断是由于过失所引起,可减轻其刑事责任。若行为人对行为性质的错误判断是由于过失所引起,可减轻其刑事责任。容易发生善意违法的几种情形,在上文中已做了分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可责难性,根据主客观一致的归罪原则,不应按犯罪处理。否则就会罪及无辜。
在不能因违法性认识错误而阻却刑事责任的场合,可否因欠缺违法性认识而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呢?笔者认为恶意违法和过失违法应分别做出规定。行为人为了达到非法目的,或出于钻法律空子的动机而触犯刑律的,其缺乏违法性意识并不能成为减轻处罚的理由。至于因过失而致发生法律认识错误的情况下应如何处理,前文已经论及。
四、附论:刑法的禁止性规定与落后地区的习俗、惯例发生冲突时的处理问题
美国学者理查德·戴格窦(Richard Delgado )在一篇研究贫穷与犯罪的论文中,曾提出过“文件隔离”可以成为辩护理由的问题。他认为某些在贫民窟中长大的青年,由于没有机会接触外部社会的观念、价值,从而就不能把外部社会普遍遵行的行为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观念。行为人因此而犯罪时,就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社会既然不能为某些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无权对其提出社会一般人可接受的要求。〔16〕在我国,电影《被告山杠爷》放映后在法学界引起的争论,也反映了人们对法律要求与传统习俗的冲突问题的关注。该影片中的主人公山杠爷是一个偏僻山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在村中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戴,把村子管理得也很好。后因村里有个媳妇不孝,经常打骂婆婆,在多次劝告无效的情况下,山杠爷令人将其游了街,这个媳妇由于深感屈辱,上吊自杀了。事发后,司法人员逮捕了山杠爷。对此,山杠爷困惑不解,他无法弄清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村里的人们也认为山杠爷的做法是对的。
对此,有人评论说司法人员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法律不能迁就某些人落后的观念。在法制发展的过程中,总要有人为之做出牺牲,唯其如此,才能把知法、守法的观念钢筋铁骨般打进民众的灵魂中去。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国家既然不能为某些地区的人们提供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为何非要把现代化的法制要求强加给他们,又有什么权力要求他们为法制发展做出牺牲?更何况,这种牺牲能否促进法制的发展,是否仅是一种没有收益的代价?
我们既然承认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既然承认一定的权利关系永远超不出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由这种经济关系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就应该承认,在当前我国还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的情况下,对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法律要求也不能是整齐划一的。对某些不具备法制实施条件的区域,应允许习俗和惯例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合法方式。在这些区域机械地司法只会损害法的形象。
所以,笔者反对刑法对落后地区的人们提出过高要求。对于依当地的习惯具有正当性而为刑法所禁止的行为,不应做为犯罪处理。因为人们只能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培养是非善恶的观念,只能从周围人都能接受的规范中寻找行为的依据。正象朱苏力先生所指出的一样:“我们应当指责山杠爷不懂法吗?可他为什么要懂那些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距遥远的正式法律呢,这些正式法律又给予过他们什么利益呢?〔17〕
总之,刑法不处罚欠缺违法性意识又不具有可责难性的行为人,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注释:
〔1〕台湾林瑞富:《阻却责任事由各国立法理由之比较研究》,台湾《刑事法杂志》第28卷第3期。
〔2〕〔9〕〔10〕〔11〕冯军:《刑事责任论》, 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3〕美国Lindgren,Crioninal Responsibility Reconsidered,(19876 Law and Philosophy)。
〔5〕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顾肖荣等译,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56页。
〔6〕参见刘明祥《刑法中违法认识的内容及其判断》, 《法商研究》1995年第3期。
〔7〕参见攀凤林主编《犯罪构成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第122页。
〔8〕张明楷:《犯罪论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127页。
〔12〕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页。
〔13〕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学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
〔14〕美Larry and Siegel Criminology,West Publish Company 1992,P60
〔15〕认为刑法是国家对个人的承诺,可以说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笔者认为承诺具有明确性、确定性的特点,而刑法则是一种抽象的、根据的规定,因此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承诺。
〔16〕引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刑法学参考资料《Topics in Criminal Law》P3009。
〔17〕参见朱苏力《现代法制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东方》199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