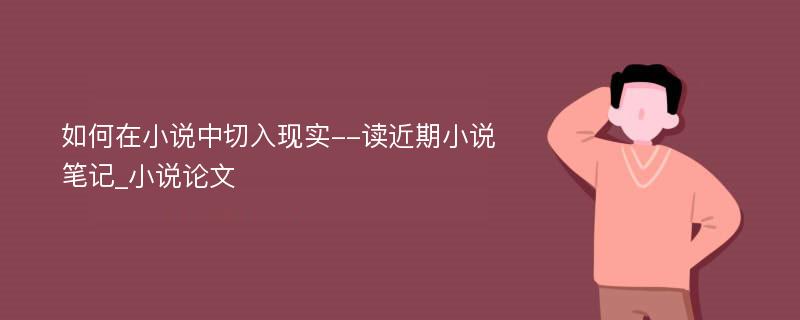
小说如何切入现实:近期几部长篇小说的阅读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长篇小说论文,几部论文,现实论文,近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真如亨利·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说的,“小说这种东西在正确观点的指引下,依然是最独立、最灵活、最奇妙的文学形式”①,那么人们在谈论这一文体时一再提及的“现实主义”,肯定就是“批评术语中最独立不羁、最富弹性、最为奇异的一种了”②。确实,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都是一个过于复杂的概念,对其详尽的探讨非笔者能力所及。因而本文只想就小说切入现实的方式,来适时地讨论近期几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问题。 小说的现实性,一直都是文学的古老命题。这也难怪,现实之于文学,总有一种天然的优先性;而小说对于现实,也有几乎命定的焦虑感。无数小说因为与现实事件的切近而获得讨论的价值,这是小说的社会学意义所在。而文学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力求在“及物”的写作中描摹世道人心,进而触摸现实议题,通过故事的讲述对社会问题进行“想象性的解决”,以此激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然而,小说究竟应该如何切入现实?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安敏成关于小说虚构的一个论断,“所有的现实主义小说都是通过维护一种与现实的特权关系来获取其权威性的。在现实主义模式的所有样本中都留有运作的痕迹。每一部新作都有权重构这一诉求,由此显示它对现实的独特把握。”③我们总是不能清楚地说出现实是什么,而只能说现实不是什么:它不是抽象的寓言,不是一览无余的新闻,更不是某种愤慨情绪的衍生品。而只能说,现实似乎是一种写实意义上的“似真幻觉”,一种显而易见的秩序的反省与重构,一种有着多重“褶皱”的神秘所在。因而对于现实的想象,也理应将小说的世界引向复杂,在诸种关系的考量中,妥善归置切入现实的具体路径和可能效果。 一、寓言/写实:现实的“主题”与“细节” 正如安敏成在《现实主义的限制》中所说的,“很多现实主义作品其实都运作于两个层面:一为对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层面。一为自觉的寓言层面。”④这种寓言与写实的区分,似乎可以分别对应达米安·格兰特所称之的现实主义的“内聚”与“应和”理论。在格兰特那里,“内聚”体现的是一种“觉悟的现实主义”,它所倚重的是“不靠模仿,而靠创造”,确切地说,是“一种运用生活材料、通过想象力调解使其摆脱纯事实性并将其移至更高层次的创造”,这也是安敏成所说的“小说的创造性生成”。在这个层面,作家会探索“写作形式的可能与局限”,进而“揭示作品内在的压力、缺陷以及作家在将素材纳入到特殊的形式建构的过程中必须闪避的陷阱”⑤。在此,寓言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创作方式,在顺利避开“真实性诉求当中的认识论盲区”之时,也容易落入某种建构主义的“陷阱”。因而就此来说,现实主义的“应和”理论所呈现的“认真的现实主义”,似乎才是小说叙述的基本态势,这也是前述“创造”得以顺利生成的基础。因为,“如果文学忽视或贬低外在现实,希冀仅从恣意驰骋的想象汲取营养,并仅为想象存在”,想象一种“游移不定、无视规则的能力”,那么现实的世界则势必落空。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就是以这种“认真的现实主义”精神,“希望把自己交付给现实世界,谦恭地向说教者敞开了大门;它用真实这一重物镇压轻佻的想象,使自己的形式、成规和严肃态度顺从陶醉于事实的心灵的净化。”⑥ 在罗兰·巴尔特那里,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⑦,这也就是昆德拉所说的,“表面是清晰明了的谎言,背后却是晦涩难懂的真相。”⑧而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学总是受着此种理论的蛊惑,在荒诞不经的现实叙事之外,希求通过寓言的捷径抵达彼岸的真理。这样的追求本无可厚非,也显示出与由来已久的“反映论”的思维定式进行卓绝斗争的努力。然而,倘若这种寓言的方式是以牺牲叙事细节的严谨为代价,那么小说现实世界的建构则会不可避免地落入岌岌可危的境地。这也是寓言与写实的矛盾所在。不得不承认,以写实的方式在总体性的意义上把握中国叙事的形式正在逐渐失效。这种情形下,如何超越日渐消隐的写实主义传统,从而获得一种新的表达,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通过最近几部乡村叙事的长篇小说,可以看出当代作家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在他们试图以“寓言化”的外在策略,超越既有的写实主义框架,使乡村叙事获得新的表达的时候,新的问题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我们知道,寓言具有一种言在此意在彼的特性,它在形式上是离心的,其结构呈现为一种不完整的、破碎的形式。既往的以表现“总体性”为旨趣的、向心性的写实已难以把握当下的内外现实,而寓言因其离心性、碎片性,其实更适于表现个体的现代情绪,比如精神的衰败等议题。借助寓言化的方式,叙事者可以获得将历史或现实生活加以荒诞、变形乃至扭曲的权利,或者用想象力“虚构”生活,改写、重构乃至消解传统的写实主义,进而获得一种深度模式和普遍寓意。这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方式。因此某种意义上看,寓言化是比较简单的,它相对于略显沉重的写实而言,又是轻巧的,甚至多少有些轻佻。比如阎连科继《四书》之后最新的长篇小说《炸裂志》,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寓言小说”,其宏大的政治批判,并不是在写实的意义上关切乡村。而是以“县志”的形式书写了一个叫作“炸裂”的山村,从村变成镇,由镇变成市,最后成为超级大城市的故事,进而通过这个村庄三十多年的历史变迁,叙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之路。正如阎连科所说的,“炸裂”的原型就是深圳,但小说并不因此而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历史表述,而是立足于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因而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讲述“中国故事”的小说。 就小说而言,《炸裂志》其实是从“改革元年”开始叙述的。这里有社会主义的失败,有人民公社化的解体,还有新自由主义的卷土重来,这当然是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图景。然而,小说最大的意义不在于细节的真实性,而在于一种荒诞不经的寓言性,它用一种“概括式”和“缩减式”的寓言叙事来囊括当代中国的整体形象,这无疑显示了作者的文学野心。在此,阎连科运用了当代作家通行的做法,即从一个村庄的变迁,来讲述当代中国的变化,这是从《创业史》到《古炉》的文学传统,而《炸裂志》也意在表明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借此对甚嚣尘上的时代主题,比如中国速度,中国模式等问题表达自己批判性的反思和忧虑。 《炸裂志》被人批评较多的地方在于要表现的观念太多,理念的先入之见等,这些都影响到小说的叙事态度。同样,关仁山的新作《日头》也在刻意追求一种显而易见的象征性。古钟、魁星阁和状元槐,这些都是日头村“文脉”的象征物,它们被认为是乡村文明的标识,作者为它们的消逝而忧心忡忡。《日头》还不乏魔幻的情节,比如会哭的杂毛狗,以及作为时代精神象征的红嘴乌鸦,都扮演着点缀作品“文学性”的重要功能。然而小说的魔幻部分还有些生硬,未能成为作品的有机成分,即这种贯穿在小说始终的可辨识的象征符号,使小说的意义变得过于明显。其中的问题在于,小说寓言的演绎显得太过粗略,而细节的编织似乎缺乏耐心,用雷达先生的话说,“作为小说,故事虽有波澜,但矛盾解决得过于轻易”⑨,以至于将小说写成了“中国故事”的粗略梗概,没能看出鲜活叙事中绵密的针脚和生动的韵味。另外,作者所运用的叙事元素其实也不新奇,无论是政治闹剧、家族斗争,以及时代荒诞的表现,都是同类叙事的常见情节。但作者却试图运用这些杂乱纷纭的叙事对现实进行饶有意味的概括,通过荒诞不经的寓言在“更高意义”上“把握”中国的内在实质。他过于刻意地将之塑造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中国故事”,即“日头村”在一个连一个的骚动中走向消亡的历史过程,以及极为宏大地书写一部当代农村文明史。而这巨大的写作野心,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又显得困难重重。事实上,作品也最终失之于细节的真实与情感的真切。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倘若没有细节的真实作为支撑,只有更高的精神追求、道义承担和主题升华,这样的叙事是否有效? 如果说《炸裂志》是当代中国发展主义的寓言,而关仁山的《日头》试图通过寓言的方式接续“传统中国”,那么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则更像是一则现代\后现代的身份寓言。这部小说以卡夫卡《变形记》式的开头先声夺人,人变成了老鼠,这固然只是现代主义的譬喻,却分明包含着异化结构中对于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揭示。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突破了惯常的叙事模式,以日常化、不乏戏谑的语言与纠缠不清的逻辑游戏,讲述了一个近乎荒诞的遗弃弟弟又寻找弟弟的故事。这个滑稽的过程,既是现代主义式的“寻找自我的历程”,又在现实意义上承载了社会百态、乡村剧变等关乎乡土前途与命运的忧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寻找”只是一个载体,既呈现出乡土文明崩溃的现实中现代人对土地的依恋,又在人性和逻辑恣意编织而成的荒诞空间中,展现了现代人对自我身份的焦虑。总之,作品折射出作者在文学创作上的自我突破与不断创新的追求,以及意欲打通哲学和现实双重世界的努力。 但在此情形之下,《我的名字叫王村》所呈现的乡村叙事反而显得简单,而无边的荒诞将叙事原本应该具有的生动细节巧妙地一笔带过。作者以乡村为名,讲述的却是现代人在荒诞的现代社会所遭逢的身份困境。因而乡村的故事只是虚有其表的外衣,并无任何实质的意义。小说之中,作者的情感投注与其说是指向乡村,关乎一位失踪者的尊严和艰辛,不如说是指向自身的,悼念的是现代个人面对这个世界时的焦虑和无奈。这也显示出作者的精英主义立场,她恐怕早已失去了感受真正乡村的能力,只能避实就虚地写作“借乡村的酒杯,浇个人心中的块垒”的现代故事,而绵密的日常生活在这看似格调高雅的叙事中早已失去了踪迹。这里的主要问题主要在于一种关切点的错位:自我与外部世界的错位,寓言还是写实的错位,也同时意味着“主题”与“细节”的错位。 当然,基于寓言的原则,展开主题先行,言在此意在彼的写作实验,这些也都没有问题,但关键是此在的世界,它也需要搭建得更为绵密细致一些,而不是为了突出地强调彼岸的寓意,而忽视此在的建构。因为多数时候,作品的气韵是在写实的过程中自然呈现出来的。因此,寓言的突显,叙事的神秘化固然重要,但如何将寓言与写实有效沟通却是当下写作,以及“小说如何切入现实”的一个大问题。 二、新闻/小说:现实的“表象”与“褶皱” 小说总是在模拟现实,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何种意义上模拟现实?是一味捕捉“表象”,“抄袭”现实,还是从现实出发,探索人性的“褶皱”,致力于文学擅长描摹的内心世界,这是小说伦理的严峻抉择。近年来,作家们对于现实的焦虑日益明显,这也集中呈现在几部以新闻素材为写作契机的长篇小说之中。由于经验能力的丧失和经验的贬值,当今世界的“个人化”被压缩到一个狭隘的生活空间之中。写作也沉迷在一种类似新闻性的表象快意之中,浅表却时尚的“街谈巷议”与“道听途说”甚嚣尘上。关于新闻与小说的关系,一度有人追问,“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如何开始”⑩,而新闻的“大”与小说的“小”,也是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如人所言的,“新闻事件不仅能够给作家带来灵感,同时也是作家拓展自己创作领地的重要外援。但是,是简单罗列或者图解这些新闻事件,还是‘深扎’进新闻事件的滋生土壤,挖掘到事件背后人物命运生成的必然与偶然?恐怕是对作家的一种严格考验。”(11) 事实上,以小说的方式,为新闻事件赋形,并将其纳入效果不一的艺术实践,是中外文学极为常见的现象。司汤达的《红与黑》便取材于一件情杀案的新闻;而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则源于一桩新闻报道的诉讼案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之中;甚至鲁迅的经典作品《药》,也是脱胎于徐锡麟行刺失败后被清兵生食心肝的真实新闻。如评论者所言,“时代的面影总是在新闻的惊悚中匆匆掠过,而时代的精神却可以在小说的幽深中长存。”(12)因而在此,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新闻取材本身,而在于小说如何以此为契机,将写作素材予以完美地消化,从而达到再造现实的艺术目的,由此呈现时代精神的“幽深”。 比如贾平凹的《带灯》就涉及了当今底层普遍的新闻景观:上访维稳、黑恶势力当政、灾害瞒报、超生罚款、牺牲环境的经济开发等。然而,面对人们已然熟悉的新闻事件,小说展现出的艺术创造力在于,它以强烈的生活质感照亮了新闻事件所寄生的人物世界。在此,乡村的世界显得自然而血肉丰满。尽管贾平凹的《带灯》不能说毫无瑕疵,但也与余华的《第七天》大异其趣。后者正是余华停笔多年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亦被认为是对现实展开“强攻”的作品,但正如人们所评价的,他所发现的问题只是流于新闻片段的拼接和微博热点的剪辑,总体上并不能令人满意。具体而言,《第七天》吸纳的新闻事件包括:上访、袭警、地陷、暴力拆迁、灾害瞒报、黑市卖肾、煤窑塌方、天价墓位、有毒食品、高官包养情妇……近几年的新闻热点都被纳入其间,这种“新闻串烧”也恰构成了一个万花筒式的当代现实世界。其中作者的激愤在于,小说里只有死人的世界才是没有贫贱、没有悲伤、没有仇恨的人人平等的所在。为此,这个平凡人“死无葬身之地”的故事,多少包含着一些“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弊病便不足为奇了。总的来看,小说流于一种浮泛式的现实描摹,贯穿其间的亦是愤恨式的情绪表达和寓言化的观念演绎,再加之小说章节之间的叙事并不流畅,情感难以衔接的弊病较为突出,这些都不免让人怀疑作者写作的诚意。 除此之外,马原的《纠缠》与《荒唐》对于新闻素材的处理,也显得不太高明。这位当年名噪一时的先锋作家,在重回“现实”之后相继推出了《牛鬼蛇神》等多部作品,虽都竭力体现出可喜的变化,但总体上并不能令太多的人满意。小说《纠缠》体现了作者在形式的迷狂之后把握当下现实的努力。故事以一个中产阶级城市家庭围绕遗产展开的各种争夺与纠缠为中心,呈现了这个以金钱为中心的“最坏的时代”。小说试图以“形而下”的姿态贴近日常生活,这一点与他过往的小说大异其趣,甚至与复出之后的《牛鬼蛇神》也完全不同。作品涉及城市生活的许多方面,机场、保险公司、法律条文等等,体现出马原小说难得一见的新意,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本人却仿佛与此有着一种刻骨的隔膜。这位当年的“先锋派”作家似乎仍未从昔日的荣光中回过神来,他始终无法清晰地讲述一个故事,因而他一再声称的日常生活也终究变了味道。这便犹如一个从来不屑于日常性的作家,突然有一天面对着如洪流般汹涌的日常生活时所展现的惊愕与无所适从。而事实上,这个一再声称的“更接地气”的作品,尽管也想竭力表达出现代生活的荒诞感,但他的刻意设计却并没有起到作用,故事情节设置和表现深度上的平庸与疲软一目了然,而所谓钱德勒式的“悬疑”更是被遍布的“狗血”桥段无情冲垮。《纠缠》之后的《荒唐》也同样平淡无奇。坦率来说,小说最大的问题在于为了增强话题的真实感,不惜破坏文本的虚构距离,直接在小说中引用一些话题性的现实元素,比如天价香烟、碰瓷、人肉搜索,以及李天一强奸案等真实事件,都被编织到了文本之中。作者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的印证,而非重新构造。 同样是对新闻片段的描摹与书写,薛忆沩的《空巢》则显得细腻而深入得多,其间的启示意义也意味深长。一直以来,薛忆沩都被郑重地视为“中国文坛最迷人的异类”,这当然得益于这位难以归类的作者,以其独特的哲学方式在小说世界里建构的“深度模式”。在多数人看来,薛忆沩的“不落俗套”意外地接续了先锋文学的余脉,而以小说的方式与存在主义哲学暗通款曲,由此在文本实验的征途上愈战愈勇,则是其对当代文学的主要贡献。然而,他那“迷人”的“异类”气质又不仅在于某种单纯的阐释乐趣,其独特魅力恰在“深度”本身所蕴含的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这种“内心的风景”所彰显的现实宽广度。 薛忆沩故事的现代主义色彩十分鲜明,他往往只抓取人物生活的片段,通过回忆和内心活动来扩展小说的叙事空间。《空巢》延续了这样的叙事风格,所竭力呈现的依然是复杂表象背后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相对于他以往的作品,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极为表象化的现实事件入手,切入到时代及其个人的精神肌理之中,触及的恰恰是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潜藏的“不安定因素”。小说讲述“空巢老人”这个流行的话题,它从电信诈骗这个司空见惯的新闻故事入手,却并不停留在故事表面,而是引出人物背后发人深思的东西。作者正是从这种常见表象和现实片段出发,来表达现实背后人们难以察觉的内心世界。小说通过一天之内的叙事时间,不断穿插主人公的记忆和个人独白,打开无穷的叙事维度,引出受骗者过往的回忆,一路走来的经历,生活的失败感,内心的屈辱创伤,以及满目疮痍的感觉。仔细读来我们可以发现,小说其实写的不是具体的事件,而是活生生的人,一个群体的症候,一代人的内心状态,以及一种刻骨的孤独与隔膜。在此,现实的表象只是一种呈现人物丰富内心世界的契机,而非小说所着力表现的对象本身。小说在此极为巧妙地将一种无法排遣、无处寄托的孤独体验,恰到好处地落实到一个极为流行的社会议题之上,从而极为从容自然地传达出寻常事件不同寻常的悲剧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空巢》尽管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但它关心的不是浅表的外部现实,而是个体生命的更为内在的真实,其叙事的野心由此可见一斑。通过对《空巢》的细读,我们也可发现,这与其说是一部虚构的“他者”的故事,不如说是作者对自我的重新书写。换言之,小说名义上是献给“所有像我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但它又何尝不是薛忆沩写给自己的人生箴言?就像他的作品所一再呈现的,那些无地自容的羞辱,尊严丧尽而又心有不甘的挣扎,以及最终宿命般自我毁弃的绝望,不正是每个孤独无助的个体面对这个巨大而空旷的世界时的真实写照吗?在这个意义上,薛忆沩的小说恰是自我的重建,是个体内心风景的见证。 薛忆沩的《空巢》让人想起以赛亚·伯林所分析的,“以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我们能潜入表层以下——这点小说家比受过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做得好——但那里的构成却是黏稠的特质:我们没有碰到石墙,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每一步都更加艰难,每一次前进的努力都夺去我们继续下去的愿望或能力。”(13)就此而言,《空巢》以现实的表象为契机,打开的其实是小说丰富的细部。这也超越了大众共识的庸常性,体现出作家个人发现的独特价值。或者换句话说,它在与社会新闻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从而确证了小说的力量。与此同时,也给了我们启示,“文学的魅力发生在与现实保持一定缝隙的距离之间。真正的思想深度、有限的思想深度,也只能从那些疏离现实的瞬间透示出来。”(14) 三、情感/理性:现实的“批判”与“重构” 小说以虚构的方式再造现实时,总免不了掺杂作者个体的情感介入,以此表明其对于社会现实及人性的理解和态度。因而当作者干脆以决绝的姿态,展开现实主义式的社会批判之时,这便难免会出现一些“操之过急”的情况。在此,基于社会现实的严峻,作者主体不可遏制的愤慨在带给人们情感震撼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摧毁小说世界本应精心设置的美学建构。这就像鲁迅所说的,“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15) 这样的道理并不高深,但对于当代小说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克服这种“批判”的迫切性,使得愤慨的情绪得以平稳,乃至沉淀,进而在理性的规约下酝酿出新的美学冲动,在小说“重构”现实时发挥作用,都是小说在处理现实议题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此或可提及莫言写于1988年的作品《天堂蒜薹之歌》。基于特殊的情势与写作动机,莫言用短短三十五天的时间,一气呵成地写出这部“最不像小说的小说”。现在看来,那部作品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多少显得有些仓促和直白。过于朴素的“不平则鸣”之中毫无蕴藉地裹挟着作者难以释怀的激愤,甚至连他自己也坦言这是一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这种“意气用事”的“例外状态”在莫言整体创作中可谓绝无仅有。“在艺术的道路上,我甘愿受各种诱惑,到许多暗藏杀机的斜路上探险”,莫言如是说。显然,他将自己颇具现实关怀与政治批判的小说视为一条“暗藏杀机的斜路”。一方面,莫言在切近现实性的小说题材中承担着失却文学性的艺术风险;另一方面,他又在以某种程度上暴露太甚的“缺德”小说,承受着可能的政治风险。而在这种双重风险的自觉承担背后,可以看出作者喷薄而出的“郁积日久的激情”,这固然是对彼时小说过于“艺术化”,而“现实性”不足的有意反拨,但小说的意义仅仅止于那令人感念的热忱与情怀,却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近两年的小说之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等,皆有因情绪的太多激愤,其下笔之“狠”多少流于意气用事的味道。这些情绪偏颇所带来的先入之见的观念,使得小说呈现出某种“单向度”的倾向,而失却了“对话”的韵致。在此需要提及的还有广西作家东西的长篇新作《篡改的命》,这部颇受好评的作品其实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坦率地说,相较于经典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的荒诞叙事所刻意塑造的隐喻性与形而上意义,《篡改的命》显得缺乏必要的蕴藉。小说并没有保留东西过去小说的先锋痕迹,而体现出向世俗生活的切近。它更多依赖的是故事本身流畅的现实感所形成的吸引力,让人们随主人公命运的起伏感受现实的残酷与震撼,进而咀嚼小人物无尽的悲苦。尽管在这部小说中,东西以从容的姿态叙述平常故事,其一贯的底层立场没有改变,但从小说标题中的“死磕”“弱爆”“抓狂”“拼爹”等流行网络词汇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唯恐“落伍”的作者竭力显示自己“时代见证”的最佳方式。尽管这一切多少显得有些做作和轻佻,但好在批判现实主义的诚意终究令人感念。但问题也在这里,某种程度上看,小说的意义其实与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有些相近,仅仅止于那令人感念的热忱与情怀。 《篡改的命》将“屌丝”的命运问题放到小说的台面上予以详查,通过人物的命运流转,来讨论这个极为严峻的社会议题。但他又不是基于现实的浮泛式的描写,即他所说的“对人物进行素描”,而是不断围绕小说的主人公,在城与乡、贫与富、当下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对其完整命运的呈现和审视,使其成为“解剖我们生活的标本”,因而小说也试图呈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幽暗。小说总体上呈现出朴实,甚至略显笨拙的样态,这不啻是对于现实“强攻”的作品,所显示的并非才华,而是批判的愤慨与诚意。但就其小说而言,汪长尺的故事其实并没有给千千万万打工者的卑微与悲苦增添更多的新意。为了更好地塑造这个从乡间来到城市的布满失败主义遭际的“屌丝”形象,作者不惜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苦难都加之于他。在他那里,事情总是如人所料地变得越来越糟,那些流行的不流行的命运遭际,都集中到了文本之中:辛苦工作却遭遇包工头卷款逃走;无奈之中为了钱给“官二代”顶罪;遇到不公只能任凭警察的推诿偏袒;承受富人的阴谋与算计,乃至残暴无情……乡下人进城的常见表述,在这部表现底层命运的小说中得到了集中呈现。 东西似乎总是推崇这种“欲说不能欲哭无泪的悲”(16),他总是陷入深深的绝望感之中,进而将之归咎为社会。小说主人公那惊世骇俗的反抗所携带的“虚妄的激情”,也只是作者刻意突显的苦难叙事的独特看点,就此来说,他其实无力也无意探讨现实的复杂,更别说寄予解决的方案。当然,文学也从来不会奢求某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篡改的命》中将“篡改的命”“篡改”回来,其实只是一种玩笑式的情绪宣泄,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绝望式的“吐槽”。就这样,《篡改的命》为了达到这种极为难得的情感诉求,将现实问题之中的阶层(或阶级)叙事推到了极致,而其对于现实的再现终究过于切近,小说汹涌着事关现实的愤怒,并将之以荒诞的形式呈现,而弥漫全篇的也是一种缺乏理性的批判之情。 这种基于愤慨所展开的社会批判,其实本可以更为文学化的方式展现出来。比如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便借助了类型小说的元素,结构了一个社会批判的文本。它意欲“透视谜一样的中国”,进而切入由官场反腐所交织的人性扇面。由此可以看出,小说需要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才能更好地呈现现实神秘的肌理。 关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宁肯有着自己的主张。在他看来,在“个人化的现实”与“通俗的”现实之间划下界限,或许是某种解决之道。如其所言的,“文学不反映现实但勇于涉及现实才可能摆脱‘反映’的通俗现实的陷阱,以及与之相关的反映论的陷阱。现实不是文学的本体,对现实的超越才是文学的本体,这个本体恰是读者所要的‘区别’。”因此,“对于通俗的现实,回避不可取,反映亦不可取,惟有‘涉及’或许是文学的‘窄门’。‘涉及’免除了回避,同时,也是一种超越性的反映现实的方式。”(17)基于此,他的长篇新作《三个三重奏》尽管涉及了非常通俗的“双规”,但他写的却又不是现实中简单的“双规”,而是“尽可能地写得不像”,以“超幻”的方式为己所用,“重构”现实。 《三个三重奏》讲述国企总裁杜远方的逃亡之路,腐败官员居延泽的审判过程,以及坐在轮椅上的叙述人“我”对1980年代的追忆,这三者是故事上的三重奏,也象征着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而他们各自的爱情故事则是人性上的三重奏。三个三重奏,回响于三个时空,而权力则在此之间伸展、变形,既扭曲又充满人性张力。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叙事者“我”的位置。作为一位博尔赫斯式的“书斋英雄”,“我”身处被图书包围的世界,并不残疾却不愿起身,宁愿沉浸在自己狭小的空间里。这无疑是一个隐喻,暗示象牙塔里对外界充耳不闻的知识者形象。然而无能的知识分子,也毕竟要用他的方式切入广阔的现实世界。而事实上,现实远比想象的复杂。这是一个被金钱、权力与腐败围困的世界,就像作者自己所追问的,“权力腐败已经很深地侵入了我们的生活。这时就要自问,作为一个当代书写者,你有没有能力面对这个东西。”(18)在此,宁肯顽强地讲述知识者与世界的关系,显示了他独特的切入现实的勇气。小说并不以快节奏的故事桥段见长,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写权力与腐败,写犯罪分子的逃逸与被审查,写权钱性的博弈,以及审讯者与被审者之间的精神对峙。因而尽管它高度地“涉及”现实,但并不是声嘶力竭地去控诉,而是去呈现,用其独特的方式在故事的讲述中自然抵达,一切都显得绵密而富有韵致。正所谓“以虚写实”,把现实处理得超越了现实,但又在精神层面上高度真切,这种“重构”的方式或许就是宁肯所说的“超幻”的意义所在。 与《三个三重奏》中批判的沉潜与现实的重构相似,刘心武的《飘窗》也通过一次不同寻常的“上访事件”的独特讲述,成全了作者绝妙的现实主义批判锋芒,进而引向一种知识分子角色的重新思索。这些都显示出小说情感的迂回与叙事的经营。这种现实直陈式的批判与重构式的“涉及”,让人想起了阿甘本对所谓“当代性”的描述,在他看来,“当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更确切而言,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过于契合时代的人,在所有方面与时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并非当代人,之所以如此,确切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审视它;他们不能死死地凝视它。”因为只有保持距离,才能“死死地凝视它”,也只有保持距离,才不会被时代所吞没所席卷(19)。这兴许就是我们永远无法抵达,但却要“死死地凝视”的现实的奥秘所在。 米兰·昆德拉认为,“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在他看来,小说应该探索人的具体的生活,抵抗“存在的被遗忘”,因此他赞同海尔曼·布洛赫的固执理念:“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的存在的唯一理由。”这也呼应了昆德拉的另一个判断:“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20)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勘探这种现实的复杂。可另一方面,小说又是以叙事的形式对于现实片断与个体经验世界的缝合,以文学的方式营造的一种内在时空的幻觉。这也就像吉尔·德勒兹所说的,“写作是一个生成事件,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中,超越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内容。这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一个穿越未来和过去的生命片段。”(21)因此,小说也理应超越具体的现实,达致一种文学性的生命维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审视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发现一方面,小说家当然是要用“谎言”来展现“真实”,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虚构的“谎言”都能自动产生更高意义上的“现实”;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需时时警惕,并不是所有的现实都具有天经地义的美学效果,它需要以文学的方式予以经营和重构。因此无论何种叙述,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寓言的还是写实的,表象的还是细节的,批判的抑或沉潜的,作者全情投入的“深描”,以及极具美学意味的“重构”,才是小说中现实叙事自我更新的机遇所在。 ①[美]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亨利·詹姆斯文论选》,朱雯、乔佖、朱乃长等译,338—33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②⑥[美]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周发祥译,1、18—19页,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③④⑤[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⑦[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⑧[捷]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7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⑨雷达:《北国土地的灵魂及其变迁——读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日头〉》,载《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日。 ⑩饶翔:《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如何开始》,载《人民日报》2013年5月17日第24版。 (11)狄青:《新闻的“大”与小说的“小”》,载《文学自由谈》2015年第4期。 (12)申霞艳:《小说与新闻的惊悚之战》,载《北京日报》2012年7月12日第18版。 (13)[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林茂译,22页,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14)陈晓明:《文学如何反映当下现实?》,载《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 (15)鲁迅:《两地书·三二》,见《鲁迅全集》第11卷,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6)东西:《滑翔与飞翔》(创作谈),载《广西文学》1996年第1期。 (17)宁肯:《“涉及”现实的文学》,载《文艺报》2013年8月12日第5版。 (18)孙小宁、宁肯:《一个现实题材的非现实可能》(访谈),载《北京晚报》2014年11月29日。 (19)汪民安:《福柯、本雅明与阿甘本:什么是当代?》,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 (20)[英]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4、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21)[法]吉尔·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1—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标签:小说论文; 炸裂志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寓言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空巢论文; 纠缠论文; 第七天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