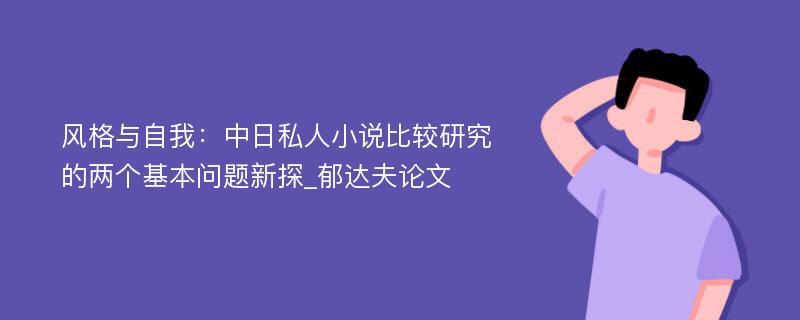
文体与自我——中日“私小说”比较研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中日论文,自我论文,两个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文体”和“自我”是中日两国私小说研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中日私小说之“私”(自我)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日本私小说中超时代、超社会、封闭的“自我”,在中国“私小说”中被置换为时代的和社会的自我;日本私小说中忏悔的自我,在中国“私小说”中被置换为反省的自我。“自我”的这种变异,决定了中国“私小说”不同于日本私小说的独特性质。
【关键词】 私小说 文体 自我
“私小说”作为产生于日本、影响到中国的一种现代小说形式,具有不同于其它小说的独有文体特征。研究私小说,首先要研究它的文体特征;而它的文体特征,又是由如何描写和表现“私”(自我)所决定的。因此,“文体”和“自我”既是私小说本身的两个基本问题,也是中日两国私小说比较研究中的两个基本问题。而这两个基本问题在中日私小说比较研究中还没有得到透彻的解决,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索。
一、流派与文体
私小说在日本有时被看作是自然主义流派的一种小说文体,有时又被看作是多流派共用的、超流派的小说文体。那么在中国,影响郭沫若、郁达夫等中国作家“私小说”创作的究竟是日本自然主义流派的私小说,还是一种超流派的、作为文体的私小说?
日本私小说起源于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它是随着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演变而逐渐形成的。中村武罗夫曾指出:私小说是“自然主义系统的最后一种小说”。[①]说它是自然主义的“最后一种小说”则因为在私小说产生之前,自然主义还使用过其它的文体形式。起初,永井荷风、田山花袋等作家摹仿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写出了《地狱之花》、《重右卫门的最后》等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左拉式的法国自然主义小说文体的移植。即使到了岛崎藤村的《破戒》(这部小说被认为是日本自然主义的第一部成熟的代表作)也还保留着左拉式的写实风格和较广阔的社会视野。直到1907年,田山花袋发表了中篇小说《棉被》,日本自然主义小说文体的独特性才开始确立起来。这部小说的特点可以归结为:⒈视野的收缩,由社会收缩到个人家庭;⒉私生活,主要是个人丑恶性欲的如实“告白”;⒊柔弱的笔调和感伤的抒情。由于它具备了以上几个特征,被认为是日本自然主义的私小说的滥觞。此后的自然主义作家,在创作上广泛运用这种私小说的形式,如岛崎藤村的《家》、田山花袋的《生》、《妻》、《缘》三部曲、岩野泡鸣的《放浪》等五部系列长篇小说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说,私小说是日本自然主义的典型的小说文体。然而,问题在于,受日本私小说影响的郁达夫、郭沫若等中国创造社的作家们,都曾明确表示反对或不同意自然主义文学观。如郁达夫在谈到自然主义所提倡的“客观描写”的主张时就曾说过:“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灭了。”他还进一步反问道:“左拉的文章,若是‘纯客观的描写的标本’,那么他著的小说何必要署左拉的名字呢?”[②]既然连自然主义的基本主张“客观描写”都给否定了,那如何还会接受自然主义的私小说的影响呢?这里必须明确,日本自然主义虽然是直接受到左拉的自然主义影响的,但日本的自然主义和法国的自然主义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在欧洲文学中,自然主义是作为浪漫主义的反动而出现的。相反,日本的自然主义却与浪漫主义保持了极为密切的关系。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失败,“大逆事件”后天皇政府对言论的严密控制,以及浪漫主义文学领袖北村透谷的自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未能充分发展就横遭夭折。在那种情况下,一批本来属于浪漫主义阵营的作家,如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田山花袋等,纷纷转向了标榜“真实”、“客观”的自然主义。但同时这些作家却也自觉不自觉地把浓厚的浪漫主义气质带到自然主义中来了。他们一开始就以浪漫主义的眼光理解(准确地说是曲解)自然主义。首先,他们把欧洲自然主义的客观科学的自然观,曲解为主观的自然观。如田山花袋在《作家的主观》一文中,就把主观区分为“作家的主观”和“大自然的主观”两种主观,并认为左拉和易卜生的自然主义就属于“大自然的主观”。他不久又在《太平洋》杂志上撰文进一步解释说:“我所说的大自然的主观,指的是nature发展为自然、天地的那种形态。由此推论下去,可以说作家即个人的主观中也就包含了大自然的面貌。所以,作家所使用的主观当然是能够同大自然的主观相一致的。”他由此得出结论说:“自我的内心也是一个自然。正如外部的宇宙是自然一样,自我也是一个自然。”“从根本上讲,自然主义完全具有主观的性质。”在这里,田山花袋彻底改造了欧洲自然主义的非自我、纯客观的性质;取消了主观自我与外在自然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正如片冈良一在《近代日本文学导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日本自然主义没有发展为泯灭作家主观的客观主义,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表现作家主观的工具。……他们没有达到彻底的客观,反而动辄长吁短叹,描写个人的伤感。”本来,主观性或客观性的偏重是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基本分野,日本的自然主义却以东方式的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观念,把主观加以客观化,从而将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互渗透、相互统一起来了。正如中村光夫在他的《风俗小说论》中所说的,日本自然主义对欧洲自然主义存有莫大的误解,它在本质上还是浪漫主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郁达夫虽然排斥自然主义,却不止一遍地阅读《棉被》,并对田山花袋表示赞赏了,因为归根到底,这种浪漫主义化了的自然主义和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是有共同之处的。在郁达夫看来,自然主义所标榜的排除作家个性的“纯客观描写”并不是真实的描写,真实是作品的生命,真实的描写必须基于事实,而事实又必须基于作家个人的经验和体验,所以他确信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一方面强调个性,一方面强调真实(而且认为事实即真实),这种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相混杂的文学观和日本的田山花袋等私小说作家的文学观如出一辙。
这种混合型的,或者说不拘于某一流派的文学观念,显然有助于中国作家从文体的角度接受日本私小说。因为私小说本身的发展成熟和演变的过程就是各种文学流派相互融合、相互积淀的过程。日本私小说不仅包容着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成分,也融合了大正时期日本文坛上各种思潮流派的各种因素。我们知道,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是在大正时期留学日本并走上文学道路的。那时,日本自然主义已是日薄西山了,文坛上出现了好几个反自然主义的文学流派,如主张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白桦派,还有唯美派、新思潮派等。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流派实际上已从文坛上退出,而与此同时,源出于自然主义的私小说却越来越成为一种为各种思潮流派所通用的一种纯文体形式了。白桦派的志贺直哉、唯美派的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新思潮派的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等,都写了大量的私小说。早稻田派的宇野浩二、葛西善藏还把私小说进一步发展改造为更注重表现内心体验的“心境小说”。到了大正年间,私小说实际上已经成为超越流派的共同观念了。也就是说,私小说已经成为为各种流派所通用的一种小说文体了。文体作为文学样式的高度凝炼,它本身就具有超流派性。就私小说来说,它脱胎于自然主义,成熟和定型于白桦派、唯美派、新思潮派等各种流派。郁达夫、郭沫若所接受的私小说,正是作为文体的私小说,所以他们对运用私小说文体进行创作的各种不同流派的成功作品都表示赞赏。据郁达夫自称,自然主义作家田山花袋、白桦派作家志贺直哉、早稻田派“新自然主义”作家葛西善藏、唯美主义作家佐藤春夫等人的作品,他都喜欢。他说过:“在日本现代小说家中,我最崇拜佐藤春夫。……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海上通信》)他称赞志贺直哉是“一个具备全人格的大艺术家”,“文字精妙绝伦”,其作品“篇篇都是珠玉”;他对葛西善藏备加推崇,对其作品“感佩得了不得”(《村居日记》)。可见,中国作家对日本私小说的接受是不拘于流派的,在创作上也杂糅了日本各文学流派私小说的诸种特点。在日本,每个不同流派的作家在各自的私小说创作中都有所属流派的主色调;自然派侧重肉欲苦闷的真实暴露和描写,白桦派追求个性自由、同情博爱的人道主义,唯美派则着意表现世纪末的忧郁和颓废,而在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有关作品中,这些特征都是兼而有之的。从根本上说,中国作家所接受的不是自然主义流派的私小说,换言之,不是作为某种创作思潮的私小说,而是对超流派的日本私小说文体的仿用。内容的自叙性、材料的日常性、风格的抒情性与感伤性、情节的散文化、结构的散漫化,构成了郁达夫、郭沫若前期小说的显著的“私小说”文体特征。
二、封闭的自我与社会的自我
文体特征是一种总体的、外在的特征。透过上述外在的文体特征,就会发现中日两国的私小说隐含着深刻的内在差异。这种差异归根到底是两种“自我”(“私”)的差异。对于中日私小说来说,自我是作品的核心,也是创作的根本出发点。而如何描写自我,如何表现自我,又取决于如何处理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换言之,“私小说”中自我的性质只能从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中才能得以定位。
在日本私小说中,自我是一种孤立于社会,或力图孤立于社会的一种存在。表现在小说的空间设置上,日本私小说的空间大都局限于个人的家庭和生活圈子。岛崎藤村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就曾说过:“我写《家》的时候,一切都只限于屋内的光景,写了厨房,写了大门,写了庭院,只有到了能够听见河水响声的屋子里才写到河,……运用这种笔法要写好这部《家》的上下两卷、长达12年的历史,是不容易的。”[③]这种不无得意的自白,表明了日本私小说作家的共同而又自觉的追求。而中国作家对这种封闭的小说空间在理论上不赞成,在创作上是不接受的。郁达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觉得那些东西(指私小说——引者按)局面太小,模仿太过,不能……为我们所取法。”[④]表现在合作上,同样是写家庭,写个人身边琐事,日本私小说写得内缩而又封闭,极少有意表现家庭和个人与社会和时代的联系,而中国的“私小说”却十分注意家庭、个人、身边琐事与时代、社会的关联。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行路难》都属于描写个人及家庭的“私小说”,但“局面”却并不小,从日本到中国,从中国到日本,足之所至,目之所及,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从创作主体上看,日本私小说作家是有意识地逃离社会,躲到文学的象牙塔中去的。伊藤整在《小说的方法》一书中指出:私小说作家是“实际生活中的失败者”,是由现实逃往文学世界的“逃亡奴隶”,其心理倾向是由社会上的“贱民”变为文坛上的“选民”,从而“弥补失落感”。他认为,日本文坛内部的人都是“为日本社会现实所不容的具有特殊意识的特殊生活者”,作家们“成了和现实社会无关的一种存在”。杉浦明平在《私小说》一文中也谈到了私小说中“自我”的超社会性的特点,即:与历史社会相游离;兴趣只在茶余饭后的琐事和自我的感想;不承担揭露社会矛盾的任务。道家忠道在《私小说的基础》一文中就断言:日本的私小说“不具有社会意识”[⑤]。在这方面,中国作家的有关作品与日本的私小说形成了鲜明对照。对郁达夫、郭沫若等中国作家来说,他们不是文坛上的“逃亡奴隶”,郁达夫、郭沫若当初在日本走上文学道路,“凫进文艺的新潮”,主要是受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感染,还有一个弱国孑民在异国他乡所遭受的耻辱,以及由耻辱所产生的爱国心。郁达夫、郭沫若最早的创作都是表达爱国情怀、抒发浪漫豪情的诗篇,早期的小说创作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写的虽然都是个人的生活体验,但他们是自觉地把个人、自我作为社会,作为“阶级”的一分子加以描写的。郁达夫说过:“我相信暴露个人的生活,也就是代表暴露这社会中的阶级的生活。”[⑥]从而保持着日本私小说所没有的浓厚的社会意识。和日本私小说一样,郁、郭两人的早期小说也都描写了个人的苦闷、孤独感伤以至病态的颓废倾向,然而,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切身体验,使他们把这些自我的情绪表现与时代、与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不像日本私小说作家那样一味在内心深处咀嚼着孤独与感伤。从个人地位境遇上看,日本私小说作家大都属于中产阶级(少部分人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一般都有一份较稳定的职业,在比较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的日本现代社会中,他们对社会有一定的认同感。他们的苦闷与其说来自社会的压迫,不如说更多地来自家庭、爱情、婚姻的不满和不幸(如田山花袋的《棉被》、岛崎藤村的《家》、志贺直哉的《和解》、谷崎润一郎的《异端者的悲哀》等);或源于个人行为的失误和性格的缺陷(如岛崎藤村的《新生》、葛西善藏的《湖畔日记》、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等)。但是,郁达夫、郭沫若等中国留日学生的苦闷和感伤,却是与国难家愁密切相关的。旅日时饱受生活艰辛和民族歧视,回国后又颠沛流离,饱尝失业、失意之苦,痛感“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这些,在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和郁达夫的《沉沦》、《茑萝集》等作品中都有细致的描写。我们在这些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到作者对不公正的丑恶社会的愤怒控诉和指责。他们常常站在社会批判者的立场上,把个人的命运遭际与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郁达夫的《沉沦》中哀叹祖国贫弱,把主人公的自杀归因于祖国的那段众所周知的结尾,以日本私小说的标准来看,自是“很不自然”的,但这正是它那强烈的社会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证明。在郁达夫的《茑萝行》中,主人公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人生失败和家庭悲剧归咎于社会,认为:“因社会组织的不良,致使我不能得到适当的职业,你(按指‘我’的妻子)不能过安乐的日子,因而产生这种家庭悲剧。“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现代的社会,就应该负这责任!”在郭沫若的小说《喀尔美萝姑娘》中,甚至当“我”一听说心爱的姑娘生病,就立刻大骂社会:“牡丹才在抽芽时便有虫来蛀了。不平等的社会哟,万恶的社会哟!”中国的“私小说”作家就是这样,他们敏感地意识到了社会的压迫,但并没有逃避社会,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声讨和抗争。正如郑伯奇所说,对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来说,“所谓象牙之塔一点没有给他们准备着,他们依然是在社会的桎梏中呻吟的‘时代儿’”[⑦]。
三、忏悔的自我与反省的自我
中国的“私小说”作家就是这样,把个人的痛苦和不幸归咎于社会、归咎于国家,而日本的“私小说”作家们却把国家、社会视为与自我无关的存在,他们不在自我之外寻找不幸的根源,一味在自我的心灵内部“反刍着罪的意识”(伊藤整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私小说”是“反省”的,而日本私小说则 是“忏悔”的。反省和忏悔构成了中日两国私小说的两种情绪状态。有人说郁达夫的作品是五四时期表现忏悔意识的代表作。诚然,私小说这种文体要求把自我的行为和心境真实坦率地加以暴露(日本人称为“告白”),它本身就具有忏悔或忏悔录的某些特点,但是,仅仅暴露自我并不就是忏悔。把中日私小说做一比较,这一点就更清楚了。日本学者荒正人、伊藤整、平野谦把日本的私小说分为“破灭型”、“调和型”两类。以表现以生存的不安、生存的危机感为创作动机的是“破灭型”的;试图克服这种不安以消解危机的是“调和型”的。从外部特征上看,郁达夫、郭沫若的“私小说”似乎是属于“破灭型”的。然而,郁达夫、郭沫若的“破灭”与其说是自我的“破灭”,不如说是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的“破灭”。换言之,这种“破灭”既不是自我忏悔后的不得解脱,也主要不是对自我的绝望,而是对社会、对时代的绝望。至于日本的所谓“调和型”的私小说,其忏悔就进一步带上了宗教性质。本来,“忏悔”这个词就是个宗教(佛教)词汇,严格意义上的忏悔必须带有某种宗教情绪。在谈到日本私小说的时候,丰田三郎曾经指出:私小说是佛教禅宗的艺术化,是“禅身的宗教”,“私小说的最高形式是对人生的祈祷,是对自然的精进斋戒,是向绝对者的皈依,是肉体的客观化”[⑧]。如岛崎藤村在《新生》中忏悔了“我”与侄女的乱伦关系,在这里,忏悔本身就是在自我中排斥非我,涤除虚伪,以真诚立身,忏悔的过程就是自我的超越、自我的修炼过程,是让有罪的“我”在忏悔后获得“新生”。同样,志贺直哉著名的长篇私小说《暗夜行路》中的主人公,面对家庭和爱情生活的一连串的打击,在山上病了一夜之后,忽然顿悟,“进入了广阔的泛神论的拥抱一切的境界”(山室静语)。这就是日本私小说的忏悔:忏悔者本身具有罪感意识和赎罪之心,忏悔者带有一种宗教的或“准宗教”的情绪,忏悔的过程就是求道的过程,忏悔后达到内心世界的净化和平衡。显然,在郁达夫和郭沫若那里,这样的忏悔是没有的。中国和日本不同,日本的私小说是在张扬个性的浪漫主义趋于瓦解之后形成的,对自我与个性的狂热崇拜已经降温,孕育私小说的自然主义所提倡的客观性原则有助于作家对自我与个性做较为冷静的反思。而在中国五四时期个性主义高涨的年代里,作家们相信个性、相信自我,远胜于相信社会与时代,个性和自我是他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是衡量一切的基本尺度。他们不是没有认识到自我与个性并非至善至美,但他们确信个性与自我的不完善不是个性与自我本身的问题,而是时代和社会的错误。显然,从这种对自我、个性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中不会产生真正的忏悔之心,而只能产生反省意识。反省体现了中国“私小说”作家的特有思维定势,那就是在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联系中反观自我,通过在社会中寻找个人行为、个人错误的客观原因,来减轻或转移自我的心理负荷。不是向内拓展自我的内宇宙,以求得淡泊、宁静和恬然,而是通过坦露自我,让他人理解、同情以至宽宥自我。正如郁达夫所表白的:“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我只求世人不说我对自家的思想取虚伪的态度就对了,我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⑨]在郁达夫和郭沫若的“私小说”中,当然也有自我谴责,尤其在描写到“我”的变态性欲的时候,传统的性道德与自我的肉欲冲动使得“我”流露出道德上的焦虑。如郁达夫笔下的“于质夫”就骂自己是“以金钱来蹂躏人的禽兽”;郭沫若笔下的“我”也自骂“该死的恶魔”、“卑劣的落伍者,色情狂,二重人格者”。然而,这些自责自骂并不是忏悔,因为在这种自责自骂的同时,又常常连带着自我开脱。如郭沫若的《喀尔美萝姑娘》、郁达夫的《沉沦》都把“我”的变态性欲及其痛苦归结于自己是一个被日本姑娘瞧不起的中国人。郁达夫还常常在作品的“自序”中为自己做辩护。在《茑萝集·自序》中,郁达夫有这样一段话:“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如此消沉时,郁达夫回答说:“……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⑩]这样的辩解,显然大大地消解了作品中的罪感意识,不是在人性本身、在自我本身寻找罪过的根源,而是把自我的罪过,人性的缺陷归因于外在的、非自我、非人性的东西。他们把忏悔所本有的内省性质给外向化了,不是谛观自我而是审视社会,因此他们不可能脱离时代与社会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纯人性的忏悔,而只能以忏悔的形式对社会做情绪渲泄,或是以忏悔形式进行社会批判。
注释:
①中村武罗夫《通俗小说的传统及其发达的过程》,原载昭和5年《新潮》1月号。
②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载《郁达夫研究资料》,王自立、陈子善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转引自枕流译《家·译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④郁达夫《林道的短篇小说》,载《郁达夫文集》第6卷第250页,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
⑤有关日本学者对私小说及其特点的论述,可参见胜山功著《大正私小说研究》,明治书院昭和55年。
⑥转引自许雪雪《郁达夫先生访问记》,载邹啸编《郁达夫论》,北新书局,1932年。
⑦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⑧丰田三郎《理想派与现实派》,原载《新潮》,昭和12年。
⑨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出处同②,第188页。
⑩郁达夫《北国的微音》,《郁达夫文集》第三卷,第91页。
标签:郁达夫论文; 郭沫若论文; 自然主义论文; 小说论文; 文体论文; 文学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沉沦论文; 棉被论文; 日本文学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