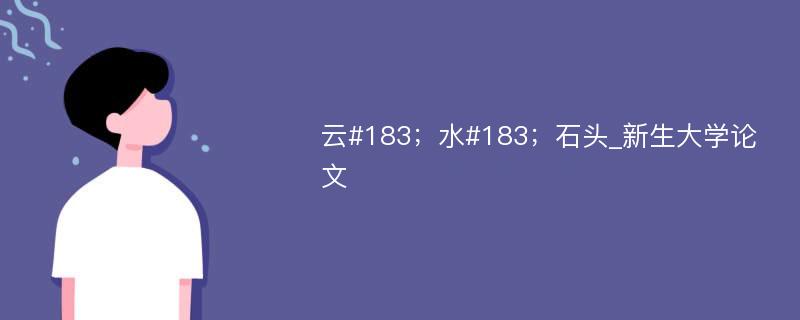
云#183;水#183;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68年春,出于偶然的机会,30岁的约翰·缪尔初次来到加利福尼亚州,欣悦于那里的原野、森林和群山。来年春夏之交,缪尔再度听到远山的召唤,于是协同牧羊人上山放羊,从山麓渐次上行,在加州东部的内华达山(the Sierra Nevada)里度过了整个夏季。山居期间所撰日记多年后经修改,于1911年成书问世,书名为《我在内华达山的第一夏》(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①了解缪尔生平事迹的读者明白,对于这位日后被尊为美国自然保护运动之父的人而言,那一夏影响至深,从此他以加州为家,甚至将内华达山视为自己的精神源泉。缪尔传记作者唐纳德·沃斯特把那一夏描述为“令缪尔终生追念、力求一再体验的悠长的狂喜瞬间”。②记载那不寻常的“悠长瞬间”的山居日记,或许能向我们启示缪尔精神源泉的某些内涵。我们不妨首先一读1869年7月27日的一段文字,当时主人公流连在约塞米蒂山谷(Yosemite Valley)上方的原野山湖,周围苍郁的山峦、嶙峋的巨石、远处晶莹的雪峰激发了心绪澎湃的几篇日记。走向泰纳亚湖(Lake Tenaya)途中,他觉得自己进入崇山之心的旅程正是回家的归途:每当我们试图聚焦某一物,就会发现它和宇宙间一切息息相关。我们不由感到一颗与人心同样拥有灵性的心魂在每粒晶体、每个细胞里跃动,于是我们愿意放缓脚步,与我们的山中伴侣花草鸟兽们一一交谈。我们的行迹愈是高远,大自然这位诗人、这位灵慧的匠人的形象愈加清晰,因为崇山就是源泉(the mountains are fountains)——初始之地,以某种方式与凡生无以知晓的本原相联。③ 这段话可以说是《第一夏》中一则核心表述,缪尔感悟到所有自然风物,包括人本身,构成了富有灵性的和谐,而此种感悟与登山经历密不可分。登山远足,使他感知塑造和谐现象的自然力,甚至可能让他隐隐亲近“本原”。围绕“崇山就是源泉”一说,④本文首先论述缪尔山居期间对自然界和谐的层层领悟,在此基础上,探讨此行在何种意义上成就了溯源之旅。 宇宙和谐之说由来已久,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奥古斯丁等思想家对此各有见解。他们基于自己关于宇宙音乐性或数学性和谐的感悟,转而沉思个体生命、社会伦理等其他意义上的和谐。⑤缪尔热爱的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中体现的大自然生命之同一性,可以看作和谐说的又一重演化。此说当然也遭到质疑,在缪尔度过青壮年时期的19世纪下半叶,质疑之声甚强。缪尔对大自然和谐的信念并不源自古典或基督教理念,浪漫主义文思对他颇具影响,而其他主要来源还得归于生活体验、博物学家式的实地考察以及灵性直觉。据他回忆,尽管自幼酷爱山野,大学期间的一次偶遇才让他顿悟大自然微妙的内在秩序。一天,一位乐于授业的同窗摘下一枝洋槐花,向缪尔逐一展示洋槐这种高大乔木的花瓣组成、花蕊形态、叶片分布乃至滋味竟与不甚起眼的草本植物豌豆藤全然一致。这位同学总结道:“植物学家只需观察花草即可知晓自然万物构成的和谐。”这意想不到的启蒙一课令缪尔欣喜,他回忆道:“此前,和别人一样,我也喜欢花,陶醉于花朵纯净姣好的仪容。而此时我双眼一亮,悟见了花的内在美,每一朵花都闪烁着神灵之思,由此将我们引向无限的和谐宇宙。”(139页)⑥缪尔顿悟的“内在美”超越了个体之美,参与并灵显着宇宙的和谐秩序。他从此潜心研究花草,数年之后,准备南下直至自己仰慕的德国博物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曾经远涉的南美丛林,通过考察丛林草木进一步探究“无限的和谐宇宙”。⑦此行并未让缪尔抵达目的地,而是辗转将他带入加州,翌年夏天在内华达山中,缪尔以诸多途径领悟到自然的和谐。 三个月里缓缓依山上行途中,倏然展现在旅人眼前的几处全景最直接地彰显了井然有序的天地。出发后第三天(6月5日),站在海拔三百多米的第一层高地上,只见:默西德河(the Merced)流域“马蹄弯道”一带的景象在眼前展布开来,这片辉煌的山野似乎唱着无数曲子发出召唤。前景呈现着线条干净流畅的山坡,松树与熊果丛如羽毛般轻覆其上,沐着阳光的林间空地错落其间;中景与远景则展现着精心塑造的层层丘陵与山脉,渐渐融入一带峥嵘的远山……视线所及之处,尽是一片起伏有致的苍翠之海……眼前景致在其主体轮廓与丰富的细部处理上同样精致,波光粼粼的河流在高耸的山崖间逶迤而行,每座山的褶皱都被雕刻得光滑得体,无一棱角,仿佛变质岩层微妙的凹槽凸脊接受了砂纸的精打细磨。这幅全景无疑是精妙设计的结果,宛如人类最卓越的雕塑作品。(158-160页)缪尔的眼光独具,此处可见一斑。“马蹄弯道”一带的景致成了拥有前景、中景和远景的画作,流畅的线条与光洁的表面、主体轮廓与细部处理共同构建了艺术和谐。原生的山野、静穆或动态的宏大全景很少以其磅礴或不羁直接博得缪尔的赞美。他称颂的是自己见证的和谐,也是自己的想象力给映入眼帘的世界创建的和谐。 7月15日,缪尔抵达海拔两千多米处,约塞米蒂山谷上方,他登高远眺,目睹了此行迄今所见的最为宏阔的内华达山诸峰之景。沿着山脊下行,缪尔俯瞰整个约塞米蒂山谷,再次礼赞他眼中的大自然刻意的整体设计与细部雕琢: [山谷]伟岸的岩壁被雕刻成种类纷繁的穹顶、三角墙、尖塔、雉堞,以及朴素无华的峭壁……平坦的谷底好似被装点成了花园,阳光普照的草地分布有致,松树与橡树聚集成一处处小树林。静穆的默西德河这条“慈悲之河”闪着波光穿行其间。(219-220页)几日后,在山谷上沿的北丘(North Dome)上写生的缪尔对眼前的画面发出如此感叹。岩石、树林与水流之间纤巧的和谐隐藏了它们恢弘的气势。千米峭崖上方密匝匝地覆盖着大树,好似青草铺满小山坡。这群峭壁之下绵延着一带十几公里长、一公里多宽的草原,却像一位农人朝夕之间就能割刈完毕的一段小草坪。数百米高的瀑布,由于依着巍巍峭壁而下,望去宛若青烟流云,尽管它们的声音充斥山谷,震颤岩石。(228页)⑧约塞米蒂的壮景,不失为伯克和康德的美学中所说的崇高之景或激发崇高之感的景观。可以想见,缪尔难免为这传奇山谷的浩大而感到震慑。可是,另一种冲动贯穿以上两段文字:缪尔的眼光有意无意地将狂野与浩瀚田园化,由此体会大自然的协调统一,使自己对崇高的敬畏从属于对和谐的称颂。 以上几段引文以全景式的画面集中体现了缪尔眼中的自然秩序,其间细节彼此相关并依托于整体,然而这部日记还展现了貌似独立、即兴、稍纵即逝的细节,不像壮阔的全景那么引人瞩目,却传达了观察者对自然之和谐更微妙独到的感受与创建。白日里,缪尔陶醉于种种野百合,赞叹山中天然百合园的完美;夜间露宿营地,他望见星空宛如一片百合盛开的原野(164页,207页)。观察某种小灌木时,缪尔感觉到其叶片分泌的蜡的气息协和地融入四下里松树辛辣的芳香(171页)。启程后不久的一夜,对远山满怀期待的旅人听到“夜风讲述着崇山的风貌,描绘那里的花园、树丛、森林,还有冰清雪滢的河川之源,风的音调甚至勾画着高山的跌宕绵延”(163-164页)。抵达高山地带之后一个结霜的清晨,缪尔感叹道:“这些寂寂深夜里,霜的形态渐趋完美超卓,每一粒晶体都像最恢弘的圣殿一般得到精心构筑,仿佛为了永存。”(292页)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偶然领受植物学启蒙到亲临崇山幽谷,缪尔所信的宇宙和谐以对应、协作、整一为特点,他不常关注或认可对立、矛盾、冲突这些在其他思想者眼里或可引致和谐、甚至于和谐必不可少的因素。 缪尔所见所悟的审美意义上的自然和谐,多半能打动读者,但他惯于强调的大自然生灵的和美生活,恐怕难以完全说服大家。鸟兽生存的艰辛看似罕见于他的早期文字,他鲜以悲叹的口吻描述世人眼中大自然的无常或灾难。在缪尔看来,人类为利益所驱的行为是干扰自然和谐的惟一因素。尽管在《第一夏》等作品中,加州群山被描绘成地上乐园,但缪尔其实并不否认或忽视自然界生灵面临的不测与艰难。他所信仰的和谐不等于道德意义上的完善,而更像一种超乎人类道德的广大神秘的秩序,其最基本的一点在于它不以人的利益为标准。譬如,说起我们称为毒漆(poison ivy)的植物,缪尔指出它对羊马无害,尽管时常伤及游人;他目睹毒漆“与它的花草邻居和谐相伴,好些漂亮的花儿信任地倚靠着它,享受荫凉与庇护”(166页)。“第一夏”行程将尽,在即将翻越内华达山之际,缪尔留意到严重的雪崩留下一片荒芜残败,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泥土流失,暴露出光秃秃的岩石,此时他不禁感慨于大自然看似无端的破坏。可是,继而在内华达山苍凉的东坡邂逅的秀丽山花,令他深切感悟荒凉与优美彼此依存,旅人于是总结道:“读着群山所展示的一页页非凡手稿——由无数次酷暑与极寒、安恬与狂暴、火山与冰川书写的手稿——我们会明白大自然的一切看似破坏的活动其实是创造,是从美到美的嬗变”,大自然“变灰烬为秀美”(288页)。看来此番经历正促使缪尔的和谐观发生变化,也许他开始意识到,对立与冲突于和谐亦不可少。 《第一夏》中时而出现的关于河乌(the water-ouzel)的描写,尤为生动地体现了缪尔对自然风物间对应以及同一性的观察与信念。⑨河乌并非水鸟,可是与水形影不离。缪尔所到之处,无论是芳草鲜美的原野,还是广漠苍凉的高山,只要有水,尤其是急流飞瀑,就能见到河乌敏捷的身影,听到它的啼啭。一如缪尔曾在夜风里感知高山地貌,他在河乌的吟唱中听见了流水的音韵。6月29日的日记里,缪尔首次描绘他当时尚不知其名、尽享“浪漫生活”的这位伙伴:“难怪它是个出色的歌手,昼夜不停地倾听溪流的吟唱。这位小诗人吸入的每一口气都是个音符,因为激流飞瀑四周的空气无不奏响着乐曲,它最初的音乐课准是在胎教阶段——当巢里的蛋随着瀑布的节奏轻轻震颤的时候——就开始了。”(190页)缪尔将河乌这位“小诗人”的歌声追溯到它的摇篮曲——山溪之音,不乏可比的先例。在1799年写成的《序曲》开篇,华兹华斯暗示自己的诗人之声,在某种意义上,源于故乡的德文特河(the Derwent): 岂是为了这一切, 那支最隽秀的清流爱将他的 喃喃低语汇入我奶妈的谣曲, 从赤杨的浓荫,从依石而泻的瀑布, 从津渡和浅滩,送来一个声音 伴着我的梦境流动?⑩看来,溪畔观鸟的博物学家和探求使命的《序曲》作者都领悟到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同本同源的属性,或者说同本同源的诗性。从上文引述的植物学启蒙一事已经可以看出,缪尔探究自然现象的动机不限于认识科学规律,而更在于加深自己对宇宙和谐的领悟。同样,从以上探讨来看,缪尔1869年夏天的山间所见,远不止科学观察所得,而同样是想像力所致。 缪尔乐于将他最奔放的想象寄予白云,寄予云与石、天与地的对应。盛夏午间,涌现长空的白云兆示暴风雨的洗礼:我们正接近白云与清流之国。正午前后,伟岸的积云出现在约塞米蒂一带上空,这组飘浮的泉源给瑰丽的山野带来新生。空中群山里,清泉从珠光莹莹的丘谷中涌出,惠赐荫凉,飘洒甘霖。没有一处山岩景观比这组空中岩石更为精致多变。云之峰峦腾起、壮大,如最精纯的大理石一般洁白无瑕、轮廓坚实,这一切不愧为创世之举的写照。(162页)积云在东边涌起。它们明珠般润泽的圆丘多么优美!与下方隆起的山岩又多么匹配。这片空中群山望去如此坚实,雕刻得如此精美……每日将近正午时分它们升腾、壮大,仿佛新世界正在创建中。(173页)今天的云之国仅一座孑然而立的雪山,可是光与影给予它丰富的面貌。硕大圆润的主峰、光洁饱满的山脊、还有此间的山坳与幽壑,都显现着妙不可言的色调。(187页)高山上空珍珠积成的云……这群浮云雪山——这至高至远的内华达山——每日的创建与消解,于我是个至上的奇迹。(194页)(11)又一个云之国。有时候云朵看上去过于成熟而略显衰败……内华达山仲夏午间的白云可不是那样……你会忍不住想攀登这群云山,追随从幽幽泉源飞流而下的瀑布。它们产生的雨水往往丰沛强劲,如山间落瀑一般拥有震慑力。无论远游何方,我都从未遇见比这些午间云山更为新鲜有趣的现象。(239页)缪尔的山间日记常常始于云景云思,有时寥寥数笔,像只是当日的气象记载,有时——如以上引文所示——则寄托了激越的心绪。上述几处描述中一再出现的三个共同点凝聚了这位观云者的灵思。从构图上看,缪尔着重揭示云景与他所处的山景、尤其是他向往并日益接近的高山景象之间的对应。崇山之上,飘浮着至高的崇山,同样层峦叠嶂,丘壑纵横。可以想见,这种日复一日戏剧性再现的天地平衡对应之态,于缪尔不啻为关于宇宙和谐的又一重启示。缪尔的“崇山就是源泉”之说,其中的一层涵义大概就在于此:回归神圣家园的山间朝圣者方能被赐予上述启示。此外,缪尔赞叹的远不止于云之国的静态构图,而尤其在于画面的动态性及其寓意。云山循环往复地涌现、壮大、消融,这才形成了缪尔崇拜的“至上的奇迹”;日日上演的创世之剧,或许暗示着创世并未结束,而在不断更新中重演?再者,横观全景、体察动态尚不能概括缪尔观云之举的全部,他似乎在找寻云山深处更新大地的“幽幽泉源”。如果说山是家,山是源,那么云可谓家之家、源之源,缪尔的白云颂仿佛寄托了对于某种更高深的本原的憧憬和探求。 前文已经提到,随着山行进程,缪尔对和谐秩序的认识趋于复杂。这一秩序并不表现为某一永久格局,而体现于普世的、每时每日抑或日久天长的运转变更。缪尔力图洞察、也乐于想象现象背后的过程,领悟现象本身所具的过程属性,这一属性给现象平添了一个含蓄的维度。例如,仲夏午后的雷雨中,云之国与山之国的交流交汇在缪尔笔下得到了富有童趣的表述: 追踪一滴雨的历程该多么有趣!我们已经认识到,从地质学角度看,雨水初临一无寸草的新生的内华达山,还是前不久的事。如今的雨水可是今非昔比!降临这片秀美山地的雨滴多么幸运……有的来到雪山,让充沛的冰雪泉源更为丰饶;有的滴落湖中,漾起水窝,吹出水泡,飘洒水花,轻拍湖面,浣洗群山之窗;有的汇入瀑布,好似切盼与之曼舞同歌,挥洒更精巧的飞沫……每一滴雨本身就是个高悬的瀑布,从云的悬崖低谷降至山的悬崖低谷,从云霄的雷鸣中来到山溪的雷鸣中。有的抵达原野和沼泽,悄无声息潜入花草的根须……有的降落在松林里,顺着松柏的尖塔而下,从闪闪的松针间播洒水花……还有些幸运的雨滴径直落入一盏盏花杯,亲吻百合的唇。(224-225页)这段引文中,缪尔用诗人的显微镜展现了自己心目中的自然过程之多样、有序、均变、统一。云滋润、更新着山,而山中之水蒸发升腾又凝聚成云。有时,缪尔则借助时间的望远镜去探究和想象辽远的自然史。譬如,细察散布在某个山坡上的一系列貌似永恒的巨石,缪尔从其各异的色彩和成分洞察到每一尊巨石都来自别处,来历久远而不一(210页)。对于云之国和山之国的联系,缪尔还以不同于前例的另一种眼光给予了揣测和遐想:关于云,可怜的凡人又能说些什么呢?每当我们试着描绘它们明灿的圆丘与山脊,幽冥的深渊与峡谷,还有轮廓柔和的沟壑,它们便消失得一无踪影,不留一丝残痕。尽管如此,这些瞬息即逝的云山同它们下方更为持久的花岗岩山一样实在和有意义。两者都被创建,也都将衰亡,在神明的历书上寿命长短毫无意义……我们应当欣慰地认识到,这些硬朗或轻柔的群山中,没有一颗水晶或一屡水汽的微粒会消失殆尽;这些山脉沉没或消融,仅是为了再度升起,从美升华到更高的美。(237页)缪尔关于大自然演变历程的认识,深受19世纪地质学说与生物进化论的启发,但与某些科学家不同,缪尔倾向于让科学观察与诗性想象相互融汇,着重于维护对自然过程之和谐的信念。(12) 以上讨论集中于缪尔在那不寻常的“第一夏”对自然现象和过程的灵思,我们不禁会问,其间缪尔对自身——无论代表个人还是人类——产生了什么样的新知?启程后不久,也就是目睹默西德河流域“马蹄弯道”一带景致的第二天,缪尔来到迎山而上两千多米的针叶林边缘,他这样描写初入森林的感受:我们置身山里,山来到我们体中,充满每个毛孔、每颗细胞,让每根神经震颤,点燃神圣激情。我们的血肉之躯(our flesh-and-bone tabernacle)有如玻璃一般通体透明,与周遭的秀美难解难分、相融相通,与空气、树木、溪水、岩石一同在阳光里颤动——我们成了大自然的一员,与之同样不老不少,既无疾病,也无健康,而是享有永生。这会儿我觉得身体好像天地那样无需呼吸和饮食。这是何等神妙的转变(conversion),如此完满彻底,以至于以往那些不自由的日子连给新生活提供对照的回忆都没留下什么!在这新生之中,我们好似一向感觉如此(In this newness of life we seem to have been so always)。(161页)这段话里,无一字符不颤动着神秘主义式的欣喜。缪尔用犹太教和基督教色彩浓厚的tabernacle一词来比拟身体,用时常意味着皈依的conversion一词来命名初入山林的体验。“Newness of life”这则日记中还将再现的短语,显然有意唤起圣保罗对基督教洗礼的著名阐释: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we too might walk in newness of life),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13)不妨说,此处缪尔将基督教教义“自然化”,以求揭示自己——以及在他看来所有人,如“我们”这一代词所示——初入森林之际脱胎换骨的神秘体验之本质。来到炼狱山巅地上乐园的但丁,并未在葱茏的圣林里欣悦若狂;升入超乎自然实体之上的天堂乐园,他方能享有如狂之喜。而缪尔在内华达山林这座地上乐园就体验了超凡喜乐,于他而言,天堂乐园即大自然这一地上乐园。很明显,缪尔在上文中表达的欣喜并非超越躯体的灵魂之乐,“每个毛孔”、“每颗细胞”、“每根神经”、“血肉之躯”等一系列词语无不凸现躯体感受。但这受福之躯已非原有的身体,而是幻变成了无拘无束、与大自然互融互通的全新实体,后者像大自然一样,既是自然的身体,也是圣保罗所说的“灵性的身体”。(14) 在经历上述转变后的缪尔眼中,大自然的永生在于每日每时的新生,而非永存不变。盛夏午后好似如约而至的雷雨,如前文摘录的雨滴赋所描述的,让他亲密见证了大自然新生的一种过程。这些过程不一而足:“让这片山野健康蓬勃,大自然花费着多少精力,倾注雨雪,降下露水,送来云彩,遍洒艳阳,让水汽弥漫,让风儿驰骋,创造各式各样的天气,使花草之间、鸟兽之间你来我往……简直超乎想象!大自然的手法多么不拘一格!”(226页)上述纷繁的过程既实现了、也象征着大自然的不断更新。整个山间夏季,缪尔本人可以说逐日亲历这样的更新。一天的漫步遐思、研究草木岩石、邂逅鸟兽虫蚁、写生记日记之后,星光下的睡眠却往往给缪尔死亡之感,7月14日的日记中出现一句概括性表达:“呼吸着山里的空气,睡眠多么像死亡,随着苏醒而来的新生又何等迅捷!”(214页)缪尔每每提到睡眠如死亡,都用平实的言辞语调,看来其目的仅限于传达实实在在的躯体之感,无意赋之以象征涵义。山居经历如此令他激奋,夜间的死亡之感恐怕难免让读者困惑。不过,随着昼夜更迭而发生的从死亡到复活的经历,倒像在演绎缪尔不止一次暗示的圣保罗名言。信徒“藉着洗礼归入死,同他[基督]一同埋葬”,为的是像基督一样重获新生;缪尔的切身体验在非基督教的层面上重演这一过程,藉着睡眠归入死,藉着复旦复归新生。 此处带有悖论色彩的核心思想,在于缪尔感到山间每日的新生持续不只一天,而成了超乎时间的永生,用前文引用的话说,“在这新生之中,我们好似一向感觉如此。”例如,进山后不久的一个清晨让缪尔觉得“我们这第一个纯粹的山中之日……仿佛无边无涯”(170页);日后他又感叹道,“这是些何等辽阔、静穆、无限的日子”(187页);六月将去,他感慨地回眸:“这个六月看来是我生命中最为浩大的一个月,它拥有最真实神圣的自由,它永生不朽,像永恒一般无边无际。”(191页)日复一日的新纯的永生,可以说构成了进入山野后缪尔的“转变”或“皈依”的核心内涵。如此永生,缪尔不认为仅属自己或人类,相反,他坚信这恰是自然万物的属性:“生命好像既不漫长也不短暂,一如树木星辰,我们不知匆忙。这是真正的自由,一种美好实在的永生”(175页);“山里的空气令我兴奋难耐,这个早晨我想像头野兽那样狂喜地咆哮”(204页);“一大早起身的时候,你会忍不住想像只公鸡那样放开嗓子啼叫”(213页);初见灵光笼罩的约塞米蒂山谷,缪尔“放声高呼,手舞足蹈”,令他的伴侣“卡洛这位圣伯纳犬好不惊讶”(219页)。从这些记载看,山中人缪尔意识到自己与草木鸟兽在本质上的亲和感,甚至几乎变成其中一员,恢复了原生之态。在此意义上,“崇山就是源泉”,山将人还原为自然一员,共享自然之不朽。此外,可以想见,静观白云之国的缪尔,也在那些日复一日的创世景象里获得关于大自然永新、永续、永生的启迪。 那么,是谁缔造了和谐秩序?是什么样的源泉让自然一再更新?如今为数众多的唯物论者和唯科学论者会觉得这是些多余的问题。于缪尔来说这些问题并不多余,反而可以说构成了贯穿这部日记的一条含蓄的主线,或者说上山之行的潜在动力。整部日记的引言初看像背景介绍,说明1869年作者得以在内华达山度过一夏的途径,也就是带着寻求夏季草场的羊群依山而上,直至“默西德河与图奥伦河(the Tuolumne)的源头——这个恰好令我向往的地方”(153页)。这两条河,还有圣华金河(the San Joaquin)与欧文河(Owen's River),为加州的主要河道,皆发源于内华达山的一带雪峰。大河之源于缪尔的意义,凭借此处的只言片语还难以体会。出发后第三天(6月5日),静观默西德河谷“马蹄弯道”一带的画面之际,缪尔听到“辉煌的山野似乎唱着无数曲子发出召唤”(158页)。山中乐曲也许来自鸟儿的呼鸣,也许发自滋润山野的清泉、激流、落瀑、河溪,也许只在旅人的想象中响起。我们可以联想到,《启示录》中,圣约翰将他听见的基督的声音比做“众水之声”。(15)缪尔探寻源流、倾听召唤的上山之行至此已隐约带有神圣使命的意味。此后旅途中,缪尔再度感受到登山是在响应某种召唤:在默西德河畔的营地度过一个月后,启程走向高山之际,缪尔听见“声声细语与午间雷鸣一同呼唤:‘往高处来’”(202页)。这“高处”会不会正是远山的圣泉?6月6日,也就是初入森林、获得脱胎换骨的新生之日,紧接着对神秘经验的记载,缪尔写道:“我的视线越过松林间的一片草原,见到约塞米蒂山谷上方默西德河源头所在的一带雪峰……它们发出的邀请何等热切!我会得以来到它们身边吗?我将日夜祈祷如愿以偿,可这看来美好得简直不可奢望。”(161页)这是缪尔在《第一夏》中首次描述自己远眺河川发源地所在的山峰,这群雪峰对他的吸引力,似乎尤其在于它们是源泉之地。描写初获新生与初见源泉所在的两个段落接连而至,兴许只是巧合,但是否也可能暗指自己的新生、大自然的永新与遥遥雪山里的大河之源密切相关?此处引文中对远山和源泉的热切企盼,以及此前业已传达的类似暗示,似乎在鼓励我们将缪尔的登山之行视为溯源之旅。 旅程之初表达的上述憧憬,不禁让读者期待缪尔随着登山之旅——特别是他亲临源泉之际——对发源地的所思所悟。盛夏之日,在泰纳亚湖畔他凝望着“遥远的南天下那诸多雪峰,河川之源泉”(243页)。夏季将逝,他登上达纳峰(Mount Dana):“沿着内华达山脉的主轴线南眺北望,磅礴的高山、悬崖、雪峰绵亘无尽,诸条大河源自高山雪泉,有的向西,经过著名的金门湾汇入大海,有的往东,流入灼热的盐湖和沙漠,蒸发升腾,迫不及待地回归天宇。”(294页)翌日,缪尔静观不寻常的彤云覆盖下的一带雪峰,一一列举发源其间的江河。数日之后,9月7日的日记这样开始:“天刚破晓就从营地出发,直奔圣殿峰(Cathedral Peak),打算从那里折向东南,来到图奥伦河、默西德河、圣华金河发源的山峰之间。”(298页)第二天,也就是启程下山前的最后一日,缪尔在日记开篇写道:“一整天都在图奥伦河与默西德河最高源头一带的山峰间挣扎攀行。”(303页)缪尔如愿来到了他数月前、或许更早前就热切向往的地方,可是,终于亲历源泉所在的缪尔,却一反常态,在这部工于描写、乐于抒怀的高潮迭起的日记里,既未描绘大河之源的面貌,也未付之于思绪,仅以上文引用的平铺直叙的寥寥几笔记载事实。这平淡的语言,或许说明这几处源泉本身对缪尔不具特别意义,仅仅标志着行程的目的地?也许,这组源泉恰恰由于意义深远超卓,令亲历者只能、且只愿以平实的记录和命名来寄托难以言表的感悟?源泉——河川之源代表的一切源泉——所激起的心绪恐怕的确超越了直接表述,除了上述揣测的方式,缪尔好似还借助了一种间接含蓄的手法让读者意会朝圣者在旅程终点、源泉之地的内心经历。9月7日来到雪峰之国后独自露宿时,旅人留意到两处细节。坐在篝火边写日记时,他发现身边的小水潭倒映着“无限星空”,浅浅水潭于是显得深不可测;营火照不到的黑暗中,传来自雪峰而下以汇入江河的诸条小溪的合唱(301-302页)。三个月前初入山地时,缪尔曾听到“辉煌的山野似乎唱着无数曲子发出召唤”,我们不妨将那“无数曲子”想象为此地、也就是源头近旁的水声合唱,这“众水之声”无异于来自源泉的召唤,而源泉本身,如映着无限星空而显得深不可测的水潭所示,意味着无限。星空、溪流、篝火以及正将这一切付诸文字的缪尔——这幅简约的山间小景成了由四元素构成的原型式画面,不乏基本的启示意义。这一刻,倾听水声的缪尔归入他追寻的源泉。显然,在星光下、水潭边、篝火旁写日记的缪尔,并不仅仅属于自然秩序,因为语言使我们有别于自然;然而,也正是缪尔的语言给读者重建山中家园,让我们感悟与自然共有的神圣源泉。 “大江流日夜”,高山雪原里的江河之源历来令人神往。水之源的象征内涵不一而足:生命源泉、宇宙原动力、万变之不变、神圣本原……内华达山的雪泉每每更新着河川,河川又一再更新着山野大地,这组源泉象征着不断更新大自然的更高源泉,实现着其意愿。如果说,据缪尔山间所悟,每一日的新生都带来永生,那么我们可以揣测,对缪尔而言,河流虽经大海、沙漠、云雨重返大自然的循环过程,但在某种属灵意义上它流向无限,也源于无限。本文开篇所引的一段文字中,缪尔仿佛预示着上述领悟:“崇山就是源泉——初始之地,以某种方式与凡生无以知晓的本原相联”,无限看来是此处所说的“本原”的属性。在伊甸园这个同样可被称为“初始之地”的地上乐园里,其河流不如其树木那么有名,但《创世记》中的几笔记载耐人寻味:“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又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绯拉全地的……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希底结,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16)从字面上看,“滋润那园子”的河起源于伊甸这片土地,但并不发源于上帝界定的乐园以内,不过这段经文的表述方式无疑会让读者将伊甸乐园想象为源泉之地,也就是滋养周遭土地、并在更广的意义上惠及四方大地的四道河之发源地,而此源泉之源泉,或许无异于通过那条未名河与乐园相联的、失乐园后“凡生无以知晓的本原”。(17)有如《创世记》中的伊甸园,对溯源的旅人缪尔而言,作为诸河发源地的内华达山也同样与某种至高本原相联,在此意义上,这一带崇山实为地上乐园,来到高山雪泉之间的缪尔返归故里。(18) 说起“凡生无以知晓的本原(sources)”,缪尔此处的选词表示他揣测中的本原未必唯一。《第一夏》中,维护和更新自然秩序的力量通常被拟人化地称为“大自然”;这位“诗人”、“灵慧的匠人”(245页)运用美妙的“手法”(226、234页)完善每一自然风物、协调总体自然格局。而自然力的源泉,看来缪尔沿用传统表述谓之神明或上帝,这神灵以光与爱充盈宇宙。神明是否拥有位格,与人类历史关系如何,此类问题在《第一夏》和缪尔其他作品中找不到答案,看来并非其关怀所在。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缪尔心目中作为自然力源泉的神明远非传统基督教教义中赋予人类支配自然之使命的上帝。(19)自然力这位诗人或匠人不断劳作,作用于现象,使之从美臻至更崇高的美,而现象之美的辉光则将我们引向至高本原。例如,缪尔在日记里不止一次将此行所见的山河原野称为“充满神意的原生大地”(例如295页);山间的日子里,“白日之光让其中一切都显得同样神圣,开启无数窗口让我们亲见神明”(187页);初临高山地带,最令缪尔欣悦若狂、无以言表的莫过于笼罩一切的“灵光”(219页)。在缪尔心目中,创建和谐秩序、让自然一再更新的神圣本原超越于自然,但神圣本原总是借助自然现象向人启示永新与不朽的生命。 ①1911年付梓的《我在内华达山的第一夏》并非缪尔1869年夏的原始日记,而是几经修改而成。Donald Worster在他的缪尔传记A Passion for Nature:The Life of John Mui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中告诉读者,缪尔修改日记后弃置了原稿(160页)。本文作者也未曾见到有关原稿全文以某种方式得到保存之说,因此无从通过对照原始日记以确认修改内容。原稿的某些片段却以其他形式留存下来。例如,Worster发现有一篇日记当年被缪尔摘录在书信中寄给友人;将这封现存书简中的摘录与出版的日记版本相比较后,Worster发现两者区别不小(474页,注释13)。结合其他证据,Worster总结道,出版的日记看来保留了原稿中的经历,但往往修改了经历所引发的思绪(160页)。1911年问世的这部“日记”不妨说融合了日记与回忆录,乃至有意无意地注入了虚构成分(当然,日记、传记、回忆录等文类本身也不乏虚构成分)。《第一夏》在内容来源上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应得到上述说明,但这并不影响本文拟做的探讨,因为本文主要目的不在于还原作者缪尔在1869年夏的内心经历,而在于探讨这部文学作品的主人公缪尔所寻求的精神源泉的内涵。本文讨论的山居生活是出版的日记中缪尔记录、回忆、想象性重构的生活。 ②Worster,A Passion for Nature,160页。本文中引文若未注明译者,皆为本文作者所译。 ③本文中来自《第一夏》和缪尔其他作品的引文,均出自John Muir,Nature Writings(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97)。此处引文见245页,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④对于浪漫主义的传人——多数现当代读者——而言,视崇山为人的精神家园或源泉来得自然,仿佛是亘古不变的基本情结,其实不然。关于西方文明传统中人对山的审美态度的演变,可参见Marjorie Hope Nicolson的经典著作Mountain Gloom and Mountain Glory:The Development of the Aesthetic of the Infinit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9)。Nicolson指出,现代人对山的崇敬并非自然而然,从古代到18世纪末,对山的审美态度大致历经了从惧怕和反感到渴望和崇仰的复杂演变过程,直至浪漫主义诗歌赋予崇山无限与永恒这些象征意义。Nicolson力求揭示上述审美态度的转变折射出西方思想史中的巨变。该书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作为其起点和终点,未曾涉足美国文学或缪尔的作品。缪尔热爱华兹华斯等歌颂“mountain glory”的诗人,无论从文化传承还是个人志趣的角度来看,缪尔都继承了浪漫主义崇山情结,对它的内化在《第一夏》中一再可见。 ⑤关于宇宙和谐说,可见柏拉图的《蒂迈欧篇》(Timaeus)和奥古斯丁的《论秩序》(On Order)等著作。还可参考Leo Spitzer,Classical and Christian Ideas of World Harmony:Prologomena to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Stimmung",ed.Anna Granville Hatche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3)。 ⑥原文为“the infinite cosmos”。cosmos古希腊文词源的意义之一是和谐有序的宇宙,英文词也保留了这一内涵。从所引对话亦可看出,此刻令缪尔感动和憧憬的显然不单是自然或宇宙本身,而更是其和谐秩序,故将原文译为“无限的和谐宇宙”。 ⑦Worster在缪尔传记注释中所引的洪堡的一段话,与缪尔的和谐观相呼应,这段话出现在洪堡的著作《和谐秩序:一幅宇宙素描》(1845-1847)的卷首:“我们若将大自然付诸理性思考,就会发现它是纷繁现象的统一体,是汇合了形态特征各异的造物的和谐体,是个恢弘的整体……生命气息赋之以活力。”(转引自Worster,472页,注释7) ⑧David Wyatt,The Fall into Eden:Landscape and Imagination in Californ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一书包括探讨缪尔的颇有见地的一章(32-46页)。Wyatt引用和解读了包含此段引文在内的一段文字(37-41页),称之为缪尔对约塞米蒂山谷最为提纲挈领的描述。从这段话以及缪尔的其他描写中,Wyatt认识到缪尔内心的一大矛盾,也就是对和谐的信念与对个体之丰富与独特的兴趣这两者间的矛盾。他还认为,与其他沉思自然的美国经典作家相比,缪尔未能转向自己的内心,让心中的核心矛盾成为思考的一大主题,这使缪尔成了他们中间最不具矛盾性、最缺少自我意识的作家。本文的主要关怀不同于Wyatt,不拟深入探讨上述观点中的议题,但它值得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思考。 ⑨《第一夏》中对河乌的描写,主要出现在6月29日和7月12日的日记中,8月21日的文字也提及河乌。多年后缪尔以河乌为题撰写了一篇灵动的散文,“The Water-Ouzel”是他的名篇之一,收录于The Mountains of California(1894)。 ⑩William Wordsworth,The Prelude,1799,1805,1850,eds.Jonathan Wordsworth,M.H.Abrams and Stephen Gill(New York:W.W.Norton,1979),p.1,ll.1-6. (11)“内华达山”(the Sierra Nevada)西班牙文原意即“雪山”。 (12)缪尔认为约塞米蒂山谷、乃至整座内华达山脉都是由冰川这位艺术家经过悠长岁月精雕细刻而成的杰作,这一说无疑符合他秉持的和谐自然观,甚至可以说源于其和谐自然观。缪尔用均变论式的冰川学说解释内华达山脉成因,而当时美国地质学界的权威阐释倾向于灾变论,详见Worster,192-199页。Wyatt对于两种地质学说之对立的哲理解读见The Fall into Eden,34-35页。 (13)《罗马书》第6章第3-4节。此处和以下的汉译《圣经》引文均取自和合本《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年版。英译《圣经》引文取自The Oxford Annotated Bible,eds.Herbert G.May and Bruce M.Metzg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14)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44节中写道:“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本文愿在此灵活借用圣保罗的言辞,将缪尔笔下与大自然神秘融汇的新生、永生之躯也称为“灵性的身体”。 (15)《启示录》第1章第15节。 (16)《创世记》第2章第10-14节。按现今通行译名,第三和第四条河分别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见The Oxford Annotated Bible。 (17)据The Oxford Annotated Bible所注,那条“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的未名河源自“地下海洋,繁盛生命之源”,与《创世记》第2章第6节中升腾而起滋润大地的雾气来源一致(3-4页)。 (18)很明显,在《第一夏》等诸多作品中,缪尔时而将约塞米蒂山谷或内华达山地视为伊甸园或地上乐园。这一联想本身并不新鲜,本文关注的是缪尔对乐园内涵的独特感悟。发现“新世界”的欧洲探险者、殖民者及其后裔惯于将美洲视作伊甸园。处于新世界边陲的加利福尼亚州,更是被向西行进的移民们想象成伊甸园。关于美国文学和历史中针对加州的伊甸园式想象,可参考Wyatt,The Fall into Eden。Carolyn Merchant在Reinventing Eden:The Fate of Nature in Western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2003)一书中指出,从基督教中世纪至今的西方文化在极大程度上都以重返或重建伊甸园为主导思想,并探讨了这一意识形态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的影响和造成的局限。本文在此处力求揭示缪尔伊甸园式想像的一个特点,即伊甸园的源泉属性。缪尔此种想象的另一非传统特征,在于他眼中大自然生灵的自由意志、智慧,以及与人类的平等关系。 (19)针对此种教义及其主导下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的批判不时见于缪尔的作品、日记和书信,最为著名的一段批判性文字,见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1916)或John Muir,Nature Writings,825-8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