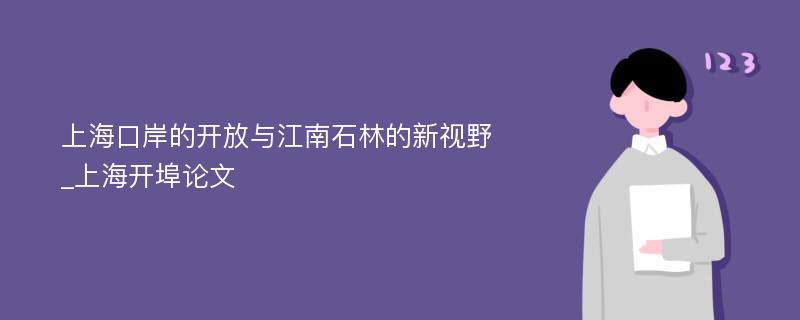
上海开埠与江南士林新的从业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上海论文,士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从业观的变化是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产物。近代以来,中国由闭锁而开放,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东来,使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基础发生裂变。近代工业的兴建,对外贸易的发展,社会近代化的发展趋势,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催化出了新的社会分工与专门化职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日趋解体,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呼唤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与个体的解放。传统的特权等级观念以及建立其上的社会结构在新的经济机制的渗透下不断分崩离析,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与流动由此产生,丹尼尔·贝尔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那种“独特的文化和品格构造”在上海及江南开始显露端倪。丹尼尔·贝尔说:“在文化上,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统)中解脱出来,以便他按主观意愿造就自我。在品格结构上,它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和延期报偿原则,培养出为追求既定目的所需的严肃意向行为方式。正是这种经济系统与文化品格构造的交融关系组成了资产阶级文明。”(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页。)士林,这个传统的地位最显赫的群体从业观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由传统而近代、由封建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大变动。
开埠后的上海,经济上的崛起,西学传播中心的确立,政治上相对宽松、自由的氛围,使之成为晚清江南士林心目中的理想之地而纷纷汇集于此。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及以后江南大地连年的战火,又使得江浙一带的士绅避乱而来沪上,“皆以上海为桃源,两省精华荟萃于此”(注:《申报》1882年1月7日。)。大上海不仅是万种商物集散之地,更成为各种新思潮、新观念的风云际会之地。“一叶知秋”,荟萃了江南名儒硕彦的上海,其士林思想的些许变化,无疑折射出江南士林的思想新动向。似乎可以这样说,沪上士林思想之嬗变,也即是江南士林之思想嬗变的缩影。
一、突破华夷之别,应聘于西士机构
现实总是矫正人们传统观念的最好利器。开埠通商使上海率先走出了闭锁的王国,世界近代化大潮在这个江南一隅的滨海小城“卷起千堆雪”。泥泞荒芜的滩涂之地铺成了马路,租界地内整洁而秩序井然,电线、电报、电灯、电话以及蜂拥而至的西洋货物,使得上海成了展示西方文明的橱窗。西方在强盛,中国在衰败,晚清寓居上海的士林在这段跌宕的历史中,咀嚼着文化盛衰之蕴。他们恨夷、蔑夷,却不盲目排夷;他们敏于发现新事物,更敢于不囿成见去接受新事物。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来自江苏的名儒冯桂芬到上海后即被各种西学书籍所吸引,眼界大开,思想骤变。他不再以华夷尊卑来看待中外关系,而是建立起了客观的世界地理概念,且一语惊人:“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收贫民议》。)17岁即赴沪学贾的郑观应作了如此反思:“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注:郑观应:《易言·论公法》,见《郑观应集》上册,第67页。)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今之天下非古之所谓天下也。古之天下不过中国一隅耳,凡不隶版图者,皆谓之为四夷, 今之天下则四海内外声气莫不通。 ”(注:《申报》1878年1月28日。)
就在大部分国人仍念念不忘夷夏大防、华夷尊卑,对世界懵懵懂懂之际,上海士林这种认识成为突破这一陈腐观念的先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夷场”之类的称呼虽偶有所闻,但人们更多地改称之为“沪北”、“洋场”,“夷”类用语逐渐为“西”、“洋”一类中性或偏向羡慕的用语所代替,西人、西学、西艺、西书是与强盛、文明、先进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于是向西人学习,与西人合作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寓沪西人创办的文化机构中便出现了许多上海及江南籍士子的身影,这不仅成为他们实现广采西学、西艺主张的渠道,也成为其新的就业门径。
(一)入洋人的书局合作译书
入洋人的书局、出版机构与西士合作译书的中国士人很多,沪上名士王韬当属于较早突破成见、与西士合作者之一。1849年王韬再度至沪,生计无着,穷困不堪,遂入墨海书馆,协助英教士麦都思工作。时人对此颇有微辞,然而,也恰恰是在墨海书馆的这段时间奠定了王韬的西学基础。他与麦都思“雅称契合”,成为传教士翻译西书的好帮手。他相继译了新、旧约《圣经》以及《中西通书》、《格致新学提纲》、《西国天学源流》等介绍西方科学的书籍,与之合作的传教士主要有麦都思、艾约瑟、伟烈亚力等人。
浙江海宁人士李善兰专擅数学,并有算学专著自刻出版。1852年他将自己的书展示给寓居上海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伟烈亚力见李善兰算学造诣颇深,当即聘其为翻译数理化西书的助手。之后李善兰与传教士合作翻译了多种自然科学书籍,如《几何原本》后九卷、《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谈天》、《重学》、《圆锥曲线说》、《奈端数理》等。与之合作译书的寓华传教士有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等。李善兰堪称将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个中国学者,他所翻译的这些科学书籍,多为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开创之作,影响深远。翻译西书的同时,李善兰也获得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后被清廷专聘为北京同文馆算学总教习,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数学家。
在上海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墨海书馆中,应聘与西士合作译书的还有蒋剑人、管嗣复、张福禧、陈萃亭、周双庚等一批中国学者。
自称“大江南北无与抗手”的蒋剑人,是苏松之地文名甚高又颇为狂傲的人物,与王韬、李善兰被时人称为沪上“三狂士”。在上海开埠之初,当人们还普遍对西人西学敌视、防范之时,他便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以中外、华夷为限,开始结交西士。他经艾约瑟介绍帮助法国巴黎的汉学家儒莲翻译了《大唐西域记》,19世纪50年代初,蒋剑人根据传教士们的口述编出了《寰境》16卷,介绍了地球四洲之情势。1856年7月,蒋剑人根据传教士慕维廉的口述,精心编译出版了《英志》8卷。在上海士人日炽的慕西学之风中,此书尚未出版即被沪上士人争相传抄阅读。
至咸丰初叶,应聘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书的还有寓沪的龚自珍之子龚橙、魏源之子魏彦、科学家张福禧、张文虎、舒高第、赵元益、赵烈文、周弢甫等人。中西士人合作译书,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阵容最为强大。被该局延聘的外国学者共9人,即傅兰雅、林乐知、 金楷理、卫理、秀耀春、罗亨利、玛高温、伟烈亚力和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中国学者50人,主要有徐寿、华蘅芳、舒高第、赵元益、徐建寅、郑昌棪、钟天纬、瞿昂来、李凤苞、贾步纬等人。
合作译书不仅成为士林新的职业,而且所译西书广泛介绍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应用技术以及西方的社会制度、史地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进洋人的书报馆
上海报刊始自寓沪外侨的外文报纸,但外侨创办中文报刊时,苦于中国文字之繁难,必聘用大批中国学者文人,甚至担当重任。此类报刊以《万国公报》最具典型意义。《万国公报》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万国公报》那读之脍炙人口、落笔不俗、博大精深的文章即出自林乐知背后一大批华人饱学之士之手,其中贡献最大者当首推沈毓桂。
沈毓桂似乎是个不太被史学家们注意的名字,然而这的确是个不该忘记的名字。
沈毓桂(1807—1907),江苏吴江县人,字寿康,号赘翁。任职《万国公报》期间,曾用20余个笔名撰文。他年轻时就已名播三吴两越之地,在上海更是与大名鼎鼎的王韬齐名的中西兼通的奇才,1850年受洗皈依基督教。1859年即入墨海书馆参与寓华传教士翻译西书、传播西学的工作。故此,1874年当《万国公报》始设主笔的时候,林乐知即请已经为他担当了六年之久录述、润色文章的沈毓桂出任此职。沈氏在《万国公报》凡18年,每日与其他华人事工一起先听西文,后造华文,晨抄暝写,工作十分辛苦。他年近九旬之时,仍无片刻之休暇。在沈毓桂主笔期间,《万国公报》还有著名的华士董名甫、朱逢甲、袁康等人,其他默默无闻的华士更多。沈毓桂卸任后,素有“上海华文报纸中最佳作家”之称的沪上名士蔡尔康、范祎相继担任主笔,应募入馆的秉笔华士更多。
在洋报馆、书馆的示范与启发下,国人自办之报纸、书馆渐趋发展,尤其是戊戌期间报业、图书业更趋兴盛。据戈公振先生对近代非官方报纸(民间办报)的统计,上海有各类日报32种、杂志46种,居全国之首;同时上海报刊业的发达与商业化,使上海及江南的士林又多了一条报酬优厚、需求量大的新的谋生之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职业,如编辑、记者等。江浙一些科场失意文人士子纷纷来到上海,在中外报馆、书局谋职。上海著名报人蔡尔康,乡试屡试不中,遂入报界谋求发展。他20多岁即任《申报》主笔,编辑增刊《民报》、文艺副刊《寰宇琐记》;1882年起又任《字林沪报》编纂总主任,连载长篇小说《野叟曝言》;后与传教士合作,从事翻译工作,“马克思”的中文译名即出自其手笔。浙江海宁名士王国维1898年到上海,入《时务报》馆担任司书、校对。江苏吴县名士包天笑,1900年来上海谋职,先后入上海金粟斋译书处、启秀编译局、广智书局编译所和珠树园译书处,任校对、印刷和编译员。1906年后包氏定居上海,即任《时报》馆撰述员, 编副刊《余兴》, 1912年起入商务印书馆。江苏名士王钝根,起初在青浦自办《自治旬报》,后应同乡席子佩之邀,到上海担任《申报》编辑,并于1911年8 月首创《申报》副刊——《自由谈》。江苏名士蒋维乔,早年曾入商务印书馆,与吕思勉、谢观等人一起为商务印书馆编纂教科书。浙江名士蒋智由,1901年在上海创办《选报》,自任总编。无锡名士王蕴章,1902年应聘至上海商务印书馆供职,编辑《小说月报》,兼编《妇女杂志》。《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的作者、浙江镇海人士张静庐来沪上先当学徒,旋即进《公民日报》、《商报》等报馆任职。江苏常熟名士徐枕亚,师范学校毕业后,即应邀至上海任《民权报》新闻编辑,并著小说《玉梨魂》。浙江人士蒋箸超,曾游学沈阳、南京、杭州,最终寓居上海,1911年应聘为《民权报》编辑,还与他人合撰《蝶花劫》连载报端。浙江绍兴人士章锡琛,1912年到上海,即入商务印书馆担任《东方杂志》编辑,后又兼编《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副刊。由上述可见,从事编辑、记者职业是江南士人日趋热门的近代职业。
(三)任洋学堂教习
西人办学如同办报一样,离不开华士的鼎力协助,延聘中国学者执鞭任教,其中以中西书院最为典型。中西书院,1881年由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先于八仙桥一带建成中西第一分院,后又于吴淞路购得一块空地建成第二分院,各延聘中西教习四五位,沈毓桂即名列其中。在中外士人的共同努力下,中西书院很快成为沪上家喻户晓的新学堂,而中西书院之所以能享誉沪上在很大程度上仰仗沈毓桂之功。“沈君人品端方,学问渊博,循循善诱,教导有方,虽年逾八十,而精神尚健,久为士人所推重,门下士已有千余人之多”(注:海滨隐士:《上海中西书院记》,《万国公报》第5卷,第60期。)。因此, 世人皆称“中西书院创自林进士乐知先生,而成于沈别驾寿康先生者也。”(注:王佐良:《中西书院志略》,《万国公报》第19期。)
近代上海(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新学制颁布前)由外人创办之中小学堂有18所,大学堂2所,这样, 就有为数众多的中国士人应聘作洋学堂的中方教习。
二、突破“奇技淫巧”观,效力洋务企业
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发展需求,使得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知识失去了用武之地,也使得汲汲于科举应试之旧式文人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另谋出路成了士人的燃眉之急。在开埠后的上海,让士人们看清的第一个道理就是学必致用。越来越多的士人不再受正统科举入仕之途的桎梏,不再甘于空疏、于世无补的词章琐句中皓首穷经。不独上海如此,讲求经世致用、切重实际在深受上海之西风影响的江南地区也蔚然成风。摒弃了科举入仕的士子们,兴致勃勃地把目光投向了讲求实用的西学。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士人们不再以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而是努力营建着以自然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结构。
士人们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热情极高,像上海人士郑嘉荣,完全凭自学成才,于机器之理无不洞悉,而为洋务大员李鸿章重用。李鸿章兴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津芦铁路、银元局、金陵制造局等,无不有郑嘉荣的一份功劳。1896年前,曾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担任过编译的人员有资料可查者45人,其中除少数人受过专门系统教育外,多数人为自学成才(注: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12页。)。
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蓬勃兴起后,上海即成为洋务事业最为兴盛发达之中心。主持上海洋务的李鸿章,会聚了或兼通中西、或熟谙西艺西技的各色人等,其中又以上海和寓沪的江浙士人居多。如:江南制造局成立后即网罗王德均、李凤苞等通晓天算地舆的士人入局,两年后,制造局附设翻译馆,更成为汇集江南各类“奇才异能”之士之所在,徐寿(江苏无锡)、华蘅芳(江苏无锡)、舒高第(浙江慈溪)、赵元益(江苏新阳,今昆山)、徐建寅(江苏无锡)、汪振声(江苏六合)、钟天纬(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瞿昂来(江苏宝山,今属上海)、李凤苞(江苏崇明,今属上海)、范熙庸(上海)、贾步纬(上海南汇)等50人名列其中。
加盟李氏幕僚的还有:吴炽昌(上海人),虽出身买办,但李鸿章欣赏他“通晓西国语言文字”,“熟悉商务”,委任其为开平矿物局、中国铁路公司会办;郑嘉荣,自学成才的上海人,先后助李鸿章兴办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等,历任提调至总办等高级职务,为李鸿章办了45年洋务;李凤苞,本不出名,李鸿章发现其颇富才能,派他为驻德国公使,兼驻意大利、荷兰、奥匈帝国公使;冯桂芬,则早在同治元年即以“精思卓识,讲求经济”(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7,第23页。)而被李鸿章点名奏调入幕,并直接进入了李鸿章的核心圈子,号称李鸿章身边的诸葛亮,深得李氏倚重。甚至因联络太平天国而受通缉的上海名士王韬也被李鸿章延揽入幕,颇受重用。
据统计,李鸿章洋务集团中的江南士人有221人,其中,买办16 人,占7.7%;官僚官吏108人,占48.9%;其他商人50人,占22.6%;地主24人,占10.8%;文人15人,占6.8%;身份不确定者11 人(注:关于李鸿章幕中江南人才之叙述分别参见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于醒民、唐继无《从闭锁到开放》,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43页。)。在李长莉编写的《知识分子参与洋务运动情况表(开明士人)》及《知识分子参与洋务运动情况表(受西式教育人员)》两表中,江南(以上海及江浙为主)籍人士占58.9%(注:此数据据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附录统计。)。盛宣怀曾说过:“(上海)为李鸿章发韧之地,有为李鸿章开办洋务、商务之初基”,“其立功实始于上海一隅”,真是一语中的。
倡行洋务的曾国藩幕府中同样拥有一大批江南才子,生于苏南、成长于上海的赵烈文就是其中之一。赵烈文往来于苏、沪两地,尤以旅居上海时居多,得以承袭欧风美雨,对世界大势多所了解。后于1861年至安庆入曾国藩幕,出谋划策、运筹帷幄,被曾氏视为“骨肉之爱”的得力谋士。
洋务大员对人才的重用,无疑为上海如火如荼的西学热潮推波助澜,为那些希图通过兴办洋务而富国强兵的江南爱国士人提供了用武之地;同时洋务事业发展所提供的新的从业机会、诱人的丰厚待遇,为江南士林提供了一个新的择业导向;入幕洋务机构成为士林竟相角逐的职业,由洋务而升迁入仕成为新的充满希望的谋生、谋官之路。
随着上海及江南各地的开埠通商,出现了一些新的涉外行政机构,如海关、各地行政长官涉外翻译机构等,也都成为士人、尤其是新式学堂毕业诸生竞相角逐的职业。
三、新的“义利”观与五花八门的新职业
鸦片战争后,西学西艺纷至沓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学传播尤烈,加之上海以及江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实求利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在沪上名士之中影响日深。沪上名士冯桂芬说“中国名实必符不如夷”,郑观应则抨击传统观念的务“虚”不务“实”,“循空文而尚谈性理”(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盛世危言·道器》。),倡导“视商如士”;王韬更是坚决地主张“恃商为国本”;而来自无锡的有识之士薛福成还努力向古代典籍中寻找“言利”的根据,论证“圣人正不讳言利”乃古已有之的道理;马建忠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重商思想,更为鲜明地指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注:马建忠:《适可斋纪言·富民说》。)。“兴利”、“言富”在沪上士林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社会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急剧地改变着中国人传统的义利观,刺激了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对资本主义伦理精神的认同,这一历史发展变化在开埠后的上海及其江南腹地表现得尤为显著。固有的“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秩序出现了很大的变动:文人士子的满腹经纶和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高高在上的地位只能作为昨日的荣耀,而那些可能识字不足半斗,但却腰缠万贯的富商豪门成为今日的英雄。失去了荣耀的士子们努力向“商”靠拢,“士”、“商”一头一尾两个社会等级的渐趋合一,又带动了整个社会的重“商”、崇“商”的风气,形成了“今天下士商相聚,抵掌侈谈四海内外”(注:《皇朝经世文编》四卷25,“户政”、“公司”。)这种新的社会现象。晚清上海有首竹枝词不无调侃地唱道:“一经贸易便财东,者也之乎路路穷。何自古人轻市井,眼前若个不趋风?”词旁还有一行小注:“近缘江夏以贸易起家,人都喜经营而贱吟诵矣。”(注:《商行竹枝词》抄本,转引自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价值观和从业观的变化促使人们走上新的谋生之路,工厂、公司、洋行、商行、职业学校、广告制作等纷纷涌现,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谋职渠道。商品大潮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投入商海,在这个“较尽锱铢,情面无亲旧”(注:王韬:《瀛濡杂志》卷六。)而人人言利的上海,“新交因狐裘而订,不问出身;旧友以鹑结而疏,视同陌路”;“舆台隶卒辉煌而上友,官绅寒士贫儒褴缕而自惭形秽”(注:海上看洋十九年客:《申江陋习》,《申报》1873年4月7日。)。在这种情况下,寓于沪上的文人士子或满怀抵触,以“足迹三十年不涉夷场为自守”而自命清高,或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趋俗就利;或一改君子重义轻利的斯文相而下海为商,反映了社会向商品经济转化的大变动时期,士子文人痛苦蜕变的心路历程。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时间上海滩或辍学经商,或学业有成而经商,或者是由士而经商者纷纷涌现,仅以川沙县为例,如:“朱纯祖,字丽生,市区人,监生。……年甫十龄,孤苦零丁,学习米业,中年创设朱丽记花米行,历二十余载”(注:《川沙县志》卷16,转引自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5页。);“姚光第,号述庭,市区东门外人,南邑诸生。 ……光第感于清季地方贫瘠日甚,就其家设机器轧棉厂,实为川沙机器轧棉之始”(注:《川沙县志》卷16,转引自上引书,第312页。); “张庆平,字耿娱,长人乡人,……孤苦勤学,旋弃儒习商,有企业思想……创办华宝化炼厂于小湾镇北市,经营渐有成绩”(注:《川沙县志》卷16,转引自上引书,第312页。)。此外上海近邻江苏南通人士、 清末状元张謇便是以士人的身份,创办南通第一个近代企业,进而发展南通近代实业的。著有《续海上花列传》等小说、曾任职《申报·自由谈》的浙江籍寓沪近代著名小说家陈蝶仙,就利用业余时间,在自家的手工作坊里钻研牙粉与化妆品制作,最终以生产“无敌牌”牙粉致富,成为大上海家喻户晓的资本家。沪上著名佛教居士王一亭,光绪七年14岁时即辍学从商,17岁考入制造局翻译馆,卒业后继续经商。浙江镇海人方液仙,从著名的斐迪中学毕业后,跟随中西书院化验师、德国人窦伯烈学习化工,卒业后即用所学知识在上海创建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牙粉、雪花膏,1915年改为有限公司,曾以三星牙膏风靡全国,远销南洋各埠。曾以《孽海花》而蜚声近代小说界的曾朴,在商潮裹挟之下,也曾以举人身份,于光绪二十三年至沪上筹办实业,经营丝业。甲午战后,民族资本进入更快的发展时期,“舍儒而商”更成为沪上、江南近代士人一个新的时尚和潮流,从商者之多,不胜枚举。
据报载:同治十一年上海开埠后,各省逐利之徒,不论长幼蜂拥而至,塾师们也一改往日不便言利的羞羞答答的模样,一旦“风闻某处有馆缺,不问东家之若何,子弟之若何,即纷纷嘱托。”(注:上海《师说》,1872年8月17日。 )而在言利乃光明正大之事这种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西文教习,更是公开言利。加之上海人学习外语热潮迭起,所以上海大多数的外语类学校、夜校在刊登广告招徕学生时,并不讳言赢利的目的。
在上海,卖文鬻画也是寻常之事。来自浙江绍兴的著名画家、海上画派的先驱人物任伯年即以鬻画营生,他的《福星象轴》、《日利大利》等画,就是应买画之人的要求而作的。为了赚钱,他有时一个晚上可以画几张甚至几十张画。其他画家,如朱熊、张熊、任熊、任薰、胡远、虚谷等人均曾在上海卖画为业,朱熊、张熊、任熊三画家由此还有“沪上三熊”之称。最典型的还是吴待秋,他毫不掩饰自己为钱而画的思想。有人因索画而请他吃饭,他谢绝说:“吃一顿工夫,我已经几张扇面画下来了,划不来,还是拿钱来吧!”(注:林树中:《近代上海的画绘:画派与画家》,《南艺学报》1982年第1期。 )江苏江都画家倪田,擅长人物、仕女、佛像,尤擅画马,于上海滩卖画30余年,名重一时。与他一起在上海卖画为业的还有画家钱慧安、宋海、舒浩等人。
画家鬻画,文人则卖文。卖文者与出版商既以赚钱为目的,就必然要想方设法打开销路,为此,就得满足大众市民口味。这样做虽然推进了文化的大众化、通俗化,但却极易造成作品格调低俗。例如,沪上大才子王韬,即写过不少艳情文字,在上海嫖业颇有影响。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等都曾涉足艳情文字生意,吴趼人还曾欣然为药商大作广告。
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因战事、灾荒频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朝廷大开捐纳之例,文职自郎中及府道以下,武职自参将、游击以下,皆像上海新出现的股票一样,上市交易买卖起来。资财雄厚的买办、商人成为捐纳制度的主要受惠者,他们竞相认捐,往往是一夜之间“市侩之徒,皆成暴贵”(注:《皇朝经世文编》二,总第359页。 )。据统计,光绪二十六年前后,上海的40名著名买办中,至少有15人捐得候补道官衔(注:参见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954页。)。 晚清的捐纳制度无疑为向商贾倾斜的社会风气推波助澜。捐纳得官人数剧增,使得正途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们一下子失去了优越感和心理平衡,怨声载道,“贫苦穷饿莫能名状,至有追悔不应会试中式者”(注:《皇朝道咸同光奏议》,见《治法通论》卷一,第8页。), 科举入仕之途更趋冷落,下海经商更趋新潮。
在上海带动下江南士林从业观的变化,是上海开埠后商品经济下新的社会需求所产生的新现象,它打破了士人几千年来恪守的君子重义轻利的迂腐观念,为他们融入社会拓宽了渠道。在他们用知识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享受到知识、才能所带给他们的经济利益。士人“舍儒而商”的趋势,不仅加速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推动了社会阶层的频繁流动,而且也为死气沉沉的社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加速了整个社会从业观念的更新。
标签:上海开埠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上海论文; 历史论文; 申报论文; 李鸿章论文; 万国公报论文; 沈毓桂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