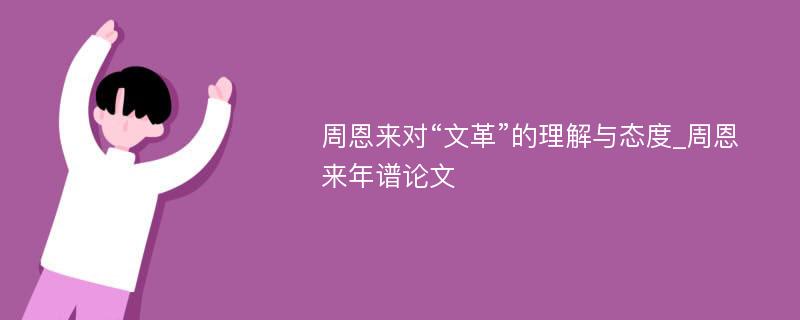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周恩来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是学术界在周恩来研究中极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本文拟就“文化大革命”前期(即九大以前)周恩来对“文革”的认识和态度谈点个人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前辈与同人。
笔者以为,“文革”前期周恩来对“文革”的认识与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并基本形成了他后来对“文革”的认识与态度。
第一阶段为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前后的“文革”酝酿和开始阶段。这时,周恩来对“文革”的态度既是被动接受的,也是拥护和赞成的
说是被动的,是相对于积极主动来说,是指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参与“文革”的酝酿与发动。这一点,联系“文化大革命”酝酿发动期间周恩来的思想和活动就看得很清楚。1966年,是我国正式执行已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周恩来作为主管经济建设的政府总理,他的主要思想和精力集中于如何在前几年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开个好头。这年初春,恰逢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大旱,周恩来打算以抓华北抗旱为突破口,把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农业搞上去,改变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南粮北调”的局面。从1月至4月,周恩来全身心地在抓这项工作。3月12日,他给中央写信说,自己“拟在河北、 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其间,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同时还忙于灾区人民的抗震救灾、恢复生产工作。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也是来去匆匆。5月初, 标志着“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时,周恩来还在忙于同以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举行会谈和陪阿代表团赴大庆、上海参观,直到5月16 日才开始参加会议。6月,他又出访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 更重要的事实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事先没有告诉周恩来。批判《海瑞罢官》,林彪、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周恩来事先都不知道。
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参与“文革”的酝酿发动,这是事实。但是,当毛泽东提出要搞“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是拥护和赞成的。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文化大革命”初始是以“反修防修”为主旨的。对反修防修,周恩来不会反对。其中主要原因,是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认识上存在着那个时代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正如邓小平所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这当然也包括周恩来在内。
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局限性,加上当时国际斗争环境的影响,导致了对修正主义认识的不清楚。修正主义的问题是由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中苏两党出现分歧而引发的。那时,不光是毛泽东,恐怕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都坚信苏共的领导权已被修正主义集团所篡夺,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变了颜色。以这样的国际“经验教训”来观察国内问题,就自然会遇到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问题。那末,中国有没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呢?当时周恩来的回答是肯定的。当然,对中国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和估计,周恩来和毛泽东是不一样的。周恩来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可能性更多的是结合我国的实际特点,从思想意识方面去认识。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只有十几年,社会主义思想阵地还不巩固。而中国的封建社会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封建思想、旧习惯、旧势力根深蒂固,容易滋生修正主义的东西。他说:思想意识问题不注意,一样出修正主义。当然不是下一道命令就可以解决,主要是通过思想革命。(注:1963年10月25日接见伊春领导同志的谈话记录。)又说: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源,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思想上的和经济上的。必须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政权虽然掌握了,但在思想意识和作风上,并不是巩固的。(注:1963年2月26 日在全国农业科技会议和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的讲话记录。)
基于这样的认识,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反修防修,周恩来尽管不会像毛泽东那样感到阶级斗争就在党内,但至少认为中国有出修正主义的潜在危险性。这样,赞成和拥护“文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次,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局限性和对修正主义的认识不清楚,又坚信苏联已经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领导权的历史氛围中,毛泽东的个人决断对周恩来认同“文革”也有一定的影响。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在反修的同时,一直在警惕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后来,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越来越觉得中国出修正主义已不再是有可能性,而成了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在1965年10月两次高层会议上,毛泽东都讲到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并发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和形成的特殊历史地位,自延安整风以来,把毛泽东与真理等同起来,这几乎成了全党的共识。1958年5月, 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检讨反冒进的错误时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从毛泽东与周恩来一生形成的历史关系看,周恩来的这段话不能看作是一种违心的表态。这也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当时党内绝大多数高层领导存在着的认识上的局限。由于这种局限,在事情没有明朗、错误还没有完全暴露时,即使自己对毛泽东的想法和做法一时不理解,也很少去怀疑毛泽东有错误,而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
第三,周恩来开始赞成和拥护“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周恩来看来,“文革”主要是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是社教、“四清”运动的继续,与社教、“四清”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也正是“文革”的本来意义。1966年8月14日, 周恩来在接见即将离任的波兰驻华大使克泰诺谈到“文革”时有一段对话。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个长期的工作。克泰诺问:对我们观察家来说,有一个问题不清楚,就是阶级斗争是长期的,为什么出现这样突然的转折?周恩来回答说:不是突然出现的。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由农村发展到城市,这首先是从学校开始的,也涉及到报纸、文化界,这些都是上层建筑,是起指导作用的地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入开展,所以阶级斗争就尖锐化了,只是形式上有些区别,而不是本质的。应当说,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在内容上与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思想改造有某种相通性。尽管周恩来过去一直主张思想改造要靠自觉,要和风细雨,但是在官僚主义及种种社会阴暗面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也不会排斥赞同用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尝试。1958年4 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谈到精简机构越精越大的顽症时曾说:经验证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必须从根本上治疗。这就是大鸣大放,依靠群众来解决。1966年6月27日,他访问罗马尼亚时, 在地拉那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经验。这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
第二阶段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这一阶段,周恩来对“文革”是在矛盾、困惑、不理解中被动地跟进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很快就超出了周恩来的原有认识和预料,周恩来的一些想法、做法也与毛泽东的考虑出现分歧,与利用毛泽东的某些错误、蓄意把运动推向动乱的林彪、江青一伙的做法更是尖锐对立。他开始对“文革”感到困惑、矛盾和不理解。
在周恩来看来,反修防修除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外,还要搞好经济建设。1963年2月26日, 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肯定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危险的同时,又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首先是要搞好国内建设。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基于这样的认识,当8 月份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影响到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和经济建设的正常开展时,周恩来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使运动有组织、有步骤地朝健康的方向发展。8月下旬, 周恩来指示陶铸起草了一个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9月初, 他又亲自起草了《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几点意见》(未定稿),主要精神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对广大红卫兵进行政策教育,使运动尽量不要影响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然而,这两个文件先后遭否定,没能发出。(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4、57页。)
在对待红卫兵串连的问题上,周恩来考虑到大规模的红卫兵串连给铁路交通造成的极大压力和给社会秩序带来的混乱,主张广大师生回原单位闹革命,外出串连的人数应当有所限制。但毛泽东认为:现在学生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我们在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不要违反学生的潮流。(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2页。)在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上,周恩来也同毛泽东的想法有分歧。(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2页。)
10月初,林彪指示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中央文革江青、张春桥等看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他们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说《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这等于宣布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与周恩来所强调的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背道而驰。11月,上海发生王洪文等制造的安亭事件,代表中央文革前往上海处理此事的张春桥公然违背周恩来给华东局的电示,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其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
对于“文革”,周恩来越来越感到困惑、不理解。难道文化大革命可以不顾一切?难道这么多的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群众运动可以不要党的领导?周恩来在许多场合都说过:“说老实话,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也不是很理解,没有想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58页。)然而,尽管这样,在这一时期,周恩来从主观上还是力图去理解、去紧跟“文化大革命”。他还总是从主观上检讨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不如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这一心态,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都流露过。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按老的办法、旧脑筋对待新革命、新运动,就不对头。过去是对的,今天就不见得是对的,因为条件变了,环境变了嘛!(注:1966年8月2日的讲话记录。)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又说: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注:1966年10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第五小组会议记录。)他还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但还有掉队的危险。大中学生放假闹革命,实行革命串连,我们接待计划总是偏于保守,原来只想接待几十万人,现在想限制在150万人左右。主席说不行,要准备突破200万、300万人。但我有信心,知错必改,努力赶上。(注:1966年11月26日中央工作会议记录。)
尽管周恩来从主观上试图对“文化大革命”努力想通、努力紧跟,但面对“文革”带来的严峻的社会现实,忧国忧民的周恩来又难以想通和无法紧跟。全国上下陷于混乱,工农业生产和各种紧急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这么多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转眼之间被打成“走资派”,周恩来怎么能想得通,又怎么能跟得上呢?相反,对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又促使周恩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文革”采取了一些限制性的举措。正如他在1966年9月7日参加中国科学院的辩论会时所说:既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要进行生产斗争;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8月底9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的试图对运动作一些限制的两个文件连遭否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努力。就经济工作方面来说,他先是指示陶铸组织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并在9月7日发表。接着又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于9月14 日同时向全国下发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又称《农村五条》)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又称《工业六条》)。11月,周恩来又组织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还支持余秋里、谷牧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座谈会,拟出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上述社论、文件、会议都是同一个精神,就是强调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革命不要影响生产,实际上是试图把“文化大革命”之火阻于工农业生产领域之外。此外,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和各群众组织代表时也一再强调,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连,不要去影响工农业生产,工人、农民不能像学生那样放假闹革命,否则,吃什么,用什么?
周恩来对“文革”的这种态度,得到了毛泽东一定程度的支持,但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力反对。在12月5日至6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针对周恩来一再表明的“欲罢不能,势不可挡”,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注:1966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
林彪这次讲话以后,中央连续下发了两个文件,“文化大革命”的“洪水”全面涌入农村、工矿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对“文革”的态度由过去的“挡”变为“因势利导”。就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结束后,12月10日,周恩来把参加工交座谈会和被揪来京的各省市负责人召集到一起,说:“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潮。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00页。)
周恩来对“文革”由“挡”到“因势利导”的过程,很能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处境的艰难和斗争的复杂性,也很能使我们理解周恩来在“文革”中为什么没有采取“拍案而起”,而是选择了一种更为艰难、更为痛苦的韧性的斗争方式。这种韧性的斗争方式,其深层动因是周恩来对党、国家、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其意义是周恩来没有被打倒而得以在“文革”中起一种特殊的中和作用,减少了动乱带来的损失。
第三阶段是1967年以后。这一阶段, 周恩来已开始逐渐认识到“文革”是一场灾难,并基本形成了他对“文革”的认识和态度
历史跛着脚,踉踉跄跄撞入1967年。
如果说,从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周恩来对“文革”还是在矛盾、困惑、不理解中被动紧跟的话,那末,到1967年以后,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及其严重社会后果的全面暴露,包括林彪、江青一伙丑恶本质的日益现形,周恩来开始逐渐认识到“文革”是一场灾难。他对“文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首先,从1967年初起,周恩来在对“文革”种种错误做法的尖锐批评中,开始明显地流露出对“文革”的痛心和不满。
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 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拍案而起,强烈抨击“文革”的种种错误做法。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会上没有过多说话,但他的思想与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是相通的。就在散会几个小时之后,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对“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发出了怒吼,并当场下令逮捕了操纵造反派夺财政部业务大权的财政部一副部长。他气愤地说: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注:1967年2月17日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谈话记录。)
1967年8月,周恩来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 先后两次明确谈了对“文革”的不满。他说:“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个样子,这对我们国家没什么好处。”(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80页。) “你们看一看,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一段一段的铁路比过去军阀内战还搞得凶……完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嘛!”(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82页。)
1968年6月28日, 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一个水电代表团时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现在这个大革命,等于打一场内战。
以上所引,仅仅是几个方面的例子。有论者认为,“文革”初期,在公众场合批评“文革”各种错误做法最多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当属周恩来。此言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周恩来是个非常谨慎和讲原则的人,通常是不会轻易把他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不同意见对人说的,尤其是对外宾。然而,对于耗尽了他最后心血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的不满似乎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故而才有不满情绪的频频流露。
其次,周恩来已觉察到“文革”中某些错误做法的“左”的思想根源,并抓住适当时机纠正和批判极左思潮。
1967年1月开始的夺权风暴, 从根本上说是“左”倾错误发展的结果。周恩来当时不同意也没料到会搞全面夺权。当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策划夺权时,周恩来还明确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帮”。在毛泽东肯定了上海的夺权后,周恩来虽然难以反对,但还是不同意中央文革所主张的全面夺权。他反复强调:夺权只能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党权、军权、财政权、外交权不能夺;也不是所有的部门都需要夺权,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要打倒。他批评当时那种对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29页。) 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及他对夺权狂潮中某些错误的纠正,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极左错误的抵制和批判。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全国局势向更“左”的方面滑去。康生、关锋抛出“揪军内一小撮”,军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王力等人唆使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大权,8月22 日又发生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件。毛泽东也觉察到了问题,对“揪军内一小撮”提出了批评。周恩来抓住这一契机,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提出批判极左思潮。
1967年8月25日凌晨,周恩来找刚从上海回京的杨成武谈话, 要杨把最近各省情况、王力8月7日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情况向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果断地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抓了起来,给了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这一“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左”的怪胎当头一棒,客观上暗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1967年8月31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部党组成员和造反派代表, 严厉批评了外交部的夺权行为。他说: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9月6日,周恩来接见联络员和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站记者,批评有些地方提出的所谓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说:这种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揪军内一小撮”是极左倾向,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周恩来批极左的言论和行动以及全国一些地方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抵制,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恐慌。1967年10月以后,他们在全国刮起了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并在1968年3 月制造了“杨余傅事件”。
应当说,后来周恩来抓住林彪事件的契机又一次大批极左思潮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前一时期批极左思潮的继续和合乎逻辑的发展。
第三,从周恩来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希望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
1967年8月,一些造反派不甘寂寞,企图再来一次全国的大串连,再造一个“文革”的高潮,提出“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连的阶段”。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种错误做法。他多次指出:这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中央没有这样的估计。现在是大批判、大联合的形势。(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76页。)9月28日,周恩来接见东北三省群众组织代表时,针对造反派无休止的闹腾,愤然指出:工厂停产你们心里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15个月,再搞15个月行吗?还要“放假闹革命”,“第三次大串连”,大错特错嘛!(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92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九大以前,周恩来已经开始认识到“文革”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文革”了,他一系列批评“文革”的言行,实际上已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性质问题,并试图在某些方面从“左”的思想根源上加以纠正。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更加深化、坚定了他的这一认识。
周恩来之所以对“文革”觉醒得比较早,与他当时所处的位置及其对“文革”情况的全面了解是分不开的。“文革”开始以来,周恩来一直在一线负责全面工作,党、政、军,工、农、商、学、兵,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所有提到中央的大小问题都推到他的面前。经过对“文化大革命”近一年的实践和观察,在周恩来看来,“文化大革命”并非像林彪所说的是“代价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 %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78页。)。举目四望, “文革”的成果是什么呢?社会秩序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极度混乱,国家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维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交通随时面临瘫痪的危险;大批的老干部被打倒,有的被残酷迫害致死;外交工作也因“左”的思想出现四面危机,就连过去一直对我国友好的国家也多有怨言,有的甚至提出要撤回驻华大使;斗私批修,非但没有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义和派性思想的大膨胀,等等,等等。对“文革”的这种种“成果”,比起在中央负责某一方面工作的其他领导人或那些被打倒靠边站的领导人,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可以这样说,“文革”以来呈现在周恩来面前的,周恩来每天接触和处理的,都是因“文革”而起的混乱和问题,而没有一件称得上是“伟大胜利”的可喜之事。正因为这样,才促使周恩来重新思考和认识“文化大革命”。
那末,既然周恩来对“文革”的错误觉醒得比较早,那为何又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并最终没能从根本上予以纠正呢?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这样两条:一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并肯定的。对自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毛泽东是决不让步和妥协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实现它。深知毛泽东性格的周恩来在对待“文革”的问题上,不能不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周恩来一贯的性格和处事方式。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注:转引自《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对话——访金冲及》。) 周恩来后来的行动可以说是对他这句话的最好注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从批林彪反党集团的错误这一方式入手,批判极左思潮,并有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势头。结果,还是为毛泽东所不允许而夭折。由此,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一种韧性的斗争方式,陆续地从局部对“文革”的错误做一些补救,的确是周恩来一种明智的选择。二是也不排斥周恩来寄希望并相信毛泽东自己能够觉醒,等待毛泽东有朝一日能像对待“大跃进”那样,自己最终会发现“文革”的错误,并加以纠正。从党的历史上看,也确实有许多错误是毛泽东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的。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虽然最终没能从根本上纠正“文革”的错误,但还是为防止“四人帮”篡党夺权安排了一个可靠的格局,对后来彻底否定“文革”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时机,及时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使党内正义力量重新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邓小平复出,国务院重要部委的领导权及军队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老干部手中。临终前,周恩来还嘱咐叶剑英等:要注意斗争方式,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24页。)
标签:周恩来年谱论文; 修正主义论文; 文革论文; 周恩来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毛泽东论文; 林彪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