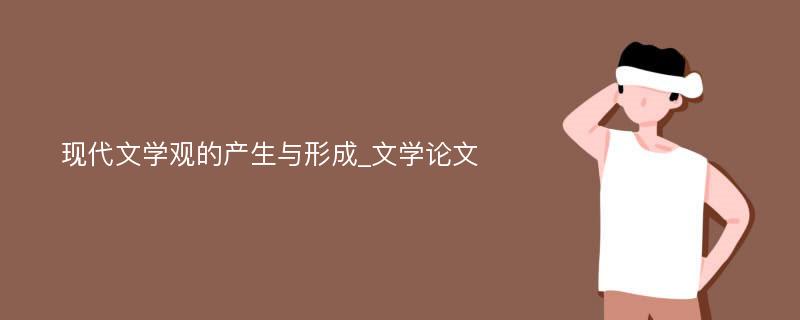
现代文学观的发生与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文学观的形成,也就是现代纯文学观念的确立和艺术自律观念的接受。我们接受了西方虚构的观念,艺术的真实不同于现实的真实。文学的内在本质是想象和情感。在这种虚构的文学观被接受的同时,中国文学的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戏剧等虚构文学从传统文学中的边缘地位进入到了现代文学的中心位置,成为了文学的正宗。因此,实际上,这种虚构文学观的发生与中国文学内部秩序的变化有一种或隐或显的相互的作用。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强调了文学虚构的性质。他说:“凡人之性,常非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梁启超最早提出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的概念(“理想派”与“写实派”),开启了现代新的文学认识维度。文学革命后,茅盾接编了《小说月报》,特辟了“创作”栏。“创作”是随着文学运动出现的一个概念。文学是一种创作,一种作家的艺术创造。“创作”的观念赋予了文学以不同于传统范畴的意义。胡愈之在《小说月报》12卷2号上《新文学与创作》一文中把文学和“创作”的观念紧密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创作”的意义。他认为创作有两个条件:(一)天才,(二)适度的艺术制作。他认为,艺术家是第二个上帝,上帝的权威是创作,艺术家的权威也是创作。“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非彻底革新不可了。但这当然不是变文言为白话的问题,也不单是从古典主义变到理想主义写实主义的问题,实在讲来,乃是文学的价值问题。中国旧文学太缺乏创作的精神,所以他本身已失却文学的价值了。”他将文学视为作家所创造的一个独立的艺术世界。他说:“创作的价值,非常重大!我们可以说:近代德意志是贵推(Goethe)西娄尔(Schiler)创造出来的;近代法兰西是卢骚嚣俄佛老贝(Flaubert)法朗西(Antole France)罗兰(Roman Rolland)等人创造出来的;近代俄罗斯是都介涅夫陀斯妥夫斯奇托尔斯泰和其余的人创造出来。”(注:愈之《新文学与创作》,《小说月报》12卷2号(2,1921)。)这样一种虚构的文学观念使文学与现实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张力,一方面,文学是一个想象的艺术世界,另一方面,文学又对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现代文学中尽管有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区别,有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和文学独立观念的对立,有着“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的冲突;然而,实际上这样一些文学观
念都是在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的范畴和新的文学地基上所展开的角逐与斗争。即使是毛泽东要求艺术服从于政治的文艺政策,实际上也恰恰凸现了艺术的特殊性,承认了艺术本身的独立性质,并且实际上提高了艺术的地位和重要性。
一、文学与启蒙
文学并不是一个有着固定的内涵的概念。文学的概念内涵在不断地发生着变迁。在19世纪还是文学的东西,在20世纪可能就不能被认为是文学;而19世纪被排除于文学之外的东西,到了20世纪却成为了重要的文学内容。美国文学理论家乔森纳·卡勒说:“文学作品的篇幅各有不同,而且大多数作品似乎与通常被认为不属于文学作品的相同之点更多,而与那些被公认为是文学作品的相同之处反倒不多。”在西方同样,已经被习惯接受了的纯文学概念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概念。乔森纳·卡勒说:“如今我们称之为literature(著述)的是25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著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200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如今,在普通学校和大学的英语或拉丁语课程中,被作为文学研读的作品过去并不是一种专门的类型,而是被作为运用语言和修辞的经典学习的。……比如维吉尔的作品《埃涅阿斯纪》,我们把它作为文学来研究。而在1850年之前的学校里,对它的处理则截然不同。”他说:“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人们对于文学的功能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在中国,有着深远影响的是“文以载道”的观念。贺拉斯《诗艺》中提出的“寓教于乐”的思想在西方同样长期发生着重要的影响。19世纪英国阿诺德甚至认为,文学将要取代宗教和哲学的功能。而近代以来,审美的文学论则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对于文学的本质和功能的看法,各个时代不仅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可能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在清代的汉学家看来,文学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知识。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乔森纳·卡勒指出:“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呈现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理念,一种被赋予若干功能的、特殊的书面语言。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中,文学被作为一种说教课程,负有教育殖民地人民敬仰英国之强大的使命,并且要使他们心怀感激地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启迪文明的事业的参与者。在国内,文学反对由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滋生出来的自私和物欲主义,为中产阶级和贵族提供替代的价值观,并且使工人在他们实际已经降到从属地位的文化中也得到一种利益。文学对教育那些麻木不仁的懂得感激,培养一种民族自豪感,在不同阶级之间制造一种伙伴兄弟的感觉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还起到了一种替代宗教的作用。”(注:乔森* 纳·卡勒《文学理论》38页,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文学的性质并不能够孤立地确定,文学作为一种知识总是与其它知识共处于一个知识的网络之中的,它的内涵是由与其它知识的关系来决定的。而现代文学独立的要求是与整个现代知识的分化相关的,是现代性知识逻辑推展的结果。现代纯文学的观念是在现代科学、道德、艺术分治的原则之上展开的。在现代纯文学观念的背后,有着现代性叙事的支配与制约。
自现代文学观念形成,我们开始把文学作为一个自律的领域。我们通常将纯文学的观念未经反思地和非历史地使用,并且因此把其它不同的文学观念轻易地排斥和否定掉。实际上,文学是一个历史地生成和不断变化的概念。郭绍虞对于文学观念的理解存在着本质主义的倾向。他说:“自周秦以迄南北朝,逐渐演进,文学逐渐正确。”然而,同时,他也意识到文学是一个历史的变化的概念,指出文学与文人的产生都是一种历史的现象。“范晔《后汉书》之所以必列《文苑传》,正是为了当时有毕力为文章,而其他无可表见的人,才辟此一栏的。使其有学问自可表见,则尽可列之《儒林传》中,何必别立名目呢?大抵自楚以后,而后世有专工于文之人;自东汉以后,而后史有专以文名之传;自晋以后,而后书有专重于文之集;自南朝以后,而后著录有专载部之目。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篇》谓‘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这诚然是一变,因为到这时候,是文学与学术分离之渐。”(注: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照隅室古曲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鲁迅认为,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也就是说,接近于现代的文学观念在当时已经产生了。萧统《文选》将文学与其它的书写物区别出来提出了文学的定义:“事出于深思,义归乎藻翰。”萧绎发现知识是在不断地分裂的,他以历史的发展来界定文学:“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性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注:萧绎《金楼子·立言》,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文学的观念在不断地发生着分裂和蜕变;然而,文学观念本身又形成了一个脉络。在文学内部,诗与文又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文以载道”/“诗言志”构造了中国的文学发展的不同传统。散文处于比诗更正统的地位,诗歌则是一种更具有个人性和抒情性的文学类型。不仅散文与诗歌之间存在着这种文学等级的差异,而且在诗歌的内部,同样还有“诗言志”与“诗缘情”的进一步分化和区别,这种性质上的差别也构成了等级上的判断。
在五四文学革命对“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批判中,艺术自律的文学观念得到了鲜明的凸现。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文学彻底摆脱传统经学附庸的地位获得了独立,甚至被置于中心地位。
1917年文学革命的发生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新文学与几千年的古典文学传统发生了深刻的决裂。中国现代文学无疑与“现代”相关,“现代”的概念又常常是与“新”的概念相联系的。中国现代文学通常单纯是指“新文学”。但是作为新文学的“新”和古代“为赋新诗强说愁”中“新”的涵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时代概念,它并不是指1917年以后中国所有的文学实践。它既是一个肯定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排斥的概念。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曾经对中国的现代作出了经典的诠释,同时它也规范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践。中国现代文学是科学民主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同时,它还包括了白话文这一新的语言实践。80年代以来,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出,现代文学的概念内涵进一步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统括在广泛的现代化的概念之下。然而,不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还是中国新文学,都共同建立在一种具有整体性特点的现代论述的基础之上。
在20世纪中国,文学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性质。“文学”这一概念经过不断的重新诠释,具有不同的内涵。在《现实主义的限度》一书中安德森说,没有任何概念像现实主义这个聚讼纷纭的概念这样,对中国现代的创作与批评产生了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同样,在现代,经过不断重新诠释的“文学”这一概念,对中国现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被赋予了知识和价值重整的重要功能。文学革命发生于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知识崩溃以及现代知识发生的时刻。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代替了传统经学同样核心的功能。它为中国现代的发展提供了一套整体性的叙事和历史想象。安德森说:“由于与生俱来的重大责任感,中国现代文学远远不止于反映时代的混乱状态。中国知识分子是在政治改革失败之后才决心从事文学工作的,因此他们是怀着一种特定的目的来进行文学活动的。他们认为,文学比政治更能发生深刻的影响,一种新的文学将会通过改变读者的世界观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变革开辟道路。”(注:Anderson,The Limits of Realism: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wlution,P.3.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1990.)
我们一直非难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尤其是80年代以来,“回到文学自身”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文学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使文学获得艺术的独立地位,文学独立的思想受到特别的推崇。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似乎压抑和降低了文学的地位,然而,实际上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神话的建立是由于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并且主要地是由于启蒙主义文学而建立起来这种声望的。从晚清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等人均是以非文学者的身份来提倡文学的,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的发生都不是用所谓“文学自律”能够解释的,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的发生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变化有着直接和紧密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很难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怎样才是处于一种正常的状态。中国现代文学既受政治“压抑”和“干扰”,同时文学的地位又空前提高,文学发生了重要的作用,文学对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叙述过他从事文学活动的动机,认为文学不是一种普通的职业,而是可以用于改造民族的灵魂。鲁迅叙述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看到日本有关日俄战争的幻灯宣传片上有中国人被日军当作俄国间谍砍头示众,而画面上的中国人显出麻木的神情。这一事件促成了鲁迅从医学转向文学。他说:“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注: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这是一个现代文学家诞生的寓言。
鲁迅参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到钱玄同的鼓励,他在《呐喊·自序》中叙述了有关启蒙主义写作的“铁屋子”的隐喻。“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他的朋友回答他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是中国现代启蒙文学的一个寓言式的表述。
启蒙的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与纯文学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文学观念内在的紧张。梁启超将文学纳入到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之中,五四文学革命同样也是一场启蒙主义的文学运动。实际上,鲁迅最初从事文学运动就深受梁启超“新民说”及其启蒙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他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注: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511-5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出现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两次思想启蒙的高潮,它们尤其重视文学的力量。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时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注: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陈独秀在起来响应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之文学。”在五四前夕,傅斯年说:“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现在有思想革命的萌芽了。”“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建设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须放在新文学的里面……所以未来的中华民国的长成,很靠着文学革命的培养。”(注: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改革》,《新潮》第1卷5号(5,1919)。)茅盾说:“中国自有文学运动,遂发生了新思潮新文学两个词……新文学要拿新思潮做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学做宣传。”(注:雁冰《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3卷1号(9,1920)。)他说:“自来一种新思想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做先锋队,借文学的描写手段和批评手段去‘发聋振聩’。……自来新思潮的宣传,没有不靠文学家做先锋呀!”(注:佩韦《现在文学家责任是什么?》,《东方杂志》17卷1号(1,1920)。)1915年10月停刊的《甲寅》月刊上,刊载了黄远庸与编者章士钊的通信。黄远庸说:“愚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国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为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注:黄远庸《释言》,《甲寅》1卷10号(10,1915)。)胡适把它称为“文学革命的预言”。黄远庸把中国的变革最后归结到文学的力量上。中国现代的文学变革总是与社会政治的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又是由于文学本身的特点,借助于艺术本身的特殊力量。郑振铎在《文学与革命》中说:“要说单从理性的批评方面,攻击现制度,而欲以此说服众人,达到社会改造底目的,那是办不到的。必得从感情方面着手。好比俄国革命吧,假使没有托尔斯泰的这一批悲壮写实的文学,将今日社会制度,所造出的罪恶,用文学的手段,暴露于世,使人发生特种感情,那所谓‘布尔什维克’恐也不能做出甚么事来。因此当今日一般青年沉闷时代,最需要的是产出几位革命的文学家激刺他们的感情,激刺大众的冷心,使其发狂,浮动,然后才有革命之可言。……我相信,在今日的中国,能够担当改造的大任,能够使革命成功的,不是甚么社会运动家,而是革命的文学家。”(注:西谛《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号(7,1921)。)郑振铎强调文学情感和心理的力量。他说:“我们要晓得文学虽是艺术,也能以其文学之美与想象之美来感动人,但却决不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反而言之,却也不是以教训,以传道为目的的。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泄于文学上的。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感情之邮。诗人把他锐敏的观察,强烈的感觉,热烘烘的同情,用文字表示出来,读者便也会同样的发生出这种情绪来。”他说:“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注:西谛《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5,1922)。)通过情感的作用,文学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力量和社会动员方式。黄远庸很早就强调文学的特殊规律及其特殊价值:“文艺家之能独立者,以其有人生观。人生观之结果,乃至无解决,无理想,乃至破坏一切秩序法律及世俗之所谓道德纲常;而文艺家无罪焉!彼其实在写象,象如是现,写工不能不如是写;写工之自写亦复如是。故文艺家第一义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技无工拙,存乎其人,天才亦半焉!吾国人之文学家,好称文以载道;而所谓古文学者,十有七八如此!大抵论教必尊孔,论伦理必尊礼教;论文必尊所谓古文;皆吾所谓专制一孔之见,其于今日决当唾弃!”(注:黄远庸《朱芷青征赙序》,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427页,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黄远庸否定了“文以载道”和“诗无邪”的传统观念,肯定了文学独立的价值。在他看来,文学的目的追求是真实。它要求打破一切旧的束缚而自我立法。而另一方面,文学是新社会的
立法者,是新的人生观的缔造者。
俄国克鲁泡特金说:“没有哪一国的文学曾像在俄国一般的占着重要位置。没有哪一国的文学曾经对于后起青年有那么直接而且深刻的影响像在俄国一样。……这原因是明白的。俄国没有公开的政治生活,……结果就使全国最优秀的人选择了诗歌、小说、讽刺,或文学批评,作为媒介,来发泄他们的感兴,他们的民族生活的概念,或他们的理想,……要想懂得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理想,翻他们的蓝皮书或打听他们的新闻界领袖是不中用的,中用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去研究他们的艺术。”(注:沈泽民《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论》,《小说月报》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9,1921)。)在中国,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替代功能。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意味着中国处身于一个陌生的生活情境和面对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而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重构生活经验和阐释陌生的生活情境的过程,它通过文学丰富的想象力和情感作用去弥合破裂和崩溃的生活世界,通过文学的想象力去重构和规划新的生活世界。
二、文学独立
在《国故论衡》中,章太炎对于文学的价值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篇章无计簿之用,文辩非穷理之器。”(注:章太炎《国故论衡》120页,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3年。)他从小学出发,来建立他的文学论:“余以为书籍得名,实凭傅木而起,以此见言语文字,功能不齐,世人经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纶,此皆后儒训说,非必欲其本真。案经者,编比缀属之称,异于得名以下用版者,……是故绳线联贯谓之经,簿书记事谓之专,以竹成册谓之仑,各从其质以为之名。”因此,他认为,“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修辞立诚其首也。气乎德乎,亦末务而已矣。”(注:章太炎《国故论衡》73-74页,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3年。)章太炎是从文字出发来认识文学的,他否定了情感与想象在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后人认为,章太炎的文学观是浑沌的,即属于前现代的。然而,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书在对于晚清文学的叙述中,表达了对于章太炎文学思想的极端推崇。他说:“章氏论文,很多精到的话。他的《文学总略》推翻古来一切狭陋的‘文’论,说‘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他承认文是起于应用的,是一种代言的工具;一切无句读的表谱簿录,和一切有句读的文辞,并无根本的区别。至于‘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和‘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区别,更不能成立了。这种见解,初看去似不重要,其实很有关系。有许多人只为打不破这种种因袭的区别,故有‘应用文’与‘美文’的分别;有些人竟说‘美文’可以不注重内容;有的人竟说‘美文’自成一种高尚不可捉摸,不必求人解的东西,不受常识与理论的裁判!”(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实际上,胡适“言之有物”的文学思想不是从儒家“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出发的,而是根源于章太炎“修辞立诚”的理论。胡适在《什么是文学》中认为:“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他说:“文学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胡适认为,文学不过是最能尽职的语言文字,因为文学的基本作用(职务)是达意表情,因此,他认为,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把情或意,明白清楚地表出达出,使人懂得,使人容易懂得,使人决不会误解。同时,胡适把文学的美也附着于第一个条件,他否认孤立的美的存在,认为美就是明白与有力的表达。胡适否认当时“纯文学”与“杂文
学”的区分:“我不承认什么‘纯文’与‘杂文’。无论什么文(纯文与杂文、韵文与非韵文)都可分作‘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两项。”由此可见,胡适深受汉学家的文学思想的影响,并且因此否定现代的纯文学观念和文学自律的理论。陈独秀强调文学独特的性质,强调“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区别,并且批评胡适“言之有物”的文学理论:“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注:陈独秀《答胡适之》,原载《新青年》2卷2号(10,1916),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茅盾也同样强调文学自身独立的性质。他说:“艺术家是拿艺术品的自身做目的,决不与旁人相干的。”(注:佩韦《艺术的人生观》,原载《学生杂志》7卷8号(8,1920),《茅盾全集》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实际上,在汉学内部对于文学存在着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论述,在汉学的内部为文学与学术分化以及文学独立观念的发生提供了理论资源。阮元从六朝的文笔论开出了“文言说”。刘师培发展了阮元的“文言说”,从“骈”与“散”的对立中和《文选》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藻瀚”的文学传统出发,来确立文学的特性。章太炎抹杀文学与学术的区别,而刘师培则明确地区分了文学与学术的不同性质:“贵真者近于征实,贵美者近于饰观。至于徒尚饰观,不求征实,而美术之学遂与征实之学相违,何则?美术者以饰观为主也,既以饰观为主,不得不迁就以成其美。”他说:“盖美术以性灵为主,而实学则以考覈为凭。若于美术之微而必欲责其征实,则于美术之学反去之远矣。”(注:刘师培《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左盫外集》卷十三,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美术是当时对于艺术的总称。1913年,鲁迅为教育部所撰《擬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出,译自英之爱忒(art or fine art)。”与章太炎建立在小学基础上的文章观念不同,鲁迅首先强调艺术虚构和幻想的性质:“然所见之物,非必圆满,华或槁谢,林或荒秽,再现之际,当加改造,俾其得宜,是曰美化,倘其无是,亦非美术。故美术者,有三要素:一曰无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缘美术必有此三要素,故与他物之界域极严。”其次强调艺术的真实与非功利特点:“顾实则美术诚谛,因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注:鲁迅《擬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根据许寿裳的说法,章太炎有关学术与文学的议论是针对当时与周氏兄弟的分歧。而鲁迅、周作人最早的文学论文正好发表在刘师培主编的《河南》杂志上。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对于“诗歌之力”的描述,很容易使人想起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有关“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夫有四种力”的论述。梁启超讲“熏”、“浸”、“刺”、“提”,鲁迅也同样是从主观的心理方面来描述文学的力量与作用。鲁迅和周作人开始走上文学的道路都是由于受到了梁启超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影响,是从梁启超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念出发的;然而,他们在《河南》杂志发表的论文,却已经对梁启超的文学观进行了批判,转向自主的文学观念。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卷。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注: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批评时人对于文学的理解“昧于文章之义”,“惑于裨益社会,别长谬见”。他说:“实用之说既深中于心,不可复去,忽岁异书而不得解,则姑牵合经为之说耳。故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各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说始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篇。别有人论之者曰:‘夫立宪之国,期于人人有自治心。何经使能自治,则唯投其心之所好而治之。’斯又将以小说范人心,代卧碑之用矣,可姑无论。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欲言小说,不可不知此义。而今有人作,或曰:此历史小说,吾将以之教历史焉。不知历史小说乃小说之取材于历史,非历史而披小说之衣也。而《爱国二童子传·序》中则又痛哭流涕,乞读者之致力商工,彼殆以是为实业小说,因寄其意乎?手治文章而心仪功利,矛盾奈何!”周作人接受了浪漫主义的情感说的文学观,批判启蒙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确立了文学自身的规范和特殊的价值意义。“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又当摈儒者于门外。”(注:独应《文章之意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7年。)他批评了传统儒家的“诗教”和启蒙主义功利主义文学观,明确提出了文学独立的思想。
王国维最早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是第一个强调文学独立的价值、肯定文学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的人。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说:“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他批判和抨击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他说:“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矣吾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他说:“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注: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文集》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鲁迅后来说,文学是余裕的产物,也正是同样的意思。王国维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建立在康德、席勒和叔本华的美学思想之上。康德认为艺术无关乎利害,席勒把艺术和游戏联系起来。王国维将文学视为一种脱离了功利的纯粹知识。文学在社会功利价值之外,具有独立自足的审美价值。我国现代的纯文学观念是通过王国维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国维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注: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王国维追求文学独立,批判了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他不仅是对于传统的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否定,同时也与梁启超所代表的现代启蒙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形成了明显的张力。他说:“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他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说:“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故除吾人之感情外,凡属于美之对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质也。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无他形式以表之,惟经过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谓古雅
,即此第二种之形式。即形式之无优美与宏壮之属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种独立之价值,故古雅者,可谓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王国维强调古雅属于形式本身,而不属于内容。他说:“夫然故古雅之致存于艺术而不存自然。以自然但经过第一形式,而艺术则必就自然中固有之某形式,或所自创造之新形式,而以第二形式表出之。”可见,形式有其特殊的独立的价值。这也是他与章太炎、胡适等人的实证主义文学观念的根本区别。
王国维的纯文学的文学观与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学观构成了现代文学观内部的矛盾。梁启超的启蒙主义的现代文学观附属于启蒙现代性,其传播的过程是现代性知识在中国扩张的过程。然而,王国维的纯文学观属于美学现代性的范畴。美学现代性与现代资产阶级世俗现代性的推展形成了对照。美学现代性是对于资产阶级世俗现代性的批判。王国维说:“新人文派之思想感情,对彼实利之人生观,实为一有力之反动,而二者之争执,迄于今日,犹未已也。”(注:王国维《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王国维的纯文学思想同样是现代性的一种逻辑展开。正如章太炎对于严复的“名的世界”这个功能世界的解构与批评一样,王国维也同样从人的目的性与主体性出发,对于现代合理化和功能化的世界进行批判,从价值理性出发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他为了反抗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理性,从人的主观意志出发构造了新的理性——生命的非理性。王国维通过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批判现代科学理性的合理性。王国维对于梁启超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进行了否定与批判。然而,这样一种对立又存在于现代性的内部。
王国维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知识:文学与科学。科学的知识是客观的,文学的知识是主观的。普通的知识是为了求真,具有功利的目的;然而,文学是一种纯粹的知识,是为了求得意志的解脱。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尼采生命哲学的影响,认为人的本质为意志。人的意志与科学知识往往互相冲突。人类的知识无不服从于充足理由律,然而只有文学不必受充足理由律的束缚与限制。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王国维引用叔本华《世界作为意志和表象》定义文学说:“美术者,离充足理由之原则,而观物之道也。此正与由此原则观物者相反对。后者如地平线,前者如垂直线;后者之延长虽无限,面前者得于某点割之;后者合理之方法也,惟应用于生活及科学;前者天才之方法也,惟应用于美术;……”他说:“由叔本华之说,则充足理由之原则非徒无益于天才,其所以为天才者,正在离之而观物耳。……最大之知识,在超绝知识之法则。”(注: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王国维从康德的形式美学和席勒的审美游戏出发,将文学视为完全脱离了功利的纯粹知识。王国维与梁启超不同的是,梁启超是从政治改良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学作为改革社会的工具,而王国维却是将文学置于艺术的范畴,探讨文学本身独立的价值,探讨文学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及文艺美学的各种问题。
在晚清,作为“纯文学”的知识是不断分化、不断生成的。这种分化和生成是一个复杂的现代知识内部关系的重新配置和对话过程。经过晚清“小说界革命”,小说和文学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之后,吕思勉将晚清大大扩大了内涵,同时被神话化和过分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小说以及文学概念重新进行剖析,鲜明地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他说:“近顷竞言通俗教育,始有欲藉小说、戏剧等,为开通风气、输入智识之资。于是杂文学的小说,要求之声太高,社会上几视此种小说,为贵于纯文学小说矣。夫文学与智识,自心理上言之,各别其途;即其为物也,亦各殊其用。开通风气,贯输知识,诚其要务矣。何必牵入于文学问题?必欲于二者相牵混,是于知识一方面未收其功,而于文学一方面,先被破坏也。”他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样一种观点并不能概括文学的全部性质。他说:“凡号称美术者,决无专以摹拟为能事者也。……夫美术者,人类之美的性质之表现于实际者也。”他认为,艺术创造包括了四个不同的阶段:模仿、选择、想化、创造(注:成之《小说丛话》,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美学现代性肯定“为艺术的艺术”即艺术独立的要求,它是对于资产阶级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同时,艺术独立又是现代知识合理分化的结果。黄远庸在《晚周汉魏文抄序》里说“古无分业之说,其思想论辩不由名学,故常以一科之学,包举万类。欧洲古代学者,举一切物理心理政治道德之理论,悉归于哲学,吾国自古亦以一切学问,纳之于文”,“若夫文学,在今日则为艺术之一部,……故文学者,乃以词藻而想化自然之美术也。其范畴不属于情感,不属于事实,其主旨在导人于最高意识,非欲以之濬发知虑,故最简明之解说曰:文学者,为确实学术以外之述作之总称,而通常要以美文为限,其他种纪载而词旨优美者,只能名为有文学之趣味,不能名为独立之文学。……吾国既公认为文学之国,自古著作若干万卷,殆无一不有文学之趣味,其足供吾人之咀嚼而涉猎者,或毕生莫能尽,必将条分缕析,发挥光大,此亦文艺复兴之说也。”(注:黄远庸《晚周汉魏文抄序》,《远生遗著》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也提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注:《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12卷1号(1,1921)。)因此,现代的文学独立包含了复杂的动力。它既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推论,同时又是对于现代性的反抗与批判,是现代性复杂的、辩证的展开。
文学独立的观念首先是现代知识分化的结果,王国维对于文学独立地位的呼吁与现代大学兴起、现代学科分化的背景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对照。这一背景在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的《文学论》里交待得非常清楚。朱希祖就是从现代知识分科来批评他的老师章太炎的文学观的浑沌未析状态的。他说:“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以与其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然而,他所依据的则是现代知识分化的逻辑:“自欧学东渐,群惊其分析之繁,……政治,法律,哲学,文学,皆有专著;……故建设学校,分立专科,不得不取材于欧美或取其治学之术以整理吾国之学……。在吾国,则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在欧美则以文学离一切学科而独立。”(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7卷5号(4,1920)。)
胡适的文学思想深受章太炎以及汉学家的文学观念的影响,相对现代已经合理化地分化了的纯文学观念来说,其文学概念是混沌的。然而,我们今天的纯文学观念同样不过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因此它们很难说有高下之别。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它不仅是历史地生成的,而且它本身也处于一个特定的知识网络之中。王国维的纯文学观念是在一定的知识条件下才得以浮现出来,而黄远庸也正是从现代知识的分化中来谈论和“发明文学独立”的。胡适从汉学家的文学观念出发所产生的“言之有物”的文学思想,既与王国维以及鲁迅的文学思想构成了对立,同时实际上也不同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胡适“言之有物”的文学思想更彻底地否定文学的独立性,因此也很容易被纳入到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功利主义文学范畴之中去。
文学革命对于传统文学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导致了传统文学观念的崩溃。因此,对于文学的定义也即文学观念的重建成为了五四时期文学理论建设的一个迫切和自觉的要求。《文学旬刊》第1号上,郑振铎发表了开宗明义的《文学的定义》一文。他说,文学的定义,像罗家伦那样可以直接到《英国百科全书》中去寻找。然而,郑振铎是从文学与科学的区别和差异中来建立文学的认识的,也就是说,强调文学与一般科学知识的对立与区分。他认为,文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一)文学是诉诸情绪,科学是诉诸智慧。(二)文学的价值与兴趣,含在本身,科学的价值则存于书中所含的真理,而不在书本的自身。……文学的价值与兴趣,不惟在其思想之高超与情感之深微,而且也在于其表现思想与情绪的文字之美丽与精切。他强调文学与情感和想象的关系。不同于科学的认识,文学是以情感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的(注:西谛《文学的定义》,《文学旬刊》第1号(5,1921)。)。严既澄说:“我们很可以相信文学永远不会自绝其生命而寄生于科学的身上”,“在文学界里,本来就没有要烦科学来插嘴的事情。哲学上的直觉(Intuition),心理学上的内观(Introspection),都是科学所极力排斥的,以为是毫无根据,不成方法的,然而这两种作用,在文学上,便占了重要的位置。想象是科学所轻视的,然而一入了文学界里,他就成了文学的主要原动力。文学可以和科学立于反对的地位,于此可见了”(注:既澄《自然与神秘》,《文学旬刊》77期(6,1922)。)。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对于文学实际存在着一次认识上的明显断裂;然而,早在白话文运动中,傅斯年就指出:“做白话文学,专靠讲究规律,已经落了第二乘了。文学原是仗着才气,兴致,感情,冲动。”(注: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1卷2号(2,1919)。)在五四时期,尤其是随着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新文学社团的出现,纯文学的观念通过浪漫主义的情感说被普遍地接受了。即使是通常被认为与“为艺术的艺术”的创造社相对立的文学研究会也同样认同浪漫主义对于文学的理解,即一种对于情感说的文学观的肯定,以及隐然把文学与天才联系起来。他们认为,文学与科学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对象与范畴。文学表现的对象是情感,而知识则属于科学的范围。
五四时期不仅确立新的纯文学的文学观念,否定传统的文学观念,同时也从根本上否定和摧毁了传统文学的格局与体制。周作人指出:“现代的中国小说,还是多用旧形式者,就是作者对于文学和人生,还是旧思想;同旧形式,不相抵触的缘故。作者对于小说,不是当他作闲书,便当作教训讽刺的器具,报私怨的家伙”,“所以司各得小说之可译可读者,就因为他像史汉的缘故;正与将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学了一点,便古今中外,扯作一团,来作传奇主义的《聊斋》,自然主义的《子不语》。”他又认为中国的讽刺小说“形式结构上,多是冗长散漫,思想上又没有一定的人生观,只是‘随意言之’。问他著书本意,不是教训,便是讽刺嘲骂诬蔑。讲到底,还是‘戏作者’的态度,……总是旧思想,旧形式。即如他还用说书的章回休,对偶的题目,这就是一种极大的束缚,章回要限定篇幅,题目须对课一样的配合,抒写就不能自然满足。……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正同旧诗旧词旧曲的形式,装不下诗的新思想一样”,“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所以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但其先又须说明小说的意义,方才免得误会,被一般人拉去归入子部杂家,或并入《精忠岳传》一类闲书——总而言之,中国要新小说发达,须得从头做起;目下所缺第一切要的书,就是一部讲小说是什么东西的《小说神髓》”(注: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5卷1号(7,1918)。)。
1921年茅盾革新《小说月报》,发表了《改革宣言》,明确主张以西方文学的历史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对照。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1期发表了他的《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一文,意在廓清对于文学的传统误解。他对“文学者”身份的确认,实际上也就是对于文学的“正确”定义的寻找。文章开头提出:“我们试把一部二十四史翻开来,查查他们的文苑列传,我们——如果我们的思想是不受传统主义束缚的——要有什么感想?我们试把古来大文学家的文集翻开来,查查他们的文学定义(就是当文学是一种什么东西),我们更要有什么感想?”茅盾说,第一,我们历来的文学者都是帝王的“弄臣”。“所以,在中华的历史里,文学者久矣失却独立的资格,被人认作附属品装饰了。”第二,文学者本身对于文学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个是文以载道,一个是把文学当作消遣品。茅盾庄重地提出:“文学到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他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有他研究的工具,便是诗(Poetry)剧本(Drama)说部(Fiction)。文学者只可把自身来就文学的范围,不能随自己的喜悦来支配文学了。文学者表现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用艺术的手段表现出来。”茅盾在《文学旬刊》第1号上发表了《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他说:“第一误在不明白文学是什么东西;第二误在不明白这些集子是什么东西。第一误必须引用西洋的学说来解说明白”,“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由于一向只把表现的文学看做消遣品,而所以会把表现的文学看做消遣品的原因,由于一向只把各种论文诗赋看做文学,而把小说等视为稗官野乘街谈巷议之品;现在欲使中国艺术复兴时代出现,惟有积极的提倡为人生的文学,痛斥把文学当做消遣品的文学观念,方才有点影响”。
文学革命一方面使文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重建了文学以及整个知识的秩序。郑振铎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中说:“中国的书目,极为纷乱。有人以为集部都是文学书,其实不然。《离骚草木疏》也附在集部,所谓‘诗话’之类,尤为芜杂,即在‘别集’及‘总集’中,如果严格的讲起来,所谓‘奏疏’,所谓‘论说’之类够得上称为文学的,实在也很少。还有二程(程灏、程颐)集中多讲性理之文,及卢文弨、段玉裁、桂馥、钱大昕诸人文集中,多言汉学考证之文。这种文字也是很难叫他做文学的。最奇怪的是子部中的小说家。真正的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等倒没有列进去。他里边所列的却所是那些惟中国特有的‘丛评’、‘杂记’、‘杂识’之类的笔记。”郑振铎指出,“中国文学所以不能充分发达,便是吃了传袭的文学观念的亏。大部分的人,都中了儒学的毒,以‘文’为载道之具,薄词赋之类为‘雕虫小技’而不为。其他一部分的人,则自甘于做艳词美句,以文学为一种忧时散闷、闲时消遣的东西,一直到了现在,这两种观念还未完全消灭。便是古代许多很好的纯文学,也被儒家解释得死板板的无一毫生气”,“我们研究中国文学,非赤手空拳,从平地上做起不可。以前的一切评论,一切文学上的旧观念都应一律打破。无论研究一种作品,或是研究一时代的作品,都应另打基础,就是许多很好的议论,我们对他极表同情的,也是要费一翻洗刷的工夫,把他从沙石堆中取出,而加之以新的发明,新的基础”(注: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文学旬刊》51期(10,1922)。)。郑振铎在《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研究》中说:“第一,我觉得新文学运动,不仅要在创作与翻译方面努力,而且对于一般社会的文艺观念,尤须彻底的把他们改革过。因为旧的文艺观念不打倒,则他们对于新的文学,必定要持反对的态度,或是竟把新文学误解了”,“第二,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故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譬如元明的杂剧传奇,与宋的词集,许多编书目的人都以他们为小道,为不足灵的;而实则它们的真价值,却远在《四库全书》上所著录的元明人诗文集以上。比如,他们先存一个凡是诗必是五七言,必定押韵的传统观念,所以就一定要反对新诗。同时,他们也会对于文学产生误解* ,如把《堂吉诃德》当做《笑林广记》看了。我们要打翻这种旧的文艺观念,一方面固然要把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诗,以及其它等等的文学原理介绍进来,一方面却更要指出旧的文学的真面目与弊病之所在,把他们所崇信的传统的信条,都一个个的打翻了”(注: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14卷1号(1,1923)。)。文学革命引起了文学观念的断裂,同时也造成了文学史的改观,文学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学史往往是百科全书式的罗列,内容十分庞杂,常常包括了经学、文字学、诸子学、史学等,而真正的文学脉络却湮没在这样一种浑沌不分的知识之中。文学革命之后,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为代表的新的文学史著作成为一种纯文学史。《白话文学史》不仅开创了文学史学科典范,而且重新厘定了文学的界线,确定了文学的内涵。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胡适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章太炎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国故论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