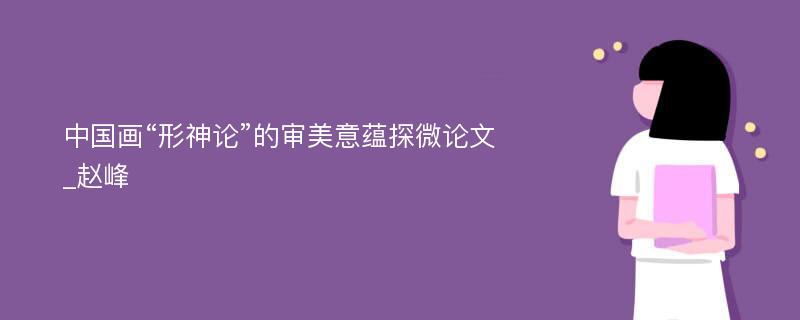
摘要:形与神是中国画论最主要的范畴之一,由于“形神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对形神的探讨,人们往往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神”这一概念上,从而忽略绘画作为造型艺术,“形”也应当是我们关注的概念。“画,形也。”(《尔雅》),“形”作为造型艺术的基本要素,在中国画论中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绘画反映生活离不开具体的形,它是用形象来说话的,因此没有形象就没有绘画。特别是在人物画中,“形”塑造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创作对象的“神”的传达,而“形”的塑造又涉及“骨法用笔”,即用线造型的问题。线条成为形与传神之间的立足点。而“意”的提出又为“以形写神”创造了条件。因此,从形、神、意三者的关系来看也就是“以形写神,意得神传”的关系。
关键词:形神;以形写神;意线
第一节、形神的本质内涵
在韩林德先生的《境生象外》一书中,他指出古代哲学中的形神概念包涵三个层次方面的含义:“其一,形指宇宙天地间一切有形之物,神指万物之本根、宇宙之造化功能,如《荀子•天论》云:‘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淮南子•原道训》云:‘神托于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总。’其二,形指生物机体,神指生物的生命活动于生理机制,如《淮南子•原道训》云:‘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其三,形指人的身体,神指人的精神意识,如葛洪《抱朴子•至理》云:‘形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嵇康《养生论》云:‘形恃神而立,神须形以存。’”由于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影响至大,因此,那种在形神统一的基础上强调神主宰地位的观点始终居于支配位置。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美学家开始自觉地将哲学领域中的形神观引入到绘画艺术领域,其标志则是东晋顾恺之在人物画领域提出传神论。在顾恺之之后,围绕“形神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使“神”的观念变得十分复杂。在宗炳的《画山水序》中,曾多次提及神的概念,一是圣人的“以神法道,法道的结果是嵩华有秀,玄牝有灵,万趣融其神思”,也就是说客观物象中含有“神”;二是“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讲的是神和理进入画面形象。因为神是无形之物,所以须依赖于有形的事物,这就是说画面形象上也可以含有神;三是“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这就是说我可畅神,主观中也会有神。按宗炳的论述,神存在于客观的山水、主观的我和画面形象三者之中。而按照我们现在普遍的理解认为:神是创作对象所呈现出来的性格、表情、心理活动、精神气质等比形更为内在的、本质的东西。画家在写生或创作时,不仅要抓住对象的形,还要抓住对象的内在气质,以对象的五官、形体、动势,甚至手指的小动作,抓住表现人物内心的细节,以达到“神似”。这是以人物画方面来讲的。其实草木未必无情,山水中也有灵秀,万趣融其神思,一切事物都有超越事物本身的精神性的东西存在,无论这种精神性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还是通过移情所产生的,岂只人物中才可有神的存在? 这符合中国画的思维方式,但这也无法准确地描述形和神的关系,神和形毕竟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绘画是造型艺术,形象是造型艺术的主要特征,我们就从造型的角度来探讨神的含义。画家进行创作,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感染和启发观众的。从造型的角度上看,造型的结果是形成画面形象,神的范畴也就只能对于画面形象而言,也就是说神是画面之形所包容的非形的东西,是形状所体现的形而上的精神内容与底蕴。形神关系即形本身和形所体现的、能被欣赏者所感知的精神性内容的关系。
据载,顾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阿睹指的是眼睛),从这事例中,我们可以作客观性的解释,即传神“阿睹”是通过形状来传客观之神。而徐渭的“笔底明珠何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是传主观之神。如何将这两种“神”从画面形象角度出发来理解呢?其实这只是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我们不必人为地将客观物象,主观精神和画面形象视为三种不同而且对立的事物,它们三者在中国画中是同一的,在画家眼里,这三者最终归结为画面形象。对于画面形象本身来讲,无论这个神是来自客观,还是来自主观,无论是抽象的哲理,还是具体的感受、它最终都要在画面形象上体现出来。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画造型的深入展开,画面形象所负载的精神内容将不仅局限在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因为整个创作过程的完成,还包括欣赏者的参与,由于欣赏者的参与,这种形象本身的精神性也就随之变化了,欣赏也是创造。客观的、主观的与形象的最终都成了形象本身的精神储藏,这种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内容为人的创造性的欣赏提供了可能。因为形象一经确定,就是千古不变的,所能变化的只是被欣赏者感知的画面形象的“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形与神在画面形象中是可以得到统一的,形既是客观物象之形的视觉整理,又是画家的意象在画面上的具体组织落实。神的概念也不单指对象之神,而是对象之神与画家主观之神的统一,为画面造型的精神底蕴。以形写神,形毕竟是传神的物质基础,得意忘形,却不能真的大象无形,形存神存,形亡神亡。而另一方面,神是“君形者”,是形的生命、形的目的。不为了神的形,是毫无意义的形。每个形都是神的形,而神须是有形之神。
第二节、形的探索
绘画是造型艺术,“形”是造型艺术的基本要素,它在中国画论中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回顾历代画论,以西汉时期的“君形者”(刘安《淮南子》)到现代的“似与不似之间”(齐白石《题枇杷》),不管对“形”是提倡还是排斥,“形”的概念始终作为论者据以阐发其艺术观点的重要的参照物。我们在前面就讲到形神在画面形象上是相辅相成的。对“形”的把握直接关系到对象“神”的体现,最终影响到画面形象。
一 中国画的认知方式
绘画是视觉艺术,首先需要眼睛这个视知觉的观察,中国画也是源起于一种观察,是一种认识论的结果。但中国画的认知方式是一种主客观统一的认识论,也就是古代画论中讲的“澄怀味象”、“凝神结想、悟对通神”等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画的认知方式不只是使用眼睛的功能去观察物象,而是调动全部的感受能力以及精神力量去体验客观事物,最终,认识的力量将物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达到天人合一的玄妙境界。这也正是中国画区别于西画的观察方式。
我们都知道“庄子梦蝶”的故事,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竟不知自己是蝴蝶变的,还是蝴蝶是自己变的。这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使两者具备了同一个生命与外形,主客观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个境界中消失了,不但忘却了我之为我,同时也忘却了物之为物。最终,一个新的合一的生命——意象诞生了。此时,画家的参照物既不是客观物象也不是内心的呼唤,中国画的认知方式在这一阶段的继续就变成了对“意象”的进一步体验、反复锤炼,直至成为画面形象。
总之,中国画的认知方式在一开始就和西画的认知方式存在区别,即中国画的认知方式是将客观物象放到胸中锤炼,做到胸有成竹,从而产生具有自己生命的意象。这个意象是可以有所取舍的,即可以根据最终的画面形象的需要来增减一些东西。这也就是所谓的“得意忘形”,但这里的“忘形”并不是说不要形,而是在有形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性的取舍,最终目的是使画面形象充分地活起来。
二 中国画的造型方法
中国画独特的认知方法必然会反映到中国画的造型方法上。首先,中国画在造形过程中,不注重客观物象因环境因素变化而变化的客观表象,如光影、明暗、色彩等,而是透过表象直接进入客观本相,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独特的笔墨语言的形式需要。这就使得中国画造型超越了对于纯粹视觉真实的追求,而致力于形状的平面化点线整理。客观物象变成主观的“象”,最终落实到画面形象上,客观的“神”与主观的意结合为画面造型所承载的形而上的东西。因此,画面形象与形象所表达的精神底蕴是不可分的,否则形象就会显得空洞苍白。
由于中国画的认知方法在造型上的这种体现,中国画的造型就不会象西画那样通过对物象明暗、体积等的刻画来进行,而是以线造型(当然还有平面造型,在这里暂且不谈)。中国画从其产生那时起一直到现在都在使用线条,悠久的线条使用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以书入画的传统财富,使线本身因工具材料的发挥而产生丰富的书意变化,也使线的使用有了独特的文化感,同时也使线条本身的形式美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欣赏价值。
三 形的内涵
中国画的认知方式产生了中国画独特的线造型,线的特性又规定着形的内涵。
“形”作为造型艺术的基本要素,在视觉艺术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现实主义的绘画,更应重视形象。绘画是立足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在处理“形”与艺术的关系上,我们强调应依据于“形”,可又不是按原本照搬于“形”,因为艺术必须要去表现在“形”的外壳里所隐藏着的内在的美的本质。绘画艺术就是要力求通过对外形的塑造,揭示出美的本质。正如席勒所说:“真正美的东西必须一方面跟自然一致;另一方面跟理想一致。”所以“形”必须是按照美的要求来规定,要达到美的要求就必须对“形”进行高度的概括,有选择、有目的地对形进行加工处理。比如顾恺之在《画云台山记》一文中强调张道陵要“瘦形而神气远”。这里讲的“瘦形”就是指概括简练,以少胜多的意思,“神气远”就是讲对本质的深刻揭示,也就是说要求以高度的抽象概括能力去揭示对象的本质。
莱辛说:“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写形”应符合美的标准,这样出来的作品才能够最大程度地达到传神的目的。现实主义绘画要做到正确地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特征,必须重视“形”在画面形象中的作用。对造型艺术而言,解决形象的造型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一个画家如果不能首先准确地抓住客观对象的形象特征,就很难谈得上揭示客观对象美的本质。
总之,“形”是绘画的基础,是绘画的起点,是达到美的手段。
“以形写神”也就是在熟练地把握住对象外部特征的基础上,去揭示出美的本质。这样,形就具备两层含义:一是写实的形,即画家在面对所要表现的对象时,首先应该抓住第一感觉把握对象的精神,做到“形准”,即解决形象的造型问题; 二是写意的形,也就是说在“形准”的基础上,按照美的要求,对“形”进行二次加工,概括提炼,创造出美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
[2]黄宗贤.二十世纪美术教育丛书.中国美术史纲要[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古代文学理论研究[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4]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J].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3):32 .
[5]伍蠡甫.文艺美学丛书———中国古代绘画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论文作者:赵峰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9月31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7/16
标签:形象论文; 中国画论文; 画面论文; 客观论文; 形神论文; 物象论文; 造型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9月31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