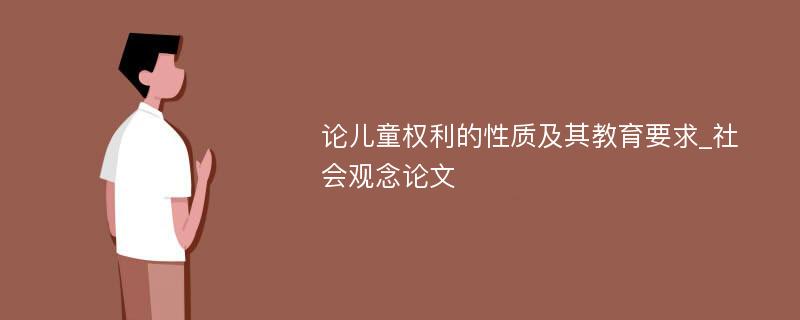
论儿童权利的本性及其教育诉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性论文,权利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09)01-0084-06
儿童享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即便家长、教师、一般社会公众乃至政府也是不能侵犯的。这意味着儿童权利不仅仅是儿童享有某些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的自由,同时它也对教育以及其他与儿童相关的人划定了行动的边界。尽管人们未必都在行动上尊重并认真对待儿童权利,但是,儿童权利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儿童享有自由和权利,它表达了一种对于教育的正当而又合理的诉求。对于教育来说,儿童权利或多或少给它“制造”了一些“麻烦”。这个“麻烦”表现在实践中儿童可能形成诉诸特定权利以对抗教育所提合理要求的偏好,会出现各种“过度维权”现象,这种“诉诸”、“维权”却因为儿童理性能力不足因而本身就是错误的。正是因为儿童理性能力薄弱,是一个不成熟的、发展中的个体,教育的存在才具有合理性基础。教育既要尊重儿童的自由和权利,但当儿童误用、滥用自己的权利时,教育又要予以必要的干涉。所以,教育是一种必要的强制。这样,教育中的儿童权利、儿童自由与必要的强制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紧张。儿童正是在权利、自由与必要的强制共同作用下,逐步成长为一个理性成熟的主体的。本文在辩护儿童权利本性的基础上阐释儿童权利的教育诉求。
一、儿童权利的本性
儿童权利从本性上来说,是儿童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根据道德以及法律的原则和规则而享有的资格,它从根本上保障着儿童的自由,护卫着儿童的利益,同时,课以他人以及社会尊重和认真对待儿童的一般性义务。
1.儿童权利预示着儿童资格。不论何种权利,如果要得到确证,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权利的根据,即是说一个人“凭什么”享有权利。说儿童享有某种权利,是说儿童享有如此这般地行动或者接受如此这般的待遇的资格。以资格来解释儿童权利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权利的来源上。“如果你有资格享有某物,那么,因他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而否认你享有它,就是不正当的。他人因你享有它而使你陷于不利或者使你受难,也是不正当的。”[1]那么,这种确定了儿童自由地行动或者接受某种对待的资格,并排除了他人因此而施加给儿童的种种不利或者非难的道德正当性其根据何在呢?换言之,儿童凭什么享有这种资格呢?其资格的来源就是道德、法律和习俗。道德、法律和习俗作为儿童权利的来源包含着规则和原则。“存在一项对某事的权利,就必定存在确定某种条件并宣布所有的、并且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才有资格享有它的规则和原则。”[1]12正是这些规则授予了儿童在法律和道德层面享有儿童自由行动和接受某种对待的权利。
道德和法律确立的规则和原则具有普遍性,通过它们,道德和法律确定了儿童享有具体的权利。小X并不因为他是小X而享有道德和法律所确认的儿童权利,他之所以享有儿童权利,全凭他是儿童。因此,对儿童权利来说,法律和道德在确认它们时至少要考虑三个根本性的理由:儿童是人;儿童是未成熟的和发展中的人;儿童是具体国家中的未成熟和发展中的人。就儿童是人而言,儿童有资格获享道德和法律确认的普遍人权。譬如,儿童享有生命权、不受专横干涉的自由权、免受精神和肉体虐待的权利等等。就儿童作为未成熟的和发展中的人而言,儿童有资格享有受到照顾的权利、受教育权等等。与一般的权利所具有的可选择性不同,儿童受照顾权和受教育权是排除选择的权利。就儿童是具体国家中的未成熟和发展中的人而言,儿童享有一个国家特定的道德和法律所赋予的具体权利。由于权利来源于一个国家的道德和法律所确立的规则和原则,受到一个国家的道德和法律传统以及现实社会条件的制约,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所确认的儿童权利的具体内容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这些差异可以概括地理解为儿童权利的文化差异。尽管儿童在一个具体国家中所享有的权利存在着特殊性,但是,受儿童作为人以及作为未成熟和发展中的人这两个根本因素的影响,儿童在特定国家中享有的权利也具有普遍性,它表现为儿童在具体国家中所获享的权利必定包含基本人权以及受到特殊照顾的权利。
正是一个国家中的道德和法律所内在蕴含的规则和原则,确认了儿童所获享的具体权利的资格。这些资格排除了他人侵犯、僭越和剥夺儿童权利的正当性,儿童有资格获得由权利所保障的正当利益,从而保障儿童自由成长和发展的根本条件。
2.儿童权利保障着儿童自由。权利与自由具有实质性关联。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自由是人的本质规定性。自由却是一个非常抽象和形而上的概念,而非一个实体概念。自由仅凭其自身难以完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得到保障,甚至当自由受到某种形式的侵犯时,如果不诉诸权利就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和补偿。因此,自由必须实质化为权利。仅仅谈论自由显然比较空洞,通过权利享有和权利行使,个体自由可以获得有力的保障。“自由首先总要表现为权利(rights),但是权利只是自由的逻辑形式,是自由的合法性表述,却还不是自由的实质。仅仅表现为权利的自由仍然是尚未实现的自由,是个not-yet,只有落实为事实的自由才是真实的自由。”[2]115权利的实质化,是说需要一种事实上的权利,即具有权力保障的权利。作为一种事实上的权利不是口头承认的权利,而是借助于权力保障的权利,只有事实上的权利才能够实现和保障自由。“真正能够保护一个人的自由的不是权利而是权力。权力是权利的实现方式,是权利的完成状态,如果不实现为权力,权利就是没有完成的目标。”[2]116权力保障权利,并通过保障权利而保障自由的问题,实质上是指权利的现实可能性问题。
在笔者看来,权力为权利所内在蕴含,权利不仅仅包括由它所设定的具体内容,而且还包括对于权利的要求权。一种没有权力的权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因为它随时可能受到不法的侵害而没有可以诉诸的强力。权利实现的前提是它在道德和法律上的正当性,这就内在地决定了权利具有可以诉求的力量。失却道德和法律上的正当性,权力就失去了合法性根据,从而,权利也就不成其为权利,因为它没有可以诉诸的力量,不但如此,它还会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干预。一种权利在其实现过程中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障碍或者困难,但就其作为权利而言,必定具有可以诉求的力量。因此,不管权利实现与否,权利与自由、权利和权力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是无法否定和取消的。借助于权利,人们划定了个人自由行动的界限,它规定了在何种疆域之内个体可以自由地行动。一个人的权利范围有多大,它的自由行动的范围也就有多大。
对儿童来说,自由的实质化问题更为重要和迫切,因为儿童缺乏必要的能力卫护自己的自由。在现实关系中,儿童自由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而遭受僭越、侵害甚至剥夺。面对自由遭受侵害或者剥夺,儿童常常不能够清楚地觉知,或者即便觉知,仅凭儿童自身也无力改变或者抗争。所以,儿童自由需要儿童权利加以保障,这意味着儿童自由必须实质化为儿童权利,并藉由法律和道德加以约束和保障。儿童的力量是薄弱的,但儿童借助于法律或者道德而获得一种权力,即对于权利的要求权或者权力权,以阻止他人对于自己自由的僭越。这意味着当儿童权利遭受侵犯、僭越甚至剥夺时,儿童(尽管通常是儿童的法定监护人)可以诉诸法律和道德的力量,要求终止这种侵犯、僭越或者剥夺,恢复儿童的自由。法律和道德经由权利对儿童自由施与的保障,给他人和社会的行动设置了必要限制,以约束他人或者社会能够道德地对待儿童。这样看来,只要某种自由表现为儿童的权利,即便当它遭受不正当的限定或者被取消而儿童并不觉知时,法律和道德仍旧可以对于僭越者施加某种强力,迫使僭越者停止对于儿童自由的侵害,从而实现对于儿童自由的保障。
3.儿童权利内蕴着儿童利益。儿童权利内在地蕴含了儿童的利益,这些利益在道德和法律层面得到了确认。损毁儿童的利益就必然侵犯儿童的权利,侵犯儿童的权利也必然损毁儿童的利益。儿童利益是儿童成长所不可或缺的善物,它们既可以是受到某种特别的照顾,也可以是“自由地实现……”,这些善物表现为能够促进儿童身体、心智和道德健康成长的活动、自由、机会、条件等等。儿童利益有别于儿童自身所欲求的任何善物,因为,儿童可能会受理性能力的限制把有害于自身健康成长的事物误认为是值得追求的善物。这就是说,并非儿童所欲求的任何一种利益都构成为一项儿童权利,尽管儿童所欲求的某些利益在成熟理性看来的确构成儿童权利。儿童正确地识别并合理地追求有助于自身健康成长和发展的善物,需要成熟理性加以引导和帮助。成熟理性的指导和帮助本身就是儿童的利益所在,是儿童的一项重要权利,并且相比于其他利益,这项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涉到儿童理性能力的成长。成熟理性对儿童的引导和帮助,其根本目的是确保儿童在身体、心智和道德方面的健康发展。
儿童不仅对成熟理性的指导和帮助有着要求权,而且有权利要求成熟理性对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指导和帮助不能侵犯和僭越儿童的基本权利。合乎道德、法律地对待儿童,不仅要求成熟理性的指导和帮助是为着儿童的利益,而且还要尊重儿童。否则,儿童的利益仍旧有可能受到损毁。很多损毁儿童利益的悲剧都是在“我是为了你好”这一动机下发生的。儿童权利为成熟理性针对儿童的行动设置了必要的限度,同时保障儿童的自由成长和发展的必要空间。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儿童限于理性的能力,是会犯错误的。儿童犯错误为儿童理性能力的成长提供了契机,儿童理性能力的成长是在“尝试——错误——修正错误——再次尝试……”的过程中实现的。于是,有一种观点宣称,犯错误也是儿童的一项权利,因为通过犯错误和修正错误有助于儿童理性能力的发展。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儿童理性能力薄弱是一个事实,基于这一事实,儿童犯错误是合乎情理的,但这不意味着它是正当的。促进儿童理性能力的发展固然与犯错误有着关联,但根源却在于修正错误。把儿童犯错误理解为儿童的一项权利,虽然看到了儿童理性能力薄弱这一事实,以及儿童犯错误对于儿童成长可能的价值,但是却误解了儿童权利的本质,简单地把一个事实问题同价值问题混淆在一起。倘或犯错误也是儿童的权利,那么,成熟理性对于儿童错误行为的干预其合法性何在呢?
因此,承认和尊重儿童权利就意味着承认和尊重儿童的正当利益,承认和尊重儿童的正当利益也就意味着承认和尊重儿童的权利。儿童个体在实现其正当利益时可能遭遇某种外在和内在的障碍,也可能对他人的正当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儿童的正当利益需要道德权利以及法律权利加以保障和限制。这既可以保障儿童正当地取得他所“应得”的利益,排除他人干预和阻难在道德和法律上的正当性,也可以限制这个儿童在追求和实现他的正当利益时可能给他人造成的侵害,从而保障他人的正当利益。显然,并非追求所有的利益都构成儿童权利,只有当一个儿童所寻求的利益具有道德或法律正当性,并且所采取的手段、方法合乎道德和法律的要求时,这样的利益才能够称作权利。由此可见,儿童权利内在地蕴含着儿童利益。
4.儿童权利课他人以义务。儿童权利是儿童根据一个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而享有从事某些行动的自由以及受到某种对待的资格。从消极意义上看,儿童是不成熟的个体,他们在身体、智力、道德等方面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他们的身体能力、心智水平、知识经验不足以让他们获得独立判断、独立生活的能力。从积极意义上看,儿童是成长中的个体,虽然他们的身心发展水平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但是,这种不成熟状态只是当下的、暂时的,随着生理发展水平的提高,生活经验的丰富,以及学校教育的正确引导和帮助,儿童可以逐步摆脱这种不成熟状态。正是因为儿童身心发展的这种不成熟性以及可发展性,一个社会的法律和道德针对父母、教师、一般社会公众以及政府有关儿童的行动设置了必要的限制。一方面,道德和法律强调,有些事情是父母、教师、一般社会公众以及政府不能对儿童做的,否则,在法律和道德上,这些针对儿童的行动就是错误的,并且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舆论的谴责。另一方面,父母、教师、一般社会公众以及政府承担着一些特别的义务,为儿童的健康和自由地发展创造必要的空间和条件。这意味着,儿童享有两种类型的权利:一种类型的权利是消极权利,就是免受不正当干涉的权利,它要求父母、教师、一般社会公众以及政府不能够肆意干涉、侵犯甚至剥夺儿童的某些权利;另一种类型的权利是积极权利,就是受到某种照顾的权利,它要求父母、教师、一般社会公众以及政府必须提供特定的帮助,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
因此,儿童权利意味着父母、教师、一般社会公众以及政府的责任担当,这个责任担当首先表现为不侵犯、僭越和否定儿童的自由,其次表现为对儿童权利所要实现的利益提供某种支持和保障。这是法律和道德根据儿童权利施加给父母、教师、一般公众以及政府的义务。儿童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那么,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他人就承担着不能剥夺或者限制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社会就有举办适当的教育机构来实现儿童受教育权的义务。如果没有人承担这样的义务,说儿童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则毫无意义,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就会成为空洞而不能实现的权利。儿童受照顾的权利也是如此。如果一项儿童权利没有与之相对的义务承担方,这项权利的存在就毫无意义,甚至这样的权利存在与否都是个问题。
综上所述,儿童权利是儿童凭借特殊的身份而享有的正当自由或者利益,这些正当自由或者利益是由道德以及法律所规约的。法律以及道德在确认儿童享有这些正当的自由或者利益时,明确赋予了父母、教师、一般社会公众以及国家所承担的某种相应义务。
二、儿童权利的教育诉求
教育与儿童权利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人们把教育看作是实现儿童权利的重要方式和途径。现代社会在确认儿童基本权利的基础上继续扩充儿童权利,尤其是在保障儿童消极权利不受妨害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儿童的积极权利——教育、医疗、照顾等福利权利。在儿童权利观念演进过程中,作为一项儿童基本权利的受教育权的确认,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借助于这一权利的保障,儿童在教育中受到知识启蒙和道德教化,理性能力逐渐发展,成长为独立的权利主体,从而能够独立和正当地行使由道德和法律所确认的各项其它权利。当然,教育对于实现儿童各项权利的关键性作用是有条件的,教育必须合乎道德和法律要求地对待置身其中的儿童,儿童权利对于教育提出特别的诉求。
1.儿童对接受义务教育具有正当的要求权
教育之所以为人类所必需,乃是因为一个显见的事实:儿童的身体和智力都处在薄弱阶段,需要教育发展他们的身体、智力和道德能力。人们确信:儿童最终要过成人的生活,接受过教育并且理性成熟之人能够帮助儿童发展理性,以避免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不必要的挫折。人们认为,如果儿童有足够的理性能力的话他一定会认识到一个成熟理性所规划的儿童发展目标必定也是他自己所欲求的目标。因为儿童理性孱弱、缺乏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计划、缺少经验等缘故,也就是说,儿童理性尚处于蒙蔽状态,所以当下状态中的儿童是不能认识这些目标的,而不能认识这个目标并不意味着这个目标就是错误的。成人根据理性所确立的目的,通过规训和强制手段,设立学校教育,规划学校课程,发展儿童理性,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儿童”,帮助儿童“自我实现”。人们确信,儿童一旦达到理智成熟的年龄,便会认同成人对于自己的“塑造”和“规训”。显然,这个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它将很容易导致教育越出“必要的强制”而无限制扩大自己的范围,并最终演变成为教育专制和教育暴力。把教育完全定位在由理性所设定的未来基础之上,而忽视儿童存在的当下性,这极有可能导致儿童消极权利的丧失,儿童的生命、自由和尊严只是在极其有限的意义上才得到承认。这样的观念很容易导致实践中肯定和强调“大我”对于“小我”的专制和残暴,肯定和强调一个外在理性权威对于不成熟理性的支配和统治,肯定和强调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自我实现”而忽视消极意义上的个体权利。
教育被普遍看作为儿童的一种积极权利,旨在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它意味着成人或者国家有义务为儿童提供合乎身体、智力和道德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但这不意味着家长、教师或者国家可以借助于教育强迫灌输一己之意。教育促进儿童身体和精神健康成长的根本性条件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必须建立在对于儿童身心特点以及对于儿童当下生活的真切把握基础之上,它为教育从根本上保障和促进儿童身体、精神成长提供知识基础;二是教育必须基于对儿童权利的认识而形成一种自律品性,承认、尊重并认真对待儿童权利,从根本上保障儿童身心健康成长。这意味着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儿童自主性和自律品性的成长,而不是“越俎代庖”,更不是“拔苗助长”。教育作为儿童身体和精神成长的积极力量,它的作用是“通过儿童”而实现的。教育是儿童的一项积极权利的含义也正在于此。
强迫义务教育的观念自从在19世纪中期兴盛并付诸实践以来,虽然为儿童接受必要的教育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随着人们对于自由和自主意识的逐步增强,很多人怀疑强迫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道德基础是否具有正当性。教育极其容易堕陷为专制的特性使得密尔坚决抵制国家直接“插手”“备办教育”,国家的义务在于监督和强迫家长提供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并进行最基本知识(事实知识和实证科学)的检测和代付困难家庭的学费。即令国家要举办教育,也只能出于示范的考虑并且所创办的学校应当和其它学校处于平等竞争之中。[3]89-111弗里德曼认为公立学校过度发展抑制了教育的多样化,强迫入学体制剥夺了人们选择教育的自由,这些都严重侵蚀到儿童的自由。弗里德曼提出了“教育券”计划,坚决主张抵制国家在教育中的过度作用,还给个人以在教育选择上的充分自由,从而坚决捍卫自由主义。弗里德曼是想根除国家对于个人自由选择教育的干预,“教育券”计划仅仅是“权宜之计”而已。[4]128人当然应当接受教育,国家自然也有义务保障公民接受基本教育的权利。但是,国家如何才能既保障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又能够最小程度地免于对儿童自由的强迫?如何才能够确保受教育权这一积极权利不至于成为对儿童基本自由的压制?这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可惜在现时代,人们却疏于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和辩护。如果我们忽视对义务教育与儿童自由之间关系的考辨,我们如何能够保证不使义务教育堕陷为对儿童自由和权利的僭越和强制呢?
2.儿童权利的实现需要借助于教育的力量
儿童作为权利主体,这不意味着儿童已经现实地具备了正当行使权利的充分能力和力量。儿童理性的孱弱是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它关乎儿童是否能够正当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理性因素不能成为否定儿童享有权利的充分根据,这是儿童权利的特殊性所在。
儿童并不“天生”知道自己应当享有何种权利,儿童的日常生活本身也不足以充分地对儿童进行权利意识、权利观念的启蒙和权利能力的培育,这不仅因为儿童个体的理性能力和生活经验具有局限性,而且因为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实际权利关系只是一个单纯的社会事实,它就是它自身,它并非为着教导儿童正确地行使权利而存在,尽管它并不排斥教育可以利用这一事实对儿童进行权利意识、权利观念的启蒙。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对于儿童当下之生活经验来说乃是一种超越,教育不仅仅基于社会事实,同时也基于特定的价值理想。教育要培养自主和自律的权利主体,就必须融入儿童的生活实践,教导儿童权利知识,启蒙儿童权利观念,发展儿童权利能力。儿童借助于教育的帮助,认识到自身是权利的主体,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权利,并且学会如何正当地行使权利。儿童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进行着权利实践,这是通向理想公民社会的必由之路。教育帮助儿童形成关于权利的正确观念和意识,是帮助儿童实现自身权利的首要步骤。
教育培育儿童成为权利主体,不能止于教导儿童“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知道”如何践履这些权利,否则儿童教育就没有充分展示出它对儿童生活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教育首先要将自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儿童生活实践,它不仅为儿童学习正确的权利知识和观念提供条件,而且为儿童进行权利实践、练习如何正当地行使权利提供“场所”。这样,儿童在教育生活中不仅学习有关权利的知识,而且进行着权利实践,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教育只是“告诉”儿童他们享有哪些权利,“告诉”他们如何正当地行使这些权利,然后让儿童“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实践”。这既错误地理解了教育,也错误地理解了权利。错误地理解教育是因为教育本身就是儿童的一种特殊生活实践,不能够把教育“剥离”出儿童的生活,否则既“切断”了教育的“根基”,又“肢解”了生活本身。错误地理解权利是因为权利本身就是一种外在的实践关系,这种“外在的实践关系”固然可以“知识”的形式存在,但其本质却不在于此,而在于一种实践关系或者说行动关系。这就是说,儿童权利从根本上来说,乃是运作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名称。因此,教育实现儿童的权利首先是在儿童的教育生活实践中指导儿童的权利实践,引导和帮助儿童实现自己的权利。
教育帮助儿童实现权利,还必须保持一种开放性。教育应当把自己理解为儿童的生活实践,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实践。这当然不是说教育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实践与儿童教育之外的生活没有关系。其实,理解儿童教育这样一种生活实践的特殊性必须建立在与一般生活实践(教育之外的生活实践)联系的基础上。一般生活实践乃是教育生活实践的根基,教育生活实践对于一般生活实践具有超越性。因此,教育实现儿童权利首先意味着在教育这一特殊生活实践中的实现,其次还意味着在一般生活实践中实现。这就要求教育必须对儿童日常生活充满关切和询问,必须了解和关心儿童在一般生活中的权利实践问题,必须对于儿童在一般生活中权利实践给予指导和帮助。一种不关注儿童一般生活实践的教育是缺乏生命力的教育,它始终只能躲避在一个“自我确证”的“乌托邦”之中。教育对于儿童一般生活实践的关注,当然不是说教育要把儿童社会生活全部纳入教育“规划”之中,而是说教育必须培养儿童的自主性和自律品性。借助于教育,儿童逐步获得一种理性的力量和行动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确保着儿童在生活中形成和发展正确地理解权利以及正当行使权利的能力。
3.教育实现儿童权利首先必须认真对待儿童的消极权利
儿童权利不仅需要借助于教育的力量得到实现,而且儿童权利本身就对教育力量构成某种限制,它为儿童在教育中的自由行动开辟出一个独特的空间,这个空间对于教育力量而言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如果教育没有特别的道德上更高的理由,侵犯这个空间就是错误的和不正义的。儿童权利观念的历史演变表明,如果受教育权这一积极权利不能够和儿童的其他基本权利取得某种平衡,奢谈对儿童提供一种积极的福利和照顾,是无法实现受教育权所要根本保障的价值的。它所带来的可能危险在于容易使得成人之“善意”成为一种压迫和伤害,而且正是在这个“善意”之下,提供“帮助”的一方觉得委屈、吃力不讨好,受到“帮助”的一方则会感受到一种外力的异化,儿童的主动精神、自律品性失却成长机会。
这意味着,教育实现儿童权利,首先应当基于对儿童消极权利的承认、尊重和认真对待。教育应当承认和尊重儿童作为权利主体,把儿童理解为自由的、有尊严的个体。德沃金强调教育对于人的平等尊重与关怀,从根本上要求把人当作人来看待。教育对待儿童亦复如此。儿童应当受到教育的平等关怀,儿童在教育中应当无条件地被看作是目的性存在,其它价值只有在这个根本性价值的观照之下才能够得到正确认识和充分理解。这意味着教育应当承认儿童是有着人格尊严的人,他们的生命、自由和健康等权利不容教育的侵犯,任何一种教育都必须建立在对于儿童生命、尊严、自由、健康的尊重和保护的前提之下,否则,这种教育就会缺乏正当性依据。承认、尊重和认真对待儿童的消极权利,将会为每个儿童确立自由行动的空间,保障儿童消极意义上的权利免受他人的侵犯。
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儿童的一项积极权利,即便是对于儿童的消极权利,教育也还承担着发展儿童行使权利的能力的义务。儿童权利是教育需要实现的一种教育基本善,也就是说儿童对于教育实现自身权利有着正当的要求权。这就意味着教育实现儿童权利,不仅表现为应当在教育过程和教育方法上承认、尊重和认真对待儿童权利,还表现为应当在教育的目的追求中把实现儿童权利作为基本内容之一。教育目的包含着实现儿童的基本权利,教育内容含括儿童基本权利的教育,教育方法和手段的抉择尊重儿童的基本权利,唯有如此,教育才能在承认、尊重和认真对待儿童权利中实现儿童基本权利,也唯有如此,才能将儿童培养成为具有自主性和自律品性的公民,公民社会才能在一种承认、尊重和认真对待儿童权利的教育中奠定扎实的根基。
收稿日期:2008-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