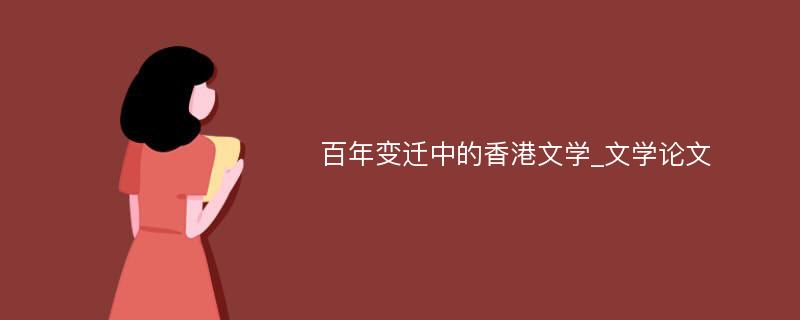
百年变迁中的香港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文学从中国五四新文学对它的孕育催生,到今天展现出绚丽多姿的地域景观,它走过了近百年艰辛曲折的发展道路。回眸这一行程,我们既能看到历史的巨变给香港文学提供的发展契机和活力,又能看到源远流长的中华母体文化在那里打下的深刻烙印,二者的影响渗透,构成了香港文学发展与传承的深层基因。从大的历史分期来讲,香港文学可划作三个发展阶段:本世纪初期至40年代末,香港文学与内地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挥了积极重要的文学阵地作用;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经济的起飞带动了都市文化的发育,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刺激和冲刷,香港文学在艰辛的探索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和确立了自身独特的文学个性;80年代至今,与经济昌盛、思维活跃、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相对应,香港文学稳步发展,形成了多元并存、繁荣向上的总体格局,今日的香港已成为亚洲重要的国际性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一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香港是中国近代史上孕育反封建进步思想的前沿地带。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管理制度,为上下求索的中国的志士仁人打开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思想的门户,像中国近代的革新人物王韬、何启、郑观应等人都与香港及其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辛亥革命时期,香港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和革命活动中心,最初与孙中山一起倡导革命、组织成立兴中会的成员,都是香港的知识分子。创刊于香港的《中国日报》历时11年,是辛亥革命期间持续时间最长的革命宣传阵地,在海内外各阶层中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革命影响。
然而,香港新文学的起步却迟于中国五四新文学革命10年之久。辛亥革命后,大部分革命党人乘势北上,而一批前清遗老避居南下,在香港集结成一个阵容庞大的旧学队伍,基本上左右了香港的文化教育局面。直至30年代,香港学校的国文课仍以“四书”等为教材,禁止白话文,新文艺新思潮被视为异端。香港新文学就在这块中国旧文学的最后盘踞地蓄势待发。
1921年创刊的《双声》,隶属于孙中山倡导的基督教机关报《大光报》,政治上倾向于反封建军阀、拥护国民革命,刊登的文学作品不少是归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但已开始出现放脚式的白话文。由黄天石作总编辑的《小说星期刊》,是1924年出现的一份新旧交替、内容杂陈的刊物,既有国粹派斥骂新文学的文言文,也有革新派放言改革的白话文,并且,此时香港的报纸也纷纷效法内地开辟副刊,发表新文学作品。1927年2月,鲁迅以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身份, 应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赴香港作了两次演讲,以《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为题,旗帜鲜明地抨击了守旧派的国粹论,号召青年们“抛弃老调子”,在无声的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来”,这对正在酝酿和发育中的香港新文学无疑是个很大的鼓舞和推进。1928年8月, 香港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正式创刊,它的出现在当时就引起了关注,据香港元老作家侣伦先生回忆,“它不但纯粹登载新文艺作品,就是杂志本身也表现了香港出版物中前所未有的新风格……当日有人写过一篇推荐这本杂志的文章,称《伴侣》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侣伦《向水屋笔语》)
第一燕的报春,迎来了30年代香港新文学的蓬勃兴起,新文学期刊层出不穷,如《岛上》、《新命》、《晨光》、《春雷》、《红豆》、《激流》、《今日诗歌》等此起彼伏,第一代拓荒者作家如黄天石、谢晨光、张吻冰、侣伦、岑卓云、黄谷柳、张稚庐、龙实秀等,他们以清新的创作和呐喊的激情活跃于香港文坛。这些香港新文学刊物一方面介绍西方的一些文艺新思潮,一方面与内地的新文学运动与创作联系密切,介绍内地文学的创作态势,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内地一些知名作家如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胡也频等人也相继在香港的文学刊物上发表稿件。香港文学在发韧之始,就显示出与内地文学同源共流、携手并进的共鸣形态。质言之,香港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扩展与延伸。
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后期,由于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内地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有两次大的南下过程。两次南下使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获得空前的交流融合,两股力量共同把香港文学推向了这一时期的发展高峰。当时,为数众多的内地作家或借道香港转赴抗日大后方,或驻足香港从事抗日宣传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文化斗争,或定居香港长期从事文艺创作。在数以百计的南来作家中,有一大批著名的作家文人,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夏衍、胡风、徐迟、端木蕻良、许地山、萧红、萧乾、聂绀弩、曹聚仁、叶灵凤、周而复、欧阳予倩、戴望舒等等。他们在香港创办大量的文艺刊物,扶持文学创作,尝试民主教育,使香港的小说、戏剧、电影、美术、诗歌等创作活动空前活跃,声势浩大,也使得这个时期的香港成为当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新的中心和重要的文学阵地,对声援、鼓舞内地的革命战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时期香港文学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内地作家在香港从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上,而且此时香港的本土作家也在深入现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充分反映香港的社会现实、艺术风格日趋成熟的作品,其中侣伦的《穷巷》(又名《都市曲》)、黄谷柳的《虾球传》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个长篇。侣伦曾参加过北伐战争,是香港为数不多的新文学拓荒者之一,也是香港公认的唯一一个矢志不移地在香港文坛上笔耕一生的老作家,诗歌、散文、小说、电影剧本、编辑、出版,直到1988年去世,侣伦与香港文学结伴走过了整整60个春秋。《穷巷》是侣伦的小说代表作,写于1948年,最初在夏衍主编的《华商报》文艺副刊上连载。小说写了抗战胜利后香港的一个穷巷里的故事:一群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穷巷萍水相逢,组成了临时的混合家庭,他们虽然相互同情和扶持,苦苦挣扎着寻觅出路,但最终无法维持生活,希望破灭,被迫离散。《穷巷》以较为园熟的艺术手法,刻画出一批性格鲜明、情感丰富的人物形象,以他们深广的生活背景反映了当时香港社会的渺茫前景和生活酸辛。它和《虾球传》的出现,标志着这个时期香港的文学创作达到了特定的历史高度。
二
50年代以后,香港的社会背景发生了显著变化。战后三、四年间,香港恢复了转口贸易港的地位,50年代末,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额已占了香港出口总值的七成,这意味着此时的香港已向工业化城市转变。及至60年代,香港经济的高速发展,大大促进了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从文学艺术方面看,在比较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影响下,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想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传播,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观念逐渐为市民所接受。从社会阶层结构来看,经济的迅速增长,使香港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华人工业、新兴金融集团的崛起,产生了一个新兴的中产阶层,他们不仅有了丰厚的物质产业基础,同时也逐渐为政府机构、政治范围所接纳;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个庞大的工薪结层、市民结层的形成。现代经济与都市的发育,将此时的香港文学推向了探索工业化都市文学形态的新阶段,并由此形成这个时期现代主义文学和大众通俗小说双峰并峙的全新创作局面。
现代主义文学又称作现代派。现代派文艺思潮源自西方较为发达的国家,包括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几十个文学流派。它的产生有着多层面的现实基础: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给社会带来的深刻危机,有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等非理性哲学思潮的广泛影响,也有文艺创作要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崭新的面目确立文艺的形态与价值的自我追求等。而这诸多现实的条件,在50年代中后期以降的香港,已是不同程度地具备了、出现了。1956年2月创刊的《文艺新潮》, 首先在香港大力倡导现代主义,系统而全面地介绍评析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和作品;改版后的《香港时报》副刊《浅水湾》也在此时广为介绍和倡导现代主义。这两个刊物的主办人马朗和刘以鬯都是三、四十年代在内地就倾向于现代派创作的作家。1958年底,经常在上述两个刊物上发表作品的王无邪、岑昆南等人,发起成立了“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创办《新思潮》、《好望角》杂志,将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文艺运动来推行,由此推出一批深得现代派意旨的新进作家如文楼、李英豪、西西、蔡炎培等。60年代中后期,一群留学欧美的青年作者加入现代主义创作行列,像也斯、戴天、亦舒、叶维廉等人,他们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视野开阔,富有活力,从诗歌、戏剧、小说到评论、翻译,都大大推进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势头。
提及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无法绕过执着追求艺术创新而又成绩卓著的刘以鬯和他的“实验小说”。刘以鬯出生于上海,中学时代就参加了叶紫倡组的“无名文学会”,读高中时经常参加学生罢课、抗日游行等活动。40年代末到香港,几十年来一直在编辑文艺报刊和进行文学创作,现任香港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刘以鬯以他多年的文学积累和创作体验,深感艺术要永葆活力,就必须刻意求新,固守传统方法只会置小说艺术于绝境。他把文学本身看作是一种创造,小说不仅仅是对人生和社会自然的摹写,而且是由小说家所创造的独立的艺术世界,因此“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必须有勇气创造并试验新的技巧和表现方法,以期追上时代,甚至超越时代。”(刘以鬯《酒徒·出版序》)刘以鬯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小说艺术的实验创新,写过一系列成功的实验小说,长篇小说《酒徒》是他的代表作。
《酒徒》最初在一家晚报上连载,出版于1963年,当时即被香港评论界誉为“中国首部意识流长篇小说”。作品写一个有文学抱负有艺术造诣的职业作家,在物欲横流、严肃文艺难以立足的时代,为了生存被迫卖稿为生,写怪异武侠、最后写黄色小说,在肉体与精神的连带危机中陷于嗜酒难拔的绝境。《酒徒》虽然有鲜明的故事情节,但小说却是以刻画主人公的精神存在和精神活动为轴心的,意在将笔触从外在的客观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外界挤压下引发的剧烈的矛盾冲突。目睹现实世界的荒谬,作品的主人公曾抗争过、曾奋起过,然而冷酷的现实一口口吞噬着他心中的亮色,他唯一的解脱就是沉入酒色,让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一同隐去。可悲的是,酒徒是一个受难而孤独的思想者,每每酒醉之时,他似乎更加敏捷清醒,睿智的思想在似真似幻的世界里飞扬驰聘,将他所迷恋的文学与人生的真知灼见一一道出,将一个个时空倒错、瞬息即逝的感官意象捕捉连缀在一起,展示出一个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现实世界……酒徒在迷蒙中追思:“卡夫卡认为人类企图了解上帝的规则是得不到结果的。那么,人是上帝的玩物吗?上帝用希望与野心来玩弄人类?……造物主创造了一个谎言,野心、欲求、希冀、快乐、性欲……皆是制造这个谎言的原料,缺少一样,人就容易获得真正的觉醒。人是不能醒的,因为造物主不允许有这种现象。”《酒徒》以冷峻的笔锋创造了一个绝望的世界,这个纯粹商业性的时代所展示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崩溃,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面临的对抗、分裂及至双重毁灭,在相当的深度上达到了作者所要追求的探求人的“内在真实”的艺术目标。
再看大众通俗小说。这个时期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城市的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在社会心理负担不断加重的情况下,欣赏趣味向消遣娱乐方面倾斜,使得大众通俗小说应运而生。这股流行的大众通俗小说在50年代中期兴起,70年代达到高潮,包括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依达、岑凯伦、亦舒、严沁的爱情小说,倪匡的科幻小说等,都形成了丰饶的作品系列、庞大的读者群。其中,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影响和关注的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又可称为这时期大众通俗小说的一支生力军。
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创始人是梁羽生,大有后来居上势头的是金庸,两位大家共开一代武侠小说的新时代。新派武侠小说总的来讲,是从大处着眼、细处落笔,以宏阔的历史背景作依托,以民族感情、爱国报国为基调,写英雄侠客的行侠仗义、情感纠葛,有较高的文学意境。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虽然早年在岭南大学读的是经济,但他真正的兴趣是文史,诗词功夫颇深。对于武侠小说,他曾明确阐释:武是手段,侠是目的,所谓侠就是正义行为,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因此,他的武侠小说写侠多于写武,侠风义气多于刀光剑影,作品写得有浓厚的历史氛围,加之融清代词人纳兰容若的词风于小说,更显得典雅风流,诗意弥漫。金庸(本名查良镛)则明显接受西方文化观念多一些,他的个人爱好和兴趣也显得较为广泛。他博学多才,既写武侠,又写影剧本,又办报,又写政论(现在又兼社会活动)。他的作品熔中西风格于一炉,既架构雄伟、气魄宏大、贯穿着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的主线,又活泼多变、诡异莫测、大开大阖、灵动流畅。金庸的作品,以武侠为载体,关注现实人生,注重探求人生、人性的哲理与生命的意义,人物的个性形态也显得丰富多彩,多重组合,富有现代审美韵味。故他的15部38册作品风行港澳台、南洋和欧美,海内外许多著名学人包括新儒学大师、文史专家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等,都是金庸小说的读者和收藏者。在金、梁武侠小说的带动下,香港武侠电影获得了新生,进入70年代,李小龙的功夫片脱颖而出,这些由塑造武功绝伦的英雄形象来表现抗污除暴、捍卫民族尊严的功夫片,一扫“东亚病夫”的耻辱,以神勇盖世的硬派魅力挺进欧美市场,在海外掀起香港华语片“中国功夫热”的波澜。
综观这一时期香港文学的发展,无论现代主义文学还是大众通俗小说,都在渐为明晰的现代都市文化背景下,呈现出广为接纳吸收、锐意创新求异的态势。它们适应经济转型期的社会对文学的要求和催动,在继承传统文化内涵、又突出现代精神的探索中,形成了香港文学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自觉的表现形态,在东西方文化日益交流融会的香港,确立了香港文学特有的形象和价值。
三
历史跨入80年代。香港现代经济的综合发展及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赋予了文学走向新的繁荣的物质条件和广阔空间,尤其是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呈现出流派纷呈、蓬勃发展的局面,这无疑给香港文学界以极大的鼓舞和推动,香港文学以更加贴近现实、贴近时代,更加兼容并蓄、自由开放的姿态,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香港文学总的趋向是多元发展,繁荣稳定。构成这一局面的首先表现为创作队伍稳定壮大,作家热情高涨,创作数量丰厚可观,各种流派活跃于文坛。像执着于实验小说探索的刘以鬯、西西、也斯等人,连续有新作问世,有新的探索意向。西西就明确要求自己,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给读者提供一样东西——内容新或技巧新,若两样都没有,就不写了。这一要求很能代表这类作家的共同追求。刘以鬯的《打错了》、《副刊编辑的白日梦》,不仅运用不同的手法和结构凸现理想与现实的对峙、时间与空间错位对人瞬间的意义,而且在《黑色里的白色,白色里的黑色》中,与题旨相呼应,还独创了黑白交错的琴键式排版方式,在视觉的刺激之余赋予作品更大的想象余地和回味空间。西西的长篇新作《飞毡》,写香港的故事却将其寓于童话意象的神奇框架,将欧美及拉美文学的神髓融合于中国语言格调之中。也斯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分校攻读比较文学,获博士学位,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给他不少启迪,他在理论与创作上有多方面的探索,旨在传统与现代、写实与象征之间寻求交汇点。他们的作品不管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给香港文坛带来一股浓厚的先锋意味。大众通俗小说自武侠小说在70年代金庸、梁羽生先后“封刀”以后,言情小说大有唱主角之势,亦舒、岑凯伦、严沁、林燕妮几位“书院女”作家创作势头不减,有的已出版百余部中长篇小说,也出版数量可观的诗集、散文集。八、九十年代又增加了新秀钟晓阳、李碧华等,李碧华的作品主要是电影小说,写故事有更多的文化意蕴;钟晓阳才气逼人,豆蔻年华已涉及诗词、散文等领地,尤其把爱情世界的缠绵故事写得荡气回肠、悲剧气氛甚浓,颇受读者与作家的看重,连续拿了几个大奖。
多元化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前期较为沉寂的社会写实小说出现高涨的趋势。社会写实小说是香港几个主要的小说流派之一,它直接承继五四新文学传统,以反映香港的社会现实生活为主要创作取向,如五、六十年代的舒巷城、夏易、海辛、张君默、三苏,七十年代的陶然、东瑞、白洛等。他们中的多数比较侧重反映香港下层社会的生活,关注社会的各类症结和问题。1982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在香港各阶层引起很大反响,香港的“九七”归属问题牵动着每一个市民的心,也成为作家们捕捉描摹的重要题材。最早在短篇中接触“九七”的是刘以鬯的《一九九七》,写一个小工厂的老板,为了“九七”之前实现举家移民的目标,孤注一掷炒股投机,最后失败,死于车祸。叶娓娜的《长廊》、也斯的《神打》、白洛的《福地》等,也是以刻画不同阶层的“九七”心态为主要内容,表现一些人对祖国的隔膜无知,对香港前途的猜疑恐惧。陶然的中篇《天平》、梁锡华的长篇《头上一片云》,将婚姻爱情与“九七”问题交织起来写。巴桐的《雾》借几个年轻人参与“九七”背景下的地方竞选,表现他们不同的人生信仰和追求。总之,香港文坛上涌现的这股“九七”题材小说,不仅反映了作家们对香港现实问题的热情关注,而且流露出在历史的转折中无论是对炎黄祖国、还是对中华文化根脉的深深认同与沟通渴求,真实地表达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所无法卸掉的那份荷在肩头的职责与义务。
社会写实小说的突破还在于梁凤仪的“财经小说”。梁凤仪曾在香港、英美等地修读文学、哲学、图书馆学及戏剧学,获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八十年代中后期步入文坛,一面经商,一面写财经小说,近期已连续创作出版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二十多部散文集。梁凤仪的财经小说以她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知识积累作基础,写的多是香港上层财经界的生活和斗争,一些大财团、家族及人物的传奇经历,反映的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都市的商界博杀、情场风云及人物起伏不定、生死未卜的命运,充满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气息,又被称作新都市小说。九十年代,她的小说也开始涉及“九七”问题,描写“九七”前夕香港过渡时期的财经风云,其间不乏民族利益的斗争和矛盾,视野更显开阔。由于梁凤仪的小说既反映了香港现代经济生活的复杂、深刻和丰富,又具有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曲折、结局惊奇的特点,故小说寓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于严肃与通俗文学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在文化市场上广为流行。
在繁荣多姿的文学格局中,还要提到的是香港名噪一时的专栏杂文。专栏杂文又称“框框杂文”,三、四十年代被称作“报屁股”,权作陪衬,无足轻重,而七、八十年代以来,它迅速发展壮大,不仅完全摆脱了文学创作的某种尴尬境地,而且一跃成为支撑香港报章业的一个重要支柱。香港著名学者黄维梁十几年前曾这样评介它:“香港的杂文是全港大部分识字居民的精神粮食,是普及文学中读者最多的文体,是香港报业的一大特色,大概也是全世界报业的一大特色。不谈香港文学则已,要谈的话,必须包括香港的杂文。香港杂文数量之多、篇幅之短、内容之百家争鸣,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说独一无二。”(黄维梁《香港文学初探·香港式杂文》)香港杂文的几个特点,让黄维梁都一一圈点。比如说它的多和杂,目前香港约有四、五十家报纸,每家报纸的不同版面都设有四、五十个专栏,每天这类包罗万象的专栏杂文的总字数就不少于100万。这使它如同一面多棱镜, 能够快速直接地反映香港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传递各个领域的知识、信息、舆论、评介,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社会代言人的角色,而受到广大市民阶层的欢迎。尤其那些笔力雄健、文采斐然的关注现实、针砭时弊、揭示生活哲理和人生真谛的文章,更富有杂文特有的审美意义和时代精神。可以说,香港自由不羁的言论空间,庞大的包括作家、编辑、学院教师在内的杂文创作队伍,一个多层面的具有较高阅读欣赏水平的消费群体,共同构成了香港专栏杂文的昌盛局面。并且由此也可以预见,这一兴盛局面还将在相当的时期内持续下去。
另外,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活跃、各类作者协会、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系列由政府机构定期组织的大型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也是这时期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例如文学批评领域,过去相对薄弱和冷清,成果稀少,影响不大。这种状况近一、二十年有了很大改观。文学批评队伍在司马长风(已去世)、刘以鬯、胡菊人等资深人士以外,还涌现出一批成绩卓著的中青年文学批评家,像黄维梁、黄国彬、壁华、梅子、卢玮銮(小思)、梁秉钧(也斯)、梁锡华等。他们有较深厚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修养,对西方各文艺思潮又多有研究,故视野开阔,融会中西,其批评研究显得说理深透、富有个性且从容大度,有鲜明的促进香港文学健康发展的使命意识。尤其是近个时期,在香港文学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成长、在香港就要回归祖国怀抱之际,香港批评界的眼光更多地由局部转向整体,由散点转向历史的反思与审视,对文学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对严肃文艺的境遇和发展前景,给予了集中的探析关注,表现出浓厚的忧患意识与期待之情。在这种清醒务实的批评空气中,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九七”之后的香港文学,在融入祖国文学发展的大格局后,在跨入21世纪的新的历史时期,一定会在新的挑战与机遇中不断探索积累,获得新的突破和跃进。
标签:文学论文; 刘以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香港论文; 艺术论文; 酒徒论文; 散文论文; 作家论文; 侣伦论文; 杂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