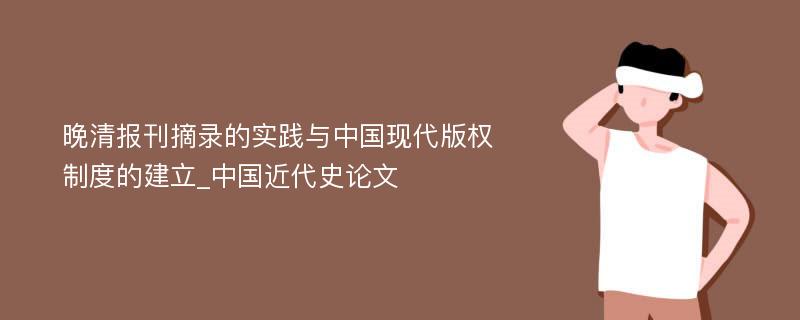
晚清报刊摘录转载的实践与中国现代版权制度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中国论文,报刊论文,版权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11)01-0100-05
中国古代版权观念虽萌发较早,其发展方向却不是近现代的版权制度,概言之,中国古代版权保护多是坊贾或政府发起,他们保护自己的出版权或垄断权,而不是作家著作权。因此,古代版权观念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就是作家著作权保护意识和制度的产生或建立。在中国近现代版权制度建立的过程中,西方版权观念的输入固然起过重要作用,但晚清报刊编辑实践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忽视,晚清报刊编辑们或引入西方版权知识、办报经验,或纠正偏颇、建立行业规则,或申明存案、争取法规保护。本文即以摘录转载的实践为视角来钩沉晚清报刊摘录转载如何被规范化以及在现代版权制度建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
一、摘录转载的普遍实践与盗版泛滥
摘录转载是指从书报上抄录文字和刊登其他报刊上已经发表过的作品。摘录转载中外文报刊上的讯息,不需许可,无需付费,成为晚清报界、尤其是上海报界能够维持发展的优势,“上海报纸,于不受政治暴力之外,尤得一大助力,则取材于本埠外报是也。”较长一段时间里,“华报所得紧要消息,十八九均自外报译录。”“转录外报,既得消息之灵便,又不负法律责任,其为华报之助力者大矣。”[1]263晚清新闻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主要通过摘录转载的方式维持报刊版面的时期,“当咸同之世,……除转录京报,并由中西通儒撰著论说外,余以采录西报为多。”[2]应该说,摘录转载这种办报方式在晚清较早就被引入并规范化,即只要摘录转载时注明来源,资源可共享,算不上盗版侵权,“一经登载,声明由某外报译录,即有错误,本报可不负责任。”[1]2631860年代林乐知主编的《上海新报》,信息转载主要来自《香港近事编录》、《香港新报》、《广州七日报》、《教会新报》等,每则摘录后都附注了来源。在晚清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中,摘录转载应用更加普遍,如《时务报》共出69册,摘录译稿共计1700余篇,50余篇路透电,一般都注明了消息来源,以第57册为例,译摘消息共45则,分别注明来自路透电音及《北中国每日报》等13种报刊。摘录转载注明出处是近代西方新闻思想的体例和办报经验,例如,《万国公报》的摘录转载就一一注明出处,对于不遵守该规则的报馆,1899年9月《万国公报》特刊出《录报须知》,对《华北月报》、《除烟报》转载未注明《万国公报》的全名或出处予以谴责,“此弋名掠美,大乖泰西报例”,并说:
按泰西报馆章程,惟有通行之官文书彼此皆可公用,若遇一家著述或他馆采访事件、翻译新闻,苟欲传抄,必须注明来自某报,否则以窃盗论。[3]
总体看来,摘录转载注明出处在晚清报界普及较早且较规范。但是,仅注明出处并不意味着著作权和出版权得到了保护。自戊戍期间始,辑录报载文字成书销售在出版界蔚然成风,1917年,近代著名报人姚公鹤回忆说:
当戊戍四、五月间,……书贾坊刻,亦间就各报分类摘抄刊售以牟利。盖巨剪之业,在今日用之办报以与名山分席者,而在昔日则名山事业且无过于剪报学问也。[1]266
辑录报刊文字成书(“剪报学问”)比出版书籍(“名山事业”)更易兜售,足见摘录转载报刊文字成书之盛况。下面是上海四马路开明启书店代售翻刻梁启超《新民说》、《宗教学术》、《学源》的广告:
以上三书自壬寅《新民丛报》中选出汇订。按梁任公著作环海知名,壬寅全年报各书坊翻印之本甚夥,价值三四元至五六元不等。本店特为选出三种,取其援古证今,融中达外,于发达思想、增长学识最为纯正,绝无流弊。实粹任公平生学文精萃。……现当各书坊争趁乡闱,本店特别批发从廉以冀开通学界,特此布告。再《并吞中国策》一书亦照此例。[4]
这则广告可以看出当时书局翻刻《新民丛报》销售之盛况。1901年清廷再次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梁启超的论述成为策论范本,时人记载:“梁氏之《新民丛报》,考生奉为密册,务为新语,以动上司。”[5]书局竞相摘录《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的论说作为“课艺”兜售,《新民丛报》:“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6]非虚言。下面是新民译印书局出版的《时务清议报汇编》的广告:
(梁启超)以锐利之笔锋与横绝之眼光,激而为谠言高论,洋洋数千百万言,不特为学堂中暴烈之灵药,即乡试一端亦允承投时之利器,万万不可不备者也。[7]
该广告还说明“广益书局、千顷堂及各大书坊均有代售。”当时,梁启超在上海下属的出版机构有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支店,这些摘录翻刻肯定没有授权且明目张胆。如果说新民译印书局等肆无忌惮地摘录是因为梁启超在日本而鞭长莫及,那么1905年群学会社对《新小说》的摘录汇刻则是光明正大的盗版,颇具代表性。1905年10月25号《时报》刊出“新小说汇编广告”:
横滨之《新小说》久为海内欢迎矣,特其内容每篇不能连贯,阅者憾焉。今觅得原书重加校对,刊为汇编,以便世之嗜阅新小说者。每部四厚册,大洋三元。寄售处,上海各大书坊。
对于这则未署明发行者的广告,广智书局(或新民丛报支店)以新小说社的名义在10月26日《时报》上刊出“横滨新小说特别告白”予以反击,其中说:
昨见《时报》登有《新小说汇编》告白一则,则实非本社所印,且并未发明箱行,所意近假冒,而书中之颠倒错乱非但有误于读者,则与本社声名亦大有妨碍。为此敬告海内外诸君,须知此项《汇编》乃系射利书贾鱼目混珠之伪版,并非本社印行。而本社刻下已将第一年未完之各种小说即行编译完全重行校印,再出汇编,廉价出售,特此声明。
这则特别告白并未能阻止木已成舟的《新小说汇编》,10月28日、11月6、10日,“新小说汇编广告”在《时报》继续刊登了3次,最后一次才附上发行者,原来是“上海棋盘街群学会社”所为。当时《新小说》已由位于棋盘街中市的广智书局印刷发行,①位于四马路的新民丛报支店亦参与营销,群学会社与它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而《时报》是梁启超主持创办的,此期间每月还在接受来自康梁保皇会的财力支持。②《时报》负责人狄葆贤与梁启超关系之“铁”为梁启超所承认,③而且负责《新小说》推销的新民丛报支店与时报馆是在一起的。④今天看来,时报馆把群学会社的“新小说汇编广告”连续在《时报》上刊登属于“大水冲了龙王庙”,应不是报馆见利忘义的结果。当发现盗版后,广智书局等也只能刊登广告指责其盗版的质量不好而已,如此说明摘报成书早已司空见惯,所以时报馆刊登这种挖自家墙脚儿的广告也不会觉得有伤和气。1906年10月新世界小说社推出《短篇小说丛刻》也是采摘他报小说成书,并堂而皇之地说是因为“散见各报,检阅不便,且恐久而散失,有负作者苦心,爰广为搜罗,都为一集。”[8]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种摘录汇集,鉴于《短篇小说丛刻》初集“出版不数月而销售殆尽,将次再版。”新世界小说社于1907年“爰赶将二三编付印。”[9]辑录报载小说出版竟成出版商盈利之终南捷径。
小说转载在晚清是普遍的现象,据研究者不完全统计,《广益丛报》转载《时报》的小说有《马贼》、《中间人》、《张天师》、《歇洛克来华第一案》、《三五少年》、《某学生与某教员》、《美少年》、《某县令》,转载《申报》的小说有《铁血姊妹》、《火刀先生传》,转载《神州日报》上的有《魑魅镜》、《支那之新鬼剧》、《世界龙王大会议》和《学生……妻》等,此外还转载了《新民丛报》、《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时报》等报刊上的小说。[10]如此看来,《广益丛报》是名副其实的小说转载“专业户”。可见摘录转载在晚清在新闻出版界普及的同时,也导致频仍的公开盗版活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传统版权观念主要是保护出版者的权利而排除对作家著作权的维护。例如,1887年味闲主人将刊登在《点石斋画报》上王韬的小说《淞隐漫录》汇集为《后聊斋志异图说初集》兜售,王韬在《申报》上刊登告白予以谴责,(《申报》,1887年8月23日)味闲主人在王韬刊发谴责广告后也在《申报》上刊登广告:“是书确系尊著,今特不惜工本重为摩印,本拟预先陈明,只缘向未识荆,不敢造次。因思文章为天下之公器,而大著尤天下所钦佩。”[11]“文章为天下之公器”的藉口反映了出版商对作家著作权的漠视。
二、“不许摘录转载”观念和法规的形成
摘录转载给中国近代版权观念带来了新的课题,其对近代版权最大的挑战是晚清一大批作家(如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的著述基本都是先刊登在报刊上,尔后结集出版。
面对摘录转载带来的利益损害,晚清报馆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属被动应对,即加快单行本的出版速度。对于可以结集出版的作品,报馆利用原有的铅字模具在连载逋结之后尽快推出单行本,这既可获得更多的利润,也可让摘录盗版者顾及不上。二是对特定文字主动申明或存案保护版权。就笔者目力所及,最早对报刊连载文字申明“不许翻刻”的是《中外日报》,1898年8月17日《时务日报》改《中外日报》后,汪康年禀请南洋大臣通饬“各报馆不准仿中外日报馆格式以获专利,”中外日报馆以后译印各书籍“通饬禁止翻刻”(《中外日报》,1898年8月10日)1899年,中外日报馆连载笔记小说《续庄谐选录》就在版心中声明“翻刻必究”。(《中外日报》,1899年4月4日)这种方式一直被中外日报馆坚持,1904年11月《中外日报》连载《七日奇缘》,特别说明:“中外日报馆附送,翻刻必究。”(《中外日报》,1904年11月18日)1906年2月至4月连载《海卫包探案》,特申明不得转载:
兹由本馆延请通人译的《海卫包探案》数种,均已脱稿,于即日起按日排入报中,决不间断以供阅者玩索,每种印毕后仍由本馆改印单行本出售,藉告各书肆勿得翻印,以致究诘。[12]
1907年2月17日中外日报馆“特别告白”云:“本馆译登各小说远近各书肆不得私行翻印,并不得剿袭原稿、改换面目,印售渔利,致有碍本报版权。合先布告,免有后言。”随后,《中外日报》连载的《母猫访道》(2月16日至2月23日)、《瓶里小鬼》(2月24日至3月7日)、《打皮球》(3月8日至3月14日)等都在报缝中声明“不得翻印”。1902年《新小说征文启》标志着近代稿酬制度的初步建立,小说在晚清开始普遍支付稿酬,中外日报馆的版权申明包括不许摘录和不许转载,保护的是出版者和作者的利益,属于现代版权制度的范畴。
1906年至1907年是晚清报刊申明“不许转载”频繁的两年,是晚清报刊摘录转载版权保护初步确立和行业趋于规范化的关键年份。例如,1906年11月1日创刊的《月月小说》第1期“申明版权”:
本社所登各小说,均得有著者版权。他日印刷告全后,其版权均归上海棋盘街乐群书局所有,他人不得翻刻。特此先为预告。
类似这样的版权广告见于第1、2、5、9、12、14、21号,至第9号《月月小说》改由群学社发行,该“申明版权”亦改为归群学社所有,(《月月小说》1908年第10期)可见《月月小说》的出版发行人版权意识之强烈。1907年4月《小说林》第3期“特别告白”:
本社所有小说,无论长篇短著,皆购有版权,早经存案,不许翻印转载。乃有□□报馆将本社所出《小说林月报》第二期《地方自治》短篇改名《二十文》,更换排登。近又见□□报馆将第一期《暖香楼传奇》直钞登载,于本社版权大有妨碍,除由本社派人直接交涉外,如有不顾体面再行转载者,定行送官照章罚办,毋得自取其辱。特此广告。[13]
这则特别广告与群学会社大张旗鼓地推出《新小说汇编》的时间相距不到2年,《小说林》通过存案和曝光的方式的禁止摘录转载,说明小说林社已经充分认识到未经授权摘录转载与盗版无异。在商业市场中,“好点子”的出现会很快就会流行起来。1907年6月14日时报馆也刊发“本馆特别告白”:“本报所登小说无论悬赏自编、短篇长幅,均有版权,不许转载,特此广告。”1907年11月创刊的《竞立社小说报》第1期封底“翻印必究”。可见,到1907年止,对报载特定内容的“不许转载”的观念要求已经开始在出版界普及。1908年3月颁行的《大清报律》第38条:“凡论说、纪事,确系该报创有者,得注明不许转登字样,他报即不得互相钞袭。”第39条:“凡报上附刊之作,他日足以成书者,得享有版权之保护。”[14]在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颁布之前,报载的部分内容是全国性法律规定最早享受版权保护的文字,这既是西方版权观念引入的体现,也是晚清报界编辑出版实践中探索、维权努力的结果。翻阅1911年以后的文艺期刊,几乎找不到没有在封页上附上“不许转载”字样的,说明擅自从他人刊物上摘录转载等同侵犯版权的观念成为常识,“不许转载”、“禁止选录”遂成为现代版权声明和保护的重要内容和方式。
总上所见,摘录转载的引入与普遍应用是晚清中文报刊发展的有力保证,报刊摘录转载促进了晚清书刊编辑出版的繁荣,在实践中,出版人及作家很快发现摘录转载报刊文字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对报载特定内容的版权保护意识和要求渐长,于是“不许转载”的要求和申明开始流行并成为行业规则,随即获得法律保护,可见,晚清报刊摘录转载的实践促进了报刊文字版权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为中国现代报刊文字版权保护行规法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总之,晚清报刊摘录转载的普及和规范化是我们认识中国现代版权意识和制度产生和建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收稿日期:2010-10-20
注释:
①《新小说》1905年2月迁至上海由广智书局发行。
②至1907年底,《时报》已累计花费保皇会10余万元。(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2页。)
③狄葆贤是梁启超故交中除谭嗣同、吴铁樵之外,“最有切密之关系”者。(《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40141号)
④1904年6月12日《时报》创刊时报馆设在“福州路巡捕房对面的广智书局楼上。”(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17页)1907年5月8日凌晨6点,时报馆发生火灾,新民丛报支店也同时被灾。新民丛报支店的广告落款地址也是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对面。(见《新民丛报》第22号所刊上海本报支店广告)
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梁启超论文; 月月小说论文; 申报论文; 新民丛报论文; 万国公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