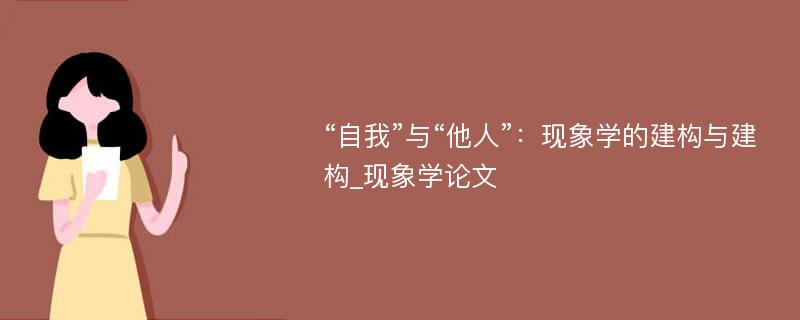
“自我”与“他人”:现象学我本学的建构与解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我本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文章讨论了胡塞尔在我本学基础上建构他人的尝试,并考察了海德格尔和萨特对此建构所进行的解构,认为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在自我与他人问题上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而萨特对自我的解构既无助于解决他人给出的难题,而且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关键词〕 我本学 自我他我 触类感通
一、问题的提法
任何一种先验唯心主义哲学都得面临“他人”的问题,现象学也不例外。
现象学还原通过将整个世界及所有别的客观性的日常设定置于括弧中而披露出一“自我本具的领域”(the sphere of ownness), 此领域不援引任何不属于我的经验,因而是完全“非他的”第一人称的领域,那么,“他人”或“他我”(alter-ego)如何在此我本的领域中给出?如何从“第一人称”在现象学意义上合法地给出“第三人称”?
这里有两点应加以说明。其一,在日常经验层次上,他人存在、自我存在、世界存在都是无可置疑的,现象学从未否认这些健全的常识观,他人的问题只是在先验的反省的层次上才有意义,而且也只在这个层次上才能被提出来。[1]
其二,在先验的层次上,他人的给出与物的给出是根本不同的。物的给出总有其视域,直接呈现于意识的只是物的一个侧面,物的其余侧面则附呈于意识之中。比如,我见到一棵树,依现象学的识见,我真正看到的只是树的一面, 其余的侧面是作为视域而被附呈(appresented),但是通过我身体的运动,原来附呈的侧面即转化成原初的直呈了(presented)。他人无疑最初也是以其身体出现于我的知觉中, 他的身体总可以明证地直呈于我,而其内心生活则是附呈的,然而这与物的附呈不同,我永远无法将此附呈转化成原初的直呈,但这不是对唯我论的支持,而恰恰是他人之为他人的标志。如若他人的内心生活完全能在我原初的体验中的明证地给出,则他人就不成为他人而成了我的自我的一部分了,我与他的区别即不存在了,这才是真正的唯我论。
因此,他人的给出是如此之特殊:一方面,他必须在我的先验自我内得到构成;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被构成为与我有别的“他”或“他我”。
毫无疑问,他人最初是以其身呈现于我眼前的,这个身(Body)决非一般的物(body),它也必须在我身基础上加以领会,我本学的他人建构遂从我身的现象学描述开始。
二、从“自我”到“他人”:胡塞尔我本学的建构
在自我本具的领域,我的机体是唯一能够被原初地构成为机体的身体(Leib),“身之为身原本即是充满心之身”[2], 是我的心灵生活与我介入事象世界的行为之间的中介。 现象学之身乃意志之身( the Body for the will),是“意志的器官”,是“自由运动”(而非“物理物的机械运动”)的场所,我心与我身的这种内在关联是原初地呈现于我的体验之中的。
胡塞尔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呈现皆有其类型化的背景,知觉世界实际上亦是类型化了的世界(typified world)。还是以树为例,我们见到任何一棵树,都在意识中将其“归类”了(此并非主动归类):它是一棵松树,于是它作为松树所具有特性皆作为视域而呈现于意识之中了。“每一日常经验都牵涉到从一原初设置了对象意义到新情形的类化转移(analogizing transfer)。”[3] 每一新对象皆被预期地(此亦并非主动预期)领悟为拥有该类对象相似的意义。
因此,当他人以其身体直呈于我面前时,因其身体与我身体的“相似关联”,遂产生了“类化领悟”,此乃是一种“同化统觉”,而决不是出自类推的推论,“统觉不是推论,不是思维行为”,它是原初的设置,是当下的“触类感通”(Empathy)。 “我实际所见的并不是一个符号,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类似物,不是任何该词自然意义上的描述,相反,它即是某个他人。”[5]
当他人进入我的知觉领域之际,一个与我相似的身体即“结成一对”,我“这里”的躯体与他“那里”的躯体因举止相似而产生“结对联想”。首先是对他人行为的理解,他人的一举一动皆被统摄为其身体的动作,其给出的方式恰如我之统辖自己身体动作相似,他人首先即是在这一“和谐的行为”中给出的,一旦这一“和谐”出现反常,比如我发现他的某个动作呈现机械性,结对联想的“连贯证实”即被打断,它原来不是一个他,而是一“伪身体”,一机器人……结对联想的第二个层次即他人心灵的感通,他人的苦与乐从我相似的环境中得到理解,我能够在我对自己生活方式的经验熟悉性基础上联想地理解之。
因此,“结对”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意义转移”的过程:他人的身体与他所统辖的自我在统一的超越经验方式下给了出来。触类感通的本质特点即是原初身心统一体的当下给出,正因有此触类感通,我们才能看到他人会心的一笑,而不是看见他脸上的皱纹与肌肉的位移,我们才能听到他的肺腑之言,而不是纯粹声波振动的音响。
“触类”即是触身体之类(Bodily type), 此身乃他人之身(Body/Leib)而非一般的物身(body/korper),“感通”即是感精神之通(Spiritualtype),我遂依自己的习惯的行为与动机, 依自己的人格来理解他人的行为、动机与人格,“他人”遂在此触类感通中向我“突然敞开”了,我遂置身于他人主体的位置中,领悟其动机,参与其生活情景,“我不仅与其思想、感情、行为‘同情’,而且我也必在其中追随他,他的动机成为我的准动机……我共享了他的诱惑,我共参与了他的谬误……”[6]他人遂成了“我本己的变换”。
只有在他人主体性给出后,客观性的给出才有可能。由于拥有“一中心这里”的我的“零身”(zero Body)可以自由地变换自己的位置,从而把任何一个“那里”转变成一个“这里”,因此借身体的触类感通,我就会当下领悟到如果我站在另一他我的位置,我也会与他看到同样的东西,我的整个自然与他人的自然是同一个自然。
毫无疑问,自然中有多少个人类个体,就有多少个主观世界,也就有多少个相关的真理,“与个体相关联的经验事物的相对性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同样,由触类感通所完成的交互主体性的客观性也是无可争议的。每一个单子,每一个单子共同体均有其自己的“文化世界”,但藉文化上的触类感通即将自身投射进异在文化共同体之中,一个人类共同拥有的世界即被构成了,每一个具体的周遭世界只不过是此共同世界的不同呈现而已。事实上,“只能存在一个单子共同体,即所有共存的单子共同体。因此,也只能有一个客观世界,一个客观时间,一个客观空间,一个客观自然”。[7]
三、自我即他人:出自Dasein生存机制的审视
胡塞尔我本学的他人建构有两个特色,一是我本学的特色,即从先验自我内给出他人自我的存在;二是他人自我的给出是附呈的,它永远无法转化成我的原初的体验。对于前者,海德格尔给出了生存论上的重新审视;对于后者,萨特则将其引申至极端而得出一始料不及的结论。
先说海德格尔。
从此在的存在于世中的生存机制来审视他人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胡塞尔的发问方式是“无根的”,因为,无论是自我还是他人皆不是最原初的现象,“无世界的单纯主体并不首先‘存在’,也从不曾给定。同样,无他人的绝缘的自我归根到底也并不首先存在”[8]。 而他人也并不是首先作为“飘飘荡荡的主体”现成摆在其他物体之侧。
自我与他人的给出必然给予真正现象学的阐明,而生存论是唯一妥当的阐明方式。因为,人的实体不是作为灵肉综合的精神而存在,而是作为“生存”而存在,“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寻视、他所烦忙的东西,在日常条件下,我们是藉我们的寻视活动以及我们所烦忙的物事来领会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实存的……”[9], 而且也正是在此在“沉迷”于它的世界之际,在寻视与烦忙之际,他人也随同烦忙活动中供使用的用具“共同相遇”了。例如我们在外面沿着走的这块地显然为属于某人某人的,由他来正常地保持着;这本在用着的书是在……买来的,是由……赠送的,诸如此类。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了,“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即使他人实际上并不是现成摆在那里,共在也在生存论上规定着此在,“此在之独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他人只能在一种共在中而且只能为一种共在而不在。独在是共在的一种残缺的样式,独在的可能性就是共在的证明”。[10]“对他人的存在”乃是一种独立的“不可还原的”存在关联。因而根本不存在一个胡塞尔意义上的“自我本具领域”,而他人也根本不是在知觉的认知活动中给出的。
甚至当胡塞尔突出地把自己说成“这儿的我”之际,这个指明地点的人称规定也必须从此在的生存论上的空间性来领会。这个“中心的这儿”并不是指我这里的一个突出之点,而是要从上手世界的“那儿”来加以领会的“在之中”,而此在作为烦忙就滞留于“那儿”。
至于胡塞尔所讲的触类感通,海德格尔也有自己的说法:“并不是‘触类感通’才组建起共在,倒是‘触类感通’要以共在为基础才可能,并且‘触类感通’之所以避免不开,其原因就在于占统治地位的乃是共在的诸残缺样式。”[11]自我与他人并不是有待于触类感通去达成共在,相反,恰恰是共在使触类感通成为可能。
以我本学的立场描述他人来照面的情况,这“岂不也是从把‘我’高标特立加以绝缘的作法出发,所以才不得不寻找从这个绝缘的主体过渡到他人的道路吗?”实际上,“他人并不等于说在我之外的其余的全体余数,而这个我则是从这全部余数中兀然特立的;他人倒是我们本身多半与之无别,我们也在其中的那些人”。[12]
四、“看”:从“他人”到“自我”
萨特则沿另一条路子来拒斥胡塞尔的我本学。在他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并不彻底,因为先验自我实际上仍带有笛卡尔实体自我的色彩,故必须被悬搁起来。胡塞尔将自我与我思置于同一层次上是完全错误的,进行反省的我是不能够统一的,被反省的我也不是反省行为中的内在所予,而只是作为反省的对象(the “me”)被给予,因而它不能作为还原的主体极。它不具游离意识的地位,不具任何现象学的合法性。
真正的先验意识领域只是一无人称(impersonal)领域,我只是显现于具体人的层次上,“自我既不是形式地亦不是内容地存在于意识之中的:它是外在的,在世界之中的”。[13]
先验自我也不是意识统一的必然要求,意识靠自身的意向性就可超越自身,它通过“逃离”自身而统一自身。况且,意识的绵延、意识的时间性、综合性这些意识统一的特征,胡塞尔早在1905年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中就讲过,而那时他并未拆诸先验自我。至于意识的个体性,它也显然来自意识自身的性质,意识象斯宾诺莎的实体一样只能自己限制自己,总之“现象学的意识概念使自我统一化与个体化功能完全成为无用的”。[14]不但无用,而且还是个障碍,因为它会牺牲意识的“非实体性的绝对性”,“先验自我是意识的死亡”。[15]
“我本学”的摈弃是先验领域的一次“解放”与“净化”,意识因而成为绝对透明的虚无化本身,成了一种无人称的自发活动,从而显示出一种空前的创造性,而且这也是对唯我论“唯一可能的反驳”。在萨特看来,胡塞尔的第五沉思并未真正解决唯我论问题,“只要我仍保留在意识的结构中,它就总使意识与他我一起和所有别的实存相对立成为能可能”。[16]唯我论是先验自我的我本学的必然归宿。而如果我成为一个超越物,它不是绝对的,它没有创造宇宙,它必须像别的超越物一被悬搁,这样,“唯我论从我不再拥有优越性的地位那一刻起就成为不可能的了”。[17]
既然自我不具任何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那么它又是如何给出的呢?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给出了独出心裁的答案:“我看见自己是因为有人看见我。”[18]于是,胡塞尔的问题完全被倒置了:不是先验自我如何给出另一个自我(他人),而是他人如何给出我的自我,“别人的问题远非从我思出发提出的,而是相反,正是别人的存在使我思成为可能”。[19]
设想我出于嫉妒、好奇心、怪癖而把耳朵贴在门上,通过锁孔里偷窥,我完全自失于偷窥活动之中,突然我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有人在看我!”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说我在我的存在中突然被触及了。”“我一下意识到我”,我因羞耻而脸红了,“羞耻是对自我的羞耻,它承认我就是别人注意和判断着的那个对象”。[20]在他人的目光下,原本“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的流动化、虚无化的自为突然被凝固成“是其所是,不是其所是”的自在了,我成了一个偷窥者,就象墨水瓶是墨水瓶一样。
在体验到我的存在的同时,我也直接地体验着他人不可理解的主体性,“通过注视,就具体地体验到他人是自由和有意识的主体”[21]。因为正是对一个自由而言并通过一个自由,而且只对这个自由而言并通过这个自由,我的诸种可能才能被“限制”、被“固定”,我不会对墨水瓶感到羞耻,也不会对小猫感到羞耻,“我对我自身的脱离和他人的自由的涌现是一回事”。[22]“他人对我表现为一个具体的自明的在场,我完全不能从我之中抽出他,而他则既不能被怀疑,也不能成为一种现象学还原或任何别的‘悬搁’的对象。”
于是情形只能是这样,或者被他人看、被他人“占有”,任凭他人的“目光”对我赤裸裸的身体“进行加工”,或者,“我以我的注视反过来凝视我的他人”,“把我的主体性建立在别人的主体性崩溃之上”。主体间的相互的看是不可能的:“一个注视不能自己注视:我刚一注视一个注视,它就消失了,我只不过看见了眼睛。在这个时刻他人变成了我所占有的并且承认了我的自由存在。”[23]二者之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在没有矛盾的情况下被抓住,二者之中任何一方都在另一方之中并且“致对方于死地”,“冲突是为他存在的原始意义”。就这样,萨特把他在集中营禁闭室里的感觉投射进整个的主体间的交往之中了。
五、对解构的解构
胡塞尔我本学的建构,在后现代主义解构内在性、解构私人性的潮流冲击下,已少有人去问津了,我本学之不成立似已成为准哲学常识了。实际上海德格尔将自我解构为存在于世中的此在的烦忙与烦神,萨特将自我归结为他人的目光,皆可被视为这一潮流的一部分。
确实,共享的语言,共享的生活方式,共享的交流模式,生存中的参与式的相互牵涉,这些前反省的层次的无可置疑的存在足以从根本上动摇我本学扎根的地基。先验自我所一向自以为本己的东西,难道实际上不全是些他人的东西、历史的东西、传统的东西、人人共享的东西吗?在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谁还坚持我本学的立场不放,如果不被视为缺乏现代哲学的教养,也会被讥为抱残守旧了。但是在对胡塞尔我本学的命运作判定之前,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有待于澄清。首先我们应明了胡塞尔我本学构成并不是时间意义上的,而是现象学意义构成这个意义上的。匿名的文化、匿名的传统、匿名的语言在时间上的在先性是一不争的事实,未反省层次对反省层次的时间上的在先性亦是一不争的事实,对此胡塞尔是有清醒认识的,生活世界的概念是胡塞尔首先提出来的,“即便是最直接的知觉的东西都是公共化了的(commun-alized)。”[24]交互主体性在前反省层次上就存在了。就个体成长而言,婴儿在母胎中的生活即是互体的生活了;就人类文明的成长史而言,我们皆处在一“历史的视域”中,在其中任何事物都是历史的,“我们人类的存在是无数传统中展开的”。[25]作为“历史共同体”、“语言共同体”的生活世界在个人生活中是先予的,“在这一共同体中,每个人都能够谈论作为客观存在的他的文明的周遭世界中的事情。每一事物都有其名称,或者最宽泛意义上是可命名即可用语言表达的,客观世界从起始就是对所有人的世界……其客观存在是以理解为有共同语言的人为前提的……人之为人,同胞,世界--我们总在谈论并能谈论的世界--与语言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的”[26]。但是,传统、语言、文化毕竟不是堆在自我面前的一堆杂乱的物事,更不是有待于我们用“吸取”或“剔除”的眼光去打量的现成品,它恰恰是通过每一个自我的构成而呈现出来的,自我既不是传统理性狡计的牺牲品,传统也不是自我随心所欲的加工物。这里有一种真正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自我是在传统即在前自我层次上进行构成的,甚至应该说传统、“历史的视域”,已规定了自我构成的范围、能力与方式。而另一方面,前自我的层次恰恰是在自我构成层次上才呈现出来,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恰恰是以其构成的自我为呈现的先决条件,过时的传统之所以过时也是相对自我而言的。不妨这样说,传统与自我是在互为根基的相互构成中呈现出来的,无传统的自我是空洞的,无自我的传统是死寂的。
达成此识见后,我们再回头审查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哲学分争问题。有趣的是,争论双方都认为对方的观点只是自己观点的“一个特例”,胡塞尔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赠书的花边上写道:“海德格尔对所有存在者和普遍者、对总体的区域世界的构成的现象学阐释腰斩成人类学的了,整个问题的框架是改换,自我对应于此在等等,因此一切都变得在深层上模糊了,而且在哲学上也失去了价值……”[27]在他看来,海德格尔抛弃我本学的立场实际上就把现象学推回到了人类学、世俗主体性的层次上了,此在是一世俗的主体性,是“素朴的”、“无根的”。而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批评也建立在类似理由上,“有什么东西比我们的给定性更毋庸置疑呢?这种给定性不是指示我们:为了源始地把这个我清理出来,就得撇开一切其它也‘给定的东西’不论--不仅要撇开存在者状态上的‘世界’,而且要撇开其他‘诸我’的存在”,然而,在人们说我就是这个存在者,而偏偏它不是这个存在者的时候它说得最响”。[28]换言之,我本学的立场看起来是“明白无误的”,但在实际上都是“素朴的”、“无根的”,自我的“形式给定性”会使现象学分析“落入陷井”。
实际上双方的指责都是建立在对对方误释的基础上的。我本学的先验自我并不是一素朴的给定性,并不是对当下现实自我的一种简单的肯定,通过现象学还原,这一切素朴设定的东西都被搁置于括弧之中了。先验自我也不是绝缘的孤立的无世界的主体,它是“irreal”,它的本真结构即是意向性,即是对世界、对传统的开放性,它必展现于世界中。同样,Dasein也并不是人类学的、世俗性的主体性,它无疑是于世之中的存在,然而这“于”(in)并非是空间现成物事的摆放,而是“ex-ist”,是有所烦忙和烦神的筹划。 我认为现象学还原在海德格尔那里才得到了真正生存论上的阐明:畏在此在中公开出向最本己的能在的存在……畏如此把此在个别化并开展出来成为solusipse 〔唯我〕……畏将此在从其消散于‘世界’的沉沦中抽回来了……”[29]在出于烦的“畏”的“良知呼唤”中,此在的本真的于世之中的存在的生存结构敞开了,而在此呼向本己的“良知呼唤”中,呼唤者与被召唤者原本即是此在自身。呼唤者对应于进行悬搁的先验自我,沉沦于世的被召唤者对应于经验自我,这不是很清楚了吗?[30]
两人的关系可以这样来表述:在胡塞尔那里,只有通过现象学悬搁达到一本真自我,才能由此自我出发重构整个文化与传统的真实意义;在海德格尔那里,只有先将被胡塞尔悬搁掉的世俗的东西的真正结构搞清楚,才能达到本真自我的体认。胡塞尔的我本学的建构与海德格尔对我本学的解构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互诠的。
至于萨特的“目光现象学”,表面看来它是对胡塞尔我本学的一次彻底反动,但在实质上却把胡塞尔的观点发展到极端的一个结果。因为在胡塞尔那里,他人的自我呈现是以身体为中介的,其精神生活是“附呈的”而永远不能成为我的“原初的在场”,不然,他人即不成其为他人了,这种“原初的不在场”并不是有空间性限制的物的不在场,因为对于后者,不在场的东西通过我的身体运动可转化为在场者。萨特将此不在场理论引申到极端:“主体-他人完全不能被认识,甚至不能被认为是主体-他人。”[31]
在胡塞尔那里,尽管他人自我的主体性不能成为我的原初的体验,但藉先验自我的触类感通,我会当下领悟到他人的主体性对他人是原初在场的。而在萨特这里,因我本学的立场已被抛弃,自我在意识中不占任何地位,结果导致了一个他本人没有意识到的悖论:没有我的主体性在场的体验,如何能给出他人的主体性的体验呢?为什么我不在墨水瓶面前、不在小猫面前感到羞耻,而偏偏在他人面前感到羞耻呢?难道这不是出于自我变了样的触类感通吗?用“他本学”来取代“我本学”不仅无助于解决我本学的难题,反而带来了新的更大的难题,这是萨特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顺便提一下,萨特对目光的现象学描述是他在《存在与虚无》中至为精彩的手笔,但却不是象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他本人的“独家发明”,实际上,早在1920年,胡塞尔就在手稿中留下了类似的字样:“当事人知道自己被一旁观者称赞或谴责,就象他通常在类似情形下称赞或谴责他人一样,他用他人的目光来评价他自己。”[32]
在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对胡塞尔我本学建构作盖棺论定尚不是时候。不过不管其成败与否,至少有两点使它在当代哲学中功不可没:一是,先验层次上的我本学建构克服了传统先验哲学避而不谈“他人”问题的偏面性,并进而为当代哲学开出了交互主体性之维。我本学的建构实际上即是对主体间交往的先验条件的探究,是对理性交信共同体的可能性的探究,这就直接预示了哈贝马斯、阿佩尔的哲学发展方向。二是,我本学身体之维的朗现是胡塞尔对先验哲学的又一大贡献。身心分离是传统二元论、甚至也是传统唯物论与唯心论肇始的根源,无身的“颈上取向”是传统先验哲学的一大特色。胡塞尔独出心裁地拈出一非心非物、亦心亦物的“身体”(Body)来作为解决他人难题的中介,被先验哲学一直忽视的身体自此以后冠冕堂皇地登上了哲学的殿堂。海德格尔于世之中的存在,乃是此身存在于此世,萨特的对“我”进行“加工”的他人的目光亦是通过我身来进行的,甚至那些维特根斯坦式的新行为主义者们,在将“内在性”、“私人性”解构为了可观察的外部动作时,也是指身体的动作,至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其胡塞尔的背景更是不言自明了。
本文1995年9月29日收到。
"Ego"and "Alter Ego":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of Phenomenological Egology
Chen Lisheng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usserl's efforts
onconstruction of alter ego on the basis of egology, andexamines Heidegger and Satre's deconstruction of Husserl'segology.The author holds that Husserl and Heidegger were notcontradictory but rather complementary, whereas
Satre'sdeconstruction of ego did not 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created by alter ego but only brought about a new dilemma.
注释:
[1][4][6] Husserl,Cartesian Meditations, D.Cairns trans.The Hague,1977,P.83,P.124,P.140.
[2][ 3] [ 5] Husserl ,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SecondBood,Rojcewicz & Schuwer trans.Dordecht,1989,P.252,P.111, P.287.
[7][9][10][11][28][2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3、148、154、146、142~142、227~228页。
[8]Heidegger , The Basic Problem of Phenomenology .Hofstadtertrans.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1988,P.159.
[12][13][14][15][16] Sartre,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go.Williams trans.1957.P.31,P.40,P.40,P93,P.104.
[17][18][19][20][21][22][23][31]萨特:《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45、316、346、358、364、 359、491、386页。
[24][25][26] Husserl,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D·Carr trans.Evanston,1970,P.163,P.354,P.359.
[ 27]
引自 AnalectaHusserliana. Volume ΧΧⅦ,Tymieniecka edited.1989,PP .643-644.
[30]萨特对此有旁观者的清醒认识:真正的现象学还原不是“知识的操作”,不是一种“智性的方法”,“它是加于我们身上而又不可逃避的畏(anxiety):它既是先验起源的纯粹事件, 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可能事件。”Sartre.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go .P.103.
[32]引自Apriori And World.Mckenna,edited,The Hague, 1981,P.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