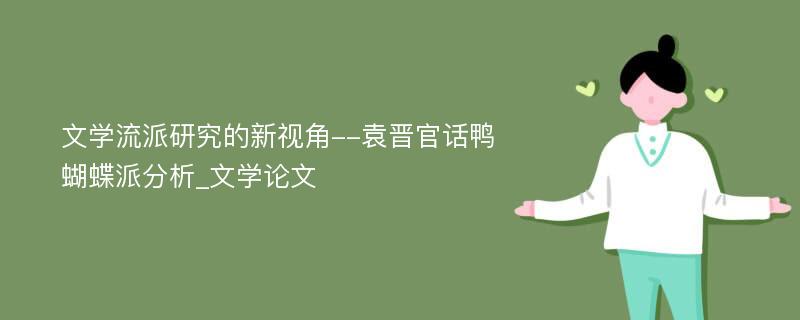
文学流派研究的新视角——袁进《鸳鸯蝴蝶派》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鸳鸯蝴蝶派论文,流派论文,新视角论文,文学论文,袁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现代文学体系的深入探讨和“重写文学史”的呼唤,出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样一个崭新的文学史概念,它打破了传统的近代、现代、当代三段式文学分期模式,从而带动了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的更新。风行近半个世纪的鸳鸯蝴蝶派,理应归属这一文学史范畴。它作为滥觞于晚清,繁盛于民初,衰落于战后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其文艺主张,团体活动及创作演变,都是一个复杂的文艺现象。以往的文学史著述,大都忽略了曾一度独霸文坛而独具代表性的鸳鸯蝴蝶派的应有地位;即使偶有提及,也多是作为“文学研究会”斗争的对立面和新文学的逆流来批判的。袁进先生的新著《鸳鸯蝴蝶派》(上海书店1994年版)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概念,将该派的兴衰流变,置放在近现代相互沟通的文学史框架内,对大量翔实的史料钩沉索隐,爬梳剔抉,分析归整,并运用一种新颖的叙述手法,透视了这一时期鸳蝴派的基本概貌。
鸳蝴派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而是由一些文学趣味相投的小说家、报人逐渐趋合的创作流派,最早多以鸳鸯蝴蝶入诗,写一些四六句的骈俪文章,如“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之类,晚清李伯元的吴语小说和吴趼人的“写情小说”也都是该派的渊始。①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称之为拟古派的末流,并把较早出现的《海上花列传》和《海上繁华梦》称为“狭邪小说”。到1914年《礼拜六》创刊,聚拢了大批江浙作家,他们在创作实践上多写一些风花雪月、男欢女爱,在格调上哀感顽艳甚至下流、肉麻的作品,在理论上也提出了趣味主义的“文学无目的”论,因此,“礼拜六派”几乎取代了原有的称号。在1921年以前,他们几乎垄断了当时所有的报刊,创作阵营颇为庞大,题材范围涉及言情、社会、黑幕、侦探、武侠、历史、宫闱、神怪、反案、滑稽、娼门等三教九流,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内,包括新闻、出版、电影、戏剧、广播乃至商业界,都占有很大的优势。但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者似乎忽略了这一文学事实,特别是鸳蝴派的称谓被蒙上“恶名”载入另册,致使该派“五虎将”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至少有三人曾否认自己是鸳蝴派人物,这无疑包含了政治批判替代文艺批评的历史因素。但是在重写文学史的今天,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价这一流派,需要做大量基础性的工作。《鸳鸯蝴蝶派》一书为该派的重新入史做了扎实的奠基工作。
一、史料的梳理和诠释。《鸳鸯蝴蝶派》是一部品位较高、雅俗共赏的文学流派小史,其鲜人耳目之处在于运用了掌故学方法和笔记式文体。当前,文学史研究一方面尚未摆脱以社会变迁为背景,以政治批判为标准的陈旧方法的束缚,对文学规律的概括和归纳疏离了艺术本体的价值规范;另一方面趋于纯粹艺术嬗变的释演,单纯依赖抽象理论的推证,忽略了演史叙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价值。《鸳鸯蝴蝶派》重视对文坛掌故的收集整理,这无疑是一个新颖的视角。
文学史的归纳是一项系统、严谨的工作。掌故不同于历史,它是一种小品(sketch),虽显得短小零散,但很多历史精神渗透在细碎的掌故之中。袁进先生注重把握这些为一般文史家不太重视的史料,运用笔记的体式巧妙地穿插在史的叙述之中。这些小品能够充分反映文艺流变的基本背景,作品创作的基本动力及文艺主张的根柢,可以从中窥视转型时期文学律动的某种心态,某种方式以及它的最终命运。因此,掌故学方法就是一种科学实证的方法。在文艺领域中,艺术和现实生活、作家的艺术体验和作品的文本生成,是18世纪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以来文艺批评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直到此后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如日本“私小说”、中国的“身边小说”)及现代主义(如日本新感觉派、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等,都倚重从作品开始的追溯上升方法和以作者生平、创作环境为契机的编年、纪传研究方法。因为对小说创作从主体到观照对象、到读者接受,都是在作品中产生关联的,作家的创作素材与生活体验以及读者的审美活动,在评价过程中及阅读效应上,都是平面的、单线式联系的。正如日本文艺史家冈崎义惠所说“文艺共同体的文艺作用关联的事实是实现文艺价值的普遍价值的方式”,②而这正是构筑文学史的基础之一。《鸳鸯蝴蝶派》重视这些基本层面的价值取舍,对鸳蝴派的缘起、流变及构成、性质,进行了较为恰切的爬梳、归整,力图在宏观上保持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同时又从横断面上展开微细的剖析。由于采取了史论结合的叙述样式,并抓住了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中的主要契因,如作家生平、理论主线、评判准则、作品梗概、作品社会影响以及相关的文坛掌故、趣闻轶事等,这些都可以作为背景材料井然有序地编织在整体的介绍和评价中。在微观研究中,作者对文学的个人样式、作品特性及流派的整体风格作了社会学考察。如关于作者,对其显匿、身份、家系、交友恋爱、社会习俗、文艺思潮、创作动机作了详尽的描绘;关于作品,对素材遴选、人物原型破译、情节创构、表现形式的确定及社会轰动效应,都依据历史的真实加以考据推证;关于作品接受状况,从读者对作品的反观体验,作品在社会道德文化碰撞中的影响、在商品经济萌芽中评价的变迁、在20世纪文学格局中的历史定位等方面,也都是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考察,而非纯粹的理论归纳。这种依赖逻辑实证的演史方法,使得该著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学史料,并直接成为某些论点的有力证据。《鸳鸯蝴蝶派》列入老作家柯灵、范泉先生主编的“文史探索书系”出版发行,这大概也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研究视角的转换和方法的更新。文学史演变的首要意义是在不断变化的文学环境中作出价值的判断和选择。中国文学的近代化过程是在一个极为困窘的环境中展开的,一方面虽然有西方文化形态作为观照,却未能形成一种新的文学价值系统;另一方面,面对古典文学中小说的卓著成就,缺乏一种历史的宏观审视和价值认同。因此,近代文学就其艺术成就而言,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形成了一种隔离机制,真正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的小说只有名噪一时的谴责小说。随着文学板块向历史荒原的飘移,学院化的批评再也难以找到能够在这一空白地带占据重要位置的小说作品。在20世纪文学史上,即使被五四文学的新形态作品占据的地位,今天看来也未必是完全相宜的,历史的相对性总会在积淀过程中淘汰一些卑微、虚假和轻浮。这是单一的评判标准给文学史家遗留的一个棘手问题。
文学史要保持自身的连续性,必须转换视角,重视文学进步、变易的每一环节,这促使研究者注意到外部环境对文学内部机制的影响,并从许多平庸作品中仔细发掘,寻觅其中嬗变的轨迹。这不意味着采取一种宁取勿弃的态度,而是采取多元的价值标准作为规导,即排除单一的艺术审美观照或纯粹的政治批判,从文化的、艺术的、社会的、历史的不同视角审视,才会得出科学的结论。鸳蝴派在近代小说变革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与白话新文学有一段同步发展的时期,这是20世纪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环节,也是文学史家不应回避的一个问题。袁进先生对鸳蝴派的历史考察正是置放在一个文化选择、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展开的。文化的变迁、语境的转换以及主体意识的确立,都为文学的歧变准备了重要条件,其结果是象征文学走向繁荣的众多社团流派的涌现。鸳蝴派是与新文学对照下的另一种文学流派,是同样在原生文化与新生文化对撞背景下分流出来的异质文化,与新文学互为反动,又有所依赖,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这一视角无疑是全新的,体现了作者的判据并未拘泥于一般的审美认识活动中。以单一的审美标准认同某些作品,或纯粹以思想的进步性判定文学的价值以此总结文学的演变过程,只能失却文学史的真实性和公正性。《鸳鸯蝴蝶派》正是对这种偏执的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拨。
三、对定论的质疑和作者的创见。在新文学史上,鲁迅、茅盾、郑振铎、瞿秋白等人都曾对鸳蝴派作过有力的批判,这是适应文学革新(包括创作观念和表现形式上的)的现实需要而展开的。鸳蝴派受到冲击后并未转向中衰,而是继续走向全盛。其最为畅销的“四大说部”,其中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均盛行于清末民初,五四后也销势不减;而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却是在1931年问世的,并成为该派影响最大、品位最高的作品;抗战以后,以天津为中心又孳生了北派小说,以上海为基地后续了秦瘦鸥等海派文人小说。因此,如果说沈雁冰改版《小说月报》削弱了鸳蝴派通俗文学的文坛地位,却不能依此认定鸳蝴派小说作品失去了市场。在当时纯文艺仍囿限于文人学者的圈子中时,新兴市民阶层阅读的并不是《呐喊》、《彷徨》、《子夜》、《雷雨》,而恰恰是鸳蝴派的通俗章回小说。当然,适应市场要求鸳蝴派在语言运用上已趋时迎新改用白话了,多数作家也注重思想的进步性。像《啼笑姻缘》、《春明外史》、《秋海棠》等,都是讲述平民百姓的故事,写民生的哀怨和疾苦;特别是张恨水,在“九·一八”事变后,创作了不少抗战小说,其《弯弓集》就是取“弯弓射日”之意。袁进先生对这些事实都作了客观的分析,给予公正的评价,他认为以往对鸳蝴派的评价有失公正,并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还可以得到许多史料的佐证。如:
1.从当时上海的社会文化环境来看,并不能把鸳蝴派简单地概括为“十里洋场的畸形产物”,不能把它的成因完全归结为“租界”的存在。上海既产生了晚清小说,也是新文学诞生的基地,而且像张恨水、还珠楼主等作家都是在北方城市成名后才来到上海的;上海出版印刷业远较其它城市发达,市民知识化程度较高;上海有一个相对开放的道德、文化、市场环境;类似的作品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属于世界共同的文化现象;真正在上海“租界”生活并创作的作者廖廖无几。因此,鸳蝴派小说是迎合上海市民生活及心理需要的通俗小说,而非“租界”的独特产品。
2.鸳蝴派小说在20世纪文学史上有独特的贡献,而不能简单地视为新文学的逆流。首先,在梁启超标举“小说界革命”的大旗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鸳蝴派曾经反对过这场“革命”,“革命”的小说理论为小说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未能使小说茁壮成长,而鸳蝴派却以游戏消闲的目标打通了小说潜移默化的通路,使小说真正进入到市民阶层。其次,五四文学革命以后,鸳蝴派小说由正统文学转入通俗文学领域,它的“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主张与“为人生”的严肃文学追求无疑是相悖的,但也没有对五四文学革命构成危害;而它的大众化文学追求的实绩却是新文学作品难以企及的。第三,鸳蝴派早期的文学刊物,曾是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园地,鲁迅、周作人、叶圣陶、冰心、刘半农等都曾有该派刊物上发表小说;当时包天笑、周瘦鹃等鸳蝴派大将,都很重视外国小说的翻译,不仅敢于突破题材禁区,而且在作品中也容受了西方小说的某些技巧;在《新青年》提倡白话的时候,包天笑也在抨击文言,提倡白话了。所有这些对新文学都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3.鸳蝴派小说不等同于色情小说。早期的部分民初旧派小说可归属为鲁迅称谓的“狭邪小说”,属于“嫖界教科书”,如张春帆的《九尾龟》,借小说传授嫖妓的经验。但早期的代表性作品《海上花列传》却属于“劝戒”之作,并曾受到胡适的推崇;符霖的《禽海石》、吴趼人的《恨海》也都是从反对封建礼教的角度“言情”的。被周作人誉为鸳蝴派鼻祖的苏曼殊,其《断鸿零雁记》描写破规破戒的“和尚恋爱”,与徐枕亚的《玉梨魂》描写“寡妇恋爱”,在题材上都敢于突破禁区,在描写上也很节制。向恺然的《留东外史》许多地方讲的是“嫖经”,但在涉及性关系时,却是极为干净的。至于40年代的冯玉奇,炮制了许多“薄利多销”的色情作品,但为鸳蝴派作家所小觑而拒之门外,鸳蝴派刊物也不登载他的作品。代表作家张恨水的小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表示过赞赏,50年代文化部也曾发出内部通告,说明其小说属于一般的言情小说,不是淫秽、荒诞的作品。③
4.鸳蝴派的消亡,除了自身发展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创作队伍日趋涣散外,其外部原因主要有二:一是40年代末期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出版业已无法依赖畅销作品维持生存,通俗文学因此萎缩;二是解放后,鸳蝴派属于改造对象,不可能再自由创作那种“游戏”“消闲”的作品。
四、媚俗倾向与品位的提升。鸳蝴派与市场行为结下了不解之缘,畅销的迎合市民读者心理需求的作品不断被加工、复制上市。商业机制是促进大众文化发展的契缘,但急功近利的商业化行为却使得鸳蝴派小说呈现粗制滥造的趋势。初期那种通过触及道德问题、新女性问题来化解正统礼教文化的功能渐趋衰微,而最终目的却明显指向商品主义、趣味主义,游戏消闲冲谈了本来就不太突出的怨世情绪和干政意识,许多小说沦为庸俗化的制品。对此,袁进先生认为:“鸳蝴派作家的早期创作已经具有较强的媚俗倾向,用故事的离奇曲折招徕读者,用中国传统的‘大团圆’结局迎合读者的心理”。“媚俗”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具整体意义不仅包含了邀媚取宠、同流合致的角色心里取向,而且最终是对文化权力的消蚀和解构。早期鸳蝴派的言情小说,其媚俗意义不仅指“文学上乘”的小说可以降尊纡贵描写才子佳人,也是作者与适应于古典章回小说的读者之间关系的调适,但这种调适是否合乎某种服从社会文化需要的形式结构和文艺自身规律的要求,袁进先生未作进一步阐明。笔者认为,鸳蝴派不仅迎合了城市市民阶层的世俗审美旨趣和商业利益的追求,而且是对“小说界革命”文学实践价值和文研会的功利主义的一种消解。如果说“小说界革命”试图借助政治小说改变世道、重新确立某种社会规范,人生小说在重新寻求一种崭新的个人意义的话,鸳蝴派则是试图在艺术的废墟上建立世俗价值的大厦,尽管它不合时宜,但作为时新的俗文化小说达到了“小说界革命”所不及的社会认同,尊雅卑俗的传统意识至此在贴近一般文化层次的市民过程中才被别置一处,彻底反转。当新文学再次确立一种新的“雅颂”意识时,鸳蝴派依据巨大的市场能力和众多读者与这种新文化意识抗衡,特别是原来的文人才子在精神上流入世俗,其独霸文坛的地位被动摇之后,最终只能无可奈何地以趣味主义相标榜,正如昆德拉所说,媚俗起源于“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④鸳蝴派早期对小说的“无目的性”追求并不把商业利润作为附加条件,然而一旦沾染了畸形的商业化社会病态,其媚俗意义便只能作为曲折离奇的情节技巧追求,通俗文学的趣味主义在“为人生”口号的衬映下,却变得毫无价值。正因如此,鸳蝴派只是面向流行的价值观念认同,而小说艺术的本体地位却难以确立,这是俗文学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种现象。
事实上,鸳蝴派在当时很难找到一个文学体系的精神支柱,一种类似美国的“牛仔”风格的开拓冒险精神或欧洲的“福尔摩斯”式的理性思辩精神,而是从世俗民情中玩味到一种“鸳鸯蝴蝶”情结来取悦世人。但是,当文学的愉悦功能耽溺于玩世、嬉谑的时候,艺术信条就被商业利润冲淡了,而原本缺乏对艺术忠诚的小说家们,就成了卖文为生的小说匠。依此,鸳蝴派小说家们最终缺乏的是一种直面人生的社会责任以及对生命本真内蕴的憬悟。
注释:
①阿英:《晚清小说史》第十三章《晚清小说之末流》。
②[日]长谷川泉:《近代文学研究法》,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
③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见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
④[捷]>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页。
标签:文学论文; 鸳鸯蝴蝶派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张恨水论文; 小说论文; 作家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