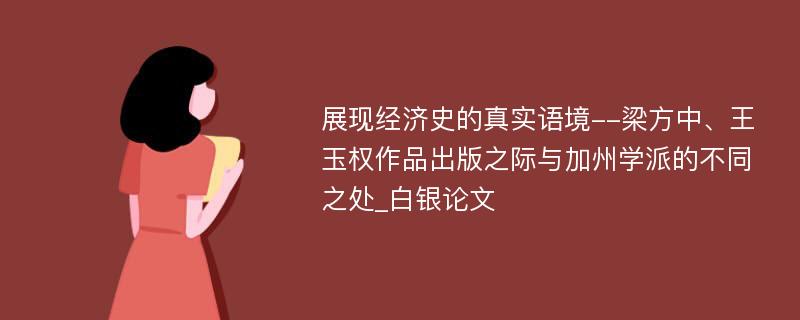
展现经济史真实脉络——写在梁方仲、王毓铨文集出版之际,兼评他们与“加州学派”的区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州论文,学派论文,脉络论文,写在论文,区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加州学派”研究中国经济交的代表作《白银资本》、《大分流》中译本出版后,受到不少中国学者推崇,这些著作认为:中国在18世纪前一直主导世界经济格局,只是因后来白银输入锐减,缺乏便于运输的煤炭等支撑工场制度发展的资源,才落在借机崛起的西方后面。所以亚当·斯密、韦伯等人把西方国家现代先进地位归因于近代以后的制度创新,这是犯了“欧洲中心论”的大错。“加州学派”力图在中国传统制度中发掘出符合现代社会方向的内质,这当然对今人评价和选择经济社会方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上述著作因满足了国人的自尊而引起喝彩本不足怪,只是相比之下,一些本土经济史研究的经典性成果长久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甚至被有意无意地淡漠和遗忘,让人颇多感慨。这里我们以粱方仲和王毓铨先生的学术方法为例,说明为什么只有如他们所示范的那样深入把握制度性质,而不是如“加州学派”那样忽视制度对经济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正确展观经济史的脉络。
梁方仲与王毓铨
中山大学最近出版了《梁方仲文集》,中华书局不久将出版《乏毓铨文集》。今人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梁、王两先生已经知之不多。梁方仲(1908-1970),18岁由南开中学跳两级入清华大学农学系,次年转西洋文学系,后转入经济系,并于两年后毕业,1930-1933年就读并毕业于清华研究院经济所,此后入中央研究院,又赴美被聘为哈佛经济系研究员、后赴伦敦大学从事研究。1947年回国后继续担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53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在中国经济史,尤其是赋税史、经济统计学中取得了惊人的开创性成就。王毓铨(1910-2002),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论文得到导师胡适的赞赏,1946年获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任美洲古钱学会博物馆远东部主任。1950年回国,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以对秦汉史、明史(尤其是经济史和制度史)、土地、户籍、赋役制度等精湛和贯通的研究著称。
梁、王两先生典型地反映了那时具有类似背景一批大学者的命运。他们在一个有着崇高学术标准的时代,早早做出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后来却只能长久默居于潮流之外,甚至他们的许多基本研究结论和方法都已不甚为学术界知晓。以受到热烈追捧的《白银资本》所讨论的17世纪前后中国输入白银问题为例,1939年梁先生发表的长篇论文《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就对中国输入白银数量、外贸规模等问题做出缜密的研究;他在对一条鞭法的经典性研究中更充分说明:中国当时赋税货币化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财政运作的需要,白银流通也主要是在政府财赋的分配领域。这种来自政治体制的上游需求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导致下游民间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但这与因民间贸易增长而启动的贵金属货币大量流通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它也根本不能引发手工业、农业的同步发展,听以梁先生后来在他另一本重要著作《明代粮长制度》中称其为“虚假繁荣”。弗兰克不知道传统中国的贸易和赋税主要是围绕统治权力的制度需要和权力集团奢侈消费为核心而进行的,仅凭想象以为中国大量用银是因为国计民生相关贸易规模的巨大、“市场”普遍发育,再推论其标志的现代制度意义远在同时的欧洲之上,进而指责斯密以来人们都犯了“欧洲中心”的大错——他对所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的茫然无知,让人叹惜。
再以王先生为例,他据斯密定义而指出近现代赋税是通过“代议制国家”和“纳税的人是那个政府的公民”等制度基础而实现的,这与传统中国赋税制度完全不同,后者的性质是百姓“因人身依附关系而隶属于帝王”,其核心问题永远是“人民和土地是怎么变成帝王的私产的”。(《纳粮也是当差》、《〈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写作提纲》)然而这样警策的结论即使是在他曾领导的中国社科院明史室,恐怕也早已被束之高阁,代之而兴的是这样的新论:“晚明白银由非法到合法,更成为社会主币,货币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市场作用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白银货币化表明中国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跃,引发了社会整体变迁,标志着社会的转型,近代的开启。”(万明:《晚明社会变迁的研究》)以为在根本的法权体系未被更动之下,货币形态的转变即可以启动和标志一个新经济时代,如此视王先生的经典结论于不顾,也颇显出“近来时世轻先辈”的风尚。
看似驳杂 实有核心
梁、王两先生的许多研究方法都值得后人学习,比如他们对每一具体问题的辨析都以把握整个历史脉络为前提,比如他们博极群书、对于正史以外浩繁资料的重视和运用,等等。但我以为他们还有着更核心的学术方法,即以对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质和统治权力组织结构的深入把握,作为解析一切经济问题的基础。
1980年代以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引起经济学从研究“悬空”的经济运行,转变为研究复杂社会环境(尤其是具体的政治、法权、国民法律文化心理环境)下的经济性状。用德国学者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的话说,制度对于经济基本环境的规定,乃是一种“统率性规则”(overriding rules),它“为低层次规则创建了一个框架”。而对于中国问题研究来说,这个视点之所以尤为重要,是因为在中国“秦制”以后“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体制中,凡土地、赋税、产权、工商业等基本经济形态,都不过是政治权力的延伸——经典性的描述是:“九州之田,皆系于官”;“(百姓)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这种法权制度始终没有改变,所以直到17世纪的商人跪在清官老爷脚下叩谢大恩时,对自己身份的概括依然是:“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这蝼蚁之命都是老相公所赐!”
梁、王两先生的工作始终是以把握上述制度特点为基础的;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秦制”后的权力形态远不仅是简单的统治理念,更是一整套高度缜密的制度结构,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支撑权力机器运行的那套犬牙交错的制度保障系统,中国一切重要经济现象的第一属性都由此决定。出于这种体察,梁、王长期学术生涯中虽研究了大量看似分散的具体经济问题,如土地、户籍、货币、军屯、矿业、运输、赋税徭役等,但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一个统一的核心而进行的。比如梁先生对于“一条鞭”的研究,着力处集中在权力体制深刻危机与税制沿革间的因果关系;再如王先生《莱芜集·前记》说自己此集涉及土地、人户、等级、阶级等杂驳的内容,但又是在研究“专制政权这个总意图下随时写出来的”。
因为抓住了制度核心,他们的洞察力就突显出来。比如,与众多学者认为“一条鞭”以后“中国税制始入近代之形态”不同,梁先生对极其浩繁的资料详细梳理之后的结论是:“自摊丁入地的办法盛行以后,一切苛捐杂税,凡可以由田赋负担的莫不尽量摊入田赋以内,大开田赋附加的方便大门,给明清以迄民国的财政史上写下最黑暗的纪录和一笔烂胡涂账”;他还指出:由于政治和赋税体制的黑幕化,所以“任意作弊”成了“一条鞭”等任何经济改革都无法触动的制度特征,“直至辛亥革命以后”依然如此。(《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再如,将中国传统农民定义为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久已众口一词,但王先生却说:
农民(明代的“民户”)的身分不可以说是“自由的”、“独立的”。他们的人身和其他编户的人身一样是属于皇帝的。……皇帝可以役其人身,税其人身,迁移其人身,固着其人身。只要他身隶名籍,他就得为皇帝而生活而生产而供应劳役;而不著籍又是违背帝王大法的。……在古代中国的编户齐民中,自由和独立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可能连这两个概念也没有。……明朝的皇帝每于郊祀上报皇天牧养有成时,都是把全国的户口簿籍(赋役黄册)陈于祭台之下,表示上天赐予他的对人民土地的所有权。有意义的是事经两三千年,在十七世纪以前,没见有人对皇帝的这种权力提出质问,更没有人讨论过编户齐民为什么或是否应该接受这种权力的支配。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人的权利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事实上它不存在。
因为这个结论基于对户籍、土地、税役等非常细致而坚实的研究,于是它对于制度经济所关联的诸如法律、伦理、意识形态、行政体制等几乎所有重要领域中的课题,都有了力举千钧的意义。
道格拉斯·诺斯对现代经济制度核心原则的定义是:“交易的基础——使交易成为可能的——是一个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他强调,确立贸易者及其商品的法权地位、“而且这些权利在法律意义上能行使”,是社会得以不断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使商品生产和“经济组织”发展起来的前提(参见《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比较诺思理论可以知道:梁、王的研究正是从“复杂法律结构及其实施”这个制度基础上,清晰具体地说明:为什么中国传统经济形态是与近现代世界方向完全悖逆的。
“加州学派”失之千里
通过梁、王的研究不难领会,为什么对于制度形态的把握不仅是解析中国经济史具体问题的前提;而且是判断这一经济形态之前景的关键。因为在这个制度环境中,许多看似通常经济现象下深藏的是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制度指向,所以研究者如果仅据一时的市场、货币、工场规模、生产技术手段等,就急于定义其如何独立于欧洲而早早昭示现代经济的意义,就可能完全与事实相左。
仍以弗兰克所说白银输入减少、才导致中国原本先进的经济体制衰落并丧失世界领先地位为例,其实他完全不知道明清时白银输入规模与“权力资本”积累运作间的比例: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70年间,中国通过与葡西日等国贸易而输入白银约一亿两(《梁方仲文集》220、222页);但这前后,极度腐败的统治权力鲸吞国民财富的规模,早就是任何贸易财富不能及其一毛了,这种鲸吞更没有因“白银短缺”之类原因有片刻停歇:比如刘瑾掌权的短短四年半中,仅搜刮到家中的白银竟达两亿五千万两、黄金一千两百多万两!以后权势人物家藏数百万、几千万两银子的情况比比皆是,如严嵩失势之后转移了大部分家财,但其一处宅邸中仍剩有四百多万两银子和无数珍宝。再比如万历时皇帝的亲信可以“五日之内,搜取天下公私金银已二百万”;广东税监李凤掠夺民财规模是“乾没五千余万,他珍宝称是”(白银五千多万两,加上等值的其他珍宝),“私运财贿至三十巨舟、三百大扛”;山东税监马堂几年之内贪污税银,仅被一次举报的就有一百三十余万两。17世纪初,全国盐税收入每年仅白银一百一十五万两;但一个官职比芝麻还小的衙门书吏,他看准“以黑吃黑”的官场机会时,举手之间敲诈分肥所得就是两万两银子!在这种“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的巨大反差之下,经济行将崩溃的结果早已不言自明。所以,如果对“权力经济”这个中国基本问题一无所知,而以为从白银输入等皮毛问题入手就可“悬丝诊脉”地判断经济制度走向,恐怕真要贻笑大方了。
再看《大分流》的论点(直至18世纪,中国与欧洲在“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都无重要不同,只因中国江南不具备英国那样方便的煤炭等资源,所以未能导致经济革命)。其实事实刚好相反:中国“市场”性质与欧洲差别极大,其最显著之一就是百姓在统治权力面前,永远不能在法权意义上具有“人的权利”和真正拥有财产,而这正是王先生早已系统说明了的基本制度背景。有关权势者通过垄断市场、欺行霸市、恶税恶法、特务酷刑等等而掳掠惨杀工商业者和市民的记述,在官方文献中汗牛充栋(详见拙文《为什么宪政对人权和财产权的保障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这种环境下,经济资源与国计民生的关系如何呢?举17世纪《富春谣》为例: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于戏,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正是因为百姓无可逃遁于“官府拷掠无完肤”的虎狼威势之下,所以即使在经济地理最优越的地区,各种丰富优质的资源非但没给小民带来丝毫福祉,相反却使其大难临头,以致他们只能以哀祈上苍将这些资源尽数摧灭。如果对此类司空见惯的现象略有所知,都不难知道把中国未能如欧洲那样自主走出中世纪的原因归于物质资源的匮乏,这与社会真相差得实在太远。
小资料
加州学派
“加州学派”是近年来在美国中国学界崛起的一个学派,因其核心人物都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而得名,有彭慕兰、王国斌、李中清、杰克·戈德斯通、贡德·弗兰克等人,他们之间虽也有争论,但都同意18世纪前后的中国比以前人们认为的更繁荣。以2001年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的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著《大分流》为例,该书认为: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大致处于同样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明显和独有的内生优势;直到18世纪末,东西方才开始分道扬镳,此后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西方走向近代化而中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彭把这个分途过程称为“大分流”。
在中外学界对加州学派好评如潮的同时,也有批评的声音,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黄宗智认为,《大分流》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加州学派把17、18世纪的清朝抬到了不应有的高度,其实清朝当时的经济状况不能与欧洲相提并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是互动的,技术与海外掠夺并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如秦晖教授指出,弗兰克动用大量资料证明的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中国在1400-1800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根作为贸易顺差流入中国。但是弗兰克从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实中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结论,即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这个推论恰恰既没有什么实证基础也没有逻辑依据。众所周知,我国现在就是世界外贸顺差最大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日本),而美国则是世界头号外贸逆差国。这能说明我国如今是“世界经济中心”而美国则是比非洲还要惨的最“边缘”之地么?
不过,从中国经济形态的政治和法权背景与欧洲的区别着眼而对于加州学派的批评,似还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