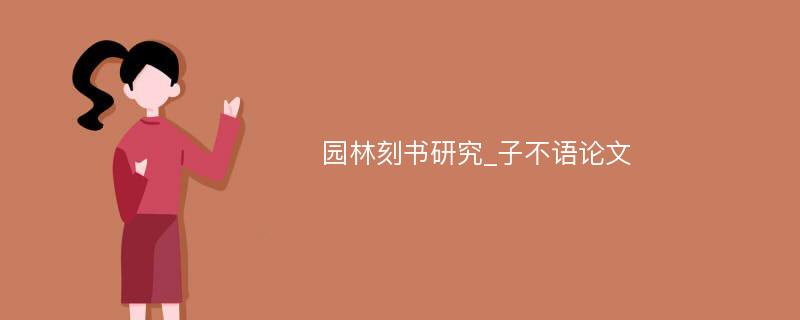
随园刻书考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随园刻书考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袁枚在清中叶文坛享有盛誉,其“性灵”诗论亦可谓深入人心。究其原因,固多而复杂,然其中《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等重要著述在生前就已刊刻并广泛传播,应该是诸多原因中至关重要的一点。钱泳《履园丛话》曾云:“自宗伯三种《别裁集》出,诗人日渐日少;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①此语虽主要着眼于袁枚、沈德潜二人诗论之不同,但对《随园诗话》出版后所造成的文坛影响,亦描述得颇为到位。所谓名山事业,不特撰著有功,刊布传播亦其中关键。惟今人在论及袁枚之思想地位时,虽多围绕其著述展开,却罕见论及出版传播情况。因捃摭所见,汇为一文,以供学界参考。 袁枚(随园)的刻书活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移居随园之前,即乾隆十三年(1748)前;第二阶段为移居随园至嘉庆二年(1798)袁枚去世;第三阶段则为袁枚去世之后。严格地说,真正由袁枚主持且发生于随园的刻书活动只有第二阶段,这也是本文论述的重点。然而作为随园刻书的前奏与延续,第一、第三阶段也是随园刻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故有必要先作些简单的介绍。 袁枚在第一阶段所刻包括《袁太史稿》及《双柳轩诗文集》。前者为制艺文集,不分卷,由弟子秦大士初刻于乾隆十年(1745),后又几经重刻,目前较常见的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袁鉴重刻本。后者为早年诗文别集,包括《双柳轩诗集》、《双柳轩文集》两种,由另一弟子谈羽仪刻成于乾隆十一年(1746)前后。此书后因袁枚“悔其少作,将板焚毁”②,故存世量极少。从版式风貌看,袁鉴重刻本《袁太史稿》(秦大士本笔者未见)与《双柳轩诗文集》颇有相似之处,而与此后随园诸刻本不同。如二者均为软体写刻,正文无界栏而刻有圈点,这与其它随园刻本的方体字、有界栏有着明显区别。这可能是袁枚刻书初期所采用的基本版式,而袁鉴在重刻时,或许有意地沿袭了其初刻本的面貌。 随园第三阶段的刻书活动由袁枚后人主持。一方面,此前随园所刻书板在这一阶段仍继续刷印并公开发售;另一方面,其后人亦有刻书之举。如袁枚《随园随笔》一书,即刻于袁枚身后③。此外,随园还曾相继刊行《筱云诗集》、《捧月楼词》、《饮水词》、《筝船词》、《绿秋草堂词》、《玉山堂词》、《崇睦山房词》、《过云精舍词》、《碧梧山馆词》九种,皆系袁枚后人撰著或编选之作。这些刻本内封仍有“小仓山房藏板”或“随园藏板”的字样,版式行款亦基本一致。据各书序跋署款,成书最晚者在嘉庆二十年(1815)前后,则随园刻书活动的下限亦当不早于是年。按袁枚二子迟、通相继于道光八年(1828)、九年(1829)去世,此后袁氏后人虽仍有刻书之举,然其时随园固已不存(随园于咸丰三年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所刻书之面貌亦与此前大不相同,故不当再计入随园刻书之范畴。 随园第二阶段的刻书活动主要集中在袁枚晚年。乾隆四十年(1773),六十岁的袁枚开始第二次刊刻其诗文著作,亦即在《双柳轩诗文集》基础上删改、修订的《小仓山房诗文全集》④。据《小仓山房文集》卷首万应馨《题辞》中“积累三十年,富敌丘山隆。先出骈体文,一扫徐庾空。诗集别专行,授梓尚未终。独将古文编排分卷二十四”等语,再结合现存书籍实物,可知所谓“全集”包括《小仓山房外集》、《小仓山房文集》、《小仓山房诗集》三种。其中以收录骈体文的《外集》最先刻成,《文集》继后,《诗集》最晚,各本初刻时分别为六卷、二十四卷与二十卷,三者共计五十卷⑤。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袁枚好友张凤孙已获赠《小仓山房诗文全集》一部⑥,可知其时《全集》初刻已完成。 随后开雕之书系其堂弟袁树的《红豆村人诗稿》。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袁枚致袁树手札中,有一段关于此书刊刻的珍贵记载: 《红豆村人集》久已刻完,今刷印百本寄上。开首一卷刻得最劣,去年我将汤鸣岐大骂一顿,命其改刻。今仍是原本刷本,看来还要赏他几两银子才好也。如弟看后,以为不必重刻,则亦罢了。二卷、三卷所以好者,以骂后所刻故也。⑦ 信中所及刻工汤鸣岐,在黄裳《清代版刻一隅》亦见提及,称其所刻《半舫斋古文》、《读史提要录》等书“精写精雕,为广陵刻本代表作”⑧,可知亦为当时刻书好手。惟今检《红豆村人诗稿》,并未留下汤鸣岐刻款,所刻亦不及《读史提要录》精善。 乾隆五十年(1785)之后,随园刻书活动日渐频繁。时相继付梓的有《南园诗选》(乾隆五十二年)、《子不语》(乾隆五十三年,后改名《新齐谐》⑨)、《湄君诗集》(乾隆五十三年前后)、《小仓山房尺牍》(乾隆五十四年)、《续同人集》(乾隆五十五年)、《随园诗话》(乾隆五十五年)、《随园诗话补遗》(乾隆五十七年)、《随园八十寿言》(乾隆六十年)、《随园女弟子诗选》(嘉庆元年)九种;此外刊行时间未详但可确定系袁枚生前所刊的尚有五种,即《袁家三妹合稿》、《续子不语》(后改名《续新齐谐》)、《牍外馀言》、《随园食单》、《碧腴斋诗存》。其中《续同》、《寿言》、《女弟子》三种为袁枚编纂,《南》、《湄》、《三妹》、《碧》四种为袁枚代刊的亲友著述,其余七种则为袁枚独撰。 综上,随园第二阶段共刻书十八种,加上第一、第三阶段的十三种,共计刻书三十一种。除《双柳轩诗文集》书板已毁外,实际行世的有二十九种。后人将这些著述辑成丛书《随园廿八种》行世(缺《随园食单》),并于第一种《小仓山房文集》卷首添加一叶丛书目录。将丛书与单行本相比,可知系同一组书板刷印,惟丛书本多断版、修版的痕迹,不少内容甚至脱落遗失,显系极后印。不过《随园廿八种》存世并不多,更常见的是另一种名为《随园三十种》的丛书⑩。此部丛书虽较《随园廿八种》更全,却并非据随园原版刷印,而系重刻之本。就笔者所见几部来看,版式面貌亦彼此不同,显然还重刻了不止一次。虽然各本内封亦有“随园藏板”字样,但其巾箱本的版式、错讹丛出的版刻,均带有浓厚的书坊气息,当出自坊间。至于其它《随园三十六种》、《随园三十八种》之类,已出现袁枚孙辈著述,显然更为晚出,此处不赘。 随园刻书,不少系随编随刊,故存世者卷数不定。此现象在古人著述编纂、出版过程中并不鲜见(11),这是因为著作初刻时作者尚在世,故仍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状态。后为补入新作,除别作续编、补遗外,亦往往直接增刻书版,补缀其后。一般来说,后来增补之本由于内容更全,会很快替代内容尚不完善的早期刻本。特别是普通家刻本,由于发行量、传播范围相对较小,更新较易,故最终流传下来的大多都是晚期足本。 然而,随园刻本却略有不同。由于袁枚晚年享有极高的文坛声誉,又兼交游广泛,其著述的发行量与传播速度着实令人惊讶。所谓“每仓山一集刷成,顷刻散尽”的盛况(12),使得今天存世的随园刻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呈现出卷数不一、内容各异的复杂面貌。以《小仓山房诗集》为例,即笔者经眼之随园刻本,就有二十卷本、三十二卷补遗一卷本、三十二卷补遗二卷本、三十四卷补遗二卷本、三十六卷补遗二卷本、三十六卷(补遗散佚)本六种,这无疑是历次增刻所造成的。再细究之,则每次增刻甚至常常不足一卷。如三十二卷补遗一卷本与三十二卷补遗二卷本,前者卷三十二仅刻至第二十七叶,后者则有三十八叶;又如三十四卷补遗二卷本与三十六卷补遗二卷本,虽同有补遗卷二,前者仅刻至第九叶,后者则有二十一叶。 更重要的差异则体现在内容上。袁枚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致梁同书的信中,曾感谢梁氏为其校勘《小仓山房诗集》并指出讹误多达九十一条。其后,袁枚不仅修改了其中八十九条,还“特将改本另刷呈览”(13)。所谓“改本”,显然是指修订后的新印之本,这说明袁枚在增刻新内容的同时也不断对此前内容进行修订。仍以《诗集》为例,其卷十八《代琴书答》末句,二十卷本作“神爵三年买奴券,袖中擎出泪如丝”,三十二卷补遗一卷本作“僮约思量父某某,低头莫怪出门迟”,至三十二卷补遗二卷本重新改回“神爵三年买奴券,袖中擎出泪如丝”,至三十四卷补遗二卷本则又改作“交代儿家诸火伴,婆娑莫怪出门迟”。区区一句诗句,前后版本之多,袁枚修改之煞费苦心,实在令人惊讶。 除《诗集》外,袁枚所撰之《文集》、《外集》、《尺牍》、《诗话》、《子不语》等著述,同样是以随编随刊、随刊随改的方式刊行,并留下卷数、内容各异的文本。其中尤以《随园诗话》留下的版本最多也最复杂。此书在初刻本与最后足卷本之间,先后出现多达三百馀处的文本修订,其中有不少更改显得耐人寻味。例如其正编卷二涉及《红楼梦》的著名条目,早期刻本作: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文观园者(按:原文如此),即余之随园也。当时红楼中有女校书某尤艳,雪芹赠云…… 而至增刻本中,“中有所谓文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之语被剜改为“明我斋读而羡之”。而正因为这段文字的版本差异,引发了红学界围绕“大观园是否即随园”所展开的长达数十年的争议。事实上,若能明确这一文本变化实发生于《随园诗话》增刻过程之中,其内容修订亦出于袁枚本人之手,或可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14)。 诸如此类的例证还有很多。今人在解释袁枚“性灵”诗论时,常常过于强调其灵巧、随性的一面,却忽略其苦心经营的一面。正如其在《续诗品》序中所云:“惜其只标妙境,未写苦心。”(15)这种苦心,或存在于创作之中,所谓“毕竟诗人诗,刻苦镂心肝”(16);或存在于创作之外,上述对诗文的反复修订即其一端。如能更进一步追寻这些文本修订的痕迹,并借此深入了解袁枚诗学文献、诗学观念变迁的细致过程,必将有助于推进袁枚之诗学研究。 古之著述文集刻成后,多举以赠人,以广其传播。随园所刻诸书,奉赠官员友人者亦不在少数。但随着袁枚声名的日渐隆盛,其著述之传播速度与受欢迎程度,实在连袁枚本人也觉始料未及,即如所述云: 吴松厓屡索我全集,理应相寄,而苦于纸价太昂、嗜痂太众。每仓山一集刷成,顷刻散尽。业已增价至五金一部,而购者不嫌其敝帚之享,当初刻集时始愿实不至此。(17) 按此信作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吴松厓指甘肃诗人吴镇(1721-1797),与袁枚虽无往来,亦闻名来索《全集》(18)。诸如此类的远交当复不少,而袁枚苦于送书成本过高,乃不得不采取定价销售的策略。至此,随园刻书遂成为一桩有利可图之事。而孙原湘称“先生每著一书,购者如市”(19),亦可见当时购求之盛况。 又前信中提及《全集》已卖至“五金一部”的售价,亦即白银五两(20),而仍供不应求。这一点在其它文献中也可得到验证: 余在山阴,徐小汀秀才交十五金买《全集》三部,余归如数寄之。未几,信来,说信面改“三”作“二”,有揠补痕,方知寄书人窃去一部矣。(21) 海内士大夫,将所著作镂板行世者,浩如烟海,阅者大率攒眉,束之高阁,甚或拉杂摧烧以之覆瓿者,无万数也。仆虽梓《全集》六十馀卷,而自视欿然,常恐亦受此惨。不料有人溺爱嗜痂出重价购之,又有人当作奇珍异宝要于路而攫之……特再寄一部,纸墨刷印,大胜于前。(22) 两则材料所述,均为同一件事。彼此参照,可知徐秉鉴(小汀)出资十五金购买三部《全集》,与前文“五金一部”正相吻合。而据袁枚之孙袁祖志所撰《随园琐记》记载,《全集》定价实分为两种: 《全集》之由本园出售者,白纸每部价银五两,竹纸每部价银三两六钱。坊间则听其自定价目。每年统销约在数百部焉。(23) 据载,“五两一部”者即白纸本,此外还有相对便宜的竹纸本。惟笔者在袁枚自述文字中,暂未见此“三两六钱”竹纸本之记载,颇疑此非袁枚生前书价,而是去世后其子孙所定售价。 此外,黄世垲亦曾提及《袁太史稿》之售价为“钱六十”: 世垲年十二出应童子试,见有卖随园先生时文者,以钱六十购得之……顾卷头署《袁太史稿》,而刻先生名处,烟楮漫灭……年二十始得拜先生于金陵,先生时年六十七。 按袁枚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以黄世垲年二十之际袁枚年六十七计,其十二岁时当乾隆三十九年(1774)。其时袁鉴尚未重刻此书,未知黄氏所买系何版本。惟从署名处“烟楮漫灭”来看,此书刊刻质量不高,很可能是坊间翻本。 值得一提的是,今人袁逸根据黄丕烈《士礼居刊行书目》所列嘉庆、道光年间十九种书籍售价,算得清中叶书价在平均每卷7.5分左右(24)。前及《全集》六十馀卷售价五两,平均每卷合银8分;而《袁太史稿》仅一卷,售价6分。两种书价,均与7.5分之均价相去不远。 可相对照的是,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五月初九日的袁枚日记中,有一段关于《小仓山房诗文全集》印书工本的记载: 太史纸一篓,有四十八刀,每刀七十五张,计可裁七千馀叶,《全集》可印三部有馀。凡印书工连吃饭,每夹计钱三分,已为足价。每夹计书二百叶。排书每夹约工钱一分。(25) 按以诗文集编年结合实物验之,至乾隆五十九年《小仓山房诗文全集》当已刻至七十七卷,其叶数大致在2000叶左右。日记云七千馀叶纸可印三部有馀,正与此数不相上下。若以每部需纸2000叶即10夹计,则印书工价约需银30分,排书需银10分,共计需银40分即0.4两。而综合周启荣、张秀民二先生对明清书籍刊刻成本的推算,清中叶每叶成本或在0.25两左右(26)。一部《全集》2000叶,则其刊刻工价可能需要500两或者更多。为计算简便,以刷印500部计(前引袁祖志文称《全集》每年销量约数百部,故实际刷印数量肯定要超过此数),再加上每部0.4两的排印成本,一部《全集》真正的成本在1.4两左右。即以售价每部3.6两的竹纸计,其获利亦甚丰润。 需要指出的是,随园所刻书中,尚有不少他人著述,以及《续同人集》、《八十寿言》等诗文总集。这些书籍的利润,显然无法与诗文集企及。因此,袁枚仍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期降低刻书成本。如其刻《子不语》一书,即辗转求刻于粤省,以节省成本: 我此番浙江一走之后,又得《子不语》数十条。弟在广东可为我博访写来,将来刻成,必风行海内也。又闻广东刻字甚便宜,不过不好耳。然刻《子不语》原不必好也。弟为留意一问。 替我打听些《子不语》事寄来。闻广东刻书虽不好而价甚贱,意欲将此等游戏之书托弟在广东刻之。(27) 与刻《红豆村人诗集》时高薪聘请汤鸣岐不同(此书出资者亦当袁树本人),袁枚谋刻《子不语》时,首先考虑的正是刻书成本。这恐怕也与《子不语》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游戏之书,“原不必好也”,故不欲花重价刊刻有关。今《子不语》署名“随园戏编”而非“袁枚”,想必也正反映了这一心态。 此外,袁枚亦积极在弟子、友朋中寻找出资刻书者(尤其是官员与巨商)以减少个人投入。早期的《双柳轩诗文集》由弟子谈羽仪代刊,而《袁太史稿》初刻、四刻则分别由弟子秦大士、官员袁鉴出资刊刻(28)。此外,尚有弟子洪锡豫助刻《小仓山房尺牍》(29)、盐商鲍志道助刻《袁家三妹合稿》(30)、官员毕沅助刻《随园诗话》(31)、官员奇丽川助刻《随园随笔》(未果)(32)等,皆属此例。 袁枚曾在其《遗嘱》中,明确交代“随园《文集》、《外集》、《诗集》,及《尺牍》、《诗话》、《时文》、《三妹诗》、《同人集》、《子不语》、《随园食单》等版,好生收藏,公刷公卖”,并云《随园随笔》刻成后亦当“定价发坊,兼可获利”(33)。“兼可获利”云云,前已述及;惟“定价发坊”等语,涉及随园书籍售卖方式,似除“公刷公卖”外,尚有与书坊合作一途。这也可与袁祖志在《随园琐记》中的另一则记载相参看: 《小仓山房全集》计三十种……装订成册,计八十本。每大比之年,任坊间自备纸工来园刷印,本园每部取板资银一两。(34) 所谓“任坊间自备纸工来园刷印”,与“定价发坊”一样,均系与书坊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而特定“大比之年”,当以江南乡试期间士子云集金陵,其购求袁枚著述者亦当增多之故。惟此处“计三十种”的《小仓山房全集》,与随园三个阶段刻书总数相近,可知所描述之情形已在袁枚身后。即便如此,亦可见袁枚著述传播之后劲。 尽管随园主动与书坊合作,但所刻书籍还是不可避免地遭到坊间翻刻。较早刊行的《袁太史稿》,袁鉴序即云其“板屡翻”。至《小仓山房诗文全集》、《随园诗话》等出版后,更是迅速遭到翻刻。乾隆五十六年(1791),袁枚作《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翻板近闻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一首》(35),可知《随园诗话》甫出版一年,就已遭“三省翻板”。而笔者所见各书翻本,亦以《随园诗话》为最多。此外,较早出版的《小仓山房诗文全集》,亦紧随《随园诗话》而遭到翻刻。笔者曾于各图书馆见三十一卷本《小仓山房诗钞》(附《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当即《小仓山房诗集》之翻本。所收除附录二十首外,余均选自《诗集》前三十一卷及补遗卷一,选入篇目约为原书二分之一。从诗作编年看,其最初翻刻当在乾隆五十六年前后。又如《诗钞》本,笔者共经眼六种,皆内容一致而版刻各异,显系不同书坊的翻刻本。其他如《尺牍》、《文集》亦多翻刻之本,此处不赘。 与今日出版界之憎恨盗版不同,袁枚对其书遭遇翻刻不但不以为忤,甚至还有些沾沾自喜。弟子刘志鹏即曾就此事寄贺云:“年来诗价春潮长,一日春深一日高。”(36)对袁枚而言,书坊翻刻代表着其著述的受欢迎程度,亦能间接扩大其著述的传播面与影响力。今各大图书馆所存袁枚著述,坊间翻刻之本占一半以上,亦足证之。 而在坊间翻刻之外,尚有倾慕袁枚之官员文人主动代为翻刻著述或出版选集者,前及《袁太史稿》即为例证。此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调元在出任广东学政期间,曾刻《袁诗选》五卷以示诸生,将袁枚诗文传播至粤(37)。至乾隆六十年(1795),李婿张怀溎又将之拓展为《小仓选集》八卷,并收入李调元《函海》之中,以广其传(38)。 更为人称羡的是,袁枚著述早在其生前就已传播海外。弟子刘志鹏曾将“著作风行海外”与“女弟子络绎盈门”视为袁枚生平最可惊羡之二事: 先生事事超绝,而鹏所最惊且羡者有二焉:《小仓山房全集》风行海外,日本、安南、高丽诸国,都以重价来购。价愈增,买愈众,甚至有偷窃攫夺者。每一书出,三省开雕,及于其身亲见之,此从古文人所未有也。女弟子二十馀人……又从古文人所未有也。(39) 按据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考订,早在日本宽政三年(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随园诗话》就已传入日本。宽政六年(乾隆五十九年,1794)有《小仓山房》十五部传入,疑即《小仓山房全集》之谓。至宽政十年(嘉庆三年,1798)则《小仓山房尺牍》、《小仓山房文钞》亦相继传入。而至文化元年(清嘉庆九年,1804),则出现了《随园诗话》的和刻本(40)。今日本犹多见袁枚著述之翻刻本,其当年之影响亦可见一斑(41)。 袁枚著述传入韩国的时间亦大致相近。袁枚曾提及“高丽进士李承熏、孝廉李喜明、秀才洪大荣等,俱在都中购《随园集》,问余起居、年齿甚殷”(42),又称“高丽国史臣朴齐家以重价购《小仓山房集》及刘霞裳诗,竟不可得,怏怏而去”(43)。按据张伯伟先生考订,李承熏、洪大荣、朴齐家诸人之燕行文献中,皆未及袁枚著述,故疑此传闻可能有误(44)。李、洪二人姑不论,于朴齐家,既云“竟不可得”,则未见记载亦属平常。而与朴齐家同时入燕的李德懋,其《清脾录》中已提及袁枚“年今七十馀”(45),则朴齐家知晓袁枚其人其书,亦不足为奇。此外,同时人崔龙见曾作《读简斋先生小仓山房集偶成二律》,其一有“名享千秋海外闻”句,末注“高丽使臣朴齐家以重价购《全集》”,亦可为一佐证(46)。按此诗其二有“时先生粤游返棹”语,可知作于乾隆五十年(1785)袁枚游粤归来之际。时《随园诗话》尚未刊行,崔氏与袁枚又从未谋面,可知其获知此事,当以其时确有传闻,而非袁枚一人臆说(47)。 随园的刻书活动集中在袁枚晚年,尤以最后十年达到高峰。而这一阶段,也正是袁枚声名达到极盛的时期。这当然并非巧合,而是袁枚努力经营的结果。早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袁枚即曾致信好友程晋芳,谈及诗文刊刻之事: 记前年与足下约毋刊所作诗文,比来思之,此语终竟未是。岂不知学与年兼,深造可喜?古人文字,无自为开雕者。然彼此一时,正难泥论。……学者如牛毛,传者如麟角。先为之传,以待后人,可也。……文章者,吾之神明也,可不存哉?(48) 按袁枚之所以改变其“毋刊所作诗文”的想法,实因是年目睹胡天游殁后,其著述遭儿辈“拉杂摧烧”,不免虑及自身。其时袁枚甫至中年,膝下无子,文坛声名尚在显与未显之间。客观上说,十馀年后随园著述的刊行与传播,大大助推了袁枚的声名,而渐盛之声名反过来又促进了随园书籍的传播。 而细究袁枚著述出版与传播之全部过程,其中既存在复杂微妙的文本修订,又存在销售牟利等商业行为,此外还涉及多省翻刻、海外传播等诸多现象。对此加以厘清,不仅有助于了解袁枚盛名形成之背后原因,也为研究清中叶民间书籍的出版流通及运作机制提供了绝佳个案。 ①钱泳《履园丛话》卷八“谭诗·总论”,中华书局,1979年,页204—205。 ②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四第十八则,清乾隆嘉庆间随园增刻本。 ③袁枚《随园老人遗嘱》:“我一生著述,都已开雕。尚有《随园随笔》三十卷,正想付梓,而大病忽来,因而中止。他日汝二人行有馀力,分任刻之。”见《小仓山房文集》卷首,光绪十八年袁祖志刻本。 ④从《双柳轩诗文集》到《小仓山房诗文集》,删改之处极多,尤可见袁枚经营之苦心。具体可参陈师正宏《从单刻到别集:被粉饰的才子文本——〈双柳轩诗文集〉、〈袁枚全集〉校读札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⑤按《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四有《全集编成自题四绝句》,其一有“编成六十卷书开”,则在实际刊刻过程中当有编而未刊或卷数调整的情况存在。清乾隆嘉庆间随园增刻本。 ⑥见袁枚辑《续同人集·文类》卷二张凤孙《答简斋大兄书》,清随园刻本。 ⑦袁枚《随园家书》第六通,手稿本,藏国家图书馆。 ⑧其中《读史提要录》卷末有“广陵汤鸣岐镌”字样,可知汤氏系扬州刻工。见黄裳《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1992年,页254。 ⑨按乾隆刻《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子不语序》仅云:“书成,即以《子不语》三字名其篇。”至嘉庆间增刻本,此序则改为“书成,初名《子不语》,后见元人说部有雷同者,乃改为《新齐谐》”。 ⑩所谓“三十种”,即增《随园食单》以及从《袁家三妹合稿》中抽出的《素文女子遗稿》。 (11)即以清人集部著述为例,如茹纶常《容斋诗集》二十八卷分别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乾隆五十二年(1787)、嘉庆四年(1799)、嘉庆十三年(1808)数度增刻;又孙原湘《天真阁诗集》三十二卷,始刻于嘉庆五年(1800),然诗集编年却至道光八年(1828),可知亦为增刻之本。更为常见的,是分编小集以区分刊刻时间。如郭麐《灵芬馆诗》初、二、三、四集,法式善《存素堂诗》初、二、续集,皆属随编随刊之本。按上述诸例,得上海大学张寅彭教授主编之《乾嘉诗文名家丛刊》诸编者同道惠示良多,特此致谢。 (12)见杨芳灿辑《芙蓉山馆师友尺牍》第三通,收入《尺牍丛刻》,清宣统三年刻本。 (13)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六《与梁山舟侍讲》,清随园增刻本。 (14)具体可参拙作《从随园诗话早期家刻本看涉红史料真伪问题》,《红楼梦学刊》2013年第2期。此外,对《随园诗话》的版本问题,笔者拟另撰一文加以详述,此处不赘。 (15)见《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版本同前。 (16)见《小仓山房诗集》卷二《意有所得辄书数句》其四,版本同前。 (17)杨芳灿辑《芙蓉山馆师友尺牍》第三通,版本同前。 (18)具体可参拙作《袁枚佚札四通考述》,《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9)孙原湘《赠随园太史》其一夹注,见袁枚辑《续同人集·投赠类》,清随园刻本。 (20)赵翼《陔馀丛考·一金》:“今人行文以白金一两为一金,盖随世俗用银以两计,古人一金则非一两也。”《续修四库全书》第1151—1152册。 (21)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六第一条,版本同前。 (22)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八《覆徐小汀书》,版本同前。 (23)袁祖志《随园琐记》卷上“记著作”,光绪三年申报馆铅印本。 (24)袁逸《清代书籍价格考》,《编辑之友》1993年第4期。 (25)此处据袁枚后人袁建中女士所提供《袁随园纪游册》书影,特此致谢。另王英志先生《手抄本袁枚日记》曾予以整理校点,见《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4期。 (26)据周启荣《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推算,明末书籍刊刻成本大致在0.083两—0.1两之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又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三章《历AI写作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记载,明季刻工每百字得银四分,至乾隆间则增至八分至一钱,可知成本约上升2—2.5倍。 (27)分别见袁枚《随园家书》第六通、第十五通。 (28)据《袁太史稿》卷首袁鉴序,清乾隆五十一年袁鉴刻本。 (29)见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首洪锡豫序。 (30)见佚名辑《明清名人尺牍墨宝》卷一袁枚致鲍志道书,上海文明书局民国影印本。 (31)按袁枚为获《随园诗话》之刻资,尤费苦心,不惜采取迂回战术,与毕沅之妾周月尊相周旋。具体可参拙著《袁枚年谱新编》乾隆五十二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页535。 (32)见《随园手翰》袁枚致法式善书:“枚有《随园随笔》三十卷,继《容斋五笔》而作,以考据之学素性不喜,故奇中丞谋为代刻,枚力辞得免。”手稿本,藏国家图书馆。 (33)见《随园老人遗嘱》。 (34)袁祖志《随园琐记》卷上“记著作”。 (35)见《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三。此事又见《随园诗话补遗》卷三第十六则:“余刻《诗话》、《尺牍》二种,被人翻板,以一时风行,卖者得价故也。近闻又有翻刻《随园全集》者。” (36)见《随园诗话补遗》卷三第十六则。 (37)参李调元《童山文集》卷五《袁诗选序》、卷十《寄袁子才先生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56册。 (38)参张怀溎《小仓选集》卷首李调元序,收入《函海》第二十七函,清嘉庆间刻本。 (39)吴贻咏《福行简斋公传》,收入《慈溪竹江袁氏宗谱》卷十八“列传正编”,民国十二年惇叙堂木活字本。 (40)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200—201。袁枚著述对日本文坛的影响,亦可参见王英志《性灵派之袁、赵对日本诗坛的影响》,《江淮论坛》1997年第2期。 (41)复旦大学陈师正宏教授曾惠示其于日本书肆所购之《随园诗话》中国坊刻本一种,以及《牍外馀言》和刻本之书影(见藏于日本金泽市立图书馆)。此二书皆可见证随园著述海外传播之广,特此致谢。 (42)见《随园诗话补遗》卷六第一条。 (43)见《随园诗话补遗》卷四第七十条。 (44)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页141—144。 (45)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页143。 (46)袁枚《续同人集·投赠类》,清随园刻本。 (47)此外收入《八十寿言》之记载更多,以皆在《随园诗话》出版之后,故不赘录。 (48)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答程鱼门书》,清乾隆嘉庆间随园增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