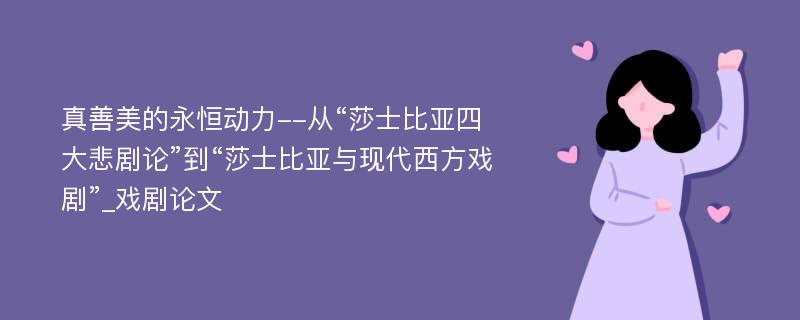
来自真善美的永恒动力——从《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到《莎士比亚与现代西方戏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真善美论文,戏剧论文,悲剧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家先生研究莎士比亚由来以久,在莎士比亚研究这块丰沃而被人耕耘过无数次的土地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中央戏剧学院莎士比亚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她就一直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在她的领导下,中央戏剧学院莎士比亚研究中心在培养人才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有重要的多方面的建树。因此也引起了国外莎学家和莎学组织的注意,受到了著名文学家、戏剧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曹禺先生的称赞,同时也得到了国内莎学同行的一致肯定。在孙家先生以毕生的精力所获得的丰硕莎研成果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和莎士比亚戏剧》、《莎士比亚辞典》〔1〕等著作, 还有《关于莎士比亚〈暴风雨〉的评价问题》、《莎士比亚喜剧和〈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令人回味的尝试》、《〈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的艺术手法》等几十篇结实而有份量的莎研论文。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中国研究莎士比亚,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不可不读孙家先生的莎学论著,也一定会知晓孙家琇先生的大名的。
198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1990年又第二次印刷,总印数已达6,000册。这个印数在我国论莎的专著中是相当高的。1994年她的另一部篇幅更大更为厚重凝聚着心血的莎研论著《莎士比亚与现代西方戏剧》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虽然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该书仅印了800册,但是一出版, 就引起了国内莎学同行的注意,一些著名莎学家也将该书介绍给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
《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莎士比亚与现代西方戏剧》(以下简称《悲剧》与《戏剧》)两部书中的有些篇章、观点,虽然过去作为论文刊物上发表过。但是这两部书并不是她的几十篇论莎文章的简单合集。而是溶她的论莎思想,体现出她的不断发展、深化的莎学观点,体现她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莎士比亚及其艺术洞幽烛微的分析,表现了她对真善美的莎士比亚世界的倾心挚爱,同时也是显示、勾勒她的学术历程的两部著作。
在这两部著作中孙先生通过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莎士比亚与现代西方戏剧关系,莎士比亚戏剧独特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和艺术手法的分析,试图解析莎士比亚世界丰富复杂的内涵,力图在理论上阐述一个中国学者的莎士比亚研究观,或者说一个中国人企图通过莎士比亚来认识世界,探寻西方文学艺术、戏剧的奥秘。甚至通过莎士比亚那“气冲斗牛”憾人心弦的精湛艺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点诚如作者自己所说,莎士比亚戏剧竟然成为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辅助教材,“莎剧中间所反映欧洲封建主义解体和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历史现实、社会家庭、人与人之间关系和思想意识等等的变化,极好地印证了马恩的理论,既促使我接受和坚信马恩学说,又使我似乎生平第一次看到了莎士比亚戏剧巨大深湛的社会性和思想性。”〔2〕反过来, 她又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莎学研究工作,“力求运用我所能理解的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和批判的原则,”〔3〕明白了任何伟大的作品都脱离不了时代的根源,它们都包含着具有历史意义以至普遍意义的思想内容。
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悲剧》和《戏剧》的第一个特点,那就是提供了一个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打开莎士比亚艺术世界风景线的成功范例,一个对莎士比亚戏剧全面而成熟的认识。既然认识、观点是中国化的,那么在梳理有关线索,介绍某些背景材料,特别是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对西方论莎观点提出不同的见解,寻找迥异于西方人的东方人观察莎士比亚的独特视角,以便从理论上对某些谬误甚多的西方莎学观点进行某种反拨,阐发中国人的莎士比亚观,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就又构成了两书的第二个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悲剧》和《戏剧》中均有《论〈哈姆雷特〉》这一节(篇)。可以想见,作者对这篇章是极为重视的。因为两部书中也仅有这一节(篇)是相同的。在这一部分里,作者首先从《哈姆雷特》与历史上同时代戏剧的比较入手,提出《哈姆雷特》同英国历史上的复仇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时过境迁,多少轰动一时的复仇剧成为“昨日黄花”,而《哈姆雷特》却长盛不衰,永葆艺术青春之魅力。这是为什么?孙先生认为关键在于莎士比亚进行创造。创造给复仇剧体裁注入了真正的生命,不仅把卖弄剧变成了大悲剧,而且使它获得了深刻的真实性和哲理性,成为具有重大典型意义的时代的镜子。
我们绝不否认西方的莎学工作者几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所取得的成果。但是他们的研究并非无懈可击。更有好事之徒以哗众取宠之心将研究引入歧路。西方的某些论者用一般复仇剧的尺码来衡量和解释《哈姆雷特》,说明他们无视《哈姆雷特》是怎样创造性地发展了复仇剧,已经与莎氏原来所本的复仇故事有了脱胎换骨的内质与外形,说明他们也不清楚什么是莎士比亚的“这一个”。为了弄清复仇剧和莎士比亚悲剧的区别,孙先生将莎剧与复仇剧进行了5 个方面的比较:即复仇剧里的鬼魂仅仅是一种标志或抽象名堂;莎剧里的鬼魂是惨遭杀害的人。在“戏中戏”的使用上,莎剧的“戏中戏”不是结尾而是高潮。复仇剧主人公往往不能迅速行动;而王子的延宕有远为复杂深刻的主客观原因。复仇剧作者写的仅仅是复仇情节剧;莎士比亚则要反映时代,褒贬善恶。起决定作用的还有,莎士比亚塑造了远非其他复仇英雄可以比拟的悲剧主人公。这样作者就令人信服的证明了莎氏悲剧和复仇剧的渊源关系以及高于复仇剧的方面。
孙先生还尤为注意《哈姆雷特》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历史。这正是作者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莎剧的一个极好证明。唯其如此,她绝非就历史论历史,而是从文艺复兴时期西欧、英国社会及社会心理的变化来认识、阐述哈姆雷特形象的典型意义。她的分析无不中肯的证明莎士比亚及是借哈姆雷特的忧郁,倾吐了人文主义者的失望甚至绝望,从而反映出当时人文主义思想的危机。关于哈姆雷特的艺术形象这一复杂而又众说纷纭的问题,作者认为关键在于哈姆雷特的多义性,不是有“有一千个人,就是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个说法吗。孙先生对哈姆雷特的性格与思想、理想主义和怀疑、忧郁、“人民性”、缺陷与弱点、拖延复仇等几个方面逐层加以剖析,引导读者充分领会哈姆雷特形象的思想内涵、人格魅力以及悲剧所表现出的政治性,主人公对世界的深刻感受、憎恶以及永恒的美的艺术魅力。
如果说对《哈姆雷特》偏重于思想主题分析,那么对于《奥瑟罗》一剧,《悲剧》一书从艺术分析入手,引领读者漫游于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空间。《戏剧》一书则在讨论伊阿古形象时刻意深化。同时,作者也旁搜远绍西方学者对《奥瑟罗》的评论,并在参稽互证中指出这些评论的优劣。鉴于《奥瑟罗》在四大悲剧中极富时代色彩的,而奥瑟罗本人则被认为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表现了莎翁关于爱情的思想”,那么莎士比亚塑造剧中人物之一苔丝德梦娜的艺术手法,就是以形象的真实体现感情的真挚,描写姣美的外形与呈现的心灵相一致,着力显示稀有的纯真爱情与热诚。孙先生认为莎士比亚塑造奥瑟罗这一人物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向人物的灵魂深处开掘;单纯高尚寓于复杂之中;在变动的过程中致力展示人物内心矛盾,造成情感的大幅度升降。我们看到作者虽然在《悲剧》中对伊阿古这个反面人物也做了详尽的分析,但是对伊阿古形象的实质、意义分析则更多地留给了《戏剧》。孙先生将其归纳为,莎士比亚刻画伊阿古最根本的用意,是要把恶棍玩弄“两面脸”手法,伪装好人的习性和本领,加以突出的深化,使其成为具有本质意义的典型。作者提请读者注意,莎氏所揭示的邪恶精神“伊阿古主义”的危险性和危害性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这乃是莎士比亚对于世界的一大贡献。
为了让读者对《奥瑟罗》一剧的评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悲剧》介绍了西方莎学家的观点,从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80年代。读者能从中窥到几百年来围绕这一问题争论的流变。肯定与否定,赞美与批判的声音并存,透过历史与现实纷纭的分歧足以说明这部悲剧的复杂。针对如此众多的评论,如此复杂的现象,如此长久引人注意的剧作,作者提出关键是避免“主观随意性”的评论,而那些抽象“人性”的标准,正是西方论者“极端随意性与主观性的根源和掩护。”而我们对《奥瑟罗》一剧的评论则应当站在能够阐明和揭示它的背景、意图、艺术成就和思想意义的基石上,这样才能有助于文学和戏剧艺术的发展。
当我们翻阅《戏剧》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对《李尔王》的评论,显然作者是把这一评论重点让给了《悲剧》。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学者越来越多认为《李尔王》是莎氏最伟大的悲剧。它规模巨大,气势宏伟,题材描写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对其评价之高,也大有超过《哈姆雷特》之势。但是早期的评价却不是这样的。孙先生在回顾其整个评论演变的历史时,特别举出托尔斯泰对《李尔王》的责难,指出由于观察角度和评论的立脚点不同,托氏不无偏颇之处。在作者眼里《李尔王》正体现了莎氏的精神和艺术更新的真谛。因为从剧中大量使人感悟到的是莎氏的勇气和崇高精神,即坚持“人”的理想、使命的信念。李尔王那憾动天地的狂暴与咆哮,实际上代表了莎氏及其千千万万人的愤怒与抗议,构成了英国现实的集中反映,人生善恶冲突的诗意幻象。至于有的论者提出莎氏对《李尔王》的情节结构重视不够,过于松散,缺少连贯,孙先生在全面考察时代、背景、人物、情节、构思、故事来源的情况下得出,该剧尽管存在一些缺点,但是说莎氏没有用心经营,则是毫无道理和缺乏根据的。如此结构和安排情节正体现了莎氏的良苦用心和有别于常人常事的独特艺术匠心,即“降低故事的重要性而运用强烈的场景;展延情节向纵深扩大;双重故事线索;‘不终止’的情节”。作者强调《李尔王》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在于,它是一出富有道德伦理和哲学意义的伟大悲剧。它通过主次双重故事反映时代生活的同时,也展示‘善’与‘恶’的实质。莎氏通过李尔王提出了人类命运、人生意义、价值观、社会不平等诸如此类带根本性的问题,那最富于艺术震撼力的悲剧氛围与情调,更赋予《李尔王》以浓重的现代意识色彩。
《麦克白斯》是四大悲剧中最后一部,也是最为独特的一部。虽然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难以与《哈姆雷特》、《李尔王》匹敌,但也雄踞于四大悲剧之中,是历来“罪行的悲剧”中一部有典型意义的作品。在《悲剧》和《戏剧》中各有两节(篇)谈到《麦克白斯》,从宏观与微观,人物形象与艺术风格,剧本到舞台演出进行了多方面论述。孙先生感慨《麦克白斯》中现实与幻想结合得如此巧妙感人!莎士比亚从来不用纯自然主义的手法,而是尽量用具体生动的细节来显示现实。作者通过具体分析令人信服地表明,麦克白斯的形象正是当时各种冒险家、野心家的艺术概括,是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产物。关于麦克白斯这个人物形象的悲剧性,作者联系诸家之说,认为:剧本主人公并不是超自然“命运”的牺牲品。麦克白斯不是一个“真正伟大美好的人”。莎氏揭露了麦克白斯的血腥罪行,尽管他的悲剧性格与沉沦令人同情,但是作为罪犯和暴君,他又使人憎恨。麦克白斯在生命结束以前,信念崩溃,精神死亡,这也是麦克白斯的命运比莎氏其他悲剧主人公来得更为悲惨的原因之一。孙先生以为《麦克白斯》艺术风格的总特征就在于展现了人与“超自然”、大自然相并存和人心异化,在于典型特征与诗意渲染的结合, 在于“离奇”与“狂放”的相交相融。 孙家琇先生一贯重视舞台上的莎剧演出实践,并多次指导中国莎剧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她认为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进修班和师资班的《麦克白斯》,抓住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运用中国戏曲表面幽默,骨子里尖刻的小丑形象也颇为成功。
《戏剧》除了以上两个特点之外,它的特点还在于比较全面的探讨了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其中包括生平、著作权问题,又有莎氏戏剧观问题,还有对悲剧、喜剧、历史剧演出形式,易卜生、斯特林堡、现代欧美戏剧与莎剧关系的研究。孙先生严肃批判了否定莎士比亚著作权和莎氏其人的谬论。她认为莎氏对戏剧总的见解就是强调戏剧是人生或时代的缩影。肯定《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莎氏早期爱情喜剧相比,所呈现的生活和社会背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应该“以时代来衡量剧中爱情的价值和悲惨结局的必然性”。孙先生认为“莎士比亚式喜剧”即不以讽刺为主,而首先是幽默抒情的,其中的浪漫主义激情、浓厚的生活气息、有趣的矛盾纠葛和活生生的人物是其成功的保证。《威尼斯商人》让人在轻松的喜剧中间看到了时代、生活环境与氛围。《第十二夜》则是“欢乐的喜剧”告别之作,它在无穷的嘻笑和奇想之中弹出了世纪转折时的忧伤情调。她认为《科利奥兰纳斯》长远普遍的意义在于使20世纪的人联想起世界大战,想起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至今阴魂不散。而享有莎士比亚第五大悲剧的《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是囊括历史剧、浪漫爱情剧和性格悲剧三种体裁特征的罗马戏。它突破传统常例、艺术综合、戏剧技巧上的创新、成熟,展示了莎士比亚所达到了创作水平。有更广泛地层面上探讨莎士比亚戏剧的特点,并以此为契机探索现代西方戏剧,特别是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的戏剧,使读者对西方戏剧艺术的发展能有一个总体的认识,这是《戏剧》的第三个特点。
面对纷繁复杂的西方莎学,孙先生始终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某些西方莎学的不合理之处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较之《悲剧》她的这一思想在《戏剧》中表现得更为系统和明确。由此,构成了《戏剧》的第四个特点。对于G.W.奈特赞美《暴风雨》中猎犬名称“富于音乐性”,猎犬充满对人有用、健康、非兽性雄浑体力的意义,孙先生认为西方论者忽视了《暴风雨》的历史典型意义。在对西方莎学的研究之中,孙先生还对诸如:不去区分凯列班形象的积极与消极方面、性格实质,大作形式主义、象征主义对比,“纯文艺”、“纯美学”论调提出批评。作者认为一些西方论者爱用一般复仇剧尺码来衡量和解释莎氏悲剧,是无视莎氏悲剧的深刻意义。“历史派”比“心理派”错误更大,从J.D.维尔逊,C.M.路维斯、L.舒克金到T.艾略特既无视莎氏《哈姆莱特》创造性发展了复仇剧,又弄不清到底什么是“莎士比亚”的东西。对于柯尔律治斥责《一报还一报》是可恨的作品;从基督教角度解释赞扬;急于表达公正、仁慈和性不道德;和现实政治挂上关系这些论点,在孙先生看来都是荒谬的。《一报还一报》的实质在于,它对社会、人性和人生之间错综关系的洞视与批判,针对的是黑暗社会反常的性欲、扭曲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观。从《戏剧》中所提到的西方莎学家和莎学观点看来(远不止本文所提到的),孙先生的论证是建立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上的,因而也是切合莎作实际的中肯之论。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既要有较强的理论光彩、严密的罗辑性,还应兼备一定的资料素质,以便读者能通过资料扩大阅读范围,了解学科进展,或深入钻研某一专题。资料性、参考性这一特点,在《悲剧》和《戏剧》的附录、注释中显得特别明显。《悲剧》一书将英国现代莎学专家肯尼斯·缪尔的关于《莎士比亚的材料来源》一书涉及四大悲剧的文章附后,使读者对四大悲剧的来龙去脉、争论焦点有了更为明晰的了解。在《戏剧》中有《致亲密剧院的公开信——斯特林堡以莎士比亚为师》,前苏联著名莎学家莫洛佐夫的莎学论文,英国理查·戴维德,G ·维尔逊·奈特,美国露比·寇恩等人论述莎士比亚与易卜生、肖伯纳、布莱希特关系的文章。这些资料给读者提供了大量信息,同时读者也可以借此来印证、检视孙先生的莎学观点。总之,由分述西方各种莎学理论到集中介绍,便于读者在接受各种莎学观点的同时,进行分析比较,以便做出自己的美学判断。这是作者为有志于深研的读者提供了一把钥匙。《悲剧》与《戏剧》是孙先生多年研究莎士比亚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莎学研究近年来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其间饱蕴着孙先生对莎士比亚真善美世界的理解。
注释:
〔1〕孙家琇:《莎士比亚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李伟民:《评孙家琇主编〈莎士比亚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1期。李伟民:《评〈莎士比亚辞典〉》, 《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1993年第4期。
〔2〕〔3〕孙家琇:《前言》,《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