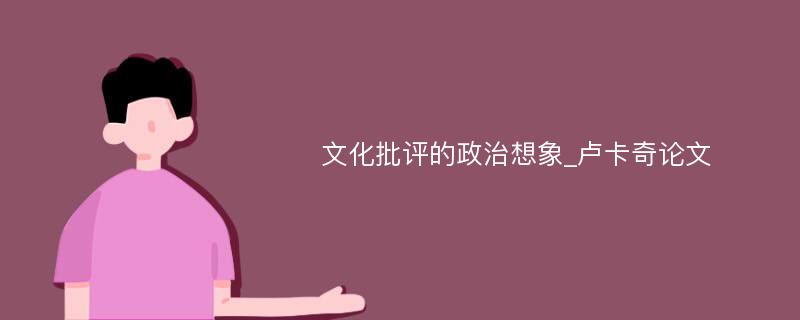
文化批评的政治想象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想象力论文,批评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4)09-0115-09 当我在百度上敲下“文化批评”这个词的时候,得到了1,350,000条结果;而搜索“cultural criticism”则有3,370,000条结果;如果把时间限定在一年内,则得到1,060,000条结果①。这不仅说明了文化批评在中国的热度,也充分证明了这种热度在最近的时间里面保持了上升的趋势。有趣的是,电视台也曾经推出“文化批评脱口秀”,甚至周立波的“清口”,也曾经被人们称之为“文化批评”,可见人们是如何乐见一种尖锐而犀利的对社会问题和艺术文化的批评。 学术界的情况如何呢?根据知网统计,以“文化批评”为主题词的研究文章,2011年为52篇,2012年为247篇,2013年则上升为299篇。2014年到目前的统计已经达到了149篇。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文化批评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加。 一方面,人们对“文化批评”寄予了热望,认为“1990年代市场化、世俗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兴盛,成为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出现的最重要的文化背景”②,也就是将文化批评看作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从而,能批判和剖析这一社会内在的意义生产和制作逻辑,并凸显特定的中国经验;另一方面,又将文化批评的崛起,看作是中国知识与西方知识的合理结合,并充满信心地认为,文化批评是“针对传统文学研究方式所进行的修正和补充”③。 不妨说,在文化批评热的背后,凸显出国人对当下生活进行阐释的强烈欲望和内在焦虑。也许我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批评”正处在一种狂热的时期,人们对于当下社会的不满,尤其是由于不知道对种种问题如何归因而滋生的对于现状的焦虑不安,会激发国人对“文化批评”寄予过高的期待。 这就牵连到文化批评的社会功能问题。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如果社会处在变动、转型、失范(Anomie)的时段,文化批评就会相对繁荣发展。就中国而言,文化批评这种文体的诞生和繁荣,本身就与近代中国的巨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梁启超以恢弘的气势撰写了大量文化批评文章,所评论和分析的现象几乎囊括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心理和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五四”运动前后,杂文随笔随着现代报刊媒介的崛起而大量出现,鲁迅的杂文作为特殊的文化批评文体,针砭时弊、嬉笑怒骂,让我们看到一个历史时代里面所蕴藏的复杂矛盾和冲突;而毛泽东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撰写的政论文章,更是将中国社会的阶级对立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甚至上个时期十年“文革”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与各种奇形怪状的文化批评——也包括姚文元等人“创造”的大批判文体,向我们证明了混乱时期文化批评的畸形繁荣状况;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批评”作为独立的学术概念传入中国以后④,它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通过文化批评的写作阐释中国、理解社会巨变和思考时代命题的功能。可以说,上个世纪90年代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文化批评的一次大爆发。 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复杂化,中国问题的特殊内涵也渐渐浮出水面。文化批评的历史使命和特定的文体意义,也应该被重新阐述。在我看来,如何发挥文化批评的批判力,重新认识并凸显当前文化批评的政治内涵,已经成为文化批评不得不面对的命题。 一、政治斗争与文化批评 在我看来,对于“文化批评”的理解,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化批评的理解,不能仅仅从这种文体的学术传承和理论谱系角度来完成,还应该将这种文体的意义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境遇紧密相关。 在德语中,Kulturkritik这个概念,“暗示着只有学究们才会去探讨的一些价值”,也就是一些所谓“不谙时政者”(unpolitical man)才会去探索的那些价值。⑤所以,从传统的文化批评的意义来看,文化批评是用来区分哪些是好的文化和不好的文化的;而有趣的是,沿着这一思路,文化批评却日益变成了与文化无关的批评。归根到底,文化批评并非关于文化的批评(criticism of culture),而很容易变成关于社会典章制度、精神意识和社会状况的批判。 而如果将文化批评仅仅限制在对于文化、审美的批评,同样也是一种“老学究的学问”。事实上,文化批评之滥觞,与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将政治领域的斗争转移到文化领域当中来的总体策略紧密相关。在这里,所谓“批判”,既是继承了康德的传统,致力于知识的判断和德行的分析,同时,更是充分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传统,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置换”为文化的批判。 事实上,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出现和社会体制的转型,令国家权力和资本的统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鼓吹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并没有及时到来,或者说并没有按照推翻一切压迫和剥削阶级的模式到来,而是被民族革命、反帝国主义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利益纷争所围困。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学者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性矛盾已经消失了: 自由民主国家的出现,各种工业仲裁形式的建立,包括法律上对罢工权利的正式承认,使工业领域的冲突得到了调解和控制。前者使政治领域中代表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正式组建成为可能,后者则使工业领域中的不同利益得到了类似的承认。由此形成的结果是,卸除了阶级冲突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并使19世纪相对激烈的阶级斗争让位于和平的政治竞争和工业谈判。⑥ 对于政治斗争的消失这种现象,虽然不同理论派别的学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的是,20世纪之后,尤其是50、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斗争形式不再是革命主导的,而是文化主导的。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法治的、秩序的社会,却隐含着意识形态的宏大的安抚工程。有人将这个工程称之为“同意工程学”(engineering of consent),它在公民中培养起“对现状的顺从”态度。⑦而教育、文化、艺术、宗教、法律等等领域,都参与这一宏大工程的“建设”。 显然,早期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人们来说,文化批评首先是一种新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形式。资本主义没有采取马克思所描绘的那种严峻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形式,而是采用了控制需要、生产欲望而博取利润的形式。在这里,现实的被剥削和压迫的状况,被文化(商品拜物教主导下的文化)所生产出来的幻境所掩盖,从而为文化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历史背景:所谓“文化批评”,不是因为文化而发生的批评,而是因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形式的批评,是被大众媒介所推动而成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之后的文化的批评。 卢卡奇这样描述了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文化逻辑: 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现象上的拜物教假象成功地掩盖了现实,而且被掩盖的不仅是现象的历史的,即过渡的、暂时的性质。这种掩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环境,尤其是经济范畴,以对象性形式直接地和必然的呈现在他的面前,对象性形式掩盖和它们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这一事实。它们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关系。⑧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批评的崛起,乃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斗争的方式,是应对资本主义物化逻辑下文化幻象生产的新的策略。只有充分认识到文化批评并不是轻飘飘的关于文化和艺术的分析,归根到底是关于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机制的批评,是如何让大多数人无法面对自身真实的处境和境遇的政治批评。 所以,文化批评,连同文化研究,之所以日益成为“关于日常生活”的学问,正是因为这种“学问”的目的并不是为生活生产意义,而是通过意义的阐释而解放生活;不是通过文化来鉴别阿诺德意义上的好坏文化⑨,而是通过文化的分析和批判,“导致”对生活真实的重构。 在这里,日常生活的批判乃是文化批评政治批评的基本原则。从马克思、韦伯到卢卡奇等人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社会、统治模式和文化逻辑的批判,都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权力不是通过警察和军队来实现,而是通过修改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欲望来实现。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确立了斗争的、对立的,即矛盾地认识和改造历史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价值在于,它总是以一种辩证性的方式敞开被历史遮蔽的生活处境——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生活的基本秘密乃在于,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总是被另一部分人压迫、剥削,而各种各样的历史哲学及其附属品都在掩盖这个秘密。而与这个秘密相对立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机制下掩盖这一秘密的“巧妙的形式”。 于是,如何理解和发现,或者说重构“真实”,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体验和感受的问题,而必须是一种超越经验、体验和感受的问题。总之,批评不再建构对世界的体系化的解释,而是置身于具体的历史境遇之中,致力于对现实问题的揭示和阐释,致力于在历史世界中搅动革命的波澜。这正是20世纪以来运行于大众媒介之上的文化批评所确立起来的品格。在这里,批判的形式致力于“文化”,这才是文化批评的主旨所在——而不是人们习惯性认为的,文化批评是运用文化理论进行的批评。正是现代资本主义运用文化来组织其社会管制和体制认同,文化批评才会纠缠于文化领域的批判与解析。简言之,文化批评的文体自觉,恰恰是建立对现代社会叙事危机的充分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 二、文化批评的想象力 文化批评必须重建社会真实,这意味着社会真实并不是直接诉至于我们眼前。对于“真实”的遮蔽,已经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现代社会的文化工程,而对于“真实”的去蔽,自然也要借助于特定的途径和模式。也许“真实”并不是呈现出来的,而是“计算”(workout)出来的;并不是表达出来的,而是暴露出来的;并不是可以反映的,而是可以折射的。 简单说,文化批评必须具备这样一种能力:除非可以想象一个时代的基本社会图景,否则就无法建构理解具体的文化问题;任何单个的文化问题,都是想象整个时代和历史的特定入口。 这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批评的想象力”问题。 美国学者米尔斯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应该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认为“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之间的联系。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在应用社会想象力的背后,总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⑩ 有意思的是,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突出强调的是一种“心智品质”,其功能就是可以“戏剧性”地让个人现实与更大的现实关联在一起。(11)米尔斯难以回答这种心智品质如何获得的问题,就只好简单地说这种想象力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即一个人可以通过个人来想象(转到)他人、通过政治学来想象(转到)心理学、通过简单的家庭考察想象(转到)国家预算的评估,也就是“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之间的联系。”(12)这种社会学想象力的方式,说到底乃是一种基于个人思维和学术视野的能力;而“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个概念本身,也蕴含了对于想象力的学理限制:即想象力是一种与科学观念和意识相对立的能力,它本不应该出现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生活的基本处境,也有必要倡导这一种非科学的方法或者说形式。(13) 事实上,米尔斯不愿意承认的一个问题乃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必须首先是一种政治想象力,否则就只能是神秘主义的胡思乱想;简单地说,只有首先保证想象力乃是建立在对当下社会现实基本矛盾、困境和冲突——即首先充分理解资本体制所规定的基本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才能建构起对“真实”的完整想象。 换言之,只有在马克思和卢卡奇的意义上理解现代资本时代所带给人类社会和生活的根本性问题,才能具备社会想象的能力。米尔斯不愿意承认想象力的政治性,只愿意承认想象力的学术性;而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派的语言来说,如果不具备总体性的意识,也就不会具备想象一个时代的能力。 在这里,真实地想象一个时代,也就是在“总体性意识”的支配下对于一个时代不可见的支配性矛盾的建构和发掘。而所谓“总体性意识”,归根到底乃是抽象地理解现实所生成的那种自我意识——在资本主义时代,这种自我意识,只有构成典型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意识)的时候,才能达到对现实的真实意识。 这也就回到了文化批评的政治命题上来了。那种尝试建构一种普适性的文化批评的理想是非常渺小的,因为这种批评只能在强调道德、信仰、灵魂和精神的层面上变成用“阿门”来结尾的说教。换句话说,文化批评只有当其具备了改变世界的政治理想的时刻,才会具备分析世界的内在能力;而其只有能够深入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和政治矛盾的内部的时候,才能有资格讨论文化的危机和症候。 这也正是卢卡奇所呈现出来的“总体性”、“辩证法”和“阶级意识”三个概念的内在一致现象。卢卡奇把科学性(真实性)和革命性(阶级意识)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卢卡奇那里,资本主义呈现出整个社会体制管理的更加合理化和秩序化(韦伯的理性化理论直接影响了卢卡奇对资本主义外在现象的理解);而这种理性化,恰恰呈现为人类生活的内在物化。在资本主义的时代,人们失去了不按照理性化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也就是说,人们没有任何可能性逃脱物化体系的自我意识和认识困境。由此,“真实”变成了符合物化的现实体感的后果,越是所谓真实的,就往往越是建立在虚假的经验和理解的基础之上,成为人们“理所当然”认为的“真实”。这就使得作为经验的“真实”,日益陷入“常识”的围困之中,而“常识”也就成了不证自明不可追问的理解世界的起点。这恰恰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症候:将日常生活的知识作为恒久的具有历史和人类价值的知识来使用,从而彻底隔绝“历史—当下—未来”的关联。一旦未来视角消失,乌托邦政治在常识知识系统面前变成虚无缥缈的可笑故事的时候,“解放”也就变成了值得同情的“革命歇斯底里症”患者的口头语了。所以,卢卡奇所强调的“真实”,就不是静如湖水的常识真实,而是波澜起伏、勾连着革命、解放和未来欲望的现实经验的再发现和再阐释的历史意识。在这样的意义上,卢卡奇始终坚持真实性必须建立在自我意识从物化的逻辑中解放出来的前提;而艺术的真实,必然同时是一种意识到总体资本主义图景的令人沮丧的那一面的真实认识。所以,在卢卡奇的理论中,革命性(阶级意识)与科学性(真实性)从来就不是两个可以分开的问题。只有通过革命性的理解,真实性才能呈现出来。这也就构成了卢卡奇的总体性原则。 要实现这一目的,文化批评总是要面对一个个单独的事件,而也总是能够透过每一个事件的不同细节,把一个文本置放在更加宏大的总体的历史进程当中去,以此来凸现文本中原本被压抑、被隐藏的、看不到的东西。在前几年的一次“五·一”节期间,天津卫视组织了四位嘉宾就“高薪还自由”一题进行辩论。论辩期间,我的对手举证广告歌曲MTV《多好啊》来证明现代人应该更多地享受自由和自然,而不应该过度地投入加班加点的工作。有趣的是,这个MTV的内容仅仅在表面上支持举证者的观点,却在文化批评的总体性上丧失了其本身的合理性。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家庭的人员,坐车到郊外野餐、假日里面给孩子买气球、夫妻两个相拥打车回家等等场景;阳光、森林、田野和天伦之乐,构成了这个MTV浪漫温馨的情调。有趣的是,一旦将这个MTV置放到中国社会面临的双重叙事危机的总体性图景中,其内部的含义就发生了逆转:阐释者在解读“多好啊”这个主题的时候,忘记了其中“不好”的元素——出租汽车司机、卖气球的人、公共汽车司机,野餐的草坪上那些没有出现的打扫卫生的人、整理草坪的人、公路上那些铺路、修路的人;大家突然就明白了,原来浪漫的“多好啊”里面隐含了多少的“不好”,才能塑造一个阶层的人们的“多好”,而这些“不好”总是不被意识到,我们也就总是被“多好”的场景所征服。显然,从单个的文本里面找到单个的细节的感情,而不把它放在一个总体的资本体制贫富分化的框架里面的话,这个MTV是非常美好的,其感染力是非常强大的;而一旦文化批评调动了总体性的想象去观察里面的场景的时候,就立刻造成了现实世界的戏剧性的颠覆。在这里,如果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的思想,也就必然丧失对这个本文所掩盖的社会真实的发现和阐释。 不妨说,文化批评要想建构和想象一个时代的“真实”,就必须首先确立基本的政治理想,即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理想;而只有具备了观察世界的基本矛盾的欲望的时候,文化批评的想象力才能被解放出来。 这就使得米尔斯所说的“想象力”由技术性和学理性的概念,变成了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概念。在这里,米尔斯对于一个时代的想象力,一旦置换为卢卡奇的“总体性”的时候,也就是一种学究式的文化批评转换成了行动者的文化批评;而一旦行动者的文化批评成为可能的时候,学究式文化批评的意义才能够真正被释放出来。 在我看来,文化的批评,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批判,乃是建立在充满解放意识的对于真实性的再把握的基础之上的。作为一种“批判”,它体现为必须把任何单独的文本,镶嵌到社会的总体性视野中才能凸显其意义的文本。这事实上为文化批评的政治品格和批判原则提供了基础。毋宁说,在今天文化消费主义的时代,艺术的真实已经被现实意识形态的总体虚假生产体系暗中操控,不再成为有自我澄明能力的历史叙事;而只有借助于艺术文化的批评,才能通过对艺术文本的重组实现对现实真实处境的“重讲”和“拯救”。 说到底,文化批评的想象力,乃是一种“批判的想象力”,即坚持用想象未来的乌托邦主义视野发现当下矛盾和困境,并通过坚守对当下困境和矛盾的开掘,致力于建构更好的未来的能力。 简言之,如果不能想象未来,也就无法发现现实的困境和内在的矛盾,从而也就无法建构真实,这正是文化批评的宿命。 三、文化批评的“批判” 文化批评,也可以叫做文化批判。但是,如果强调文化批评的政治想象力,不妨将文化批评的批判性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来使用。 “批判”既是文化批评的效果,也是文化批评的基础。也就是说,只有具备想象未来的能力,才会有批判的意识;而只有充分认识到当下社会的种种矛盾困境,才能建构批判的冲动;而只有坚守对于当下矛盾困境的政治想象,才能实现批判的使命。 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化批评的批判就不能仅仅是愤懑、怨咒、辱骂和角斗,也不应该陷入谴责、对抗、纠缠和解构,而是一种充满了对未来的召唤的批判,是一种努力从当下的社会问题发现蕴含着导向更好的未来的愿望,从而最终是一种暴露生活的根本性危机、理解社会发展的核心阻力和揭示新的可能性的批判。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文化批评的批判就必须建立在这样几种基本的想象力的基础之上:将一个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作为“寓言”或者说“症候”来使用的想象力,不妨称之为“辩证意象的想象力”;能够在简单的事物中发现复杂的社会运转过程的想象力,也就是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最终,要具备抽象而简明地建构关于历史发展“神话”的想象力,命名为“乌托邦的想象力”好了。 对于辩证意象的想象力来说,文化批评应该同此前普通的社会批判和审美批评划清界限。文化批评致力于在文化艺术乃至社会现象间,发现内在的历史叙事危机,凭借强大的想象力,将一个简明的意象叙述为蕴含着矛盾和对立的冲突性意象。正如本雅明引用波德莱尔的话所说的那样:“一切对我都成为寓言”。(14)在这样的寓言中,一切可能性里面蕴含着颠覆和摧毁,在丝绒的光滑里,可以看到对于破碎的过去的留恋,在玻璃的透明中隐含着崩坏时刻的坍塌。本雅明这样说明这种意象的特点:“暧昧是辩证法的意象表现,是停顿时刻的辩证法法则。这种停顿是乌托邦,是辩证的意象,因此是梦幻意象。商品本身提供了这种意象:物品成了膜拜对象;拱廊也提供了这种意象:拱廊既是房子,又是街巷;妓女也提供了这种意象:卖主和商品集于一身。”(15)在本雅明那里,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生产逻辑就蕴含着意象的想象力:商品通过新奇诉之于其消费者,而商品不过是且总是陈旧的剥夺的形式。于是,本雅明有能力,通过巴黎林荫大道的建设想象对于革命者的警惕,在闲逛者那里想象知识分子寻找出卖自己机会的猥琐,也在辉煌的世界博览会中看到了特制品的统治力。甚至资产阶级的主人意识,统治一切的思想,本雅明也是在城市的“痕迹”这种意象中来想象和解读:“他们乐于不断地接受自己作为物品主人的印象。他们为拖鞋、怀表、毯子、雨伞等设计了罩子和容器。他们明显地偏爱天鹅绒和长绒线,用它们来保存所有触摸的痕迹”。(16) 显然,辩证意象的想象力,说到底乃是能够在当下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间解读造就这种现象的各种力量的能力。这种想象力令一个简约的文本,变成了具有寓言内涵的文本,令日常生活具备言说历史故事的能力——简言之,并不是任何对于当下历史的言说都是关于现实的,只有富有这种想象力的对当下历史的言说才能“构造”现实的历史。(17)因此,辩证意象的想象力,就是通过建构“琐碎”的文化地图来建立关于历史真相的惊鸿一瞥的能力。在这里,“每一个人、每一个物、每一种关系都可能表示任意一个其他的意义”(18),一个文化批评的学者,也应该像本雅明所说的寓言作者那样,在所面对的对象中建立一种可以通向“隐藏的知识领域的钥匙”(19)。 在这里,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本雅明的辩证意象的创造,也就变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辩证地想象一个意象的意义,也就是在单个的意象中发现历史,令社会变成寓言,即在日常生活的变迁中,发现主导性的社会权力的存在。 问题在于,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所匮乏的乃是一种政治批判的勇气和能力。于是,在他看来,社会的种种困境乃是可以通过技术调节来去除的困境。比如他提出社会维持平衡的两种形式乃是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一方面人们要自我驯服,成为社会化的人,另一方面,也要存在社会控制系统,规范和强迫人们的行为。(20)这样,在米尔斯的理论中,社会学的意义就在于发现并找到维持这种平衡的基本结构条件。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遭遇到了失业的困境,那只不过是个人生活的困扰,只有当大多数人失业的时候,才需要思考经济和政治制度问题。(21)这事实上等于去除了个人生命经验与米尔斯所倡导的时代环境的勾连的能力。在这里,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只肯承认公共性论题的价值,而不愿意从抽象的层面上来反思一种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本身的结构性困境。这种数字型管理的社会,所追求不是建立在基本公平基础上的社会,而是建立在基本平衡的基础上的社会。 显然,辩证意象的想象力与社会学的想象力,都必须依托乌托邦的想象力。对于米尔斯来说,想象力只能止于从个体中发现全体,在论题中找到问题,而无法从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的层面上想象未来。所谓文化批评的乌托邦的想象力,也就是一种敢于想象未来的能力,“即认为未来有可能优于现在的一种信念”(22),这正是文化批评所需要秉承的基本的批判精神。在一个消费主义不断塑造神话来闪烁人们的认识、构造虚假经验的时代,对于当下社会的批判必须建立在对于未来社会的合理想象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只有具备富有政治批判性的乌托邦,才能令自己对当下社会的批判具有政治力度;反之,一旦匮乏对于未来的想象力,也就只能在当下的话题中转转呼啦圈,导致花样百出的循环论证。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文化批评必须承担建构未来的使命;但是,文化批评终究不是为了回答当前中国电影的艺术风格或者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格局的批评。文化批评乃用文化观察和分析的方式,凸显陷入到文化领域中的权力制衡力量的状况,又能够在大胆想象未来的勇气中分析和思考社会问题困境。 也正是在这里,文化批评的批判,在技术上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在方式上是辩证意象的想象力,而在批判的原则上,或者说在其根本性的历史品格上是乌托邦的想象力。 四、失范的时代与文化批评的未来 有学者这样描述我们所处其中的时代: 人自身对于创造一种“属于人类自身的生活”已经没有了信心。他们宁愿把自己托付给无聊、沉沦与堕落:无论是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还是左派,如今都不再、也没有能力梦想一个迥异于现在,而且远较现在优越、完美、自由、幸福的未来。 说的更严重些,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已经丧失了想象未来的能力。不,这样说还不够准确!毋宁说,人类已经丧失了想象力本身!没有想象力,自然也就没有洞察力,这两者的丧失,恰恰证明了人类自身的迷惘、困惑与沉沦。畏畏缩缩的人类,搔首弄姿地向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实利主义谄媚,同它们调情,像个淫荡的妇人周旋于功利与物质的胯下。(23) 尽管作者使用了诗性的语言夸张地描绘了想象力的丧失这个话题,却也很精准地将当下人们的精神和生活的基本症候暴露了出来:因为被琐碎而强大的功利和物质的欲望围困,人们丧失想象未来的能力。 事实上,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结构性的功能就是令人们丧失想象另一种生活的能力。在资本统治的时代,人们不是通过满足他人的欲望而获利,而是通过控制资本流通的方式,来控制人们的欲望。垄断让人们只能接受高出成本许多倍的价格来购买必需品;标准化生产让人们丧失想象另一种生活需要的能力。 就当前中国而言,这种资本机制的困境和社会主义想象未来能力的消失,共同造就了一个“失范”(Anomie)的时代。 在这里,所谓“失范”,首先是涂尔干意义上规范和传统被破坏,而新的规范和传统尚未建立起来的那种混乱和失衡的状况。“在社会生活的某一特定领域,如果没有明确的标准指导人们的行为,失范就会出现”。(24)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社会叙事在日常生活层面上讲述其规范的合理性,而社会主义的社会叙事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构造其规范的合法性。合理与合法的内在矛盾不仅仅构造了《秋菊打官司》(1992)中现代社会转型的痛苦,也构造了当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双重危机。(25)在这里,失范指的是规范在位而无所从。 有趣的是,中国的文化危机还存在于涂尔干思想的修正者默顿的描述中。默顿认为,当社会的宏大叙事所允诺的东西是虚假的,不可能在现实层面成功的时候,失范也就出现了。(26)正如电影《老男孩》(2010)所呈现的那样,“80后”在童年时期接受了美丽的王子与公主的教育,却在成年后面对残酷的丛林规则的社会,这种巨大的反差正是失范发生的关键性根源。 显然,中国的所谓“失范”,正是在丧失了想象未来能力的时刻,又丧失了理解社会总体内涵的想象力的时刻。其导致的结果就是从普通人到学者,往往会陷入不知所措而又不得不立刻行动的窘境之中。米尔斯说:“当人们珍视某些价值而尚未感到它们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体会到幸福;而当他们感到所珍视的价值确实被威胁时,他们便产生危机感——或是成为个人困扰,或是成为公众论题。如果所有这些价值似乎都受到了威胁,他们会感到恐慌,感到厄运当头。但是,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珍视什么价值,也未感到什么威胁,这就是一种漠然的状态,如果对所有价值皆如此,则他们将变得麻木不仁。又如果,最终,他们不知什么是其珍视的价值,但却仍明显地觉察到威胁?那就是一种不安、焦虑的体验,如其具有相当的总体性,则会导致完全难以言明的心神不安。”(27)在这里,这个时代所具有的冷漠和麻木不仁,乃是与这个时代的价值失衡和规范失范紧密相关的。于是,“我们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但尚未以合适方式表述明确,以使理性和感受力发挥作用。人们往往只是感到处于困境,有说不清楚的焦虑,却不知用——根据价值和威胁来定义的——困扰来形容它;人们往往只是沮丧地觉得似乎一切都有点不对劲,但不能把它表达为明确的论题。”(28) 不妨说,这段批评,恰恰可以看做是对当下中国文化批评丧失政治想象力的状况的一种批评:文化批评被看做是建构公共领域的核心形式,我们却发现公共领域的文化批评变成了道德批评或者贴身肉搏;文化批评被当做是文学艺术新批评的形式,却事实上强化了文化批评的学院化色彩,令其变成了学究式的价值表述。 简言之,中国文化批评的病症,作为政治想象力丧失的后果,乃是将文化批评变成了失范时代想象性地克服生活焦虑的代用品,却无力将其作为未来生活的召唤者。 在这里,文化批评经常性地弱化为琐碎的道德批评——如梁文道在其《关键词》中分析“炫富”时所做的那样:“我们国家这批炫富者其实就是一群很没有自信心的可怜人”,(29)这种看法只能止步于从道德修养层面来理解“炫富”,没有能力想象炫富乃是权钱私通所“圈养”出来的一种权力私通者的能力证明;或者,文化批评被当做是一种不同文化派别之间的战斗形式——肖鹰生动地用一连串判断句宣告韩寒的无价值,(30)却没有能力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创造了韩寒这种“无价值的价值”;而文化批评想象力的缺失,也可以体现为没有能力阐释当下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复杂隐喻,只能从画面和文字的直接意义来讲述意义,这种过度依赖体验和感官的批评,更是想象力匮乏的表征——正如陈林侠专文批评《天注定》(2013)这部电影时所看到的那样,作者天才般地想象了这个电影生产机制过程中的资本媾和,却令人吃惊地看不到作品所呈现的底层暴力背后对压制性机制的绝望和麻木。(31)看到鲜血就骂暴力,这正是文化批评的政治想象力逐渐被街头骂架的想象力所替代的有趣后果。 总而言之,文化批评的政治想象力,并不是简单的政治批判,也不是不得要领的道德谴责,更不能成为立场鲜明而匮乏辩证意象能力的学究式拷问。在我看来,当前中国文化批评乃是失范时代焦虑症患者的医疗代用品,也是建构未来的关于危机的预言家。总之,文化批评的未来与中国社会的未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注释: ①http://www.baidu.com/s? q1=&q2=%CE%C4%BB%AF%C5%FA%C6%C0&q3=&q4=&rm=100&lm=360&ct=0&ft=&q5=&q6=&tn=baiduadv,搜索时间为2014年7月13日。 ②陶东风、徐盛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③王晓路:《文化批评:为何与何为》,《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④一般认为,“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这个概念是由雅克·巴曾(Jacques Barzun)在1934年说明的,大约由布莱克(Casey Nelson Blake)于上个世纪90年代作为术语被使用。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想和后殖民理论传入中国后,文化批评这个词也就频频出现,并逐渐形成影响。相关资料参考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Cultural_critic)、王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⑤[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局2000年版,第13—14页。 ⑥⑦[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批判的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2页。引文为吉登斯总结的达伦多夫的观点。 ⑧[匈]捷尔吉·卢卡奇:《卢卡奇文选》,李鹏程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⑨相对来说,阿诺德文化理论同样认可文化谋取真实的意义。他这样说:“现在恰是文化起作用的时刻了。文化之信仰,是让天道和神的意旨通行天下,是完美。文化即探讨、追寻完美,既然时世已不再顽梗不化地抵挡新鲜事物,那文化所传播的思想也就不再因其新而不为人所接受了。一旦如此领悟文化,即认识到文化不仅致力于看清事物本相、获得关于普遍秩序的知识,而这种秩序似乎就包含在世道中,是人生的目标,且顺之者昌,逆之者哀——总之是学习神之道——我说了,一旦认清文化并非只是努力地认识和学习神之道,并且还要努力付诸实践,使之通行天下,那么文化之道德的、社会的、慈善的品格就显现出来了。”“人类是个整体,人性中的同情不允许一位成员对其他成员无动于衷,或者脱离他人,独享完美之乐;正因如此,必须普范地发扬光大人性,才合乎文化所构想的完美理念。”[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10页。 ⑩(11)(12)(13)(20)(21)(28)[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14、5—6、15、33—34、7、9—10页。 (14)(15)(16)[德]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2、45页。 (17)历史的亲历,不等于有能力“进入”历史。在电影《斗牛》(2009年)中,主人公虽然“身陷”抗战的历史之中,却又无法理解和阐释这段历史,从而并没有“人在其中”。一方面是自顾自的历史(荷兰奶牛的反法西斯故事),另一方面则是个人无法逾越的记忆鸿沟(当下生命经验的局限性)。在这部电影中,“红色记忆”被撕裂为一种非连续性的“突发事件”,而个人的亲历性故事则保持着完整的形态。于是,作为功能性记忆形式的“红色记忆”,其连续性历史的宏大诉说能力遭到空前的质疑,而“私人”,作为记忆主体,被赋予了极大的功能性记忆的地位。在这里,对于革命时代的历史记忆,“重建记忆主体”乃成为20世纪历史重写的一种集体行动。简言之,只有借助于想象性记忆,才能完成亲历性记忆。参考周志强《身体狂想与想象性记忆的建构——以萧峰为个案》,载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8)(19)[德]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222页。 (22)[美]拉塞尔·雅阁比:《乌托邦之死》,姚建彬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3)姚建彬:《乌托邦之死·译后记》,载[美]拉塞尔·雅阁比《乌托邦之死》,姚建彬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24)(26)[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198页。 (25)详见周志强《景观化的中国》,《文艺研究》2011年第4期。 (27)[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10页。米尔斯区分了“论题”和“困扰”,在他看来,“困扰”仅仅是个人生活的偶然遭遇,而“论题”则是“困扰”达到了一定基数之后,成为牵连到社会基本制度的各种困境,并因此备受公众关注的话题。 (29)梁文道:《关键词》,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30)肖鹰:《“天才韩寒”是当代文坛的最大丑闻——〈后会无期〉与韩寒现象》,《中国青年报》2014年8月19日。 (31)陈林侠:《〈天注定〉:走向偏激的“底层发声”》,《社会观察》2014年第8期。标签:卢卡奇论文; 米尔斯论文; 想象力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社会学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