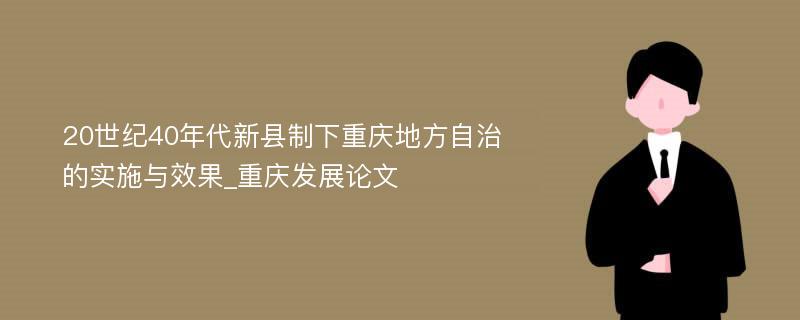
20世纪40年代新县制下重庆地方自治的推行及其成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县论文,重庆论文,成效论文,年代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3.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0)06—0094—08
地方自治是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所实行的规模宏大的社会政治运动。20世纪40年代,新县制下的地方自治政策,主张以保甲制度来推进地方自治,强调建立地方各级“民意机构”,试图在加强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同时,发挥“民意机构”的作用,以发展地方事业,维护自身统治。新县制下重庆市地方自治的推行具有代表性,通过考察其实际推行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从社会基层的角度来认识国民政府统治崩溃的部分原因。
一 重庆市为推行新县制下地方自治所作的努力
为了进一步改进保甲制度,确立新县制的基础,重庆市于1939年12月22日,成立了“保甲设计委员会”,公布了该会的组织简则及办事细则。1940年1月12日所填的该会委员的简历表显示, 该会的成员可谓学历高且“年富力强”。重庆市保甲设计委员会由23人组成。除2 人中学毕业,1人商业学校毕业,1人不详外,其余皆为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曾留学美日英法苏联者达10人之多,占43.5%。其年龄多在30—45岁之间[1]。
重庆市保甲设计委员会会同其他自治研究机构,根据重庆市颁布的“改进保甲,养成人民自治实施程序”等法案,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推行保甲制度的具体议案,包括《充实各级保甲机关人事案》,《订定区署、镇公所办事细则案》,《重庆市各镇镇公所办事细则》,《订定区镇保甲职员任用办法案》,《召开保民大会案》,《保障保甲人员工作地位案》,《举办现任保甲职员甄别考试案》,《区镇长应定期视察保甲案》,《改善保甲人员经办征募款项案》等等[2]。
重庆市的有关保甲法案使保甲制度不仅局限于编制,而且深入到人事、办事细则、民意机构等各具体方面。一方面,规定以警察机构作为区镇行政及自治的领导机关,严格保甲人员的考试任用制度,加强区镇长对保甲的指导监督等,均体现了上层加强对基层控制的意图。另一方面,重视保甲的地位,发挥保民大会对保甲的监督作用,禁止非公益的征募等,均体现了发挥地方基层民意的初衷。
重庆市还成立了多个自治协会组织,指导推进该市地方自治的实施。这其中包括1941年5月12日成立的“自治法规研究委员会”, 该会的任务为“研究关于市自治法规各种问题并负建议考察之责,所有研究结果应于五个月内制成方案,将省市施行新县制异同之点明确列出送市参议会咨请市政府转呈中央采择施行”[3]。
根据重庆市临时参政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成立的“重庆市地方自治促成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自治协会组织。该会由市参议会聘请中央及本市对于地方自治素有研究之人士45人组成,其中包括翁文灏、胡子昂、甘乃光、郭沫若、张澜等名人。该会制订的《重庆市地方自治方案》于1940年5月2日通过。该方案要求“明白规定重庆市为地方自治模范区”;将地方各级组织,“全予实现,此项限期,愈短愈佳,最迟不能超过三年;要求中央补助重庆市的自治经费;要求加强地方自治人员的训练;要求迅即召开保民大会”[4]等等。
此外,1943年11月还成立了重庆市地方自治协进会。“该会之建议均送请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转请政府采择施行”[5]。
各种自治研究会、协会的成立,有较高地位和素质的会员的参予,使重庆市地方自治的具体法规、方案较其他地区完善。不仅如此,重庆市政府为了“广征各区自治人员对于各该区及全市有关地方自治工作意见与对于政府法令得有充分之认识,以便推行自治业务起见”,决定“随时召开本市自治人员座谈会”[6], 并要求迅速制定简则公布施行。
1946年11月2日,南京市政府致函重庆市政府, 要求惠寄“有关民选区保甲长单行法令及实施办法以资借镜”,并称“贵市办理是项工作卓著成绩”[7]。 这表明重庆市自治法规的制订推行工作实较同时期其他地区为优。
重庆市区地方自治的推行仍旧遵照《县各级组织纲要》来办理。重庆市的18个区即相当于18个县,其下的编制为镇、保、甲。这与其他县乡的组织结构基本相同。略有不同者即是从上到下确立起了警察机构的领导监管制度,使从上到下的控制力较县乡强。
为了保证新县制在城区的顺利推行,重庆市政府还规定按月派人考察该市各区的地方自治及新县制实施成绩,逐月办理上报[8]。
重庆市自新县制实施以来,一直坚持进行地方自治的竞赛工作。这种竞赛工作实际上是按照四川省颁布的《地方自治工作竞赛实施办法》及《地方自治工作竞赛通则》,并结合该市实际情况来办理的。四川省的有关竞赛规则要求竞赛对象为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镇与镇,保甲与保甲之间;竞赛项目为各该年度工作计划及工作进度所定之中心工作,包括各种行政及自治工作;考察办法为,“由省政府于每期竞赛之最后一月内派员分赴各县市实地考察拟定分数报由省政府核定,分别酌予奖惩”[9]。四川省其他地区的竞赛工作断断续续地举行, 而重庆市的自治竞赛工作从194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8年,从未中断。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重庆市为推行新县制及地方自治所作的努力较其他地区为优。
二 重庆市推行地方自治成效检讨
(一)从自治竞赛的成绩看其成效
1943年1月25日,重庆市政府会同内政部、工作竞委会、市党部、 市参议会、警察局、社会局等机构对该市第一期地方自治工作竞赛成绩作出了评定。80分以上,列为甲等者共19镇;成绩恶劣分数不及格者有6镇[10]。重庆市1943 年度第二期地方自治竞赛及第四期地方自治巡回视导办理完竣后评定成绩为:80分以上有11镇,在整个列入竞赛的71个镇中,所占的比例为15.5%;成绩不满60分的有2镇,所占比例为2.9%[11]。1945年度,重庆市各区地方自治工作竞赛成绩为:80分以上列入甲等的共6区,在18区中所占比例为33.3%,其余皆为乙等, 没有不及格者[12]。1947年度重庆市18区地方自治竞赛成绩为:80分以上列为甲等者5区,所占比例为27.7%,不及格者1区,所占比例为5.5%[13]。凡考核列为甲等者,重庆市府通令嘉奖,并颁发奖状,不及格者,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将受到申诫、记大过直至撤职等不同程度的惩罚。
单从以上数据来看,历年受嘉奖的比例远大于受惩诫的比例,办理合格且不惩不奖的占多数。这似乎表明重庆市推行新县制成绩较好。不可否认,作为陪都的重庆市推行新县制的成绩确实比其他县乡为优。但以上数据并不能反映重庆市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的成绩。理由如下。
从竞赛项目来看。所谓的自治项目,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上层加强基层管理的行政事项。1943年1月所列的竞赛项目包括:户口清查, 户口异动登记,市立小学校舍设备情况,扫除文盲,清理区坊教育产款,组训国民兵队,举办警卫联系,保民大会之召开及对保内福利之贡献,召开保民月会,国民精神动员, 消费合作社之召开及贡献, 环境卫生。1947年度的自治竞赛项目包括:办理户籍,公共造产,整理财政,健全机构,训练民众,设立学校,办理警卫,修筑道路。以上所列竞赛项目,真正属于健全自治组织,健全民意机构,发挥民众积极性的事务并不多。地方自治所谓成绩显著,实际是指从上到下的行政管理事务办有成效,而于自治本身的民主意志,却未能有效发挥。1943年1月16 日所列竞赛项目中关于自治本身内容的保民大会之召开情况及对保内福利有无贡献一项,所填内容大多为“间有未能按月召开”、“间有举行”,但“多无福利决议案”[14]。1942年10月18日,重庆市财政局长勺培然总结了他考察25个镇的情况。他认为自治成绩主要表现在镇公所规模渐具;户籍调查渐臻确实等[15]。这些事务多为行政事务。勺培然认为:“本市推行自治之成绩,顾其缺点滋多”[15],表现在“各局对于主管自治业务,无目的,无计划,无考成,听其自然,尚未能积极从事推动”;“经费不足,有所举办,须向市民强行摊派,自治人员既感棘手,自治机构亦成怨府矣”;“自治人员程度不够”[15]。
重庆市推行新县制之初,在各级警察机构的监管下,从上到下严密组织,加强控制,确实办有一定成效。这种情况明显反映在自治竞赛成绩中,但它并不能反映自治的真实成绩。
4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政府“行宪”的声浪高涨,重庆市基层的户长会议、保民大会、乡镇民代表会等所谓民意机构频繁召开,议案迭出,从表面上显示出地方自治的成绩显著,这也反映在自治竞赛成绩中。客观地讲,此时的“民意机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民众的呼声,要求举办一些维护基层民众利益的公益事务,反对损害民众利益的一些作法。这比以往地方自治以及新县制推行之初单纯承办上级委办之行政事务确实进步不少。但此时的民意机构仍未从根本上摆脱各级行政机构的从属地位,承接办理上级委办之事仍属其主要任务。
先以重庆市第十一区第一保保甲户长会议集会概况为例。该保甲户长会议自1945年4月24日成立起,已集会1—5次, 会议决议重要案件不多,多限于“清洁沟渠”、“整理甲务”、“征求航空建设会员”、“调查户口”、“调查壮丁”、“征收冬防费”等,其中大部分为上级委办事务,无选举罢免事项[16]。
再看重庆市第十一区各保保民大会1946年度的集会情况。该区各保保民大会自1946年5月29日成立起,至10月止共开会5次,个别保多1—2次。实施选举保长一次,是因为个别保长副保长辞职或病故。无罢免例。实施创制复决事项为“创制保甲公约”。涉及公共事务的议案有“建设公厕”,“清除沟渠”,“整理市容”,“饮水问题”,“清除垃圾”,“修建水池”,“建修校具校舍”等,这些议案表明保民大会能够协助办理一些地方公益事务。不过,这些事务的负担几乎全分摊到一般民众身上,筹集举办上级委办事务及自治事务的经费仍是该保的重要任务。该保就有许多筹募各种经费的议案,如“筹募冬防经费”、“清洁费收集”、“制服费募集”、“航空会员费”等[17]。
1946年12月3日,重庆市第二区第一保12月份保民大会会议记录, 再一次说明保民大会之召开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地方民众的疾苦,向行政机构表达减轻民众负担的愿望。如该记录第四条决议:“全保民众深感清洁费数字甚巨,难于负担,请保办公处呈请上峰减少办理。”[18]第五条决议:“呈请区公所、教育局、市府恢复本保保国民学校。”[18]此外,还有保民陈松泉报告“菜市场地租增加过巨,呈请减轻”[18],保民大会的决议“须由陈松泉先生联名具文来保转呈上峰核办”[18]。尽管保民大会能反映民众的一些呼声,但能否得到解决,却全由上级行政机构决定。而保民大会主要扮演的角色,是讨论如何落实上峰所派的任务。该次保民大会所议事项为:如何推行义务劳动;为蒋介石60大庆劝募,搞自由捐献活动;劝募冬防治安费;如何征收清洁费;如何续租地以恢复保国民学校[18]。
重庆市区民代表会的召开,对沟通上下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以重庆市1946年8月29日第五区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为例。 会议上午由领导讲话,作报告,下午由区民代表提问,区行政人员予以答复。区民代表的提问多涉及有关区民的具体利益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以民政为例,有“保办公处之修建费是否应由区所核定后再筹”;“各保募款不按规定者,请区所制止”[19]。还有不少讨论提案,如“为请函善后总署配发火灾灾民克林奶粉案”;“前任30保保长王大荣筹款修理保办公处,于交卸时并未交出,现办公处已倒塌,应饬交出此款培修案”;“为检举28保保长张学周贪污澄清吏治案”;“请制止非法套买金介眉地产案”[19]。
在区民代表大会上,对于代表的询问,有关行政人员都及时予以答复,对于代表的提案,决议案都作了妥善的安排,表示要迅予解决。不可否认,区民代表们的一些意见确实在会后得到了落实。但由于区所应付上级委派各种行政事务已属力不从心,再加上区民代表会的监督职能有限,区行政职员的民主意识普遍淡薄且吏治败坏,区民代表们的许多建议,尤其是要求减轻负担、规范摊筹派募的呼声,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重庆市的区民代表会、保民大会,除部分区保在最初召开大会时比较认真外,大部分区保逐渐趋于敷衍应付,此类会议也往往不能按时召开。以至1946年11月,重庆市民政局训令:“区民代表会,保民大会为集中民意民力,协助推行地方自治之基层机构,其选举罢免各权之运用及地方自治公约之精神,尤应藉使一般民众彻底了解、观察、仿效……区保务会议亦为推选工作策励检讨所必需,凡此各种会议均应按时召开。”[20]
(二)从选举制度的推行看地方自治的成效
新县制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建立起民意机构。地方自治完成的主要标志是民主选举各级官员。因而考察民主选举的实现程度是总结新县制下地方自治成效的关键。
地方自治及新县制理论一直把训练人民行使四权及实现民选作为努力方向。1943年5月, 四川省政府训令颁发《四川省各县市局训练人民行使四权办法大纲》。该大纲再次强调,“必使人民了解民权真谛引发其参加政治之兴趣,然后民权充张,民意斯达,一般豪强土劣始无从操纵于其间”[21]。该大纲将训练人民行使四权的重点放在基层。“选举权及罢免权之行使应以乡镇保甲长为对象,创制权及复决权之行使应以保甲公约为范围”[22],“以户长会议及保民大会训练人民行使四权之中心”[22]。为了督促该大纲的实施,1944年1月, 四川省政府还制定了《四川省各行政区督导各县训练人民行使四权概况汇报表》,要求各地切实办理,定期填表上报[21]。
四川省政府将自治选举工作看得十分重要。1944年8月, 在实施乡镇自治人员及县市参议员选举之初,曾密令地方官员谨慎行事,“尤其对于贿赂选举、把持选举各种弊端,更须严切查禁,盖有一于此即属推行地方自治之重大耻辱。且自治人员既由贿选把持而来,自必别有用心,于其就职以后,亦必作奸犯科,为所欲为,自治前途,夫复何望。各县市局长监督有责义无旁贷,仰望随时督饬所属切实奉行是为至要”[23]。
重庆市作为陪都,又是“双十协定”的签定地,政协会议的召开地,推行新县制的示范区,因而在40年代中期民主浪潮高涨,民选基层行政自治人员成为时尚之时,重庆市率先普遍推行。
重庆市于1946年5月至6月份,在该市18个区首次普遍推行区保长民选。这次选举与过去一般士绅退缩不就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士绅及优秀青年踊跃竞选”,并且“民选”的区保长的素质较未民选前有所提高[24]。从当时各区正副区长履历表反映的情况来看,中等以上的文化程度占多数,无文盲。年龄从28—59岁不等,绝大部分在30—55岁之间,可谓年富力强。籍贯以四川,尤其是巴县人占绝大多数,基本体现了“以地方之人,用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的目的[25]。重庆市第十二区第十二保保甲长简历表显示,文化程度以私塾及小学毕业者居多,无文盲,年龄在25—52岁之间者居多,也可谓年富力强。籍贯也以重庆市所辖各县为多[26]。
区正副保长一改以往由上级选派的方式而采取“民选”制,一度造成“区保长副因属民选,对上方委派事务未能认真执行”[24]的情况。这反映出“民选”产生的区正副保长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地方的利益,抵制上级机构强加给下层的一些负担。
但应该看到,这里所指的民选,并非是人民直接选举。早在40年代初,重庆市所制定的《召开保民大会案》即表明,保民大会的参加人数并非全体保民,而是正副保长、各甲甲长、各户户长。选举权也是由这些人来行使[27]。直到1948年8月28 日重庆市政府以市民字第一二三四号训令修正的《重庆市区保长(副)选举实施办法》仍旧坚持非全民直接选举制,并继续赋予上级机构在候选人提名及监督中的决定权力。该办法规定,正副区长候选人的办理由市政府主持,正副保长候选人的办理由区公所负责,然后在上级机关派员监督之下,交由区民代表会及保民大会(实际上是户长会议)来选举产生[28]。
重庆市在基层行政及自治人员选举中所采用的户长制及间接代表制,在当时家族制盛行,人文未盛,社会缺乏稳定的政治、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选举的形式,而是选举活动是否公正,人口占多数的一般民众的利益能否得到维护,地方士绅及“土劣”的权势是否受到了有效的约束。
从重庆市在40年代中后期的民选实践中可以明显看出“有产者”在基层的选举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以重庆市第二区第四保为例,该保由户长选出的16名甲长中,除2名副理,1名襄理外,其余13人均为从事工商业的经理[29]。
基层自治人员,如保甲长,“皆非专职,而是兼从事其它职业”[30]。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依靠地方有力者,是难以胜任的。正因为要从事其它职业,所以更便于利用职务之便维护自身的职业利益。对于区镇以上的专职自治职员而言,更需要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或依赖于地方有力者的支持来参加竞选活动,致使贿赂选举事件层出不穷。
重庆市第三区二十二保李高升贿选案具有代表性。李高升于1942年以哥老会成员身份被推举为第三区第一保保长。抗战期间,他在推行公债、办理兵役等事中营私舞弊,三数年间竟挣家产近400万元。 后因诱奸民妻, 霸人钱财,被判徒刑半年。出狱后,恰逢1946年6月的民选。他认为“保长系发财之路”,于是千方百计变卖财产,“作孤注贿买选票竟得复充副保长”[31],后遭到民众的控诉而被查办。
1946年5月,重庆市第二区第八保选举王维岳、 龙肇基为正副保长。随即该保便有人以快邮代电的方式向重庆市民政局控告两人在选举中违法舞弊。“采用违法手段,串通新磁器街居民秘密合作,一家数张公民证,指定选王为正保长”,“王维岳舞弊公民证十余张,证据确凿,并非徒托空谈”,并且揭露王、龙两人“吸食毒物,私卖毒物”,指出其并无资格当选正副保长[32]。
1946年8月22日, 重庆市第十区第二十三保公民黄格卿等控诉刚当选月余的该保保长裴寿华舞弊贿选:“当选举时,只裴寿华一人监场,临场投票时,代书人不照当事人指定者缮写,听其直书裴,此监选之公然舞弊者也”,“当时裴寿华私派族人沿街收集公民证,领票冒选,代书人估写裴之名,有不愿写者而在会场中谩骂,几乎酿成重大纠纷”[33]。裴氏的选举舞弊行为经政府派人查实认定“确属实情”[34]。
1946年4月3日,重庆市第九区公民具结控诉该区民政股主任张孝良:“自到职以来,莫不朝夕蓄意贪污,用肥私囊,其妄法情事,不胜枚举,尤是此次区民代表之选举,该孝良乘机捣鬼,特为显著,勾结土豪,大批出卖选票,每张五千元或一万元不等,收获颇巨,并嘱购票者不得传扬,否则严惩等语,一般无智劣绅,为利害相关,只得同流合污,咸默不语”[35]。
重庆市的贿选行为绝不是个别现象,以上所举仅是从大量被控案件中随样抽取的。当时社会上流行一首诗:“陪都文人真是少,竞选草包当代表,投票诸公皆聪俊,为何糊涂作戏耍。”[36]其实被选出的人并非“草包”,他们善于行贿,善于贪污,勇于贪污,按时下的话讲,他们是很“精明”的人。这也正如蒋旨昂早前所说的:“贪污的人,不一定是不办事的。而且事实上,许多贪污的人,都是很能干的。他们因为能干,才敢贪污;也因为有事干,才能假借此事之名,去行贪污之实。”[37]聪俊的投票者变成了糊涂虫,多因被人“施其铜臭魔力”而已[36]。
国民政府多次推行地方自治,但都未能大规模地开展地方行政及自治人员的民选活动,直到40年代中期,始在陪都重庆及四川等省的部分地区推行,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却弊端丛生,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三)从重庆市地方自治经费的筹募看地方自治实施的困难情形
重庆市作为抗战期间的陪都,同时也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按理讲,其推行地方自治的经费应远比其它县乡充足。但细考其实际,我们发现它同样面临着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
重庆市的基层自治机构普遍存在缺乏“经常费”的情况。《重庆市第二区各级自治机构筹备经过概况调查表》显示,尽管该区保办公处成立日期从1940年10月至1943年7月各不相同, 但各办公处的“经常费”均“无”[38]。
重庆市基层自治机构自身收入有限。1946年重庆市财政局制定了《重庆市各区自治经费统一收支办法》,该办法要求“各区公所各种收入悉由市政府财政局委托区公所人员办理纳库手续”[39]。并列出了各区应交市政接收之款产共四项:“甲、区公有款产收入;乙、区公营事业收入;丙、区造产收入;丁、其他依法赋予区之收入。”[39]重庆市民政局训令各区“拟具意见呈报来局以凭核办”[40]。各区的报告多称未有上列各种收入。如重庆市第一区区公所的回复意见为:“关于本表所列甲乙丙丁四项公共收入,经查本区并无上四项之收入,拟据实答复。”[41]
重庆市的自治经费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这与民政局经费的入不敷出状况密切相关。1947年以后,这种状况更是每况愈下。重庆市民政局1947年6月至9月的经费入不敷出额为94□010元, 其中自治经费入不敷出额为680600元,占总额的比例较大,达到72%左右[42]。
自治经费的缺乏直接影响了自治事务的推行。选举作为自治事务中核心内容之一,同样面临着经费支绌的问题。
重庆市办理市参议员及区民代表选举费用,曾经市民字第四二○号训令及重庆市字第二三九号训令颁发了统一支给标准,规定在自治经费内撙节开支[43]。由于自治经费缺乏或入不敷出,许多地方的选举费用靠基层垫支,而政府又没有切实的补偿办法,必然导致地方随意摊派、民众不堪其扰局面的形成。
重庆市第三区于1946年4月12日呈奏的选举实支费为1661830元,除遵照规定开支标准列出631340元外,尚不敷开支法币1030490元[43 ]。
重庆市第十区区公所于1946年7月给重庆市政府的呈文中称, 该区自1945年12月奉令办理参议员及区民代表选举,所需费用甚多,且均由该所挪支垫付,各保因办理选举所用费用均由各保长筹款垫付。该区公所请求市府设法筹措归垫[44]。
1946年6月26日,重庆市第十七区区公所呈文市府称,该所1945 年12月起奉令开办甲长讲习所及区民代表选举,市参议员选举,以及1946年5—6月份保甲长选举,区民代表大会成立,选举主席及正副区长所需费用,“若由地方负担,不特难于筹办且时间迟延缓不济急,迫不得已将本所1945年度积余经费及代收各保缴来的新兵招待费、安家费一并挹用……请准在以上经费项内作正开支核销”[45]。而重庆市民政局于1946年7月12日的批示中却否绝了该区的请求。 指出:“选举费用早有府会规定贴补办法,其额外超支应由该区长自行负责,不得在其他结余项下挪支……1945年度经费积余应悉数缴库不准动用……选举费用应遵照府会在该区自治经费收入项下开支。”[46]
自治经费短缺,办理地方自治事务所需经费采取临时挪用垫付的办法,而政府又不予支持,令区长等自治行政人员“自行负责”。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乱摊派的现象,一则加重民众之负担,一则更有利于地方有产者对诸如选举等自治事务的控制。
重庆市对地方自筹自治经费也作了相应的管理,曾明确规定赋予民意机构以征募捐款的议决与审核权。
1945年2月, 为筹措区保经费,加强该市各区保自治业务的推进,重庆市废除了原来的《各镇经募捐款办法》,制定了新的《区保经募捐款办法》[47]。该办法赋予了区民代表会及保民大会以相当权利。其中第三条规定:“右列捐款应拟具预算订定募集办法提经区民代表会或保民大会议决,呈由主管局呈准市政府后行之。”[48]第七条:“经募捐款应于事后将收支情形向区民代表会或保民大会报告并由各该会推举代表审查帐目单据后专案捡据报核并公布周知。”并规定:“违反本办法之规定者以贪污勒索论罪。”
重庆市在主张地方筹募自治经费的同时,也曾设法避免地方的乱筹行为,杜绝苛捐杂税的征收。1946年3月4日,重庆市政府训令,要求各县市政府查报1945年度各项自治税捐征收情形,并将所废止之苛捐杂税以及各种摊派名称报由贵市政府查核,“其能恪遵功令或有奉行不力者,似应分别酌予奖惩”[49]。此举的目的为“推进各项法定自治税捐及厉行废止苛集摊派”[49]。
重庆市在征募自治经费时力图发挥区民代表会、保民大会的作用,避免苛捐杂税。但由于民意机构自身的产生及运作严重受地方有产者及行政人员的制约,其自身处于依附地位,民意作用难以发挥。经费征收不能因贫富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中饱现象禁而不止。 经费征收困难。1947年12月27日,重庆市第一区公所指出,该区之临时自治经费总共派募额为7000余万元,而收到仅2000余万元,并有数保分文未缴。“似此情形,非但有碍自治工作之推进,且有不重视法令之嫌”[50]。1947年12月,重庆市1至18 区正副区长联名指出:“区公所自治经费以及区保专任人员薪津责令地方自筹,在政府初意或以市库支绌原为不得已之措施,但其结果实足以显示政府无推行地方自治之诚意,因而形成自治机构与市行政机构之差等,引起人民歧视地方自治人员之错觉。”[51]“加以物价狂涨,人心不安,人民生活困难万状,至此而由辅导民众训练民众之自治机构,人民选举之区长就近向人民征收自治经费,姑不论反响如何,但人民内心之怨恶与憎恨当为任何人所能想象。”[51]他们因此而提出的解决办法为“市属机关原则上一律平等,人员因待遇同工同酬,自治经费列入市预算统筹统支以提早完成地方自治,配合行宪而利建国”[51]。重庆市正副区长的以上建议得到市府、市参议会的认同,他们于1948年1月9日制定了《重庆市自治经费征收办法草案》,规定:“所有以前各区保征收各项临时自治经费概行停止,由市财政局统收统支” [52]。 该办法草案得到了市参议会第七次会议通过。1948年1月23日,重庆市1至18区地方自治专任人员因待遇菲薄,生活已频绝境,恳求政府实践诺言,一本同工同酬,同地同酬之旨,迅即按照新调整数发给薪津以维生计而昭公允[53]。
1948年初,一方面重庆市地方自治专任人员要求与政府行政人员同工同酬,自治经费实现统收统支;另一方面,市府又面临着1947年度的经费仍未收纥的困难。旧帐新款,加重了征收工作的难度,尽管政府一再催征,但统收统支的新方案却难收其功。
重庆市第一区公所于1948年1月26日编造完成了1947 年临时自治经费追加数,并派主任及助理纷赴各保劝募。1948年2月5日,该区公所针对1947年度临时自治经费有延缴、抗缴情事,规定了缴款的最后期限,愈30天不缴,加收滞纳罚款50%,愈期仍就不缴,得请各区警察分局协助追缴[54]。民政局汪局长把最后期限规定在1948年3月15日[54 ]。但过了此期限,情况仍未改善。1948年3月15日, 第十区第六保向区公所呈文指出,该保征收1947年度及1948年1—3月份临时自治经费共计收入290万元,尚未募足1947年度的340万元的预算额,入不敷出甚巨[55]。1948年3月26日, 该区与保办公处呈文区长称:“本保专任人员薪水未增加,难以维持最低生活。”[55]既然上级不予解决,他们只得召集该保士绅及各甲长会议,想法先向民众摊收300万元, “以救专任人员燃眉之急”[55]。
重庆市作为当时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地区,从开始推行新县制以来,同样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经费缺乏问题。经费缺乏使一些基本的自治事务如选举事务都不能得到相应的经费保障,更不论其它需费甚巨的自治建设事项了。重庆市政府所采取的地方自筹和统一征收的办法,都未能使贫富分担合理,无一不加重基层民众的负担。政府限期催征的办法,非但没能从根本上改善征收困难的局面,而且更增加了民众的怨愤程度。
收稿日期:2000—0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