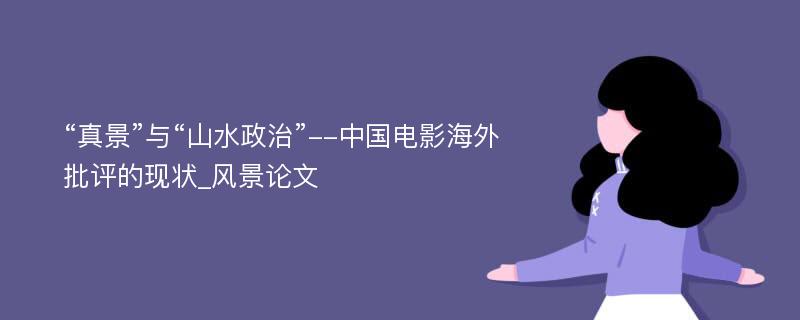
真实的风景与风景的政治——中国电影海外批评的当下取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景论文,中国电影论文,批评论文,真实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风景与电影
风景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可能未必有简单明了的答案。在中国电影研究界对这一术语仍略感陌生之际,海外学界的风景研究已经蔚为风气,“风景与记忆”、“风景与权力”、“风景与电影”等诸多议题,均已有专著出版加以研究。海外学者以不同的专业背景(包括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生态学、绘画史、历史、文学、电影、文化研究等)进入关于风景的讨论之中①,各种观点互为借鉴,风景界定也纷繁多样。值得关注的是,持续的讨论逐渐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方向,达成了某种共识:风景不同于自然,而是意识形态建构的所在,是文化的所在。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这段话被广泛征引:“风景不仅可以成为感官的栖息之地,更重要的是,风景还是精神的艺术。风景为记忆的深层——正如地壳中的岩层——所构建。风景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才是自然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均有想象性的建构投诸其上。”②加拿大电影学者马丁·列斐伏尔(Martin Lefebvre)在视觉文化的背景下对风景加以进一步界定,认为将风景与自然相区别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列斐伏尔坚称,风景并非自然,而是自然的寓言,是自然的图像,而非自然本身。在他看来,风景被视觉装置——包括摄像机、凝视、取景框以及与视觉文化相关的技术——彻底渗透。“通过框取,自然转而为文化,大地转而为风景”③。
电影是对风景进行影像再现的主要媒介。电影中的风景很早便成为风景/电影研究者所关心的对象,相关的探讨从爱森斯坦就已经开始。通常,电影中出现风景的时刻,大多是没有人的空景,具有过场的功能,即所谓的空镜头。爱森斯坦认为,无声电影中的风景,承担了“发出音响”的使命,“脱离常态”从而“转入到另一向度”,接近于音乐的功能。“因为风景是影片中最自由的因素,最少承担实在的叙事任务,最能灵活地表达情绪、感情状态、内心体验,总之是那些因其朦胧多变而只有音乐才能充分表达的那一切东西”④。沿着这个思路,列斐伏尔以是否承担叙事任务为衡量标准,将场景与风景互为区分。场景是叙事的发生之地,而风景却从“发生性”(或译为“事件态”)中抽离出来,独立存在⑤。
相对于叙事的封闭性,风景更具有开放性。风景更接近于罗兰·巴特所谓的最具颠覆性的“可写的文本”⑥。丹尼·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将其作如下概括:“这类文本(可写的文本)并不提供明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要求读者不断地积极参与到它的建构中来;与之相反的是可读的文本,它提供一个令人愉快的参考框架,垄断言说的资格,从而诱使读者沉溺于陈词滥调。”⑦风景意味着间歇,意味着由间歇而唤起的填充意义的冲动,召唤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去填补缝隙,因而,其实现方式具有多种可能。观影人不断地创建理解模型,而同时又认识到理解模型都是脆弱的。沃尔夫冈·伊瑟尔称其为“在幻觉的建构和破灭之间或多或少地来回摇摆”⑧。正是这种意义加诸风景的脆弱性及其所带来的挑战难度,让自视甚高的研究者一时技痒,跃跃欲试。
如今,关于风景的界定可能更为广泛,人文景观跻身风景之列,成为大势所向。张英进试图将族群景观(ethnoscape)也纳入风景的范畴,这似乎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以及激发风景研究之价值的双重考量⑨。美国印度裔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将族群景观定义为:“游客、移民、难民、流亡者、异国劳工以及其他迁移的群体和个体,他们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一个本质特征,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影响着民族之中(及民族之间)的政治。这并不是说,由亲缘、友谊、工作、休闲、出生、居住及其他关系形式所构成的、稳定的社群和网络已不复存在。但它意味着,这些稳定性与人群的流动处处经纬交错,因为更多的个人和群体都面对着不得不迁移的现实,或怀有迁移的幻想。”⑩这同样也是列斐伏尔关于风景的定义的必然延伸,但凡是脱离叙事进程的再现,无论其景观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均可为风景。于是,山山水水不再独占风景,人文景观也有了享列其间的权力。
由此更进一步的是,风景还是权力交织的所在,这无疑使得风景政治学成为了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议题。W.J.T.米歇尔将风景从它所隶属的社会阶层中抽离出来,加以重新形塑,认为风景有证实社会身份与捍卫权力关系的功能。“风景并非‘是什么’或者说‘意味着什么’,而是‘做了什么’,如何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而运作。我们认为,风景不仅仅意味或象征着权力关系,而且是文化权力的生产装置,也许还是权力的代理”(11)。继承米歇尔的批判传统,美国人类学者温迪·达比(Wendy Darby)也断言:“风景的再现并非与政治没有关联,而是深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并认为:“多重视角的研究使沉默的风景意象发出声音,使隐藏在关于风景及风景意象的知识和体验之后的社会性基础显现出来——这种社会性基础就是历史上各种排斥与包容的观点。”(12)
风景政治学的知名个案,便是约翰·巴瑞尔(John Barrell)的专著《风景的阴暗面:1730年至1840年英国风景画中的乡村贫民》。作者试图揭示在18世纪的风景画和诗歌中,风景如何将乡村的贫苦形塑为自然而然,以至于成为达官显贵的沙龙乐于接受的装饰。“唯有贫民劳作的画面,方能被用来再现他们的生活现状;描绘他们休息的方式,则是将其感伤化或牧歌化”(13)。巴瑞尔指出:这便是风景的阴暗一面。爱德华·萨义德的观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他认为,风景的发明或发现是被操控的,例如耶路撒冷的地理风景已经全然被记忆遮蔽:“耶路撒冷完全笼罩于各种象征性的联想之下,这完全掩盖了耶路撒冷作为一座城市与一个真实地点的存在事实。”(14)李政亮将注意力置于风景形塑与民族主义的隐秘关联之上,认为现代国家通过文化生产机制将风景形塑为民族认同,历史上日渐崛起的德国以及日本均为此例(15)。纳粹掌权前后的德国,出现了以山岳之壮美象征雅利安文明之优越、以人与自然的抗衡暗示雅利安人种之优秀的山岳电影(Mountain Film)。19世纪末日本地理学家志贺重昂面对欧风美雨之际坚守国粹立场,极力彰显日本风物以显示大和民族之优越:“江山之美,植物种类繁多,也正是涵养日本人过去、现在、未来审美观的原动力。”(16)形形色色的风景背后,是多种力量互为交锋的话语场域。其实,风景的政治是要透过风景的真实来理解和认知的。
真实的风景,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也是海外观影者批评中国电影的当下取径。当代中国电影的真实风景,之于海外观影者而言,某种意义上并非是尚待探索并试图掌控的“未知之地”(17),而是业已路经仍频频回首的熟悉之地。
二、现代性对风景的消蚀和“液化”
时光留痕于身体,岁月留痕于风景,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言,风景是“带有历史进程的印迹”(18)。经历沧桑的风景,是集体记忆的承载。
《电视指南》(TV Guide)影评人肯·福克斯(Ken Fox)在看罢《三峡好人》之后感叹道:“中国第六代导演绝少如贾樟柯一般,以犀利的目光和沉重的心情,直面中国迅猛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剧变。”(19)《三峡好人》里有两个主角。男人韩三明来自汾阳,是个忠厚老实的煤矿工人,到奉节是为了寻找十六年未见的前妻。女人沈红来自太原,是名沉默寡言的护士,到奉节是为了寻找多年不曾与自己联系的丈夫。故事并不复杂:两人的寻找之旅异常艰难,最后的结果均不甚如意。两人不曾相识,也从未相遇,唯有风景穿插其间,为二人所共享。《纽约时报》影评人曼诺拉·达吉斯(Manohla Dargis)觉得影片中的风景那样的耐人寻味:“韩三明和沈红为空间和各自的故事所离间,却为背景、文化、语言、风景所联系。异常美丽的群山高耸于他们的头顶之上。在自然环境、毁弃的建筑以及周围峡谷的映衬之下,他们不出所料地微不足道。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之间、永恒自然的轻松美感与毁弃文明的可怖美感(贾樟柯是一个歌咏毁坏的诗人)之间的联系,铿锵有力又令人不安。”(20)风景之所以变得如此突出和强烈,正是它自身的渐次消失的一种暗示,而集体记忆随着风景的衰微而淡忘,人民币背后的夔门山河不再矗立,我们只能靠印刷品的复制来打捞失落的集体记忆。
流行歌曲被嵌入风景之中,同样承载着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当邓丽君的歌声响起时,往日的时光重现,成为一段值得分享的情感。与感伤的音乐相较,林立的风景总是沉默无言,似曾相识,独立生姿,不过,风景的真实品质往往更为海外影评人所看重。其原因在于,专业影评人大多具有丰富的从业背景,他们对“煽情主义”的处理方式相当敏感,也并无好感。刻意追求耸人听闻的轰动效果,为坚持严肃品质的新闻人所不屑。银幕落下,黑暗降临,观影者会发现电影中即便音乐偶或煽情,但风景却静默无声,更何况呈现风景的镜头语言(多为固定的远摄镜头,偶或移动)往往是朴素的、去技巧化的(21)。风景并不坦言立场而是潜藏命意,这暗合了某种叙事的规范,故而被认作客观真实。
影评人韦斯利·莫里斯(Wesley Morris)认为,贾樟柯的系列作品,绝不仅仅是偶然的,将其放到一起来看,它们实际上创造了一部“超现实的国家编年史”。他还进一步提醒我们,关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有企业的风景,至今依然清晰可辨:“人们劳动在巨型的机器里面,潮水一般地涌向建筑,里面挤满穿着统一制服的身体以及缺乏表情的面孔。”(22)集体记忆似乎并未离开我们,而是寓于风景之中。而面对贾樟柯《二十四城记》中“不断出现的恢弘的工厂大门——拆除和移置的标记——以及渐次拆除的和已成瓦砾堆的工厂楼层”(23),我们越发意识到:“历史无论何时被自然之光所照见,只有生动如画的毁坏之境,才能具体而物质地吸纳历史事件。”(24)
历史事件的重现,使得拒绝摆拍获得了纪实风格。然而,延宕的风景会将故事片与纪录片的边界处理成模棱两可,使得风景与纪录片之间更为隐秘的渊源可能在于,风景延续早期纪录片所具有的“牺牲者的传统”。布莱恩·温斯顿(Brian Winston)提醒我们,警惕纪录片制作中的这种倾向,即纪录片工作者在对拍摄对象进行浪漫或诗意再现的同时,社会关怀以及慈善式的感同身受等伦理道义将不可避免地掺杂其间,从而拒绝接受将被摄者与拍摄者置于同等地位的拍摄理念(25)。风景好似一匹横亘千里的巨兽,身处其间的人们难免会显得微不足道,这使得观影者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风景是如此广袤无垠以至于难以掌控,它更倾向于将剧中人刻画成一个个消极无力的形象,这使我们对剧情的参与者可能正积极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点视而不见,我们反而将风景中的人看作是无可奈何的牺牲者,他们被认作是承受了集体记忆的重负,忍受集体记忆消散的痛苦。正如大卫·丹比(David Denby)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指出的那样,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不去选择生机勃勃又杂乱无章的生活,而是像所有歌咏荒凉的诗人一样,选择既美丽又怪诞的空白空间(26)。在这个扁平的空白空间之中,除了一味地忍受之外,主人公无疑是难有作为的。
鲍曼指出,现代性是一种“液化”的力量,它使得“旧有的结构、格局、依附和互动的模式统统被扔进熔炉中,以得到重新铸造和形塑;这就是天生要打破边界、毁灭一切、具有侵犯色彩的现代性历史中的‘砸碎旧框架、旧模型’的阶段”(27)。显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静止的、凝固的、过往的风景会激发我们内心深处的怀旧之情。
《二十四城记》中的四○二厂(成发集团),一座从东北迁至四川的飞机军工厂,在特殊的年代里它曾是无数人羡慕与自豪的所在,然而,和平的局势和体制改革却将它的光鲜逐渐剥蚀。贾樟柯选择让当事人(或由演员饰演的当事人)直接走向镜头,诉说人生际遇的关键时刻。离合寓于讲述之中,悲欢现于神色之间。镜头扫过工人宿舍区,退休工人郝大丽举着吊针向我们走来,隐忍着讲述了迁厂途中孩子不幸失踪的故事。在访谈的末了,影片插入摘自《成发集团发展史》的一段话来佐证这段记忆并非虚构,失踪确有其事。这让我们倍感不安——演员所述并非杜撰而是事实,而且是如此惨痛的事实。《村声》(The Village Voice)的影评人詹姆斯·霍伯曼(J.Hoberman)指出:“一方面,《二十四城记》似乎是回望社会主义的包含矛盾情绪的诗化实践……另一方面,这种对工业生产的颠覆性的旧式赞歌,为反传统的、含混的荒诞细节所充斥(比如,一个年老的工人经过废弃的飞机,高举吊瓶好像手执自由的火炬),以及点缀其间的伤感的流行乐和忧愁的诗篇,包括叶芝的诗:‘在我青春说谎的日子里/我在阳光下招摇/如今我已萎缩成真理。’”(28)霍伯曼似乎猜透了其中的奥秘,怀疑贾樟柯将叶芝所谓的今已萎缩、昔日招摇的“我”影射为“今显落寞、曾经骄傲的普罗大众”(29)。这种对旧日风景的隐秘改写不能不使人们意识到,“当下的面貌是历史性的,在任何一文化里、在任何一代人中连续不断地获得重生”是可能的(30)。
在徐刚(Gray G.Xu)看来,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讲述了一个关于变迁的故事:北京靠急剧发展而跻身世界之列,随之而来的变迁,靠老北京最后剩余的胡同来提醒;外来劳工艰难挣扎,靠效仿城市居民,以期获取金钱的或象征性的资本;北京新一代的年轻人试图追赶纽约、东京的最新潮流”(31)。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流动中酝酿。流动不仅驱动整个时代,也牵动着人们的命运与悲欢。风景亦然。风景所能够提供的是那样一种抒情的怀旧气息,即便是最为寻常的瞬间,如穷困时的捉襟见肘、辛酸中的些许机智,也成为抒情和怀旧的难忘时刻。“即便是对北京的影像再现,竟也营造出了令人最为难忘的瞬间。以其中的一幕为例,其展示了普通大众对自行车和三轮车的五花八门的巧妙应用: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载运电冰箱,一个人推车一个人扶;还有用三轮车运送巨大的衣橱,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还另载一个人以保持平衡。伴随着简单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音乐节奏,以现实主义为定位的镜头,为北京城平添了抒情而怀旧的气息”(32)。这种民生多艰的风景,在高度发达的欧美国家已经不在,海外观影者难免藉此抒发自身的怀旧之情。英国人文地理学家大卫·罗温索(David Lowenthal)为这种透过风景来怀旧的倾向提供解释说:“即便当我们为忠诚于历史而苦苦努力之时,我们也在生产反映我们习惯和偏好的新东西。”(33)
霍伯曼在看罢《三峡好人》之后评论说:“永恒的是无常,或者说,只有无常才是永恒的?奉节,这个在长江之畔伫立千年的古城,如今旦夕之间即被荡为一片瓦砾。人们辗转觅食于断砖碎瓦之间,艰难谋生于废弃的码头与搁浅的驳船之上。”(34)霍伯曼或将情绪导向感伤忧愁,或将追问引向无常的永恒,但无论是伤感的怀旧情绪,还是类似宗教体验的情绪,我们都会意识到:随着风景的徐徐展开,没有什么比天大地大的风景更适合于作为返躬自身、叩问心灵的场所了。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风景也是一种遮盖,叙事被硬切至风景,像巨幅张贴画被猛然刷上公告栏,中断了我们的追寻。于是,追问就此告罄,问责就此打住。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或有缺陷的体制及其操作过程豁免于其本应承担的责任。风景或许并不为艰辛的人生提供严格意义上的解释,而只是愿意提供些许安慰,但由此看来风景总是会巧妙而迂回地表现意识形态。风景表面上中立、客观,似无偏向,但这并没有抹去它的生产过程,反而突出了自身乃是一种人为的建构。
三、风景一角与镜头意识形态
海外对于娄烨《苏州河》(2000)的批评,倒没有我们预料的那般——对其遭禁的待遇津津乐道,而是惊异于《苏州河》能从历史中发现一处鲜为人知的侧面。借用张英进的一句话,《苏州河》揭示了“官方修辞和商业电影所支撑的经济改革的显赫外观的另一面”(35)。
《苏州河》讲述的是一个庸俗老套的爱情故事,其叙事不止土气,而且不能叫人完全信服,气氛效仿王家卫,悬念又不及希区柯克(36)。尽管如此,海外观影者仍然难以打消对它的兴趣。“最复杂也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苏州河’这一片名‘角色’的出场了——一条蜿蜒穿过上海工业城区的肮脏的人工河道”(37)。伴随着苏州河风景的展开,独白开始,似乎要展示一段私密的个人体验史:“我经常一个人带着摄影机去拍苏州河,沿着河流而下,从西向东,穿过上海。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传说、故事、记忆,还有所有的垃圾都堆积在这里,使它成为一条最脏的河。可是还是有许多人在这里,他们靠这条河流生活,许多人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一生。”(38)《纽约时报》影评人斯科特(Anthony O.Scott)甚至惊异地发现,即便是离开影院,苏州河所带来的潮湿寒意也同样挥之不去(39)。
对于《苏州河》,徐刚则别有一番况味。与黄浦江迥然不同的是,苏州河承载着底层命运与希望,是一条属于底层的河流。娄烨执意选择此种视点,令人诧异的同时,又因其人道主义理想而使人倍生敬意。“常被称为‘上海腋窝’的苏州河,并没有为试图寻找刺激的都市图景的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的视角。如此完美的视角却可以为黄浦江所提供:在它的西岸就是外滩,沿岸一列的乔治时代的建筑代表了上海的殖民历史与久经沧桑;在它的东岸则是东方之珠,象征着全新的上海。对比之下,苏州河并没有如黄浦江一般的显赫历史与繁华当下。它是一条属于劳苦大众的河流,是上海排污的下水道,它同时也是自上个世纪以来,来自这个繁华孤岛周围的广大农村的千万劳工进入上海的主要门径。虽然苏州河被居住在‘上只角’——曾经是列强的租界——的上海本地人所轻视,但是它为居住在‘下只角’——老地图中指与农村相毗邻的城市——的外来移民与劳工阶级提供生计与安全的港湾”(40)。当摩登都市为官方修辞和商业电影所反复再现、精心修饰之际,这种看似逆向的展示诉求难免令人产生不适。然而事实却是,层层累积现代神话的黄浦江,一如层层堆积垃圾污染的苏州河,谁也不是摩登都市的全部。张旭东认为,上海往往成为了现代性的终极想象。“农村的或前资本主义性质的旧中国背景,被视作前现代的困境。与其不同的是,上海这一都市丛林往往被中国或西方居民视作历史的先驱、文明的孤岛,以及‘现代性’真正出现的最终表现。与腐朽的历史截然不同,上海的活力被视作天然的内驱力,其爆炸性能量以及改造的力量,被期望为对国家的强有力拉动——或者说一群独特的中国人——摆脱了邪恶的传统怪圈”(41)。《苏州河》的风景打破了这种神话,它提醒我们:即便摩登如上海,也还有藏污纳垢的角落,也还有羞于示人的历史景观。
激进的影评人可能会认为,对于这种侧面的针对性展示,潜藏了自我东方主义化的危险倾向。然而,风景的真实性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提供了抵消此类批评诟病的有效屏障。侧面终究是侧面,导演固然无意也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视界的制高点。然而,这种苛求不应该成为我们苛责风景的理由。发现新的风景,一个为显赫历史所遮蔽不显的侧面,诚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能带来关注和思考,而不是熟视无睹或是掉头不顾。你不去关心,风景依旧倔强地存在。《苏州河》似乎早已预料到其糟糕的结果,影片中的独白试图提醒我们:“不过,你要是不喜欢我拍的你,可别怪我。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不过,风景的摄取确有其讲究,景深镜头之下隐含着意识形态的诉求。众所周知,景深镜头中的远近意味着与观影者的亲疏:遥不可及疑似幻象,触手可及方为惯常。比如《二十四城记》的结尾,前景是坐在“甲壳虫”汽车里面的时尚年轻的娜娜,中景是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远方的背景是从废墟中拔地而起的严整有致的建筑工地。这个镜头不啻暗示了:远方的历史废墟已经清理,现代化的建筑得以兴建,而现代已经走到了我们的面前,一切都显得令人愉快(42)。与之相对比的《苏州河》,摄像机更愿意在船板上向外随意取景,摇晃而倾斜的风景标榜了记录的真实性。其中一处,以浑浊的苏州河为前景,以岸边破败的平房、桥梁为中景,以远方朦胧的东方之珠为远景,这样的风景提醒我们:破败和污秽围绕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周遭,是触手可及的,而现代性的景观无非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无情地矗立在远方,与我们的距离不可谓不小。正如徐刚所观察到的那样,“新的摩天大楼和新的电视塔淡入背景;其中,垃圾和毁弃的建筑造成了视觉上的突兀。因此,娄烨的城市史是关于腐朽城市遭致毁弃的历史”(43)。现代性的神话面临崩坏的危险,继之而起的是矗立的风景。既有拔地而起的现代建筑,更有尚未清理的废墟;既有外滩的光鲜亮丽,更有内河的肮脏污染。这虽然谈不上令人欢欣鼓舞,但也不至于叫人灰心丧志,至少能让观影者告别盲目,摆脱幻想,放低眼界,关注日常。
达吉斯在看罢《二十四城记》后曾说过:“反反复复地观看这部片子,感受真实与想象、人们与地方之间的东西,忽而沉醉其间,忽而隔离远望。”(44)虚构的叙事使我们沉醉其间,真实的风景令我们驻足远望。倘若虚构的叙事被精心地编码,朝着同一个方向,无比锐利地前进,那么,不难想见,敏感的观众会从沉醉中抽身出来,对叙事的指向持保留态度,甚至拥有某种怀疑、指控、抵抗叙事的企图。在海外发行的过程中,充斥强烈意识形态的作品,极易引起反感而遭致批判。力强而至,不能久持,却易反噬其身(45)。而风景却能从叙事的序列中抽身出来,从容不迫,静默无言。风景将镜头中的叙事性因素暂时悬置或者说清空,减慢叙事节奏,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讨论平台,容许我们反省先前已经看到的事物,而不是将影像诉诸劝说式的宣传处理。对于海外观影者而言,风景真实可信,可以毫不费力地深入人心。
风景本身并非不生产知识,不过是将知识生产的过程悄悄地隐藏起来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风景的背后隐匿着更为深刻的政治。风景诚然是暧昧而复杂的,既是激进,也有保守。风景的激进一面在于:伴随着风景的坍塌而来的,是神话的消解,包括集体主义神话以及现代性神话。旧时风景的沦陷与消歇,是集体主义神话的破灭;显赫景观的蹩脚侧面,是现代性神话的断裂。拆解神话的过程同样也是否定信仰的过程,令人遗憾,引人感伤,使人震惊,或将促使观影者起身求证真相。当然,吐故纳新,也有新的可能性在酝酿。然而,风景的保守一面在于:风景将观影者的情绪引往辽阔天地,从中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告慰,以至于中断持久性的追问,更何况,处于风景之中的卑微个人或将仅仅限于牺牲者和观望者,对抗性的力量将销声匿迹。
风景一旦成为争论的中心,它会提醒我们隐藏在我们身后的风景。风景,是中国走向现代的物质见证者——这一过程的艰难曲折、欣喜悲伤皆深深印刻其上,同时也是我们回望、缅怀、审视、反思的对象。风景中国,既伤痕累累、毁弃遍地,又百废待举、新兴在望。对风景巨细无遗的展示,不啻在提醒海外观影者一个事实:我们正视风景,我们在对其进行反思。
注释:
①关于风景的讨论,参见Peter J.Howard,An Introduction to Landscape,Farnham:Ashgate Publishing,2011。
②Simon Schama,Landscape and Memory,New York:Knopf,1995,pp.6-7.
③⑤Martin Lefebvre(ed.),Landscape and Film,London:Roudedge,2006,p.xv,pp.19-60.
④爱森斯坦:《并非冷漠的大自然》,富澜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⑥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1页。
⑦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
⑧Wolfgang Iser,"The Reading Process: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New Literary History,Vol.3,No.2,On Interpretation:I(Winter,1972):293.
⑨张英进:《民族文化,个人视野,多地记忆:当代中国电影的真实风景》,郑焕钊译,载《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⑩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4页。
(11)W.J.T.Mitchell(ed.),Landscape and Pow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p.1.
(12)温迪·达比:《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13)John Barrell,The Dark Side of the Landscape:The Rural Poor in English Painting 1730-184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92.
(14)Edward W.Said,"Invention,Memory,and Place",in W.J.T.Mitchell(ed.),Landscape and Power,pp.246-247.
(15)李政亮:《风景民族主义》,载《读书》2009年第2期。
(16)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321页。
(17)“未知之地”这一神话既是发现的幻想,意味着终极的知识和洞见,又是他者的传说,意味着神秘与含混。即便有穷形尽象的探索和烛幽发微的描绘,也难以穷尽有关未知之地的全部奥秘,结果带来了更为强烈的探索与征服的愿望(参见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第165页)。
(18)Walter Benjamí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1963),trans.John Osborne,New York:Verso,1998,p.180.
(19)Ken Fox,"Still Life:Review",TV Guide,http://movies.tvguide.com/still-life/review/292189.
(20)Manohla Dargis,"Those Days of Doom on the Yangtze",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8,2008.
(21)如《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影评人迈克尔·菲利普斯(Michael Phillips)发现贾樟柯在《三峡好人》里的镜头限于固定镜头和横移镜头。
(22)Wesley Morris,"24 City:Sweet and Sentimental Stories of Displacement",The Boston Globe,August 20,2009.
(23)(28)(29)J.Hoberman,"A Chinese Factory Reborn as Condo Heaven in 24 City",The Village Voice,June 3,2009.
(24)(31)(32)(40)(43)Gary Gang Xu,Sinascape: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7,p.80,p.70,p.72,p.80,p.80.
(25)Brian Winston,"The Tradition of the Victim in Griersonian Documentary",in Alan Rosenthal(ed.),New Challenges for Documenta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p.269-287.
(26)David Denby,"Moral Landscapes",The New Yorker,January 21,2008.
(27)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页。
(30)(33)David Lowenthal,"Past Time,Present Place:Landscape and Memory",Geographical Review,Vol.65,No.1(January,1975),p.36,p.36.
(34)J.Hoberman,"Drowning in Progress",The Village Voice,January 8,2008.
(35)Yingjin Zhang,Chinese National Cinema,New York:Routledge,2004,p.291.
(36)J.Hoberman,"Eternal Return",The Village Voice,November 7,2000.
(37)(39)Anthony O.Scott,"A Chill Scene for Shadowy Characters",The New York Times,March 25,2000.
(38)娄烨《苏州河》(2000)台词。
(41)Xudong Zhang,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China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8,p.197.
(42)这种镜头被怀疑试图“兜售微妙的议题”,具有美化倾向。尽管“有些批评家将其视作对过去严厉政策的辩护,或者视作对中国新工业的非凡成就和消费主义横行的庆祝”,不过大抵还是被接受了(Joe Morgenstern,"Ferrell Flounders in Feeble Fantasy 'Land'",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5,2009)。
(44)Manohla Dargis,"An Upscale Leap Forward That Leaves Many Behind",The New York Times,June 4,2009.
(45)重金打造的《金陵十三钗》遭遇海外恶评以及冲击奥斯卡失利,即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参见肖鹰关于该片的系列文章以及施畅《金陵十三钗中风尘女子的救世神话》(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