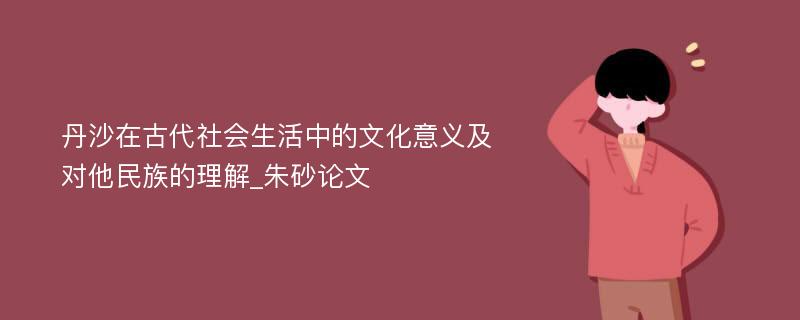
論丹砂在古代社會生活中的文化意義與巴寡婦清其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丹砂论文,其人论文,古代论文,生活中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寡婦清乃先秦一位女杰,但關于其記載則留下不多,《史記·貨殖列傳》:“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雖此寥寥數語,其人之超逸絶倫已躍然紙上。“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可謂位極人望。能得如此恩寵隆渥,全在其富厚之實,而富厚之實根于其數世擅丹穴之利。因此,欲解巴寡婦清其人之謎,必須從剖析丹砂之社會價值入手。 一、丹砂在古代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廣泛應用 《說文》謂丹乃赤石,亦稱朱砂,語曰“近朱者赤”,故一般視丹、朱、赤爲同色,丹成爲朱赤色的代表性概念。丹砂作爲朱赤裝飾色采顔料,在古代社會生活各方面有較廣的用途,亦特顯其社會文化意義。《書·梓材》:“若作梓材,既勤樸斫,惟其塗丹雘。”此以丹砂爲采飾,是說“塗丹雘”乃成器前的最後一道關鍵性工藝。《左傳》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之楹。”①此乃以丹采飾宗廟之柱。魯莊公此舉被斥爲非禮,但意在爲向即將迎娶到來的夫人示誇美之意。《詩·秦風·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顔如渥丹,其君也哉。”按“錦衣狐裘”乃諸侯所受命服,其鮮艷如潤漬之丹赤色采。是丹采用于華貴盛服之飾。《禮記·郊特牲》:“丹漆雕幾,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也。”即祭祀爲“報本反始”,故乘無裝飾的素車,不用丹漆雕飾的華貴車器。由此反襯出丹漆雕飾者的富麗華美,乃當時車器中的極品。《左傳》宣公二年:“從有其皮,丹漆若何?”即丹漆是皮革加工時經要常用到的顔料。《禮記·檀弓上》:“褚幕丹質。”即以丹布爲覆棺的褚幕。《呂氏春秋·離俗覽》:“丹績之衤旬。”即以丹采織績而成的帽纓。《國語·吳語》:“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此乃以朱赤丹采裝飾甲旗兵器。《儀禮·鄉射禮》:“凡畫者,丹質。”鄭注謂射侯“皆畫雲氣于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即以丹采爲射靶裝飾底色。又《大射儀》載射禮于堂上兩楹之間,“若丹若墨”用來畫物。②以上諸例表明,丹砂應用既較廣,又往往用于珍貴華美器物的裝飾,足見其品味之高,至于其被用于丹書之類檔書寫形式,更可見其莊重珍貴的品性。 記載上所謂丹書似有兩義,即其一指用朱筆書寫的文字,其二指書寫載體爲朱赤色。無論如何,此二者均應指具有某種特殊意義的書寫檔。 首先,丹書在記載中被指爲告示某種祥瑞的徵兆。《田俅子》曰:“少昊之時,赤燕一雙,而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③此丹書應爲河洛之類的受命圖書,以下兩則記載可資比較。一曰:“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鄗,止于昌戶。乃拜稽首受,取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也。”又:“季秋之月甲子,有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④此乃周文王受命丹書,與上少昊受丹書可資比較,應同爲河洛受命圖書一類,此乃戰國秦漢時代極盛行的聖王受命神話。與河圖洛書相應,漢代符命興起。如《漢書·王莽傳中》元始五年,“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王莽以白石丹書之符受命,《後漢書·光武帝紀上》記劉秀以“赤伏符”受命。按“赤伏符”與白石丹書同爲符命形式。與此丹書符命相關,東漢時道教興起後,出現諸多硃書道符。⑤丹書形式由此與天命鬼神結緣聯繫。其次,丹書被用爲記載嘉謀聖道。如《大戴禮記·武王踐阼》記師尚父告武王以黄帝、顓頊之道“在丹書”。《越絶書》記越王聞范子之言而善之,“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⑥再次,以朱書文字作爲特殊記載檔的標誌。甲骨文有黑色與紅色的契文,經化驗分析,黑色是一種與黑墨相近的碳化合物,紅色乃是丹砂。⑦山西侯馬出土一批盟書,“盟誓辭文用毛筆書寫,字迹一般爲朱紅色,少數呈黑墨色”⑧。此朱書者應爲盟誓文件。關于盟法,孔穎達認爲,先殺牲于坎,“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孫詒讓駁之,認爲“殺牲歃血,所以申誓,盟辭書于策,非用血爲書也”⑨。按雖非“用血爲書”,但不影響朱筆書盟辭,故侯馬盟書之“‘載書’都用朱筆寫于圭形玉石片上”⑩。可以認爲,用朱筆書寫的盟誓載書應爲丹書的一種。甲骨上的紅色契文與玉石片上的朱書文字,一用于占卜,一用于盟誓,雖用途各异,但都是被用于某種目的的特殊檔形式。 丹書更多是此類被用于具有各種目的或用途的特殊檔形式。《周官·秋官·司約》:“小約劑書于丹圖。”鄭注:“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11)如鄭玄所言,丹圖即丹書,又以鐵券丹書爲丹圖、丹書舊典遺制。據《周官·秋官》,約劑掌于司約,盟約掌于司盟,二者性質相近,都是被用作相互約束的質信形式。按鐵券丹書在記載上多見于漢代,《三輔故事》載:“婁敬曰:臣願爲高車使者持節往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至,曰……汝作丹書鐵券曰: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土盟子然後還。”(12)此乃以“丹書鐵券”用作土地畫界的約定文件。按記載上有所謂“圖書”,如《韓非子·大體》:“不著名于圖書,不録功于盤盂。”故丹圖、丹書爲同類無疑,但以稱丹書爲多,漢代且主要用于封賞功臣。如《漢書·高帝紀下》:“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又其《高惠高後文功臣表》:“申以丹書之信。”此丹書鐵券多被用作皇帝封爵功臣的約信證明檔。此丹書又與刑獄處罰制度有關。《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于丹書。”孔疏:“近世魏律,緣坐配没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13)此丹書遺法以“赤紙爲籍”值得關注,即丹書一方面使用朱書文字,另一方面又用赤色紙張爲檔載體,這證明前文對丹書兩種形式的說法正確。此外,丹書、赤紙所録乃罰没爲奴的罪隸,而囚徒罪隸又服赤衣,如《新序·善謀》:“赤衣塞路”,赤衣又稱赭衣。(14)由丹書、赤紙、赤衣、赭衣證明朱赤色與刑罰罪囚處罰制度相關,相關又有用于書寫罪囚名録的“丹筆”。謝承《後漢書》:“會稽盛吉爲廷尉時,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而决其罪。”(15)《北史·儒林列傳》載劉炫自謂“名不挂于白簡,事不染于丹筆”。(16)按“白簡”乃彈劾章奏,“丹筆”乃罪囚名録。由上述丹書、赤衣及丹筆等概念,證明朱赤色用于刑獄處罰制度,淵源久遠,丹書則在此表現爲一特殊的刑罰處理檔。(17)丹書除上述被用于政治及管理上各具目的、用途的檔形式外,與之相關者尚有丹青一名,它後來成爲史籍代稱。丹青作爲顔料,既可用于作畫,亦可用于書寫,應用亦較廣泛。《說文》:青,“東方色也,木生火,從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青爲東方色,赤爲南方色,木生火猶青生赤的五行相生之必然,是即所謂“丹青之信”。此乃視丹青爲一種顯著鮮明的色采之象。《揚子法言·君子》:“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乃將聖人之言比爲丹青之焕炳昭著。《後漢書·襄楷列傳》李注:“《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主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也。”此謂“丹青之信”與《說文》合,其說丹青亦本五行之說,但已涉及經籍著述的具體樣式。此本爲釋《太平清領書》之裝潢。《襄楷列傳》謂:“其師幹吉于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李注:“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爲介道。首,幖也。目,題目也。”(18)此謂道書裝飾以白素、丹青諸色,以顯其神聖。由于丹青二色寓義更可作爲其內容宗旨標徵,故即可用丹青代稱之。所謂“丹青之信”除裝飾色采的意義外,亦謂其所述內容不僅合乎大道,焕炳可徵,且可用于傳誦、正世、教人。徐鍇曰:“凡遠視之明,莫若丹與青,黑則昧矣。阮籍《咏懷詩》曰:‘丹青著盟誓’,言若丹青之分明也,猶《詩》云‘有若皎日’。”(19)桂馥說:“《東觀漢記》光武語曰:‘明設丹青之信,太元赤石不奪節士之必。’注云:‘石不可奪堅,丹不可奪赤,猶節士之必專也。’”(20)二者皆釋“丹青之信”,亦都有取于丹青焕炳昭明之義,由是後來有“名垂丹青”之語,丹青已用指史籍。由丹書而丹青,又由檔形式而稱史籍,皆與丹砂的書寫功能相關而在文化史上留下其較大的影響意義。 有學者注意到,從新石器時代直到戰國秦漢墓葬的防腐措施中,較多使用朱砂。(21)其實墓葬中使用朱砂的原因之一,應與古人對朱砂安神祛邪屬性的認識有關。如《神農本草經》謂丹砂“養精神,安魂魄”,“殺精魅邪惡鬼”。(22)墓葬中使用朱砂,最重要的應是“安魂魄”,其次是殺魅邪鬼。此外,丹砂朱赤,乃吉利正色,前引《太平經》:“赤者太陽,天之正色。”即以丹砂朱赤爲正色。《廣雅·釋器》:丹,朱,“赤也”;《呂氏春秋·誠廉》:“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古代視丹、朱、赤爲同色,其顔色主要源自顔料丹砂。徐鍇曰:“《山海經》有白丹、黑丹,丹以赤爲主,白、黑皆丹之類,非正丹也。”(23)此謂赤丹之外,還有黑丹、白丹,但以赤丹爲正。《說文》:雘,“善丹也”。段注:“凡采色之善者皆稱雘。蓋本善丹之名移而他施耳,亦猶白丹、青丹、黑丹皆曰丹也。”(24)按其意亦以赤丹爲正丹。故在不同顔色的衆丹之中,朱赤爲丹之正色。丹赤正色又引伸爲凡誠正事物之稱,如赤心、丹心。《周官·秋官·朝士》載外朝之位有“左九棘”、“右九棘”,鄭注:“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25)赤爲正色,故赤心猶丹心,皆謂誠正之心。聽訟斷獄當以正心,故樹棘于外朝以喻示公卿大臣之聽斷獄訟者。《禮記·王制》:“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與此義同。又《春秋元命苞》:“樹棘槐,聽訟于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26)即謂赤心乃誠正之心,其義本丹赤爲正色。周人上赤,故丹赤色受到推重。《左傳》襄公十八年:“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27)《公羊傳》莊公二十五年:日食,“以朱絲營社”,何休注:“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28)朱爲正色,象徵陽,吉利,故祈祭用之。相關周人于行禮祭祀的器服多用朱紅色,《公羊傳》昭公二十五年:“朱幹玉戚以舞大夏。”(29)見于《禮記》者如朱韠、朱幹玉戚、朱幹設錫、朱衣、朱弦、朱紘、朱組纓、朱路等。(30)《檀弓上》:“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31)據注,日出時色赤,故祭祀等大事于日出時,騵與騂俱爲赤色,《郊特牲》:郊祭,“牲用騂,尚赤也”。(32)周人尚赤,故祭祀行禮器服多用朱赤色。這裏的問題是,周人尚赤未必同珍愛丹砂有何直接關係。因爲按古代說法,周人尚赤是按黑白赤三統循環排出來的,故未必同珍愛丹砂有直接關係。但赤色的産生與丹砂作爲顔料間的關係,卻不容完全否認。此外,丹砂受推重必不僅僅因爲其爲赤色,關鍵還是因丹砂社會用途較廣而受各方面珍愛青睞相關,從而亦使其社會文化價值較多被認同。 二、丹砂産地及古代對丹砂生産的管理 以上所述丹砂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廣泛應用,表明其乃重要的物質資源,因此較早起就由國家予以管控,與此相關的第一個措施就是定其爲方貢。如《書·禹貢》記荆州諸貢物之一是“丹”,《周官·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謂荆州“其利丹銀齒革”,與《禹貢》以丹爲貢物合。《逸周書·王會》:“卜人以丹沙。”卜即濮,乃西南之蠻,貢丹砂。(33)《逸周書·伊尹朝獻》記正西昆侖諸國貢物中有丹青,即丹砂與曾青,二者作爲顔料可用于畫繪,前文已述及。《禮記·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即天子在祖廟中舉行大祭,要獻上各地貢物以致敬于先人,其中丹漆、絲纊、竹箭等乃是各地貢物中的代表性物品。丹漆即丹砂與漆。 就産地講,丹砂多産于南方,如此荆州、西南蠻濮人俱以丹砂貢。又《呂氏春秋·求人》記禹“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按丹粟、漆樹俱應爲南方地名,因其地盛産此二物因各以爲名。(34)《荀子·王制》歷數四海方貢物産,將丹幹即丹砂歸于南海。記載中多見丹穴概念,解者多說爲南方地名。如《莊子·讓王》成玄英疏:“丹穴,南山洞也。”《釋文》引《爾雅》“南戴日爲丹穴”證之。(35)《爾雅·釋地》說四極有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智。”即以丹穴稱南方,邢昺疏:“言去中國以南,北戶以北,值日之下,其處名丹穴。”(36)《淮南子·氾論》高誘注即本《爾雅》爲說曰:“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37)按五行說,南方色赤,丹砂赤色,故按五行方位丹砂以産于南方爲宜。記載上多言丹砂産于南方爲宜。記載上多言丹砂産于南方,以丹穴稱南方,顯受此觀念影響。(38)其實丹砂不只産于南方,如《山海經·大荒北經》:“有始州之國,有丹山。”郭璞注:“此山純出丹朱也。”(39)其他如《西山經》、《中山經》俱有“多丹粟”的記載。前引《逸周書·伊尹朝獻》正西昆侖諸國貢物中俱有丹青,皆可證丹砂非皆出南方,但以南方産地爲多而已。 由于丹砂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價值,國家注意對它的生産開采,因此形成相關的生産知識與技術。古書中記載了一些找礦經驗,如《管子·小稱》:“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表明當時已知入山尋礦的道理。礦物藏于山,因此勘山探礦就成爲礦業生産的重要準備前提,這在《山海經》中已有所反映。與《山海經》相關,又有《五藏山經》之名。在《山經》的結尾載禹曰:“天下名山……言其五臧。”以下歷數出銅之山,出鐵之山,繼曰:“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40)此雖托名“禹曰”,但內容所述同《管子·地數》,故管子學派注重工商經濟生産的思想滲透其中。(41)郝懿行如此評說二者關係:“今案自禹曰以下,蓋皆周人相傳舊語,故《管子》援入《地數》篇,而校書者附著《五藏山經》之末。”(42)無論如何,皆可見《五藏山經》與《地數》之間的互通之義,如在有關礦藏知識的記載上,就可以看清此點。郝懿行又引《漢書》“山海天地之藏”釋“此經稱五藏”(43),適可有解于《五藏山經》多記動、植尤其是礦物的寓義,亦可昭示其確有留心“國用”之意,其資源地理與經濟學意義爲之突顯。在《五藏山經》對諸多礦物資源的介紹中,就涉及丹砂。如《南山經》之雞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雘”;《中山經》之堇理之山“其陰多丹雘,多金”。這實際已接觸到丹砂與金之間共生共存的礦脉關係,只是在叙述上尚不如《管子》那樣清楚明白。至《地數》則明確指明如赭與鐵、鉛與銀、磁石與銅金,包括丹砂與金之間的礦脉共生關係。如《地數》:“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又:“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注)金。”此明確道出丹砂與金的礦脉共存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地數》叙述相關的礦脉共存關係後,都要接“此山之見榮者也”一句(44),解者曰:“英猶榮,皆以草木之華榮喻礦蔵之礦苗也。”(45)由此礦苗之說,可見其時采礦經驗及知識之豐富深入。如以《五藏山經》與《地數》相比,後者更顯得深入專業。就是在如此的采礦知識基礎上,形成以丹穴爲主要形式的丹砂生産規模。 據考古發現研究,中國古代的采礦業與采礦方法,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至戰國時代,由于鐵工具的普遍使用,使得采掘與礦井支護技術俱有較大進步,基本已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采礦技術系統。(46)文獻記載中所謂“丹穴”與此相關。《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象丹形”。段注:“采丹之井,《史記》所謂丹穴也。吳、蜀二都賦注皆云出山中,有穴。”(47)可以認爲,丹穴應即有木結構支撑的采丹礦坑,可能爲豎井式,亦可能爲斜井式的礦坑。巴寡婦清世擅丹穴,亦即掌握了較成熟的丹礦生産開采技術。《管子·侈靡》:“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即丹砂已用于流通交换。丹砂生産的商業化交换適應了丹砂在各方面廣泛應用的社會性需求,從而對丹砂生産也起到刺激推動作用。春秋戰國時代包括丹砂在內的商業交换活動的發展,也從商業角度折射出丹砂生産事業在其時的發達。 由于丹砂已成爲國家注意管控的資源,于是形成相應的管理制度,國家府庫負責收藏保管,並分配給官府百工用于生産。由此可見丹砂在當時的國家經濟體系中占有相當地位。《周官·秋官·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徵者,辨其物之美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按金指金錫,石指玉石丹青,都是一些有特殊用途的資源。鄭注謂守藏之府指玉府、內府,按《周官·天官》之《玉府》、《內府》二職,其中收藏有玩好等奢侈品,玉石丹青可派上用場;孫詒讓曰:“丹青並以共石染,故此官令取之也。”(48)丹青用于織物染色之用。《地官·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故《礦人》與《職金》爲官聯,二者分別掌管金石的開采保管,以作爲官府百工的生産原料,其中包括丹砂。《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49)丹漆乃重要應用物資,與金鐵、皮革、筋角等俱由國家府庫保管。這些物資大部份用作軍用、民用及貴族消費品的加工製作。(50)《呂氏春秋·貴信》:“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是丹漆乃用于官府百工織染、製器的生産原料。《呂氏春秋·當染》載“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說明當時在官工業之外,私營織染業亦已存在,其必促進丹砂的生産交换之發展。至少在春秋戰國時代,以丹砂爲染料的染色技術已發展成熟。 中國古代染法主要有草染與石染兩種,草染用草木染料,石染用礦物染料,主要爲赤石、涅石,赤石即丹砂或朱砂。人類最早利用的礦物顔料幾乎都是紅色的。我國最早使用的是赭石,即赤鐵礦;第二種紅色礦物顔料即朱砂。考古發現證明,我國于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已經發現和開始利用朱砂。(51)古代祭服用石染,又稱染玄纁。祭服皆爲玄上纁下,玄纁乃天地之色,故用爲祭服以示天地之尊色。染玄纁之石染法見于《爾雅·釋器》與《考工記·鍾氏》。《鍾氏》曰:“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52)《釋器》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53)所述乃染玄纁祭服的工序方法。即首先須把朱砂與丹秫一起浸泡三個月,再用火炊熾,見丹秫變稠厚,則用于浸染。一入爲縓,再入爲赬,三入爲纁。(54)纁若再入赤汁則爲朱,是朱染四。以上爲染赤的工藝。如若染黑,則用涅而不用朱,即纁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是四入爲紺。若更以紺入黑汁則爲緅,是五入爲緅。紺、緅二色相近,故《論語》有“君子不以紺緅飾”語。更以此緅入黑汁則爲玄,是六入爲玄。更以此玄入黑汁,則七入爲緇。緇與玄二色相近,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此外,染赤與染黑二者在朱湛丹秫、熾之、淳漬的工序方法上相同,朱即朱砂,從可見朱砂乃是染玄纁的基礎性主顔料。(55)朱砂既作爲染玄纁的基礎性顔料,其重要性可知。又經此石染法工藝技術經驗的長期積累,人們也加深了對朱砂性質的認識,從而爲更有效地深度利用朱砂提供了可能。 三、丹砂與古代醫藥及神仙金丹之關係 有著作指出,丹砂即朱砂、辰砂。丹砂以湖南辰州所出最有名,故又稱辰砂。丹本指自然狀態存在的丹砂礦,而朱、硃則指由水銀還原的朱砂,即所謂“銀朱”。《廣雅·釋器》:“水銀謂之澒”,《正字通》:“俗鴻字,道家改作汞。”汞是丹砂(一硫化汞)經鍛燒還原出的水銀。汞之所以稱水銀,是因爲經鍛燒的丹砂,其中的硫磺成爲二氧化硫脫去,還原的汞成液態,有銀白色光澤之故。水銀一詞早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已見。(56)丹砂的此類屬性引起煉丹家的注意,而丹砂在成爲煉丹的重要原料後,因與神仙道教結緣,使其影響格外爲之增大。據現有記載推測,中國煉丹術應起源于戰國時代,最初的煉丹材料主要應與丹砂有關。丹砂最早主要被用作顔料與染料,在製顔料與染料的過程中可能發現其化學性質,因此進一步被用作煉丹材料。煉丹家最早注意的藥物應是丹砂。丹砂即紅色硫化汞,一經加熱便分解,析出汞,汞又極易與硫重新化合生成黑色硫化汞,再經加熱使之升華,就可回復成紅色硫化汞。煉丹家把升華後的紅色硫化汞稱爲還丹,多次反復進行這種加熱分解、化合及升華的過程,所得的紅色硫化汞就被稱爲九轉還丹,又稱神丹。煉丹家比附地誤以爲,人服食還丹就就會象硫化汞那樣脫胎换骨,飛升成仙,長生不老。(57)所以,煉丹術應是在對丹砂生産使用過程中累積經驗的總結而成,但卻是在錯誤觀念主導下被用于醫藥養生的歧途。煉丹術的形成雖借鑒和吸取了諸多的相關知識和技術,但對丹砂的認識和利用卻是關鍵。在外丹術基本形成後,以之爲基礎又形成內丹術。所以,僅此一個丹字,就足以反映出丹砂在煉丹術發展中地位意義之重要。煉丹術首先與當時的醫藥衛生知識有關。較早的醫藥書《神農本草經》,所記諸多藥材中的第一味即上藥丹砂,是丹砂早經被肯定爲諸藥之冠。丹砂本爲石類,故它與金石概念又發生關聯。前引《周官·職金》把金、玉、錫、石、丹、青六者總稱爲金石,金指金、錫,二者本是冶煉青銅的基本原料(58),後來金、錫都是化煉金丹的主要材料。玉、石、丹、青總稱爲石,石又以丹砂爲代表,故段玉裁說:“丹者,石之精,故凡藥物之精者曰丹。”(59)是以又有藥石、丹石之稱。玉、石、丹、青乃煉丹家所注意的煉丹材料,故《周官》所謂金石成爲後來煉丹家看重的金石藥。因爲金石具有堅剛不朽的屬性,故若能煉成金丹,人服食就可如金石一樣堅實長壽,故金石藥備受推重。由煉丹術的主導思想,可見古代醫藥養生知識的歧誤,亦可見天人合一思想在實際運用上的誤導。過分誇大的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內含並不是完全合理的。 以上說明,煉丹術的發明與人們對藥物功能的認識有關,尤其是對金石藥物的認識有關。新石器時代製作石器與製陶業的發達,使人們在選擇陶土與石料的過程中,加深對二者屬性的認識。後來土、石類構成早期藥物學知識的內容,應與此有關。《史記·五帝本紀》:“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此謂黄帝注意對天地自然的經營管理,除農作生産外,對自然界的動、植及水土金石各物,天文星辰,即對與人類生存密切相關的周圍物質環境,無不悉心關注。所謂“土石金玉”代表各種自然礦藏,其中包括後來的金石藥;若按現在對中醫藥史研究的分類,俱可入所謂“礦物藥”。(60)作爲金石藥物類,此土石金玉俱與後來的神仙丹藥相關,而且很早就被注意到,如《山海經》中對土石金玉類就多有記載。(61)對土石金玉屬性的認識亦較早,《管子·侈靡》:“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此論珠玉、金石屬性功能之珍貴。所謂“其化如神”乃指珠玉具有的特殊功能。如古人論神仙往往有入火不熱,入水不濡之說,《莊子》所謂真人就有如此能力。《抱朴子·內篇·仙藥》謂如燒玉爲粉,“服之一年以上,入水不沾,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即服食玉粉就可使人産生上述那樣的神仙功能。故金石珠玉的神异功能似早經爲人認識,故寶藏之。《抱朴子·內篇·仙藥》以珠玉、金石俱爲煉製服餌的仙藥材料,與上寶藏珠玉金石之說互證,說明後來對其作爲長生仙藥性質的認識,源頭頗早。《荀子·王制》:“南海則有……曾青、丹幹。”楊注:“曾青,銅之精,可繪畫及化黄金者……丹幹,丹砂也。”(62)此曾青、丹幹爲玉石藥,與神仙金丹有關,楊注已露此意。《荀子·正論》:“雖珠玉滿體,文綉充棺,黄金充槨,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覲(瑾)以爲實,人猶且莫之抇也。”此乃論盗墓。墓中隨葬丹矸、曾青,楊注謂“言以丹青采畫也”(63),其實此二者外,還有珠玉、黄金等,因此這些隨葬品還有另外的可能用途,即一爲防腐。西漢馬王堆和江陵鳳凰山西漢墓中的尸體不腐,浸泡在紅色的棺液中,棺內有固體朱砂,棺液分析結果,證明棺液就是煉丹作配的“丹砂水”。學者推測,煉丹家從西漢棺液能保存尸體不腐而以服食此液可以不朽的誤會出發,配製出最早的“丹砂水”。(64)那麽,至少朱砂的防腐作用是被當時人認識到的,漢墓中發現的金縷玉衣,證明玉也被認爲是有防腐作用的。其二用珠玉、黄金、丹青、犀象、琅玕等華美之物可裝飾起理想仙境,此金玉諸物亦可提供給仙逝者服食養生之用。如果是這樣,金石珠玉的特异藥用功能,至少在春秋戰國時已爲人認識,並以此爲基礎催生出神仙丹術。 中國古代藥物學原稱本草學。歷來有藥食同源之說,那麽,本草學之始應于神農時代。因爲古謂神農教民農耕,又嘗百草,傳世最早的本草學著作名《神農本草經》亦可爲證。故本草學起源于上古農業種植時代,其濫觴則應于采集時代。早在《山海經》中已記載一些草、木及動物的藥性功能。如其開篇《南山經》之首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華,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饑。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65)此于草、木、獸各記其一,且分別述其性狀及藥性。有些且兼記其味、嗅及藥性,如珠蟞魚,“其味酸甘,食之無癘”;薰草,“臭如蘼蕪,佩之可以已癘”;丹木,“其味如飴,食之不饑”。(66)又十巫升降的靈山乃“百藥爰在”(67),反映出早期巫醫與醫藥的關係,而且所知藥物種類已頗不少。由于《山海經》所記諸動植物,往往言及其藥性、藥味、療效及産地等,已近于古代本草學知識的性質,而且所言亦以草木鳥獸魚蟲等爲主,亦合于本草學知識範圍。(68)如上所言,《山海經》中亦記載了土石金玉等,只是其是否具有藥性尚不甚明確,但石、玉二者略顯特殊。《西山經》密山“其中多白玉……黄帝是食是饗……黄帝乃取密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69)《中山經》休與之山,“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服之不蠱”。(70)二者乃玉、石中的特殊者,顯然具有一定藥性,與前引《管子》寶藏珠玉金石之說亦略相符。土與金亦頗有所記,只是其是否具有藥性亦不甚明確。《西山經》槐江之山的記載有些特殊,其曰:“丘時之水出焉……其上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黄金銀。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71)郭注謂平圃即玄圃,又作縣圃,昆侖縣圃乃仙山,其生青雄黄、琅玕、黄金、玉、丹粟、黄金銀,乃仙山的特殊環境,諸物亦供帝仙神人修煉服餌之用,有類金石丹藥。《史記·封禪書》謂海上神山,“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其物禽獸盡白而黄金銀爲宮闕”,相比之下,縣圃的仙山性質可見。(72) 以《神農本草經》代表的早期藥物學著作,對藥物的認識以草木藥爲主,包括玉石藥,但尚不及金銀。《周官·天官·疾醫》有所謂“五藥”,鄭注說爲草、木、蟲、石、穀。它是早期一般藥物種類的代表,後來因本草學的發展,藥物種類益加豐富,但大抵仍以此五藥爲基礎。孫詒讓曰:“謂動植庶物入藥分者,約有此五類也。《大觀本草》引陶宏景《本草序》附載《本草經》舊目,有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食八類。鄭此注依經五藥約略數之,故與彼不同。”(73)此八藥與《神農本草經》種類相近。(74)但無論五藥、八藥俱無金銀,這或者與金銀入藥主要同煉丹術的發明有關。因爲人工製造金銀是各國煉丹術的目標産品(75),所以,金銀對煉丹術而言極其重要。而且金銀入藥,意在煉成金丹使人堅如金石而長生不老,他們認爲草木藥是不具備如此功能的,葛洪在《抱朴子·內篇》中反復强調此觀念。故金石藥的概念形成應晚于草木藥出現,煉丹家以金銀入藥,就相當于以金石藥概念取代了本草學原有的玉石藥概念。在《神農本草經》中所載與神仙修煉有關的玉石藥,除丹砂外,還可舉出一些,如玉泉,“神仙人臨死服五斤,死三年色不變”;樸消,“輕身神仙”;太一餘糧,久服“飛行千裏神仙”,此皆在“玉石上品十八種”。(76)故由《神農本草經》可證,最早的神仙丹藥乃玉石藥,尚未及金銀。雖然石膽有“成金銀”、空青有“作金”、曾青有“能化金銅”之說(77),但畢竟未將金銀二者正式列于諸藥之內。這至多說明它借鑒了煉丹術,但並未從藥物體系上接納煉丹術。金銀入藥,是煉丹術形成的根本標誌,是另一個神仙丹藥體系。如前所言,人工製造金銀,是世界各國煉丹術的目標産品,故金銀對煉丹術而言至關重要。同時因金銀入藥,使原來的本草學被極大改變修正,形成另外的神仙丹藥體系。(78) 本草學有自己的傳統藥物體系,它不全同于神仙丹藥體系。《博物志》引《神農經》曰:“上藥養命,謂五石之煉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黄除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痛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痛也。違其藥,失其應,即怨天尤人,設鬼神矣。”(79)張華所引《神農經》與今傳《神農本草經》論上中下三藥功效之義相近,唯用語更簡明清楚;但隱然已對神仙思想超出藥性自然的荒謬違理之妄誕,作了批判。此乃立于本草學體系對包括神仙家在內的批判。(80)從《神農本草經》至陶宏景的總結性本草學著作,雖以玉石爲諸藥分類之首,但决不以金銀入藥。馬王堆出土醫書中的藥學分類中雖有礦物藥,但其中金屬類僅有鐵、鍛鐵灰、銅屑、鉛、水銀等幾種,亦决不以金銀入藥。(81)至《抱朴子·內篇·仙藥》則以金銀入藥,曰:“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黄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82)那麽可以認爲,在煉丹術形成之前的本草學著作一般不以金銀入藥;煉丹術形成之後,不但金銀俱入藥,而且以金銀爲丹砂之外的煉丹主藥,由是“黄白”之名大顯,葛洪且專作《黄白》篇論之,其曰:“《神仙經黄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黄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83)總之,煉丹術的出現,引金銀入藥,對古代本草學的認識有很大修正,此可以《抱朴子·內篇·仙藥》所述內容爲代表,它完全反映的是煉丹家的神仙丹藥觀。其實在《神農本草經》關于藥性的一些叙述中,已可見神仙思想,如上舉其玉石藥之例可證,但《神農本草經》並未正式列金銀于諸藥之內。雖在玉石類也混入金屬類礦物藥,如中藥玉石類的水銀、鐵精平,下藥玉石類的鉛丹、粉錫,俱爲金屬類礦物藥。只是此四者藥性品類未列入上藥之內,故亦未如金銀那樣受神仙家之稱揚推重。對金銀的高調重視使用,反映了煉丹家從神仙丹藥角度對本草學的重大修正,此應引起足够關注。 以金銀入藥應與人們對金銀屬性之認識及相關比附思想之出現有關,尤其是它被神仙家接受,並試圖通過煉製金石神丹而予實現的願望,密切相關。如古代記載中對于金石之堅的肯定,《墨子·兼愛下》:“鏤于金石,琢于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84)此言金石之堅足以不朽,故可長存于世並傳遺于後,其影響及于人對自身年命的認識。《韓非子·存韓》極言秦不可攻韓,其中有曰:“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集解》引王先謙釋“與金石相弊”曰:“謂與金石齊壽也。”(85)這表明其時已相信人自身年命可如金石一樣堅固長存。此觀念被神仙家接受,如《抱朴子·內篇·微旨》:“黄老玄聖……淩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86)即神仙家接受此金石之喻,並已把仙聖身體堅實强固與金石爲比,又試圖借助金石丹藥之力助成之。《抱朴子·內篇·仙藥》曰:“玉亦仙藥,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87)玉與石同類,只不過玉爲石中上品。此神仙家認爲,服食金石丹藥則人身可壽如金石而不老。可以說,很大原因是由于金石不朽的屬性,給了神仙長生思想與煉丹術發明以極大啓示。 煉丹家引入金銀藥之後,金石成爲煉製金丹的主材,而且二者關係密不可分。如關于五金與五石有如此記載,《太古土兌經序》:“金、銀、銅、鐵、錫,謂之五石。”《孫真人丹經》:“五金:朱砂、水銀、雄黄、雌黄、硫黄。”(88)按此顯然混金、石二者不分,其所謂“五石”當爲五金,其所謂“五金”當爲五石,其五金中唯水銀爲金屬,餘四者皆爲石。按一般意義,金、石二者有別,如前引《周官·職金》以金、錫爲金,玉、石、丹、青爲石。此混稱金、石而不予詳辨,只能說明金、石二者皆爲煉製金丹不可少的主材,以致二者形成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又與丹砂可煉製黄金的認識密切相關,或者說,丹砂乃煉製黄金以至金丹的基礎性主材。《史記·封禪書》謂“丹沙可化爲黄金”,“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黄金”。(89)顔師古引晋灼曰:“道家言治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黄金。”(90)此皆謂由丹砂煉製黄金。前面講過,煉製九轉還丹,就是對丹砂反復進行加熱分解、化合以及升華的過程而得到;朱砂與黄金練製,乃成仙上法,所謂“朱砂爲金,服之升仙者,上士也”。(91)丹砂與黄金二者亦即金、石在煉丹術中的主材意義,由此益明。而且對金丹神效的認識不必晚至葛洪,在秦漢的方士中已有類似之見。如受鄒衍影響的衆多方士,争相向秦始皇進“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92)所謂“食金飲珠”,就是對金石仙藥神效的認識,較爲久遠。但是一定與練製金丹有聯繫。 煉丹家引入金銀藥,但本草學奠定的丹砂爲諸藥之冠的上藥地位,並未因此受到影響。葛洪以煉得金丹爲成仙要法,然以丹砂作金,直至煉得金丹,俱以丹砂爲本。《抱朴子·內篇·黄白》:“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于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爲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又曰:“《銅柱經》曰:丹砂可爲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93)此並以煉得金丹爲成仙要法,且强調了丹砂與黄金二者的主材重要性,但二者中尤以丹砂爲煉得金丹之本。道家崇尚道法自然,故葛洪還要申言煉成金丹乃“得夫自然之道”,這是道教尊奉道家而不得不然之論;但又謂化作之金“勝于自然”,則乃道教爲神化吹噓金丹術所造作之說。《抱朴子·內篇·金丹》:“長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道引與屈伸也,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爲之實難也。子能作之,可長存也。”(94)此亦申言練得金丹爲得道成仙之要,這是神仙家造作的金丹長生决定論。綜之,由丹砂而成金,再煉成金丹,丹砂在煉丹術中乃重要的基礎性主材,是無可替代的。而且,煉丹術雖引入金銀藥,丹砂的重要性不僅未減,反而更加彰顯它在煉丹術中作爲丹石之藥的價值。《神農本草經》分諸藥爲上藥、中藥、下藥三等,丹砂列爲玉石上藥第一位,至《抱朴子·內篇·仙藥》仍列丹砂爲“仙藥之上者”,排在黄金、白銀之前,這反映了煉丹家的認識。《神農本草經》中對丹砂藥性的描述有曰“能化爲汞”,可證本草學與煉丹家有相通的一方面。可以認爲,《神農本草經》的認識决定了丹砂在煉丹術中的重要地位。這樣,煉丹家雖引入金銀藥,但仍繼承了本草學以丹砂爲諸藥之冠的傳統。丹砂由本草學奠定的這種地位,在煉丹術興起後仍未動搖,那麽,丹砂生産的重要性不僅未降低,反而會因神仙煉丹術的興起而提升;這應是今日認識巴寡婦清數世擅丹穴之利而頗得秦始皇恩寵隆渥原因的樞要所在。 四、關于巴寡婦清名氏身份的考察推測 關于巴寡婦清其人,首先應解决其名氏問題。《史記·貨殖列傳》稱巴寡婦清,又稱“清,寡婦也”,後因“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那麽,她單名清,俗稱巴寡婦清,秦皇爲表彰她而稱“女懷清”。不稱寡婦而稱女,乃予表彰之嘉稱也。《說文》:女,“婦人也”。《公羊傳》隱公二年:“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婦人。”何休注:女,“未離父母之辭”。(95)《集韻》:女,“楚人謂女曰女”(96),即女乃對父母而言的女兒之稱。故一般對婦稱未出嫁者曰女,此乃女的特定意義。但一般而言,女只是男女性別的區別字。此需指出者,名字中見女者,又未必一定是女性。《漢書·古今人表》中見女艾、女志、女妨、女媧、女禄、女潰、女罃、女趫諸人,其中女禄爲顓頊妃,女潰爲陸終妃、女罃爲舜妃、女趫爲禹妃,女志爲鯀妃。其餘女艾、女妨俱爲男子。女艾見《左傳》哀公元年,乃夏少康之臣。女妨爲秦之先人,見《史記·秦本紀》,作女防。最有争議者乃女媧,古書或以爲上古女皇,有學者力辨其非。梁玉繩曰:“至以女媧爲婦人,恐更難信。女媧或國名,或人名,蓋與太昊同族。女當音汝,即如字直讀,亦古人姓名所有。夏女艾,商女鳩、女方,秦之先女防、大夫女父,齊女齊、女寬,鄭堵女父,陳女叔,《公羊傳》子女子,《莊子》女商,《後漢書·方術列傳》魯女生,《魏書·孫道登列傳》宗女,《金史列傳》活女,詎得指爲婦人哉?”(97)是稱名爲女者,未必一定爲女性。女懷清不存在此問題,女應爲尊稱字。秦皇築臺稱之女懷清,有人稱:“懷,疑女之姓氏。”(98)不確。女懷清者,懷女清也。懷者懷慕,女清即寡婦清之尊稱。女既可爲女性區別字,這裏實相當于尊稱,此稱表達了秦皇對其敬重之情,《貨殖列傳》謂“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可證。既稱女懷清,其必有可尊尚懷慕之處,或者以其擅丹砂之利,因可貢獻丹藥燒煉之材與方而合于秦皇神仙長生之願乎? 《史記·貨殖列傳》稱:“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沙、銅器竹木之器。”(99)是巴蜀本多産丹砂,是後巴蜀成爲早期道教發祥地,亦極有可能成爲早期神仙思想與煉丹術興起地區之一。關于道教興起,清楚明白的記載是《後漢書·劉焉袁術呂布列列傳》:張陵“順帝時客于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100)張陵客于蜀學道,那麽蜀地早期道教之興必先于張陵,或可追溯于西漢、東漢交替之際。而蜀地亦自認爲其有較早的神仙與道教人物淵源。如《華陽國志》曰:“王橋升其北山,彭祖家其彭蒙。”又:“大賢彭祖育其山,列仙王喬升其岡。”(101)此王喬與赤松子齊名,見于《淮南子·齊俗》及《泰族》,高注說爲蜀人。(102)赤松子見于《列仙傳》之首,王喬亦應爲古仙人,與周靈王太子晋及《後漢書·方術列傳》王喬似非一人。(103)彭祖多見于經傳記載,《華陽國志》亦曰:“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于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爲殷太史。夫人爲國史,作爲聖則,仙自上世,見稱在昔。”(104)是蜀地自認其有久遠的神仙傳統。關于道教亦然,《華陽國志》:“嚴遵,字君平,成都人也……專精大《易》,耽于《老》、《莊》……著《指歸》,爲道書之宗。”(105)按“道書之宗”乃指《老子指歸》爲道教先驅性著作。(106)是蜀地自以爲有淵源久遠的神仙與道教傳統,對此不宜輕否,亦有助于對巴寡婦清其人歷史的認識。秦始皇對神仙長生的貪戀追慕,决定了巴寡婦清出現在他視域之內的可能。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齊人徐巿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三十二年,“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三十五年,“盧生說始皇曰:‘臣求芝奇仙藥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勿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107)秦始皇如此追慕神仙長生,恰爲擅丹穴之利的巴寡婦清接近他提供了條件。 秦始皇追求神仙長生,與鄒衍在當時的巨大影響相關。《漢書·楚元王傳》:“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更生幼而誦讀,以爲奇,獻之,言黄金可成……吏劾更生鑄僞黄金,繋當死。”(108)此言劉向得淮南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乃言“黄金可成”及“鑄僞黄金”,此皆極值得關注。因爲鄒衍乃秦漢方士不祧之祖,言神仙方術事不可不及。《史記·封禪書》記秦統一,方士們曾奏進其說于秦始皇,其中應包括“重道延命方”,再加上“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劉向從之鑄金之事,那麽,鄒衍與煉丹術之關係可由此加以推定。又據《鹽鐵論·散不足》:“秦始皇覽怪迂,信禨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巿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鹹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109)按所謂“覽怪迂,信禨祥”乃謂鄒衍學說(110),此謂方士受鄒衍影響,以神仙長生說秦始皇,其中謂“仙人食金飲珠”,應與長生金丹有關。(111)故鄒衍與煉丹術之間的因緣聯繫,非全然無據。以上所述說明,鄒衍之時應超出呼吸導引、本草養生諸術,燒煉金丹之術已有某種程度的早期發展。故如煉丹術在秦時已形成,那麽,巴寡婦清更有可能因擅丹穴及煉丹術而獲寵于秦始皇。前文言丹砂從夏以來就以地方貢物的形式向諸侯徵收,可見握有者身份地位之重要。巴寡婦清以私營工商業者的身份擅有丹穴,乃其取得“禮抗萬乘”地位的可致之資,其近于周代諸侯的地位,使其接近秦皇的條件益多一點身份上的可能。加之,她掌握丹砂開采,可提供煉丹材料,並且在煉製丹砂的過程中可能對煉製丹藥的技術有所認識,從而引起秦皇的興趣而寵幸之。綜之,由于其地位身份具有迎合滿足秦皇神仙長生企望的諸種條件,她能得到其賞視眷顧,也就不難理解。 此外,巴寡婦名清,這很可能是她與道家乃至早期道教具有某種關聯的標徵。加之巴蜀是早期道教的重要發源地,煉製服食丹藥又是道徒追求得道成仙的重要手段,所以,從巴寡婦名清結合其地位身份,既可有助于推見到其與道家乃至道教之間的某種關係,又可推見到其與丹藥煉製之間的淵源聯繫。 老子道家以清静無爲爲宗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所謂:“李耳無爲自化,清静自正。”(112)是乃司馬遷對老子宗旨的總括。後《四庫全書總目》評道家本旨時有曰“主于清净自持”(113),即本司馬遷之論。此可證“清”乃道家思想主旨中一極重要概念。此外,相關如太清、三清等乃道家及道教思想中極重要的概念。一般認爲,六朝時期以三洞、四輔概稱道教諸經,總合爲七部,七部乃《道藏》之同義詞。(114)三洞中《洞真經》爲上清派經典,四輔之一爲太清部,此亦可見“清”在道教經典系統中意義之不凡。這需要對道家乃至道教思想體系的系統考察,方可清楚。 清本指元氣之類。如唐代楊倞曰:清,“謂沖和之氣”。(115)《黄帝內經素問》王冰注:“清,勝氣也。”(116)清本指清明元氣。下結合《淮南子》考察相關的“太清”概念。如: 《俶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 《俶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 《精神》:“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于太清”。(117) 以上所謂“太清”,應指清明潔净之太空大氣場,又以喻清静無爲、素樸恬淡之道家理想勝境。又: 《精神》:“以道爲紃,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 《精神》:“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于太清之本而游于忽區之旁。”(118) 大清元氣彌滿于宇宙,太清之本乃指作爲太清元氣本體的道。又: 《本經》:“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寞”。高注:“清,静也。太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暴物也。”(119) 按此太清亦應指太清元氣,用以喻說清静無爲,素樸寂寞的原初上古時代。又: 《道應》:“太清問于無窮,子知道乎……又問于無爲……太清又問于無始……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高注:“太清,元氣之清者也。”(120) 按此乃寓言。太清、無窮、無爲、無始皆可作爲道之屬性特徵,此則乙太清爲無窮、無爲、無始之元首本初。故太清者乃清明潔净之元氣,爲大道之本,宇宙天地之原;只是體一用多,隨物因應,與物變化,難于稱舉模寫。《淮南子》號爲雜家,但其大旨以道家爲主,這在其書內容中有明顯反映。此外,最爲顯著者乃置《原道》爲全書之首,明確揭示了其以道家爲主的思想宗旨。故《淮南子》所揭太清乃道家概念,道教興起後,太清則被納入並成爲道教三清概念之一。 道教中的太清概念與道家有相近的一面。《太上老君開天經》曰:“蓋聞未有天地之間,太清之外,不可稱計,虛無之裏,寂寞無表。”又:“伏羲已前,五經不載,書文不達,唯有老君從天虛空,無億河沙,在太清之外,不可稱計。大道既分,天地以來,開置皇化,轉佐天帝,通流後世,以自記之。”按此“太清之外”乃指天地開闢以前的混沌狀態,相應自天地開闢之後,大道流布,于是人文教化亦始。又:“太初始分別天地,清濁剖判……清氣上升爲天,濁氣下沉爲地。三綱既分,從此始有天地。”(121)此亦言天地開闢,始有人文綱常教化,天地乃由清、濁二氣分別形成。就是說,天地開闢之後,始由清氣彌漫成太清元氣流行播散的宇宙世界。據此可以說,道教的太清概念與上述《淮南子》大體相近,亦同可稱宇宙構成的太清元氣論。至葛洪已把太清說成是剛氣凝聚成的太空,《抱朴子·內篇·雜應》:“上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剛,能勝人也。”(122)後世神仙可騰雲駕霧,行走于空中,多本此說而來。 此外,太清乃三清之一,三清在道教中是一個具有多重意義聯繫的綜合性概念。這要從道教以無、妙一、三元、三氣推究世界及道、道尊、道經以及天地萬物的起源觀念談起。 《道教三洞宗元》曰:“原夫道家,由肇起自無。先垂迹應感,生乎妙一,從乎妙一分爲三元,又從三元變成三氣,又從三氣變生三才。三才既滋,萬物斯備。其三元者,第一混洞太無元,第二赤混太無元,第三冥寂玄通元。從混洞太無元化生天寶君,從赤混太無元化生靈寶君,從冥寂玄通元化生神寶君。大洞之迹,別出爲化主,治在三清境。其三清境者,玉清、上清、太清是也,亦名三天。其三天者,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是也。天寶君治在玉清境,即清微天也,其氣始清。靈寶君治在上清境,即禹餘天也,其氣元黄。神寶君治在太清境,即大赤天也,其氣玄白。故九天生《神章經》云:此三號雖殊,本同一也。此三君各爲教主,即是三洞之尊神也。其三洞者,謂洞真、洞玄、洞神是也。天寶君說十二部經爲洞真教主,靈寶君說十二部經爲洞玄教主,神寶君說十二部經爲洞神教主。故三洞合成三十六部尊經,第一洞真爲大乘,第二洞玄爲中乘,第三洞神爲小乘。從三洞總成七部者,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爲輔經。太玄輔洞真,太平輔洞玄,太清輔洞神,三輔合成三十六部,正一盟威通貫,總成七部,故曰三洞尊文,七部玄教。”又曰:“三氣者,玄、元、始三氣也……又從玄、元、始變生陰、陽、和,又從陰、陽、和變生天、地、人。故《道德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23)按此段文字詳述了道教有關世界及道教體系自身的起源問題,其中可考見三清概念在道教理論中的重要性。首先,其世界創生程式爲:由無而妙一,而三元,而三氣,而三才,于是由天地人而萬物化生具備。其次,三清指三清天,三清境,即道教所謂三十六天中僅次于大羅天的最高天界,乃由大羅天所生玄、元、始三氣化成。三清境指玉清、上清、太清;三清亦名三天,即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玄、元、始三氣分在三天。再次,三元分別化生天寶君、靈寶君、神寶君,三君分主三清境及三天,三君亦各爲教主、三洞尊神。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三君各說一洞真經爲教主。另有四輔,即太玄輔洞真,太平輔洞玄,太清輔洞神,正一通貫三輔而成四;三洞四輔合爲七部,構成道經文獻的宏大系統。由此可見三清概念在道教系統中,具多重意義聯繫的綱紀性根本地位。道教又有“一氣化三清”之說(124),如上引《神章經》亦曰:“此三號雖殊,本同一也。”是三氣分在三天,三氣、三天而三清,其本爲一,一生自道體本元,爲三清本元之氣,相當于所謂“妙一”。總之,由道而氣而三清,總羅天地萬有,三清是道教體系中一個具根本性的概念。 道典《靈寶經》曰:“一氣分爲玄、元、始三氣。”玄、元、始三氣又分別出自空、洞、無,即“玄氣所生出乎空,元氣所生出乎洞,始氣所生出乎無”,此空、洞、無即道本所化,即前文所謂:“原夫道家,由肇起自無。”由無而妙一而三氣,而化生世界萬有,故道經又曰:“故一生二,二生三,三者化生以至九。玄從九反一,乃入道真。氣清成天,滓凝成地,中氣爲和,以成于人。三氣分判,萬化禀生,日月列照,五宿焕明。上三天生于三氣之清,處于無上之上,極乎無極也。”又曰:“天地萬化,自非三氣所育,九氣所導,莫能生也。三氣爲天地之尊,九氣爲萬物之根。故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也。”(125)這段文字襲用了《易緯乾鑿度》的說法,即:“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爲天,濁重下爲地。”(126)是一爲變之始,九爲變之終,終而復始完成一個變化過程,此即所謂“故一生二,二生三,三者化生以至九,玄從九反一,乃入道真”,即經歷一個終始變化過程,産生出天地人及世界萬有。其中道爲化生天地萬物之本原,其化生過程被簡化抽象爲,“一生二,二生三,三者化生以至九”。當由天地萬物溯本求原時,又由天地萬物回歸道本,即“玄從九反一,乃入道真”,“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也”,此“道真”、“天地之極”皆謂萬有所回歸之道本。至于“氣清成天”、“上三天生于三氣之清,處于無上之上,極乎無極也”,不僅將道本說爲清明元氣,而且“三氣之清”所生三天乃宇宙天地的極致。綜之,清乃是道教義理中一個本原性概念;清與三清概念之淵源自應前有所承,至少它們與道家的繼承關係似無可疑,但道教自身對之亦有所豐富發展。至于巴寡婦何以名清,現已無從確知。但由于她擅丹穴之利,又得貪戀追慕神仙長生的秦始皇寵重;加之秦代方士極爲活躍,神仙長生思想彌漫一世,而且煉丹術在當時可能亦已形成,故不由不使人生出她與煉丹術及道教相聯繫的猜想。清、太清、三清在道教中是極重要的概念,那麽,它們是否與巴寡婦名清之間存在某種關聯呢?儘管此事極難考明,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是令人不能不産生,而且又並非完全無此可能的有益猜想。 綜之,巴寡婦清掌握丹砂生産,又得到追求神仙長生的秦始皇的隆渥恩寵,使之極有可能與煉丹術之間有所關聯。巴蜀是古代道教起源的聖地,清、太清、三清是道家以至道教極重要的概念;巴寡婦既然名清,二者間在形式上的這種聯繫是無法完全否認的。雖然由于史料記載關係,無法確切考明其人與道教間的真正聯繫,但又無法完全徹底否認這種聯繫的存在。那麽,這裏不妨提出這樣一個假設,即通過上述考察可以推測,巴寡婦清極有可能是與道家或道教思想存有某種意義關聯之人。如果是這樣,巴寡婦清不僅是古代社會文化史上的一位女杰,而且其人還有助于對秦漢時期早期道教發展史的重新審視。 ①又見《國語·魯語上》。 ②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上册,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010、1034頁。 ③此乃《田俅子》佚文,孫詒讓所輯,見其《墨子間詁》後語,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492頁。 ④[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上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1、370頁。 ⑤參王育成:《文物所見中國古代道符述論》,載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67~301頁。 ⑥袁康、吳平:《越絕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4、96頁。 ⑦錢存訓:《書于竹帛》,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第143頁。 ⑧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盟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1頁。 ⑨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852頁。 ⑩王貴民等:《春秋會要》,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93頁。 (11)《十三經注疏》上冊,第881頁。 (12)趙岐等撰,張澍輯:《三輔决録三輔故事三輔舊事》,而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57~58頁。 (13)《十三經注疏》下冊,第1976頁。 (14)趙仲邑:《新序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275頁。赤衣又稱赭衣,同為罪囚所服,故《漢書·刑法志》及《吾丘壽王傳》俱作“赭衣塞路”,《司馬遷傳》:“衣赭關三木。”三小乃刑具。《尚書大傳·唐傳》:“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赭衣即赤衣。 (15)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91頁。 (16)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766頁。 (17)現代以來公布槍决人犯,皆用紅筆鈎名,當是此制的遺存。 (18)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084頁。 (19)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7頁。 (20)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2頁。 (21)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第290頁。 (22)黄奭輯:《神農本草經》,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頁。 (23)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6頁。 (24)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15頁。 (25)《十三經注疏》上冊,第877頁。三刺乃聽訟斷獄之法,見《周官·秋官·小司寇》、《司刺》。 (26)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90頁。 (27)《十三經注疏》下册,1980年,第1965頁。 (28)同上,第2238頁。 (29)同上,第2328頁。 (30)分別見《玉藻》、《明堂位》、《郊特牲》、《月令》、《樂記》、《禮器》、《祭義》等篇。 (31)《十三經注疏》上冊,第1276頁。 (32)同上,第1452頁。 (33)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19頁。 (34)丹粟即丹砂,《山海經·南山經》記英水“多丹粟”,郭璞注:“細丹沙如粟也。”見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頁。 (35)劉文典:《莊子補正》下冊,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72頁。 (36)《十三經注疏》下册,第2616頁。 (37)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436頁。 (38)《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黄……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十三經注疏》上冊,第918頁。此以五行說天地四方之色。《周官》以上下四方六位立體為宇宙框架,在此基礎上接納平面五行說,二者略异而大體不違。 (39)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24頁。 (40)同上,第179~180頁。 (41)齊自太公、管子以來奠定工商立國的經濟政策,此為管子學派所宗奉。 (42)《山海經校注》,第180頁。 (43)同上。 (44)黎翔鳳:《管子校注》下册,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355、1360頁。 (45)郭沫若:《管子集校》(四),《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1頁。 (46)楊文衡等:《中國科技史話》上冊,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第71~75頁。 (47)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215頁。謂丹穴即采丹井,徐鍇《說文解字繫傳》丹字下已如此說。 (48)《周禮正義》,第2858頁。 (49)又見《呂氏春秋·季春》。或謂《月令》本為《呂氏春秋》十二紀,後被儒家取焉《月令》並收入《禮記》。殊不然。《月令》是典型陰陽家之作,《呂氏春秋》雜取諸家成書,于是取《月令》編入。秦漢之際陰陽家匯入儒家,于是《月令》又入《禮記》。《月令》成書在《呂氏春秋》之前,本焉陰陽家。 (50)《左傳》隱公五年:“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以之與《月令》“五庫之量”相較,可見國家府庫收藏資源之責。《左傳》雖因數及種類之少,未提丹漆,其必在府藏之藏無疑。 (51)聞人軍:《考工記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6頁注②。 (52)《十三經注疏》下冊,第919頁。雖鍾氏曰“染羽”,但染絲、帛、布(葛布、麻布)亦如此。 (53)同上,第2601頁。 (54)孫詒讓曰:“入,謂入染汁而染之,故《爾雅》云三染也。朱染四,黒染三,各有其名。”見《周禮正義》,第3313頁。 (55)以上所述染玄纁的石染法,可參《十三經注疏》上冊卷四十《鍾氏》疏,《周禮正義》卷十六《染入》及卷七十九《鍾氏》疏。 (56)以上見王鳳陽:《古辭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73~74頁。 (57)楊文衡等:《中國科技史話》上冊,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第223頁。 (58)金早期指銅,但漢代尤其是金銀用于煉丹術後,則主要指黄金。 (59)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215頁。 (60)參馬繼興:《出土亡佚古醫籍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77~281頁。 (61)張岩《〈山海經〉與古代社會》對此有叙述,見其書第十二章《〈山經〉水系和土石金玉等內容》,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只是其書未注意到土石金玉與神仙丹藥的關係,且某些分類不甚準確,如謂櫨丹、丹粟為何物不詳,且歸入“土”類。其實櫨丹應即黑丹,丹粟即丹砂。見袁珂:《山海經校注》,第137~138及9頁。故二者不應入“土”類,應入“石”類。 (62)王先謙:《苟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61頁。 (63)《荀子集解》,第339頁。 (64)孟乃昌:《道教與中國煉丹術》,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第154~156頁。 (65)袁珂:《山海經校注》,第1頁。 (66)同上,第106、26、41頁。 (67)同上,第396頁。 (68)《山海經》中關于草木鳥獸蟲魚的此類記載,應源自狩獵采集時代的知識,故可作為推斷《山海經》最早成書及其資料來源的史影根據。 (69)《山海經校注》,第41頁。 (70)同上,第141頁。 (71)同上,第45頁。 (72)《淮南子·地形》記縣圃所在的昆侖虛,“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琁樹、不死之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碧樹、瑤樹在其北……傾宮、旋室、縣圃、凉風、樊桐在昆侖閶闔之中……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凉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縣圃在昆侖仙山系統內,其上有各種珠玉不死之樹及神泉百藥,是以產玉焉主的仙山,故神仙服食當以玉焉主,反映的是以玉石藥焉諸藥之冠的早期本草學系統,與金銀丹藥系統有別,這在下麵論到。如以縣圃與平圃相比,平圃仙藥種類繁多,丹砂、玉、金、銀俱產,與以產玉焉主的縣圃不同,故郭注可商。 (73)《周禮正義》,第328頁。 (74)黄奭輯《神農本草經》分藥物為以下十類:玉石、草、木、人、獸、禽、蟲魚、果、米穀、菜。見黄奭輯:《神農本草經》,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2年。有學者指出陶宏景總結本草學分類方法,分焉以下各類: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食及“有名無實”等。見廖育群:《岐黄醫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2頁。與孫詒讓所言稍异,但可見本草學有自己的藥物傳統體系。 (75)孟乃昌:《道教與中國煉丹術》,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第169頁。 (76)分別見《神農本草經》,第10、16、22頁。 (77)同上,第18、19、20頁。 (78)一般認焉,《神農本草經》乃中國古代第一部本草學專書,但有學者提出,它僅是秦漢臂藥學史上集一家大成之作,不足以體現西漢以前藥物學發展的全貌。見《岐黄醫道》,第151頁。此說有待商榷。 (79)范寧:《博物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8頁。 (80)有著作謂《太平御覽》等書所引《本草經》(或神農)曰:“凡藥上者養命,中藥(者)養性,下藥(者)養病”,更象原始“經”文,而如《神農百草經》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焉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以及相關中藥、下藥的同類內容,則焉“說”文。見《岐黄醫道》,第147頁。結合上《博物志》所引《神農經》,可證《神農本草經》在流傳中應產生過不同抄本,互相在內容文字上有些出入,此區分“經”、“說”文之論,或者與此有關。這在古書流傳中多見,尤其象《神農本草經》這樣出現早且影響大的古書,在傳抄中互多歧异,更無足怪。又《神農本草經》雖有“上藥養命”之說,但非承認長生不死之神仙說。即在神仙家自己,所謂長生不過指延年、增壽而並非可以不死,神仙家縱然荒誕,還不至如此不明事理。《神農本草經》玉泉“神仙人臨死服五斤,死三年色不變”,是對神仙不死說的否定。此雖出自本草家之口,對合理認識神仙長生說是有益的。 (81)《出土亡佚古臂籍研究》,第278頁。 (82)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96頁。 (83)同上,第283頁。按《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已曰:“言神仙黄白之術。”見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145頁。 (84)又見《墨子》之《天志下》、《非命下》、《貴義》、《魯問》、《明鬼下》諸篇。 (85)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4頁。 (86)《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第122頁。 (87)同上,第204頁。 (88)陳國符:《道藏源流續考》,臺北:文明書局,1983年,第208~209頁。轉引自李零:《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年,第344頁。 (89)[日]瀧川資言等:《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92頁。 (90)王先謙:《漢書補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57頁。 (91)《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第287頁。 (92)王利器:《鹽鐵論校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55頁。 (93)《抱朴子內篇校釋》(增釘本),第286、287頁。 (94)同上,第77頁。 (95)《十三經注疏》下冊,第2203頁。 (96)丁度等:《集韻》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45頁。 (97)梁玉繩等:《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513頁。 (98)《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下冊,第2044頁。 (99)同上,第2045頁。 (100)《後漢書》,第2435頁。 (101)劉琳:《華陽國志校注》,成都:巴蜀書社出版,1985年,第273、330頁。 (102)《淮南鴻烈集解》,第361、676頁。 (103)參王叔岷:《列仙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65~68頁。 (104)《華陽國志校注》,第897頁。 (105)同上,第701~702頁。 (106)《華陽國志》記嚴君平事固有取于《漢書·王貢兩龔鮑傳》,但亦略异之,實反映了蜀人對本地先賢的認識。 (107)《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上冊,第164、166、168、169頁。 (108)《漢書》,第1928~1929頁。 (109)《鹽鐵論校注》上冊,第355頁。 (110)《史記·孟子苟卿列傳》謂鄒衍“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因載其襪祥度制”。見《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下冊,第1431頁。 (111)《抱朴子·內篇·仙藥》所列諸仙藥,包括“黄金”、“明珠”,可與此“食金飲珠”相證。 (112)《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下冊,第1300頁。 (113)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241頁。 (114)朱越利:《道經總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83頁。 (115)《苟子集解》,第401頁。 (116)《黄帝內經素問》,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第161頁。 (117)以上分別見于《淮南鴻烈集解》上冊,第51、54、235頁。 (118)同上,第228、229頁。 (119)同上,第244頁。 (120)《淮南鴻烈集解》上册,第378~379頁 (121)張君房:《雲笈七簽》,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第8,9,8頁 (122)《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第275頁 (123)《雲笈七簽》,第10~11頁 (124)任繼愈:《宗教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第69頁。 (125)分別見《雲笈七簽》,第6、6、10、6、6頁。 (126)《緯書集成》上册,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