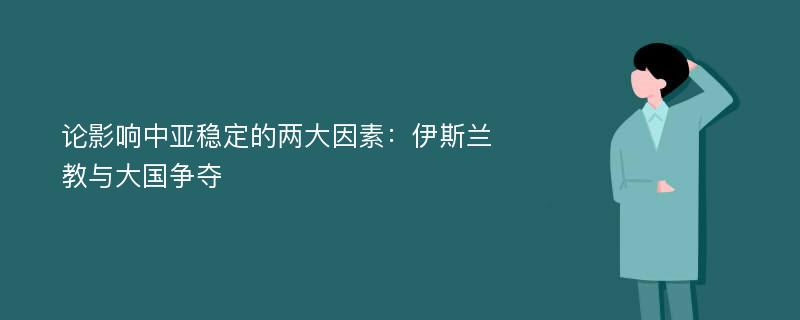
常玢[1]2000年在《论影响中亚稳定的两大因素:伊斯兰教与大国争夺》文中认为论文论述了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传播、发展的历史,以及冷战结束后大国势力在这一 地区的角逐与争夺,侧重论述苏联解体以后中亚伊斯兰教的状况及与地区稳定的关系。 公元七世纪末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势力开始对中亚进行军事进攻、经济掠夺和宗教 传播。伊斯兰教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亚,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中亚地区在历史上 曾经繁荣过,是各种文明交融、汇集、碰撞的舞台。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相当不均衡, 呈由南向北依次减弱状。同典型的近东穆斯林国家相比,中亚伊斯兰教属于区域型,边缘 型,此为其一。其二,由于中亚在地缘上具有“双重边缘性”,处于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 交汇处,相应地也就有“早期伊斯兰化”和“晚期伊斯兰化”的划分。伊斯兰教传入中亚 以后,也有一个民族化和本土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持续了上百年的时间,当伊斯兰教通过 暴力与和平两种方式传播进来以后,便以顽强的生命力迅速蔓延。 沙皇俄国向中亚地区的扩张始于十八世纪中叶,哈萨克草原是首选目标。俄罗斯是东 正教居主导地位的国家,伊斯兰教的地位和势力没有东正教大,但沙俄统治者仍对伊斯兰 教采取了一种宽容、理解甚至是支持的政策。中亚伊斯兰教在当时既保留了其固有的特点, 也有鲜明的地区特色。与此同时,沙俄的统治也给中亚地区带来了欧洲工业文明的讯息, 对伊斯兰教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使中亚的经济结构中出现了某些资本主义因素。为巩固对 中亚的统治,沙俄对伊斯兰教实行控制与利用的两手策略。随着海上航运的开辟,古代丝 绸之路也随之趋于衰落,中亚社会特有的封闭性开始显现。沙俄的崩溃促进了中亚各族人 民的觉醒。从此,中亚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制订了一系列宗教政策。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头十年是处理 民族宗教问题比较谨慎的时期,在中亚采取了一些既有别于俄罗斯又符合中亚实际情况的 宽松政策和措施,甚至沙俄时期某些有关伊斯兰教的规定也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勃列 日涅夫执政后,在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超越阶段思想的指导下,对待宗教的极左倾向十 分严重。尽管长期无神论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宗教的社会作用,但伊斯兰教似乎有更 顽强的生存能力,植根于信教群众心中的宗教信仰仍孕含着巨大的社会潜能。戈尔巴乔夫 于1985年3月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对宗教和宗教组织的严格管理与监督出现失控,长 期受压抑的中亚伊斯兰教呈复苏态势。苏联解体使中亚地区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真空,已 经沉淀为民族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伊斯兰教便乘虚而入,迅速蔓延,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 由于社会历史状况不同,中亚五国伊斯兰教复兴的程度也各有特点,发展是不平衡的。 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较早接受了农耕文明,而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长期从 事游牧生活。由于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各国的时间不同,伊斯兰教对中亚各国的影响表现为 由南向北逐渐减弱,即在中亚,塔、乌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较深,而哈、吉和土受伊斯兰 文化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在哈北部地区,东正教的影响甚至比伊斯兰教的影响还要大。 哈萨克斯坦经常使用“伊斯兰复兴”这个概念,但哈的伊斯兰教从复苏到复兴的过程 也是当地穆斯林群众宗教意识增强和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它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发 展进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哈当代社会文化、宗教的多样性,具有植根于欧亚大陆历史 的深厚渊源。这种多样性的现实,客观上不允许某一种宗教在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乌 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显然更广泛、更活跃、更深刻。伊斯兰因素在乌民众意识中 根深蒂固。由于吉尔吉斯民族长期处于游牧或半游牧状态,伊斯兰教对其影响要比乌和塔 弱。他们似乎保留着拜物教的形式,对伊斯兰教规和仪式的遵守则多限于生活层面上。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在塔吉克族中历久弥新,是回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宗教信仰还仅仅是一种生话方式,尚未成为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的信念。苏联解体以后;土库曼斯坦的国内政治气氛骤然宽松,加之受周边伊斯兰国家影响较深,伊斯十运动亦比较活跃。但同中亚其他国家相比;土库曼斯坦是伊斯兰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中亚各国伊斯兰复兴运动大多停留在文化层面上,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复兴。但是若不加以必要疏导,极有可能对社会稳定和地区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中亚各国独立后,相继颁布宪法和法律,确立了民主、世俗、法制的国家政体和发展万向,为防l卜宗教干预国家社会政治主活提供了怯律保障。由于这一地区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民?
杨鸿玺[2]2010年在《论美国中亚战略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文中研究表明美国中亚战略既存在比较明显的确定性,同时也存在比较明显的不确定性。从宏观和总体看,冷战后美国的中亚战略经历了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历程,呈现一种相对明显的“螺旋式”演进。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国家利益与价值关怀总是相互支持,总体以前者为主,但后者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因总统价值观、美国安全战略进展等因素而有所突出。当然,最终是往往是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占据上风。美国中亚战略目标中始终把安全利益、地缘利益、能源利益等现实和“有形的国家利益”放在主要位置,予以优先考虑和满足,有关软实力和价值观等“无形的国家利益”推进则相对处于次要位置。美国基本的战略目标具有相似性与相对连续性,以确定性为主,不确定性为辅,美国中亚战略的基本路径也有相似性与协调性。但美国决策机制、总统个人倾向、中亚的大国博弈、国际形势变迁与美国实力变化等一系列内外制约因素,也给美国中亚战略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导致不同阶段内美国中亚战略表现出较多差异性、非连贯性乃至矛盾性。美国中亚战略带来多重后果,继而成为带来新不确定性的原因,制约美国中亚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不时使美国政府面临艰难抉择,促使政府不得不进行反思和改进。不同时期、不同的美国政府,其中亚战略体现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不同侧重及其带来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以及实用主义外交本质带来的折中性。相对而言,美国中亚战略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更多与确定性相契合,而其中的价值观外交、多边主义外交等理想主义色彩,则可能面临或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使美国被迫或不断面临安全与民主孰轻孰重的艰难取舍,最终往往倾向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天平。不能轻易判定不同政府的中亚战略是现实主义抑或理想主义,是确定性抑或不确定性,很多时候这种界定是相对的、动态的。
宋延明[3]2010年在《中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原因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对国际政治冲击最大并不断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的伊斯兰教,它以伊斯兰传统文化为底蕴对现代西方文化保持疏离与批判姿态的行为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本文以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传播、发展的历程,以及冷战结束后大国势力在这一地区的角逐与争夺为切入点,重点论述了中亚伊斯兰教的发展状况及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在中亚地区兴起的原因。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党和政府一直以来对宗教和宗教组织的严格管理与监督出现失控,长期受压抑的中亚伊斯兰教呈复苏态势。苏联解体使中亚地区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真空,原有的社会文化结构趋向解体,外部伊斯兰势力乘虚而入,已经沉淀为民族意识重要组成部分的中亚伊斯兰教复兴并迅速发展,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亚地缘政治地位十分重要,美国对中亚地区一直十分关注,苏联解体和中亚五国独立后,美国借口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恐怖活动驻军中亚,并利用所谓民主、人权,推动中亚各国进一步西化,把中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使其成为制约俄罗斯的潜在伙伴的行为,危及到中亚社会稳定和伊斯兰民族因素的存在,因此,大国的争夺促进了中亚伊斯兰教的复兴。此外,苏联解体和中亚五国的独立,原有的社会文化结构趋向解体,转型中的中亚社会贪污腐败层出不穷,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贫富悬殊,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民族问题是伊斯兰教在中亚五国复兴的内在原因。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的历程及特点;第二部分介绍了中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状况、特征;第三部分深入分析了当代伊斯兰教在中亚迅速复兴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期望通过本文的论述和分析,能够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中亚伊斯兰教复兴的原因,对中亚伊斯兰教复兴有一个比较全面认识。
田霞[4]2009年在《苏联时期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状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宗教问题常常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伊斯兰教在中亚五国居民中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已成为中亚当地民族心理素质和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文对苏联时期中亚地区的宗教信仰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当局所实行的宗教政策进行考察和分析,并由此得出结论,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信仰问题是解决好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十月革命前,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不同,中亚伊斯兰教传播和发展是不平衡的,由南向北逐渐减弱。列宁时期,在正确的宗教政策指引下,苏联中亚地区广大穆斯林居民在享受宗教信仰自由、接受无神论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同时,坚决打击敌视和反抗苏维埃政权的反动宗教势力,宗教工作卓有成效。列宁逝世后,苏维埃政府在中亚地区实行的宗教政策发生了变化,通过改革宗教教育、妇女解放、文字改革、关闭伊斯兰教活动场所等一系列措施,开始加强对伊斯兰教的控制。卫国战争时期,由于特殊的国内形势曾经一度放松了对伊斯兰教的控制。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苏联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反宗教运动,利用各种措施不断强化无神论宣传教育。勃列日涅夫在位的18年间,虽然纠正了赫鲁晓夫对宗教的一些偏激做法,但仍未给宗教应有的地位。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党和政府对宗教和宗教组织几十年来一贯采取的严格管理与监督政策出现失控,长期受压抑的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呈现复苏态势,为以后的苏联解体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文章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十月革命前伊斯兰教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介绍了列宁时期采取的宗教政策;第三部分,论述了从列宁逝世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的苏联无神论教育;第四部分,深入分析了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改革以及对伊斯兰教复兴所产生的影响;第五部分,总结了各个时期苏联对伊斯兰教采取不同政策的原因,以及产生的后果及影响。期望通过本文的论述和分析,对我国民族和宗教政策的制定产生些许的借鉴作用。
王彩云[5]2010年在《中亚五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文中研究表明中亚五国大部分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在这里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出现伊斯兰教复兴,与此同时,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与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相结合,对中亚五国及其周边地区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中亚与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接壤,双方不仅有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群体更有大量同源跨国民族的存在,这为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向中国西北地区蔓延提供了可能。因此,本文从历史角度切入对中亚五国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的原因、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西北地区安全的影响进行考察和分析,并由此对中国如何维护与巩固西北边疆安全提出几点思考。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中亚五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从中亚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阶段、沙俄时期中亚伊斯兰教的发展以及苏联时期中亚伊斯兰教的概况三个层面回顾了苏联解体前伊斯兰教在中亚五国的发展历程。第二,分析了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伊斯兰教的发展情况。文章第二部分阐释了中亚五国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与嬗变。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概念进行了阐释,明确指出伊斯兰极端主义不具备宗教属性,它只是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一股异化了的激进社会思潮和政治力量;其二,分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在中亚五国出现的内外原因;最后,介绍了目前在中亚五国境内活动比较频繁的“乌伊运”、“伊斯兰解放党”等几个代表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具体情况。文章第三部分从中亚地区与新疆紧密的地缘联系及存在大量跨国民族的现实入手,解读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在我国西北地区活动的便利条件,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具体分析了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对我国西北地区安全的影响。文章第四部分针对目前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对中国国内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提出了几点应对措施,明确提出中国须在发展国内政治经济的同时,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合作,通过构建国际安全合作机制为我国西部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杨琪[6]2016年在《转型进程中哈萨克斯坦政治认同问题与意识形态建构》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裹挟在独立浪潮中的哈萨克斯坦被迫建国。创建主权国家与重构政治体制,新旧交替的剧烈变迁挑战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而民族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所要面临的政治认同问题首当其冲。解析哈萨克斯坦建构统一国家意识形态应对政治认同问题的举措与路径,总结这个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在变革中将历史自觉与制度理性相结合的成功之道,对于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中亚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顺利转型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与意义。本文侧重于国家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哈萨克斯坦为应对和缓解国内政治认同问题而进行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研究。第一部分详述哈萨克斯坦转型进程中政治认同问题的表现:国家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危及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降低危及民众对政府权威的认同,执政党执政效能不足危及民众对政党合法性的认同;公民的非理性政治参与危及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继而指出“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价值冲突、利益分化与失衡、玉兹传统与社会结构以及多元文化冲突等是造成政治认同问题的原因。第二部分通过阐述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内在的政治逻辑,揭示政治认同问题威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第三部分从树立核心思想、巩固经济发展、发展多元包容的民族文化和拓宽媒体渠道等方面总结哈萨克斯坦缓解政治认同问题、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路径及显著成效,但哈萨克斯坦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仍然面临伊斯兰政治化倾向和西方输出“颜色革命”的现实挑战。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不可能一蹴而就,哈萨克斯坦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对于国家转型和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朝飞[7]2018年在《中国在中亚的软实力外交研究》文中提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在中国东南沿海一直构筑所谓第一和第二岛链,奉行“遏制而不孤立”政策,在东北亚、东海、南海和南亚四大区域构筑反华“C型”包围圈,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是“东亚国家”,但中国更是一个“亚洲国家”,通过陆海联动、东西联通凸显陆海两栖型大国的优势与地位。中亚是中国突破西方封锁和战略围堵的重要突破口,是中国巩固西北边境地区稳定、预防极端组织和思想渗透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和拓展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软实力外交是新时代中国对中亚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政治塑造力、经济影响力和文化亲和力构建意义重大,也与美国、俄罗斯、欧盟和地区大国在中亚的软实力外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软实力外交包括宣介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念、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吸引力、宣传中国模式和建立孔子学院等方式,未来还可以通过发展中国旅游、建立文化代表处、促进中国经典作品外译和促进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与中亚各民族民心相通。中国在中亚的软实力外交是中国特色的大外交,它是实力与影响力、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内宣与外宣相互统筹的结果,也是外交部、文化部、宣传部与商务部等各部委既相互分工又彼此配合的重要实践。主体、客体、路径和话语是新时代中国软实力外交的四大要素。未来,中国在中亚的软实力外交应在主体整合、客体选择、路径创新和话语构建等方面,充分利用好“组合拳”,以民心相通为目标,以“一带一路”为抓手,以政策沟通为保障,以上海合作组织为载体,讲好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民生优先”的故事,增强中国文化的亲和力、中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和中国政治的影响力。
曲鸿渤[8]2017年在《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政策研究》文中指出2010年6月素有“中亚民主岛”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爆发大规模民族冲突,并造成重大的国际影响,其国内民族形势与国家民族政策已然成为近年国内外政治学和民族学相关领域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于1991年8月31日正式脱离苏联宣布独立。但其国内“以吉尔吉斯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并存”的民族关系格局却是早在苏联时期就已形成并确立的。独立之初的吉尔吉斯斯坦继承了其在苏联时期的部分民族问题,这些问题对其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造成一定消极影响。随后在其26年的国家建设过程中,吉尔吉斯斯坦为了应对苏联遗留的民族问题,对苏联时期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进行了反思,同时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民族理论及经验,逐步确定了本国的民族政策原则及相关措施。然而,在这些新的民族政策实行过程中,又暴露出一些新的民族问题。本文首先对民族政策研究的一般理论进行梳理,然后从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沿革入手,通过对苏联时期促使吉尔吉斯成为多民族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分析,阐述其“以吉尔吉斯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并存”的民族关系的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关系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类研究,并分析了当前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关系形势。随后对其独立后的民族政策的主要原则和具体措施进行了概述。最后,从政策效果角度对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政策做出评价,并提出了本人的几点相关思考。
刘志强[9]2011年在《中亚五国宗教与民族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中亚五国独立后,随着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这一地区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宗教极端势力也趁机扩大自己的影响,甚至利用恐怖手段来强迫当地居民接受自己的主张。宗教和民族问题日益成为影响该地区政治形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中亚与中国之间跨国民族和跨国宗教的存在,使中亚地区的宗教和民族问题也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对中亚五国宗教和民族的历史考察,从宗教与民族的关系角度分析中亚五国的宗教和民族问题,探讨宗教与民族问题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以及这些问题的演变趋势。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追述了历史上中亚地区曾经存在的民族与宗教并且介绍了中亚五国宗教与民族的现状。这部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从历史角度回顾了中亚五国宗教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其次,从中亚五国伊斯兰教的复兴和中亚五国的民族与宗教状况两个方面介绍了宗教与民族在中亚五国的分布现状。由此,总结得出对中亚五国社会生活和民族、宗教形势影响最大的二种宗教和六个民族,即伊斯兰教与东正教和中亚的五个主体民族与俄罗斯族。文章第二部分从宗教与民族的关系角度论述了中亚五国现存的宗教和民族问题。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通过分析宗教与民族的区别和联系论述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介绍了中亚五国存在和面临的’宗教与民族问题,并试图从宗教与民族的关系角度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最后,论述了中亚五国宗教和民族的互动影响。在文章第三部分,先是分析了宗教与民族问题对中亚五国及周边地区的影响,接着论述了中亚与中国之间的跨国宗教和跨国民族问题,文章最后探讨了宗教和民族问题的演变趋势。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和分析,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中亚五国存在和面临的宗教与民族问题;同时也期望本文或许能对我国宗教和民族政策的制定产生些许的借鉴作用。
黄立言[10]2009年在《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及对中国的影响》文中认为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的国际战略地位凸显。不仅有其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价值,也具有丰富的资源价值。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的发展并非是一厢情愿的,而是彼此之间都有着各自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利益的需要,因此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的发展是两者彼此利益推动的结果。正是因为两国各自的利益需求,促使着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关系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在政治关系方面,两国从建交到民主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逐步升温;在经济关系方面,两国贸易规模逐渐扩大,能源合作日益紧密;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不仅自身与哈萨克斯坦建立各种关系,还以北约为依托与哈萨克斯坦发展军事安全关系。通过美国政府为发展与哈萨克斯坦关系所做的一系列实际的工作,为未来发展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国关系将会长期持续稳定地发展。但是在两国关系的发展的过程中,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不仅会受到地缘、大国力量、伊斯兰力量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美国和哈萨克斯坦各自内部因素的影响。对于中国,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的持续发展必然会对中国的边境安全环境产生不确定因素、对中哈关系的发展产生双重的影响、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而中国面对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当积极应对,加强与哈萨克斯坦的对外交流,提高中国自身的影响力;妥善处理中美在哈萨克斯坦的利益冲突;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利用地缘优势;加强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关系。
参考文献:
[1]. 论影响中亚稳定的两大因素:伊斯兰教与大国争夺[D]. 常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2]. 论美国中亚战略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D]. 杨鸿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3]. 中亚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原因新论[D]. 宋延明.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0
[4]. 苏联时期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状况研究[D]. 田霞.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9
[5]. 中亚五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D]. 王彩云.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0
[6]. 转型进程中哈萨克斯坦政治认同问题与意识形态建构[D]. 杨琪. 新疆师范大学. 2016
[7]. 中国在中亚的软实力外交研究[D]. 李朝飞.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8]. 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政策研究[D]. 曲鸿渤. 黑龙江大学. 2017
[9]. 中亚五国宗教与民族的关系研究[D]. 刘志强.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1
[10]. 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关系及对中国的影响[D]. 黄立言. 湘潭大学. 2009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民族问题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美国宗教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哈萨克斯坦总统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国家软实力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苏联解体论文; 宗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