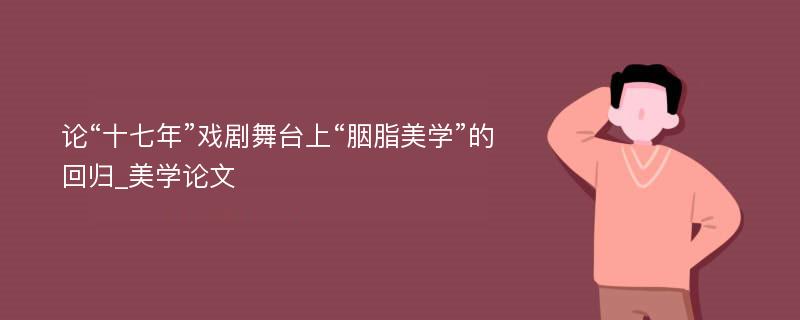
论“十七年”话剧舞台上“胭脂美学”的回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胭脂论文,话剧论文,美学论文,舞台上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0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549(2014)04-0104-09 满面红光的工农兵形象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油画、宣传招贴、年画、连环画、戏剧、电影等大众媒介中常见的视觉符号。只需稍稍关注中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政治波普”,以及世界范围内对那段历史的戏仿,便可感受到这一形象深入人心的程度。这种占据人物面部的“胭脂美学”,俨然成了日后人们眼中“毛时代”的标志。在话剧舞台上,“胭脂美学”滥觞于“十七年”期间(1949—1966),并经历了一个逐步定型的过程。马克思说:“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1](P.107)话剧舞台上人物面部的妆容便是这样一种表征着“最一般的抽象”的普遍“具体”,往往能透露出一个时代的文艺倾向,乃至时代本身的真相。可以说,它是话剧舞台艺术对时代氛围的一种具体回应。令人饶有兴味的是,在“十七年”期间,这种回应是以一种“美学复兴”的特殊方式进行的,涉及中国话剧舞台艺术风格的创生与嬗变,并折射出中国社会文化自近代以来的变迁轨迹,故特别值得考察。 要了解某种造型美学的实质,免不了考察其物质基础与技术规程。众所周知,在话剧先行者的推广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正规剧场的舞台上,演员脸颊上的妆主要使用戏剧油彩。戏剧油彩的优点有二:一是色彩变化多,用它打底子可以适应各种照明环境,从而能实现各种剧本规定的肤色,可谓淡妆浓抹总相宜;二是塑形效果细致入微,可以精细地勾勒脸部的轮廓,分明暗,造凹凸,从而获得一种立体化的视觉效果。有时为了获得幅度更大的易容效果,还需辅之塑形功能更强的“鼻油灰”。顾名思义,鼻油灰主要用于改变鼻型,偶尔也施用于其他部位,比如耳廓、下巴与颧骨。可以说,戏剧油彩擅长通过立体化的外部塑形,突出人物的个性。 但是,在“十七年”期间,本该以立体的写实妆为擅长的戏剧油彩,却投入了“胭脂美学”的怀抱,不断回避自己的造型潜力,走向了平面化。当然,戏剧油彩的变味非一日之寒,变味的方式也有讲究。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演出中,我们看到的是戏剧油彩妆出神入化的写实能力,择其荦荦大者,主要有两端:首先是经典剧本中复杂角色的塑造。“北京人艺”等演剧机构贡献的《茶馆》《龙须沟》等剧目,其人物造型在历史性与艺术性上成就极高,堪称“十七年”话剧写实美学的巅峰。在这些剧目中,人物的处境与经历往往较复杂,心迹亦曲传不易。面颊的外部造型既要刻画出岁月与环境的印记(如由青春至衰老、由腾达至衰颓等),也要透露性格的幽微(如亦正亦邪、勤俭混合着圆滑等)。其次,知名人物的肖像妆。这种妆型往往需要再现某位为人所熟知的人物的形象,对面部造型的写实性要求甚高。如“十七年”中被许多剧院上演的名剧《带枪的人》[2](P.35)与《悲壮的颂歌》中的列宁造型,[3]以及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于鲁迅诞生80周年纪念会期间上演的《呐喊自序》与《为了忘却的纪念》。①后者乃片段演出,主要是展示人物形象,颇有点时下流行的“戏装扮演”(Costume Play,略写成Cosplay;日文写作「コスプレ」)的意思。这两种需要发挥戏剧油彩写实功能的妆型基本属于“易容化妆”,需要大幅度改变演员的本来面目(肤色、面部的肌肉、骨骼的走向与结构等),当然,造型的最终完成还需辅之其他造型手段,如假发、服饰、小道具等。 被“胭脂美学”重点渗透的是“着重化妆法”。“十七年”期间数量众多的现当代题材剧目多使用“着重化妆法”,对演员本色进行微调,其中戏剧油彩起到的主要是修饰作用,即敷好肤底色后,围绕演员本人的五官、脸型细笔勾勒。“胭脂美学”的渗透通过一道化妆工序来实现,即敷好一层肤底色后,用红色或橘色系的化妆颜料平涂脸颊,俗称“拍颊上红”[4](P.19)、“打红”[5](P.28)、“腮红”[6](P.16)或“打胭脂”[7](P.16)。其中,“拍”与“打”指上妆的手法;“颊”与“腮”是上妆的位置;“红”即所用颜料的色相。需要说明的是,“打胭脂”不一定真的是用胭脂上红。一般来说,着粉妆时才单用胭脂,且为面脂(施于面部,而不是口脂,后者施于嘴唇)。胭脂,又作燕支、燕脂、臙脂等,由红蓝花、茜草、紫矿等诸种植物制成,过去也是妇女的日常化妆品。晚近以来,本土的胭脂逐渐被“洋胭脂”(一种类似土胭脂的盒装颜料)代替。据国画家于非闇的考察,1955年前后土胭脂已经很难找到了,当时能见到的各地土胭脂,其性状也有所不同:“广东的胭脂饼,它的颜色近于紫,是紫矿制成的……福建的胭脂饼、杭州的棉花胭脂,这都是用红蓝草、茜草制成的……甘肃、新疆和西南边疆等地的胭脂格外地红”。[8](PP.14-15)而“十七年”舞台上常用的为一种红色与金黄色的干胭脂。按照“十七年”的演出惯例,只有露天演出或游行演出等场合,粉妆才是第一选择,它有着简便、经济的优点。但粉妆的限制也不少,“光影与色彩的变化少,色彩也单一,不及油彩化装那样理想”。[9](PP.34-35)因此,戏剧油彩在很多场合被用来代替胭脂“拍颊上红”。戏剧油彩的色调有很多标号,色谱较广,模仿起色彩单调的胭脂来,绰绰有余。总之,打胭脂或平面化使用戏剧油彩,起到的基本是一种平面装饰效果,在外形上只能显示戏剧人物的一般化特征。 “十七年”话剧舞台上“胭脂美学”的施用,存在一个逐步定型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依托戏剧油彩的写实妆仍是各大话剧院团的主导风格。一些来华讲授专业课的苏联专家所传授的化妆术也是立体写实的法子。如苏联专家苏赫米娜在《戏剧报》上连载5期的教程《舞台化妆》。②本土的一些造型师还能立足于戏剧油彩的写实美学标准,居高临下地批评粗陋的“胭脂美学”。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汇演中,湖南省话剧团演出的《雷雨》中的某些人物造型便饱受诟病。如扮演周朴园的演员“在粉色的面孔上涂了两团胭脂”,被讥为“像京剧中的花旦”。[10](P.1114)但随着“胭脂美学”的普及与改进,这种批评就再难看到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胭脂美学”在摸索中与类型化的写实化妆术实现了无缝对接。翻检“十七年”流行的化妆教程,我们发现书中总会辟出专门的章节,谈如何在舞台上表现男女、老幼、胖瘦的化妆术。一般情况下,这些教程并不能告诉化妆新手们在面对剧本中某一具体人物时该如何合理操作,但总有一个环节是少不了的,那就是“上红”。教程中往往按不同的人物类型分出不同的“上红”惯例,如中年的腮红“应该比青年装的胭脂略暗一些(红中可加点棕肤色)”;儿童的“胭脂比青年装更突出,红的重点不是在颧骨上,而是靠下,在嘴角外的面颊上”;[6](P.22)“脸小的人,就需要将红抹大一点……若脸宽而短,就把红打得近鼻根……若脸长,而要短,那就把腮红抹高一点”。[5](P.28)如此这般,人物在满面红光之中又生出些区别。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伪写实,一种拟真。到了“文革”期间,“胭脂美学”最终定于一尊,化妆师李秀雯多年后回忆起那段历史,仍心有余悸:“由于受‘三突出’谬论的影响,用的都是橘红色底彩,似乎正面人物都是红光满面,粗眉大眼……粉碎‘四人帮’后,首先突破红色面具的是话剧《丹心谱》,用淡淡的油彩勾画人物,恢复了我们十几年来的老传统,既有鲜明性格又真实可信。”[11](P.500)李秀雯说的是当时水准最高的“北京人艺”的情况,在那些写实传统较弱的地方剧院,“红色面具”的现象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已然出现,而最终的落脚点正是工农兵这类角色。“胭脂美学”在“十七年”的兴起是在50年代后期,如1958年的《把一切献给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烈火雄心》(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飞出地球去》(中国儿童剧院)、《枪》(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青春之歌》(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1959年的《革命的一家》(中国儿童剧院)、《地下少先队员》(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草原上的风暴》(青海省话剧团)、《南海战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广州文艺代表队)、《红旗谱》(河北省话剧团)、《槐树庄》(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话剧团)、《八一风暴》(江西省话剧团)、《降龙伏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高潮则是在“文革”前的一两年,如1964年的《龙江颂》(福建省话剧团)、《千万不要忘记》(上海青年话剧团)、《丰收之后》(山东省话剧团)、《激流勇进》(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小足球队》(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1965年的《代代红》(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女飞行员》(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战红图》(河北省话剧团)、《英雄工兵》(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话剧团)、《比翼高飞》(重庆市话剧团)、《电闪雷鸣》(湖南省话剧团)。③ 需要注意的是,化妆术的这种拟真特性与“胭脂美学”所服务的扁平化的剧本是相侔的。可以说,正是在这种类型化的剧本的召唤下,“胭脂美学”才现身于话剧舞台的。陈大悲当年在反对文明戏的“脸谱”时,就曾明白地阐释过剧本与化妆术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浪漫派时代,西洋舞台上的化妆是容易的……演剧人都有许多“派别”(Types)的成例可援,各派有各派的特殊化妆法。这种分派的化妆法虽不与我们现在的“文明戏”完全相同,但是大致却相仿佛……“文明戏”很富浪漫的色彩……自从西洋戏剧受到易卜生底(的)影响之后编著剧本的技术已不像从前那样容易。现代剧本中的人物各有各的个性。编剧人的第一资格就是能描写各个人底(的)个性。演剧人的第一资格就是能扮演各个人底(的)个性。因为扮演要恰恰与个人底(的)个性相合,所以演作的技术较之从前难上好几倍。[12](P.102) 熟悉中国话剧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话剧在早期主要就是受了西方浪漫派佳构剧与易卜生写实戏剧的影响,尽管在借鉴的过程中存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但对剧本中人物个性的日益重视是有目共睹的事实。20世纪30年代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陆续出世(如《雷雨》《上海屋檐下》等),此时的剧本已经可以提携舞台艺术,其艺术抱负与能量已非“脸谱”所能承载。故“化妆术”随剧本的改进,逐渐走上了写实一途。到了“十七年”期间,不但那种易卜生式的剧本变得罕见,连曾提倡或接受易卜生主义的文化人也成了被批判或改造的对象。④在激进思潮下,剧本创作每况愈下,大半集中于扁平化的工农兵题材,“胭脂美学”应运而生。 “十七年”话剧舞台上片面化的“胭脂美学”与传统舞台上的程式美学异曲同工。可以说,传统戏曲与文明戏中的胭脂妆是“十七年”话剧“胭脂美学”的先驱。胭脂妆在传统戏曲中常施用在旦角的面部。在清末的一些戏曲画或剧照中犹可一睹这些妆容,如沈蓉圃的戏曲人物画《同光十三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治、光绪两朝的旦角其面部便抹着一层淡淡的水粉与胭脂。[13](P.282)水粉,即搽胭脂前敷的一层铅粉。铅粉又名胡粉、官粉、铅华、银白。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铅粉也是妇女们常用的化妆品。[8](P.11)尽管用铅粉做底色时,在色彩上比戏剧油彩单调,且在舞台灯光下“惨白得可怕”,[12](P.100)但在上妆的工序上,戏曲旦角的胭脂妆与“十七年”间“胭脂美学”还是有相通之处——也是先打一层底色,再涂抹色调明艳的其他颜料。这一事实以及上文提到的舞台化妆术的当代变迁,提示我们:物质材料(如化妆品)的更替,不一定能引起某种既成美学的即时改变,反之,旧美学有时也可能驯化新材料,以巩固自身的地位,如“胭脂美学”对“洋胭脂”的兼容,以及“十七年”时期对戏剧油彩的平面化改造。 文明戏与“爱美剧”基本继承了传统戏曲的“胭脂美学”。当时的从业者对近代话剧的化妆术还比较陌生,不得不借鉴传统戏曲的做法。剧评人对这一“遗形物”时有批评。1924年,《少奶奶的扇子》的上演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看了(少奶奶的扇子)以后》一文,对此剧赞誉有加: 表演方面,我只能说一个“好”字,因为在现今中国这种鬼怪妖狐出现的艺术界,戏剧协社诸君的艺能虽然不免还有许多缺憾,但大体上总要算是难得再有的了!(北京陈大悲一派究竟如何,我未见过——无从与之比较。在长江上下游,则这出《少奶奶的扇子》的确是从春柳社以来所未见过的。)[14] 尽管如此,剧评人还是指出了几处令他“引为憾”的缺点,其中一个就是“打胭脂”,他认为此法“不脱旧戏的做作”。[14]《少奶奶的扇子》历来被看成中国话剧舞台艺术,脱离旧戏做派,走上现代戏剧正途的转折之作:一是洪深将导演制首次贯彻到中国的话剧舞台上;二是舞台上首次搭建起了写实的真门真窗的箱式硬景,并使用了正规的照明。口5]此剧演出中浮现的诸多现代性因素,更衬托了“胭脂美学”的顽固,它就像一个幽灵,盘踞在早期话剧的舞台上,驱之不散。 概而言之,在大多数中国话剧的先驱者眼中,平面化的“胭脂美学”对当时的话剧艺术有两点戮害:一是不自然,过于突出舞台的假定性,如上文提到的“做作”;二是破坏舞台人物预先设定的性格与气质。对于这点,文明戏时期的剧评人深有体会:“常见今之新剧家化装大名鼎鼎之小生,其面上所涂之粉厚如石灰,连(脸)额所抹之脂红如猪血,至雄而雌之,贱物安能当‘温文尔雅’四字。”[16]可见,在部分早期话剧家与观众眼中,“胭脂美学”已经与经验真实(台下生活中的人的自然状态)背道而驰了。 “十七年”话剧舞台上的“胭脂美学”,终极目的是为了颠倒经验真实。其实,“十七年”话剧舞台对“胭脂美学”怀着更大的期待,藏着更深的用意。对其隐匿的终极目的之把握,要在其基本功能上着眼。胭脂妆一般用来装饰或者说美化,赋予舞台上的人物一种健康的“好气色”。这在“十七年”之前,也是话剧舞台上的常识。如袁牧之的《戏剧化妆术》在讲到脸颊化妆时,说:“搽胭脂是有两种用意:一种是表示健康有血色,还有一种是表示化过装的……男子需要搽胭脂,大概是前一个用意,除非是在特别情形之下。”[17](P.67)在“十七年”期间,这种“好气色”第一次与“政治正确”绑定在一起。“好气色”逐渐被“工农兵”角色垄断,并设置了“气色不好”的人物序列——“地富反右坏”,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的格局。在“胭脂美学”支配的话剧舞台上,盛行的是这样的做法:“无论什么题材的演出,总是将剧中角色首先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在化妆中把暖色和浓眉大眼等用在英雄人物脸上,把冷色和小眼细眉用在所谓反面人物脸上。甚至将化妆油彩分为相对固定的号码,在化妆时,正面人物直接用某号油彩,反面人物用几号油彩就行了”。[18](P.75)当然,这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身份的视觉渲染。但我们仔细考察“胭脂美学”所服务的这些人物与情境就会发现,“胭脂美学”起到的作用,远不止身份标识那么简单:在满面红光中,本应该营养不良、面有菜色的被剥削者变得身强体壮、气血充足;本应是营养充足的剥削者却一个个尖嘴猴腮,弯腰弓背,面色如土(如《红旗谱》等);本应是天真的活泼的少年儿童,却个个化着与成人一般的胭脂妆,变成了小大人(如《枪》《地下少先队员》等);娇弱的女性、男性伤病员也在胭脂妆的修饰下变得战斗力十足(如《战斗的青春》等),⑤这种种现象都是对生活常识的颠倒。尽管戏剧艺术中的面具与脸谱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但一般情形下,它们造出的形象,至多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真实相去甚远或若即若离,极少有像“十七年”话剧舞台上那样,对经验真实(生活常识)整个来了个颠倒。 “胭脂美学”的当代复兴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吊诡,不仅与中国当代话剧曾师法的苏联戏剧的写实经验迥异,也是对前50年话剧舞台美术总体趋向的反动。那么,其回潮的深层原因何在?问题的答案恐怕还要到历史中去找寻。 当年对新剧舞台上“胭脂美学”等脸谱化做派的批评中,陈大悲的观点最深入。他较早点破了问题的实质,相关的知识积累也使得他能够从世界戏剧史的潮流着眼来看问题。他将传统戏曲,以及受传统戏曲影响的文明戏、“爱美剧”中的非写实的化妆,一概称之为“脸谱”,与西洋话剧舞台上正规的“化妆术”相区别: 据我所知,实在是因为许多人都把化妆术看得太轻了。有许多人竟把化妆术当作西洋式的“勾脸法”,他们以为新剧与旧剧底(的)分别犹如土货与洋货底(的)分别一样。所以要学新剧的化妆术,只须与旧剧伶人一样熟记了一种新式的“脸谱”就得。岂知西洋戏剧的艺术与自然科学人生科学同时并进,面具式的“脸谱”早已成了戏剧历史中的一种传说,即有采用的也只是马戏和杂戏场里的丑角;现代舞台上的角色久已不能成为几种刻板的容貌所限制。[12](P.96) 陈大悲对西洋戏剧“化妆术”的文化定性(科学的)不无道理。陈大悲将此“化妆术”概括为:“用不害皮肤的各种彩色油彩及其他附属品在演者的皮肤(不被服装遮掩的部分)上,施行合理的妆饰法,使演者易于表现各种戏剧的情绪”。[12](PP.96-97)在陈大悲看来,这种“化妆术”的“科学”性在于“与画学、心理学、哲学、生理学、解剖学、光学等均有密切关系”;[12](P.97)在戏剧舞台上的优势则在于能呼应“剧中个人底(的)个性及心底的变幻”,从而“在表现方面帮助演者”。[12](P.95) 陈大悲的观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如火如荼的“科玄论战”。如果说话剧的化妆属于“科学”的范畴,那么旧戏的化妆可以说是“玄学”体系的一部分。董健先生《20世纪中国戏剧:脸谱的消解与重构》[19]一文立足启蒙文化,试图直面“脸谱”的玄学本质。他将戏剧文化中的“脸谱现象”(包括作为妆容的脸谱)看成是一种历史绵延体——延宕至今的“巫文化”,并以一种反思的立场看待之。这对于揭示事物的真相十分有益。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曾这样概括原型研究的伦理:“在一个表面上‘祛魅’的文化里……不把神话当一回事,事实上只会使我们对这个共同的世界的认识愈加浅薄,同时也是把这个问题弃权给那些与它没有任何批评距离的人,他们并不是将神话当作一种历史现象,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不容置疑,长期存在的神秘事物。”[20](P.153)显然,在“批评距离”这个问题上,董先生超越了国粹派的盲目崇拜。需要补充的是:首先,“面具式的‘脸谱’”在世界戏剧舞台上是否如陈大悲所认定的那样“已过时”,是值得商榷的。其实,在世界范围内,脸谱与面具都是比较出彩的剧场手法,观众也喜闻乐见,只是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在演出新剧时,它必须给更符合新剧气质的“科学”(写实)“化妆术”让路。其次,戏剧舞台上出现的作为艺术手法的“脸谱”或“面具”或许是“巫文化”的产物,但这种形式一旦成熟并产生过良好的艺术效果后,它们便自动成了舞台艺术“样式库”中的一个备选项。作为艺术手法的脸谱或面具,与启蒙文化并不必然矛盾,也不固定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决定它们文化属性的因素主要是日后的使用“语境”。因此,上文所提的“十七年”时期“胭脂美学”回潮的深层原因这个问题,也可以转换一种问法:“十七年”话剧舞台上“胭脂美学”的施用,其所处的“语境”是什么? 传统戏曲中的化妆,以及脱胎其中的“胭脂美学”,都或多或少臣服于一种成为惯习的“秩序”(包括“禁忌”),隶属于某种“符号/象征性的意义共同体”(symbolic universe)[21](PP.92,108)。关于后面一点,从胭脂与铅粉等颜料在传统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广泛应用,亦可窥之一斑——它们既是戏曲舞台化装中的常备颜料,也是国画以及妇女日常化妆中的基本颜料。众所周知,旧戏演出(传统戏曲及文明戏)一般要求人物在装扮上“一看便知”其谁,戏曲在服装上的要求更严格,有“宁穿破不穿错”的说法。因此,人物造型的自由创造,绝无可能。可以说,在成熟的旧戏舞台上,服饰与化装等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固定的。旧戏中的角色制更是怂恿了这种舞台表达,为其发育提供了空间。有些学者从“特殊的性格化”角度阐释戏曲的妆容的定型化,[22](PP.136-140)无异于缘木求鱼。用时髦的话说,是一种美学上的“自我殖民化”,被话剧舞台美学所“殖民”。 也许倒过来看,更容易把握问题的实质。其实,这类符号在表达上的清晰性,更依赖舞台上的“秩序”,而与易变多样的人物个性关涉殊少。日后脸谱美学的松动,根源就在于原先支撑这一“符号/象征性的意义共同体”的玄学体系的崩溃。具体来说,这与中国20世纪初以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现代戏剧文化的崛起有关。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的导言中早就点明:中国的现代戏剧(主要指话剧)是“新文化”的产物,其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23](P.5)经验主义一般认为,感性知觉是认识的起点与知识的来源。“五四”时期的中国恰逢王纲解纽的时代,旧时的统一世界观逐步瓦解,个人不得不“反诸求己”:或转向个人内心的体验,或转向对个人周围世界的观察。这种新的世界观,表现在日后的话剧舞美上,即信奉“眼见为实”。只有在经验主义的观察方式下,那种千变万化、贴合个性、逼近日常视觉经验的舞台装扮才能成立。而“十七年”平面化的“胭脂美学”的回归,则说明一种新的“符号/象征性的意义共同体”的玄学出现了,而之前的经验主义的世界观受到了冷落。这种新玄学,在剧本创作上的表现就是盛行的工农兵题材剧目;在话剧舞台人物妆容上的体现,则是满面红光的“胭脂美学”,其巅峰在“文革”,崛起则在之前的“十七年”。 注释: ①剧照见《戏剧报》1961年第19、20期插图。 ②该教程刊载于《戏剧报》1957年第24期、1958年第1期、1958年第3期、1958年第4期和1958年第5期。 ③剧照见1958年、1959年、1964年和1965年《戏剧报》与《上海戏剧》的彩页、封面、封底。 ④参见陈丁沙、梁灏:《清除胡适反动理论在戏剧界的影响——评张庚著作〈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张庚:《对〈中国话剧运动初稿〉中错误的初步认识》以及佚名:《清除胡适在戏剧方面的流毒》,三文均载于《戏剧报》1955年1月号。 ⑤剧照见1958年、1961年《戏剧报》封面、封底与插图。标签:美学论文; 脸谱论文; 中国话剧论文; 胭脂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少奶奶的扇子论文; 戏剧论文; 陈大悲论文; 化妆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