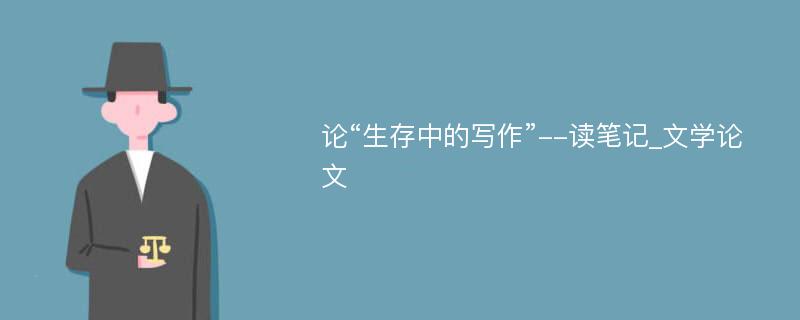
关于“在生存中写作”——编读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编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以来,在报刊媒体将“80后”写作,将一些中产趣味写作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在“80后”写作与中产趣味写作赢得市场、大行其道的时候,却另有一种孤独而执拗的写作力量在用尽生存之力呼喊着敲打着文学之门。当我们读到一批被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冠之以“打工诗歌”、“打工文学”的作品时,便仿佛听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在这声音中,我们感受到了他们正从人们平时习以为常的“文学”领地之外带来一种新的文学。甚至我们连这样的奢望也似乎有些多余,因为他们所奋力敲打的,与其说是“文学之门”,实质上勿宁说是“生存之门”。
他们给“文学”带来了文学。这表明了另一种真实的多样性文学的可能性,也意味着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学空间的可能性。其实我们原来所呼唤和指实的“多样的文学”,大抵是囿限于一个整一的文坛、一个有着专业化的以创作文学为职事的中国文坛,所谓多样性不过是这个整一而专业化的文坛或文学内部的“多样性”。在此之外,我们便看不到多少文学存在了。新世纪以来,这个“文坛”的整一性受到了来自其外的群体性写作力量的挑战。首先是面对“80后”青春写作现象的来势不小,如若从这个具有专业化身份的文坛看去,有人便判断他们是“进入了市场,而没有进入文坛”。这个具有洞察力的鲜明而又模糊的表述其实在说明“80后”所没有进入的,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固定的、整一的文坛,成长中的“80后”的写作尽管有许多可商兑之处,但终归它被判定构成不了所谓的“文坛”哪怕只是其中的一角。而没有进入固有的主流文坛,还算进入了这现成的“文学”吗?显然要打折扣不少了。这里有着多么矛盾的态度!令人不可思议,也迫使正宗、主流的“文学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不管你怎样说法,“80后”在自己特定的“成长”位置上,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和市场之维创造着自己的“文学”之梦。
时代迅变真是令文坛猝不及防。而与“80后”青春写作这样的都市青春文学或校园文学宗旨完全不同的,一些以“进城务工”的所谓“农民工”青年写作者为代表的“打工诗歌”、“打工文学”,却连市场之梦也是没有的,他们的写作的确在试图撬开命运和生存的一点缝隙,却无缘靠写作赢得市场而成为市场的文学“雇佣劳动者”,因而很少有金钱的光顾,倒是特定的生存性直接地转化为了特定的精神性,一批裹着浓厚的生存真相和灵魂意涵的文学作品产生了。
然而我们的文学和文坛,这些年来不能不说对他们有很大的忽略,有时更以一种纯文学、高审美的眼光拒绝了他们。他们在文学更在文坛之外。但历史的真实是,他们无可置疑地应在文学之内。他们伴随着中国当代改革的新社会创业之潮而生,已积蓄了相当的时间和作品,在新世纪终于积聚成为一个你不能不面对他们瞪大双眼的文学群体。这是我们在读到曾经是打工者和打工诗人的柳冬妩所编的《中国打工诗选》,以及他所写的近期发表于《读书》杂志,以及《文艺争鸣》杂志上的阐释“打工诗歌”的文章之后才感受到的一个事实。我们陆续读到了一些这样的生存最前沿者写作的文学作品,想一想,在一个分工化过分的现代技术社会里的文学存在以及存在的文坛,一百多年前马克思说过的话仍然使我们警醒:“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
我们愿意称这种文学为“在生存中写作”。
毕竟,诸如“打工”这样的概念似乎更多地专指“农民工”,概念运用上有些“窄”。当然这只是概念形式运用意义上的“窄”,其实目前中国的农民工,据相关资料说大约有1亿多人口,已是一个相当于英法两国加在一起的规模,从这个意义上看,又何“窄”之有?其实面对偌大的中国社会及其人群,每一个很“窄”的概念之下,都可以概括和潜藏着一个丰富的世界、一个很多很大的人口或生命存在。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那些以其“廉价劳力”的“边际效应”支撑和创造了新世纪中国经济崛起的亿万人群,之于中国的意义,是应给予高度评价的。他们的生存和人生,是真正的“中国化的人生”,只有中国及其广阔而一体化的时空与文化,才生存着这样巨大的流动、迁徙的人群,这样的人群也创造了他们的“中国”。然而我们愿意用“在生存中写作”来说明这种现象,指称这个群体的创作,主要的还在于这个词组更能从文学写作方式的意义去标明或凸显该类文学写作的特殊含义和性质。这不仅因为“打工诗歌”、“打工文学”有其确指地把意义定在“农民工”上,除农民工外,还有在写作方式上相似的如其它城市工人或其它在生存前沿坚持文学写作的现象,如内蒙古平庄矿区的工人写作等,而且,正由于强调了这是“在生存中”的“写作”,强调了这种写作更加逼近生存现场的意味,强调了“生存”对于这类创作实际的生活意义和实在的文学意义,强调了一个在生存现场打拼的“生存者”所能带给文学的全部奉献和局限,这种文学才会区别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坛的常规写作方式,所谓“作家”的写作方式,我们才得以从一个更宽的角度来打量一个更大的文学或文坛的整体性存在。也许,从前我们会对此以“专业的”或“业余的”文学创作加以区隔,但今日看来,专业或业余的区隔显然有着现代性职业分工的陋见,也不无歧视性的意涵,因为“专业”永远不会是文学高尚或伟大的保证,而“业余”也完全可能回避生存的本真。还是让我们直面生存来说话吧。
人类的语言在构成思维、交际与表达时,同时也构成了意义的陷阱。“在生存中写作”同样也有着不少“词不达意”的局限。语言在这里会形成繁殖或生产语言的自身缠绕,总免不了越解释越多的循环怪圈。正如“生活”这个概念,平时人们说到要“深入生活”,另外一些人则辩到:你不就在生活中吗?怎么还有“深入”之说?“在生存中写作”也大类相似,人们会问:谁不在“生存”之中?难道还有一种不在生存之中的写作吗?应该说,这些追问有其存在的理由也挑战人的智力,其追求意义澄明的动向值得肯定。对此,我们要进一步限定和说明的是,这里强调的“在生存中写作”的“生存”是指那种在为衣、食、住等基本生存目标而奋争的人们的意义上的生存,或者说是第一生存,或者套用晚近以来中国文学中的一个主题词语,是“活着”意义上的生存。生存(活着)跟生存(活着)是不一样的。在“第一生存”不成问题的人们看来,“发展”是有别于“生存”的,他们可以在“休闲”中生存,可以在“资本”中生存,可以在“发展”中生存,可以在日常的“稳定”与“中产”状态中生存,更可以在“审美”或“艺术”中生存,在“写作中”生存,这些生存中当然也可能包含着“第一生存”的打拼内容,但毕竟很多时候,那些挣扎于“生存”第一要义的内容已不很重要,甚至可以用丰富的物质和优雅的精神加以“超越”了。然而这个时代,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之下,还有许许多多为着基本生存或第一生存而打拼而挣扎于困境的人们。尤其让我们深受触动的是,即使这样,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没有忘记文学。此时的文学是怎样的一种文学?就是一种“在生存中写作”的文学,这个概念强调了这样一种基本生存状态与文学写作胶结在一起的写作方式。
这种写作最鲜明的特征是“写作”与“生存”的共生状态,或者“第一生存”体验对于“写作”呈现了最直接的意义,这与目前主流文坛的写作方式有很大不同,他们是“在生存中写作”,而目前文坛存在的职业性作家文学则在很大的意义上是“在写作中生存”。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作家写下的夫子自道:文学写作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是以文学的方式活着、生存。除了“文学”和“写作”的“拜物教”,他们的生活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他们为了文学殚精竭虑,皓首穷经,语不惊人死不休,令人感动,构成了现代性文学的主流存在方式。在一个分工化形成的文学社会,写作本身构筑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形成了一套自我设计的“精神生活”的生存躯壳,这种写作即或去书写底层,去书写第一生存的要义,也注定是俯瞰式的,尤其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自我精英化、自我封闭化、拒绝改造的年代。而那些把基本生存与文学胶结在一处,发生于生存前沿的生存者笔下的写作,同样也令人尊敬,虽然他们往往以边缘的位置,以流动性极大的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与文学写作状态来理解和处理文学,自身的“生存问题”和“文学”的胶结也不是他们所能够自由选择的,但他们为什么还要在生存的诸多困境之上再追加“文学”?他们完全可以全身倾力于生存而不理会什么“文学”。而眼下这些写作表明,“在生存中”有“写作”出“文学”,这底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只能说,看来所谓“精神”也并不总是离生存很遥远,有多样性的“生存”,也会有多样性和多层面的“精神”。在人的基本生存现实中所产生的精神现象无疑最直接地裸露了生存的基本要义,并体现了这种人生状况中的人的那点子真正的基本精神。与“在写作中生存”的写作方式相比较,在读了诸如“打工诗歌”、“打工文学”的这些“在生存中写作”的若干作品之后,我以为,其一,这些作品表现了一种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和感受,也体现了一种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情境中的为基本生存而奋斗的精神。在当下文坛现代小说和现代诗歌那里所出现的生活景观,很大程度上都与此“生存”大异其趣,因为先锋式的现代小说和现代诗歌大都把这些现实的“生存”转化为一种“存在”,存在哲学的精神使他们笔下的“生存”抽象化,它稀释甚至牺牲了很多生存的日常性、现实性和实在性。而“在生存中写作”的文学,则有着建立在基本生存之上的真实情感,撕心裂肺或困顿徘徊,以及所有的想像和心灵体验,都建立在“我手写我口”式的内在基础上,化为一股为生存而斗争的时代精神充盈其间。其二,因此在当下文学的某些“在写作中生存”的作品那里,其对现实的关系总是外在的、隔膜的,生存中的苦痛最终成为一种如陈晓明所说的“无根的苦难”,苦难史最后转化为某种当代性史、狂欢史或美学游戏,为一种中国当下文学的“审美脱身术”所消解,生存的本质和生存的批判都变得暧昧、软弱,而又虚幻。而“在生存中写作”的作品中,却充满了真正的现实精神,即有硬度和反抗,也有细腻和妥协,一句话,很现实。没有多少审美的精神幻觉。也许我们不能再习惯地使用19世纪或20世纪的“现实主义”概念来硬套,说他们反映或表现了现实,这对他们的写作方式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一定要表达这层意义,我以为说他们的写作充满了“现实精神”是恰当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现实,以人的生存意志面对和处理现实的现实精神在他们不仅是本色的,更是本真和本质的,是他们仿佛与生俱来的处境的现实性和精神性的自我呈现。基本生存的“现实”与基本生存的人的“精神”的胶结,形成了直截了当、很少雕饰的现实精神美学。其三,当下文学的“在写作中生存”,很注重对所谓的“启蒙话语”的演绎与消解,“人文精神”也随之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批评概念,这种知识分子性的概念用在这些“在生存中写作”的作品身上,也相形见绌,其实在这些作品中所得以大力张扬的,也许不是什么“启蒙话语”“人文精神”,而直接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壮大和立体的“人的精神”,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以人为本”的人,去掉了“文”而直接显现的“人”,这些作品中充满了现实化的生存诉求与公平正义诉求,那些劣质的生活场景和悲苦的命运所生发的情感细节与心灵的呼喊,那些打工地理学、城乡心理学所布满的神经网络,那奔波于这些网络中的卑贱、平凡的无数的“中国化的人生”,天生地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具有人道主义倾向。最后,相对于“在写作中生存”的主流写作,“在生存中写作”也许由于首先要面对生存的窘迫与压力,总是来得不那么“自由”,不那么纯粹的“精神性”,但是这些作品不但证明了精神终归是来自生存境况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且,就是这种粗硬的、艰辛的生存现实,也同样能够产生一些让我们刮目相看的有着特定精神诉求的作品,真是可以庆幸的。诗意无处不在,关键还在于要有发现诗意的眼睛。而他们为了自己的“现实精神”和“人的精神”,牺牲一些“美学技巧”也就可以得到文学的原谅了。有时,正由于他们牺牲了某些“美学技巧”,却在一些优秀之作那里获得了自然浑成的美感,一种质朴率真的心灵的锐利。那是生存和文学胶着在一起给他们的回馈。马克思说:“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谦虚的方式来表达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们忘记这种语言的。”中国是我们的故乡,面对“在生存中写作”的文学现象,我们以为它像一面镜子立在了这个主流文坛的面前,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带来了种种新的激活与思考,这正是它的意义所在。同时,它记载了我们这个改革中走向富裕和文明时代的一段真正不可忘却的身世史,那些在非科学观的“发展主义”和“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旗号下被掩藏的大写的“人”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那些不断隆高的现实的前生今世,那些总被遗忘、不为人知的力量和眼泪、血汗和温情,那些生活底处横亘的脊梁的基本生存及基本情感,自有其价值,也弥补了主流文坛的缺失造成的遗憾。
当然,“在生存中写作”的情况也是形态多样的,王小妮的《张联的傍晚》所评论推介的张联,无疑对我们的上述阐释提出了难题,他无疑也是一个在我们所谓的“第一生存”现实中寻求精神价值的诗人,我们惊讶于贫瘠的生存现状与超越的诗歌写作之间竟如此悬殊地同一显在于张联这个人的身上,当会引发更多的另外的关于主体与自由的思考——审美的超越与匮乏的生存现实的逆向生成,造成了多么陡峭的精神悬崖!我们相信在诗人张联这里,这些都具有存在的真实性,而不是虚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