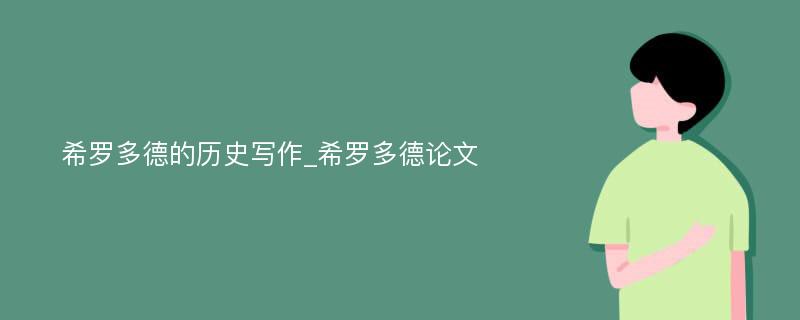
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德论文,希罗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不同的文本形式或话语结构与史家所要叙述的事件以及所要表达的思想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历史学家对材料的选择以及写作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叙述的展开、思想的脉络,并且也会对读者的理解和分析产生影响。而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最大特点就是那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创作活动,同时也是在口述传统的背景下,从主题确立、叙事风格、资料选择中表现出一种对公众记忆的尊重与服从。
一 “插话中的插话”与“荷马式的”风格
读希罗多德的《历史》是需要很大耐心的,这不仅是因为此书牵涉的地区、年代跨度太大,人物、事件头绪太多①,而且作者特殊的讲述方式更是难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书中,他不断地打断自己的叙述,不断地在一件事尚未讲完时插进一段相关的背景介绍。这种插话,短则一、两节,长则多达整整一卷,最长的一段就是介绍埃及风俗的第二卷。更有甚者,还有“插话中的插话”,即在一段插话之中再插进另一段。比如《历史》第五卷第55节以下,希罗多德讲到反抗波斯的爱奥尼亚起义的领导者之一阿里斯塔戈拉到希腊本土寻求支援。他先到了斯巴达,没有结果,又转去雅典。在此,作者插进一大段追述(卷五55-96),向读者介绍雅典是如何摆脱僭主的统治,走上民主之路的。这本不算过分。可他在卷五的第57节又插进了一段,介绍起杀死雅典末代僭主希匹亚斯之弟希帕科斯并最终引发人民起义的两位英雄的原籍——盖菲拉(Gephyraei)。而这还不算完,在紧接下来的卷五第58节,他又开始讲述和盖菲拉人一道在希腊本土定居的腓尼基人,进而讨论自己的一个研究成果——他认为希腊字母是腓尼基人传来的,并花了3节的篇幅(卷五59-61)来举例说明。诚然,这个研究成果或许是很具洞察力的,但是这与盖菲拉人有什么关系?与雅典人摆脱僭主有什么关系?与爱奥尼亚起义又有什么关系?这种三次插话在希罗多德的书中并不只此一处。②这种不时脱离主题的叙述方式,过去通常被视之为主题不明确、主线不清楚,并将其视作是当时写作技巧不完善的结果。但是,我们认为,这恰是希罗多德叙事方式的独特之处,这种叙事方式表明希罗多德所引用的材料主要是来自于口述的,同时其著述的流传也仍然保留了便于口述的形式。因为他是在面对听众讲故事,这种讲述就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听众有不同的需要和兴趣而不断地打断他的叙述。这是一种随着语言本身的流动而流动的讲述方式,是一种随时准备分流、回溯,然后再重新汇合的言说方式。讲述者和听众,有着一种当下的、直接的、即时的交流。这种讲述方式想向人们展示的,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着清晰的原因—结果的、单线条的固定的叙述客体,而是一个有着众多线索、可以随时把某一段拆开来单独讲述,并可从不同视角、不同目的去解读的东西。
而有关希罗多德的叙述风格为什么是“荷马式的”,也与希罗多德采用口述的材料以及他的历史书写必须兼顾公众记忆的特点有关。由于城邦时代希腊人生活的共同性和公开性③,个人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其价值来自于城邦也依赖于城邦。因此“对于古代希腊人来说,‘不死’意味着一个离开了阳光的人却永远存在于集体的社会记忆之中,……集体记忆的功能就像是某种机制一样确保某些特定的个体在其光荣逝去之后仍然能够继续存在。因此,代替永生灵魂的则是不朽的荣光与人们永久的怀念。虽然没有为世俗之人保留的天堂,然而确有一个为应得之人保留的永恒的记忆,那是停留在活着的人居住其中的社会内心深处的。”④这里的“集体记忆”显然是指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也即是共同体的传统。因为记忆不仅是一种生理功能,同时它还具有社会功能,社会环境和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相互作用是记忆的重要因素,并在时间和空间里对集体记忆起到某种调整的作用。如果说,史诗是希腊人对本民族最早的集体记忆的记录的话,那么,希罗多德的《历史》便应该是对城邦时代希腊人公共记忆的记录和反映。
早期学者们曾一度认为,从赫卡泰乌斯到希罗多德是一条直线的发展过程。但是,早在古代,希罗多德就被认为是古代作家中“最荷马的”,也就是说,对希罗多德产生最大影响的是荷马。首先就其形式而言,《历史》是荷马式的:希罗多德使用的是荷马式的语言、直接的演说词、相同的主题以及相似的情节结构。比如在《伊里亚特》中,我们经常看到诗人在介绍某位英雄时,总会追述他的祖先及其家世。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对于书中重要人物同样也是如此处理的,比如对斯巴达王列奥尼达、波斯王薛西斯等,他都花了不少笔墨来介绍他们的家族谱系。⑤再比如《伊里亚特》第十七卷一整卷的主题就是双方为争夺阿喀琉斯的朋友帕特洛克罗斯的遗体而战,为此双方一共进行了4次争夺战。而《历史》第七卷第225节写到斯巴达军队和波斯军队为了争夺列奥尼达的遗体,也混战了4次。这样的战斗或许确实发生过,但为什么这么巧,都是4次?在题材方面,《历史》与荷马史诗的类似在于它们都描述了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大战,希腊人都最终取得了胜利。希罗多德在叙述手法上很多地方也是学习荷马的,比如荷马对奥德修斯历经磨难的返乡途中所遇到的那些国家民族风土人情的描写,让人自然联想起《历史》中的类似章节。只是,前者想象的成分更重些,但是这种风格的类似却是很明显的。由此,甚至有论者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是用散文写成的史诗。”⑥
除了这些形式上的相似以外,更重要的是希罗多德似乎也与荷马一样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讲故事的游吟诗人,而不是一位作家。在希罗多德的时代,讲述和写作可以理解为是大体上重合的两个概念,讲述甚至包括了写作。⑦德国古典学家弗雷德里克·克罗伊策说,“希罗多德从一开始构想撰写希波战争直到最后完成他的计划,不时出现于他的头脑中的是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他指出,要完整地理解希罗多德的著作,就必须首先对史诗作完整的研究。克罗伊策认为,希腊历史学起源于史诗,从史诗发展到史学,经过了四个阶段:1、荷马史诗,2、史诗组,3、散文纪事家,4、希罗多德。在这几个阶段中,只有荷马和希罗多德不是按照事实的表面顺序,而是以真正的艺术的完整性组织他们的叙述的。他认为,希罗多德与荷马不仅在叙述的安排上,更在精神、因果关系都是一致的。⑧这样,他就赋予了传统认为希罗多德是荷马的模仿者这一观点以深刻的意义。而希罗多德像诗人那样,向公众朗诵他的作品则从另一方面不仅证实了历史是从史诗发展而来的理论,同时也证明了口述传统以及公众记忆对于早期历史叙述的重要性。然而,作为口述历史的实践者、公众记忆的保存者,希罗多德是用什么方法确保其叙述的真实以及我们如何认识他的真实性呢?
二 《历史》中的资料与证据
考察《历史》,我们发现希罗多德所使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文学作品。在《历史》中多次提到散文记事家赫卡泰乌斯以及许多诗人的作品。⑨这些文学作品有的是他叙述依靠的资料,有的是用来证实他的叙述的,还有的是出于批判的目的。二、神谕。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引用了大量的神谕,使得人们猜测他有可能看到整理成册的神谕,但也仅仅是猜测而已,同时也不排除它们来自于传说这一可能性。三、纪念物、档案与铭文。与文学作品和神谕不同,铭文没有证实作者叙述的目的,它们或是用来渲染气氛,或是表明作者进行了实地的考察。但就铭文的内容而言,我们难以看出它们有什么重要价值,相反还带有一种讽刺的意味。⑩
20世纪以来大多数学者基本上都认可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主要依靠口述资料的观点。(11)然而,口述资料的性质使学者们无法追究资料的提供者究竟给希罗多德说了些什么,《历史》中大量口述资料的使用使得一些学者对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真实性提出了新的质疑,代表人物是费林,在他的《希罗多德和他的“史料”》一书中,认为希罗多德的叙事方式只是古希腊的一种文学习惯而已,他既没有得到任何口述的资料,也没有得到文字的资料。希罗多德从事的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历史著述。(12)不过,施林普顿和吉利斯利用光盘检索的方法对《历史》中口述资料的引用作了广泛、翔实的分析,证明了希罗多德对口述资料的引用并不是在编造故事。(13)在希罗多德引用的188条有出处的资料中,96处来自希腊人,其中54处是希腊主要城邦的资料,如雅典人、拉西底梦人、科林斯人和埃吉纳人等,还有三处引用了马其顿人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希罗多德叙述的故事不可能是他编造的,而只能是他的希腊听众记忆中的事件。这也表明费林认为希罗多德的资料引用是他编造故事的说法是不妥的。
抛开学者们的讨论,让我们回到文本自身,在《历史》中希罗多德并没有明确提出“证据”这一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叙述中无据可依。从表面上看,他只是尽可能地搜集遗闻旧事,几乎有闻必录,甚至把那些他个人也觉得“不可索解”的事情也照样收录。其实,希罗多德是深知历史真实性的重要的。他一再告诫读者:“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1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有作为一个记录者的责任感,他自己虽然缺乏鉴别史料的能力,但仍然有着追求历史真相的愿望。同时,他也竭力想要从当时存在的各种不同说法中做出明智的选择,他对那些认为的确不可信的东西就采取了拒斥的态度。(15)希罗多德在书中时常还会对同一件事情列举他听来的两种以上的说法,并做出个人的判断,比如他说:“对于这些不明确的事情,现在我必须提出我个人的意见来了”;“这是埃及祭司们的说法,但我个人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人们可以相信任何一个他认为是可信的说法;但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我自己关于它们的意见”;“这是在传说当中最为可信的一个说法。”(16)这些话反映了早期希腊史学朴素、客观的处理方法。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希罗多德的方法粗糙,既像游记又像口头传闻,但他绝对不是不加批判的。譬如他区别了事实和神话,他知道耳闻和目睹的分别,他也知道事件发生的原因与前奏。”(17)具体而言,在《历史》中希罗多德辨别材料真假的标准有二:一是看其是否有确凿的证据,以神话为依据的观点在他看来是不可信的。他所谓的证据主要是公众承认的事情,即普遍性。例如,关于伊索是雅德蒙人的说法。(18)二是看所闻之事是否合乎情理。所谓“合乎情理”一方面是指所闻之词与希罗多德的亲自观察相吻合,如在谈到埃及人是如何哺育婴儿时,他不仅引用了祭司们的话,而且还做了实地考察,他说:“我甚至为了这个目的到底比斯和黑里欧波里斯去,专门要去对证一下那里的人们所讲的话是不是和孟菲斯的祭司们所讲的话相符合。”(29)另一方面,合乎情理也指所闻之词合乎常人之常情,这其实也是普遍性的表现,比如在谈到一个司奇欧涅人的故事时,希罗多德用了这样的说法:“如果一般的说法是真实的话,……”。(20)有时,他则将这两项标准结合起来以辨真伪,例如关于波斯王薛西斯战败逃跑之事。(21)可见,希罗多德已能初步运用批判的方法,注意考订口述史料的真假,比较各种记载或传说的异同,从而使历史学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虽然希罗多德的著作有时因失于轻信,仍有谬误,但总的看来,正如现代美国史家汤普森所说:“在批判精神方面,他还是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22)可以说,希罗多德为古典史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也正是对此的肯定,当代英国史家彼得·伯克在总结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时,认为其中的一个特点便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注意对史实的查验,即鉴别和评估他们听到或读到的有关过去的个别的故事,以便获取对历史事件的最可靠的史料。西方史学传统之所以在这方面具有其特点是因为它同时关注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23)
其实早在16世纪,西方学者就对希罗多德使用口述资料的作法予以了肯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许多人的写作也完全是根据亲身的经验和即时的需要而成,由此他们通过亲身的经历表明,人们能够广泛地游历,自然会碰到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事情,也可以通过口述资料重构遥远的过去的历史,但未必就是说谎者。(24)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希罗多德所用资料的可靠性再一次受到置疑,为什么西方学界对希罗多德的评价会有如此的反复?这固然与《历史》中个别明显的错误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虽然学者们认识到希罗多德生活于一个口述的社会,以及他对口述资料的依靠,却未曾考虑口述的历史对记忆的依靠。也就是说,学者们没有从记忆(特别是公众记忆)这一角度来思考希罗多德的真实性问题。由于当时的大多数希腊人是在“听”而不是在读他的作品或其他书面文本,口头证据始终是探究以往的事实与意义的问询者获取材料的主要途径。希罗多德是在没有图书馆的条件下进行他的“探究”的,他记录的是考古学出现之前的古代的事情。因此,采用大量传说见闻作为史料不仅不是他的过错,反之,应视为他的重大成就和贡献才是。当然,记忆不可避免会带有记忆者鲜明的个人色彩与事后解释的偏见。当人回忆时,那些最初的信息会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塑造,他会用习惯性的术语描述他记忆中的事情。这些术语带有他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特征。这也就解释了希罗多德对非希腊的传说的描写为什么会带有希腊风格的原因。因此,在评价希罗多德真实性的时候,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希罗多德实践的是口述的历史学,而口述的历史依靠的是记忆。由于任何口述者都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中,主观因素在他们追述历史中不可避免地被加入进去。而且口述者在追述记忆时,往往是有选择地回忆以及有选择地叙述他们认为有意义且无损自身形象的那部分记忆,由此自然会削弱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希罗多德历史叙述中的缺陷可能就是由口述或者说是由记忆失误造成的,但这并不是一种自我欺骗或有意的对他人的欺骗。“观察者把所有的事情搞正确是不可能的。详细的准备和训练只能减少错误,但要消灭错误是不可能的。”(25)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希罗多德由于这种原因而犯的错误称作是谎言。更何况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口述史料是经过史学家与口述者双重主体选择后形成的。这样,在口述史中,历史主体就不只是历史学家,而且还应该包括口述者,这能使历史学家避免其一已之主观性。这一点在古代希腊尤为重要,因为在城邦的语境下,任何口头传说都会在社会共同体中不断地被塑造再塑造,经过集体记忆的检验,这种记忆的方式使人们对那些关乎城邦生活的重大事件拥有了某种共同的记忆,因此古典史家在选择资料、记录发生的事件时,就会力图在兼顾自己的认识的基础上把集体记忆加之于历史之上,在他们看来,这样历史叙述才是有意义的,也才是会被人们所认可的。
三 《历史》的神“话”与“神事”
城邦时代,希腊人对神的崇拜不是统治阶层的特权,而是城邦的公共活动,是全体公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而且,城邦存在的合法性及其神圣性正是从那些在神庙前围绕祭坛与坛火所举行的公共活动中确立起来。所有的公共活动都是从某种对神表示敬意及虔诚的仪式中得以展开的,可以说,没有一次公共活动不是在神的关注下举行的。在这些活动中,共同的敬畏和共同的希望,通过人们共同的关注,将团体中的不同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社会伦理控制的巨大力量。因此,有学者指出,“城邦的整个生活,渗透着神性,希腊人是与神生活在一起的。我们只有理解‘神’的因素在希腊人生活中的作用,才可理解希腊人的城邦”(26)。与史诗相比,希罗多德探究的主题似乎不再包括“诸神的业绩”,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在他叙事中的缺席。事实上,我们发现希罗多德似乎对预兆、神谕以及祷文、先知等深信不疑,认为正是这些预示着事情的成败。他说:“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27)其实,希罗多德的这种态度是当时希腊人普遍心理的反映。古代的希腊人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个人的生活问题都喜欢求得神的旨意,然后在神的名义下进行。希罗多德书中那些随处可见的神谕表明他对神灵降旨的相信,同时也是他想为自己所记载内容的准确性寻求根据和保证的表现。
唐纳德·拉特内尔将希罗多德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总结为五种因素:神的嫉妒、命运或循环、神意、行为和报应以及历史的分析。(28)除了历史的分析法以外,其余四种都与神有关。首先来看神的嫉妒。希罗多德通过梭伦、阿玛西斯、阿尔塔巴诺斯等人之口道出了“神是非常嫉妒的”这样的观念。(29)我们同意福里斯特的论点:对希罗多德而言,“嫉妒是保持公正的力量,把‘扰乱’看作自然秩序的人是不会担忧命运之神对人类的扰乱的。”(30)在希罗多德看来,招致神嫉妒的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因财富而来的傲慢之心。同样,成功也引起人们的傲慢之情。因此,人的傲慢、盲目的享受财富,看似无止境的成功都会引起神的愤怒和嫉妒,因而也招致了他们的灭亡。(31)第二种因果关系的形式是命运(fate)和循环。德尔菲的女祭司佩提亚说:“任何人不能逃脱他的宿命,甚至一位神也不例外。”(32)命运的力量是强大和不可思议的,克诺索斯、冈比西斯、波律克拉铁斯和阿尔凯西拉欧司的结局都是命中注定的。(33)人们既无法理解,也不可能避免它。因为在古代希腊人的眼中,人并不是无拘无束地存在的,而是生活在一定的关系范围内。这些关系最初被理解为绝对合理性、秩序和充满意义的宇宙。这些不以人为转移的宇宙力量,决定着人的外部状态,使人感到它是一种决定劫数和命运的普遍力量。在《历史》中,希罗多德还在一两处说到了历史中不可抗拒的循环运动。最清楚明白地表达了这一意思的是克诺索斯。他对波斯国王居鲁士说:“人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车轮上面的,车轮的转动是决不允许一个人永远幸福的。”(34)这种循环运动的观念看似一种命定论,但其实它代表的仍是平衡的原则。希罗多德使用的第三种因果关系的解释是神意。他说:“一切事物和这些事物的适当分配都是由神来安排的。……正是由于上天的智慧才有这样合理的安排,使一切那些怯弱无力和适于吞食的生物都是多产的,这样它们才不致由于被吞食而从地面上减少。但那些残酷的和有害的生物则生产的幼子很少。”(35)正是神使自然界恢复了平衡与和谐,同理,正是神的嫉妒和惩恶扬善保持了人世间的平衡与和谐。只要是神的意愿,就必定能够实现。表面上看,它与第一种和第二种的解释有些重合,但却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解释体系。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神意呈现了两种情形。一是对人类恶行的惩罚,如克诺索斯的遭遇是神对他的祖先的恶行的报复,特洛伊的毁灭是天意注定的,“这件事将会在全体世人面前证明,诸神确是严厉地惩罚了重大的不义之行的。”(36)培列提美她凄惨的死亡是因为她的过分残酷的、丧失人性的报复行为遭到神的忌恨和厌恶的结果。(37)其次,神意还表现为神对人类的救助。如神对掠夺戴尔波伊财产的波斯军队的毁灭性打击。(38)希罗多德使用的第四种因果关系的解释是报复。在报复的原因中,既有神的报复,也有纯粹人的报复。如同神的嫉妒一样,神的报复也通常是施加在那些过分幸运的或拥有过分权力的人的身上。这样,神的报复也代表了一种平衡的法则,以恢复人世间的平衡。
总之,德尔菲神庙上那句“认识你自己”的谕言,对于希腊人来说,不仅仅是意味着人应当反思自身,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人的凡人的身份以及他在尘世间的地位,明白自己是人而非神,因此,其所作所为就不应该僭越人的适当的行为规范。(39)这一神人关系的指导思想无疑也是希罗多德历史书写中处理神人关系的准则。有人认为这种思维模式不仅使希罗多德的批判力度被削弱,而且也使其著述的真实性受到怀疑。然而,我们认为,这表现了古典史家对公众价值观的遵从,也恰好符合当时城邦语境中人们对于“历史”及其“真实”的理解。
四 《历史》的主题选择
最后,再让我们从希罗多德对主题的选择上来看其历史书写的时代特征。
在一个口述传统的语境之下,希罗多德所掌握的主要史料大多不是官方的或非官方的书面文件,而只是同时代人的口头证词及自己的游历,这样得来的材料难免头绪众多。由此,后世学者对于希罗多德是否赋予他的历史书写以一个自始至终的主题?《历史》的结构是否具有完整性?等问题争论颇为激烈。(40)在此,我们先将现代学者的讨论放在一边,而对希罗多德所用historia一词的含义及其语义背景做一番简单的梳理:英文history一词是由古希腊文historia(意为“探究”)转化而来,其词根是histor,最早见于《伊利亚特》中,指能够从诉讼双方的讼词中调查出真相、并做出判断的人,他因此而获得报酬。(41)后来方法扩展到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获取知识,比如通过对目击证人的询问,而并不一定要通过亲自经历。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它的含义演变成通过收集和甄别证据然后以人的理性评判来获取真知。换句话说,对于古希腊早期史家来说,经过问询得来的口碑史料就是“历史”。而这种历史叙述的内容不仅包括人类的活动,动植物、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等也都可以成为探究的对象。因此,在希罗多德的心目中,希波战争是他写作《历史》的主要题材,但并不是唯一目的。他在《历史》的开篇之处就将自己的写作目的定为:一是记录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功绩,二是希腊人与异邦人发生纷争的原因。于是,他在《历史》中以将近一半的篇幅讲到了希腊人和异邦人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例如,卷二中几乎全是埃及的事情,包括埃及的地理环境、发明创造、奇闻逸事、宗教信仰等等。他说:“关于埃及本身,我打算说得详细些,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42)言下之意,若不是埃及人创造了如此伟大的功勋,他是不会如此详尽地用180节的篇幅去介绍埃及。他这样做并不是离题,而正好是他探究精神的体现。可以说,希罗多德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报告自己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并说明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最伟大和最主要的设施。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而有关纷争的原因也做了交代,可以说,希罗多德著述的两大目的都已完成。
曾有学者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没有写完,也有人为其以精妙的高论结束全书而赞叹。或许这些说法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我们认为,希罗多德之所以没有提及战争的最终结果,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普拉提亚战役后,希波战争的性质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它已从一场整个希腊世界团结自卫的解放战争变成了一场为争各自私利而进行的掠夺战争。若再写下去,势必提及雅典与斯巴达的分裂、它们为争夺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这不仅与希罗多德著述的初衷和主题(他在提及其写作目的时没有说他要写战争的结果)相悖,更为重要的是这与当时整个希腊世界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绪相违背的。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人们想要记住的是他们同仇敌忾抵御外辱并终获胜利的光荣,而不是内部的相互争夺彼此削弱而终致衰落的局面。希罗多德说:“如果他们为领导权而争吵,希腊便一定要垮台了。……因为内争之不如团结一致对外作战,正如战争之不如和平。”(43)这种表述并非只是古典史家个人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是公众记忆的表达和再现;是与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相一致的。
而正是从对主题的选择上,古代史家比较了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之间的优劣,狄奥尼修斯从主题和描述方法上对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叙述进行了比较。他说:“对所有史学家来说,首要和最基本的任务是为他们的读者选择一个美好和令人高兴的主题。我认为,希罗多德的选择比修昔底德的要好。他的历史是有关希腊人与蛮族人的总体的历史,如同他所说的,‘为了使人类的业绩不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被遗忘’……但修昔底德仅仅描写了一场单独的战争,这一主题既不高贵,又非常不幸。它本不应该发生,但却事与愿违,它应默然置于一旁,并且被后代遗忘或忽视。”修昔底德声称他所记载的战争充满前所未有的灾难,狄奥尼修斯以为,这正显示了修昔底德主题的低下。他说:“历史写作的第二项任务是知道从那里开始,应该走多远。在这方面,希罗多德远比修昔底德明智。他始于蛮族人对希腊的第一次侵略,结束于他们遭到惩罚与报应。而修昔底德却从希腊民族陷于困境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叙述。他,一个希腊人,实际上一个雅典人不应该如此做……他的总结性叙述是巨大的错误。尽管他声称他目睹了整个战争,并允诺描述战争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但他却止笔于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间的塞诺西马战役(发生于公元前411年)……如果他完整地叙述了整个战争,如果他有一个令读者高兴的、不同寻常的结尾,比如,使全篇结束于雅典重获自由后,流放者们从菲尔归来(即公元前403年,民主制的恢复)之日,那么,他就较好地完成了史学家的任务。”(44)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的这种态度是否具有代表性呢?有学者认为,虽然没有有力的证据对这一问题做出非常肯定的答复,但可以相信狄奥尼修斯的观点代表了古代批评家们的普遍看法。(45)狄奥尼修斯对两位古典史家的评价为我们理解希腊城邦时代的古代思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狄奥尼修斯所提出的评判标准实际上就是要求史家应该对公众的记忆及其价值取向表示尊重和服从。而我们显然应该尽可能地在古人的话语中,以古人的诠释来理解古典史家及其作品。
总之,古典史家历史书写的方式及著述的目的的确与今天的史学家不同,他们的因果概念也与我们今天的概念不同。他们并不像现代的学者那样关心细节的准确无误,他们也不通过分析和批判文献来“研究”历史,他们自然也就不会根据经验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历史的准确性。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要以迷人的风格叙述他们的故事,并以此将公众记忆保存下来。事实上,历史的含义并不只能从文献中获得,也能从记忆中获得,这是另一种历史的真实,即记忆的真实。因为,口述史(46)按其性质来说,同样是历史,它是一种来自社会并要求回到社会中去的历史。可以说,口述的历史非但没有偏离历史学家对于真实的追求,反而反映了历史生产的真实过程,以及当时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真实看法,而这也正是历史学家求真求实的根本。《历史》中的资料当然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记忆会影响希罗多德的叙述,他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更多依赖口头传说的社会,因此,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到希罗多德的局限性,但也不可否认,《历史》中的绝大部分仍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资料。希罗多德的世界是一个不同于我们生活的世界,他的想法及其出发点也与我们不同,但无论希罗多德与现代史学家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都不能使我们因此而否认他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作品的真实性及其价值。正如蒙米格里亚诺所说:“直到今天,他的《历史》仍然是我们研究希波战争和东方历史文化的最好的资料。如果没有希罗多德,希腊史和东方史的研究不会在17、18和19世纪取得那样大的进展。信任希罗多德是我们卓有成效的探索遥远过去的首要条件。”(47)
注释:
①从空间上看,东起印度、西至直布罗陀海峡,北到北极圈附近,南达尼罗河的源头,希罗多德都涉及了。从时间上看,从吕底亚王国的兴起(大约公元前680年)到希腊人击退波斯人的侵略(公元前479年),前后大约200年的时间。这还只是书中的主线,如果加上插叙中提到的其他事件,则有的可以上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②《历史》插话多的情况主要出现在前五卷中。后四卷因为已经直接开始叙述希腊—波斯战争,插话就减少了很多。
③所谓“共同生活”,韦尔南认为是指“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都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参见[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38页。
④Jean Pierre Vernant,The Greeks,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19-20.
⑤参见《历史》VII204,VII11。
⑥卢里叶:《希罗多德论》,转引自张广智:《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第79页。
⑦城邦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希腊人传播知识、探讨智慧、表演戏剧、讨论事务的主要方式仍然沿袭了荷马以来的口述传统,对于当时的希腊人来说,“讲述”是高于“写作”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完成形式。因为一个作者写出一段文字后,只有当他讲给大家听了才算是最后完成。
⑧转引自Amaldo Momogliano,"Friedrich Creuzer and Greek Historiography",In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Garland Publishing,1985,pp.75-90.
⑨19世纪的学者认为,希罗多德引用了许多散文记事家的作品。但随着早期散文作家著作残篇的系统出版,这一观点遭到否定。
⑩韦斯特在《希罗多德的铭文趣味》一文中认为,希罗多德常常误述外国的文本,似乎是在有意弱化蛮族的力量。参见S.West,"Herodotus Epigraphical Interests",CQ 35 (1985),pp.278-305.
(11)比如阿利等一些学者利用研究民间传说的方法再次研究了《历史》,认为《历史》中的许多资料来源于口头传说。参见W.Aly,Volksmarchen,Sage und Novelle bei Herodotus und seinen Zeitgenossen,转引自John Van Seters,In Search of History:Historiography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eal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p.41.
(12)Detlev Fehling,Herodotus and His "Sources":Citation,Invention and Narrative Art,J.G.Howie,tr.,Francis Cairns,1989,p.115,p.257.
(13)他们对“资料引用”作了严格的界定,即指“在既定的上下文中被归于一种资料或多种资料的任何持续的,或实质上是持续的叙述或陈述。”他们对各卷中有出处的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并制表说明,认为希罗多德在资料引用上似乎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即时间、空间距离和文化转换。施林普顿和吉利斯把时间的标准定为距希罗多德撰史前一百年。距离的标准是希罗多德所说的已知世界的尽头或是那些非常遥远而他不能到达的地方。文化的转换包括所有从非希腊文化向希腊文化的转换。(参见G.S.Shrimpton,History and Memory in Ancient Greek,Montreal & Kingston,London,Buffalo: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pp.235-239.)
(14)《历史》II123。
(15)有关例子可参见《历史》的第2卷和第4卷。
(16)《历史》I24,II121,II146,II9。
(17)Donald Kelley,eds.,Version,of History:From Antiquity to the Enlightenme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23.
(18)《历史》II 134。
(19)《历史》II 3,还可参见《历史》II 5,II 10,II 15等等。
(20)《历史》VIII 8。
(21)参见《历史》VIII 119-120。
(22)(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5页。
(23)(英)彼得·伯克:《西方历史思想的十大特点》,王晴佳译,《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
(24)Amaldo Momigliano,"The Place of Herodotus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in Studies Historiography,p.137.
(25)Shrimpton,History and Memory in Ancient Greece,p.230.
(26)洪涛:《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27)《历史》VI27。
(28)Donald Lateiner,The Historical Method of Herodotu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9,pp.189-210.
(29)《历史》I32,III40,VII10。
(30)转引自Michael Grant,The Ancient Historian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0,p.49.
(31)这与悲剧何等相似,在希腊悲剧中,“一个又一个的伟大人物穿梭于舞台,但结果都因骄傲而遭到毁灭。导致毁灭的原因是因为人自身的缺陷,因为人可以为所欲为;但神却注视着人类和自然界,他们会惩罚人类的傲慢。寓于悲剧中的道德教训是,人类必须培养sophrosyne,即一种适当的平衡和对自身真实位置的自觉。”参见:Chester G.Starr,A History of Ancient World,Oxford,1983,p.325.
(32)《历史》I91。
(33)《历史》I91,III64-65,III142,IV164。
(34)《历史》I207。
(35)《历史》II52,III108。
(36)《历史》II120。
(37)《历史》IV205。
(38)《历史》VIII137。
(39)韦尔南说:“德尔菲神庙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并不是像我们所假想的那样,是在称赞一种回到自身的转变……‘认识你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了解你的局限,明白你是一个凡人,不要试图与诸神平等。”见Jean-Pierre Vernant,ed.,The Greeks,trans.By Charles Lambert and Teresa Lavender Fagan,1995,p.16.
(40)在有关《历史》结构的问题上,西方学者通常分为两大阵营:一派被称为“分析学派”(analytic),另一派则是“统一学派”(unitarian)。他们的争论围绕着《历史》的起源、发展、主要的观点和最后的形式等等问题展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分析学派持一种发展的理论。他们认为,《历史》的各卷最初只是一些互不关联的单独的叙述,只是在某年某月,作者的兴趣发生了转变,遂将它们整理在一起。明显的证据就是书中大量的插话,以及缺乏明晰的、决定性的中心主题。希罗多德兴趣的转移也标志着他由旅行家或商人向历史学家转变的过程。然而该派的最大弱点在于,他们无法准确划分出希罗多德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统一学派则认为,贯穿《历史》的不仅仅是一个连续的主题,而且全书的叙述模式也极为一致,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渗透了作者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但即使在统一学派内部也没有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主题,而且他们也注意到希罗多德在叙述东方和希腊时明显存在着观念和语言上的差异。也有学者认为,两派的观点“并不是不相容的。”分析学派较好地解释了希罗多德是如何开始逐步撰写历史的,他为什么记载了如此之多的有关埃及的河流和风俗的情况,以及他为什么给每个故事以特别的形式和长度。统一学派则充分解释了贯穿始终的作者的精神和他的文学技巧。(参见C.W.Fornara,Herodotus:An Interpretive Essay,Clarendo Press,1971,p.5.)
(41)参见《伊利亚特》XVIII.497-508,XXIII.486。在这两个场合中,histor通常被理解为相当于仲裁者,根据传统习俗以及调查事实来判定过错在哪一方。
(42)《历史》II 35。
(43)《历史》VIII 3。
(44)Dionysius,On Thucydides,15,41.
(45)参见Woodman,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p.66,note 237.
(46)我们在文章中使用的是广义的“口述史”概念。而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Oral History)出现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从方法上说,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注重田野工作即实地调查的学科相结合的产物。
(47)Momigliano,"The Place of Herodotus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in Studies Historiography,p.141.
标签:希罗多德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集体记忆论文; 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希腊人论文; 荷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