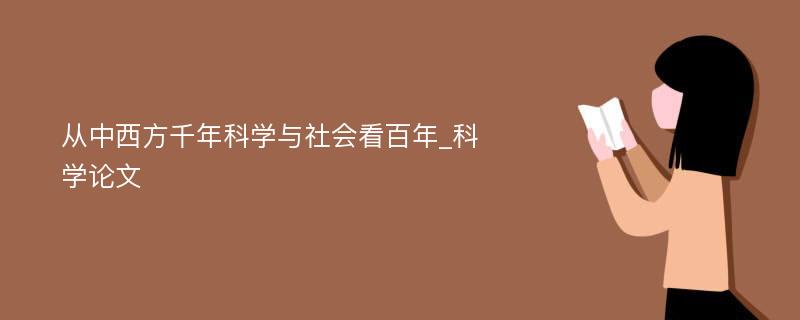
以千年看百年——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千年论文,科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并且在近百余年来迅速成长为世界文明的基础。但直到科学的迅速发展期中国才真正开始接受产生自欧洲的科学,并且迄今对于世界科学发展的贡献率仍然是微乎其微。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在科学上的失败,如何改变当今中国科学事业的落后状态,一般说主要通过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去探求。但有关科学与社会的讨论,通常多只作某种“因果性”的分析,往往忽略“目的性”和“偶然性”的分析,而实际的历史进程总是三者协调作用的结果。面对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检讨百余年来的中国科学事业,至少要回溯到千年以前世界形势的变化。那时欧亚大陆两端的文明发生了趋势相反的变化。西端的欧洲在基督教的旗帜下从分裂和混乱中觉醒而日益强盛,而东端的中国则从其发展的顶峰跌落下来而日趋衰败。欧洲国家体系通过大学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等一系列的变革,而攫取了世界文明的中心地位。中国虽然先后在北宋、明中和晚清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尝试,但分别由于“靖康之变”、“甲申鼎革”和“虎门销烟”而中断,并最终沦为世界文明的边缘地位。
1 科学与社会的一个思考框架
按照生物进化论推衍的观点,人类是地球上生物进化的一个偶然的结果,而作为自然进化产物的人类却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里的“文化”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广义文化概念,它包括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物质的和精神的创造成果。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是相对“自然”而言的,自然是人类的生存条件,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是连接自然和文化的惟一中间环节。任何人群总是要在人与自然、人与文化这两种基本关系中生存,不利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有时会构成对人类生存的“挑战”,因而不得不发挥其潜在的创造力而作出“应战”。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A.J.Toynbee,1889-1975)在其12卷本《历史研究》(1934-1961)中提出的的“挑战和应战”推动文化进化的观点,是本文主题讨论的重要论据之一。
人类是经过几百万年从猿到人的生物进化而开始进入其文化进化阶段的,并且其生物进化率似乎是恒定的,而其文化进化率则几乎是按指数规律增长的。人类学把文化进化区分为三个时代,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在几十万年来的文化进化中,绝大部分时间处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不过约为几万年而已,而文明时代只是最近的几千年。这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历史,绝大部分时间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只是最近的几百年,而以研发为主导的科业文明的兴起发生在最近几十年。人类的生物进化已退居次要地位,文化进化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人类基因组的信息量约为几十亿比特,人脑的信息量约为千万亿比特,而作为大脑集合的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文化信息量每年竟多达百亿亿比特,与文化进化相比人的生物进化已是微不足道。
按照人类学家怀特(L.A.White 1900-1975)在其《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1949)中进行的研究,文明时代的文化可以看作是由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如果我们进一步对其三个子系统进行划分,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主题讨论的另一重要论据。技术作为可操作的知识可以区分为三大类,即以自然物操作为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的行为操作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操作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作为人群的组织形式可区分为三大类,即以信仰为结合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力为结合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结合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也可区分为三大类,即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如果我们不认为文化系统中的三个子系统有进化链上的因果关系,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为环境,而自然界是整个文化系统的环境。按照进化论的观点,这文化系统的进化就根源系统自身的变异和环境的选择。文化系统的进化的历史表明,它经历了技术主导的农业文明和制度主导的工业文明两个阶段,并且正在走向观念主导的科业文明。
如何从这样的文化系统结构导出科学与社会的思考框架,关键在于科学的文化定位问题。对于科学可以分外延不同的三个层次理解,首先是纯粹的自然科学概念,其次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广义科学概念,再就是包科学、技术和工程在内的大科学概念。无论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还是广义的科学都定位在观念文化系统内,并且属于观念文化子系统中的理性类,信仰观念和价值观念是科学理性的直接文化环境,技术和制度两个子系统则是其间接的文化环境。大科学则定位在观念和技术两个子系统内,制度唯一地作为其文化环境。因此,我们有关科学与社会的讨论,对于纯粹科学来说其与信仰和价值的关系是首要的,而对于大科学来说其与制度的关系则是首位的。
2 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的冲突
文化进化的总趋势是游牧阶段先于定居阶段,但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这种进化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在广大的江河流域,由于得天独厚的沃土和风调雨顺的气候,人们易于扎根在那里从事农耕。而在森林、草地和沙漠地区,不仅土壤贫瘠而且极易受季节变化的影响,由于难以定居人们过着牧畜和狩猎混合的生活。所以在文化进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定居和游牧分叉的现象,在跟随食物缓慢游动的诸多漂泊群体中,有的群体有幸遇到沃土而定居下来,而有的群体则因没有这种机遇更明显地游牧化了。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H.G.Wels,1866-1946)在其《世界史纲》(1920)中所提出的两类共同体的概念,为我们的主题讨论提供了一个可以扩展的研究纲领。
游牧和定居两种人群的结群方式是不同的,定居的民族多倾向于结成“服从的共同体”,而游牧的民族则多倾向于结成“意愿的共同体”。所谓服从的共同体指定居区的人们屈从于神王或神授之王,国王具有非选举的神圣性及其天生的世袭统治权。而所谓意愿的共同体指游牧区的人们自由选择首领,首领是被人们追随而不是强迫人们服从的主人。由于安定的农耕生活所养成的习惯,定居的民族多身体柔弱而好和平。由于不稳定的而且不安全的游牧生活的锻炼,游牧的民族多身体强悍而好战。定居民族的顺从天性易于形成规模巨大的服从共同体并能持久地维持它,而游牧民族的倔强天性不仅难以形成巨大的意愿共同体,即便勉强形成也难以长期维持。
定居的民族视游牧的民族为野蛮人,而游牧的民族又视定居的民族为懦夫。当游牧的群体遇到生存危机时,他们往往以侵犯定居民族的方式来解决,于是就发生游牧民族与农业文明的冲突。沿着各种发展着的文明边缘,以好战的游牧部落和山居部落为一方,以好和平的城镇和乡村居民为一方,彼此之间经常发生争吵甚至袭击。一个在军事和政治上软弱的文明,被那些掠夺成性的游牧民族看作是一份长期有效的请帖。由于游牧民族作为征服者往往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强加给被征服的定居民族,这不仅中断了原地的文化而且把当时最先进的冶金技术用于铸剑而引向毁灭文化的无尽战争,并且随着战争掠夺的加剧而导致奴隶制社会出现。
在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反复斗争中,往往是那些征服了定居民族的游牧民族被同化于农业文明之中,因而富有冒险精神的游牧民族几乎总是为服从共同体提供新的统治者。虽然文明一直是沿着服从的共同体方向发展的,游牧的自由精神还是被部分地保留下来。它们潜藏在后代的血液中,特别是在君主和贵族的血液里,表现为扩张疆域和统一天下的那种强烈欲望。屈从与自由两种传统的斗争被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希腊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以及后来诸多专制与共和之间的左右摇摆表明,从服从的共同体转向意愿的共同体是人类潜藏着的天性。
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之间的这种冲突,贯穿整个农业文明史的始终并且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世界各地的许多主要古代文明中心,几乎都是在这种征服、同化和再征服、再同化的延续中形成的。在亚欧大陆上,由于有喜马拉雅山脉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种天然的屏障,这种野蛮与文明的冲突和融合基本上是在其两侧分别进行的。在这大陆的东西两端,虽然自两千多年以来就陆续地出现一些和平的贸易往来以及规模较小的冲突,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则主要发生在最近的一千年里。而且正是在东方和西方的大规模冲突中所导致的文化融合,促成了人类走向现代社会。
3 千余年来的中国与欧洲
大约一千年前后的几百年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亚欧大陆东西两端文明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交汇。一千年来,亚欧大陆的两端似乎发生了方向相反的变化。西端的欧洲在基督教的旗帜下从分裂和混乱中觉醒而日益强盛,而东端的中国则从其发展的顶峰跌落下来而日趋衰败。欧洲国家体系通过大学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等一系列的变革,形成了新的工业文明并从而成为世界文明的新生长点和地理中心。中国虽然先后在北宋、明中和晚清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尝试,但分别由于“靖康之变”、“甲申鼎革”和“虎门销烟”而受挫,并最终沦为世界文明的边缘地位。
这种情况的发生与中国和西欧之间的文化传统差异密切相关。虽然两者在文化的基本结构方面并无原则性的差别,但文化要素的结合方式却有明显的不同。在技术系统方面,在中国是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关系比较受重视,而在西方则是自然技术与思维技术的关系比较受重视。在制度系统方面,在中国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较受重视,而在西方则是政治与宗教的比较受重视。在观念系统方面,在中国是理性与价值的关系比较受重视,而在西方则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比较受重视。在所有这些差别中宗教的文化地位的差别最突出,在西方宗教足以同政治抗衡,而在中国宗教不过是政治的附庸,而且西方的宗教以入世为特征,而中国的宗教则是以出世为其特征。因此,在西方由于教权与王权的争斗民主和自由得以获得其必要的生存空间,而在中国则由于王权独行而限制了潜在的民族创造能力的发挥。
在中国由于赵宋王朝(960-1279)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907-979)短暂的封建割据,在面对来自北方的辽(916-1125)、西夏(1032-1227)和金(1115-1234)等游牧政权挑战的形势下,曾一度把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都发展到其繁荣的顶峰。金兵攻陷北宋都城汴梁的“靖康之变”挫折了其创造力的继续发挥,入主中原的蒙元王朝(1271-1368)短命而无所作为,宋元之际某些值得称道的科技成就不过是强弩之末,接下来的朱明王朝(1368-1644)把中国社会带到了更加专制的方向,再后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1644-1911)也没能走向融合创新的道路。中国社会在征服和同化的循环中进行着王朝的更替,疆域因入伙者带来大片土地而扩大了,但其文化创造力却犹如江河而日下。
在西欧由于日尔曼人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的查里曼帝国(742-843)的解体,才真正开始从奴隶制时代进入封建制时代。面对来自东方的塞尔柱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挑战以及黑死病带来的空前灾难,借助于基督教的精神文化和源于中国的技术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希腊科学传统的冲击,不仅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而且一个以民族为基础,以知识为条件的新型的意愿共同体也经过种种曲折而最终被发展起来。觉醒了的欧洲人通过大学革命、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开创了一个比延续几千的农业文明更为有效的工业文明,并且通过血腥的殖民活动把它推广到世界各地。葡萄牙在16世纪、荷兰在17世纪、英国在18和19世纪、美国在20世纪先后称雄世界。
贯穿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人类之主要冲突,本质是游牧的野蛮与定居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但自欧洲发展出工业的文明以来,人类的主要冲突就转变为本质上是新兴的工业文明与古老的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游牧与农耕之间长达几千年的连续不断的诸多冲突中,几乎总是落后的游牧民族进犯先进的定居民族,其结果又总是以文明同化野蛮而结束。而近几百年来的人类冲突,则几乎总是新兴的工业民族侵略古老的农业民族,其结果又总是古老的农业文明为工业文明所取代。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一直进行着的是农业文明同化游牧民族的过程,自鸦片战争以降的150年才面对工业文明的挑战,而且第一次感受到被异文化同化的危机。以千年看百年就是要认识和思考,中国曾经怎样和今后该如何应对这一前所未遇的新挑战。
4 百余年来中国的科学与社会
虽然在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中就发生了中国和西方的第一次碰撞,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在中国的真正冲突始于中英鸦片战争。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败北,使中国统治者确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略,产生自欧洲的现代科学技术在20世纪的中国迅速发展起来,在上半叶完成了基础科学的奠基,在下半叶又建立工业技术体系的基础。其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三大转变,既从传统到现代的心态转变,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模式转变和从国防到经济的动力转变。尚处在第三次转变途中的中国科学技术事业,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充满机遇和挑战地迎接新文明的时代。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考虑,应如何评价我们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中的表现?该如何展望世界历史的进程并筹划中国的未来?
在中国社会遭遇工业文明进犯的19世纪中叶,世界上诸多农业文明国家几乎都成了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面对被西方列强瓜分危险的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的变革,开明的政府官员们领导洋务运动、维新派政治家们发动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新型知识分子们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经历了一个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的变革过程。因为欧洲的现代化过程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技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是欧洲现代化程序的反演,在半个世纪中草率地反演了欧洲近五个世纪的现代化历程。这种程序倒置所固有的不彻底性导致此后的中国不得不程序紊乱地反复重演欧洲走向现代社会的诸进程。这种程序倒置或许并非中国现代化战略的错误,因为几乎所有后发现代化国家都有这种经历。不仅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如此,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印度和自称“脱亚入欧”的日本亦无不有如此经历。
欧洲工业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成功之关键在于,建设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市场与技术相互促进,民主与科学互为保证。市场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只有在市场的激励下企业的决策者才会不断地投入到技术进步之中。民主为科学发展提供思想自由的保障,科学创造不仅要有内在的思想自由,也需要由国家制度保证的外部自由。科学社会是嵌在大社会里的小社会,科学小社会是以大社会为其存在条件的。科学家们为获得研究的自由总是以承认占传统地位的社会准则为代价的。同样,任何社会要想接纳科学并发挥其社会功能,都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创造适合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科学进步的程度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使这些条件越来越充分地增长的。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障碍主要在制度方面,包括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协调问题。技术在中国长期没有市场经济的环境,虽然国际经济学界早巳证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最有效的经营方式,而在中国竟为要不要市场经济争论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制度一经转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以后,马上就面临缺乏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社会政治条件的挑战。因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要求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没有一个在权力、职能、规模等诸多方面严格受社会和法律制约的有限政府,完善的市场经济将难于形成。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有关政府机构改革的一系列举措也只是开了好头,如何构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限政秩序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追赶工业文明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终极目的,因为工业文明并非人类文明的终极形式,我们的目标应锁定在通过应战工业文明的挑战创造新文明。百余年来超越工业文明的诸多尝试,似乎都没有以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融合作为出发点,这或许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从工业文明产生的经验和百余年来世界发展趋势考虑,以观念为主导的未来文明将借助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而形成。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出这新文明的具体内容,但我们可以揣摩其特征将是科学理性与生命价值的结合。我们无法预料这新文明将产生在哪里,但在游牧与文明冲突中最有希望而却不幸丧失机遇的中华民族,无论如何不应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中再度错过创新文明的机遇。
收稿日期:2002-04-16
标签:科学论文; 游牧民族论文; 工业文明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