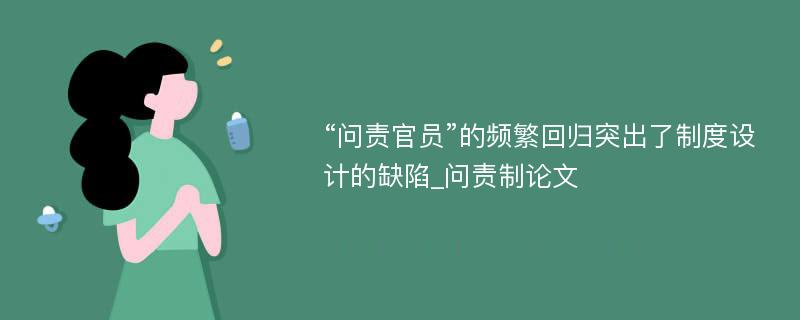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频繁论文,缺陷论文,官员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行政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近年来实施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人们在肯定问责制的同时,对官员被问责后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一个时期以来,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问责官员”频繁复出何太急
近年来,在公众的助推下,“问责风暴”一再掀起,由一些重大突发性事件所引发的官员引咎辞职、免职的现象也日渐增多。然而,就在广大群众为之叫好、拍手称快的“火线问责”过后,一些“问责官员”却悄然复出、重新上岗,有的换岗为官,有的异地履新,转瞬间就“东山再起”。在一些地方,“问责”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问责官员”们躲避风头的“港口”,一旦“问责风暴”吹过,他们便再次走马上任。联想起诸多曾被问责的官员纷纷易地为官,人们在问:问责制到底怎么了?
2008年发生在贵州瓮安县的“6·28”群体性事件震惊中外,瓮安县原县委书记王勤也因对事件处置不当而被撤职。日前,媒体相关报道披露,王勤已经复出,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另据报道,山西临汾“黑砖窑”虐工事件曝光后,副县长王振俊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撤销行政职务。然而,撤职没过几天,王振俊便以县长助理的身份再次上岗。
事实上,被问责官员短期内重新当官的新闻并不少见。2009年3月因三鹿奶粉事件被国务院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已于2009年4月出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不但鲍俊凯异地复职,因三鹿事件而被记过的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也早在今年1月份被选为邢台市市长。
其实,被问责后不久即复出的,并不局限于地方干部,一些在各种具有广泛影响的事件中负有不同责任而被问责的高级官员也在悄然之间纷纷复出。2003年因处理SARS疫情不力,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其后张文康转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任,并当选全国政协科文体委员会副主任,而孟学农则获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委办公室副主任,后任山西省省长,但复出刚满一年又因为襄汾溃坝事故再次请辞。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解振华因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此后不久,解振华的名字出现在国家某部委新领导名单中。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井喷特大事故夺去了243条人命;2004年4月,中石油老总马富才提出引咎辞职,后复出任国家能源办副主任……
应该看到,一些官员被问责丢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刚刚调任某个地方,工作情况还不熟悉,就因为发生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而引咎辞职;有的没有履行安全监管义务,由于事故重大,不得不辞去现任职务;有的确因失职、渎职导致发生重大责任事故被撤职。他们在事故中有的负政治责任,有的负道义责任,有的负法律责任,尽管应负责任程度不同,但这些“问责官员”复出的理由、过程、条件等关键性的问题,都无一例外地不透明,民众不知情。这不能不令公众困惑不已,许多人质疑:为什么那些被问责的官员会在被问责后短时间内纷纷复出?问责制到底有没有漏洞?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问题的关键不是“问责官员”能不能复出的问题,而是复出的理由充分不充分、程序合理不合理、民意是不是得到尊重。
二、对官员问责走过场挑衅党心民意
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政府官员都有明确的任期目标。如果在任期内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官员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即使事故不是行政一把手直接造成的,也应为此承担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但如果把被问责的官员撤职,风头一过就又悄然官复原职,或者易地任职,这种“避风头”式问责无疑是对问责制的异化,与行政问责制初衷相去甚远,让问责效力全无,其危害性是明显的。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有损政府公信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官员也是人,也会犯错误。“问责官员”并没有原罪,但被重新任用必须符合程序,尊重现有制度。如果复出无理、无据、无程序,那官员的复出就很难让人心服口服,这种“躲猫猫”似的问责制度本身可能就需要被问责。现在大多数地方复出的“问责官员”,都是在一种非常态、不公开、不透明的情况下被起用的,群众对其复出的过程不知情,从而认为政府有暗箱操作之嫌。这种人事任免公平公正的法定程序的缺失,破坏了公众对政策的信任感,自然会影响和破坏党委、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公信力和形象。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有悖现行法治精神。对官员问罪与定罚应该循法,量才与起用更应当循法。如果“问责官员”复出没有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仅凭领导者的个人意志,那么“法治政府”在民众心目中就成了口号。从目前看来,尚未形成一套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犯过错误或违过规的“问责官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曲线做官”、“异地做官”,甚至重回重要领导岗位,并掌握各种实权。很显然,在没有保证程序透明和公正的前提下就再次安排“问责官员”上岗,某种意义上,其必然呈现出“人治”特征,这是有悖于现行民主法治精神的。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冷却民众参与热情。对官员问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意的一种表达方式。实践证明,官员问责制的建立、完善和发展有赖于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也只有在群众积极参与下,才能对政府行为提出质疑并实施责任追究,才能增强政府对群众需求的回应性和调适性。“问责官员”接二连三“东山再起”,就是对民意的嘲弄。被戏弄的广大民众必然产生对政治的厌恶之情,随之生成的政治逆反心理也必然会使得其政治参与、政治监督的热情逐渐减弱,甚至会呈现出一种政治冷漠的心理表征。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消解制度警示作用。问责不是一种政治表演,不是为了做给舆论看和讨好公众,不是为了安抚死难者家属和平息公众愤怒,而是让官员为自己的失职付出代价,在问责中震慑官员,从而避免悲剧的重复发生。杀鸡骇猴、以儆效尤,问责的目的是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问责官员”轻易复出,不仅没有达到问责的效果和实现惩罚的初衷,反而给其他官员造成一种暗示,即“问责风暴”就像一阵风,只要躲过风头,过后一切安全,照样当官。这不仅使得问责制流于形式,更重要的是对其他官员也没有任何警示和教育意义。
三、官员问责制度设计存在先天缺陷
问责制在我国发展历史不长,总的来看,这一制度设计有利于整肃吏治,优化干部队伍,增强干部的责任心,也有利于疏通干部能下的渠道。让那些无所作为者下台,才能使那些有所作为、大有作为者上台,形成良好的能上能下、新陈代谢的用人机制。但在实施过程中,问责制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问责官员”复出容易引起人们的争议,也主要是人们对官员复出的原因、条件和程序不清楚。
问责制缺乏专门成文法。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的行政问责法律,只有一些行政制度和散见于相关法律中的规定碎片,问责的法理依据主要是《公务员法》、《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在这三种规范性文件中,只有《公务员法》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其他两种规范文件虽有一定约束力,但只能算是执政党内部纪律规范,行政问责还没有专门的、完善的成文法。正因为问责制法理依据不完善,问责处理在法律上缺乏可操作的程序,加上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以至于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
问责制缺乏内在驱动力。在问责制成熟的国家,问责与事件影响大小和民愤没有多大关系,问责制的运转依赖的是“失职就必须担责”这种责任伦理的驱动。但在我国,目前问责制的运转主要依赖于媒体和舆论的外在驱动。很多事故发生后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多数并非制度自动驱动的,而是舆论关注的压力迫使问责制度运转起来。只有某个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关注和激起很大的民愤时,在强大舆论压力下,相关部门才启动问责制,处理几个官员给舆论一个交代。如果缺乏舆论关注或压力很小,问责程序很难正常运转起来。缺乏一种“违规即追究”、“失职即问责”的内在驱动机制的问责,让官员对躲避问责心存侥幸。如果某种失职能够瞒过媒体,也就能躲过问责。即使“不幸”成为舆论焦点而被问责了,当某一天淡出舆论视野的时候,也一样可以瞒着媒体悄悄复出。
问责制主体和范围过于狭窄。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才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对象应是人民群众,官员问责的主体也应是人民群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同级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要对人大负责,人大代表有宪政权威上的质询权。但现在的问责还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同体问责,缺乏人大、群众等异体问责,更缺乏对上级的问责。仅仅是同体,而且是上级对下级,这样的问责制度显然难以实现责任政府的目的。在问责的范围上,行政问责一般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且一般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行政问责事由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问责一般只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问责的环节也多局限于执行环节而少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问责制操作程序大而泛之。制度设计粗疏,导致对官员问责过于随意。是否问责、如何问责,大都由地方、部门各自确定;问责往往因人而异,该问责的不被问责,或者问责过了头,甚至出现官员开会打瞌睡即被免职的简单式、粗暴式问责。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会被撤职,追究责任会追到哪个级别和何种程度,除撤职外还须承担何种责任,以后又如何复出,这些都还没有制度化和规范化。只有这一切成为稳定、必然的制度,才能给官员确定的预期。否则,官员只会对同僚被问责充满“碰上了就自认倒霉”的同情,而不会反思自身的职责。被问责者也会对被撤职毫无愧疚之感,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只平息民怨的替罪羊。
问责制监督环节不完善。完整的制度体系,一般都要包括制度的设定、操作和监督、反馈等环节,形成自足的闭合系统。目前,大多数地方的问责制体系缺乏监督、反馈环节,使制度执行的效果大打折扣。首先,在问责过程中监督不到位。由于尚未形成程序性问责,在问责过程中,谁来监督、监督什么、如何监督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方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次,问责后的监督存在缺失。问责后的监督包括问责的效果如何、公众有何反应。就目前而言,这方面的监督还不够健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莫让问责变成平息民愤、取悦舆论的作秀
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不断规范和完善,与之相对应的官员复出机制却并不健全,相关规定十分模糊、笼统,缺乏操作性和程序性,弹性和随意性很大,成为实施问责制的瓶颈。当务之急,是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的原则,制定一部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厘定问责标准,规定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可喜的是,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标志着党内第一部专门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规面世。贯彻好这一法规,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必须做到“五个明确”。
第一,要明确问责的责任主体,解决由谁来启动和实施官员责任追究的问题。完备的问责制必须具备完善的问责责任主体制度。在行政问责制下,须强化上级监督下级的责任,但根本上是为实现向人民负责的目的,不能将问责制简单地等同于上级惩罚下级。要建立问责的长效机制,在强化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问责责任的同时,必须运用已有的其他制度资源来健全行政问责制。按照国家制度的设计,人民代表大会有依照宪法和法律对各级政府监督的职权,人民政协可以通过政治协商对各级公权机构进行监督,人民团体因可以依法进行政治参与而有权问责,这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二,要明确问责的对象范围,解决向谁追究责任的问题。问责就需要严格划定责任对象范围,明确哪些人需要承担公共权力不当使用或者未尽职责的责任。问责对象的划定,要按照权责相一致的原则来进行。授权的范围有多大,就应当在多大的范围内问责。近年来的问责对象主要是针对行政官员,但考虑到现实的公共权力格局情况,问责对象的范围并不能限于此。而且,问责的介入时间也不应局限在事件发生之后,可以拓展到决策和监督环节,比如对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质询、听证等。如果问责与现实的职责格局不符合,则难以起到问责的真正作用。
第三,要明确问责的事项事由,解决如何确定追究责任事由范围的问题。现实中问责的大多数是对社会生活造成直接损害的公共事件。对造成社会普遍不满和震动的事件必须问责,但其范围也应科学界定。从制度化、规范化角度,可进一步确定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而采取不同的问责措施,以提高问责的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程度。在这一情境下,明确规定“问责官员”应负什么责任,怎样才能复出,什么条件才能升迁,问责制才有可操作性。解决这一问题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规定公务人员的各自职责,明确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使一个公务人员对履行什么职责、承担什么责任一目了然;另一方面,科学规范对官员问责的事项、程度,使党政干部对应承担政治责任、道义责任还是法律责任一清二楚。总之,事故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果会导致官员下台,官员心里要有数,老百姓心里也要有数。
第四,要明确问责的方式手段,解决如何追究责任的问题。问责的方式手段,是问责制的重要内容。方式手段真正落实了,问责制的意义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强化问责手段措施的落实,仍然是当前完善问责制过程中的重要任务。要完善问责的相关实体和程序法律规定,解决问责的方式、步骤和证据规则不清等问题,实现问责的制度化。官员问责的一般程序主要包括立案、调查、申辩、公布调查结果、提出处分意见和做出处分决定。官员问责程序的主要制度具体包括回避制度、听证制度、申辩制度、救济制度、公开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
第五,要明确问责的责任期限,解决追究责任时限的问题。现代行政伦理表明,对行政人员责任追究是有时效的。对于曾经负有责任而降职、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并非一概不能起用。如果因为一次失误,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这样的问责过于偏执。相反,给“问责官员”一个复出的机会,给那些改正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成绩的“问责官员”一个升迁机会,更能体现出制度的善意与理性。既要防止把那些被问责的官员一棍子打死,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也要防止过快地让其复出,甚至让其凭不正之风将问责的效果虚化。对于那些确有所长,或者在实践中重新赢得社会尊敬的,应当通过公开的方式,特别是通过群众选举的方式,允许其重新参政。对于主动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可以予以适当安排,并建立健全跟踪、考核、评价机制。对进步较快、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绩的,可根据工作需要予以提拔使用,努力形成领导干部既能上能下又能下能上的良好局面。
标签:问责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