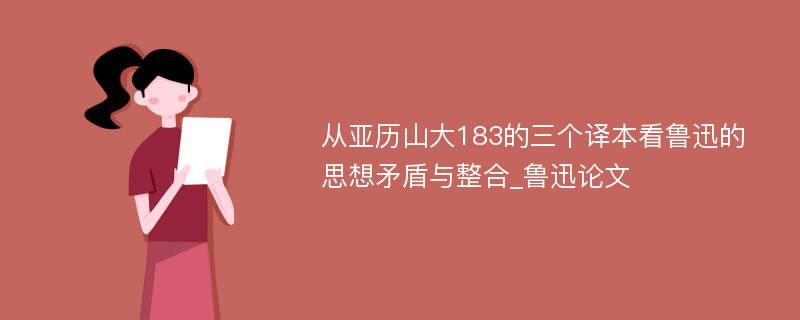
从《亚历山大#183;勃洛克》三个译本看鲁迅的思想矛盾及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克论文,亚历山大论文,鲁迅论文,译本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历山大·勃洛克》是托洛茨基所著《文学与革命》的第三章。托洛茨基在时代变革的辩证认识中,肯定了勃洛克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这位表现前革命时期特有习俗和节奏的作家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尤其关于勃洛克代表作《十二个》价值与意义的探究和发现,体现出托洛茨基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成熟的政治意识。此书对鲁迅影响深远,可以说鲁迅后期思想的变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学的许多见解均与之相关。1926年,鲁迅为北京大学俄语专修科学生胡斅所译《十二个》校订,并亲自翻译了《亚历山大·勃洛克》放在诗的前面,又作《〈十二个〉后记》加以解释,这是《文学与革命》部分内容在中国最早的翻译。1927年傅东华翻译了全文,由汉口《中央日报》副刊连载。1928年韦素园、李霁野再次翻译,以未名社名义出版。1960年王凡西又根据1957年9月纽约罗素书店出版的英文再版本全译。其后王士花根据内村刚介版本译出,晚近还有刘文飞、王景山等人的译本。未名社发行的译作大都出自鲁迅和他当年所培育的文学青年之手,他们的译本在接近鲁迅1920年代对苏俄文艺态度方面具有很好的参照性。王凡西早年留学苏联,拥有较为完整和丰富的认知托洛茨基的文化背景,颠沛流离的生涯中矢志不渝地关注和研究托洛茨基主义,本着对托氏虔敬的信奉和中国革命问题深入的观察,王凡西重译《文学与革命》,王译对原著的尊重和对历史的透彻使得其书在知识体系、现实视野上富有无可比拟性。故而,本文采用韦、李版本,王译版本与鲁迅所译《亚历山大·勃洛克》作对照,以期把握鲁迅翻译的特有方法和原则,以及翻译式样背后所隐藏的思想矛盾与整合情况。 《文学与革命》是一册循序渐进地论述无产阶级文学发生、形成、本质以及方向等问题的著述,第一章谈前革命时期的艺术,第二章介绍“同路人”文学,接下来就专章研究勃洛克。作者起首便承认勃洛克属于十月革命以前的文学,但并未因此降低对勃洛克的评价,反而从勃洛克象征主义的两重性,勃洛克进入革命的方式,书写革命的策略,表现革命的手段等多个方面讨论了勃洛克的时代意义。托洛茨基把握写作对象的这种平等观念和整体立场唤起鲁迅的“旧营垒”身份认同不容置疑,但鲁迅的翻译中却出现了较为鲜明的对好恶的显现和遮蔽,逐一来看: (鲁译)勃洛克是知道智识阶级的价值的——“无论怎么说,我在血统上也还是和智识阶级连接着,——他说,——但智识阶级总常被放在束缚的纲中。”① (韦、李译)勃洛克知道知识阶级底价值:“我也一毫不差是知识阶级底有血统关系的亲属”,他说,“但是知识阶级常常是消极的。”② (王译)勃洛克认识知识分子的价值。他说:“我终归还是知识分子的血亲,但知识分子从来总是否定的。”③ 对比之下,三个译本最大的区别在于“束缚的纲”、“消极”和“否定”。翻译的年限越往后,可参阅的版本就越多,韦、李和王凡西应该都熟知鲁迅的译文,但却都未使用“束缚的纲”类似词语,反而选取了接近的“消极”与“否定”,后者词性所含贬义色彩,且批判程度强于前者。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勃洛克既自知个人所属阵营,同时又对其进行评判。鲁迅所译的勃洛克并没有彻底地抨击这个与自己关系紧密的阶层,而着意指出这个群体先天的不自由。那么,勃洛克究竟看到了智识阶级的哪些桎梏?——“风呀,风呀!/人的脚都站不住……滑呀,难走呀/每个行路的人/都会滑倒”,这是《十二个》里的诗句,对风和雪的感受在同年写作的《俄罗斯和知识分子》中进一步得到阐述,“革命,像大旋风,像大飞雪,永远带着新的和出人意外的事物,它残酷地欺骗了许多人,它轻易地在自己的漩涡中损毁了有价值的人,它常常把没有价值的人带到陆地上来而不受到损害。”④勃洛克作为智识阶级的一分子感受着革命,体会到革命巨大的挟裹力,这力既是摧毁朽坏旧物的利器,也是不能商量不可回避的指令,一旦卷进那洪流便只能顺从革命的节奏。智识阶级的先锋性决定了只能受此约束,由诗印证:勃洛克的束缚感即为革命开启之后的直观情绪。 是否可以认为鲁迅也因为感知到勃洛克的困境,所以采用了“束缚的纲”的翻译?确实如此。我们知道,鲁迅在1920年代初期谈论革命大都不是指代切切实实的社会革命,那他内心的束缚感究竟因何而起?换句话说,鲁迅借勃洛克之口说出了智识阶级的处境,他怎样“总常被放在束缚的纲中”?与“束缚的纲”相对的即为反抗,鲁迅对于反抗有过表白,“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他自己解释为“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⑤那就可以知道所谓束缚一定不是身外的牵制,而在于内部的挣扎。鲁迅在翻译对象那里投射翻译主体的精神写照,可以从当时他本人在思想、情感、历史、时代等多层面所受的束缚来解读。在思想方面,鲁迅受到“灵魂里有毒气与鬼气”⑥的束缚,老庄与韩非对鲁迅来说都是塑造他的资源,鲁迅在更为古典意义上接受了思想的规训,而他则需要用这种精神的内质来做吸纳新思想的基础。讲出这个心理真相的同一天(1924年9月24日),他写作了《影的告别》与《求乞者》。两篇散文诗一则剖析作者的思想暗影,一则对他个人阴影的否定以及在此暗影之下生活方式的嘲讽和拒绝,字面背后隐含着无法安放的主体自我斗争的荒谬感和虚无感。在情感方面,鲁迅认为当人与人之间的爱被伦理道德诓骗为一种畸化的牺牲或报酬时,就会导致人的本质的弱化与消解。无论是父与子之间,还是非血缘的相识关系,他都希望“‘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⑦抑或如过客,既不带走小女孩的裹布,也不接受老翁的挽留,但是拒绝布施的独自远行使他面临人群中温情与恩义的缺失。在历史方面,鲁迅家庭出身和情感出身的分裂使他在更激进的情势下理解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相互制约。根据冯雪峰的回忆,“我(指鲁迅——引者注)除‘本阶级’,即小资产阶级或‘封建残余’外,比较熟识的,还是农民。但也已经长久隔离了。现在如再去接近他们,他们会用特别的眼光看我,将我隔离起来了”。⑧也就是说,鲁迅心底深处是洞悉这种区别的,而且在《故乡》中已经有了暗示:“我”是“辛苦辗转而生活”,闰土们是“辛苦麻木而生活”,同为辛苦,“我”所代表的智识阶级和闰土代表的无产阶级在生活的心态和形态上已做出区分。在时代方面,尽管十月革命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对1920、1930年代新兴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形成巨大的辐射力量,以俄为师的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第二轮思想输入的浪潮,但对鲁迅而言,新的思想的共鸣一定要从生命实践中迸发出来。既然从地理空间上远离革命漩涡,从信息接收上错位革命潮流,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缺乏直观体验,也就无法据此准确判断和调整个人革命策略。以上列举的这些束缚,大都是鲁迅屡屡提及,或者由他的文章反映出来,有的来自翻译主体的身份局限,有的根源于客观条件的拘束,这种束缚之力是普通新青年或同时代知识分子难以想象和体会的。韦素园、李霁野和王凡西都不是在鲁迅的立场上感受中国智识阶级面对革命而生成的矛盾,他们用了一种外在的评价术语“消极”和“否定”,潜意识里承认了勃洛克的落后而做出检讨。鲁迅对革命的渴求、奉献以及身在其中受到的阻碍,使他应用了“束缚的纲”这样具有属己性质的语汇,试图诉说的是个人投身革命的努力尝试和无奈境遇。 (鲁译)骇人的变故的音乐,授意了勃洛克:你到今所写的事,全都不是那么一回事;另外一些人在走着,带着另外一些心;在他们(革命人),这是无用的;对于旧世界的他们的胜利,同时也显示着对于你的胜利。⑨ (韦、李译)可怕的大事件底音乐,感兴了勃洛克。这似乎向他说:“你直到现在所写的东西,都是不对的。新的人来了。他们带来新的心。他们不需要这个。他们对于旧世界的胜利,显示着对于你的胜利”。⑩ (王译)可怕事件所组成的音乐感动了勃洛克。它仿佛在对他说:“以往你所写的一切都不对。新的人正在来临了。他们带来新的心灵。他们不需要这个。他们所取得的对旧世界的胜利,也意味着对你的胜利”。(11) 勃洛克将革命称之为“一部盛大的Orchestra(管弦乐、和声——论者注)”,意味着革命的感染力以及呈现的形式正如不同的音按一定的法则同时发声而构成的音响组合,即革命瞬时的思潮是杂沓的,内部充满异声。然而,即或是这样危机重重的革命阵营也对勃洛克进行了不屑的嘲弄。作者描绘勃洛克在革命形势中的被动与孤立,比较三段译文,有两处明显的差别:鲁迅把现有革命对勃洛克的宣判译为“不是那么一回事”,而其他版本则直接译作“不对”,与此相应,鲁迅把勃洛克的对立面译为“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心”,而韦、李和王翻译成“新的人”、“新的心(灵)”。从字面来看,鲁迅所译的感情色彩更中立,没有正误对错的价值论定,也没有新旧优劣的褒贬之意,仅仅作为一种历史发生的并行现象给予客观的描绘。这是因为鲁迅既能够深解古今新旧之辨,更具备取舍时机的裁决。首先,他当年反对读古书,所反对的是陷于个人喜好地摆弄古学,并没有从根本上除去古书之意。同样,勃洛克即使成为革命的对象,也不能证明他此前的一切思想和创作就没有价值。从感情层面来讲,鲁迅是无法认可将勃洛克的创作视为“不对”的。勃洛克身为革命前的作家,“将这革命的承受,竭力用了极端的形状来表现……娼妇的团结,赤军兵士的卡基卡杀害,贵族层楼的破坏……然而他说——承受这个”,《十二个》证实他从革命中采取了精神路向,这种直视革命并抱拥革命的姿态是有力的、正面的。其次,当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十月革命风潮传到中国来时,鲁迅对苏联的好感并不能立马移植到对应的社会革命中,他存有对革命基础和革命依靠力量的怀疑。尤其是挂了革命的招牌是否就具有革命的进步性,在鲁迅看来这尚难确定,于是,能不能谓之“新”也就值得商榷。鲁迅以“另外”来称与勃洛克不同的类型,一则肯定了勃洛克的革命合法性,同时也表明了对革命肇始时期怀着各种动机的革命分子的保留态度,因此,他用“一些人走着”代替“来了(正在来临)”。 在鲁迅心目中,真正的革命和革命者能否来到尚是未知,“走着”更像是说一切还在“进化的链条上”。当他被称为“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的“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他的创作被贬斥为“死去了的阿Q时代”,鲁迅只辛辣地回应:“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意在表达普罗文学大潮“奥伏赫变”的姿态并不能掩藏“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而恰恰是“五四”一代才具有那种真正的革命性。包括“左联”批胡秋原、苏汶为比民族主义文学“更前锋”的敌人、“统治阶级的走狗”,鲁迅并未认可其论调,而是较为公允地分析了“第三种人”的艺术观、政治观和相应的阶级立场,并且将解剖也指向左翼内部,坚持要团结“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12)在“同路人”队伍不断分化和转变的年代,鲁迅动态地、发展地看待革命进程,给躁动、偏激的理论批评界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阶级原则,这一革命文艺思想体系的建构,与他翻译托洛茨基时的独特见解密不可分。 对于翻译,鲁迅认为“‘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同是一种外国文学,“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绝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他还说到自己翻译《苦闷的象征》,“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13)《苦闷的象征》译于1924年9、10月间,也即是说,那个时候,鲁迅的翻译观就成熟并固定下来,强调翻译以信为主,顺在其次。与《亚历山大·勃洛克》另外两个版本相比,鲁迅时有增删,这些解释、评论或隐去的文字,可以看到鲁迅对勃洛克以及所处时代的理解。 (鲁译)第一革命将他从个人主义底的自己满足和神秘底的寂静主义拉开,而向他突击。革命中间时代的间隙,在勃洛克感到了好像精神底空虚,时代的无目的性——好像用莓汁代替了血的闹戏场似的。(14) (韦、李译)第一次革命进入了他底灵魂,而且把他从个人主义的自满自足和神秘的静死主义拉开。勃洛克觉得两次革命中的反动,是一种精神底空虚,而于时代底无目的性,他觉得是一种以莓汁替代了血的闹戏场。(15) (王译)第一次革命进入了他的灵魂,将他从个人主义的自满与神秘的恬静主义(Quietism)中拉开来。勃洛克觉得两次革命之间的反动时期是一种精神的空洞;那个时期的浑浑噩噩,他觉得是用蔓越橘汁来代替鲜血的马戏场。(16) 这段话描述了勃洛克在俄国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这期间的思想情景:诗人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感召,保守颓废的个人意识受到动摇,而同时,勃洛克也意识到革命的不彻底。在具体形容第一次革命与勃洛克关系的时候,三个译本的差异就在于鲁迅增添了“(革命)向他突击”这个态势的书写,韦、李和王较为一致,均采用“革命进入灵魂”的翻译,“突击”和“进入灵魂”相比,前者明显地凸出革命的侵扩性和革命声浪中每一分子的无力拒还。鲁迅为何要强调这种力的不平衡?对鲁迅来说,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个人主义是抵抗泯灭个性的封建意识的借助力量,而且,尼采式的个性塑造被他引为精神进化方向。鲁迅早在日本留学阶段就已经完成了现代意识的建立,可这一个性的苏醒并没有为他开拓社会革新之路带来显著的成效,相反,超前性的个人主义让鲁迅更加深味集体无意识的麻木和腐朽。因而,鲁迅完全熟悉勃洛克在革命爆发的时代中,为强大革命精神所攫获的状貌,不是革命者掀起潮流,并叱咤于波诡云谲之中,却是震慑于革命威力,做出对自身精神结构的深刻反省与重置。翻译中还有一处鲁迅减略的地方,韦、李和王都译出了“两次革命”中间的“反动”时期,鲁迅译为“革命中间时代的间隙”,为什么不显现“反动”的含义?“反动”在语境中更接近落潮的意思,即革命意义的背离,这就关涉到鲁迅如何认识两次革命的关联。从翻译时间可知,鲁迅亲历的第一次革命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国共合作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战争应当是第二次革命。中华民国建成之后的十余年内,鲁迅有过沉寂,也有过呐喊和彷徨,如果说勃洛克感受到了精神的空虚和时代的无目的性,鲁迅更是感同身受,但这种虚无却是不一致的。“革命时常还要走走曲线路,但是布洛克不愿有任何的调和。在最恐怖的时日,革命有时在自己的血路上还震动颠簸一下,然而布洛克……爱上了革命的心灵,而非革命的理性和计划”,(17)也就是说,勃洛克对革命本质并没有形成个人独立的见解,因而会因为表象的变动而承受内心的期待、失落和虚空。1925年国民革命高潮之际,鲁迅借安特列夫《往星中》谈到自己对革命行进和暂停的理解,“我以为人们大抵住于这两个相反的世界中,各以自己为是,但从我听来,觉得天文学家的声音虽然远大,却有些空虚的。这大约因为作者以‘理想为虚妄’之故罢。然而人间之黑暗,则自然更不待言”,(18)天文学家的儿子为了拯救穷民参与革命而入狱受虐,天文学家以“无限的宇宙”为目标,活在“冷而平和的‘自然’中”,儿子的未婚妻以“诗的、罗曼的、情感的境界”为鹄的,愿意回到“热,满有着苦痛和悲惨的人间世”去。从安特列夫的象征来看,父亲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儿子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其妻带着小资产阶级的动机拥抱革命,鲁迅没有否认后者的合理性,却肯定了两种属性革命的紧密联系。在他的意识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截然的“反动”,而是像他多次表达的一切都在历史进化的链条上。翻译的增删,与鲁迅当时整个的世界观变化相关,无论是强化革命发生的情势,还是对革命浪潮涨落的认识,都饱含着他对勃洛克特殊的定位,这一评价又基于对作者托洛茨基的信任和对自我历史境遇的体察。事实上,当社会革命发生,新的思潮勃兴,在鲁迅心里唤起的是对过去数次革命的比较和思索,托洛茨基以连续的、动态的、整体的原则把握勃洛克在革命传承路上的得失贡献,引发了鲁迅的认同和共鸣。勃洛克创造了革命前的艺术,更深深地被十月革命吸引,“既被时代所卷走,又将时代翻译成他内心的语言”,《十二个》的写作呼应了鲁迅所认为的:“呼唤血和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是空洞。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他看到勃洛克“真的神往的心”,像他一样接受着生命的驱使,并感同身受地写到,“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进了,然而反顾,于是受伤”。(19)那种隔着时空的知遇感,使得他在译诗时更兼顾了勃洛克的革命话语。 (鲁译)这样——满足者都愤怒着,沉重的肚子的满肚是厌倦着——槽不是翻倒着么,他们的烂透了的牛牢不是闲着么!(亚·勃洛克,《满足者》。)(20) (韦、李译)一切饱足者是这样愤怒,大肚子底满足是这样渴望,他们底槽子翻了,他们底牢中起了纷扰。(《饱足者》)(21) (王译)被喂养的是如此地咆哮,一切显要的肚子如此地热望装饱,他们的槽儿给打翻了,他们龌龊的厩栏就弄得一团糟。(《被喂养的》)(22) 勃洛克曾说“一个真实的诗人的诗歌的形象、节奏,时常总是由当时的时代暗示给这个诗人的”(23),此诗中所描写的旧世界的食客即为资产阶级的恶棍,勃洛克对这样一批人的认知建立在他革命化的心态之上,鲁迅洞悉这一情绪并阐释此诗。与另外两个译文相比,从切入点选择来看,鲁译侧重于从进行时态(另外两个版本是一种过程的叙述,呈现为现在完成时态)表现满足者的贪欲无度,暗含着“愤怒”从过去到现在未曾停止,甚至还有无限膨胀的可能性,因此革命的紧迫性和必然性就呼之欲出;从理解的偏好和偏重点来看,鲁迅认为剥削者的压榨是“沉重的肚子的满肚是厌倦着”,其本质便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厌倦”一词意味着既得利益的侈靡豪奢,其代表的阶层反映出历史的落后性和腐朽性;从对文本的期待值来看,鲁迅用“不是……不是……”揭示了革命发生的动力机制,否定的语气创造出一种革命者与革命相关联的生命意志。可以说,诗句的译出完全反映了鲁迅沿着勃洛克的主体视域运行的轨迹,鲁迅对诗情和内涵的准确把握拟题为“满足者”,与“饱足者”和“被喂养的”相比,后者更平面化,直接陈述的写实性更强,而鲁迅的标题还原了象征意象的丰富与厚重,这恰恰是勃洛克诗歌最突出的特征。“满足者”的核心是无法餍足,既是权势地位的贪得无厌,也是压迫勒索的不择手段。正是因为鲁迅对勃洛克的两心相通和惺惺相惜,鲁迅的译笔才保证了既从个人心灵深处而来,又符合勃洛克原诗的意境。 选译《亚历山大·勃洛克》出于鲁迅对勃洛克文学才华以及革命进步性的肯定,尽管鲁迅欣赏和理解勃洛克,但对其投身革命的方式和程度仍做了客观的认识,从侧面也体现出鲁迅辩证的革命意识。这一思想倾向隐含在鲁迅有目的地突出施动行为和被动受者区别的翻译技法上。 (鲁译)他的觉得混沌者,就因为他没有使主观底的事物和客观底的事物相一致的才能。又在强大的震动已经准备,以后便爆发了的时代中,他也没有本身意志,能自己作最深的警戒,受动底地等待着。(24) (韦、李译)他所觉得是混沌者,是他无能力把主观和客观的东西结合起来,是他底小心谨慎的意志力之缺如,在先见到最大事件底预备,后见到最大事件爆发的时代中。(25) (王译)他感觉到混乱,那是因为他不能将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中,当最伟大事件的准备与后来的勃发均可见到的时代中,他却小心谨慎,徘徊却顾,缺少意志力量。(26) 这是托洛茨基对勃洛克较为深度的一个剖析,也是勃洛克被称为前革命艺术的根本原因。所谓“主观”指的是个人在历史动荡中的精神根基与转换,“客观”即社会形势的发展与演变,主客观的调适往往有三种形式:主观落后于客观,或主观超前于客观,以及主客观协调一致。革命作为时代的“大事件”,势必造成主观上的波动和异常。按照调适形式的划分,第一种属于非革命者,第二种属于革命先锋,第三种属于革命的依靠力量。勃洛克经历着十月革命却未能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有两种情况:一是不情愿,二是缺乏能力。鲁迅强调其不能“作最深的警戒”,“受动底地等待着”,便是看到了勃洛克在革命蓄势和爆发阶段的被动性。这种被动性的来源值得关注,据后文的解释,与勃洛克的宗教相关,“想将基督的艺术底形态,藉革命来支持”,说明勃洛克对革命的不适和抵制并非源于对革命目的的怀疑和破坏,而是他性格中的结构性缺失。据此,托洛茨基无法漠视勃洛克,并推及关注革命中的“勃洛克”们。可以说,勃洛克的存在,《十二个》的诞生,写完《十二个》之后勃洛克的沉默,这一连串的关系为托洛茨基审视革命提供了充分而完备的个案。首先,参与革命有主动与被动之分,被动的承受依然含有革命的元素,“有着对于灭亡了的过去的绝望的呐喊”,根底上是“提高到向着未来的希望的绝望的呐喊”。其次,被动地接纳革命,也可能制造正宗革命者所忽视的一部分,“对于变革,勃洛克连想要俨然地加点白糖的影子也没有。却相反,他将这收在最粗野的自己的表现里面了”。再次,被动革命的产物留下对其成分分析的经验:“勃洛克便用基督来装饰革命。然而无论如何,基督总不是革命的出产,不过是过去的勃洛克的出产”。托洛茨基对被动性的阐述分布在全篇,鲁迅从勃洛克芜杂的思想中精准地捕捉到革命的“受动”特质,其时,鲁迅还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区别来自于他对人的本质与历史进化的判断以及对中国革命实情的观察与思索。而且,托洛茨基的革命观和勃洛克的革命姿态也深化了鲁迅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认知,尤其为他后来进一步思考革命队伍与革命前途的问题引入了前理解。其一,他警惕那些主动投向革命的人,反问买革命杂志的人,“意在看书呢,还是要穿丝光袜”,揭示“无产阶级咖啡”(27)的虚假革命实质;其二,他亦如勃洛克对变革不加白糖一样,披露“假救国”、“伪文艺”等革命中的丑陋真相,他说“认真的在告警,于凶手当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还没有僵死”,并且对自己的文字“不求保护”;(28)其三,借托洛茨基“同路人”观念,提出需要正确地看待所谓“落伍者”,并以邹容“革命军马前卒”为例,指出对革命性的评价标准应兼顾历史发展水平,而非机械地、僵死地认识革命言行及理论;其四,勃洛克的“天鹅之歌”与“基督之歌”虽有不彻底性,但也令鲁迅意识到“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29),鲁迅后期对“貌似彻底的革命者”的否定即建立于此。 有如一种无形的力感染译者,译文中反复出现受动性的强化,体现鲁迅对勃洛克与十月革命关系的细察。鲁迅未尝不是正经历着国民革命此起彼伏的冲撞力,他对于人的革命的主张在政治革命高涨的形势中被一点一点湮没。作为白银时代象征主义诗歌集大成者,勃洛克以《十二个》形象地揭示了复杂时代与宗教传统、社会变革与个人体验的隐蔽关联,但也被日盛的阿克梅意主义(实感派)盖过。当然鲁迅和勃洛克的革命遭遇有本质区别,勃洛克难以抓住革命的轴心,是因为他仅仅有“对于那革命洪流的混沌的音乐的理解”,而缺乏“革命的别的信念”,历史的进程并不迁就受革命感动的那位浪漫派的心理需要。鲁迅是一种超前性的革命逻辑,他身体力行的思想革命和时代有一种表象上滞后的错位,所以他依然感受到了那种被动性,并对施动和受动建立了个人认识。 (鲁译)勃洛克的象征主义,就是这密接而又可厌的氛围气的变形。象征者,是现实的受了概括的姿态。勃洛克的抒情诗是罗曼底的,象征底的,神秘底的,非形式底的,非现实底的——但在其间,却豫含有已被决定的种种形式和关系的很现实底的生活。(30) (韦、李译)勃洛克底象征主义,是这种密接而又讨厌的环境底反映。一种象征,是一种现实底概括的形象。勃洛克底抒情诗,是罗曼的,象征的,无形式的,非实际的。但是他底诗,预料着一种有明确形势与关系的很真实的生活。(31) (王译)勃洛克的象征主义乃是这个直接的与可厌的环境的反映。象征是现实的一个概括化了的形象。勃洛克的抒情诗是浪漫的、象征的、神秘的、不定形的与非现实的。不过要有这种抒情诗,先得有具有一定形态与一定关系的很现实的生活。(32) 鲁迅翻译从三个层面体现出受动立场:一、勃洛克的象征是主观“变形”,而不是客观“反映”;二、象征的使用是有意识塑造“姿态”,而不是作为结果的“形象”;三、勃洛克抒情诗与生活的关系是“被决定”。如果把象征的抒情理解为一种革命衍生物,革命主体并非天然施动者,而是受到外部世界刺激,引起内心召唤之后做出的主动性反应。就革命者从事革命的心理角度来讲,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但从革命作用于革命者的角度来看,则革命主体始终是处于受动位置。鲁迅没有以参与革命的方式和手段作为判定革命积极与落后的标准,而是从方向性上理解对待革命的态度,他以“墨迹”和“血书”做譬,认为后者“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但前者“恰如冢中的白骨”,所以“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33)鲁迅后来对柔石、叶永蓁、萧红等青年作家、包括一八艺社木刻作品的评价和鼓励,均突破了当时“革命文学”整齐划一的规则,鲁迅以个人的言与行为尺标,跳出革命身份、革命符号、革命载体等框架定势,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成熟和壮大带来了新的面貌。 为保证原著的忠实可信,鲁迅认为:“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34)容忍“不顺”在鲁迅的翻译策略中直观地体现为一种语序的“不顺”,三个译本相互对照更能看到鲁迅的有意为之。鲁迅对语序的处置,对原意的强调,一定程度上也出于结合著作整理个人观念表达的需要。 (鲁译)将觉醒和活动的目的和意义的感觉,给与了他的,是第二革命。勃洛克不是革命的诗人。正消灭在革命前的生活和艺术底没有出路的忧郁的状态中,勃洛克一双手抓住了革命的车轮了。作为那接触的结果而出现的,就是诗《十二个》。这在勃洛克的作品中,是最为重要的东西,是也许要跳出时代而生存的唯一的东西。(35) (韦、李译)第二次革命使他觉到觉醒,活动,目的和意义。勃洛克不是革命底诗人。正消灭在革命前的生活与艺术底没有出路的忧郁状态中,勃洛克抓住了革命底车轮。诗十二个,勃洛克底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唯一的可以存留许多时代的东西,是此种接触底结果。(36) (王译)第二次革命给了他以觉醒、运动、目的与意义的感觉。勃洛克不是革命的诗人。当勃洛克在前革命时期的生活和艺术的愚昧的断头巷里呻吟待毙之时,一手抓住了革命的车轮。题为《十二个》的那首诗——勃洛克最重要的作品,这是他唯一可以传世之作——正是此一接触的结果。(37) 三种翻译句序中,鲁迅设置顺序依据为诠释法,即后一句对前一句做出解说与定义。一方面,这种习惯源于文学家的偏好,比较注重语势的层层推进,追求一咏三叹的效果;另一方面,鲁迅始终以“觉醒和活动的目的和意义的感觉”与“接触的结果”为主,两次强调的语式凸显出“十二个”与“第二革命”的关联,而韦、李和王置于主语的仅仅是孤立的“第二革命”或“十二个”。即鲁迅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更是形成这一样式的过程和内容,他的观察不是止步于某一新现象,而是辨析那个现象生成的所有因素。第二革命固然重要,但是什么原因使得十月革命空前的具有渗透力,这是令人思索的,否则这种革命的传输到最后就有可能演变为一种概念的模仿。鲁迅不止一次地谈到“新漆剥落,旧相显出”的原因在于“治”的方法,所谓“治”,应该是“新的用新法,旧的用旧法”,才能杜绝生搬硬套革命公式运用于一切反抗的领域。并且,觉醒、活动、目的、意义的感觉在鲁迅看来,正是勃洛克从革命中领悟的真谛,而且这些感觉直接作用于诗人革命前的意识,产生了同过去的比较和反思。鲁迅译文中诠释式的句序强调了《十二个》不单是第二革命的证书,同时也是与历史联接的枢纽,在此基础上,烘托出旧时代与新兴革命的关系。 任何时候,鲁迅都没有割裂历史来处理现时性问题。1926年他的学生董秋芳翻译《争自由的波浪》,该书不是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作品,收录的三篇散文、四篇小说都属于旧时代文字,原名就是《俄国专制时代的七种悲剧文字》。鲁迅为其写广告语时,用了“战士的热烈的叫喊,浊世的决堤的狂涛”(38),为其作序时又写到“以前的俄国的英雄们,实在以种种方式用了他们的血,使同志感奋,使好心肠人堕泪”,证明鲁迅注意到构成革命的每一种要素,就如同岩石一层一层的凝聚,石头的坚硬不能够缺少任一的自然积淀。对过往和当下以及未来的联系,鲁迅也说到,“书里面的梭斐亚的人格还要使人感动,戈理基笔下的人生也还活跃着,但大半也都要成为流水帐簿罢。然而翻翻过去的血的流水帐簿,原也未始不能够推见将来,只要不将那帐目来作消遣”,这便是历史与革命的内在理路关联。因而,鲁迅认为此书有利于读者“明白别人的自由是怎样挣来的前因,并且看看后果,即使将来地位失坠,也就不至于妄鸣不平”。(39)托洛茨基把勃洛克放在历史的进化史中,既周全到其萌发革命的潜质和动机,也留意到其演绎革命的独创和限制。鲁迅则在译介过程中强化了这一点,表达他关于处理革命进程中个人思想演变的见解。 (鲁译)和一切过去的痉挛的悲痛的诀绝,在这诗人,是致命底的裂痕。可以支持勃洛克的——如果离开了起于他的全生活体中的破灭底的过程——恐怕只有革命的诸事件的永是增加上去的发展,和抓住了全世界的强有力的震动的旋涡罢。(40) (韦、李译)痉挛的,悲痛的,与一切过去的决裂,对于诗人变成了致命的破坏。离开他底有机体里继续进行的破坏的历程,勃洛克怕只能借着革命的诸事件底继续不断的发展,借着可以拥抱全世界的那强有力的震撼底螺旋线,而向前进行罢。(41) (王译)与整个过去作痉挛性的与悲怆的决裂,在诗人看来,这是一次最后的破裂。除了那些合他脾气的毁灭性的过程之外,能使勃洛克振作精神的只有靠革命大事件之继续发展,靠囊括世界的大震动的有力转进。(42) 鲁迅用特殊的语序强调了两个方面:其一,诗人与过去的告别充斥着无以复加的痛苦,并且引发他对造成这一内部分裂的外部革命的深思;其二,勃洛克的革命感悟既来自于过去的历史经验,也与当下的生活状态密不可分,即使诗人仍旧置身革命漩涡,如果结束过去的累积,也会终止他的革命想象和创作。翻译《亚历山大·勃洛克》的时候鲁迅尚在北京,革命氛围不如南方,可鲁迅后来去了厦门、再到广州,最后去往上海,甚至发生“革命文学”论战之后,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包括去世之前,他依然重复这一点——对旧时代积弊以及旧时代孕育的一切认知给予重视,也可以理解为任何革命都是一种返回,返回检视,进而知道前进的路径,这也应该是托洛茨基发现,并由勃洛克传递给鲁迅的信息,从现实来说,也是一种对鲁迅当时矛盾的中和,更是鲁迅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认识基础。这是另外两个译文所不能表达,也未能显示的。 中国知识界比较集中地介绍托洛茨基始于1924和1925年间,当时托洛茨基在中国的形象就已经毁誉兼具。一方面,由于苏联的党内路线斗争,他在政治革命实践中不断地遭到批判,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他的精神魅力却吸引了不少时代先驱者的崇奉,鲁迅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在一直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的鲁迅看来,托洛茨基这个立志挽救民族危亡,又不陷于任何主义的迷障,并且有魄力敢担当的“少数派”的思想领袖,就是当年自己曾经推崇过的“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文化英哲和精神界战士。从上述三个译本的比较中,从鲁迅后来在“革命文学”论战中对《文学与革命》的一些重要观点的引用的文学实践中,都可以看出鲁迅对托洛茨基的由衷的欣赏及其深刻的理解。托洛茨基既宽容前革命时期的非革命文学、又相信革命之后其改造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的辩证言说对处于转型矛盾之中的鲁迅形成了传感,使鲁迅找到了自己前进的自信。尤其是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以及勃洛克的感召,形成了鲁迅迥异于“革命文学”论战中的对手们的思想资源,也使鲁迅在阶级立场的标准之中保存了精神的、艺术的一个面向。因此可以说,《亚历山大·勃洛克》的阅读,提供了鲁迅思考历史、思考革命、思考自身的一个场域,而融合个体生命经验的躬行翻译,更是鲁迅有意识地直面并整合个人思想矛盾的显现,造就了鲁迅对革命与文学,以及革命与文学者等相关思想的复杂性与辩证性,同时增加了193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维度。 注释: ①⑨(14)(20)(24)(30)(35)(40)鲁迅:《亚历山大·勃洛克》,《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159、158、160、158、157、158、160页。 ②⑩(15)(21)(25)(31)(36)(41)韦素园、李霁野:《文学与革命》,北新书局1928年版(下同),第154、156、154、160、155、152、155、155页。 ③(11)(16)(22)(26)(32)(37)(42)王凡西:《文学与革命》,信达出版社1971年版,第25、25、25、26、25、24、25、25页。 ④(23)戈宝权:《十二个》,时代出版社1951年(下同),第71、11页。 ⑤鲁迅:《250530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493页。 ⑥鲁迅:《240924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1卷,第453页。 ⑦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鲁迅全集》第1卷,第380页。 ⑧冯雪峰:《鲁迅回忆录(十二)》,《文汇报·笔会》,1946年11月12日。 (12)鲁迅:《论“第三种人”·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451页。 (13)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204页。 (17)蒋光赤:《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见陈思和、贾植芳:《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32-834页。 (18)鲁迅:《250930致许钦文》,《鲁迅全集》第11卷,第517-518页。 (19)鲁迅:《〈十二个〉后记·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312页。 (27)鲁迅:《革命咖啡店·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117页。 (28)鲁迅:《帮闲法发隐·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第290页。 (29)鲁迅:《非革命的革命急进论者·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231页。 (33)鲁迅:《怎么写·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19-20页。 (34)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392页。 (38)该广告见于勃洛克原著,胡斅译,《十二个》初版本(《未名丛刊》之六,北新书局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版权页后。 (39)鲁迅:《〈争自由的波浪〉小引·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318页。标签:鲁迅论文; 勃洛克论文; 托洛茨基主义论文; 洛克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古典自由主义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读书论文; 王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