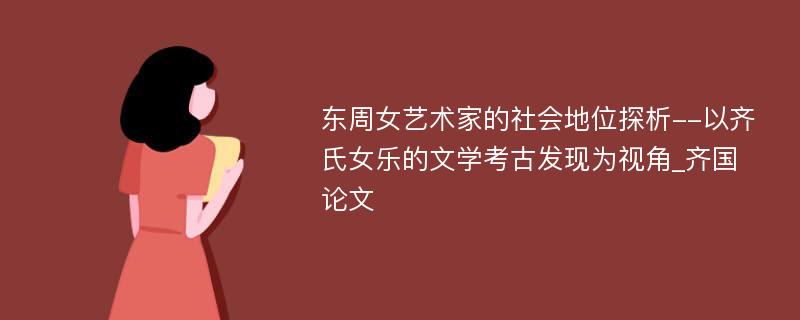
东周时期女性艺人社会地位管窥——以有关齐国女乐的文献与考古发现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周论文,齐国论文,视角论文,社会地位论文,艺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4; 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4)08-0118-03 一、先秦女乐概览 女性自古以来就是音乐舞蹈活动的重要承担者。远古时代,兼具色、艺之长的女性表演常被作为祭祀时取悦神灵的手段。步入阶级社会后,男性统治者把以往祭祀鬼神的女子表演用作自己的享乐,这些供统治者享乐的女性艺人被称为女乐。据传,夏桀之时有“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1](p327)商代某些歌舞表演被形容做“恒舞于宫、酣歌于室”,[2](p51),其“殉于色”的动机彰然可见,1950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商代晚期大墓出土的随葬品中发现有女性骨架24具,研究者认为这些人骨生前就是墓主所拥有的女乐。 西周初年,统治者吸取前代灭国的教训,制礼作乐以巩固统治。对于音乐,他们强调其背后所隐匿的道德力量,而不是旋律美带来的享受。因此周代雅乐乐舞的表演者是国家音乐机构中受教育的青、少年贵族子弟,引人狎昵、沉迷的女性表演被视为“淫于色而害于德”,[3](p160)不许用于重要祭祀。春秋以后,原有社会经济、政治格局被打破,礼乐废弛的局面随之形成,上层社会的享乐之风迅速滋生,关于女乐的文献记载也多了起来。例如:“晋献公伐虞、虢,乃遗之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女乐六”[4](p387)“郑伯嘉来纳女、工、妾三十人,女乐二八,歌钟二肆,及宝镈,铬车十五乘”;[5](p251)“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其大宗赂以女乐”[6](p417)等。女性表演声、色俱佳的双重效果得到了充分利用,大量地位低下、失去人身自由的女性艺人不仅被迫以技艺与美貌来取悦并满足男性统治者,还常常被当作礼物相互赠送,而这种行为背后的政治目的往往十分明确。正因如此,女乐又被视作催人堕落的因素,背负着“蛊惑丧志”、“祸国乱政”等骂名,为统治者的荒淫无能充当替罪羊,也成为他们权力之争的牺牲品。 二、东周齐国女乐 东周时期,郑、宋、卫、齐、赵、中山等国女性表演十分兴盛,是当时音乐“淫于色”的典型代表,其中,齐国音乐被形容作“齐音骜辟骄志”。[3](p160)《论语·微子》云:“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7](p73)齐国的女乐能使鲁国统治者迷恋得不断往观、怠于政事,其艺术表现力从中可见一般。孔子因此离开鲁国,并作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蓋优哉游哉,维以卒岁!”[3](p226)从孔子无奈的歌声中,可以想见齐国女乐音乐语言十分尖刻犀利,齐国派往鲁国的应该不是仅以色、艺诱人的一般女艺人,而是一群经过特殊训练、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甚至政治素质的女子。这与文献中对赵、中山、郑等地女子“目挑心招”、[3](p356)“游媚贵富”[3](p355)的形容截然不同。齐国女乐之所以不同凡响,应该与齐国社会、历史、风俗方面的特点分不开。齐建国之前该地原为东夷部族所居,东夷人自古有好乐传统,齐国统治者历来奉行“因其俗,简其礼”[3](p183)的治国方略,使齐文化中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古老的东夷风俗,管仲等改革家又大力倡导尊重民众对饮食、侈乐的向往,因此东周时期齐国自宫廷到民间音乐生活均极为活跃。频繁的音乐活动中,自然缺少不了女子的表演。另外,齐地“地瀉卤、人民寡”,[3](p355)不适宜大规模农耕,女工之业尤为重要,齐国女性比同时期其他国家女性更能在生产上独当一面,人格独立性也更强;得益于君主顺应民俗的统治思想,齐国女性所受礼教束缚相对较少,性格大胆、开放、不囿陈规;齐国工商业极盛,受民风中尚智辩、多权诈的商人性格影响,齐国女性足智多谋、能言善辩、通权达变;东周齐国统治者设学纳士、虚心纳谏,在国内形成了民主宽松的政治氛围和自由辩论的社会风气,国中女性也能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多有讽君谏上、参与政事的高行义举。 综上可知,齐国女乐不仅以美貌和技艺吸引男性统治者,在思维、语言、交往能力等方面应该也有较大优势,其他地区的东周女乐大都仅见文献记载,齐国女乐的存在却得到当地大量考古发现的印证。已知的东周齐地考古资料中,女性随葬现象十分惊人,例如:临淄郎家庄一号墓、[8]临淄东夏庄四号墓[9](p58-60)临淄东夏庄六号墓、[9](p95-98、113-116)临淄淄河店二号墓、[9](p309、322-333)章丘女郎山一号墓[10](p115-149)等的殉人、陪葬人中,能够确定年龄和性别的年轻女性比重极大。而在观察齐国东周时期乐器文物时不难发现,许多乐器出自有女性随葬人的墓葬,据统计,这样的墓葬迄今已知5座,占鲁中、北地区目前所见9座随葬乐器齐墓总数的55.6%,在该地区现知的21座大、中型殉人齐墓中则占了23.8%的比例。 女性随葬者与乐器同出的现象在其他地区东周考古挖掘中也能见到,但不若齐国墓葬这样资料集中。古代人殉制度中,除被杀害的奴隶外,侍卫、幸臣、私昵、嬖妾等也常为主人随葬,这其中,女性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兼具色、艺之长的女乐自然更难于幸免。虽然我们无法断言与乐器同出的随葬女性哪些生前是从事歌舞表演的女乐,但这些女性骨架中包含有当时的女乐是毫无疑问的,《墨子·节葬下》云:“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必大棺中棺,革阓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11](p71)正是这种现象的写照。 三、东周时期女性艺人的社会地位 女乐在我国古代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中起到过不可低估的作用,但这个特殊的女性艺人群体,始终为礼法之士所不齿,其作为男性附庸的地位在我国古代男权社会中也一直未得到改变。尽管东周齐国女乐有着令他国女乐望尘莫及的种种优势,却也不能例外,她们的悲惨境遇是当时各国女性艺人社会地位的缩影,也是后世女性艺人所受诸多不公待遇的开端。 1.女性艺人的生存权。我国古代的人殉制度,大约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到殷商时期最为鼎盛。西周时期人殉之风依旧存在,但随着对奴隶使用价值的认识有所提高,以及保持军队人数、防止奴隶倒戈等考虑,统治者不得不对奴隶的生命加以重视,以生人殉葬随之减少。与此相适应,迄今所知的西周墓葬中,女性随葬者与乐器同出的现象相对较少,这当然也与周人建国后制定礼乐典章、严格控制恣意享受女乐有关。春秋中叶以后,人本思想萌芽,残酷的人殉制遭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谴责,人殉行为更加收敛,出现了代替活人的随葬俑,但将女性乐器使用者与乐器一起随葬的现象却有增无减。较之西周时期,东周社会的文明意识无疑是有所进步的,但女性艺人的生存权反而更加无从保障。女性随葬者与乐器同出,尤以齐国墓葬最为突出。本文认为,当时齐国国内确实尚存以生人殉葬的陋俗,但统治者对女乐的贪恋程度应该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另外,临淄郎家庄一号墓、章丘女郎山战国墓等东周齐墓发现的随葬俑人也以女乐造型居多,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东周考古发现中同样可以得见,当时女性艺人地位之卑下以及在殉葬者中的比例由是可得旁证。西汉初年,人殉被正式废除,这种残酷的行为虽未就此绝迹,但远不如先秦之规模巨大,女性艺人的生存权才得到一定保证。只是,从后世大量的女乐造型随葬俑中,仍然可以感受到男性统治者对死后继续享受女乐之色、艺的觊望。 2.女性艺人的物化与商品化。大量女性艺人在争战不休的东周时期或被作为诸侯之间政治博弈的手段,或被主人用来行贿营私,主人死后又被作为随葬品,她们与珍玩、金玉、马牛、布帛等并列,人格上被完全的物化。东周时期各国实行不抑商政策,出现了齐国临淄、楚国郢都等著名的大都会和商品交换中心,在新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被物化的女性艺人又开始了逐渐沦为色性商品的不幸命运。女性的商品化,从工商业发达的齐国开始,春秋时期“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12](p32)开女子色性交易之先河,这种举动一来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二来可以笼络往来于各国之间的游士,同时也能满足贵族们自身的享乐需求。女闾的设立是我国古代官妓制度的萌芽,虽然女闾中以色营生的女子很多是获罪之人的妻女或者寡妇、战俘等,与当时宫廷、贵族所豢养的专业女艺人并不等同,但这些以“娱人”为职业的女子,其劳动内容除了出卖色相外,音乐舞蹈定然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东周时期“女乐”概念的涵盖范围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了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值得一提的是,齐国女闾中专职为贵族们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尽管其真实心理状态史书记载缺如,但应该与当时赵、中山、郑等地女子自愿取悦男子的动因不同。《史记·货殖列传》云:“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3](p356)赵女、郑姬为改变生活境遇而苦练技艺、精心妆扮,不远千里外出谋生,通过色、艺博取富人欢心,且不择老少,只要有利可图就去追随,几乎成了社会风气。齐国音乐虽也因女性的大量参与而遭到礼法之士排斥,但富裕殷实的齐国与地薄人众的赵、中山等国不同,文献中并无齐国女子迫于生计或受经济利益驱使主动游媚富贵的记载,齐桓公设置女闾,遭到“国人非之”。[12](p32)说明当时齐国国内或有以女子色性牟利的做法,却并无女子靠色性为业的风习。 然而,不论以色性为业是出于主动抑或被动,在男权社会中,包括齐国女乐在内的各国女性艺人最终都难逃依附男性、遭受压迫、失去人身自由乃至生存权的命运。周代是男权社会性别制度的初始阶段,女性所受的禁锢和歧视程度尚不若后世之剧烈,但东周女性艺人的命运反而比前代和后世的女性艺人更为多舛,她们不仅是男性统治者生前的玩物和交易品,也是为他们死后随葬的上上之选,这一点在齐国贵族墓葬中的累累女性白骨和随葬乐器中完全得到证实。标签:齐国论文; 齐国君主论文; 东周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国学论文; 春秋战国论文; 军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