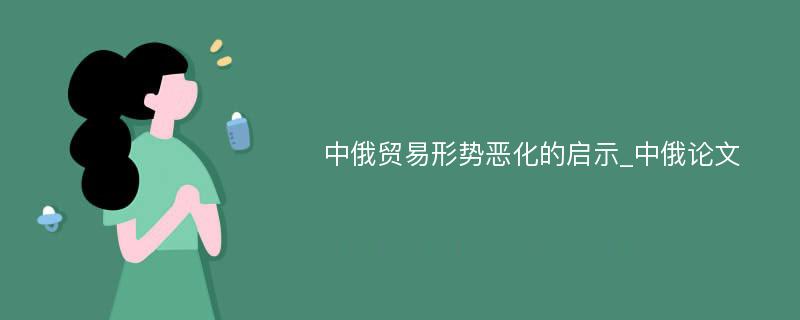
中俄贸易形势恶化的寓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寓意论文,中俄论文,形势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中国大陆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至少下降了30%,而在这之前的几年里,中俄贸易额一直是逐年上涨的;1993年比1992年就上涨了31%。在没有什么偶发事件影响、没有什么人为因素作用、没有什么重大政策变动的情况下,两个国家的贸易状况发生如此之逆转,确是挺值得琢磨的一件事。
九十年代伊始,随着两个东方大国先后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两国间贸易体制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由政府间贸易转向了公司间贸易。贸易主体的改变进而引发了整个双边贸易制度的一系列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制度需求,这些需求又反过来烘托出了“中俄贸易”这一局部市场的制度缺陷,如结算、信用、保险、仲裁等诸多“制度零件”的缺如。
中俄双边自由贸易的最早的制度创新者大概是黑龙江两岸的老百姓。当一个中国农民用一舢板西瓜换回一辆吉普车的时候,当一个俄罗斯小孩怀揣两个小狗崽到黑龙江南岸换回一打“阿的达斯”的时候,中俄贸易制度的“转轨”便由此开始。进而,两国迅速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民间贸易公司;在这些贸易公司的外围,又形成了一支巨大的个体“背包者”大军。这些有组织或没组织的商人们是中俄贸易市场形成的最重要的条件。他们的勇气不亚于当年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帮。在没有有效的结算货币,没有可靠的结算机构,没有正常的贸易信用,没有规范的贸易保险,没有公允的贸易仲裁,在非常原始的制度条件下,市场竟然自发地组织了起来,并且靠着这个简陋的制度工具能够把中俄贸易一再推向高潮。这真是一个奇迹。政府间记帐贸易结束的1991年,靠着这个自发的、原始的市场,中俄贸易额竟能维持在39亿美元的水平上,比上年的42亿美元只略有下降,而这一年俄国同一些东欧国家的贸易则下降了50%左右。1992年,中俄贸易额便达到了58亿美元,大大超过了最后一年中俄政府间记帐贸易的42亿美元的水平。到1993年达到76亿美元,最终使中国成为俄罗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这些成效的一大半应当归功于自然经济式的以货易货贸易和短促突击、全面开花式的边境贸易。
但是,“新制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易货贸易中,贸易公司既要在国内市场上为对方所要的货找到卖主,又要为对方所提供的货找到买主;它还要为出口货物和进口货物同时张罗运输、保险等一应事务。除了这些明显的效率缺陷外,银行结算所附带的信誉调查、合同监督、强制支付及贸易信贷等信用工具,在易货贸易下都无法加以利用。政府间记帐贸易结束的几年来,中俄贸易的合同履约率一直在30%左右徘徊,如此之低的合同履约率意味着易货贸易的高风险,这种高风险与低效率一起,构成其局限性。
如果说,这种局限性在最初几年还没有在贸易实践中充分显现出来的话,那么,1994年便是一个转折点。从1994年1月15日开始,中国持因公护照的人到俄国去也需要签证了,有人认为这导致了中俄贸易的逆转。这大概是因为人们在1994年实在再也找不到更有说服力的反常事件来解释问题了。还有人把中俄贸易下降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商品质量问题。其实,商品质量低是结果不是原因。是低质量的制度把低质量的商品吸纳进这个越来越混乱的大商场里来的。如果让有着“以优质取胜”之经营传统的日本大公司的老板们改行去京——莫列车上经营“车窗贸易”,他们立刻就会改取“以劣质取胜”的经营战略。因为在这个制度条件下,往车下甩鸡毛服确比卖正经的羽绒服利润高。
刚刚从计划经济的生活环境下解脱出来的两国商人们,起初就象循规蹈矩的小学生一样,他们需要花时间来学习进行自由贸易。他们起初并不是骗子,是这种漏洞百出的贸易体制把他们逐渐地变成了骗子。随着商人们对国际贸易越来越了解,他们对如何利用贸易制度的缺陷也越来越清楚。于是,中俄贸易中骗局在逐渐增加,一锤子买卖越来越多,客户关系越来越不稳定;贸易公司们变得越来越谨慎,一些中国公司在与俄国人打交道时开始奉行“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原则,在实际贸易谈判中因先撒兔子还是先撒鹰的支付顺序问题而搁浅的项目越来越多。中俄双边贸易中的“囚犯难题”终于形成。不完善的贸易体制经过了几年的运转以后,其破坏力被释放出来了——这就是笔者对中俄贸易额大幅下降的解释。
中俄贸易问题在整个经济转轨潮流中应当说是一个小问题,一个小角落;它繁荣也罢,恶化也罢,于大局无碍。然而,从91年到现在中俄贸易演化的这段戏剧性公案,会给改革的“大哲学”提供一些启示。这些启示恐怕是极有价值的。
启示一:我们之所以把我们正在进行的过程称之为“经济改革”而不是“经济革命”,是因为这一过程是有政府的。但有政府的改革并不意味着凡事由政府来办。有许多事情,由政府来办不但效率低,而且甚至根本就办不成。中俄贸易市场的建设与完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其实,自结束政府间记帐贸易后,中俄两国政府一直在商量建立相应的贸易新体制的问题,特别是贸易结算银行问题。中俄两国都曾是计划经济的国家,从政府官员,到学者,到商人,大家仍然保持着凡事由政府解决的思维习惯。但经过几年的谈判,事情的艰难度逐渐地被当事人们体会到了。试想,要让双方政府拿出美元,组成合资银行,为两国经贸合作办理硬通货结算,政府除了要考虑能不能或愿不愿拿出钱来的问题以外,至少还要考虑诸如合资比例、注册地点、服务范围、服务对象、存款来源、贷款方式、外汇流失等等一系列问题。它可能还要担心,社会主义国家中银行对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会不会象计算机病毒一样传染到这特殊的金融机构中来。另外还有一个谁掌握经营权的问题,掌握了经营权的一方是否会在贸易贷款上偏向本国企业,而形成拿着对方的钱为本国贸易公司服务的现象。例如,如果一家俄罗斯贸易公司从中俄合资银行中获得了10万美元的贸易贷款,之后不久,这笔贷款变成了死帐。从法理上讲,这是贸易公司与银行的关系问题,是银行的利益损失;但从国家关系上讲,这是中国的利益损失。假如这个合资银行的合资比例是对半的话,则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从中国挖走了5万美元的利益。从这个假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由政府出面组织合资银行为本国的企业办理贸易结算,这本身就包含着许多矛盾,在实际经营中这些矛盾定会衍生出诸多麻烦。这恐怕就是中国银行在经过了几年的周折以后失去了搞合资银行的兴趣,转而谋求发展自己在对方的独资银行的重要原因。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为什么非得由政府来办呢?政府办不了的事为什么不能交给市场呢?中俄贸易服务系统的机构缺如,说来说去,最根本的不就是缺银行吗?世界各国的外贸银行多得很,为什么中俄两国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
问题出在中俄两国现行的金融制度上。中国压根就没有私人银行;俄国虽有私人银行,但没有有能力、有信誉、有资格可以经营中俄经贸结算的私人银行,所以事情还得由它的国营外经银行来办。本来,中俄经贸结算机构的缺如对于金融商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投资机会,可是,这一投资机会被双方的官办银行垄断以后,变成了一场没有前途的旷日持久的政府间谈判。中俄两国特殊的金融制度把市场问题转化成了政府问题,而政府又解决不了问题——这就是中俄贸易结算问题上的症结。
打开症结的办法是有的,那就是:请第三国来办银行。
这条路在技术上没有什么大的难关。在俄罗斯和中国都已经有外国银行,并且已经有少数中俄大公司间的贸易结算是由第三国银行来办的,现在缺少的是那种专营中俄贸易的,以中俄两国的贸易公司、特别是象中国的边、地贸公司那样的中小贸易公司为服务对象的银行。其实可以让第三国的金融投资者来办一个集结算、信贷、保险、信息、仲裁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贸易服务体系。关键在于中俄两国的政府能不能放开政策,放开市场,放弃垄断。
1994年实际上是两个东方大国的政府对其双边贸易最重视的一年,这可以从这一年两国政府首脑接触的频度、级别和主题上得到证明。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这一年两国的贸易状态发生了恶变。现实的经济结果与政府的努力目标背道而驰。社会主义者们把其国家的经济史仅仅理解为其经济政策史的时代已经结束。
启示二:人们尽可以把人类历史上的市场经济理解成自然长成的,但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经济转轨和市场建设则很大程度上应当是一个人工的过程。或者说,制度创新必须是一个自发行为与自觉行为相配合的过程。我们不能等待市场自然地长成,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那个时间条件和人文条件。
在我们的旁边已经有一个成熟的西方市场摆在那里,它的存在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的价值。它既可以让我们根据这个榜样来设计我们的制度以防止人们在市场交易中“发坏”,同时也可以使商人们从中学习如何“发坏”。我们的证券交易法规的制订者与证券交易中的作弊者是同一个老师的学生。有了旁边这个老师,商人们“学坏”“学奸”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试想,假如这个世界上除了中俄两个国家以外都是印第安人或爱斯基摩人,或者,现在的中俄易货贸易是发生在二千年以前,那么,事情会恶化得这么快吗?历史会给双方提出如此之紧迫的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吗?历史上的市场确是自然长成的。但是要知道,人类的历史并非仅仅是一部经济史,它还是一部全面的人文的、社会的历史。制度在变,人自身也在变。制度的变化与人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从人类最初的交换活动的产生到第一宗欺骗案的产生,可能要经历一个好长时间。从第一条防止欺骗法规的形成,到人们想出第二个“坏点子”,可能又要经历好长时间。随着人越来越“坏”,制度也越来越完善。古人们“坏”得慢,市场建设得也慢。在我们把制度创新和市场完善的历史理解为一个效率资源开发的历史的同时,我想,是不是也应当承认这里所说的这条逻辑线索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人类的经济史不仅是一代一代的制度设计者越来越聪明的历史,而且也是一代一代的经商发财者越来越“坏”的历史。在此次密西根年会上(中国留美经济学会1995、8),有人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应当把中国市场建设中的SEARCH和RESEARCH这两种活动区分开,也就是说要把SEARCHER和RESEARCHER这两类人区分开。我借着这个概念来说,所谓SEARCHER可以理解为那些淘金者、创业者、想点子发财者、钻空子谋利者、损人利己者等等,而所谓RESEARCHER则是那些理论研究者、法规制定者、利益协调者、制度设计者、公共产品提供者和公共事务管理者等等。这两类人在共同地进行着制度创新,共同地创造着我们的经济历史。随着SEARCHER越来越“坏”,RESEARCHER也越来越“聪明”。
而现在的矛盾是:我们的制度挺原始,但我们的人却很现代。指望这些现代人象古人们那样通过其自发活动而自然地长出一个市场来,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在中俄贸易这个局部市场中所看到的结果——如果没有及时的、与商人们的自发活动相配套的自觉的制度建设、制度补充和制度完善,则这些现代人的自发的经济开发和制度创新活动很快就会走向反面,他们会反过来用他们的“坏”来扼杀由他们自己创造的经济成果和制度胚芽。如果没有RESEARCHER的作用,单从SEARCHER的角度看问题,那现代人(“聪明人”)比古人(“傻人”)在交往中更容易形成囚犯难题。在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改革中,我们不是在许多领域里都可以发现这个逻辑吗?我们的SEARCHER已足够“坏”,但我们的RESEARCHER却不够聪明。在当前的制度创新中,SEARCHERS做得太多,而相比较RESEARCHERS做得太少。(本文是一篇经济学文章,因而这里的“坏”、“奸”等名词不具有道德含义。)
启示三,经济转轨不仅是功能转轨,更重要的是制度转轨。中俄贸易体制的转轨,不应仅是将原来由政府间来做的贸易现在转由公司们去做,更重要的是,要将原来的政府间谈判、政府间记帐、政府间交货的整个一套贸易制度,转变成为以赚钱为目的利益实体间的商业活动,转变成公司客户、公司间合同、信用证、银行转帐结算、银行贸易信贷、保险公司保险等一个新的概念体系,以及和这个概念体系相联系的人们的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俄贸易恰是因为仅仅进行了功能转轨,没有及时地完成整个的制度转轨,所以最终显示出转轨的缺乏后劲。在我国改革的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例如,乡镇企业的产生当然是我国当前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成就。但细想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功能转轨——它把相当大的一个部分的经济增长的任务承接下来了。而在制度转轨上,即如何把乡镇企业建成一个合理的经济体系和有生命力的制度形式方面,其漏洞还是很大的。其实,从制度特征上来看,乡镇企业之未来的生命力是很可疑的。其最大的制度漏洞是其创业人权利的不清楚及它象国有企业一样是乡镇政府的直接所有物。要知道,无论是正面的市场竞争,还是背后的私下交易,乡镇企业在商业上的优势都是从国有企业那里来的,随着国有企业体系的逐渐弱化,乡镇企业的优势也会逐渐消失。与此同时,它的制度缺陷则可能突然开始发生作用。就象中俄贸易中易货贸易这一经济现象的历史命运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