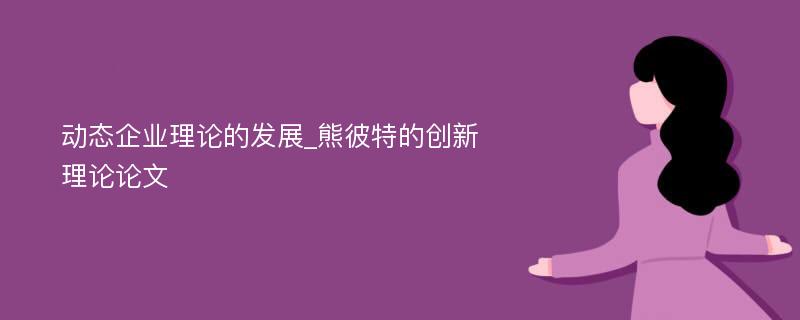
动态企业理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动态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从新古典到科斯和熊比特
这是一组系列文章,总体目的是向中国的理论界和企业界介绍一个在西方学界迅速发展中的企业理论的流派。这个流派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组织理论、企业史和战略管理等领域中的不同学者的工作。虽然这些学者是从各自的领域出发来研究特定的现象和问题,但他们的理论观点在关于企业基本性质的问题上汇合并趋同,从而逐渐塑造出来一个反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发展起来的企业观可以被称之为“动态企业”(the dynamic firm)理论。
近年来,从国外管理学文献中传来的企业核心能力或核心竞争能力的概念在国内引起广泛注意。这个概念的实证性使人们很方便地从直观的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它。但如果不清楚这个概念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渊源及其意义,则很难在理论上准确地使用它。实际上,核心能力是动态企业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既是对企业在实际经济过程中某些特定现象的概括,也代表着突破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发展。
以系列文章的形式来介绍这个企业理论的流派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动态企业理论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一个流派。如果以熊彼特传统为源头,动态企业理论的框架至少经历了半个世纪才逐渐形成。事实上,这个流派本身就是由一些“contending theories”(互相竞争的理论)所组成的。因此,讲清它的兴起过程需要通过不同的章节追溯到不同领域中的理论发展。第二,这个理论框架是几代杰出学者的研究工作所奠基的,其中某些主要学者的研究本身就是值得专门介绍的。因此,本文不是一般的综述,而是通过对主要奠基人及其工作的介绍来展现这个流派的理论渊源,从而使读者把握动态企业理论的发展脉络,并理解企业理论争论的基本问题。
对任何现代企业理论的介绍都不能不从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批评开始,因为在经济学中,企业理论的发展动力首先是来自对新古典理论教条的质疑。动态企业理论是和新古典经济理论对立的流派,其源头是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这篇导言将对新古典理论框架下的企业观和熊彼特框架作一扼要评述。
任何一个企业理论都必须回答两个基本问题:(1 )企业存在的理由(目的);(2)什么因素限制着企业的规模和范围。 在经济学理论中,对这两个问题(即企业性质的问题)的特定看法受制于对什么是经济体系运转中心问题的一般看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体系运转的中心问题是一个经济体如何在给定的技术和个人偏好条件下来配置资源。经典性的论述如下:在一个经济体中,一方面是构成人口的消费者,而另一方面则是这些人中碰巧掌握了生产性资源和才能的生产者。问题在于如何使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口的各种需求?解决这个经济中心问题需要两个东西:第一,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传达需求的强度及其满足需求的各种生产手段的相对能力;第二,需要有一组制度使生产者自发产生出在最高报酬点来使用生产资源的普遍倾向(即追求利润最大化)。自由市场和私有制正是提供了这种经济组织机制的精髓。一个自由市场为产品和生产要素定价,以更高的收益来奖励把生产资源置于更有紧迫需要的方面,以收入减少和损失来惩罚这样的生产—它所投入的生产要素可以在其它地方产生更高的报酬。私有制则保证了自发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又创造出作为组织原则的市场。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经济行为,动机和绩效(performance )的分析是从自利的理性个人行为出发的。根据这个理论,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会使整个经济体系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每个人都能在给定的资源占用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这个理论实在是关于一个理想的市场模型:通过市场自由交换的价格机制,经济个体的最大化行为能够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而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干预(最初表述这个思想的学者是亚当·斯密)。因此,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价格竞争,而价格竞争所导致的市场均衡则是具有唯一福利优势的总体经济秩序:社会效率是在帕累托效率的基础上实现的,即在市场均衡的条件下,不可能使任何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条件下改善自己的福利。这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两个基本福利定理所告诉我们的信条。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企业是按个别消费者的形象所设计出来的经济单位,根据最大化的行为规则来运行。将企业的目标定义为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新古典模型设定企业面临着给定的并可以意识到的各种选择和约束。由生产函数所概括的技术是外在于个别企业的而且可以被企业免费获得(即公共产品);由成本函数所概括的经济约束由生产要素价格的组合所决定,而这些价格又决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市场约束则由企业之间的竞争所决定,这种竞争塑造了企业的定价和产量的决策。于是,在最大化行为的假设下,企业在给定的技术和各种约束下从一组可能的选择中挑选自己的生产方案,并且毫无障碍地(即既无信息限制又无不确定性)选取能使其利润最大化的行动(价格和产量)。但是,这个貌似无所不能的企业却是彻底被动的:是外生变量,即给定的技术,成本结构和市场条件,来决定企业的活动边界和生产率,而企业自身的能力问题被彻底压制了。从个人的理性选择出发并以市场均衡为归宿,新古典理论的理想市场模型并没给企业的作用留下什么余地。
但既然市场如此美妙,为什么还会有企业?这正是科斯所提出的问题(Coase 1937)。科斯修正了新古典模型关于市场交易可以顺利进行的假设,认为存在着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即交易费用),而把原来通过市场自由交换的活动置于组织层级的权威关系之下,企业可以节约因市场摩擦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于是,科斯把企业的起源归因于市场交换过程中的摩擦,而“企业与众不同的标志就是它对价格机制的替代”(同上,389页)。 科斯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并由此而修正了它的假设,但他并没有挑战新古典理论框架本身。他的中心论点——在存在交易费用条件下,企业产生于对价格机制的边际替换——仍然是以市场均衡论为基础的。事实上,无论是继承了科斯路线的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Williamson 1985), 还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Alchian and Demsetz 1972),还是修改了新古典理论完全信息假设的委托-代理理论,实际上都不过是在市场均衡论的框架下做一些局部修正。在这些理论背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典型的新古典理论信条:市场是第一位的,而企业是第二位的。在这些理论中,由于企业的存在只能归因于市场失败,所以仍然没有企业的主动地位。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兴起之后,重新定义了中心经济问题并恢复了企业在经济理论中的主动地位的第一个经济学家是熊彼特( JosephSchumpeter)。看到“在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自动破坏可能达到的任何均衡的能量源泉”,熊彼特力图建立的是一个关于经济变动的理论,它“并不仅仅依赖于外部因素来把经济体系从一个均衡推向另一个均衡。”(《经济发展理论》日文版序言)一反瓦尔拉斯的均衡论观点,即经济生活本质上是被动的而经济理论必须限于研究静态的过程,熊彼特认为,“应该掌握的要点是,当我们研究资本主义时,我们是在研究一个进化过程(an evolutionary process)。 没有人看到这个如此明显并被马克思很久以前就强调过的事实,看起来也许是一件怪事”;“资本主义就其性质来讲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不仅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1979/1942,103-104页)。在这个被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过程中,“开启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其不断运动的基本推动力来自于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的市场,和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新的工业组织形式。”(同上,104页)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创新。很显然,熊彼特对非连续历史跳跃的强调是与边际替换的概念不相容的。
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采取这样一种动态观点,熊彼特摈弃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条。起中心作用的是他对竞争过程基本性质的重新定义: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后者较之于前者,“其效力之区别就象大炮狂轰与徒手推门之间相比。”(同上,107 页)而在新古典理论中,实质性的竞争是价格竞争。根据价格形成的机制,竞争被分为三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和完全垄断(参见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从配置效率的角度看,垄断导致较小的产量和较高的价格,因此只有充满小企业的完全竞争才是最理想的境地(注: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只有生产要素的报酬,而没有利润;利润只能产生于垄断);但从熊彼特所定义的创新效率的角度看,垄断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而完全竞争的工业一旦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即创新),完全竞争的状态也就不存在了。完全竞争还会造成浪费:“一个完全竞争的工业,在进步和外来干扰的冲击下,比大企业更容易被击溃,因而更容易散布萧条的病菌”(同上,133页)。 在熊彼特看来,利润来自于创新,因创新而获取的暂时的垄断利润则是为保持企业创新能力所必需的财务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是:它(指带有垄断色彩的大企业)已经成为经济进步的尤其是总产量长期扩张的最强大的发动机,总产量的长期扩张不仅是在这种尽管从个别事例和个别时点来看如此受限制(指垄断对产量的限制)的战略下出现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这种战略而实现的。从这点来说,完全竞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低劣的,它没有资格被树立为最佳效率的典范。”(同上,133-134页)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朵奇芭,他的理论框架从经验角度上看如此令人信服,即使是笃信正统经济学的理论家也鲜有人敢于去否定。从熊彼特对创造性毁灭的论述上,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是经济进化的发动机,所以企业具有超越外部经济条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够塑造市场条件。但熊彼特的框架很宽泛,它的实质内容有待于他身后的学者去填补,而潘罗斯就是这样一位先驱者。
潘罗斯的企业增长理论
美国女经济学家潘罗斯发表于1959 年的《企业增长理论》(Penrose 1995/1959;以下页码均指本书),是一部继承了熊彼特传统,从经济学角度通过研究企业内部动态活动来分析企业行为的开山之作。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被主流经济学是作异类而冷落,在其发表之后的约二十年间在经济学界响应者寥寥。然而,随着工商管理学院的全面发展,美国大学中与管理相关的博士数量的迅速增长,非央格鲁萨克逊工业社会(如日本)的崛起,以及非主流经济理论(如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这本书的影响已经变得如此之大,直至今天仍然被认为是关于企业能力思想最丰富的论著。事实上,充斥于当代西方管理学文献中的各种“基于资源的企业观”(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全都是建立在潘罗斯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1.潘罗斯关于企业的定义
潘罗斯这本书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是:在企业的本性中,是否存在着什么内在的力量既促进企业的增长而又必然限制着企业增长的速率?注意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均衡论的颠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企业的增长不过是给定产品产量的增加,企业的最优规模是其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上的最低点;对企业规模的限制是对企业生产给定产品数量的限制问题,其结果由用来代表企业的产品成本和收益曲线的相互关系来决定;因此企业的增长和规模是由产品需求和供给的市场均衡力量来决定的。如果承认企业自身有能力改变其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结构(如收益递增),那么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石的均衡论就被动摇了。
潘罗斯从企业的定义出发来提出她的主要命题。在她看来,工业企业的基本经济职能是“为了向国民经济提供产品和服务,依照在企业内部形成和执行的计划来利用生产性资源。”(15页)她进一步区分了企业内部经济活动和市场上的经济活动:二者之间的实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在一个行政组织内部进行的而后者不是(同上)。因此,潘罗斯把企业定义为“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并限定边界的资源集合。”
从这个定义出发,潘罗斯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企业的内部资源上。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之处是潘罗斯对生产性资源和生产性服务的区分。根据潘罗斯的论点,资源本身从来不可能是生产过程的“投入品”,投入品只可能是资源所带来的服务。由资源所产生的服务是其被使用方式的函数——同样的资源,当被用于不同目的或不同方式,并与不同类型或数量的其它资源相组合,会产生出不同的服务。因此,资源和服务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组成一组潜在服务的资源可以在不涉及其使用的条件下被定义,而服务却不能在这个条件下被定义。‘服务’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功能,一个活动。”(25页)(注:这段论述可以这样来理解:物质和人力资源是普遍存在的(即它们“可以在不涉及其使用的条件下被定义”),它们只有在被特定的企业所使用时才能成为企业的内部资源;而企业使用资源需要企业本身的活动(即服务),同时这种活动(即服务)也离不开使用资源而独立存在。所以潘罗斯所指的“企业内部资源”事实上主要是“生产性服务”,虽然生产性服务的产生离不开对生产性资源的使用。)
潘罗斯对资源和服务的概念区分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服务只能产生于对资源的使用过程,所以每个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生产性服务就必然是独特的(unique),即企业特定的(firm specific )或其他企业难以模仿的。如她自己所说,“现存的管理人员提供从企业之外新雇用来的人员所不能提供的服务,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构成了除了他们自己的行动所无法扩张的行政管理组织,而且也是因为他们从在企业内部一起工作中获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对他们与之相连的特定群体的工作提供有独特价值的服务。”(46页)
注意,虽然潘罗斯没有在书中使用能力的概念,但她的服务概念主要是指企业管理活动的服务,所以“服务”与“能力”的概念有相通之处。事实上,潘罗斯的服务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目前被广泛使用的能力概念的早期表述下面我们会看到,潘罗斯认为企业使用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源所产生的服务是企业成长的原动力,所以企业的成长并非由市场的均衡力量所决定,而是由每个企业自身的独特力量(即由使用资源所产生的服务或能力)所推动,而无论所有企业是否面临着同样的市场条件。
2.企业增长的内在动力
企业增长的动力源泉
当资源被结合在企业行政管理的框架之下,对生产性资源的使用就会产生生产性服务,而生产性服务发挥作用的过程则推动知识的增加——这个逻辑是理解潘罗斯企业动态增长理论的关键。
潘罗斯认为,企业的生产活动受制于企业家可以发现和利用的“生产性机会”(the productive opportunity),所以企业增长理论实质上是对变化中的企业生产性机会的考察(31—32页)。生产性机会可分为主观的和客观的。客观的生产性机会受到企业能够做到什么的限制,而主观的生产机会却是一个企业认为它能够做到什么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因素决定着企业家关于企业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想法,什么因素决定着“主观的”生产性机会的性质和限度。因此,企业增长理论的目的在于确定是什么重要因素在扩展企业的生产性机会并推动这种机会随着企业运营的时间变化而系统地变化。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潘罗斯把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看作是关键变量:“……一个企业的‘预期’(expectations),即它诠释所处环境的方式,既是企业家个人素质也是企业内部运营和资源的函数。”(41页)
论述企业的增长,首先要分析增长的限度。潘罗斯否认新古典经济理论认定的对企业规模的三个限制因素-即管理能力,产品或要素市场以及不确定性和风险。她认为真正限制着企业扩张的因素来自企业内部:“……企业现存管理人员的力量(capacities)必然在任何给定的期限内限制企业的扩张。”(45-46页)因为如前所述,这样的管理服务是无法从市场上雇到的。但是,由管理力量所决定的企业扩张的限度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一个可以随着管理力量的扩展而不断退却的限度( the receding limit)。
这就是说,既然企业的增长主要受制于管理力量,那么管理力量的增长也必然会推动企业的增长。在企业有计划的增长过程中,也可通过逐步吸收新的管理人员来增加管理服务。更重要的是,企业不仅生产产品,而且生产知识。管理服务的实践可以产生新的知识,而知识的增加又会导致管理力量的增长,从而推动企业的增长。
潘罗斯是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上第一个强调企业内部知识创造是企业增长源泉的经济学家。她把知识分为两类:客观的和经验的。客观的知识独立于个人或团体之外,可以通过书籍、蓝图和语言向任何人传播。经验却无法通过这些途径来传播:“它引起个人的变化—经常是微妙的变化,而且无法与个人分开。”(53页)同时,企业是一个超过个人简单集合的实体:“它是一个有一起工作之经验的个人的集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团队合作’。”(46页)因此,管理经验会产生内在于企业的知识。企业运营的经验所获得的知识增加会创造出许多生产性服务,如果企业不增长,新增的服务就不会得到利用。所以这些服务提供了扩张的内部诱因。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中,企业的知识在给定时间内不发生变化,所以管理服务的供给是固定的。因此,只要经济体系的参数(如产品需求、要素价格、作为公共产品的技术等等)不发生变化,个别企业的生产机会就是固定的。如前所述,这种对企业行为的静态设定是均衡分析所必须的。经济人是否具有完全理性并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因为新古典经济理论设定的个人理性是天生的,而不是通过经验发展出来的。潘罗斯关于经验积累——知识增加——服务增长的动态框架则否定了静态均衡分析规定的企业被动性:“一旦承认运营和扩张过程本身与知识增长过程密切相连,那么立刻就会清楚,一个企业的生产机会甚至在外部条件或基本技术知识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时都将发生变化。”(56页)所以潘罗斯的企业是一个学习企业(a learning firm), 动态企业的概念可以由此而生。
潘罗斯关于经验知识的见解产生出对企业计划活动的不同诠释:“全面的计划要求许多个人的合作,而这要求相互了解。”(47页)对潘罗斯来说,合作需要时间并影响生产性服务的型式(pattern)。 因此,计划的功能并不仅仅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对市场协调资源的替代(科斯的论点)。不仅如此,从特定企业的经验所产生的知识还会是独特的:从团队合作中获得的经验“不仅使个人的集合能够成为一个工作单位,而且发展出关于行动可能性和团队自身即企业行动方式的不断增长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增加不仅引起企业与外部环境变化无关的生产机会的变化,而且对每一个企业生产机会的‘独特性’(uniqueness)发生作用。”(53页)有效的管理服务来自团队合作的经验,而知识的经验性则决定生产机会的独特性。这是后来被概念化的所谓独特或难以模仿的企业能力的最初的理论表述。
企业增长的诱因和压力
外部环境对企业的扩张既有诱因(如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和新技术的出现等等)又有障碍(如获取技术知识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困难等等)。潘罗斯则着重从企业内部分析企业扩张的诱因和障碍。
根据潘罗斯的分析,企业有获取剩余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倾向。第一,由于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资源会被批量地购进,所以一些服务会“成捆地”(inbundles)获得, 哪怕企业当时只需要某一种单一的服务。因此,企业内部总会存在着未被利用的资源。剩余资源的存在是效率的损失,所以只要任何资源没有在当前的运营中被充分利用,企业就存在着利益动机,来找到能更充分利用它们的途径。
第二,生产性服务会在使用资源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知识来。而知识的增加总会“使用服务的可能性随知识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关于资源的物理特性,关于使用资源的方法,或关于有利地使用产品等方面的知识增加,更多的服务就会出现,以前未用的服务会被利用起来,而已用的服务又会成为未被利用的。于是,在企业人员所拥有的知识类型和从企业物质资源上可获取的服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76页)
正是因为这种生产性服务和知识创造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新的管理服务在企业的增长过程中会不断被创造出来。增长意味着管理资源被用于发展新的管理系统。但是,每当一个管理系统被建立起来,而管理程序成为惯例,闲置的管理资源就会出现。除非企业愿意忍受管理资源的闲置,管理者就必须找到使用这种资源的新领域。所以,企业管理者受到内部的压力来寻求增长和创新的新途径。总而言之,“对有进取精神的企业来说,未被利用的生产性服务同时是对创新的挑战,对扩张的激励和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它们促进了在企业内部引入资源的新组合,即创新。”(85页)
规模经济效益和扩张经济效益
短期内, 现有的或者可被吸收于现存组织中的管理服务限制着企业的增长速率。但潘罗斯并没有给企业的最终规模设定一个限度。用她自己的话说:“企业这种改变自己行政管理结构的能力,可以使企业里的许多人在不损害企业的实质性团结的前提下作出真正判断性的、非惯例的管理决定,这使我们很难有信心去说存在着某一点,企业达到它时会太大太复杂,以致无法有效地被管理。”(18页)因此,潘罗斯认为富于进取精神的企业具有不断的扩张激励,也不存在着对这些企业绝对规模的限制。这个论点与新古典经济理论关于企业只有一个“最优”规模的见解泾渭分明。
但是说企业的规模很难存在着限制并不是说较大的企业会比较小的企业更有效率,因为在潘罗斯的分析中,效率来自动态的扩张经济效益(economies of expansion)或增长经济效益(economies of growth),而不是来自静态的规模经济效益(economies of size)。 无疑,较大的企业享有较大的扩张经济效益:“大企业的巨大威望建立在它探索、试验和创新的能力上;正是这种能力,结合它的市场地位……给予它许多扩张经济效益。”(262 页)但扩张经济效益并不自动转换成规模经济效益:“增长经济效益是个别企业可以使用的内部经济效益,它使企业在特定方向上的扩张有利可图。它们是从企业所拥有的生产性服务的独特集合中衍生出来的,并为该企业创造出在向市场提供新产品或更多老产品方面对其它企业的区别优势。在任何时候,这种经济效益的出现都是未用的生产性服务在企业内被不断创造出来的……那个过程的结果。它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规模经济效益。”(99页)换句话说,“增长经济效益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这些效益依赖于特定企业的生产性资源的特定集合,而且对这些资源所提供机会的利用也可以和企业的规模没什么相关。”(100页)因此,“增长经济效益存在于所有规模的企业,所以从企业的观点和整体经济的观点两方面来看,任何规模企业的增长都可以是对资源有效率的使用。”(262页)
另一方面,当扩张完成后,较大的企业并不必然具有规模经济,它们所新建的分部或工厂经常可以在不损失效率的情况下被分立出去(注:例如,建立起一支高素质工艺工程师队伍的企业将能以较低的成本来建立新的工艺流程;但当生产被惯例化了以后,这支工程师队伍的成本优势就消失了,不如将其分立。)。如此这般,“我们于是有了一个有意思的悖论:企业的增长与社会资源的最有效使用相一致;而过去的增长结果——在任何时候所达到的规模——却没有与此相应的好处。每一个增长的相继台阶对企业都有利可图,而且,如果利用不足的资源得到使用,对社会都有好处。然而,任何扩张一旦完成,扩张的原始理由就随着新的增长机会的出现和被发掘而变得没有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道理说大企业从整体上比它的各个部分独立地运营和增长更有效率。”(103页)
很清楚,潘罗斯把增长过程定义为对不断产生出来的未利用资源的利用,而对未利用资源的发现则主要是知识的增加所推动的。从这种观点出发,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有效使用资源,而停滞则导致低效率,不管已经达到的经济规模有多大。这个结论无论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还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都是一样的。
3.经济变化,竞争和企业的增长
企业扩张的战略方向
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把企业的生产要素设定为同质的(homogeneous)不同(没有这个假设,自由价格体系导致市场均衡的分析就难以成立),潘罗斯认为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企业家服务(entrepreneurials ervices)。“多数资源可以提供出许多不同服务的事实对一个企业的生产机会具有重要意义。是从企业的资源中可以得到的生产性服务的异质性,而不是同质性,赋予每个企业以独具的特征。不仅一个企业的人员可以提供一系列不同质的独特服务,而且企业的物质资源可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意味着这些资源能提供不同种类的服务。”(75页)用当代管理学文献中的语言来表达这段话的含义就是:企业的内部资源对企业的战略具有重要的影响。但个别企业的扩张战略是否具有共同的基点呢?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企业扩张的方向问题。
企业扩张的方向必须从企业“继承的”(inherited)资源, 即以前获取的资源,及其为日常生产和扩张而从市场上新获取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事实上,“企业任何计划的起点由企业的资源及其提供的服务所限定。”(86页)这是因为管理者和企业家的思想,经验和知识与企业所运作的各种不同资源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每一个企业只关心有限范围的产品,并将其注意力集中于从整体市场中选取的特定产品-市场。有关产品-市场的选择必然决定于企业‘继承的’资源,即企业已有的生产性服务。”(82页)
这种历史继承关系必然影响到企业竞争和扩张的战略:“在某些专门制造领域高度的胜任(competence)和以技术知识为基础进行多样化和扩张是(美国)许多最大企业的特色。这种类型的胜任与市场位置结合在一起是一个企业所能发展的最强大和最持久的阵地。”(119 页)很显然,这种阵地构成企业的核心资源和在竞争环境中继续增长的基本武器:“长期内,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生存和增长并不那么取决于能组织生产大范围多样化的产品,而更取决于有能力建立一个或更多的宽阔而相对坚不可摧的‘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企业能够在一个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和竞争性的世界里调整并扩展它的业务。重要的考虑并不是生产规模,也不是企业的大小,相反,而是企业能为自己所建立的基本阵地的性质。”(137页)
就通过兼并的扩张而言,理论逻辑也是一样的。由于可使用的生产性服务限制着企业扩张的速度,所以“没有任何企业可以在任何给定期限内兼并每个在其视野中的可能的企业;它必须选择,而且因为错误可能代价高昂又无法弥补,它会选择那些看来最有可能补充或填补其现行活动的企业,部分是因为它的管理层的偏好和经验,部分是因为这些企业好像会盈利更高。”(129页)因此, “一个企业现有的资源不仅限定通过兼并的成功扩张的范围,而且还会影响外部扩张的方向。无怪乎对合并和多样化的调查表明只有少数企业进入完全不相关的领域;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合并企业之间也存在着比马上能看出的更多的联系。”(129-130页)
在这里可以预先提请读者注意,潘罗斯关于企业扩张战略必须以其最具竞争优势的资源和服务为基础的思想,为后来被其他学者发展了的企业核心能力的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
大企业和小企业在增长的经济中的位置
保持“坚不可摧的基地”或“纵深防御”的必要意味着大企业会被迫进行专业化经营。专业化的结果会在市场上留下“空隙”,由此所带来的机会会向小企业开放。“……由于资源有限,一个在无数活动领域内对其它企业具有优势的企业将会发现,它最有利可图的扩张是在它最有优势的领域内。空隙必然会被创造出来,因为每个企业包括较大企业的扩张速率都有限度;空隙的性质取决于这种活动的种类,在那里较大企业发现最有利可图的机会并专业化于其中,使得其它机会保持开放。”(223页)
当扩张的机会比大企业可以抓住的增加得更快,可以被小企业填补的空隙就出现了,而其中有些小企业自己将最终变成大企业。
通过为中型企业创造出增长机会,空隙限制着工业集中的程度。潘罗斯总结道:“……在稳定增长的经济中……集中的过程将会结束并最终自我逆转。”(258页)
竞争:上帝和魔鬼共舞
在潘罗斯写书的50年代,竞争是指(美国)大企业之间的竞争。竞争所经常采取的形式是新的产品、工艺和组织形式,而不是价格。在这个背景下,潘罗斯加入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斯的行列论证说,一个由小企业组成的经济创新能力弱。原因在于只有大企业才能控制市场,而控制市场对创新者回收成本是必要的。没有对市场的控制,免费就餐者可以不付成本地模仿并出售创新。用潘罗斯的话说:“……对产出、市场和价格的控制必须握在承担了为不断提高产量和不断改进产品所必须的‘发展成本’的企业的手中。”(233 页)小企业的问题在于它们不控制市场却反而被市场所控制。同时,如果竞争限制新的竞争者的进入,未被填补的空隙将成为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因为如前所述,大企业不可能追求所有的增长机会。
与熊彼特认为工业组织将被更少但更大企业所主宰的预言不同,潘罗斯的分析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对她来说,相对于小企业的大企业的构成不是由生物或技术性决定的。这是因为“竞争同时是上帝和魔鬼。”(265页)基本的矛盾在于:“竞争是大企业之间斗争的实质,它引发并几乎是强迫大企业从事广泛的研究和创新,并证明整个体制合理;同时,大企业期待对它们努力的奖赏,但它们能有这种期待恰恰是因为竞争可以被限制。”(264 页)问题不在于大企业对经济是好还是坏。这种判断取决于企业的处境和行动;问题在于因为大企业必须要求控制价格以取得收益来资助产品创新,而恰恰是这种权力本身可以被用来树立市场进入的壁垒,从而阻碍为刺激创新所必需的竞争。这还意味着管制政策或工业政策不能建立在最优企业规模的简单法则基础之上。
以上就是对潘罗斯企业增长理论核心内容的简介。通过论证生产性服务是在行政协调下使用生产性资源的经验函数,潘罗斯在继承熊彼特传统的基础上,把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强调市场均衡力量所抹杀的管理功能重新引入经济分析,作为塑造公司远大目标、组织和文化、预见各种变化、制定竞争战略和发现未来机会的解释性变量。这正是为什么潘罗斯的企业增长理论被看作是当代企业战略管理学一个理论根源的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潘罗斯把知识的增加定义为基于内部资源的企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世界经济日益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今天,潘罗斯的学习企业的概念为理解新的经济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潘罗斯这本书的思想非常丰富。本文读者将会发现,几乎所有当代动态企业能力理论的核心概念,如基于资源的战略、组织惯例、企业独特的能力、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等等,都可以在潘罗斯的书中找到直接或间接的表述。这本书至今仍是并将继续是许多学者寻求灵感的源泉。
标签: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过程能力论文; 个人管理论文; 产品概念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展能力论文; 企业内部环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