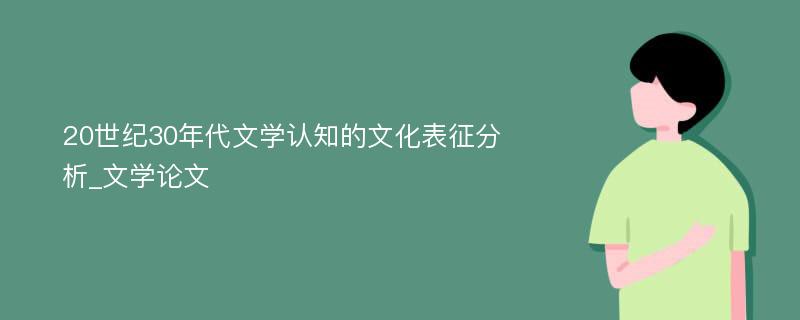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文学认识的文化症候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症候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3)04-199-04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接二连三的失败让文化上的“体”、“用”之争变得毫无意义,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成为中国富国强兵别无选择的选择。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国人的科学意识仍然十分淡薄,其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就是概念使用混乱、学科意识欠缺。概念认识与学科意识恰恰是体现科学精神的两个文化硬指标,对这两个文化指标加以理论症候解析,找出该时期文学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薄弱的原因,不仅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当前文学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的历史渊源,也能给当下文学理论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一个学科的成熟与否,取决于该学科的核心定义是否明确,因为学科定义决定着学科的界线、范围。文学理论的学科发展取决于人们对“文学理论”的定义,“文学理论”的定义取决于人们对“文学”的定义,因为从逻辑层次上说,“文学”是“文学理论”的上位概念,如果上位概念定义不清,人们在定义下位概念时必定陷入混乱。20世纪30年代时,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缺乏基本的逻辑意识,对“文学”和“文艺”两个概念不加区分,把它们放在同一段文字中混合使用或交替使用,并不觉其不妥。就是对单一概念“文学”或“文艺”的认识也不统一:对“文学”存在着两种认识,对“文艺”存在着三种理解。
对文学的第一种认识侧重语言、艺术与审美等内部因素。钱歌川所著《文艺概论》以“媒介”为文学的本质,张崇玖著《文学通论》视“思想”、“情感”、“审美”等因素为文学的本质,孙俍工著《文学概论》与陈穆如著《文学理论》认为“思想”、“情感”的“艺术化”才是文学的本质,周作人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美妙的形式”为文学的本质,曹百川著《文学概论》认为“美感”是文学的本质因素,沈天葆所著《文学概论》则以“内容”上的“情感”、“形式”上的“音韵”为文学的本质。对文学的第二种认识侧重社会性、政治性等外在因素。这类认识以王森然著《文学新论》、顾凤城著《新兴文学概论》、陈彝荪著《文艺方法论》为代表,这类著作认定文学的本质“是一种意识形态”,以表现时代精神、暴露社会黑暗、唤起民众的阶级意识为文学的最高理想,以社会认识作为文学研究的头等目标。
对“文艺”的第一种理解是把“文艺”理解为“文学”与“艺术”的合称。1930年《文艺研究》第1期的“例言”称:“‘文艺研究’又甚愿文与艺相勾连,因此徽志,所以在此亦试加插图,并且在可能范围内,多载塑绘及雕刻之作”。把“文艺”视为“文学”与“艺术”合称的认识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已出现。傅东华所著《文艺批评ABC》中说:“‘文艺’两字,分开来讲,就是文学和艺术;合起来讲,就是文学的艺术,或涵有艺术性的文学。照普通的用例,这两个字是合起来讲的。本书所谓文艺,也是合起来讲的。”①把“文学”和“艺术”“合起来讲”的典型例子就是钱歌川所著的《文艺概论》,该书共分四章:“艺术概论、文学概论、美术概论、音乐概论”,仅从书名及这四章的题目,也能看出钱氏所说的“文艺”就是“文学”和“艺术”的统称。
对“文艺”的第二种理解是把“文艺”看成是“总称文学美术的名词。……用作艺术全体的意义”②。蔡元培对人们以“文艺”做“艺术全体”统称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文学是综合视听两觉的,他的积字成句,积句成篇,是视觉的范围。他的语调,节奏,协韵是听觉的范围。文学可以离其他艺术而独立,而其他艺术,常有赖于文学的助力”,由此断定“文学有统制其他艺术的能力”,并据此“推文学作一般艺术的总代表”。③郭沫若为文学“统辖其他艺术”的思想提供了认识例证,他在讨论“国防文学”问题时说:“我觉得‘国防文学’不妨扩张为‘国防文艺’,把一切造形艺术,音乐、演剧、电影等都包括在里面。凡是不甘心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文艺家,都在这个旗帜之下一致的团结起来。”④“把一切造形艺术,音乐、演剧、电影等”都包括在“文艺”概念里面的提议,正是以文学统制其他艺术的思想实践;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兼收并蓄了艺术界各路英雄,则是以文学统制其他艺术的体制实践。19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组织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从学术理念上来说,仍然是“以文学统制其他艺术”的文学观念在起作用。以文学统辖全体艺术的理由虽然说起来十分动听,从逻辑上来看却是一个错误:“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不管其功能多么特殊,都无法和艺术构成并列关系,其理犹如不能因为孔子伟大谈起人类便称“孔子人”一样。
对“文艺”的第三种理解是把“文艺”理解为“文字艺术”的简称,这种意义上的“文艺”就是当时人们所称的“纯文学”、“美文学”、“狭义的文学”。早在二十年代末,夏丏尊就有了“文艺是什么?文艺与文学,有何区别?”的疑问,他认为“文学与文艺,原可作同一的东西解释”,为了强调“文学”与“史书论文”不同,“和雕刻音乐绘画”一样是“艺术的一种”,“所以不称文学而称文艺”。⑤夏炎德接受了夏丏尊的认识,他在《文艺通论》中界定“文艺”概念时几乎照搬夏丏尊的说法,也以“文艺”指称“纯文学,即艺术的文学”,并强调“所谓文艺,是艺术的一种”,因而不同于“哲学、科学”。⑥
两位夏姓学者试图通过概念之间的细微差异在传统的杂文学观念和现代纯文学观念之间拉开距离,体现了现代学者少有的科学精神及学科意识。把“文艺”界定为艺术化的表现文字,既突出了文字艺术的媒介和类型特征,又消除了人们在杂文学概念或广义文学概念认识上的混乱与歧见。从逻辑上说,“文艺”这一名称比“文学”更能体现文字艺术的特征,因为“文艺”一词的中心语素是“艺”,“艺”字具有的心理暗示作用会引导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往“艺术”的方向联想;而“文学”一词的中心语素是“学”,“学”字具有的心理暗示作用会引导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往“学问”、“学术”方面联想。退一步说,即使采用“纯文学”、“美文学”这样的称谓,其效果也并不比“文艺”的说法好,因为“纯”、“美”虽然具有定义上的限制和区分作用,但三个字的称谓无论如何都比两个字的称谓显得啰嗦、累赘。再者说,“纯文学”、“美文学”之类的概念再怎么强调也都脱不了一个“学”字。就此而言,以“文艺”指称文字艺术,比以“文学”指称文字艺术更富有合理性。
人们对上位概念“文学”、“文艺”认识上的参差,导致下位概念“文学理论”、“文艺理论”使用上的不统一,笔者对之曾作过两组概念使用情况的随机抽检:
郁达夫在1931年第3、4期《读书月刊》合刊中的《学文学的人》一文中使用了“文学理论”一词,胡秋原在1932年第2期《现代》杂志中的《浪费的论争》一文中使用了“文学理论”一词,周起应在1933年第1期《现代》杂志中的《文学的真实性》一文中使用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这样的词汇,李长之在1933年第1期《清华周刊》中的《红楼梦批判》一文中混合使用“文学”、“纯文艺”、“文学理论”等术语,沈从文在1934年第9期《国闻周报》中的《禁书问题》及1934年5月3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栏的《〈凤子〉题记》中均使用了“文学理论”这样的词汇,庚(鲁迅)在1935年第4期《文学》月刊的《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使用了“文学理论”一词,胡风在1936年第2期《中流》杂志的《自然主义倾向的一理解》一文中使用了“文学理论”一词,沈从文在1936年第3期《大众知识》杂志的《文学界联合战线所有的意义》一文中使用了“文学理论”一词。
鲁迅在1930年第4期《萌芽月刊》中的《我们要批评家》一文中使用了“文艺理论”一词,易嘉(瞿秋白)在1932年第6期《现代》中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宋阳(瞿秋白)在1932年第3期《文学月报》中的《论弗里契》中均使用了“文艺理论”一词,洛扬(冯雪峰)在1933年第3期《现代》杂志的《并非浪费的论争》一文中使用“文艺理论”一词,萧乾在1935年3月10日《大公报》谈书评的文章中也用到“文艺理论”这个词,1937年4月10日《文艺科学》创刊号署名“编委会”的文章使用“文艺理论”一词,老舍在1938年第7期《抗战文艺》中的《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一文中使用“文艺理论”一词,周扬在1939年《时论丛刊》第1辑中的《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一文中使用“文艺理论”一词。
读者从这两组统计中可以发现,该时期人们对“文学理论”、“文艺理论”的使用同样很是随意。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左翼文艺理论家对“文艺理论”这一术语使用的频率远远高于“文学理论”。左联成立后,左联机关刊物《秘书处消息》和《文学导报》各期所发的“秘书处通告”中,凡涉及理论之时,均以“文艺理论”名之。在左联理论骨干中,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用的几乎全是“文艺理论”这一术语,这原因自然是前面提到的以文学“统制其他艺术”的实用思想的影响。
批评领域文学核心概念不清,教育体制内文学的学科归属及概念使用情形又是如何呢?就体制层面说,一个学科的成熟与否,首行要看该学科在教育体制内的建制归属。从学科建制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对“文学”学科的范围也不甚了了,各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范围往往很广;除纯文学外,更涉及哲学,史学,考古学等”⑦。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建制设置有下列系目:“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系、历史系、社会人类学系”⑧,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文学”的学科定位与理解还不甚了了。学科建制规划的混乱表明,“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还处于探索阶段。
一个学科的成熟与否,还要看专业人员对该学科核心概念的使用情况。专业人员的职业使命就是制造知识,对每个名词、术语、概念考镜源流、细加推敲。文学理论专业人员主要是大学教师和研究机构的职员,他们的工作就是对文学理论学科的专业名词、概念、命题进行专业探讨或系统梳理,然后形成专著或教材之类的东西。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理论专著与教材虽然有很多,但在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并不统一,对概念的理解也不一致;这一问题的基本表现就是文学原理类书籍在概念理解上不一致,在学科范围认定上有差异。
概念理解不一与学科范围认识差异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对“文学理论”学科尚未有明确的意识定位。学科命名不同于个体认识分歧,后者要求主体之间彼此彰显各自创造的独立性,个体之间的差异越大,越能彼此激发理论上的创新与发展。学科发展要体现知识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任何一个学科领域,其基本概念的命名都需要统一和明晰,而不是“多元”和“差异”,因为多元和差异只能导致人们在基本问题理解与认识上的困惑、混乱。“文学理论”课程名称与教材名称的不确定,表明作为一个基本的知识学科,文学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还未形成自身完备的知识体系和知识架构。“文学理论”命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正体现了其时文艺家们背负的社会问题以及知识、文化结构存在的先天缺陷。
对“文学”、“文艺”、“文学理论”、“文艺理论”这几个名、义相近的概念的区分并非无聊的文字游戏,因为理论的意义取决于理论术语的描述,术语不准、概念不明,对意义的理解必致歧途。现代语言哲学正是借助于逻辑和概念分析,才完成其对意义世界的探索。后期分析哲学家以及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意义分析方法颇为值得文学研究者借鉴,这种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从词义方面对哲学的词汇或概念进行分析,从相关词汇或概念的细微区别中,发现哲学意义混乱的原因,并加以意义澄清或排除。
同一术语同名不同实,或同一概念被不同使用者赋予不同的内涵,这类认识混乱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精神弊端,诸如“文学”学科无法明确定位,人们在问题讨论时自说自话、谁也说服不了谁。从逻辑上来说,如果讨论者使用的术语在概念上不同一,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产生明晰的辩论结果。当时的中国文艺界并不缺乏硕学鸿儒,也不乏具有清醒学科意识的有识之士,理论认识混乱的原因又在哪里?若细察之,就会发现其间原因多多。
文学认识混乱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文学主体理论思维存在的问题。概念不清表明人们还没有摆脱传统的模糊思维习惯,还没有养成区分性、精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这暴露出中国学者先天禀有的思维缺陷这一文化症候。作为主体性结构中的无意识结构成分,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制约着主体知识建构的方向。模糊思维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集体无意识,在20世纪30年代依然支配着文学认识主体,这种情形产生了两个理论后果:一是文学批评中“话说人”而不是“人说话”,二是在文学研究中,主体对科学意识这一现代文化“结构的作用的听不出来、阅读不出来”⑨。个别学者在文艺名称非科学性问题上虽有洞见,却于问题的解决毫无办法。
文学认识的混乱也折射出中国传统实用理性在20世纪30年代的强大影响。实用理性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为了某种功利目的,可以删改诗书,可以焚书坑儒。“五四”文化先驱虽然试图通过“输入学理”的方式给这一传统进行精神换血,但由于西学底子不够厚实,他们对“赛先生”的宣传既不彻底,也未能深入人心,以致知识界一直有人对科学抱有怀疑和敌视态度,怀疑和敌视的证据便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科玄论战”。“科玄论战”虽然以玄学派的失败而告终,却也从反面证明了非科学乃至反科学的思想在知识界还有相当大的势力。科学派只是取得了论战上的胜利——科学意识与科学精神并未在学术研究中得到实际应用和贯彻,文学研究中的概念认识混乱足以说明这一点。
以文学统辖其他艺术的认识是实用理性在20世纪30年代文艺领域继续延续生长的明证。该时期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以及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不断,这种复杂的社会局势使非科学的实用理性精神再次找到延续的社会土壤;各种政治势力和集团都极力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扩大自己的影响。在诸意识形态宣传工具中,感染性和鼓动性最强的莫过于文字艺术,因为文字艺术融艺术与思想为一体,文字类的标语、口号、诗歌、快板、报告、速写能够直接进入人心,且较少受媒介限制,宣传者既可直接用自己的嘴进行宣传演讲,也可以把宣传内容刻画在墙体上、树干上、道路旁,当然也可以通过印刷媒介以及无线电传播。因此,文学在那个时代被人们称为宣传领域里的轻骑兵。其他种类的艺术,如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因受媒介限制,不但宣传范围大大缩小,而且在宣传方面的信息含量也赶不上文字作品。由是之故,文学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坐上了第一把金交椅,在政治宣传的社会目标下,各种艺术团体和组织在联合进行精神作战时,自然要统一在文艺的大旗之下。
文学认识混乱也暴露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学科意识的匮乏及学科建设的不足。中国学术本来就缺乏科学主义传统,缺乏科学研究的精密意识和分析精神,在这种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斗争的双重影响下,文学批评家及专业研究人员头脑中不可能产生思想认识必须保持思维同一、严密的逻辑意识。没有同一、严密的逻辑意识,也就不可能对每个具体的概念进行学院式追根究底的推敲辨析;没有同一、严密的逻辑意识,其研究成果不可能严密、精确;研究成果不严密、精确,其相关认识也就不具有科学性;不具有科学性的认识自然无法得到知识共同体的集体确认,得不到知识共同体确认的认识无法成其为知识;没有确定性的知识支撑,学科构建也就无从谈起;没有明确学科形态的对象无法在教育体制内得到认可和重视。由于这种原因,该时期大学的“文学概论”课无人愿意讲授,各国立大学文学院虽都设置有文学理论课,终因找不到授课之人复又悄悄把该课程取消。直到1939年的新《文科大学现行科目修正案》把“文学概论”列为文学系第一必修课,这种情形才得以改变。
20世纪30年代文学认识不清的精神后遗症十分严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内地学界,人文学科的从业者对“文学”、“文艺”、“文学理论”、“文艺理论”等概念糊里糊涂。传播文学基本知识的“概论”、“教程”、“原理”类的教科书,其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名前冠以“文学”,有的名前冠以“文艺”,有的冠以“文艺学”。在以“文学”或“文学理论”冠名的期刊、辑刊、论文集中,常常收有美术、音乐、雕刻、电影类研究文章。直到现在,这种模糊认识仍未改变。还以期刊而论,在学界颇有影响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其中一辑名为《文艺理论》,该刊只复印文字艺术方面的研究文章,并不转载文字艺术以外的其他艺术门类的论文,其“文艺”二字显系“文学艺术”的简称。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专业名刊《文艺研究》所刊文章既有文字艺术方面的,也有美术、音乐、舞蹈等方面的,且以后者为主。该刊“文艺”秉承的理念显系20世纪30年代“以文学统制其他艺术”的思想。这种概念不清的情况给文学知识的讲授和传播带来了麻烦,给文学知识的接受者带来了不必要的记忆负担,给文学研究者造成了理解和认识的混乱,也给中国文学界与国际文学界进行学术接轨带来了障碍。
①傅东华:《文艺批评ABC》,ABC丛书社1928年版,第1页。
②孙俍工:《文艺辞典》,民智书局1928年版,第55页。
③蔡元培:《文学和一般艺术的关系怎样?》,《文学百题》,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3页。
④郭沫若:《国防·污池·炼狱》,《文学界》1936年第1卷第2号。
⑤夏丏尊:《文艺论ABC》,ABC丛书社1929年版,第1-2页。1930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夏丏尊所著《文艺论ABC》实为ABC丛书社1929年所出同名书的再版。
⑥夏炎德:《文艺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18-19页。
⑦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概况》,《清华周刊》1931年第35卷第11、12期合刊。
⑧见“国立清华大学规章”第二章第三条“文学院”“分属之各学系”,《清华周刊》1931年第35卷第11、12期合刊。
⑨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