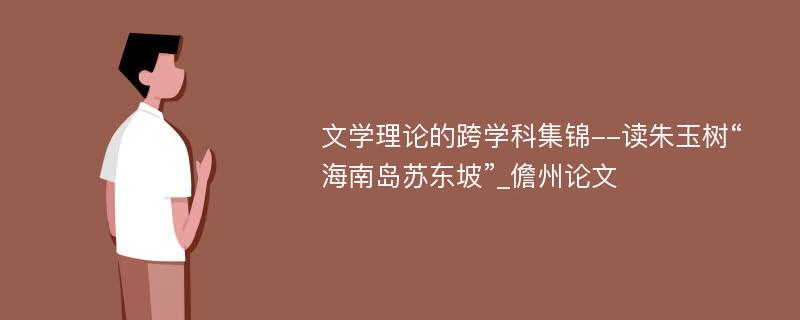
跨学科的文论集——朱玉书《苏东坡在海南岛》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南岛论文,文论论文,苏东坡论文,读后论文,朱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东坡离儋北归常州行至江苏镇江金山寺时,曾作《自题金山画像》诗,给自己的一生作出了如下总结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东坡在官场和贬地尤其在海南儋州,可说是历尽坎坷艰辛,已经被折磨得心灰意懒,但他也度过了颇富意义的即将结束的人生历程,创造出他值得自慰的“与渔樵杂处”、“超然自得的”“功业”。
对于东坡晚年遭贬海南儋州的这段历史和“功业”,过去学者的研究较为薄弱,近读了朱玉书于1993年结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东坡在海南岛》,我们感到这是当前学界第一部较为完整地论述东坡遭贬海南的研究专著—一它独辟蹊径地对东坡进行了跨学科的探讨,系统、形象地介绍了东坡在儋州的种种“功业”;其文笔质朴轻松、平淡自然、夹叙夹议、循循善诱,欣喜之馀,作此文以推荐之。
一、史观价值和史料价值
众所周知,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要研究东坡居儋的生活史,首先要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通过东坡居儋的生活史,又能了解到当时儋州的历史面貌。朱玉书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时势造英雄”观为指导,重视从具体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出发来研究东坡在儋州的活动。
衡量东坡在儋州的“功业”,并不是他挂有“琼州别驾”的虚衔,而是他被贬为民的诗人角色。东坡自己也说:“老拙百念灰寂,独一觞一咏,亦不能忘”(《与朱行中书》)。朱玉书在其“文集”中,以鲜明的唯物史观,对东坡晚年的思想作出了符合历史真实的评判,他一方面指出了文史学家所曾认为的:“这主要是苏轼精神上始终立着佛老思想这根柱子的缘故。”但他一面更着重指出东坡思想的另一主导面:“苏轼晚年的创作成就及其他非凡业绩的取得,跟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密切相关。”而且“由于几十年投闲置放,报国无门,到了晚年,他的爱国情怀就愈加深厚。因此,“他晚年谪居海南民族地区,身体力行,仍然比较注意,从各民族的利益出发,做民族团结的促进派。(《晚景情怀》)这样评价是作者唯物求实精神的体现。
研究历史无证不信、孤证不立,必须坚持文字记载与实物证明相结合。对于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有关的建筑物、纪念物和碑坊及其附载文字、历史资料,哪怕是三言两语,也都是其真实片断或侧面纪录。朱玉书在“文集”中,调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尤其是方志资料、文物考古资料、历史遗存物,紧密结合东坡作品,对东坡贬儋的时间、行程、生活、人物交往、风物气候,作了系统的考证和阐述,补充了以前东坡居儋生活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有些资料是诸种东坡年谱所从未记载过的,可谓填补了空白,为我们今天认识东坡先生,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导读物。“南贬行踪”、“遇赦北归”、“南荒交游”、“遗迹考录”、“琼岛珍物西蜀藏”、“谈谈《东坡笠履图》”、“东坡居琼家事录”、“天涯鸿爪”等篇章,为我们勾勒了东坡在儋州的行踪和生活风貌的清晰画图。读来亲切真实,质朴自然,宛如令人亲眼目睹了一般。
二、民俗学价值和旅游学价值
“民俗”即民族风情,它包括民间文学、民间习俗、民间信仰、民间组织等。中国的传统民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那些具有特色的民俗,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传统,形成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而民俗学(Folklore)就是研究特定社会区域、特定民族风情的一门学科,包括物质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和精神文化诸方面的内容。朱玉书的“文集”虽然不是民俗专论,但其中许多篇章都具有民俗学的价值。他“以东坡居琼的有关诗文为线索,对古代海南的民族民间习俗作点小考。”他指出了东坡的诗文,“真实而生动地涉猎了当时海南岛的民间民族风俗习惯(包括衣食、服饰、娱乐、信仰、礼仪、节庆、禀性等),触及了他的前代文人未曾触及过的题材领域,不但在文学上是一份珍贵的遗产,而且对了解和研究古代海南的社会状况、生产方式和民族文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进而认为:“掌握它,利用它,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去粗取精,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入乡写俗》)朱玉书还引用了王国宪的《重修儋州志叙》中的话来印证东坡随乡入俗而改俗之“功业”:东坡“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使整个儋耳地区‘书声琅琅,弦歌四起’。”如果说,东坡作了海南民俗的发现和采录的文字工作的话,那末朱玉书则作了东坡诗文礼俗内容的保存和传播的注释工作。在其“文集”中,他大量再现了东坡与海南民俗的原始面貌。这对弘扬东坡文化这一宝贵的精神遗产不仅是有益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玉书探讨东坡贬居海南民俗活动的这些篇章,还“是我们今天了解以往的社会历史,特别是人民自己的历史的最忠实、最丰饶的文件。”(《民间文学》发刊词,1955年)。
再者,“旅游”对于人的生活,是一种“增益生活的准备”(李大钊语)。古代的许多大家如司马迁、李白、苏东坡、徐霞客等人,他们之所以文彩翩翩,风流后世,就是他们善于在游途中塑造自我而成为社会和自然主人的形象的。苏东坡一生尤其在晚年因贬谪海南,生活在民间,放浪山水,才成了一位名符其实的“旅游家”。东坡在离儋北归渡海时高唱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东坡把自己遭贬儋州,看成是一次“冠平生”的“奇绝旅游,不仅表现了他对险恶处境的戏谑,也实在是他坎坷一生的重大旅游。海南原是荒蛮之地,山水朴野,只因东坡涉海登览,写诗作文,而使之声名大震。朱玉书在其“文集”中,以翔实的资料,将东坡笔下的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寻根追底地复画了出来,使得儋州“山以贤称,境缘人胜”(王元恽《游东山记》)。其中“笔端风物”、“遗迹考寻”、“名人、名食与海南旅游”等篇章,名义上是再现东坡笔下的山川风物、民情风貌的本貌,实际上是以东坡为楔子,为儋州的“文化旅游”、“经济旅游”、“民俗旅游”作宣传。因此,朱玉书便进一步提出了研制与东坡相关的旅游产品的历史文化依据,不失为一家之见。他还指出:“强化旅游商品的竞争意识,开发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增加名胜风景区的吸引力,当是海南发展旅游业的重要一环。”真可谓旅游学教科书的一种新见,也富有启迪意义。
三、文艺学价值和自然科学价值
东坡不仅是一位贬官、而更重要的是他以平民诗人和歌手的角色出现在海南黎族百姓中间,所以他在儋州的“功业”才熠熠闪光。文艺批评是“被艺术所创造,而不是本身创造艺术的科学。它不能对艺术发生影响,而只能对公众的鉴赏力发生影响。”朱玉书深知对东坡的文艺进行批评乃是做一种“不断运动着的美学(别林斯基语)的工作,这对大众的鉴赏力无疑会发生影响。东坡在海南的文艺成就是很多的,可以说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民间歌谣,样样新奇,但最出色的是他的“和陶诗”、“咏物诗”、“生活诗”。朱玉书分别从审美心理、文体功能、艺术技巧、语言风格以及文化内容诸方面打开了新的研究视角。在“诗歌风格”、“民歌知音”等篇章中,处处满怀热情,体现了文艺家评论象火星一样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巨火。他认为“诗人在美学上追求的是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诗歌风格》)这种对东坡晚年的“平淡”诗风所进行的较为实际的分析、探讨和评价,于当前学术界的争鸣是有参考价值的。他还借用子由和许觊的话说,东坡在海南,“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东坡海南诗,超然迈伦,能追李、杜、陶、谢。”便更加突出地说明了东坡居儋作品的独特的文艺学价值。
马克思曾站在文艺生态学的角度说过:精神的太阳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不能强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同一芳香。东坡在儋州,由于过着旷达、闲适、自然的游鉴交友生活,大量记叙和美化了大自然的种种生灵,使得他的咏物诗、生活诗竟成为物化文艺生态学的范本。朱玉书在其“文集”中,将东坡诗文中出现的有关山川气候、自然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的内容,作了真实、生动的介绍,宛如一部小辞典,为地理学家、地质学家、物候学家,生物学家以至旅游学家研究海南自然生态提供了可贵的文献资料。这种将文学与自然科学联姻的研究,实属一项开拓性的举动,值得提倡。
总之,“文集”是一部具有多学科价值的著作。由于朱玉书长期生活在海南儋县,工作在文化战线的基层,与海南群众朝夕相处,对那里的风俗、民情、服饰、语言、歌谣、山川、气候、动植物都较熟悉,他才能如此准确、真实、具体地解释、考证、论定了东坡诗文的诸多创作和典实,纠正了他人的许多误解和附会,画出了东坡在海南生活、创作的一个清晰轮廓,考订了东坡的一些佚诗佚文,这对我们苏学研究工作者,特别对海南人民深入了解、体味东坡的作品,弘扬东坡文化遗产,开发和建设新海南,提供了可贵的咨询和借鉴。再者,整个“文集”,反映出朱玉书对东坡是那样的一往情深,崇拜敬仰之心可谓弥诚,恐怕这也是他能写出这部著作的动力之一吧。
最后,我们期望朱玉书对东坡在海南岛的活动作更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探讨,以再上一层楼。
